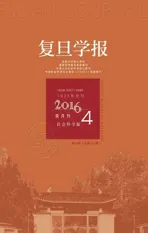是东夷,也是南越
——读《魏志·倭人传》
2016-12-17戴燕
戴 燕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是东夷,也是南越
——读《魏志·倭人传》
戴燕
(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33)
【摘要】在《魏志·倭人传》的研究中,向来最有争议的,一是它的史料来源,二是它所描写邪马台国的位置。针对这两个问题,本文首先论证东夷校尉及护东夷校尉的设置,才是包括《倭人传》在内的《魏志·东夷传》写作的制度性基础。同时,通过与《史记》、《汉书》、鱼豢《魏略》的比较,指出《三国志》之所以弃“四夷”而仅仅写有《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这一篇“夷传”,也是由陈寿过去蜀人的立场及其视野决定的。其次是说明三国鼎立,魏、蜀、吴都有意在海上拓展自己的势力。由此,东夷包括倭的存在,他们的地理种族、自然环境及资源、社会结构、宗教习俗,他们与中国的往来,才引起格外关注,进入中国历史的大叙述,而这也导致陈寿在《魏志》中写邪马台等倭诸国时,并不是只采取魏这一个视角,同时也采取了吴甚至于蜀的视角。所以,一方面他是以带方郡为起点,记载下从景初三年到正始八年的魏与邪马台女王国在政治上的往来,从这一角度,将倭归于东夷;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强调倭在文化上,还是与会稽、东冶即旧时吴越相近,生态和习俗更等同于儋耳、朱崖,而从这一角度看,倭就变成了南越。
【关键词】《魏志·倭人传》东夷校尉带方郡会稽东冶
(一)
《三国志·魏志·倭人传》是3世纪陈寿所写,可是在日本,大约从8世纪舍人亲王等编纂《日本书纪》开始,*虽然有人怀疑《日本书纪·神功皇后传》注引《魏志·倭人传》是后人所添加,但是内藤湖南就认为《日本书纪》的作者不仅读过陈寿的《三国志》或者鱼豢的《魏略》,也认定其中的卑弥呼就是日本史上的神功皇后。见内藤湖南:《卑弥呼考》之三“本文の记事に关にする我邦最旧の见解”,原载《艺文》第一年第三号,1910年,转引自《内藤湖南全集》第七卷,东京:筑摩书房,1970年,第255~256页。又可参见坂本太郎、家永三郎、井山光贞、大野晋校注:《日本书纪上·解说》之“中国の史书”,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7,东京:岩波书店,1967年,第17~22页。对它的征引和研究就不计其数。1910年内藤湖南发表《卑弥呼考》、*内藤湖南:《卑弥呼考》,引自《内藤湖南全集》第七卷,第251页。白鸟库吉:《倭女王卑弥呼考》,原载《东亚之光》第五卷第六、七号(1910年6-7月),收入《白鸟库吉全集》第一卷《邪马台国问题》,东京:岩波书店,1969年,第84页。白鸟库吉发表《倭女王卑弥呼》,这两篇划时代的论文对它们以前日本历史上的相关论述都有所勾稽。1970年代以后,则有三品彰英编著的《邪马台国研究总览》,除了对《魏志·倭人传》加以注释,还为《日本书纪》等相关文献210篇做了提要,*三品彰英编著:《邪马台国研究总览》,大阪:创元社,1970年。后来又有佐伯有清编的《邪马台基本论文集》三卷,汇集1910~1970年代的有关重要论文91篇,*佐伯有清编:《邪马台国基本论文集》三卷,大阪:创元社,1981~82年。这些都能使人了解到日本从来研究《倭人传》的脉络,得窥冰山之一角。
日本学界之所以关心《魏志·倭人传》,当然是由于它写到了古代日本,为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日本记载。在过去的研究中,由此也可以看到这样两个路向,一个就是利用它来构建早期的日本史,往往归于日本国史,还有一个是借以考察2、3世纪的中日及东亚关系,纳入东洋史的范畴。这两方面的成果,对于《倭人传》的解读都贡献极大。靠着长期、耐心的研究,日本学界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推动了《倭人传》的研究:其一是将《倭人传》记载的倭诸国,通过文字对音和地理考察的方法,一一还原到现实的日本,并在这一过程中订正了若干版本之误,如对马,原有一宋本作“对海”,一支,多本作“一大”,邪马台,宋本以下作“写马壹”等。其二是通过与《日本书纪》、《古事记》和《三国史记》等日本、朝鲜文献的对照,厘清了《倭人传》记述的倭诸国史事,如卑弥呼的身份、邪马台之所在、与女王国对立的狗奴国情况,等等。其三是利用“倭奴国王”金印及此后不断出现的考古资料,如古坟、铜铎、铁刀、铜镜等,印证并丰富了《倭人传》的记载,又在与中国、朝鲜半岛所发现文物的比较中,重新认识了这一东亚世界在3世纪前后交流往来的状况。
中国学界对《魏志·倭人传》的关注远远不及日本,不过值得一提的,仍有如较早出版的丁谦的《三国志东夷传地理考证》。*丁谦:《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附鱼豢魏略西戎传地理考证》,收入《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一辑,浙江图书馆校刊,1915年,第17页。较为全面的论述,则有如汪向荣的《邪马台国》、沈仁安的《日本起源考》,而这两位学者在日本史研究上的成绩,固然与他们熟悉中国历史中有关日本的文献有关,同他们对日本学界的深入了解也不无关系。*汪向荣:《邪马台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汪向荣又有日文本的《中国の研究者のみた邪马台国》,崛浏宜男译,东京:同成社,2007年。沈仁安:《日本起源考》,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年;沈仁安还有日文本的《倭国と东アジア》,东京:六兴出版社,1990年、《中国からみた日本の古代》,藤田友治、藤田美代子译,京都:ミネルウア书房,2003年。在日本还有华人学者如谢铭仁出版的《邪马台中国人はこう読む》,东京:立风书房,1983年第一刷、1985年第二刷。此外也为日本学界重视的,又有王仲殊的《关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问题》等系列论文,*王仲殊:《关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问题》,原载《考古》1981年第4期,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王仲殊文集》第二卷《中日两国古代铜镜及都城形制的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他的相关系列论文,也都见于该《王仲殊文集》第二卷并第三卷《古代中国与日本等东亚诸国的关系》。又,参见王仲殊:《日本の三角缘神兽镜について》,收入王仲殊、西嶋定生等:《三角缘神兽镜の谜:日中合同古代史シンポジウム》,东京:角川书店1985年,第19~39页;王仲殊:《中国からみた古代日本》,东京:学生社,1992年;王仲殊、樋口隆一、西谷正:《三角缘神兽镜と邪马台国》,福冈:梓书院,1997年。涉及《倭人传》以及在日本大量出土的铜镜,而随着考古资料层出不穷,这方面的讨论还将持续。
在上述《魏志·倭人传》的研究中,长期以来最大的争论,在日本,首先就是邪马台国究竟在大和(近畿)还是九州的问题。据白鸟库吉说,争论之所以不得解决,就是因为《倭人传》记载的从带方郡到女王之都邪马台这一路的里程、方位、日期,有很大的伸缩性,要靠它来确定女王国的位置,几乎不可能。如果相信它说的倭在会稽、东冶之东,邪马台应该是在台湾附近。*白鸟库吉:《倭女王卑弥呼》、《邪马台国について》,原载《考古学杂志》第十二卷第十一号,1922年,转引自《白鸟库吉全集》第一卷,第4、13、72页。与这一争论密切相关的,其次是《倭人传》的史料来源。由于在陈寿以前,《汉书·地理志》只有“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寥寥十几个字的记载,到《三国志》变成近二千字的《倭人传》,对倭的关心和认识,在这一个多世纪里何以如此增加,也成了一个谜。内藤湖南、白鸟库吉以来的日本学者大多强调陈寿是取材于鱼豢的《魏略》,*内藤湖南:《卑弥呼考》;白鸟库吉:《卑弥呼问题の解决》,石田干之助记录,原载《オリエンタリカ》第一、二号,1948年、1949年,《白鸟库吉全集》第一卷,第84页。也有人说还应包括《汉书》、《东观汉记》、王沉的《魏书》。*参见何远景:《〈魏志·倭人传〉前四段出自〈东观汉记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以下的讨论主要围绕这两个问题。
(二)
按照解决问题的顺序,先来看《魏志·倭人传》的史料来源。接着前人的论述,这里主要也就陈寿和鱼豢的关系加以说明,看陈寿是否对鱼豢亦步亦趋?他们之间是不是也有差异,为什么会有差异?
陈寿是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出生在后主初期即蜀建国的第十三年(233),大约31岁时经历了蜀为魏所灭,48岁时又目睹了吴亡、晋武帝实现天下大一统。他在蜀国做过东观秘书郎、黄门侍郎,36岁后从成都到洛阳,在西晋王朝举孝廉,为平阳侯相、佐著作郎、著作郎。在著作局期间,有条件接触到三国档案以及相关记载,得以写下《三国志》,直到元康七年(297)去世。*《晋书》卷八二《陈寿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
据他在《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评曰”中说:“《史》、《汉》著朝鲜、两越,《东京》撰录西羌。魏世匈奴遂衰,更有乌丸、鲜卑,爰及东夷,使译时通。记述随事,岂常也哉!”*陈寿《三国志》卷三十《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陈乃乾校点本,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限于篇幅,以下引《乌丸鲜卑东夷传》文字,均不再注明。可知《三国志》的撰写,体例上受到《史记》、《汉书》、《东观汉记》的影响。而由于汉武帝的“情存远略,志辟四方,南诛百越,北讨强胡,西伐大宛,东并朝鲜”,*《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传》载汉灵帝时议郎蔡邕之议,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年。从司马迁开始,在《史记》里就辟有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大宛列传,班固的《汉书》也有匈奴、西域、西南夷两越朝鲜传,以后史书中设有“四夷传”、“外国传”,基本成为常态。陈寿之所以写作《乌丸鲜卑东夷传》,也正是遵循这一模式。
过去学者论及《魏志·倭人传》的史料来源,多是从文献采集、承传的角度考虑,这里要补充的一点是恰如陈寿在《魏志·东夷传序》中所说:“及汉氏遣张骞使西域,穷河源,经历诸国,遂置都护以总领之,然后西域之事具存,故史官得详载焉。”西域都护的设置,是史家掌握西域情报的必要条件,东夷传的写作,也要等到汉魏间有“东夷校尉”出现。东夷校尉本来是针对鲜卑而设,三国时,魏将东夷校尉设在襄平(今辽阳),统领辽东、昌黎、玄莵、带方、乐浪五郡,司马懿灭公孙渊后,改称护东夷校尉。*晋司马彪撰、梁刘昭注补《后汉书·百官五》注引《晋书》称“汉置东夷校尉,以抚鲜卑”。又据《晋书》卷十四《地理志上》,幽州下旧有平州,“汉属右北平郡。后汉末,公孙度自号平州牧。及其子康、康子文懿并擅据辽东,东夷九种皆服事焉。魏置东夷校尉,居襄平,而分辽东、昌黎、玄莵、带方、乐浪五郡为平州,后还合为幽州。及文懿灭后,有护东夷校尉,居襄平”。参见金毓黼:《东北通史》上编,长春:社会科学杂志社,1978年翻印,第121~123页;张溥泉:《东北地方史稿》,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25页。这样,在过去主管边疆事务的匈奴中郎将、乌桓校尉、护羌校尉等之外,*《后汉书·百官五》。就有了专门负责东夷的官员和机构。这当然表明汉魏以来对东夷的重视,汉魏政府与东夷各族各国间的区域交流更加密切,彼此的了解逐渐增加。也正是在这一形势下,陈寿才能够像鱼豢一样,在《史记》、《汉书》之“朝鲜传”的基础上,从乐浪、带方所属之地一直写到倭诸国。
但陈寿又和鱼豢不同。鱼豢是京兆(今西安)人,做过魏郎中,*《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史部·杂史》著录《典论》八九卷,谓“魏郎中鱼豢撰”,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年。《史通》卷一二《古今正史篇》谓:“魏时京兆鱼豢私撰《魏略》,止乎明帝。”他的五十卷《魏略》大约在宋以后亡佚,清代张鹏一编有《魏略辑本》二十五卷,后来在日本发现的张楚金撰《翰苑》也保存有十来条,*张鹏一《魏略辑本序》称“倭人事,《魏志》最详,然《魏略》今有佚文,详《魏志》所略”。见张鹏一《魏略辑本》,太仓李澍农校字,陕西文献征辑处,1924年。又,张楚金撰,雍公叡注:《翰苑》,竹内理三校订、解说,福冈:太宰府天满宫文化研究所印行,1977年。其中都有《倭人传》的佚文。*《魏略辑本》卷二一有从《三国志》裴注、《通典》、《法苑珠林》、段公路《北户录》辑出的四条,《翰苑》所存《藩夷》部也有“倭国”条。不过从现存的《魏略辑本》可知,鱼豢除了写到乌丸及倭、扶余、东沃沮、高句丽、濊、三韩等东夷,还写有南蛮、西戎,表明他是按照《史记》、《汉书》的办法,兼顾“四夷”。然而,在陈寿的《三国志》里,却只有《魏志》中的“乌丸鲜卑东夷”这一篇“夷传”,与陈寿自己提到的《史》、《汉》、《东京》相比,缺少匈奴、西域、两越、西南夷、西羌等传,与鱼豢的《魏略》相比,也缺少南蛮、西戎传。这自然是有意为之,是陈寿所说“记述随事”,这里要讨论的就是他何以要做这样的减法,他对历史即“事”的判断,还有他书写(剪裁)历史即“记述随事”的原则,到底是怎样确立的?
陈寿并没有交待他为什么不写南蛮和西戎,可是不妨先来看一看《魏略》的南蛮、西戎传,以便了解陈寿为何弃之不取。《魏略·南蛮传》仅存南蛮用獭为冠、高辛氏有盘瓠和汉令哀牢民家出盐一斛为赋等三条佚文,*据《魏略辑本》卷二一《南蛮》,这三条佚文,分别出自《太平御览》卷912、卷785及卷979、《北堂书钞》卷146。后两条,张鹏一已说明又见于《后汉书》的《南蛮西南夷传》。这三条佚文,恰好都见于范晔的《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及其唐代李贤等注。据《后汉书》说,盘瓠是传说中长沙武陵蛮的祖先,正是武陵蛮“冠用獭皮”,*《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传》。沈约《宋书》卷九八《蛮夷传》仍说“荆、雍州蛮,槃瓠之后也”,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7年。而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置哀牢县(今云南盈江县东),归于永昌郡,永昌太守“与哀牢夷人约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夷俗安之”。*《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从《后汉书》的这些记载可知,鱼豢所谓南蛮,其实是三国时蜀、吴的边地,或为诸葛亮征讨的南中,或为孙吴控制的荆交,在《三国志》里,称之为“南越”,*《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称诸葛亮“外连东吴,内平南越”,而卷四九《吴志·士燮传》“评日”也称士燮为交跤太守是“作守南越”,卷五七《吴志·陆债传》又称陆续为郁林太守是“作守南越”。而鱼豢还是延续了汉代大一统时的习惯,仍视其为魏的南蛮。
可是,到了陈寿撰写《三国志》时的西晋,三国合而为一,蜀、吴的存在虽有其历史的合法性,在历史书写中却是失去了与魏同等的正统地位,魏帝可以称皇帝,入本纪,蜀帝、吴帝只能称主、称王,入传。蜀、吴既然都不再被当作政治中心,不能代表华夏正统,《蜀志》、《吴志》中也就不会出现“四夷”传,只剩下《魏志》有写“夷传”的资格。这大概便是《三国志》里,唯独《魏志》有一篇《乌丸鲜卑东夷传》的原因。而另一方面,由于魏与蜀、吴亦非“华夷”关系,魏更不曾越过蜀吴,与南蛮发生联系,因此陈寿也不肯像鱼豢那样,替魏写一个观念中的南蛮,这或许又是他不愿在《魏志》中写南蛮传的原因。
至于西戎,鱼豢所写《西戎传》涉及西域的地理、族群、宗教、语言、物产等许多知识,也包括中国与西域诸国往来的历史,据说颇可见出《汉书·西域传》以来的汉魏时人对中亚的认识增加。*据钮仲勋说,《魏略·西戎传》的有些记载与《汉书·西域传》大致相同,但它说“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所述三道情形都较《汉书·西域传》详细而有新的认识。见钮仲勋:《我国古代对中亚的地理考察和认识》,北京:测绘出版社,1990年,第17页。可是即便如此,鱼豢联想到“俗以为营廷之鱼不知江海之大,浮游之物不知四时之气”,依然有“飞思乎八荒”而不能穷尽的感慨。*《魏志·倭人传》裴注引《魏略西戎传》“鱼豢议曰”。可知他这个魏的京兆人,虽然生活在三国分裂时期,却依然保持着汉代人“情存远略,志辟四方”的精神。就在他生活的魏晋之交,蜀刚刚被灭,据说司马昭便派人“撰访吴、蜀地图”,为“大晋龙兴,混一六合”做准备,裴秀因此还绘制了《禹贡地域图》十八篇。*《晋书》卷三五《裴秀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年。鱼豢对世界的想象,因此是与司马昭、裴秀一致的。后来《晋书》的作者,在讲到晋武帝代魏吞吴后,过分“矜来远之名”,频繁招待“凡四夷入贡者,有二十三国”,不久却“天邑倾沦,朝化所覃,江外而已”,对他迁就“胡人”而“蘧沦家国”,很有微辞。*《晋书》卷九七《四夷传》序、史臣曰。这是唐人的后见之明,却反映出西晋初年的风气,是以“混一六合”的大一统为思想、知识界的主流,鱼豢正是在这个潮流之中。
和鱼豢不同的是,中年后才从成都来到洛阳的陈寿,似乎并没有完全进入这个潮流,就像他在《乌丸鲜卑传序》中说:“孝武虽外事四夷,东平两越、朝鲜,西讨贰师、大宛,开邛苲、夜郎之道,然皆在荒服之外,不能为中国轻重。”对于汉武帝的“外事四夷”而不分缓急,他就并不是那么理解和认同。当然与此同时,他也就没有鱼豢那样的紧张,不担心自己变成心胸狭隘的“营廷之鱼”、“浮游之物”。
所以,陈寿说他写乌丸鲜卑传,“但举汉末魏初以来,以备四夷之变”。“以备四夷之变”,本是《史记》以来的传统,如司马迁说“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作《匈奴列传》”,*《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甚至陈寿在《乌丸鲜卑传序》中所写“《书》载‘蛮夷猾夏’、《诗》称‘猃狁孔炽’”云云,与班固的“于惟帝典,戎夷猾夏,周宣攘之,亦列风雅……述《匈奴传》”,*《汉书》卷一百下《叙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如出一辙。但是,陈寿到底还是打了一个折扣,他写来“备四夷之变”的,其实只有乌丸鲜卑这一东胡。他解释这是由于只有乌丸鲜卑才如汉代“最逼于诸夏”的匈奴,令“北边仍受其困”,其余都“不能为中国轻重”,言下之意,只要记录下最有利害关系而值得戒备的。以同样的理由,他说东夷也比西戎更应该关注,因为龟兹、于阗等西域各国,对魏“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都可视若平常,不像在平定辽东、征讨高句丽以后,魏便“东临大海”,与东夷的交通豁然打开,“使驿时通”,记录下这一过程,有“接前史之所未备”的价值。
这就是陈寿所谓“记述随事”的“事”,是他对魏以及魏与其周边民族、国家关系的认识,也是他认为具有现实意义而值得记录的历史。他的这一看法,当然首先是基于魏设有东夷校尉、护东夷校尉的事实。其次,也是由于他看到东夷尤其高句丽,一度为魏、吴、公孙氏的三方争夺之地,连带高句丽以南的三韩、三韩连接的倭诸国都受到影响。所以,他说司马懿灭公孙渊,“而后海表谧然,东夷屈服”,毌丘俭讨高句丽,“遂周观诸国,采其法俗,小大区别,各有名号,可得详记”,他对魏在东夷的势力及其所引起区域性的变化,格外敏感。鱼豢也有这种敏感,也写下《东夷传》,或许还是在陈寿之前为东夷立传,但是陈寿只写了一个《东夷传》,更把包括倭在内的东夷的重要性推到了极端。这就是他说“记述随事,岂常也哉”,他要循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是亦步亦趋地追随前人。
那么接下来,倒是可以看一看他对于时代变化的把握,是不是很有道理。不妨以几年后陈留(今河南开封附近)人江统写作的《徙戎论》再来作一番比较。由于从元康四年(294)起,匈奴郝散就攻上党、杀长吏,马兰羌、卢水胡等也相继造反,到元康六年(296)也就是陈寿死前一年,氐帅齐万年被拥立为帝。这些“夷蛮戎狄”带来的动荡,使得江统对汉末三国以来因各种机缘迁入内地的“四夷”,产生了高度警惕。不管是过去由曹操迁入秦川以抵制蜀的氐人,还是关中的诸羌、并州的南匈奴,又或是毌丘俭从辽东塞外迁到荥阳的高句丽,在他看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都必须小心提防,应该赶紧把这些“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的异族,统统送到边塞之外,使他们“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为寇暴,所害不广”。*《晋书》卷五六《江统传》。当然,事实是不幸被他言中,“五胡之乱”来得之快,也许更超出当时许多人的预想。而《徙戎论》的警告仅仅发出在陈寿死后第三年,如果是拿江统的敏感和担忧来作对照,则可见陈寿以为他写乌丸鲜卑传,便能“备四夷之变”,与现实是有多么大的距离!而他以为撰次东夷各国,足以证明“中国失礼,求之四夷”,又是多么的不急之务!
不过,也正是因为陈寿基于他个人的视野和关心,判定东夷这一区域极为重要,才使东夷受到真正的关注,从此列入正史“四夷传”之目,又因为他独具慧眼,才使“倭人”在中国历史中正式登场。“倭人传”的出现,就是这样从《三国志》开始的。
(三)
但是,陈寿讲述的日本,据白鸟库吉以来的很多日本学者考证,在方位、里程、海陆之行所需时间等方面,都偏离实际。按照他的描写,倭不仅比现在的日本位置更靠南,也比现在日本的南北更长。*室贺信夫:《魏志倭人传に描かれた日本の地理像—地図学史的考察》,原载《神道学》10,1956年8月,转引自佐伯有清编:《邪马台国基本论文集II》,大阪:创元社,1981年,第363~364页。过去,白鸟库吉曾分析这是倭人为了防备魏在征服高句丽之后进一步讨伐倭,故意夸大倭国的数量、面积和人口,还故意把自己说得更往南,暗示可以同吴联合。他也同意一些日本学者的看法,以为《魏志·倭人传》是由若干种史料拼合而成。*白鸟库吉:《卑弥呼问题の解决》,《白鸟库吉全集》第一卷,第117、121、140页。但汪向荣虽然同意说陈寿是利用了不止一种材料,他本人只是在文字上作了“最低限度的修润、连缀工作,以使能合成一篇”,却强调“这个史书是以中国为本位的”,在日本人看来是错误的记载,也是出于中国人的水平和观点,跟日本人怎么想,不是一回事。*汪向荣:《邪马台国》,第19~22页。一个是按日本的习惯揣摩,一个是凭中国的经验推断,好像南辕北辙,不过都接受了同一个前提,就是《魏志·倭人传》对倭的方位的描述很使人迷惑,看起来是取材于不同地方。
这里要说明的是,三国时代魏、蜀、吴的竞争,尤其是吴对东南沿海的开发,导致这三国都有意向东部及东南沿海拓展,扩大自己在海上的势力,由此东夷以至于倭的存在,他们的地理种族、自然环境及资源,他们的社会结构、宗教习俗,还有他们与中国的往来,才引起更多关注,进入中国历史的大叙述,这无疑是“东夷传”在魏晋时期出现的一个重要背景。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带来陈寿在写作《倭人传》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个视角,至少有一个魏的视角,还有一个吴的视角。*王仲殊就认为三国时倭与江南的吴有民间往来,他认为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就是吴的工匠东渡日本后,在日本制作。见王仲殊:《从日本出土的铜镜看三世纪倭与江南的交往》,《王仲殊文集》第三卷,第116页。不过最近在洛阳据说发现了三角缘神兽镜,对王仲殊的说法提出挑战,参见张懋鎔、王趁意、张迪《关于在中日调查三角缘神兽镜的基本思路与方法——三论洛阳发现的三角缘神兽镜》(《文博》2009年第5期)等。
当陈寿写到“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中”时,这是魏的视角。是从朝鲜半岛上的带方郡(郡治有说在今首尔),由狗邪韩国(今韩国金海)渡朝鲜海峡,到对马(つしま)岛,南渡瀚海到一支(いき,壹岐),再渡海到末卢(まつら,松浦),登陆而向东南到伊都(いと,丝岛),又向东南到奴(な)国,向东到不弥(ふみ),向南到投马(とうま),更向南,到女王之都邪马台,女王国的南面还有狗奴国。这是从魏出发的路线,是魏与倭的使者行走的路线,《魏志·倭人传》记载景初三年(239)到正始八年(248)的几次往来,都是走的这一条路线。
在这一条路之外,陈寿又说“计其道里,当在会稽、东冶之东”,这就是吴的视角。会稽、东冶,都是三国吴地,《三国志·吴志》说孙策已曾“据会稽,屠东冶”。*《三国志》卷四六《吴志·孙策传》。会稽郡是秦合吴、越所设置,起初辖有长江以南至福建北部十三县,治所在吴;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分其钱塘江北为吴郡、钱塘江南为会稽郡,会稽领山阴、章安等十余县,移治山阴;建安十三年(208),在会稽郡之今浙皖一带,另设新都郡;三国时的吴太平二年(256),于其东部再分临海郡;永安三年(260)又于今闽北、过去称东冶的东部侯官,设建安郡;*汉末孙策攻打会稽,原会稽太守王朗浮海逃亡,《三国志》卷三十《魏志·王朗传》记其“至东冶”,《三国志》卷五七《吴志·虞翻传》又写虞翻追赶他至东部侯官,说明东冶、东部侯官指的是一个地方。《史记》卷一四四《东越列传》说“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裴骃《集解》引徐广曰:闽中郡,“今侯官是”,司马贞《索隐》引徐广云“本建安侯官是”,《汉书》卷二七《地理志上》“会稽郡”下二十六县,有冶,颜师古注称“本闽越地”,均可参考。并见《晋书·地理志下》扬州建安郡条:“故秦闽中郡,汉高帝五年以立闽越王。及武帝灭之,徙其人,名为东冶,又更名东城。后汉改为侯官都尉,及吴置建安郡。”宝鼎元年(266)于其西部再分东阳郡,会稽郡就这样从辖有广大的吴越,逐渐缩小到只剩下今绍兴、宁波。*见《三国志》卷四七《吴志·吴主传》、卷四八《三嗣主传》,并见《后汉书》志二二《郡国志四》“会稽郡”条、《宋书》卷三五《州郡一》“扬州刺史”条。又参见陈桥驿:《绍兴史话》二《古今沿革·会稽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25~26页。陈寿所说会稽、东冶,指的就是现在的绍兴、宁波到福州这一带。
秦汉以来,会稽、东冶往往也被当作东南沿海最有标志性的地界,如《史记》说秦始皇三十七年出游,最后一站到会稽,祭大禹,就是在这里“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记秦始皇此次“行出游会稽,并海上,北走琅邪”,也是说从会稽入海北上。《汉书》说“会稽海外有东鳀人,分二十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下》“吴地”条。也是把会稽当作最靠海边的地方,出了会稽就是海外。陈寿在说到孙策“渡江略地”,会稽太守王朗“拒战败绩,亡走浮海。(虞)翻追随营护,到东部侯官”时,*《魏志·王朗传》、《吴志·虞翻传》。也是把会稽、东部侯官(东冶)看成沿海的地标。
作为临海之地,会稽、东冶还担负了东汉三国时的海上运输和贸易集散,如《后汉书》说“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沿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据《后汉书》卷三三《郑弘传》,郑弘出生会稽,东汉章帝建初八年(83)代郑重为大司农,因交趾七郡泛海贡献很危险,“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陈寿也说有亶洲人,常“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吴志·吴主传》。亶洲或说就是日本列岛,王仲殊便据以论定三国时有吴的工匠渡海到日本,也有倭人西渡到会稽进行贸易。*见王仲殊:《关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问题》,《王仲殊文集》卷二,第127~128页;并《从日本出土的铜镜看三世纪倭与江南的交往》,《王仲殊文集》卷三,第116、121页。当时的航海技术是不是已经提供了由会稽到达倭的条件,姑且不论,这些记载却是都证明了就像朝鲜半岛上的带方为三国时魏对东夷的窗口,会稽、东冶也是吴对其东南及南海海域的港口,会稽、东冶与带方一样,是连接海外的很重要的地方。所以,正如说“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是从魏的角度,说倭“当在会稽、东冶之东”便是立足于吴而言。
陈寿又形容倭“男子无大小皆黥面文身”,*《汉书·地理志下》注亦引如淳曰:“如墨委面,在带方东南万里。”臣瓒曰:“倭是国名,不谓用墨,故谓之委也。”他说这就跟“夏后少康之子封于会稽,断发文身以避蛟龙之害”是一样的道理,即“文身亦以厌大鱼水禽”,只是倭人后来又把这些纹饰发展成了社会性的标识,“诸国文身各异,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在《史记》里,司马迁说夏后帝少康之庶子是禹的后代、越王勾践的祖先,他被封会稽时,“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见《史记》卷三一《吴太伯世家》、卷四一《越王勾践世家》。班固写《汉书》,也有吴粤之地“其君禹后,帝少康之子云,封于会稽,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的记载。*《汉书·地理志下》载粤包括有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等。陈寿在《魏志·倭人传》里又一次重复了这个说法,这说明:第一,他也像以中原为中心的那些古代中国人一样,对会稽人亦即旧时吴越人有一种成见,以为这里有和捕鱼业相关的蛮族风气;第二,之所以从倭人的“黥面文身”联想到会稽人身上,是因为他不但觉得倭与会稽、东冶有某种共同的山海之人气质,更重要的是他把倭划在了会稽、东冶,也就是旧时吴越的文化范围。因此,虽然是在《魏志·东夷传》中写倭人,可是他看待倭实际还有另外一重视角。政治上,倭是归在与魏相交往的东夷;文化上,却归于南越,也就是过去的吴越、三国时的会稽和东冶。
说倭在文化上与吴越接近也并不是陈寿个人的主张,鱼豢在《魏略》中就说:“其俗男子皆点而文,闻其旧语,自谓太伯之后。昔夏后少康之子封于会稽,断发文身以避蛟龙之害,今倭人亦文身以厌水害也。”*张楚金撰、雍公叡注:《翰苑·蕃夷部·倭国》,第62页。又见《魏略辑本》卷二一“倭人”条,引《通典·四裔》称“倭人自谓太伯之后”。可见倭人有“黥面文身”的特征,大概是魏晋时人比较普遍的看法,陈寿不过是重复了这一常识。而具有这一特征的,据陈寿在《魏志·东夷传》中说,也不光是倭人,还包括部分韩人,如马韩“男子时时有文身”、辰韩人“皆褊头,男女近倭,亦文身”等。*《三国志》卷三十《魏志·东夷·三韩传》。这说明在他心目中,文身还是一个区域性的文化现象,绝非倭人所独有。由这一点,则可知其所谓“会稽、东冶之东”,应该是指一个涵盖今东海、南海、黄海以至日本海海域的广大范围。
在说到倭“当在会稽、东冶之东”之后,陈寿还提到儋耳、朱崖。他说倭这个地方,“其风俗不淫,男子皆露紒,以木绵招头。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妇人被发屈紒,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种禾稻、苎麻、蚕桑、缉绩,出细苎、缣棉。其地无牛、马、虎、豹、羊、雀。兵用矛、楯、木弓,木弓短下长上,竹箭,或铁簇,或骨簇。所有无与儋耳、朱崖同”。儋耳、朱崖,是汉武帝平南粤后设的两个郡,在今海南岛,当时归于交趾。汉昭帝时儋耳并入朱崖,元帝时罢朱崖,*《汉书》卷六四《贾捐之传》说“元封六年立儋耳、珠崖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广袤可千里”,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记元帝初元三年(前46)罢之,立郡六十五岁。吴赤乌五年(242)恢复朱崖郡,至西晋灭吴,朱崖并入合浦。*《吴志·吴主传》记赤乌五年,“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儋耳”。又,《三国志》卷五三《吴志·薛综传》谓“珠崖之废,起于长吏睹其好发,髡取為髲”。并《晋书》卷十五《地理志下》“交州”条。
虽是汉武帝时立郡,当司马迁写《史记》时,对儋耳、朱崖还知之不多,只是说“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史记·货殖列传》,张守节《正义》谓:“今儋州在海中,广州南,去京七千余里。言岭南至儋耳之地,与江南大同俗,而杨州之南,越民多焉。”但是到班固写《汉书》,讲到“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珠崖郡”时,对当地的自然及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就有了更多的说明,如称“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贯头衣称“著时从头而贯之”。男子耕农,种禾稻、苎麻,女子桑蚕织绩。亡马与虎,民有五畜,山多麈麖。兵则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为镞”,又称入海后船行数月,更可至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黄支国,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再往南,尚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下》,并见《汉书》卷九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有很多人都注意到陈寿在《魏志·倭人传》中对倭的介绍,像穿贯头衣、种禾稻苎麻、蚕桑缉绩、兵用木弓等情节,与班固上述对儋耳、珠崖的形况若合符节,陈寿自己也有一个总结,就是说倭“所有无与儋耳、朱崖同”。可是,儋耳、朱崖更在会稽、东冶之南,他为什么要“截取”《汉书》里的这一段来说明倭与儋耳、朱崖相似?
答案也许就是在《魏志·倭人传》所说“参问倭地,绝在海中洲岛之上,或绝或连,周旋可五千余里”,从倭的使者或是其他知情人那里得知倭是一个很大的岛屿,岛上的情形便可照着同样是海岛的朱崖、儋耳去想象。而这里更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根据《晋书·地理志》的记载,朱崖郡虽是在三国时由吴恢复,归于交州,晋灭吴后,才省朱崖入合浦,可是蜀也曾“以李恢为建宁太守,遥领交州刺史”。晋灭蜀后,照样“以蜀建宁太守霍弋遥领交州,得以便宜选用长吏”。建宁郡是诸葛亮于建兴三年(225)南征后,改益州郡设。*《三国志》卷三三《蜀志·后主传》、《晋书》卷十四《地理志上》“益州”条。蜀以至西晋都以建宁太守遥领交州,便意味着交州也包括朱崖的归属,在三国西晋时是“有争议”的,是吴、蜀、西晋都想要控制的地方。如果说交州既为吴所辖,同时也为蜀和西晋先后拥有,在陈寿的观念中,当他写下倭“所有无与儋耳、朱崖同”时,也许还不免有他蜀人的意识、情感掺杂其中。
从与会稽、东冶乃至于与儋耳、朱崖的相关性来看待倭,将倭放在旧时吴越、三国时南越的范围,倭就从“东夷”变成了“南越”,并非说地处南蛮,而是在生态和文化上属于南越。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魏志·倭人传》里会有看似矛盾的记录,仿佛几种来源不同的材料的缀合。在信息还不足够充分的时候,文化联想、文化分类往往充当着把握陌生事物的门径。陈寿就是在相关档案、报告以及前人记录的基础上发挥文化想象,将倭首先归类在从东海到南海的岛屿的。
可以证明陈寿很清楚倭是跟魏有着政治上的往来,但在文化上他却和鱼豢一样,有意识地把倭划归旧时吴越的,是5世纪的范晔在《后汉书》中也接受了这一双重视角,既说“倭在韩东南大海”,又说“其地大较在会稽、东冶之东,与朱崖、儋耳相近,故其法俗多同”。*《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倭列传》。范晔还接受《汉书》的说法,写到“会稽海外有东鳀人”,又接受《三国志》的说法,写到“又有夷洲及澶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会稽市。会稽、东冶县人有入海行遭风,流移至澶州者。所在绝远,不可往来”,*《三国志·吴志·吴主传》。几乎是将以前有关会稽、夷洲、亶州的记载都连缀在《东夷·倭传》,*王仲殊认为范晔能够根据各种史料,对《魏志·倭人传》作出补充和修改,在倭诸国方位的记载上有独到见解。见王仲殊:《关于〈魏志·倭人传〉、〈后汉书·倭传〉的标点和解释》,《王仲殊文集》第三卷,第112~113页。而在这些来自不同时代的文献中,还是可以明显看到“东夷”和“南越”这两条叙事线索。一直到唐代人撰写《隋书》,仍然采取两重视角,一面说倭“在百济、新罗东南”,一面说它“在会稽之东,与儋耳相近”。据说隋炀帝大业四年(608),裴世清奉命出使倭国,从百济出发,先到都斯麻国,“迥在大海中”,再经过一支、竹斯,东至秦王国,当时见“其人同于华夏”,还“以为夷洲,疑不能明也”。*《隋书》卷八一《东夷·倭国传》。这已经是7世纪,通过朝鲜半岛前往倭国的隋朝使者,依然懵懵懂懂分不清夷洲和倭国。如果怀疑《后汉书》、《隋书》只是被动地接受旧史料、旧观念,那么应该指出这里面也有两个例外:一个是《宋书》,只写到倭“在高句骊东南大海中,世修贡职”;*《宋书》卷九七《夷蛮·倭国传》。还有一个是《梁书》,也是仅仅写有“倭国在带方东南大海中”。*《梁书》卷五八《东南夷·倭国传》。沈约和萧子显似乎更实事求是。
因为文化上是如旧时的吴越,甚至如儋耳、朱崖,陈寿写倭人便与当时的中国有很多不同。当时的中国早已有极为讲究的衣冠制度,不必细说,即使是其他东夷,据陈寿说,就如“以殷正月祭天”的夫余人也已经在家出国衣制不同,“在国衣尚白,白布大袂,袍、袴、履革鞜。出国则尚缯绣锦罽,大人加狐狸、狖白、黑貂之裘,以金银饰帽”。还有与中国关系若即若离的高句丽人,每有正式集会也是“衣服皆锦绣金银以自饰”,大小长官都还戴有帻、弁一样的帽子。更不要说受过箕子之教的濊,“男女衣皆著曲领,男子系银花广数寸以为饰”。与这些东夷人相比,陈寿说倭人衣着俭朴,大概只有韩人“魁头露紒,如炅兵,衣布袍”的样子比较接近,可是韩人尚且“足履革蹻蹋”,倭人由于“倭地温暖”都是“冬夏食生菜,皆徒跣”。
相当有趣的是,陈寿对倭人“男子皆露紒,以木棉招头。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妇人被发屈紒,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皆徒跣”的描述,本来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汉代以来人对儋耳、朱崖的印象中“复制”得来,这个被“复制”的印象竟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构成了人们对倭人的想象。现存《梁元帝职贡图》(北宋摹本)残卷上的倭国使者以布裹头、袒胸赤脚,就是陈寿描写的这个样子,而在倭国使者像旁边的《题记》中所写“在会稽东,气暖地温”、“□面文身,以木绵帖葛衣,横幅无缝”云云,毫无疑问也是来自《魏志·倭人传》。能够与倭国使者这一身装扮相媲美的大概只有狼牙修国(在今马来半岛)使者,而据7世纪姚思廉所编《梁书》说,狼牙修国在南海中,“其俗男女皆袒而被发”。*《梁书》卷五四《诸夷·狼牙修国传》。这说明不管实际往来的情形如何,对倭的文化联想和文化记忆总是相当顽固。所以,在《隋书》中还记载着隋文帝叫人向倭国来使询问当地风俗,报告里也还是提到“人庶多跣足”,只是日本天皇已经开始正衣冠,“其王始制冠,以锦采为之,以金银镂花为饰”。*《隋书·东夷·倭国传》。又据《梁书》卷五四《诸夷·倭传》说,“富贵者以锦绣杂采我帽,似中国胡公头”。
(四)
汉代以来人对倭的印象,是他们顺从、恭敬,能按时朝贡,*《说文解字》:“倭,顺貌,从人,委声。”《汉书·地理志下》:“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与《魏志·东夷·高句丽传》所写“性凶急,喜寇抄”的高句丽最形成对照。陈寿虽然提示了倭在自然环境、风俗习惯上与会稽、东冶和儋耳、朱崖相近,可是如果按照他引述陆逊的说法,即“朱崖绝险,民犹禽兽”,*据《三国志》卷五八《吴志·陆逊传》,孙权“欲遣偏师取夷州及朱崖”,而陆逊上疏言:“将远归夷州,以定大事,臣反复思惟,未见其利,万里袭取,风波难测,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驱见众,经涉不毛,欲益更损,欲利反害。又朱崖绝险,民犹禽兽,得其民不足济事,无其兵不足亏众。”孙权征夷州,得不补失。又按照他引述薛综之论交趾的上疏,即“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民如禽兽,长幼无别,椎结徒跣,贯头左衽,长吏之设,虽有若无”,汉武帝以来“颇徙中国罪人杂居其间,稍使学书,粗知言语,使驿往来,观见礼化”,“然而土广人众,阻险毒害,易以为乱,难使从治”。*《三国志》卷五三《吴志·薛综传》。那么,在《魏志·倭人传》中,他还是突出了倭的秩序井然的一面。
在对马、一支、伊都、奴国、不弥、邪马台等国,都有官和副官,女王国、狗奴国还有王,社会上“宗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国收租赋,有市场,交易由大倭监督。一般人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于是养成“不盗窃,少诤讼”的风气,就连“国大人皆四五妇,下户或二三妇”,妇女们也“不淫,不嫉妒”。在伊都国这个相当于刺史驻扎的地方,还设有监察倭各国的机构,带方、韩国及倭的使者往来,也都在此“临津搜露”,传递文书礼物,均“不得差错”。在这里,“下户与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传辞说事,或蹲或跪,两手据地,为之恭敬,对应声曰‘噫’,比如然诺”,都是各守本分、彬彬有礼。
邪马台女王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由她弟弟辅政,并不露面,却也把邪马台国治理得井井有条,卑弥呼死后还修了很大一座坟墓。尽管为继任人的问题,起过一场纠纷,死了千余人,但是等到卑弥呼十三岁的宗女壹与就任王位,便又恢复平静。卑弥呼最大的敌人是狗奴国的男王卑弥弓呼,不过陈寿只记录有听说双方互相攻击多年,点到为止,并无细节。
陈寿对倭的讲述,特别是他所描述倭诸国有序而宁静的氛围,深深影响到后来人对倭即日本的观感,《隋书》中就还记着倭国“鲜争讼,少盗贼,人颇恬静”。由此,当开皇二十年(600),突厥、高丽、契丹的使者纷纷来朝,倭王阿每(あめ)字多利思比孤(たりしひこ)也派来使者,使者介绍倭王是“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天未明时出听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务,云委我弟”,隋文帝听了以后就很不舒服,他大概从未想到倭人竟有如此“狂放”之言,斥责“此太无义理,训令改之”。*《隋书·东夷·倭国传》。
吴建国的第二年即黄龙二年(230),孙权便派将军“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却因亶洲在海中“绝远”,最后只到了夷洲,得不偿失而还,两位领队的将军因此被处死。夷洲,即今台湾,据三国时吴人沈莹作《临海水土志》说,“夷州在临海东南”,“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此夷舅姑子妇卧息共一大床,略不相避”,“取生鱼肉杂貯大瓦器中,以盐卤之,历月所日,乃啖食之,以为上肴”。*沈瑩:《临海水土志》,《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倭传》李贤等注引。参见《太平御览》卷七八0《东夷一》,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第3455页。亶洲,或以为海南岛,或以为日本列岛*参见李勃:《“亶洲”不是海南岛》,陕西师范大学主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3期;何兹全分册主编:《中古时代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5卷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6~177页。,陈寿说,当时传言它为“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徐福一去便不复返的地方。*《吴志·吴主传》。而所谓徐福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最早见于《史记》的记载,说的是秦始皇派方士徐福入海求神异物,徐福谎称“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童女求之”,秦始皇便差遣他带“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不料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卷一一八《淮南衡山王列传》。到了三国时代而有亶洲便是徐福所到之处的传说,南朝时倭与亶洲又似乎被合二为一,*《后汉书·东夷·倭传》。于是倭才成了蓬莱、方壶仙山之所在。唐代诗人李白写《哭晁卿衡》的诗,说:“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二五《古近体诗·哀伤》,北京:中华书局整理本,1977年。想象日本晁衡即阿倍仲麻吕的归国就是回到蓬莱、方壶仙山。杜甫有一首《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讲他的画家朋友王宰“一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最终绘成一幅《昆仑方壶图》,画面上有“巴陵洞庭日本东,赤岸水与银河通。舟人渔子入浦溆,山木尽亚洪涛风”,也仍然是把日本跟方壶仙山联系在一起。*仇兆熬注:《杜诗详注》卷九,仇注称“此记图中山水,昆仑方壶,山既自西向东,故巴陵、日本,水亦自西向东”。中华书局整理本第二册,1979年,第755页。到了14世纪,日本的《神皇正统纪》记载着当日本孝灵天皇四十五年,秦始皇“既而好仙,就日本求长生不死药,日本又就求三皇五帝书,始皇送之。其后三十五年,始皇焚书坑儒,故孔子全经存于日本尔”,*北畠亲王著,平泉澄解说:《神皇正统纪》,白山本,日本出版配给株式会社,1934年出版、1945年增补三版,第37页。不但显示徐福漂洋过海到日本的传说,在日本得到“落实”,同时日本真正变成了“中国失礼,求之四夷”的宝地。而这些有关日本的观念,最初都是从陈寿《三国志·魏志·东夷·倭人传》中来的。
[责任编辑陈文彬]
[作者简介]戴燕,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Being EasternYiand SouthernMan: ReadingTheRecordsofThreeKingdoms:WeiChronicle’s“Biography of the Wa People”
DAI Yan
(Department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FudanUniversity,Shanghai200433,China)
Abstract:Among the hot debates on The Records of Three Kingdoms: Wei Chronicle’s “Biography of the Wa People”, the two topics have been mostly discussed: the origins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the description of Yamatai’s physical location and geography.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se two issues. It begins with examining the installation of military officers governing the Eastern Yi tribe, including the fundamental system described in the Wei Chronicle’s “Biography of the Eastern Yi ” (the same source of the “Biography of the Wa People”). Chen Shou’s The 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including only one piece of ethnic minority —“Biographies of Wuhuan, Xianbei, and Dongyi” has demonstrated that Chen Shou’s perspective was limited by his standpoint and viewpoints of a Shu -man. Chen’s descriptions of Wa and Yamatai, however, also had underlying perspectives of Wei and Wu: politically Wei had established certain connections with Dong Yi, whereas culturally these peoples stayed much closer to the culture of Wu and Yue, being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cultures of the Southern Man.
Key words:Chen Shou; Wei Chronicle’s “Biography of the Wa (Japanese) People”; military office of the Eastern Yi; Yu Huan’s Wei Summary ; Yamatai; Dai Fang County; Kuai Ji’s Dongyi County; Daner and Zhuya
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