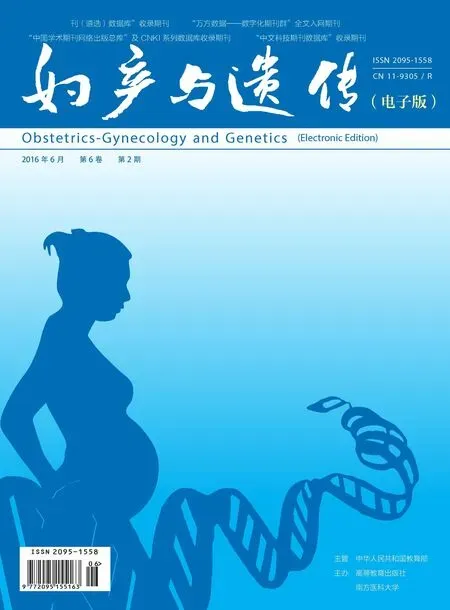子宫腺肌病介入手术技巧探讨
2016-12-16王绍光陈勇华
王绍光 陈勇华
子宫腺肌病(adenomyosis,AM)是因子宫内膜及腺体侵入子宫肌层,以经量增多、经期延长及进行性痛经为主要临床表现的妇科常见病之一,多发生于30~50岁经产妇,发病率为10%~47%,近年来发病率增高及年轻化趋势明显。其治疗方法一般有药物治疗、手术治疗和血管介入治疗。随着介入放射学的发展及子宫动脉栓塞术治疗子宫腺肌病临床研究的不断深入,血管介入治疗已逐渐成为该病重要的治疗方法。血管介入治疗子宫腺肌病主要是指通过栓塞子宫动脉,使异位的内膜和增生的结缔组织发生缺血坏死,进而溶解、吸收,达到缓解症状的一种方法,其选择性去血管化的基础是异位病灶的血流明显多于正常肌层组织。近年来该方法已应用于临床,适用于诊断明确、希望保留生育功能的子宫腺肌病患者[1-3]。有不少学者报道[4],用动脉栓塞疗法治疗子宫腺肌病,近期效果明显,痛经缓解率达90%以上,月经量减少约50%,子宫及病灶体积显著缩小,彩色超声显示子宫肌层及病灶内血流信号明显减少。关于子宫动脉栓塞术(uterine artery embolization,UAE)的副反应尚有争议,由于整个操作过程时间较长,而卵巢对放射线敏感,远期疗效及对日后生育功能的影响尚待观察。
随着介入放射学的不断发展、血管介入技术的不断成熟、介入器械和设备不断更新,经子宫动脉栓塞成为盆腔出血性疾病和肿瘤治疗的重要治疗方法,但盆腔解剖范围狭窄,盆腔内脏器前后重叠,髂内动脉分支细小密集、起源复杂,尤其髂内动脉脏支由于血管细小,起源变化大,向盆腔中线集中[5],有的影像重叠,给介入操作带来很大困难,使手术时间延长、对比剂使用过多而长时间盆腔X射线透视照射对卵巢功能有影响,卵巢中卵子受X射线照射有致畸的潜在可能性[6],因此,缩短介入操作时间、X射线透视时间、减少对比剂的用量是术者、患者和医疗安全的需要。子宫腺肌病介入治疗是以血管为基础的,严格掌握好适应证和禁忌证是取得良好治疗效果的前提,而后续的良好的手术技巧则是治疗成功的关键。结合自身临床经验,本文分别从以下方面探讨子宫腺肌病介入手术的技巧。
一、股动脉穿刺置管
患者取仰卧位,穿刺侧髋关节外展30°~45°,采用Seldinger法穿刺。此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1)穿刺点选择准确,应位于腹股沟韧带下2 cm~2.5cm(腹股沟皮肤皱褶下1 cm~2 cm)股动脉搏动最明显处(肥胖者略靠上,瘦弱者略靠下),穿刺点位置过高则血管后壁穿刺点越过股动脉后方的骨质结构,则术后不易压迫止血,形成血肿;过低则导丝易进入股动脉分支。(2)由于髂外动脉狭窄或闭塞及其它因素如肥胖、低血压,有时触及不到股动脉搏动,可采用盲目法穿刺股动脉,首先触摸有无股动脉条索样改变,如能触及则穿刺此点。透视下,97%股动脉通过股骨头内侧1/3靠近髋关节间隙,如股动脉搏动不明显,可据此为定位依据。(3)穿刺过程操作轻柔,进退导丝导管时,如遇阻力切忌蛮力操作,以免造成导丝导管在血管内断裂[7]。
二、投照机位选择
自腹股沟韧带下方置管后,经过各级髂动脉和/或腹主动脉至子宫动脉,沿途所经腹盆腔血管因患者身高、体重、年龄、遗传等因素的影响具有个体化的走行差异。研究发现子宫动脉的起源及开口类型多样,其中起源包括:Ⅰ型(臀下动脉的第一个分支,占60.53%),Ⅱ型(臀下动脉的第二个或第三个分支,占12.53%),Ⅲ型(子宫动脉、臀下动脉和臀上动脉以三叉的形式从髂内动脉同时发出,占7.47%)和Ⅳ型(髂内动脉的第一个分支,占19.47%)。子宫动脉开口有正常、直角、钩形、倒钩、大螺旋和小螺旋等,子宫动脉的走行有上平直下螺旋、全程平直、全程螺旋等几种情况。术中有时需反复造影以了解动脉走行及开口,从而使手术时间延长,不仅使患者和医生的受线率增高,还因反复插管损伤血管内膜,导致血栓形成的风险升高[8]。
只有正确的投照体位,充分暴露子宫动脉开口,才能保证子宫动脉超选择插管的顺利进行。杨建国等[9]认为取同侧31°~45°前斜位最佳,而况圣佳等[10]的研究则相反,为对侧31°~45°前斜位。临床实践中我们发现大部分病例的子宫动脉开口在侧旋25°~30°时可清楚显示,极个别的病例需向相反的方向侧旋30°方能显示子宫动脉的开口。
三、路图的应用
确定最佳工作机位后透视下“冒烟”形成的图像经二次减影,血管影像成为白色的“路图”。子宫动脉周围存在许多条开口和走行与之相似的血管,常规透视下插管即使有造影图像作为参考,亦容易致导丝误入其他血管。而路图作为进一步插管的背景,对导丝和导管的插入起导向作用[11]。
常规数字减影血管造影,因其单一角度图像受血管前后诸多方位重叠的影响,对血管的具体空间解剖位置的了解干扰较大, 随着技术的进步,目前提出平板旋转造影结合3D路径图用于介入治疗。3D-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是在工作站上将所获得的数据进行处理,利用MPR、MIP、SSD、VR等技术进行三维重建,对影像可在三维空间做任意角度的观察,清晰显示子宫动脉走行及其与周围血管毗邻关系,使操作更加直观。
四、超选择子宫动脉插管
血管内介入治疗以血管为基础,引起的并发症也多数与动脉插管操作相关,导管导丝在循动脉系统进行选择性插管的过程中,操作稍有不当,就有可能导致动脉割伤、动脉穿孔和血管痉挛等潜在危险。熟悉血管的走行、分支、分布和侧支循环等必不可少,使复杂的血管腔内操作步骤变得直接明了。在血管性介入操作过程中,血管的开口一般依靠骨性定位标志,但是盆腔血管分支多,结构复杂,而且血管开口变异较多,相对固定的骨性标志往往难以准确定位子宫动脉开口,况且盆腔骨性定位标志较单纯。而臀上动脉距离子宫动脉较近,且臀上动脉较为粗大,无论子宫动脉开口起源于何种动脉,其必然在臀上动脉开口附近,手推造影剂时首先往往能显示粗大的臀上动脉。已有研究提示:子宫动脉开口至臀上动脉开口平均距离约11.71 mm(3.04 mm~18.31 mm)[12]。
UAE的时间多消耗在超选择子宫动脉插管上,由于上述研究根据子宫动脉开口距离臀上动脉开口的平均距离,再结合子宫动脉开口最佳显示角度范围,我们可对子宫动脉超选择插管制定如下策略:5F Cobra导管首先超选择进入髂内动脉,然后将球管旋转至侧斜位25°~30°,打开DSA机SUB减影键,快速推注3 mL~5 mL 对比剂,建立髂内动脉的路图,臀上动脉粗大较易观察,由于臀上动脉开口距子宫动脉开口的平均距离约11.71 mm范围,在此范围内改变导丝的倾向角度和上下移动,当子宫动脉开口为正常开口时,超滑导丝大多可以顺利进入子宫动脉;当子宫动脉开口为直角、钩形、倒钩、大螺旋和小螺旋等几种特殊类型时,此时子宫动脉插管往往较困难;当发现超滑导丝头端于髂内动脉内壁的某处存在阻挡时,稍微用力便会弹过此处,则提示此处多为子宫动脉开口,可以将导丝头端卡于此处,适当调整导丝头端方位,可以旋进或弹进子宫动脉。有时子宫动脉起始段扭曲角度大而长度短,超滑导丝进入子宫动脉而Cobra导管却无法跟进此段动脉,可更换较粗的泥鳅导丝引导5F Cobra导管进入子宫动脉,再进微导管系统(如progreat微导管导丝)[12]。
待导丝弹入子宫动脉时,缓慢跟进推入导管。子宫腺肌病的异位内膜病灶多位于子宫体部,而子宫颈部位受累较少,因此应尽量依托微导管插管至子宫动脉上行支从而实行“精准”子宫动脉上行支栓塞术,并由此避开子宫动脉输尿管支和膀胱支,最大限度地靠近病灶血管床进行栓塞,有利于栓塞剂准确输送到病灶血管床,避免栓塞剂过早地在迂曲的子宫动脉主干中沉积,导致病变栓塞完全的假象,影响手术疗效。目前常用的微导管内配有微导丝,可以较好地完成子宫动脉上行支精准插管。微导丝不仅可用来引导微导管,亦可在子宫动脉内形成内襻,有助于避开子宫动脉小分支。另外微导丝头端柔软,有一定的可塑性,可以人工塑型,以保持合适的角度在子宫动脉内行进。子宫动脉的两分支:输尿管支和膀胱支,此二者的开口和走行在某些情况下与子宫动脉的主干较为平直,特别是二者的开口在子宫动脉主干发生扭曲的部位时,微导丝易误入这两分支血管,此时应用微导丝成襻法可完成精细子宫动脉插管。
微导丝内襻成襻技巧有两种:(1)微导管头端和子宫动脉扭曲部位间隔1 cm~2 cm,将微导丝前行到子宫动脉扭曲部位,逆向调整微导丝头端方向,使微导丝顶于子宫动脉内壁,形成一定的支撑力,顺势前推微导丝,使微导丝柔软的头端部分形成弧形,微导丝头端指向子宫动脉的近心端,至此内襻形成。(2)当子宫动脉全程走行较为平直,无适当的扭曲部位提供成襻支撑力时,可在体外人工塑型微导丝头端,将其形成小的内襻性状。在推进微导丝的过程中,襻的最前部由于成弧状支撑于血管内壁,其只能顺动脉主干前行,由此避开子宫子动脉小分支。栓塞时尽量使微导管插管至子宫动脉上行支,自宫底部往回至上行支起始部逐部逐层栓塞子宫体部血管网,然后再回拉导管至子宫动脉上、下行支外侧栓塞子宫动脉主干[13]。
五、栓塞操作
1.栓塞剂选择
选择合适的栓塞剂对保证疗效、减少并发症的发生非常重要。子宫腺肌病介入的实质是将某种栓塞剂通过导管注入靶血管内阻断子宫及病灶血流供应,使病灶缺血坏死,进而病灶溶解、吸收,同时由于子宫本身的缺血,使增生的肌层组织萎缩,子宫体积变小,达到症状改善或消失[14]。
毛细血管前小动脉丛的血流通畅必须得到保证,某些可消灭血管床的极细胞材料如明胶海绵粉以及无水乙醇等液性材料为禁用栓塞剂。目前子宫腺肌病栓塞剂较为常用的有明胶海绵颗粒、海藻酸钠微球和聚乙烯醇。
明胶海绵为可吸收非永久性栓塞剂,介入栓塞血管后可引起急性坏死性动脉炎,栓塞动脉血供及形成血栓,栓塞效果持续存在数月,一般在45天后血管明胶海绵基本可吸收完全,明胶海绵栓塞后可达到持久的血管闭塞。由于其较快的可降解性,仅可作为子宫腺肌病栓塞治疗的补充栓塞物质。
海藻酸钠微球是从天然植物海藻酸中提取的多聚糖钠盐,水和力强,可溶于水形成黏稠胶体,在钙离子作用下可产生大分子链间铰链固化。海藻酸钠微球在血管内磷酸缓冲液的环境下,钙离子渐渐析出,微球以分子脱链的形式在栓塞后3~ 6个月内无毒降解。降解时不产生碎屑,最终降解产物为无毒的不参加机体代谢的多糖——甘露糖和古罗糖随尿液排出。 由于其结合了明胶海绵和永久性栓塞剂的部分优点,适合于未生育女性介入治疗。
聚乙烯醇由聚乙烯醇与甲醛经交链、干燥、粉碎、过筛而制成,为非水溶性,遇水性液体可膨胀,体积将增加20%,生物相容性好,在体内不被吸收。聚乙烯醇是一种永久性、不可降解栓塞物质,不适合应用于较年轻、尚有生育要求的患者。
由于子宫动脉上行支和卵巢动脉吻合口大多<500 μm,而每种固态栓塞剂都有大小不同直径的规格,综合考虑患者年龄、生育要求、子宫体积大小、病灶血供选择不同的栓塞剂:40周岁以下或有生育要求的患者选择规格较大的(700~900 μm)可降解的固态栓塞剂,40周岁以上如无生育要求则可选择规格较小(500~700 μm)的固态栓塞剂,以达到较彻底的栓塞作用[13,15]。
2.栓塞技巧
子宫腺肌病的异位内膜多呈弥漫分布,造影可表现为子宫肌壁内血管网多较纤细,如发丝状,但致密、着色较深,以上特点决定了其栓塞要求较高。在前述精准子宫动脉分支置管于子宫动脉上行支的宫底部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栓塞剂分层栓塞,逐步回撤微导管并推注栓塞剂,以保证肌壁血管网栓塞的彻底性。其次推注栓塞剂宜采用低压流控法,当微导管进入子宫动脉后,子宫动脉被部分阻断,血流压力明显降低,卵巢动脉血流压力大于子宫动脉卵巢支血流压力,血流方向从卵巢动脉通过侧支向子宫供血区流动,当看到有部分栓塞剂进入子宫动脉卵巢支时,暂停推注,卵巢动脉的血流将栓塞剂冲入子宫供血区,充分利用血流的冲刷作用,将栓塞剂靶向性地分布于子宫肌壁血管网[13]。
栓塞结束时机至关重要,其决定了手术的栓塞程度和疗效。当对比剂出现停滞、子宫动脉内出现对比剂立柱现象、对比剂向子宫动脉开口反流或反流入髂内动脉时,栓塞就可以结束了。为了帮助确认结束时机,可以应用Shlansky-Goldbeog推广的拇指法则,子宫动脉主干内注入的少量对比剂缓慢前行并保持显影,在消失于远端分支之前应持续5次心跳的时间。
介入治疗技术在妇产科的应用不到百年,近年发展迅速,对于任何新技术我们都要创新与规范紧密结合,规范只在一个时期内起指引作用,如一成不变到一定时期会阻碍技术的发展,只要“科学和合理”就会使我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达到一定层面而冲破规范的束缚从而有所创新,以达到“个体化精准治疗”的目的。目前基于CTA、MRA的计算机三维重建可以术前构建患者个体化的血管三维模型,可对后续UAE进行实时导航,实现子宫腺肌病治疗过程中更加精准栓塞的目的。这将简化今后我们的手术操作。
[1]Marshburn PB, Matthews ML, Hurst BS.Uterine artery embolization as a treatment option for uterine myomas [J].Obstet Gynecol Clin North Am,2006,33(1):125-144.
[2]Wang S, Meng X, Dong Y.The evaluation of uterine artery embolization as a nonsurgical treatment option for adenomyosis [J].Int J Gynaecol Obstet,2016,133(2):202-205.
[3]刘文新,张铁青.子宫腺肌病的治疗进展 [J].黑龙江医学, 2014,38(11): 1237-1238.
[4]季菲,艾星·艾里,丁岩,等.子宫腺肌病诊断及治疗研究进展.中国妇产科临床杂志,2009,10(2):155-158.
[5]Cai-xia L,Hong M.The anatomic stuey of the internal iliac arteriography and its guidance for vascular interventional proedures [J].Prog Obstet Gynecol,2006, 15(2):121-124.
[6]Nikolic B, Spies JB, Lundsten MJ, et al.Patient radition dose associated with uterine artery embolization [J].Radiology, 2000,214(1):121-125.
[7]陈春林,刘萍,王绍光.实用妇产科介入手术学[M].北京:人民军医版社,2011:73-75.
[8]陈春林,段慧.数字化三维影像学与子宫肌瘤动脉栓塞治疗 [J].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2016,32(2):139-145.
[9]杨建国,贺能树,张长林,等.盆腔动脉造影正位与斜位对子宫动脉开口显示的比较 [J].临床放射学杂志,2003,22(4):324-326.
[10]况圣佳,辜斌.不同投照角度对髂内动脉造影时子宫动脉开口位置的比较 [J].江西医学院学报(医学版),2003,43(2):106-108.
[11]何玉圣,鲁东,吕维富,等.DSA特殊功能在子宫肌瘤栓塞治疗中的价值 [J].介入放射学杂志,2009,18(11):868-871.
[12]袁牧.3D-DSA在子宫动脉开口定位与最佳显示角度中的临床应用研究[D].合肥:安徽医科大学,2012,20-21.
[13]陈春林,刘萍,王绍光.实用妇产科介入手术学[M].北京:人民军医版社,2011:138-152.
[14]程曙,王士甲,张国富.子宫动脉栓塞在治疗子宫腺肌病中占有重要地位 [J].介入放射学杂志,2010,19(12):925-927.
[15]吴国燕,米建锋.不同栓塞剂介入栓塞子宫动脉治疗子宫腺肌病的效果观察 [J].右江民族医学学报,2014,36(3):408-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