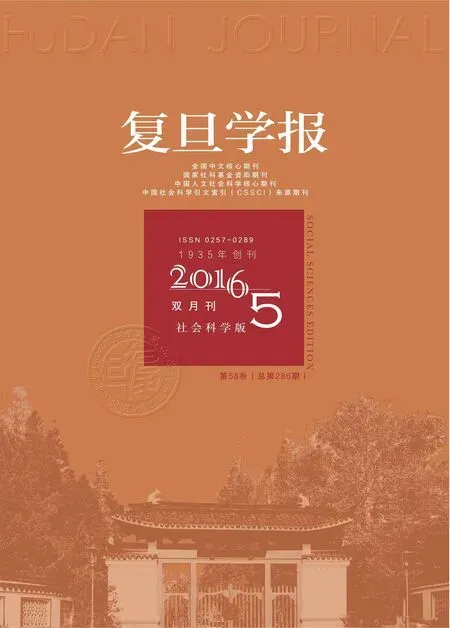论“第六代”电影的东方主义困境
2016-12-16谭逸辰
谭逸辰
(“国立中央”大学 中国文学系,台湾)
影视理论研究
论“第六代”电影的东方主义困境
谭逸辰
(“国立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台湾)
在中国当代电影中,“第五代”和“第六代”电影都有浓重的东方主义倾向,但两者是有区别的。“第五代”在他们的电影中作了大量传统“东方主义”的表述,“第六代”则在“东方主义”框架下构建出新的“他者”形象,并试图取代“第五代”与西方的“共谋”关系,获得自己在国内的“权力话语”。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电影工业体制的变化和民间资本的崛起,官方和资本完成了对“第六代”的合围,而“主流电影”话语也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权力中心,绝大多数“第六代”导演选择融入主流,放弃东方主义叙事,基本摆脱了东方主义困境,但同时也失去了其曾经赖以生存的西方市场。而有一小部分“第六代”导演仍在东方主义框架下进行新的尝试,其中最为成功的是贾樟柯,他灵活地游走在中西之间,依靠其对东方主义新的诠释在中国国内和西方都收获了成功。
“第六代”电影东方主义贾樟柯
“第六代”这个群体可以说是在整个中国电影行业、理论界和大众一致的热切期待下诞生的。这种期待与他们的前辈“第五代”关系密切:一方面,“第五代”在国内和国际上的成功增强了各界对新时期中国电影的信心;另一方面,“第五代”电影的一些问题又使人迫切希望看到新的电影人站出来反驳他们、纠正他们,而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第五代”电影中存在的传统的东方主义叙事。自萨义德(Edward.W.Said)在《东方学》中提出“东方主义”这个概念以来,已有近40年,但“东方主义”问题并没有被妥善解决,它仍是阻碍东西方正常交流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中涉及了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冲突等诸多领域。并且随着全球关系的复杂化,东方主义不仅在西方作为维护文化霸权的理论工具,它作为一种话语也被东方人自己所使用:一方面,欧美东方主义的认知和方法,在20世纪已经成为东方“自我形象的构成”;另一方面,则如岩渊功一所说的那样,东方的知识分子也在一种“自我东方论述(self-orientalism)”中获利。*详见岩渊功一:《共犯的异国情调——日本和它的他者》,《解殖与民族主义》(香港岭南学院翻译系文化/社会研究译丛编委会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20世纪80、90年代,包括“第五代”、“第六代”电影人的众多中国年轻知识分子都切身参与了这种双向的“共谋”。然而,这种“共谋”并没有使其在中国取得所谓的“强权话语”。相反,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社会文化及政治局势的复杂性,使他们非但没有获得理想中的地位,甚至更加边缘化了。而他们又无法轻易抛弃之前所倚靠的“东方主义”话语,可以说是陷入了一种“东方主义困境”。
(一)
电影这一20世纪才出现的新兴媒体在近几十年里逐渐取代小说、诗歌等传统媒介,成为西方在进行“东方主义”表述时最乐意使用的手段,原因不外乎其作为一种影响更广泛且深远的大众话语,电影有着更高的传播效率和在将东方“小丑化”、“女性化”时所具有的更强的表现力。更重要的是,电影不但有着极强的意识形态传播功能,这种特性还被掩盖在了其远高于其他媒介的娱乐性之下,这种隐蔽性正是“东方主义者”所迫切需要的。因为在全球权力关系越发复杂的今天,民族主义和“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在各个所谓“第三世界”国家快速发展,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因为已发生变化了的东西方权力关系而显得过时,在诸多层面上都不再有说服力。因此,西方需要缝合在面对东方经济崛起时所造成的现实矛盾和裂缝,巩固自我中心主义以平复竞争的焦虑。在那些披着国际主义全球化外衣的好莱坞电影中,成龙、李连杰等中国演员和《功夫熊猫》等影片中的中国元素,实际上都在参与这种修复支配地位中做了努力,进行的是典型的东方主义表述。
而我们主要想要讨论的是在“第五代”和“第六代”电影人身上体现出的东方主义在东方的发展,也就是所谓“东方人的东方主义”。这个概念是德里克(Arif Dirlik)在萨义德理论基础上进行的拓展,他认为东方主义不仅是欧美发展,进而抛向“东方”的一个自治产物,更是欧美与亚洲之间一种扩展中的关系的产物,需要有后者的共谋才能使这种关系具有似真性。
这种“共谋”在这两代电影人身上是有区别的,这主要体现在“东方主义”表述的内容上。“第五代”在他们的电影中进行了大量传统“东方主义”的表述,并由此获利:西方人在东西方权力关系发生变化之后,已不再满足于《大地(the Good Earth)》(1937)这样来自西方的东方主义文本,而是需要来自东方、来自“他者”的声音,作一个“客观”的叙述,借以重塑西方的地位。而《黄土地》(1985)这样既来自“本民族”,又同时兼备了“历史文化反思精神”的“西方”特征的电影,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被追捧的对象。这种追捧和随之产生的名利双收显然影响了“第五代”在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创作风格,尤其是进入90年代后,他们在此基础上又创作出了《菊豆》 (张艺谋,1990)、《大红灯笼高高挂》(张艺谋,1991)、《风月》(陈凯歌,1996)、《炮打双灯》(何平,1994)、《家丑》(刘苗苗,1994)、《五魁》(黄建新,1994)、《大磨坊》 (吴子牛,1990)等一批具有明显东方主义特征的影片。这些电影有着相同的特征,即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空间指涉,而是一个彻底寓言化的东方故事。这些故事所表述的中国,是“在对‘民族特性’的刻意展现中,一个纯粹以东方主义观念想象的‘中国’”:压抑的宗族社会、封闭的宅院、残酷的宗法、无能的男性、情欲受到压抑的女性、奇异的民俗等“东方主义奇观”。*胡谱忠:《当代电影中的“东方主义”与“性别政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这些电影文本为西方人的东方主义提供了新的佐证和材料,并且影片中表现出来的所谓“历史反思”,又是对东方主义本质上的“历史主义”和“文化主义”的一种认同和主动归附,将其作为了“普遍主义”的标准和自我身份确认的依据。
然而“第五代”在国际和国内所受到的追捧并没有持续多久。在国内,针对这种忽视正在“大步迈向现代性”的当代中国,却不断往国际社会输出中国“前现代(premodern)”形象的行为,整个社会持有一种极为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是混合了中国电影崛起和中国文化获得国际关注的奇特自豪感,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负面文化民族特性的过度表述而产生的抵触情绪,这也使得以清理西方权力话语为目标的后殖民批评在当时大为风行。这种矛盾心理催生的是对影坛下一代的期待:“第五代”在国内和国际上的成功增强了各界对新时代中国电影的信心,而“第五代”电影中的“东方主义”问题,又使人迫切希望看到新的一批电影人站出来反驳他们、纠正他们。
可惜的是,这种社会各界一致的期待,非但没有使新一代电影人摆脱德里克所说的“东方人的东方主义”,或者梅拿(Miller)称之为“自我东方论述(self-orientalism)”的逻辑,相反,由于这种期待加强了“第六代”作为“子一代”的焦虑,再加上国内外权力关系的复杂化,以及国内市场格局的剧变,反而使得他们更加依赖这种“共谋”关系。
究其原因,第一,从国内环境因素上来说,“第六代”在中国国内舞台登场的时机,相比他们的前辈来说是很不理想的:一方面由于国内电影工业的转型,他们没能像“第五代”那样得到国家体制的大力支持;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加入WTO,一度坚持艺术电影的“第六代”,面临着电影商品化潮流的巨大冲击。在体制和市场的双重围攻下,“第六代”有的只不过是一种并不可靠的“社会承认的权威”,想要在中国国内影坛站稳脚跟是相当艰难的,给他们用于突围的选择也并不多。而进一步利用“东方人的东方主义”这套逻辑,一方面可以使“第六代”获得来自西方的援助(不管是经济上还是声誉上的),使他们得以避开与商品化潮流的正面冲突;另一方面,利用“东方主义”逻辑加固强化这种“社会承认的权威”,占领文化制高点,在国内塑造自己的权力话语,更是一种变被动为主动的突围策略。
第二,从国际环境因素上来说,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中国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能动参与者,加入到了新的东西方权力关系中,已经不再处于被动接受西方支配、重构的地位上了。但事实上,“西方——东方”的权力支配体系并没有因此被打破,只不过欧洲/美国中心主义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在后现代时代,‘东方’被全球化了:它可以是任何地方,并且任何地方都能被将自己定义为西方的权力视角所东方主义化”*“In postmodern times,‘the Orient’ has been globalized: it is located everywhere and everywhere it can be subjected to Orientalization,from the one ruling perspective that defines itself as West“ZiauddinSardar,Orientalism,P114.。这使得“第六代”即便只是试图在中国影坛占据一席之地——在中国/东方内部获得权力话语——也必须在对“现代性”的阐释中掌握主动,与其他同样来自“东方”的话语相互角逐,成为能够支配其他话语的“强权话语”。
第三,从内部需求上来说,由于一种剧烈的“影响的焦虑”与某种意义上的“弑父情节”,使得“第六代”在诞生之初(甚至是之前),就将这一电影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设定为针对“第五代”进行的“对抗性书写”。他们作品中的一些显著特征,比如“真实”、“现场”、“描写当代城市”等,都如同口号一般直指“第五代”,试图对抗其东方主义话语。这种对抗性的“反向书写”与历史重述,旨在针对“第五代”所代表的那种西方对东方的传统偏见和“错误表述”,重塑一个“真实”的东方/中国。然而这种激烈的对抗情绪使得他们在进行表述时,也失去了客观性和全面性。实际上使用的也是“东方主义”的那一套逻辑,甚至演化出了一套更加符合后殖民/后冷战时期全球关系的新“东方主义”表述,试图借此取代“第五代”去与西方进行“共谋”,建立起自己在国内的“权力话语”。显然,这种行为“不过是用本土霸权取代西方霸权,这不是真正的‘解放’,而是‘权力置换’”*张兴成:《东方主义的全球扩散与再生产——兼谈文化民族主义的内在逻辑》,《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在这一层面上,“第六代”作为“东方人的东方主义”在东西方权力关系中的实践,是与“第五代”一样的:不仅在帮助“西方”对“东方”进行“殖民”,同时也在依靠民族主义叙事进行一种“内部殖民”*“‘东方人的东方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多重角色,它巩固了两种霸权形式,它通过自我东方主义化而自动本质化(self-essentialization),一方面因内化了东方主义的历史前提而巩固了‘西方’的意识形态霸权,另一方面又通过确立民族主义叙事的合法性权威地位而成为压制国内差异的内部霸权,即一种‘内部殖民’。同时,它还有第三重角色,即‘东方人的东方主义’还将东方主义文化霸权衍化为东方人或第三世界民族国家之间权力争夺的话语策略,从而使东方主义问题进一步复杂化、顽固化。”张兴成:《跨文化实践中的东方主义话语》,《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2年第6期。。不同的是,“第六代”借机抛弃了传统的“东方主义”叙事,在“东方主义”框架下构建出了新的“他者”形象,并以此试图取代“第五代”与西方的“共谋”关系,获得自己在国内的“权力话语”。
(二)
对“他者”的建构是“东方主义”在实践中的基础。正如萨义德所说的:“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的存在。”*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427页。“第六代”也必须在中国社会建构起一个作为自身镜像的“他者”,来补完“东方主义”逻辑中的权力关系。但他们面临一个问题:传统“东方主义”表述中的中国形象,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下这个后殖民/后现代语境之中了。一方面,中国在经历了20世纪几次剧烈的社会变革后,很多文化和社会形态已经消失,使得类似“第五代”电影中的那些所谓“历史反思”、“民族性探讨”等元素,显得多少有些过时,或者说在全球化语境中已经无力支撑起一个具有明显权力支配关系的“东方主义”逻辑了。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中国模式”、“儒学复兴”等概念的出现,中国的形象越发正面,因而文化奇观式的东方主义的消费价值也已经明显降低。
当“东方”越发接近“西方”,不再有足够的“东方性”时,以东西方的“疏离”作为基础的“东方主义”将如何应对?这种情况并非没有先例: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经济和技术快速崛起,甚至一举攀升,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这彻底打破了西方人一直以来的“技术中心论”,也同时破坏了“东方主义”逻辑中西方/东方和现代/前现代之间单一的稳定关系。“日本的挑战使人怀疑西方是否仍是现代性构想的文化和地理中心,推翻了只能以西方建构起的形态来表述现代性,挑明了现代性的基础是种族主义。”*张兴成:《东方主义的全球扩散与再生产——兼谈文化民族主义的内在逻辑》,《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针对这种情况,西方人将日本的这种“现代性”表述为一种代表了技术的“冷漠”、“非人性”的异质属性,进而不惜创造出“技术东方主义”这种模糊“东方性”与“西方性”界限的概念,来将日本再次“他者化”。
而西方对中国“他者”形象的重新阐释,其实要相对容易得多,只须对中国快速崛起这一事实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即可:即中国的“现代化”虽然类似西方,但实际上是由“集体主义”、“极权”等并非代表了西方“现代性”的社会主义国家特性才得以快速发展的,而这种快速发展也导致了“道德沦丧”、“非人性”、“信仰缺失”等典型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问题。对这种表述我在这里暂且称之为“后社会主义东方主义(Post-socialist Orientalism)”。
“第六代”在他们的电影中进行这种“后社会主义东方主义”表述时,主要使用了如下两种表现方式:
第一,寓言化。和“第五代”对“乡土中国”的包装一样,“第六代”在其电影中也勾勒出了一个残酷冷漠的后社会主义“城市中国”。“第六代”的所谓“真实客观”,并没有将真实的中国城市还原出来。由“个人体验”转化而成的叙事元素,虽然具备一定的具体性,但也被“第六代”导演先在的一种审美倾向和偏见所歪曲、肢解,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典型东方主义文本所需要的“想象性东方”。
第二,奇观化。在“第五代”影片中,构成“奇观性”的主要元素是各类民俗:日常民俗、仪典民俗和“文革”等政治民俗。而在“第六代”电影中取而代之的则是所谓“城镇化”。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城镇化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用贾樟柯的话说:“在当下的中国我觉得有一种超现实的气息,因为整个国家、社会都在一个巨大的莫名的推动力之下飞速地发展,人们承载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人际关系、处理问题的方法,有很多奇怪的你不能想象的东西。”*《把贾樟柯彻底搞清楚》,《南方周末》2002年4月30日。然而“第六代”在对这一社会文化“奇观”的呈现上,却套用了后社会主义语境中的东方主义“常识”:信仰的崩塌、社会结构的解体、在钢筋水泥丛林中无处可去的未来和逐渐泯灭的人性。
就拿“第六代”电影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流浪北京》(吴文光)作例子。这部中国新纪录片的开山之作,是导演通过对同类的反复诘问而进行的一种自我表达。片中的这些“流浪艺术家”尽管居无定所、经济拮据,在社会上还被用“盲流”这样一个饱含轻蔑的词汇,与地痞流氓、乞丐游民划为一类,但从他们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他们对生活还是充满希望的,因为他们身处北京,而北京在某种程度上是当时中国内陆离“西方”最近的地方。张慈这样讲述她来北京前的生活:她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云南一个叫作“个旧”的县城做编辑,张慈称这个地方大概是她在中国到过的“最恶心”的地方,“每一天都像度过沙漠一样”、“想起来现在都(觉得)恐怖”、“每天盼着的就是吃”、“特别苦闷”。这段叙述形象地塑造出一个因工作分配体制而不得不遭受剧烈精神痛苦的艺术青年形象。而在这段叙述前,导演显然有意放置了一组描绘张慈在一处破旧水斗洗衣服的镜头,用她在北京生活的艰辛,来进一步衬托出北京在她精神世界的重要意义。于是“流浪北京”就成为了象征“追寻梦想、追寻自由”的文化寓言。而贯穿整部影片的“盲流”一词,更是不断暗示着户籍制度这一“中国式奇观”。摄影师高波是采访中对这个词最为敏感的。对这个称呼,他的表述显得有所顾忌:一方面他认为“人多少都应该有点盲流性,中国人就是缺少这种盲流性”;做出这种宣言后,他又辩解道:“我当盲流不是为了当盲流,是没办法,我也不觉得光荣”,但马上就补充说“没办法,我也喜欢(这种生活)”。高波的这种表述首先将“盲流”与“自由”、“解放”等象征了所谓西方思想的概念,联系在了一起,紧接着的辩解又让人联想到意识形态对立所带来的压迫,而最后的表态则有种抗争的意味在里面。这塑造出的是一个受到压迫却不放弃希望的进步青年形象,这一形象又因为影片自我表达的性质,而直接指涉了“第六代”导演自身。
这种“边缘人”的自我指涉,实际上是“第六代”在进行“后社会主义东方主义”表述时的一种补充:即利用“东方”内部的“反抗声音”,对“东方”形象进行一种补正,使其在全球化语境中更具有说服力。
“第六代”电影在西方也经常被称为“中国地下电影”。实际上,“地下”一词就是在给这一批电影贴上“后社会主义东方主义”的标签:在后冷战的全球格局中,西方权力话语已不满足于中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异域国家形象,充当西方的想象对象,而是希望中国接替前苏联成为极权体制的象征,成为自由世界的对立面。而构成这种象征的就不仅需要专制的当权者和恭顺的人民,还需要来自其内部的反抗声音,而“第六代”正好表达了这种声音。这一受压迫的形象作为吸引西方观众的要素之一被广泛使用,观众们去电影院看这些电影的主要目的,就是想看看究竟什么样的内容会被中国政府禁止,从而沦为地下电影的。一如张艺谋和张艺谋式的电影满足了传统东方主义的审美期待,即“铁屋子”中被扼杀的欲望故事。“第六代”的这种地下身份,则是“被用于补足西方自由知识分子先在的、对九十年代中国文化景观的预期”*戴锦华:《雾中风景:初读第六代》,《天涯》1996年第1期。,为他们在自己的东方主义世界观中,勾勒出中国的“进步”、“民主”、“公民社会”、“边缘人”等形象,通过描绘这些人群在东方的悲惨处境,从而再一次强调西方自由社会的进步性。
“第六代”的这种以“边缘人”的自我指涉来增强“后社会主义东方主义”表述说服力的策略,还包含了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
德里克在分析东方主义的历史时,借用了普拉特的“接触地带”概念,*普拉特所说的“接触地带”并不是指文化的交集,更强调的是东西文化碰撞中所形成的不同于两种文化的空间。它既不等同于“自我社会”,也非“他者社会”的照搬。而是“疏离”,一种与自我、他者的双重疏离,即是对权力结构的某种修正,但同样遵循权力思路、竞争意识。陈林侠:《跨文化背景下东方人参与的“东方主义”——以成龙的好莱坞电影为个案》,《戏剧》2013年第1期。即“殖民遭遇的空间,在地理和历史上分离的民族相互接触并建立持续关系的地带,通常涉及到压制、极端的不平等和难以消除的冲突的状况”*阿里夫·德里克:《中国历史与东方主义问题》,《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90、93页。。“第六代”斩获了许多奖项的各种国际电影节便是这种“接触地带”。这些电影节虽然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文化和价值体系的电影人,但其评价体系始终是以“西方”为主导的,这就使得这些电影人最终放弃自身各不相同的文化经验,转而服从来自“西方”的权力话语。因此,可以说在这个“接触地带”,“权力结构”并没有被废除,反而是增强了。
而作为东方的东方主义者,“第六代”巧妙地利用了这一东西文化的“接触地带”,利用塑造“东方”内部的“边缘人”,营造出了文化的“疏离感”,传达出一种“似西似中”但又“非西非中”的文化样态,对应于西方社会的某种期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修正了中国原有的传统“东方主义”形象。
另一方面,这种自我指涉也暴露出“第六代”自己的“野心”:即在国内构建以精英主义为基础的“权力话语”。他们的逻辑就类似德里克对杜维明等人在创建文化中国问题上的立场所作的评论:“杜维明的立场揭示出一种类似的、得益于他作为西化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越地位的精英主义(elitism)。在谈到文化中国时,杜指出,一个文化中国的创造必须从‘周边’(periphery)到‘中心’,从海外华人到中国的中国人。就中国社会来说,中心——周边这种划分意味着‘文化中国’的创造要通过来自几乎无权或根本无权的边缘地带的知识分子对权力中心进行改造来完成。然而,从全球的视角看,权力关系就似乎完全不同了,因为从那个视角看,周边与全球权力的中心相偶合,而中国社会的‘中心’则出现在周边的位置。‘海外中国人(Diasporic Chinese)’,甚至在全球经济或文化中获得了成功,然后充当改变中国的能动力。”*阿里夫·德里克:《中国历史与东方主义问题》,《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90、93页。
“第六代”的策略也是类似的。作为在中国国内并不享有话语权的“边缘人”,他们在“西方”和“接触地带”获得了认可和成功,挺进到了全球化视角里的“中心”,并试图利用从中获得的“话语力量”,从外部改变中国影坛、中国文化的“权力中心”。
但“第六代”的问题在于,电影是一种大众文化媒体,他们的目标不仅是在知识界获得“权力话语”,而是需要将这种话语转化为电影市场上的成功。在这一环节上,“第六代”一直没能找到切实有效的手段,来利用在“后社会主义东方主义”表述中所获得的权力和地位,反而是由于死守“东方人的东方主义”以及“精英主义”话语不放,导致他们长期游离于市场和体制之外,失去了占领本土市场和培养固定受众群体的最佳机会和时间。与此同时,代表了官方与资本在新时期合谋的所谓“主流电影”,又给了“第六代”以致命一击。
(三)
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电影工业体制的变化和民间资本的崛起,官方和资本在合谋中彻底完成了对“第六代”的合围,而“主流电影”话语也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权力中心。而在这一境况中,绝大多数“第六代”导演都选择融入主流,放弃或极大地削弱了这种“后社会主义东方主义”表述,也因此可以说是摆脱了“东方的东方主义者”的身份。
当然其中也有例外,有一小部分“第六代”导演仍在东方主义框架下进行一些尝试,但他们都在“后社会主义东方主义”表述的基础上,做出了一些改变或修正。如娄烨的中法合拍片《花》(2011)和郭小橹的《中国姑娘》(2009),更是在某种程度上回归了传统东方主义叙事里的“西方情人”母题。正如胡谱忠所说的,在《红河谷》 (冯小宁,1997)、《黄河绝恋》(冯小宁,1999)这样的影片中,“以女性自居的叙事姿态所婉转表达的‘暗恋’,变成了直接呈现的西方情人与东方女性的廉价遇合。”这种欲望主体和欲望客体的直接遭遇,标志了作为欲望客体的东方对传统东西方权力关系上的地位变化,开始了一种“恰到好处的自我膨胀和自我弘扬”*胡谱忠:《当代电影中的“东方主义”与“性别政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而在《花》和《中国姑娘》之中,“第六代”又将这种权力关系的变化进一步向前推进。在这两部影片中,不再是“西方情人”在古老的东方国度遇见美丽却又深受苦难的东方女子,而是有独立精神的东方女子只身前往西方,在双方各有所需的情况下进入“西方情人”的生活。虽然这种欲望客体对欲望主体的主动迎合,被影片中西方男性的主动占有甚至是暴力占有所遮蔽,但实际上东方女性与“西方情人”在权力关系上是对等的,甚至是优越的。两部影片中的“西方情人”皆有明显的缺陷:《花》中的Mathieu并非文明世界的化身,他粗鲁、暴力、文化程度低,甚至完全无法融入花的社交圈子;而《中国姑娘》中的Mr.Hunt和Rachid,一个是性无能的孤独老人,一个是同样来自第三世界的印度餐馆老板。而花的知识分子形象和李梅的上进心,都和他们产生了鲜明的对比,并且这种对比在影片的女性视角下被更加放大。这使得传统东方主义表述中性别化的角色设定也因此颠覆,取而代之的实际上是一种在后现代语境中,相对于全球化“西方”的,糅合了代表传统东方的中国和陈旧西方——即老牌欧洲国家的“新东方”。娄烨和郭小橹显然是试图用这种新的东方主义权力关系,在目前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权力体系中寻找一席之地,而这两部影片所得的国际奖项,也可以算作是他们成功的标志。
与娄烨、郭小橹类似的,贾樟柯也在用修正过的“东方”形象来赢得西方进一步的接受和肯定,并且显然他做得更为出色。与上述两位不同的是,贾樟柯没有选择进行露骨且意图明确的东方主义表述,而是在坚持他自己所谓“业余”、“草根”特色的同时,在有意或无意间流露出一种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下,更受西方欢迎的东方主义倾向。其受欢迎的原因笔者认为有如下两点:
第一,贾樟柯的电影聚焦的是介乎“第五代”的“乡土中国”与“第六代”的“城市中国”之间的场景,也即中国的小城镇。经过“第五代”和“第六代”在海外市场持续十几年的传播,西方已经开始厌倦寓言化的传统东方和作为自身投影的后现代东方,而贾樟柯所带来的这一新的场景,可以说是西方梦寐以求的新素材,用以补足全球化语境中的新东西方关系。在这一场景中的中国人形象,混合了传统东方的闭塞落后和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彷徨无奈,就如《站台》(2000)中的文工团,他们一方面在表演着作为政治民俗的革命文艺,另一方面在徒劳地想赶上整个社会急剧的现代化进程,以一种绝望无助的姿态成功博取了西方的关注和同情。
第二,贾樟柯的电影更加直白地暴露后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中的一些社会矛盾。例如,他在2013年的电影《天注定》中,选取了在当时中国国内引起轰动的一系列社会事件,拍摄了一部由四个互无关联的小故事组成的影片。这四个故事的核心可以用以下关键词来表述:“腐败”、“暴力”、“拜金”、“剥削”、“贫富分化”和“信仰缺失”。这些关键词恰好是构成西方想象中后社会主义东方社会的典型特征。或许导演的用意确实是想用这些内容揭露社会上的问题,但这种集中的、针对性的表述,显然也在有意或无意间充当了全球化语境下“后社会主义东方”的最佳想象材料。
有趣的是,贾樟柯在近期的电影中,却使用了一种近乎含蓄的方式来表现这种东方主义倾向,这在他的“纪实虚构(docufiction)”风格电影《二十四城记》(2008)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从表面上看,影片似乎不仅聚焦于这些底层工人在改革中所做的牺牲,而是对这场剧烈的社会变迁进行了全景式的描绘,采用的拍摄手法也是较为客观真实的纪录片模式。但实际上,这部电影就像贾樟柯的其他电影一样,是一部用极其小心的镜头组成、取景和场面调度来精心安排和控制的电影。影片中反复表现这些工人在怀念工厂黄金岁月时所流露出的那种对组织的归属感,似乎在试图唤起观众对“集体”这一典型东方化概念的一种认同,但实际上,尽管受访者一再强调自己的牺牲“谁也没有错”,观众还是能明显地感受到这种对组织的辩护是非常无力的,只不过是受访者在避免因为否定组织而陷入一种“自我否定”的更为尴尬的境地。这种安排使得观众对这些被牺牲的底层工人产生了更为深层的同情,并强化了对后社会主义中国社会冰冷残酷的固有想象。
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有表面上迎合官方权力话语的意图,但笔者认为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这种内含矛盾的叙事方式,固然可以使后社会主义中国这一新的东方形象更为生动和丰满,但本质上作为西方自由世界对立面的实质却是没有改变,甚至是被加强的。
上述两种新的东方主义尝试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尤其是贾樟柯,他不仅是硕果仅存的仍然受到西方大量关注和赞誉的“第六代”导演,他作品中的批判精神和现实主义元素,也使其在国内网络媒体上受到广泛追捧,而他本人也对这种新兴的媒体赞誉有加,称其“改变了我们对中国的认识”*详见Michael Berry对贾樟柯的采访:Speaking in Images: Interviews with Contemporary Chinese Filmmake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203.。作为2013年前后在网络上享有巨大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微博大V”之一,贾樟柯似乎在借助公众影响力构筑一种新的话语中心,用以巩固自己已经建立起来的新东西方权力关系,不过由于之后政府的介入也逐渐式微了。
直至今日,不管自愿与否,“第六代”大多已经融入主流文化并基本摆脱了东方主义困境,但代价也是巨大的:他们因此失去了曾经赖以倚靠并用来武装自己的“西方权力话语”,也在曾经滋养他们的西方市场和“接触地带”——西方电影节上不再受宠。而如贾樟柯这样灵活地游走在所谓“西方”和“东方”、“独立”和“共谋”之间的“第六代”导演,则依靠其对东方主义更加巧妙的阐释,在中国国内和西方都收获了成功。而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快速崛起,中国极有可能成为新的东方主义话语中心,那么“第六代”又会不会集体回归某种意义上的东方主义叙事呢?对此,我们拭目以待。
[责任编辑罗剑波]
The Orientalism Predicament of the Sixth Generation’s Film
TAN Yi-che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Taiwan,China)
Among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both “the Fifth Generation” and “the Sixth Generation” have a strong preference of Orientalism.However,there is a clear de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instead of making classic representation of Orientalism,“the Sixth Generation” had built a new image of “other” under the frame of Orientalism,and tried to replace “the Fifth Generation” in the collus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West,in order to build their own domestic “power discourse”.In the late 90s,with the changing of Chinese film industry and the rising of the non-government capital,the authority and the capital,as two claws,had cut “the Sixth Generation” off,which made the discourse of the “main stream film” became the true power center.Most of “the Sixth Generation” directors chose to join the “main stream”,and abandoned the Orientalism narrative.As a result,they managed to get rid of their Orientalism plight,but also lost the West market.Still,there are a small group of directors are making new attempts under the frame of the Orientalism.Among them,Jia Zhangke is the most successful one.His flexibility and new interpretive of the Orientalism made him popular both in China and West.
Chinese cinema; the sixth generation; rock music; orientalism
谭逸辰,台湾“国立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