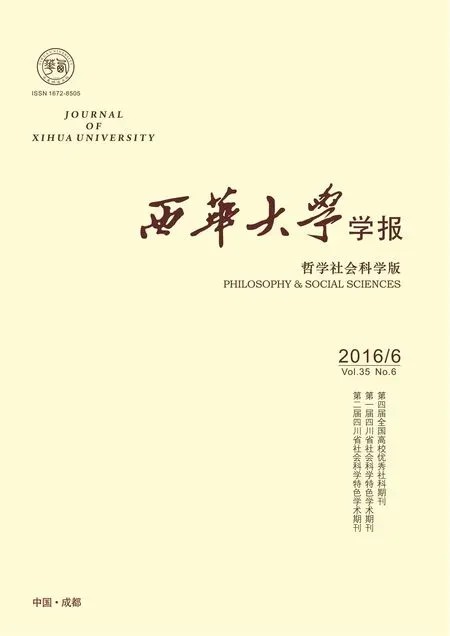从三个诗学命题看苏东坡文论的佛教背景
2016-12-15高云鹏
高云鹏
(北京体育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北京 100084)
·蜀学研究·
从三个诗学命题看苏东坡文论的佛教背景
高云鹏
(北京体育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北京 100084)
从苏轼“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随物赋形”“物无陋者”这三个诗学命题可以看出,苏轼的文艺思想具有深厚的佛教背景。佛教的基本观念、认识论,尤其是禅的本质、不可言说性、判断标准、认知和观照方式以及佛经中对丑怪事象的描写乃至佛教的绘画、造像艺术等多个方面都对苏东坡的诗学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教思想的影响是苏轼诗学观既深刻而又极具个性色彩的重要原因之一。
苏轼;诗学;佛教思想
苏东坡一生对佛教的研究用力颇多,他的佛禅思想被编选成《东坡禅喜集》流传至今,他本人更是被传为是五祖转世而为人所津津乐道。佛教在苏东坡的思想境界、人格建构、文艺创作等方面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以苏东坡三个重要的文论命题为例,探索佛教思想对苏东坡文艺思想的影响,从而获得对苏东坡极具个性色彩文艺思想的更加深入的认识。
一、“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
苏东坡论诗重“趣”。关于什么是“趣”,其《书柳子厚渔翁诗》云:“反常合道为趣。”[1]《佚文汇编》卷五,2552“反常”是说违背正常的思维和逻辑;“合道”则是对“反常”的限制,要求诗人在“反常”的同时不违背艺术规律(“道”)。苏轼于诸多的诗“趣”中最看重“奇趣”。“奇趣”的提出有其特定的批评语境,苏轼在《书柳子厚渔翁诗》中批评柳宗元《渔翁》云:“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熟味此诗有奇趣,然其尾两句,虽不必亦可。”[1]《佚文汇编》卷五,2552苏轼认为柳宗元的《渔翁》有“奇趣”。这首诗的奇妙之处便在于“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渌”[2]1252两句。“烟销日出不见人”的场景中突然出现了“欸乃一声”——无人之境中突然出现了由于人的活动而发出的桨声。另外,山水变得清澈本是“烟销日出”之后所出现的自然现象,“欸乃一声”则是由于渔翁划船而发出的,二者之间本无必然联系,但在诗人看来山水忽然变得清澈仿佛就是“欸乃一声”使然。这两句诗都不能用生活常识来检验其合理性,但是却富有“奇趣”。可见,“奇趣”的获得与“反常”是分不开的,而艺术中的“反常”归根到底就在于对常情常理的违背。诗歌的创作并不是为了把生活中的景物、事物原原本本地“复写”出来,苏轼要求诗歌能够通过艺术化的表现手法给人以奇妙的审美情趣。另一方面,诗歌艺术中的“奇”和“反常”与荒唐、怪诞是有本质区别的。这就涉及到“趣”的另一个属性——“合道”。所谓的“合道”,指的是合乎艺术规律和审美心理,而不是合于抽象的理。因为诗中的“奇趣”最终是要使人获得审美享受,它的获得不依靠理性知识和逻辑推理,而是来自于人的艺术想象力和审美感受能力。
除了以“奇趣”来批评柳宗元的《渔翁》诗以外,苏轼还用“奇趣”来批评陶渊明的诗歌,其《书唐氏六家书后》云:
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覆不已,乃识其奇趣。[1]卷六十九,2206
苏轼认为智永禅师的书法和陶渊明诗歌的相似之处便在于“精能之至,反造疏淡”的艺术风格。所谓的“枯淡”,也就是苏轼在《评韩柳诗》中所说的“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1]卷六十七,2109-2110以及《与子由六首》其五中的“质而实绮,癯而实腴”[1]《佚文汇编》卷四,2515。我们知道,通常的诗歌创作一般都是于质朴或绮丽的艺术风格中偏重其一,于散缓或紧严的审美效果中只执一端,但是陶渊明却将两种互相矛盾的风格统一在自己的诗歌中,这不能不称为“奇”。同时,其“奇”的创造又不违背艺术规律,故此在“反常”的同时做到了“合道”。可见,任何作品要想“得趣”,“奇”和“反常”都是不可或缺的。具体地说,“趣”是根本,“奇”是其外在体现,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关于苏轼以“反常合道”为内涵的“趣”论,很多学者都已注意到它与禅宗是有一定关系的。周裕锴《宋代诗学术语的禅学语源》(《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6期,第70—76页)、詹杭伦《苏轼文艺审美理论六题》(《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54—60页)等文都指出了这个诗学命题的“语源”——“反常合道”是禅宗话头之一。周裕锴先生还在《文字禅与宋代诗学》一书中把“曲喻”和“佯谬”两种表现手法当作“反常合道”的实现方式[3]167-181。杜松柏先生则通过对三桩禅宗公案的分析,揭示了禅宗奇言异行所体现出的反常而合于道的特点与禅诗中的“反常合道”存在着一些相似之处[4]332-333。上述论著都发现了禅宗的“反常合道”与作为诗学命题的“反常合道”之间存在着某些相似性,但是究竟是何种原因使得禅宗的“反常合道”与诗学中的“反常合道”走到一起,则仍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禅宗和诗歌在表达对象、表达方式以及认知心理、判断标准上的相似性是促成苏轼借用这个禅宗话头来论诗“趣”的直接原因。
1.禅与诗表达对象的不可言说性。禅不可言说,这是由禅宗所参悟和表达对象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禅”不是可以通过学习能掌握的,其需要依靠参禅者自己的体悟,这种体悟又只能向内求取,一切向外搜求的做法都是徒劳的。所以,禅宗的基本问题都是无法直接给出正面回答的。周裕锴指出,为了解决“不立文字”与“不离文字”的矛盾,“宋代禅师借鉴并改造了佛经诠释学中‘遮诠’的方法,在语言唇吻中杀出一条‘活路’来”[3]181。所谓的“遮诠”,是相对“表诠”而言的。“表诠”是指从正面进行肯定性的诠释;“遮诠”则是指从反面进行否定性的诠释。既然无法从正面来说什么是禅,那么就只能从反面来排除什么不是禅。将这种做法推到极致便是对参禅者不当的发问采取拒斥的态度。由于不能向外求取,所以提问行为本身也就没有意义。我们来看两则禅宗公案:
(1)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汝问不当。”[5]卷二,59
(2)有坦然、怀让二僧来参问曰:“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何不问自己意?”[5]卷二,72
禅师直接指出“祖师西来意”这个问题是不该问的,当然也就不会作出回答。诗“趣”也是这样。“趣”是一种审美体验,无法直接言说。袁宏道在《叙陈正甫会心集》中对“趣”作了如是描述:“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6]463袁宏道一语道出了“趣”不可言说的特性。从本质上看,禅趣与诗趣都不能直接用语言来表述,且都只能以“会心”的方式来感知,二者在这一点上是共通的。
2.禅和诗表达方式的特殊性。由于禅趣和诗趣都是不可言说的,它们的表达自然就需要通过一些特殊的方式和手段,而这些特殊的方式和手段都以“反常”作为最显著的特征。先看禅宗的表达方式。如果说“绕路说禅”的表达方式是为了让人理解,那么禅宗其他的表达方式就显得让人难以琢磨了。试看如下几桩公案:
(3)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汝问不当。”曰:“如何得当?”师曰:“待吾灭后,即向汝说。”[5]卷二,69
(4)集仙王质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青山影里泼蓝起,宝塔高吟撼晓风。”[5]卷二,123
(5)僧问大梅:“如何是西来意?”大梅曰:“西来无意。”[5]卷二,143
(6)江州龙云台禅师,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昨夜栏中失却牛。”[5]卷四,196
(7)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庭前柏树子。”曰:“和尚莫将境示人?”师曰:“我不将境示人。”曰:“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庭前柏树子。”[5]卷四,202
(8)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东土不曾逢。”[5]卷五,272
(9)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道士担漏。”[5]卷六,328
(10)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定州瓷器似钟鸣。”曰:“学人不会意旨如何?”师曰:“口口分明没喎斜。”[5]卷十一,657
面对同样的问题,禅师们的回答却各不相同。但是这八则公案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禅师们非但都没有作出正面回答,而且他们的回答都表现出“反常”的特点。案(5)中禅师所说的“西来无意”看似是对“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这个问题作出了否定的回答,但这个答案显然是不可信的。祖师“西来有意”是众所皆知的,参禅者是因为不知道“西来”有何意才发问的。所以唯一能被人们所普遍认可的解释就是大梅禅师用“西来无意”作答是为了告诉发问者这个问题不该问。案(3)中虽然禅师指出了提问不当,但是他用“待吾灭后,即向汝说”来回答“如何得当”却是不能让人接受的,因为这个荒谬的回答彻底堵死了继续发问之路。案(8)中“东土不曾逢”的回答也是没有意义的,同样也使得发问者无法继续追问。如果说以上三种回答尚能让人理解的话,那么其他几种回答就更让人摸不着头脑了。因为禅师们的回答看起来都是信口乱说的,而且多是不着边际的,他们的回答与问题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比如案(7)是取眼前之物——“庭前柏树子”,而案(4)(6)(9)(10)则是随口说一些与问题不相干的话。虽然很多人都尝试为这些公案作出一些解释,但却多是似是而非,不能令人信服。那么,禅师们给出种种“反常”的回答究竟目的何在呢?笔者认为,禅师们给出“反常”答案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暗示和启发(“我不将境示人”),更不是为了使发问者陷入对自己给出的“答案”的冥思苦想之中,而是为了使参禅者在“绝望”的情境中彻底放弃继续思考,从而回到正确的道路上。“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对于参禅者来说是有意义的问题,但是对于禅本身来说却没有意义,这是禅师们采用“反常”的方式来进行回答的根本原因。从这个角度看,“反常”是禅宗的一种表达策略。禅的性质决定了对禅的体悟不依赖理性和逻辑,因而不能采用正面的劝导或直接告诉参禅者答案的方式,正常的思维方式有违禅的本质。日本学者铃木大拙对禅的这一特点进行了描述:
在禅中,依靠师傅的说明引导弟子得悟是不可能的吗?悟完全不能作知的解剖吗?禅对未开悟的人来说,是无论怎样说明、怎样论证也无法传达的经验。如果可以分析,依靠它使不知悟的人完全明了,这就不是悟了。因为这种悟已变为不成其悟的概念,禅也不再是经验了。[7]96-97
可见,禅师们的奇言异行并不是为了奇而奇、为了怪而怪,奇和怪只不过是一种言说方式,诗歌亦是如此。从根本上说,诗歌的创作并不以传达知识为根本目的,一些说理诗就因为枯燥乏味而被斥为“理障”,如胡应麟在《诗薮》内编卷二云:“程、邵好谈理,而为理缚,理障也。”[8]39另外还有一些诗歌作品因一味追求形似而缺乏情趣和生气也颇受指责,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中就曾说过:“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9]卷二十九,1525诗的价值在于使人领会其中的审美情趣和韵味。诗歌要想走出淡然寡味的藩篱、具有鲜活的艺术生命力就必然会走上“反常”的道路,从而突破文字表面,产生奇妙的审美效果。从“反常”这一点上看,诗与禅也是一致的,这是由禅和诗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是不得不为之的结果。
3.禅与诗判断标准的相似性。前文说过,“反常”如果失去了“合道”的制约就会流于荒诞,禅与诗莫不如此。苏轼曾明确反对禅宗的呵佛骂祖等极端行为以及由此带来的狂怪之风,他在《书楞伽经后》中就曾批判过“近岁学者各宗其师,务从简便,得一句一偈自谓了证,至使妇人孺子,扺掌嬉笑,争谈禅悦……余波末流,无所不至,而佛法微矣”[1]卷六十六,2085的现象。所以,“反常”的合理性必须经由“合道”来检验。由于本质和言说方式的特殊性,禅的“合道”与否是不能用寻常的理性判断和逻辑推理来裁定的。在禅宗这里,一种言行可能或对或错,也可能既对又错,还可能是因人而异,同样一句话在这个人身上是对的,在另一个人身上可能就是错的。禅师的回答只对发问者负责,答案的正确与否并未被考虑,此所谓“应机问答,杀活临时”[5]卷十六,1069。例如:
逾旬,果天龙和尚到庵,师(案:指俱胝和尚)乃迎礼,具陈前事。龙竖一指示之,师当下大悟。自此凡有学者参问,师唯举一指,无别提唱。有一供过童子,每见人问事,亦竖指祇对。人谓师曰:“和尚,童子亦会佛法,凡有问皆如和尚竖指。”师一日潜袖刀子,问童曰:“闻你会佛法,是否?”童曰:“是。”师曰:“如何是佛?”童竖起指头,师以刀断其指,童叫唤走出。师召童子,童回首。师曰:“如何是佛?”童举手不见指头,豁然大悟。[5]卷四,250-251
鼓山来,师作一圆相示之。山曰:“人人出这个不得。”师曰:“情知汝向驴胎马腹里作活计。”山曰:“和尚又作么生?”师曰:“人人出这个不得。”山曰:“和尚与么道却得,某甲为甚么道不得?”师曰:“我得汝不得。”[5]卷七,396
同样是回答“如何是佛”这个问题,俱胝和尚通过竖手指来应对就是“合道”的,童子竖手指则不“合道”。俱胝和尚看到天龙和尚竖手指便“当下大悟”,童子则是在断指之后才开悟。同样的言行有对有错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得汝不得”。可见,是否“合道”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如果一定要找一个衡量标准的话,那就只能是看相关言行的发出者是否真正对“禅”有所领悟。这种领悟也是体验性的,同样不能用语言来描述,只有真正切身体认到的人才能作出会心的回应,如同“世尊拈花,迦叶微笑”[5]卷一,10的故事。诗歌亦然。一首诗要想取得奇妙的审美效果,除了依靠种种艺术表现手法实现“反常”以外,同样离不开“合道”的制约。艺术中的“合道”指的是符合艺术规律和审美心理,但是,所谓的艺术规律和审美心理也依然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与法度和规则不同,真正的美只能依靠读者的切身体验来感受,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更不能用某种固定的理论来检验。中国古代的诗文评点只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美”“妙”“奇”一类的判断,却很少说缘何而美、妙在何处。这绝不只是文艺批评的习惯问题,而是因为美妙之处需要读者的会心体悟,是无法言说的。可见,诗与禅的判断标准——“合道”同样是相通的。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禅趣和诗趣只能体悟、不可言说的性质决定了它们的表达方式都必须包含“反常”的因素。两者虽然都不是为了奇而奇,但却都“以奇趣为宗”。虽然都是一反常情常理,但合理性又都在于“合道”。禅宗公案中所记录的言行因“反常合道”而为后人所津津乐道,诗歌也因“反常合道”而饶有趣味,二者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同时精通诗歌和禅学的苏轼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才会把“反常合道”应用于诗学领域。苏轼在《书焦山纶长老壁》中谈到了自己的参禅经历:
法师住焦山,而实未尝住。
我来辄问法,法师了无语。
法师非无语,不知所答故。
君看头与足,本自安冠屦。
譬如长鬣人,不以长为苦。
一旦或人问,每睡安所措。
归来被上下,一夜无著处。
展转遂达晨,意欲尽镊去。
此言虽鄙浅,故自有深趣。
持此问法师,法师一笑许。[9]卷十一,552
苏轼向法师问法,法师不回答,其原因是不知道如何回答,因为佛法、禅法是不可言说的,一旦回答便开口即错。只有当苏轼自己得悟以后,法师才许以一笑。苏轼对“诗趣”的理解同样深刻。苏轼看到对“诗趣”的体悟同样不依赖他人的说教,而是靠读者的切身感悟。同时精通禅与诗的苏轼发现了二者的共通之处,故而借“反常合道”来论诗“趣”。
二、“随物赋形”
“随物赋形”可以说是苏轼的所有诗学命题中最具特色的。苏轼借水没有固定的形态、随地势的变化来改变自身形态的特点对自己的创作体验作出了生动形象的描述,其《自评文》云: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1]卷六十六,2069
“随物赋形”表现在苏轼的诗文中便是在自然流畅的气势之中充满了曲折变化。这一方面固然与苏轼在创作中所使用的顺逆、虚实、反正相间等表现手法有关,但从根本上说,苏轼诗文中灵感和新意随地涌出、将一意翻作几意的章法结构以及表意层叠往复的效果与他所采取的观照方式是密不可分的。
周裕锴先生在《宋代诗学通论》一书中通过比较提出:“禅定式的观照是‘不将亦不迎’,任‘万象自往还’,如明镜,如古井,如澄潭,更宁静,更超然,更客观;而道家式的观照是凝神于物,‘其身与竹化’,或是‘其神与万物交’(《苏轼诗集》卷七十《蜀李伯时山庄图后》),相对显得投入、参与、主动一些。……就宋代而言,前者多见于诗论,后者多见于画论。”[10]363这个特点在苏轼的诗论中有着明显的体现。苏轼用“随物赋形”来批评自己的诗文,却不用它来论画①;他屡次使用道家“凝神”“虚静”等观念来论绘画创作,却鲜用它们来论文学。“随物赋形”的创作方式要求创作主体在立意取境以及创作之时随机应变,将自己即时的想法写进作品之中,而不是严格按照预先构思好的内容来表情达意。这种方式与佛教的认知方式以及禅宗的参悟方式十分相似。下面就佛教思想对苏轼观照方式的影响作一简要的分析。

2.禅宗“随缘自适”“逢场作戏”等独特的参悟方式对苏轼创作的影响。禅宗观照外在世界讲求“触目而真”“随缘自适”。《楞伽师资记》记载了禅宗的四祖道信语“亦不念佛,亦不捉心,亦不看心,亦不计心,亦不思惟,亦不观行,亦不散乱。直任运,亦不令去,亦不令住。独一清净,究竟处心自明净”[13]85册,1286的修行和参悟方式。这种观念对后世的禅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无论是南宗禅还是北宗禅,都不乏阐发这种认识论和修行方式的论断。《景德传灯录》卷第二十八载洪州禅的始祖马祖道一云:“法身无穷,体无增减。能大能小,能方能圆。应物现形,如水中月。滔滔运用,不立根栽。不尽有为,不住无为。”[13]51册,440由于法身是“应物现形”的,所以对“诸法”的观照就应该是随时随地的——“诸法不出于真如,行住坐卧悉是。不思议用,不待时节”[13]51册,440。宗密大师《大方广圆觉经疏》卷三以“触类是道而任心”[14]14册,557a来概括洪州禅的这种思想。对于参禅者而言,即时的所见、所闻、所感莫不是禅的显现,因为法身和般若是随时显现、无处不在的。如《景德传灯录》卷第二十八中所云:“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13]51册,441所以必须采用“随缘自适”的观照方式,而不应主动向外界求取,故《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中有“向外作工夫,总是痴顽汉。尔且随处作主,立处皆真”[13]47册,498之说。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苏轼的“随物赋形”说与禅宗的这种观念是非常相似的。苏轼在《送参寥师》中曾说过:“颓然寄淡泊,谁与发豪猛。细思乃不然,真巧非幻影。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9]卷十七,906-907苏轼认为“空”和“静”是“诗语妙”的前提。他还在《朝辞赴定州论事状》中说:“处静而观动,则万物之情必陈于前。”[1]卷三十六,1019其《书王定国所藏王晋卿画〈著色山〉二首》其一亦云:“我心空无物,斯文何足关。君看古井水,万象自往还。”[9]卷三十一,1639苏轼多次强调“空”和“静”的重要性,这与禅宗认为参禅必修清净之心的主张是颇为相似的。苏轼的“随物赋形”说注重直觉在创作中的作用,以即景会心的观照方式把握事物,立意取境随机应变,这与禅宗的“应物现形”等观念也同出一辙。
苏轼一生与佛教结缘甚深。据黄学明在其博士论文《东坡与佛教》中考证,苏轼一生中至少读过《楞严经》《金刚经》《法华经》《坛经》《心经》《涅盘经》《楞伽师资记》等近二十部佛典以及《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等多部禅宗语录[15]34-42。苏轼出生在一个有浓厚佛教信仰气氛的家庭中。受母亲等人信佛的影响,苏轼小时候就阅读了很多的佛教经典,还与很多僧人有过交往。苏轼步入仕途以后,尤其是贬谪黄州期间,他的思想和创作都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并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其弟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所说:“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16]1127这样的经历和遭遇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佛教的很多基本观念,如“现量”观等以及禅宗“触目而真”“随缘自适”的思想对苏轼的文学观念和创作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他借自己所熟知的佛教思想来论文学就不足为怪了。
三、“物无陋者”
苏轼《送钱塘僧思聪归孤山叙》云:“古之学道,无自虚空入者。轮扁斫轮,伛偻承蜩,苟可以发其巧智,物无陋者。”[1]卷十,326苏轼所说“物无陋者”并不是在无原则地抹杀“美”与“丑”之间的界限,而是强调“物无陋者”应以“可以发其巧智”为前提,也就是说该事物在“求道”的过程中应能够给人以启发。其《超然台记》亦云:“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哺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1]卷十一,351苏轼认为所有的事物只要“有可观”“有可乐”,也就都有其自身的价值,而不必计较其外在形式的美与丑。“物无陋者”和“物皆有可观”的思想既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认识论,同时又可以在审美领域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苏轼在《次韵子由论书》中说:“貌妍容有矉,璧美何妨橢。”[9]卷五,210苏轼认为“丑”(“矉”“橢”)的存在并不会妨碍到作品的“美”,“丑”有些时候恰恰是“美”能够存在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又如他在《答李端叔书》中所说:“木有癯,石有晕,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1]卷四十九,1432苏轼指出了“妍”的显现恰恰在于“病”的存在。“病”“丑”“怪”在表面形式上固然是丑陋或是有缺陷的,但这些因素对美的构成却又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丑”和“病”往往就是该种事物与众不同之处的体现,也就是其“奇”“趣”之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判断一种事物的美丑并不能仅从外形的“丑”和“病”来得出结论,而是要深入审视“丑”和“病”之中所蕴含的美的价值。也就是说,在审美领域,美和丑是相对的。
如上所述,苏轼发现了在艺术审美领域“丑”的相对性,同时还揭示出了以审美的眼光观照外形丑怪的事物往往会获得独特的审美效果。但是苏轼并不是无原则地追求新奇丑怪,他在《题柳子厚诗二首》其二中便提出了“好奇务新,乃诗之病”[1]卷六十七,2109。他在《谢欧阳内翰书》中也说过:“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1]卷四十九,1423苏轼深知怪奇风格发展到极端就会走入“怪僻而不可读”的歧途。这在苏轼对孟郊、贾岛诗歌的批评中有着鲜明的体现。苏轼指出孟郊、贾岛为了追求“新奇”“险怪”而采用的“苦吟”的作诗方式不可避免地带来其诗歌的气象狭窄局促等诸多弊端,故东坡在《祭柳子玉文》中评孟郊、贾岛诗云:“郊寒岛瘦。”[1]卷六十三,1939《读孟郊诗二首》其一亦云:“何苦将两耳,听此寒虫号。”[9]卷十六,797除了表达出对孟郊、贾岛诗风的不满意之外,苏轼还在《赠诗僧道通》中借对诗僧道通诗风的赞赏明确地提出了自己所推崇的风格:
雄豪而妙苦而腴,只有琴聪与蜜殊。
语带烟霞从古少,气含蔬笋到公无。
香林乍喜闻薝蔔,古井惟愁断辘轳。
为报韩公莫轻许,从今岛可是诗奴。[9]卷四十五,2451
可见,苏轼所欣赏的诗风是以“雄豪”为主,在此基础上融“雄豪”“妙”“苦”“腴”等多种因素于一体。苏轼认为过分追求艰涩怪奇、为了奇而奇、为了怪而怪的人只能成为“诗奴”。结合苏轼的创作看,其诗歌中虽然不乏丑怪的事物,新奇意象也屡见不鲜,但是呈现出的却是雄浑阔大的气象。诚如敖陶孙《诗评》所云:“宋朝苏东坡如屈注天潢,倒连沧海,变眩百怪,终归雄浑。”[17]这是因为苏轼从未以搜奇抉怪为写诗的目的,而是只把它们当成表情达意的手段。苏诗的“雄豪”之气发自胸臆,所以无论是丑怪意象的使用还是怪奇风格的创造,都是不得不为之的产物,诚如他自己在《答黄鲁直》中所说的“凡人文字,当务使平和,至足之余,溢为怪奇,盖出于不得已尔”[1]卷五十二,1532。相反,如果把写丑当成创作的目的则是本末倒置,就会破坏作品应有的美感。这是“以丑为美”的前提和原则。
苏轼的“以丑为美”同样也深受佛教的影响。前文说过,苏轼对佛教有很深的研究,他不仅研读了大量的佛教经典,还对佛教艺术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佛经中以地狱为代表的血腥、恐怖场景,其间充斥了大量的对丑怪形象、事物的描写和刻画。黄修复《益州名画录》“张南本壁画评语”说佛教绘画中“千怪万异,神鬼龙兽,魍魉魑魅,错杂其间”[18]。无论是佛经还是佛画,都不是为了表现恐怖而描写各种恐怖事物的,佛经、佛画中刻画种种丑怪、恐怖的事物是宣讲佛理的需要,因而就具有了美的内蕴,这与艺术领域中的“以丑为美”是异曲同工的。另外,吴道子是苏轼颇为欣赏的画家之一,他就是以画地狱变相见长的。《宣和画谱》卷二说吴道子“世所共传而知者,惟地狱变相”[18]。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中记载了这样一则关于吴道子画地狱的传闻:“见之而惧罪改业者往往有之。”[18]吴道子等人佛画中的丑怪形象和恐怖场景也从侧面对苏轼的“审丑”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在探讨苏轼“物无陋者”这个诗学命题的时候不能不谈佛教的影响。
通过对上述三个诗学命题的研究可以发现,佛教思想对苏东坡文艺思想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佛教的基本观念、认识论,尤其是禅的本质、不可言说性、判断标准、认知和观照方式,以及佛经中对丑怪事象的描写乃至佛教的绘画、造像艺术等方面都对苏东坡的文艺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所研究的三个诗学命题仅是这个大问题之一隅,希望能够起到“举一隅而以三隅反”的作用。
注释:
① 苏轼另一处涉及“随物赋形”的艺术批评见于他的《画水记》(又作《书蒲永生画后》,《苏轼文集》卷十二,第409页):“唐广明中,处逸士孙位始出新意,画奔湍巨浪,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尽水之变,号称神逸。”这里的“随物赋形”所论的是水的特点,而并非绘画创作活动本身。这段论述与创作活动本身并无关联,故本文未加采用。另外,笔者认为,道家与“随物赋形”有关的思想对苏轼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生观方面,而非文学方面(详见高云鹏《苏轼“随物赋形”说新论》,《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第119—126页)。
[1] 苏轼.苏轼文集[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2] 柳宗元.柳宗元集(卷四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 周裕锴.文字禅与宋代诗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4] 杜松柏.禅学与唐宋诗学[M].台北: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6.
[5] 普济.五灯会元[M].苏渊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
[6] 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卷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7] 铃木大拙.禅学入门[M].谢思炜,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
[8] 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9] 苏轼.苏轼诗集[M].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
[10] 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1] 渥德尔.印度佛教史[M].王世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12] 方立天.佛教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13] [日]高南顺次郎,渡边海旭.大正新修大藏经[M].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6-1931.
[14] [日]前田慧云,中野达慧.续藏经[M].京都:京都藏经书院,1905-1912.
[15] 黄学明.东坡与佛教[D].南京:南京大学文学院,2004.
[16] 苏辙.栾城后集(卷二十二)[M].陈宏天,高秀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
[17] 敖陶孙,撰,程兆胤,录.诗评[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
[18] 永瑢,纪昀,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Z].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责任编辑 燕朝西]
On the Buddhism Influence on Su Shi’s Literary Criticism Seen in His Three Poetic Propositions
GAO Yun-peng
(SchoolofInternationalEducation,BeijingSport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Poem’s essence being for interest and interest being unusual butreasonable”“shaping up according to anything encountered”, and “anything being poetic” are the three poetic propositions of Su Shi, from which we can conclude that Su Shi’s literary thought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Buddhism. Many things in Buddhism have exerted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Su Shi’s poetic theory, including the basic concept and the Buddhist epistemology, especially the essence of Zen, ineffability, evaluation standard, and cognitive perspective, and other aspects such as the ugly and strange description in Buddhist works and Buddhist paintings, sculptures, etc. The influence of Buddhism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for Su Shi’s profound and unique poetics.
Su Shi; poetics; thoughts of Buddhism
2016-09-02
高云鹏(1981—),男,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唐宋文学与古代文论研究。
I206.2
A
1672-8505(2016)06-000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