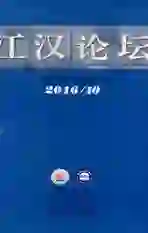哲学的新生
2016-12-09杨虎
杨虎
摘要:基础主义是指这样一种信念:一切存在物及其相应的知识、价值等等都奠定在某种“基础”之上。反基础主义是相反对的信念,认为不存在着万事万物最终奠定于其上的“基础”。传统基础主义表现为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由此反基础主义的核心即在于“拒斥形而上学”,二者都误置了基础,真正的基础并非某种先验设定的“形而上者”,而是原初的存在结构及其领悟。鉴于反基础主义的经验化道路之不可取,而形而上学又是不可避免的,为此需要走新基础主义的道路,不仅要超越传统基础主义而且更要超越反基础主义,进一步寻求形而上学之“后”、之“基础”,这更可以说是反基础主义之“后”、之“基础”。由此,新基础主义道路必须展开“返源”与“立相”(绝对相以及相对相)的双重向度,由“返源”而成“源论”——揭明一切事物之源,并在此基础上“立相”——重建我们时代的“体用论”(形而上学本体论和形而下学)。从而。在新基础主义的“道路”上,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才能并且必将获得“新生”:形而上学观念“生”成于更加先行的“基础”,并植根于我们时代的存在样式而成一种不同于传统哲学的“新”的哲学形而上学。
关键词:哲学;形而上学;新基础主义;反基础主义;传统基础主义
中图分类号:B0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10-0047-07
当前学界流行着诸如“反基础主义”、“拒斥形而上学”这样的口号,其影响遍及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且易于被人们引以为典而不深察。笔者以为,当代哲学对传统基础主义、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形而上学乃是不可避免的,反基础主义的道路并不可取。本文就这一论题做出正面探讨并对其中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予以澄清,由此初步提出在传统基础主义和反基础主义之“后”(同时包涵“基础”义)的今天。我们应当走新基础主义的思想道路。在新基础主义的“道路”上,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才能而且必将获得“新生”。
一、传统基础主义与反基础主义
“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一词来源于美国哲学家罗蒂对传统哲学的批判,意指这样一种信念:存在着某种“知识基础”、“绝对的基础”:“反基础主义”(Anti-Foundationalism)则是作为其对立面的一种信念。学界通常认为“基础主义”是属于现代哲学的,尤其是认识论层面的,而“反基础主义”则是属于后现代哲学的理论倾向,后现代哲学是对现代哲学的批判。这些理解都是非常狭隘的。
1.“基础主义”信念:一切存在物及其相应的知识、价值等等都奠定在某种“基础”之上。
首先,罗蒂从知识论层面展开了对传统哲学基础主义的批判,但传统基础主义并不局限于这个层面。在广泛意义上说,“基础主义”就是这样一种信念:一切存在物及其相应的知识、价值等等都奠定在某种“基础”之上。R·伯恩斯坦的界定是:“存在着或必须存在着某种我们在确定理性、知识、真理、实在、善和正义的性质时能够最终诉诸的永恒的、非历史的基础和框架。这个基础或框架也就是一个‘阿基米德点,基础主义者认为。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去发现这种基础是什么,并用强有力的理由去支持这种发现基础的要求。”
其次,基础主义并不局限于现代哲学,反基础主义也不局限于后现代哲学。类似“现代哲学是对基础的探求:当代哲学则广泛地把这种探求作为错误而加以摒弃”这样的理解是不对的。
其一.古往今来一切哲学形而上学必然是“基础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核心是“本体论”(ontol-ogy),是关乎“本体”这种“形而上者”的思考,它要解决的是一切形而下的存在物之所以存在的“根据”的问题。这进一步决定了关乎形而下存在物的知识、价值等等;相应地,形而上学乃是“知识论”、“伦理学”、“价值论”等等的“基础”。这是一切哲学形而上学的基本思路:“形而上者”为“形而下者”奠定“基础”,形而上学为形而下学奠定“基础”。
其二,“反基础主义”并不局限于“后现代哲学”。后现代哲学拒斥形而上学、反对理性中心主义,反对本质主义等等,这些都是“反基础主义”的具体表现。由这些表现来看,哲学史上某些怀疑论、经验论思想也具有“反基础主义”性格,因为它们同样拒斥形而上学、反对本质主义、反对理性中心主义。当然,后现代哲学的“反基础主义”对于传统哲学的冲击是最大的,故而我们的讨论材料集中于此。
其三,后现代哲学的“反基础主义”信念和理论倾向并不仅仅是对现代哲学的批判,而是对整个传统哲学的批判,因为传统形而上学都是“基础主义”的。为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厘清传统基础主义之历史展现。
2.传统哲学基础主义的历史展现
首先,关于“世界”、“本质”的预设和信念。可以说,没有基础主义信念就没有哲学。哲学开端于早期形而上学的建构,由此,哲学在本质上就是形而上学,即关乎“形而上者”、“存在者整体”的思考,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哲学即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着眼于存在,着眼于存在中的存在者之共属一体,来思考存在者整体——世界、人类和上帝。”这样的思考旨在说明,一切形而下存在者是何以可能的。例如柏拉图有个著名的说法“拯救现象运动”。按照它的理解,现象是变动不居的,为了说明现象的存在.就需要寻求其背后的存在根据。柏拉图认为,现象世界是对理念世界的募仿:“一件事物之所以能开始存在,无非是由于它分沾了它所固有的那个实体。”理念世界由各种等级、层次的理念组成,最高的理念是“善”理念,也就是世界的“本原”、“基础”。
反基础主义者罗蒂认为:“自希腊时代以来,西方思想家一直在寻求一套统一的观念,这种想法似乎是合情合理的;这套观念可被用于证明或批判个人行为和生活以及社会习俗和制度,还可为人们提供一个进行个人道德思考的框架。‘哲学(爱智)是希腊人赋予这样一套映象现实结构的观念的名称。”这个说法不无道理,类似“善”和“正义”的理念就是为了给现实世界中的价值判定和伦理秩序提供形上学的说明,或者说提供一个“合法的”“地基”(康德语)。不惟西方哲学,中国哲学也是如此,例如王弼的“本末”论。王弼在《老子指略》一文中指出:“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这乃是王弼对老子思想的一种理解:“无”是世界的本体。是“母”。是一切相对的、形而下存在者“子”的存在根据。“守母以存子”,质同于“拯救现象运动”。要而言之,中西哲学形上学关于世界及其本质、本体的思考,是“基础主义”的一种展现。
其次,关于“上帝”或“天”的预设和信念。神性形而上学关于“上帝”或“天”的言说也是如此。西方宗教哲学中的“上帝”,被视为万事万物的“基础”,没有“上帝”就没有一切。这就是对世界本体的一种神性化言说。例如,关乎人类生活的伦理规范“摩西十诫”被看作是上帝所规定的。中国哲学中也有类似的神性形而上学的言说,例如董仲舒的“天”论。为了给形而下的伦理规范“三纲”提供合法性说明,董仲舒以“天”、“天道”作为“基础”来说明:“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春秋繁露·顺命》)按此,形而下的社会伦理秩序是以“天”、“天道”为“基础”所推衍出来的先验结构.因而具有“先天的合法性”。毫无疑问,这些神性形而上学的言说也是“基础主义”的。
再次,关于“主体性”或“心性”的预设和信念。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哲学之事情就是主体性。”“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之事情乃是存在者之存在,乃是以实体性和主体性为形态的存在者之在场状态。”海德格尔的这一评论所直接针对的是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绝对即精神”。黑格尔说:“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实体是能动的,所以同时也是主体,二者其实是一个东西——(绝对)精神——的二重性,真理就是精神从实体转化为主体的历程。因此,世界就是“现象诸历程”、“意识诸形态”,是绝对的自身展现。这种绝对主体性就是世界的“本质”、“基础”。中国哲学关乎“心性”的言说,例如宋明理学的心性论也是“基础主义”的。李泽厚先生认为:“宋明理学是一种伦理学主体性的本体论。”这个表达并不确切。宋明理学的心性本体论确乎是一种主体性哲学,但不是伦理学层面上的东西,而是旨在为伦理学提供“基础性”说明的形上学。例如,周敦颐的“诚”本体论,诚作为心性本体,它乃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换句话说,形而下的伦理规范是以“诚”为“基础”推衍出来的。这显然是“基础主义”的思路。
要而言之,传统哲学关乎“世界”及其“本质”、“上帝”或“天”、“主体性”或“心性”这些“形而上者”的思考和言说都是旨在为一切事物提供先验的“基础”,都是“基础主义”的。
3.“反基础主义”信念:不存在着万事万物最终奠定于其上的“基础”。
反基础主义是与基础主义相反对的信念和理论倾向。既然传统哲学形而上学都是“基础主义”的,那么反基础主义自然“拒斥形而上学”、“拒斥本体论”。这尤其是后现代哲学中反基础主义的明确口号。例如德里达对“在场形而上学”的批判。德里达吸收了海德格尔的相关思想,认为传统存在论把“存在”理解为“在场”,并进一步把握为诸如“真理”、“理念”、“实体”等。德里达认为这与“逻各斯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是不可分割的:“对真理的一切形而上学规定,直接与逻各斯的理性思维密不可分。”为此,德里达提出了“延异”思想,以期消除一切“第一性”的东西。要言之。德里达拒斥具有同一性的“基础”以及被进一步把握为“逻各斯”、“真理”、“实体”的东西。因为所有这些“同基础、原则或中心联系在一起的名字都指定了一个永恒的在场”。
再例如,罗蒂虽然没有直接从“形而上学”的角度对基础主义展开批判,但在他的言说中认识论的即是形而上学的,他明确反对“认识论一形而上学基础”:“我们应当摒弃西方特有的那种将万事万物归结为第一原理或在人类活动中寻求一种自然等级秩序的诱惑。”由此,罗蒂提出了“后哲学文化”,主张以一种“教化哲学”代替“系统哲学”、“大哲学”.这意味着在“后哲学”时代建立“形而上学体系”是不必要也是不可能的了。从这种观点来看,任何试图再建立作为科学、伦理学等形而下学基础的“形而上学大厦”(康德语)都将是不合法的,正如利奥塔说的:“大叙事失去了可信性”。
要而言之,反基础主义是这样一种信念:不存在着万事万物最终奠定于其上的某种“基础”,所以“拒斥形而上学”是反基础主义的核心信念和理论倾向。
二、传统基础主义与反基础主义对“基础”的共同误置
由上可知,无论是传统基础主义还是反基础主义对“基础”的理解都局限于某种“形而上者”。这其实是对“基础”的误置。事实上,传统基础主义把某种“形而上者”视作一切事物的“基础”,并不意味着发现了真正的“基础”。同理,解构传统形而上学并不等同于要解构“基础”和抛弃基础主义信念。例如,海德格尔哲学既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一种解构,同时也是一种重返“基础”的思考。海德格尔并不反对也从未停止过对“基础”的追思,毋宁说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基础主义”者,他所反对的乃是以某种“存在者整体”、“形而上者”为“基础”的传统形而上学,认为传统存在论是“无根”(无基础)的存在论。所以,海德格尔企图通过对“存在问题”的重新发问,建构为形而上学奠定基础的“基础存在论”。
无论是汉语观念中的“基础”还是其所对应的“Foundation”一词,都是很形象的说法,都包涵了建筑物的“地基”这一意思。例如《水经注》云:“今碑之左右,遗墉尚存,基础犹在。”这本来表示建筑物的地基,可以引申为事物的根本、基础。所以康德曾经有为形而上学打“地基”的形象说法,如果说形而上学好比一座大厦,那么形而上学的基础就好比说是这座大厦的“地基”。当我们“查看”形而上学这座大厦的地基时,就意味着我们在寻找关乎“形而上者”思考的形而上学之基础,这已然超出了形而上学的视域。其实海德格尔正是沿着康德的思路在走,撇开此在的生存论进路,他提出的存在领悟确乎是一切存在者的基础。这是因为,一切有分别相的存在者是从原初的存在领悟中脱身而出的。在我们的观念呈现中,未分判的存在领悟总是先行的,只有当我们从其中挺立而出成为一种主体性存在者时,才有种种的分别,由此对象化才是可能的。例如,科学所需要的“主一客”架构便由此产生,它乃是奠基于原初存在领悟的。当我们置身于这种存在者化、对象化生活,再对其进行反思时,便会有形而上学的追问,这种“主—一客”架构是何以可能的?由此,我们预设某种绝对的主体性,亦即某种“形而上者”。秉持着这种信念,我们认为,关乎形而下存在者的知识论、伦理学等奠基于关乎形而上存在者的形而上学。不难理解,所谓的形而上学其实就是对原初存在领悟的一种本体化把握,从某种角度说,它仍然是对存在领悟的“存在者化”的把握。在这个意义上,传统基础主义对“基础”的把握并不彻底,它没有进一步还原到自身的“地基”。同样,反基础主义所反对的也正是这种被误置的所谓“基础”,亦即某种自身亟待奠基的“形而上者”。这和传统基础主义一样是对基础的误置。反基础主义的积极意义在于揭示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危机,但并未超越它而反倒陷入了某种经验化立场。
首先,“反基础主义”仍然是以“基础主义”为标准的。所谓边缘化、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等等,其实是以中心化、逻各斯中心主义等等为标准的。这就犹如海德格尔说的:“什么叫做非理性的观念?这只能根据一种理性的观念来界定。”这仍然没有摆脱罗蒂等人自己所批评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其次,反对先验的设定而走向经验化思路,就会陷入“认识论困境”。正如胡塞尔所揭示的:“在客观科学那里存在着超越的可疑,问题是:认识如何能够超越自身,它如何能够切中在意识框架内无法找到的存在?”反基础主义者拒绝哲学为认识和科学提供“合法化元叙述”,认为知识和科学的合法性“是一种通过事实达到的合法性”。显然,这种“事实”乃是经验性的,但它是如何“切中”自身的“事实”的呢?反基础主义并不追问这样的问题,毋宁说他们根本置这些问题于不顾,这在罗蒂的相关思考中也可见一斑。尽管罗蒂说他吸收了现象学尤其是海德格尔的思想,但在对待这个问题的思路上与现象学、海德格尔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众所周知,胡塞尔现象学的两大问题:欧洲科学的危机和人性的危机,在海德格尔那里都有延续:科学奠基问题和主体性奠基问题。并且,二者最终都收摄在主体性奠基问题上。在海德格尔看来,为主体性奠基就是要对“人之有限性本质”做出“存在论上的分析”。此即他所说的存在问题的首要目标“不仅在于保障一种使科学成为可能的先天条件(科学对存在者之为如此这般的存在者进行考察,于是科学一向已经活动在某种存在之领会中),而且也在于保障那使先于任何研究存在者的科学且奠定这种科学的基础的存在论本身成为可能的条件”。如果说一般存在论为科学奠定基础,那么基础存在论就是为一般存在论奠定基础。这种基础存在论被海德格尔规定为关乎人之有限性的生存论。罗蒂对海德格尔的“有限性”思想有所吸收,但并未因此走向“生存论”进路,而毋宁说走向了被海德格尔视为“流俗化”的经验化道路。作为一位自觉的实用主义者,罗蒂提出在“后形而上学”时代以“希望”代替“知识”的“新实用主义”:(1)没有与实在相符合的真理;(2)没有本体或本质的世界;(3)没有原则的伦理学。显然,这些都是经验化的思考和言说。罗蒂明确表示拒斥本质、本体的预设,这集中体现了他的拒斥形而上学的立场,在知识和价值、伦理问题上也主张不从某种“基础”或“原则”出发。然而没有本体的世界即使依然成立为一世界,但却会是一个无从安立的世界,没有存在者整体之存在的承诺,我们关于万事万物的言说将是不可能的:没有与实在相符合的真理则科学将不具有客观性(普遍必然性);没有原则,伦理学亦能成立,但却可能是动物性的丛林法则。
总之,传统基础主义主要表现为哲学形而上学,反基础主义主要表现为拒斥形而上学;而无论是传统基础主义还是反基础主义都误置了“基础”;并且,当前的反基础主义道路并不可取。故我们今天应当走一条新基础主义道路:解构传统哲学形而上学,寻找更加本源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重建我们时代的哲学形而上学以及奠基于其上的伦理学、知识论、价值论等形而下学。
三、新基础主义道路的思想视域:返源一立相
新基础主义(Neo-Fundationalism)承认反基础主义对传统形而上学批判的积极意义,但并不因此就走向“拒斥形而上学”的道路,而是进一步追问形而上学的“基础”——为形而上学及以其为“根据”的形而下学奠定“基础”。这即是说,我们不仅要通过解构形而上学而发现真正的“基础”,还要在此基础上重建形而上学、形而下学。相应地,这就意味着首先从“存在者”返回到“存在本身”,其次在此基础上重新给出一切存在者(形而上存在者、形而下存在者),笔者曾把这两种向度称之为“返源”与“立相”。
“返源”的任务所指向的不仅是从形而下存在者返回到形而上存在者,而且要返回到一切存在者的“基础”。由此,在这个层级上的言说构成“源论”。“立相”的任务不仅是要给出一切形而下存在者,也要给出作为本体的形而上存在者,即不仅要挺立“相对相”也要挺立“绝对相”,这两个层级的言说构成“体论”(形而上学本体论)和“用论”(伦理学、知识论、价值论等形而下学)。自奠基序列言之,此即“源→体→用”的观念构成。这就意味着哲学的“新”“生”:通过“返源”,发现了“形而上者”及其所给出的“形而下者”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得以“生成”;但它不同于传统哲学,而是植根于我们时代存在样式的“新”的哲学。
1.哲学即形而上学,其核心是本体论。
新基础主义道路并不是“哲学的乡愁”,因为它理解的“基础”超越了形而上学的“根据”,而在一个狭义的定义上,哲学就是形而上学。不仅基础主义者如海德格尔曾经下过这个判断,反基础主义者也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例如罗蒂同时有“后哲学文化”和“后形而上学”的提法,在他的语境中,“哲学”就是“形而上学”。
从西方哲学来看,“形而上学”(metaphysics)与“哲学”(philosophy)的渊源也可验证这一点。metaphysics一词出自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其原意是“物理学之后”,亚氏去世之后200多年,编者将亚氏著作当中讨论超越经验以外对象的若干卷安排在《物理学》一书之后,汉译本叫做《形而上学》。亚氏认为,“第一哲学”讨论的对象乃是“作为存在的存在”:“我们应当把握的是作为存在的存在之最初原因。”但这里说的“存在”与海德格尔的理解不同。因为在亚氏看来不管存在有多少种意义,“全部都与一个本原相关”,这个本原就是实体,所以“哲学家应做的事就是掌握实体的原因和本原”。在亚氏看来,哲学(形而上学)的任务就是对“实体”的追问,从而,“作为存在的存在”被把握为“实体”。虽然海德格尔批评亚里士多德混淆了存在与存在者,其所谓“作为存在的存在”只不过是“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但这仍然反映出对某种原初“实体”、“本体”的追问乃是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之核心所在,这就是本体论。
中国哲学的“形而上”一词也是对某种终极实体、本体的描述。古代中国并无“形而上学”一词,但有“形而上者”一词,例如《周易·系辞上传》:“形而上学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所谓“形而下者”就是指一切相对的、形而下的存在者,“形而上者”则是指作为一切形而下存在者之根据的绝对的、形而上的存在者,这在中西哲学中被把握为诸如“本体”、“实体”、“存在者整体”等等,所以汉语“形而上学”即关乎“形而上者”的思考和言说,这正对应于西语“metaphysics”一词的涵义。无论是汉语的“形而上学”还是西语的“metaphvsics”其核心都是关乎这种“形而上者”的追问,亦即“本体论”(ontology)。
尚需提及的是,“meta”这个前缀,汉语可以翻作“元”或者“后”。“元”字本义为“首”,引申为“本来”、“开端”、“基础”等意思,例如“元犹原也”(《春秋繁露·垂政》);再如“元初”、“元气”、“元始”等说法也都体现了这一点。这正对应于,如果说“physics”乃是作为“自然学”的形而下学,那么“meta”所指向的乃是作为形而下学“基础”的形而上学,即亚里士多德的所谓“第一哲学”。同样,“meta”也可以翻译为“后”。“后”的本义正是“元”的引申义之一“君主”,例如《尚书·尧典》:“班瑞于群后”;《诗经·周颂·时迈》:“允王维后。”“君主”在当时的语境中又称为“首”、“元”,这正对应于一种形象的说法:形而上学乃是一切科学的“女王”(康德语)。罗蒂说的“后哲学”、“后形而上学”并不是这种意义上的“后”,他使用的不是“meta”而是“post”,这对应于汉语的时间次序在后的涵义。今天的诸多“后……”的提法,例如“后现代主义”的“后”也是“post”而非“meta”,这说明,它们都缺乏更加本源的思想视域。
2.形而上学本体论不可避免
之所以要“返源”,即返回到形而上学之“后”、“基础”、“源”,一方面是因为反基础主义道路之不可取,另一方面是由于形而上学本体论不可避免。
首先,对存在者领域、“形而下者”的言说必然包涵了对“存在者整体”、“形而上者”的承诺。就此而言,笔者认同黄玉顺先生的一种解释:“形而上学之所以是必然的,根本原因乃在于人类思想观念之构造的一种内在的逻辑承诺:对任何一个存在者领域之存在、甚至对任何个别存在者之存在的承诺,都已蕴涵着对存在者整体之存在的承诺。”其实蒯因的“本体论承诺”(Ontological Commit-ment)也触及到了这一点。蒯因认为任何理论陈述都有它的“本体论承诺”,亦即关于“言说中何物存在”的承诺。这里需要注意的是:(1)本体论承诺旨在把本体论问题转化为语言哲学问题。作为一位分析哲学家,蒯因的“本体论承诺”思想是旨在消解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问题的,蒯因把本体论的“事实问题”简化为“事实上何物存在”并予以悬搁,主张从“承诺问题”出发,把本体论问题转化为一个语言学问题:“当我探查一个给定学说和理论的本体论承诺时,我只是问根据那个理论存在什么。”亦即,本体论的承诺问题局限在理论陈述层面。(2)本体论承诺直接指的并不是对某种“存在者整体”、“本体”的承诺,而只是作为理论陈述所涉及对象的“某物存在”。“某物”既可能是形而下存在者,也可能是形而上存在者例如“上帝”、“本体”等等。尽管如此,当我们陈述形而下存在者时总还是可以追溯到形而上存在者,因此,本体论承诺非但不能消解形而上学本体论问题,反倒是从语言哲学层面证明了它的必然性。
其次,形而上学本体论并不仅仅是一个语言、陈述的理论设定问题,它乃是渊源于我们的存在领悟,是对存在领悟的本体化言说。古往今来,这种本体化言说主要表现为神性化的和理性化的,由此而产生了神性形上学(宗教)和理性形上学(哲学)。而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形而上学本体论不断地被解构、建构,就是由于每个时代的存在方式及其领悟有所不同。例如奥古斯丁的“上帝”、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董仲舒的“天”、朱熹的“天理”等等,其实都是对他们的存在领悟的一种(神性化或理性化的)本体化表达。我们固然可以批评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遗忘了存在”(海德格尔语),但不能否认它们也是渊源于存在领悟。也就是说,人类两千年来的形而上学本体论解构、建构历程正是对“形而上学不可避免”的事实证明。
再次,关乎相对存在者的形而下学奠基于关乎存在者整体的形而上学。例如,科学需要相应的知识论,而知识论的核心在于范畴表。所谓范畴(Categories),其实就是指的高层级的存在者领域,它必然包涵了对存在者整体的承诺。不仅知识论,伦理学也有它的(广义的)范畴表,例如中国古代的“三纲”、“五常”、“六纪”观念,其实就是指的几种大的伦理范畴、存在者领域。以“五常”为例,仁、义、礼、智、信这几种伦理范畴,在传统儒学的言说中都是有它的形上学根据的。程颢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这里“仁”单提出来说时,就不再是伦理学层级上作为“五常”之一的“仁”了,而是指的“仁体”,亦即形而上的本体。仁体是五常的根据,“义、礼、智、信”,都是由“仁体”所给出的,这表明关乎相对存在者的形而下学奠基于关乎存在者整体的形而上学。
3.返源一立相
形而下学奠基于相应的形而上学,随着形而下学问题的变化,形而上学也在不断变化,此即传统形而上学的解构、建构之历程。所以,尽管形而上学不可避免,但我们今天绝不能延续某种传统形而上学,而是要解构传统的形而上学本体论。为此,我们首先需要“返源”以发现形而下学、形而上学之“源”、“基础”,在这个层级上的言说构成“源论”(Theory of source as Being)。源的本义为水源,引申义为本源、源头,它的古字是“原”,如“原泉混混”(《孟子·离娄下》),此原字又作动词用,意为推究本源、本情,如“原情立本”(《新语·道基》)。通过返源发现一切存在者之源,此源即先行于一切存在者的存在本身。即原初存在结构,源论就是要揭明原初存在结构及其显现样式。着眼于此,能够解释古往今来的形而上学之不断解构、建构的历程:一切存在者都生成于原初的存在结构,而随着其显现样式的变化,关乎相对存在者的形而下学问题也会相应变化,从而需要解构旧的形而上学建构新的形而上学。新的哲学建构总是以某种先行的存在论建构——源论为基础的。
其次,重建我们时代的形而下学及其相应的形而上学。此即给出形而下的相对存在者和形而上的绝对存在者。笔者把这种向度称之为“立相”。立即挺立、绽出的意思,如孟子谓“先立乎其大者”之“立”;相之一词有取于佛教,相有二义:(1)差别的相状,当性与相、体与相相对而言时,意味着某种现象、状态而与本体、本质不同。例如“别相”之谓,这是指的相对之相,对应着相对存在者。(2)等同于本体、本质的“总相”。例如《大乘起信论》谓“心真如者,谓一大总相法门体”,此“总相”即是指“真如之体”,这就是对“存在者整体”、“本体”的规定。再如法藏谓:“总相者,一舍多德故;别相者,多德非一故。”(《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此“总相”即超越差别相的“一真法界”,它对应着某种“存在者整体”、“本体”之绝对相。所以,立相这一向度包涵了立“绝对相”和立“相对相”这两个层级,分别对应着绝对存在者和相对存在者。相应于这两个层级的言说构成关乎本体的体论(形而上学本体论)和关乎相对存在者的用论(知识论、伦理学、价值论等形而下学)。
总而言之,新基础主义道路不仅需要建构体用论,更要以源论为基础。归根结底,所谓“源、体、用”并非是指三个“东西”,而是存在本身各层级的显现样式,这是一而三、三而一的,这就是笔者曾经提出的“切转”之意谓。我们不仅要超越传统基础主义,更要超越反基础主义,惟其如此,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才能而且必将获得“新生”。
(责任编辑 胡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