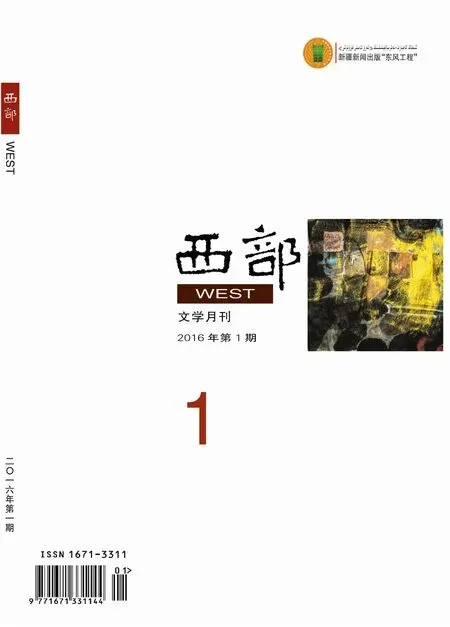饥饿之噎与少更之事
2016-12-07凸凹
凸 凹
饥饿之噎与少更之事
凸凹
一根肠子的狗
人字就是两根肠嘛。是人,都是岔肠子。据说,狗只有一根肠,而狗身上最好吃的东西,就是狗肠。狗肠也是所有肠肴中最棒的肴。人如果真是两根肠子,其中一根,一定去心里边绕了几圈,九里十八弯后,才与另一根肠子会师;或者两根都去绕了,心上心下心心相印地绕成了花花肠子。
一根肠子的狗的耿直我是亲见过的。小时候,我见过邻家男人杀一条老黄狗。邻家男人是这条老黄狗的主人。
狗主人用粗糙的麻绳圈一个篮球大小的活套,提拎在手上,将麻绳另一端抛上一棵歪脖子核桃树耷拉下来,然后吆唤他家老黄狗把头颈伸进麻绳活套圈中。老黄狗明白主人意思,就摇头摆尾小跑过来,乖乖把头颈伸入套中。狗主人立即提拎绳子,不料套没系好,老黄狗一弓腰,一动弹,梭掉了。
老黄狗并没梭远,只梭了十几米,就停住,回身蹲在院坝上,望着主人。狗主人提拎着空绳子,一边笑,一边骂自己咋个绑个套都绑不抻展。
狗主人没多看老黄狗一眼,只专心做绳套。做好手上的活儿后,狗主人才抬了头,吆唤狗了。老黄狗竖耳听了下,起身走来,走走停停,不情愿了。显然,老黄狗已明白,自己先前的明白是不明白。狗主人生气了,大喝,砍瓜儿的,快点!老黄狗瞻前顾后,犹犹豫豫,它
在找女主人,也在找小王爷和小公主,甚至还在找老主子。老主子是个寡母子,不在。除了寡母子,都在,他们满院坝站着呢,伸个脑球,脖子细成了一根筋。老黄狗找到了他们,显然失望了。他们的眼睛伸出手来,一些在推它前进,一些在拉它后退,但前者的力量老大了,大得后者没有了力量。我平时把您伺候得多周到,多舒坦,关键时刻咋能不在呢。老黄狗说的是老寡母。其实老黄狗是知道老寡母啷个不在的,这样说,也就说说而已。老黄狗一点不怪老寡母。
老黄狗刚把头伸进绳套中,主人便提拎了绳子,不想狡猾的狗还是逃脱了圈套。主人这下真生气了,生了更大的气了。你看,他用更大更野的粗口糙话骂狗的声气儿,连窝在山盆盆里的小县城都能听见。主人的斥责,让老黄狗自责,无地自容,愧色满脸了。老黄狗第三次走向绳套,每一步都走得像雏婴像病老,心惊肉跳。我看见老黄狗流泪,是那种浑浊的、脏兮兮的东西,稠得像脆干的狗屎蛋子。狗主人在前边,一手背着,一手提拎着绳套,大山般纹丝不动。
森林、草坡、田野,四面八方的路可广了,广得只剩下面前这个绳洞,这独肠一样的绳洞。世界上这个最短的、最柔软的洞,成了老黄狗一生最漫长、最要命的路。
是时候了,该上路了,必须上路了。
老黄狗终于走到终点。它将头颈伸进绳套,见主人不动,它也不动,伸着套了绳索的头,无辜而安静地望着主人。狗主人见老黄狗不动了,就挑逗性地抖了几下绳子。随着绳子的抖动,老黄狗跟着抖动,几抖几不抖,绳子再动,老黄狗不再动。狗主人见老黄狗坚决不再动弹,这才伸出背后的左手,不慌不忙,逍逍闲闲,帮右手稳稳扎扎把套子收小。待套子完全而且均匀地隐在老黄狗颈毛中,与颈肉熨帖妥当后,狗主人才双手用力猛地提拎起绳子,同时用左手狠拉从歪脖子核桃树上垂下的绳头。随着篮球大小的绳套,变成排球,变成橄榄球,变成牯牛卵子,老黄狗只轻轻细细呻吟哼唧了几响,就踢打着蹈空的四蹄,稳稳当当吊在了树上。那一会儿,老黄狗就像在水中游泳,准确地讲,是在水中弹命,喊命。
挂在歪脖子核桃树上,老黄狗身子骨从没这么长过——长长的,细细的,像一根肠。
接下来,狗主人把绳头系死在树身上,回屋拿了一把明晃晃的剐刀,剥了老黄狗的皮。狗主人剥得耐心、精致,现在想来,其脾性与手法,像极了一生都在黑屋里工作的称职的推拿师。老黄狗被狗主人开膛剖肚时,我嗅到了一股喷薄而出的热烘烘的腥臭,熏死人了。正因为熏死人了,我连狗肚里到底是一根肠还是几根肠都没看清白。很快,狗的一坨肉,全部的肉,被一寸一寸扒拉了出来。狗空闲了,轻松了,伸开四肢,头朝上,端端正正一丝不苟趴在了邻家土瓦房外墙上,薄薄的,像一张摊饼,更跟一张完整的狗皮没有任何区别。干了,硝好缝制后,它会上谁的身呢?想远了。老黄狗的崽儿小黄狗不知从哪儿钻了来,它看了看趴在土墙上的妈,若无其事转过头,对着主人直摇尾巴。狗主人用皇帝之于太监的眼光斜睨了它一下。小黄狗尾巴扇出的风,让墙上妈的皮毛,有一种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古意。
萝卜煨狗的肉香,很快从一口黝黑吊锅中飘了来,让人奴相丛生,深呼吸,一下进入饥饿时代的肃杀。杀狗的邻家男人,其实是个大孝子,杀狗,是因为瘸腿老中医说,大病一场的老寡母需要一锅萝卜狗肉汤补补了。
一阵短一阵长,飘了一整晚的狗肉香味,成了打开邻家男人花花肠子抽屉的润滑剂。那
层峦叠嶂的抽屉,码放了邻家男人不可告人的心思。
一根肠子的狗,说一个字是,汪,说两个字是,汪汪,说三个字是,汪汪汪。一根肠子的狗,所有的语言,说一辈子的话,就一个字,汪。在邻家男人和老黄狗这里,物质的一根肠,与精神的一声“汪”,被一粒“孝”字轻轻消解了?或者说,物质的一根肠,与精神的一声“汪”,不经意间,就煨出了一粒“孝”字?
多年后,甚至现在,老远,我一见邻家男人就躲。从杀狗那天起,我越看邻家男人越像一只恶狗,且是野的疯的那类。而一看见幺指拇粗细的麻绳,就像看见邻家男人的花花肠子。
柔软的兔
父亲将一只饥饿的手伸进木笼,一把攥了大白兔的双耳,手回缩,木笼中最大那只兔子就被提拎了出来。世界上没有比在木笼中擒兔更简单的事了,瓮中捉鳖也不能比。你伸手捉鳖,鳖却一昂头咬了你的手往肚袋里扯,这到底是谁捉谁呢,显然,转瞬之间,情势逆变,反客为主了。
兔子就不同。
兔子伸个又长又鲜明的耳巴子出来,就像火上茶壶伸个把,摊子上冬瓜伸个藤,仿佛没有别的功能,唯一的作用就是喊你一把攥了它,提拎起来。再说,窝在笼子里的短跑健将,还能是短跑健将吗?顶重要的事实是,兔子并不想跑,并不忌惮一对招风耳被父亲这样的主人家提拎。从小到大,兔子被提溜得还少么?放风般的敞放要提溜,给一窝小兔崽子喂奶要提溜,打扫兔笼要提溜,病了萎了打针灌汤药要提溜……提溜,几近大白兔的日课。因于此,一只手进得笼来,兔们欢喜了,盼着提溜呢。你看,大白兔被提溜出笼,次大白兔、小白兔、细白兔,全都嫉妒兼吃醋了。
但此一时彼一时。这一次是要命的提溜。
除了父亲和我,兔儿们绝对想不到,这个和煦的国庆节上午,有人会来这一手。
大套、粗糙的父亲,眼里飘过一线杀气。这是我的想象,一个山区小县城初中生的想象。事实上,父亲满脸都是喜洋洋呢。
知道父亲今天要杀兔,不知道怎样杀。
我家住的是县农业局宿舍,一排平房,端头的一间。得了端头便利,父亲就率领全家倾巢出动,倚山墙砌了一间牛毛毡偏房。端头就俩,另一个还没空地,这唯一的可堪造化的端头谁都想得,但没人争得过父亲。念过重庆中正中学、读过西南园艺学校的父亲,工龄长嘛,加之母亲也在农业局,双职工加分,端头房就非吾家莫属了。牛毛毡偏房,除了堆放煤炭、柴禾,摆设鸡窝鸭窝鹅窝,就是沿墙安置兔笼。兔笼有长脚,离地两尺许,笼下地面撒有炭渣煤灰,每天都换的:换走的,做苹果园地角菜畦肥料;换来的,刚从炉膛取出,把潮湿的地面弄得滋滋冒烟,一股熏人的兔尿骚味随烟扑腾,追着人咬。
父亲提溜着兔子,转身出了牛毛毡偏房。我跟在父亲屁股后边,到了房前坝子。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父亲提溜大白兔出来,还真是不想让木笼里的活物看自己对待它们同类的暴行。何况,木笼中是兔,不是狐,兔死兔悲,这样的悲,又比兔死狐悲重了几成。偏房促狭,但用来要一条兔命,还是绰绰有余的。
坝子里早备了一个装满凉水的铁皮桶。桶花里胡哨,显然为废弃的油漆桶。桶面,风吹起水纹,水中漆斑缤纷,像贴着桶壁游弋的一尾一尾的丁丁鱼。父亲看了眼水桶,我跟着看了眼。几乎有些明白了,今天的水桶,之于大白
兔,不是逼供的刑具,而是子弹、铡刀、绞绳。
父亲又看了眼提拎在右手上的大白兔,我也随之看去。我看见大白兔最大限度拉长着身子骨,两只肥厚的后腿自然下垂,俩前脚不完全贴身,半伸出去,朝下略弯,呈最舒坦的松弛状。这会儿,大白兔该弹命了吧,却这么安详、柔顺,一点没体会到危险已然逼近。水桶一动不动,但它作为杀手的脚步声,却砰砰响起;响得太响,我都听见了,大白兔咋就听不见呢?大白兔的眼睛红彤彤的,却不是急火攻心瞬间充血的红,更不是革命的红,它是它本来的红——本来的,红包的红,红双喜的红,大红灯笼高高挂的红。大白兔翻眼朝上望着父亲,甚至还插缝横扫了我一眼。父亲伸出无事可做闲得慌的左手,把大白兔捋抹了一遍,从脑球开始,经过背脊、臀部、短尾、大腿,直到后脚趾结束。父亲的手广大无比,经过后腿时,一把箍了俩后腿。这样,俩后腿,就像在一个山洞中奔跑,并从虎口处噔噔噔一跃蹿出。整个过程,看上去,父亲的捋抹,像极了一位柔情万端的男人对着一团雪花倾心抚摩,亦像一位胸挂十字架的牧师在为死囚喃喃祷告。
我注意到了,父亲捋抹大白兔脑球时,有意躲开了那对大红眼。难道,那是两笼烫手的火炉?
父亲一边捋抹,一边说话。不是我要杀你,真的不是。我是不想杀你的,这个,你应该知道。可我又不能不杀你,不能不杀呀。谁让你长这么快这么大呢?你不长大不行吗,咋这么傻呢?可身为兔子,又必须往大处长,必须裹人腹,这是你的命,也是兔之为兔的正道啊。
其实父亲一个词儿没有。上面的屁话,倘不是父亲说的,难道是我说的不成?
见我的神态有些异样,既亢奋,又沮丧,既勇往直前,又战战兢兢,父亲说话了。父亲说,你要害怕,就背过身去。我听出了,父亲使了一招激将法,目的是不让我背过身去。我从小胆嫩,父亲借杀兔之机逼我练胆。一个尚未弱冠的少年,哪扛得住父亲老谋深算的招数?当即脖子一梗,说,谁怕呢,谁说怕了,我吗,才不!父亲笑了,说,等会儿,你给我当下手。我瓮兔子的时候,你上来搭个手按住它,免得它乱弹。我毫无底气却老气横秋地说,嗯,要得。说话间,父亲迎着铁皮水桶,一个马步,立定。来,把袖子给我绾高些。父亲一边说,一边将提溜大白兔的右手支向我。我避着大白兔,不让身体碰着它,在此前提下,把父亲右手衣管抓住,尽量往上绾,直到抓不动为止。
仿佛是为了考我反应,父亲只说了两个字,好了,就连同右手把提拎着的大白兔脑袋深深地摁进了铁皮水桶中。顺立的兔,一下来了个一百八十度,成了头朝桶底、尾对长天的倒立的兔。桶开始地震,仿佛水怪出现,并伴有沉沉的闷响。父亲的动作,飞快,突然,弄得我措手不及,更弄得兔子措手不及,先是四蹄发飙,周身乱舞,乾坤大挪移,跟着水溢了出来。由于大白兔太大,父亲的高绾及臂的衣袖都被打湿了,大白兔的两只后脚还有小半截没有入水。作为父亲的杀兔助手,我的帮忙是下意识的。应承着父亲的动作,急忙扑向水桶,伸双手,让手掌平摊开,最大化,化身桶盖,向下方桶口盖压下去。说时迟,那时快,一团净水自下而上泼来,又一团泼来,白白的,柔柔的;以为是兔呢,不由吓得连连后退,兵败如山倒。待抹了眼睛上的水珠,喘过气来,才得知大白兔早蔫了气。刚才眼见的大白兔应该是有气泡在水面上咕噜咕噜闹出动静并被我瞥见的,只因杀兔的动静太大了。
待大白兔不再动弹,完全消停,父亲把它提溜出水,向我递来。父亲说,拎着。我不想拎,
但还是壮着胆子用右手接过来拎了。父亲手一松,大白兔沉得直往地下坠,我不自觉地伸出左手托它的背,谁知刚一接触到它的皮肉,却又怕兮兮起来。我接触到的哪是硕壮的皮肉,分明是刚分娩出的连皮毛也无的瘫软如稀泥的幼婴身体。大白兔从我手中滑落,出笼以来不声不响的大白兔,此时发出啪的一声巨响。
水淋淋的大白兔,铺在坝子石板上,像一床永远不能洗净的旧絮。
父亲倒掉铁皮桶里的水,弯腰,一把抓起大白兔,扔进铁皮桶。之后,父亲让我从火上提来一壶开水往桶里倒。这时,母亲也来了,还有二弟三弟,一家人绾了衣袖,围着大白兔,开始一爪一爪扯毛。褪尽了毛的兔,已不像兔。猫尸、大鼠尸、小狗尸?都像,又都不像。它纯粹就是一坨白生生的带皮的肉了。父亲说,连皮带血一囫囵吃进肚家坝,一点不抛洒,划算。父亲的意思是,杀兔,哪需动用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呢?
吃兔肉是午后两点,我和父亲去火车站接了婆婆回家才开伙的。婆婆从重庆来,是幺爸送的。父亲收到电报后,就起了杀兔的念。母亲做的是粉蒸兔,底子是洋芋坨坨,尖尖一盆。一大家子围着伸筷,大盆很快见了底。刚开始,我总觉得粉蒸兔还欠点火候,没熟过心,有一股血腥味。可一见大家伙儿如狼似虎抢得凶野,也就赶忙加入到争抢的阵仗中。父亲实在看不下去,对着我们三兄弟歪鼻子瞪眼,但没用,就说话了,抢什么抢,多给婆婆拈几筷子嘛,你们细娃儿,一辈子要吃多少好东西!
当天晚上,我发觉全家人都在打屁,不响,臭死人了,但没人承认。我是很久没打过奢侈的臭屁了,通顺,豪华,怪舒坦的。
经过了这码事,我看见那只铁皮桶,就总能听见一记一记沉沉的闷响。尤其黑灯瞎火起床屙夜尿,不小心一脚踢上去,咚一声,响上加响,奇响,让人惊惶不已。有一天,瞅家人不注意的空儿,我把它拎去废品站,换了小半把壳儿钱。父亲外号“魏大炮”,不知为啥,这次却不响,只生了几天闷葫芦气。
记得是次年春季开学报名的那几天中的一天,父亲盯着一只大白兔,又一次起了杀心。
这次杀兔,父亲没有沿袭上次的水杀,也没施用刀杀、锤杀、醉杀、绞杀和不可能的毒杀。父亲用的是拔拉。而这次,我没有逃脱命运的安排,真正地勇敢了一回,真正地成为了帮凶。父亲可以不让我参与的,那样他就只能做弹簧拉力器的扩胸运动了,那样就很费力,达不到一招致命的效果,更不能让他腼腆得说话都脸红的大儿子练胆。
父亲提溜着大白兔的大耳朵,走到房前坝子,对我说,来,咱俩爷子来拔河。又说,你逮脑袋,还是脚杆?父亲在逗我呢,父亲知道我不会选择脑袋的。我确实不能想见,将包含了眼睛、眉毛、嘴巴、鼻子、耳朵、胡子等元件的脑袋,包含在自己的两片巴掌里——两片死亡之海里——会产生怎样的毛骨悚然的感觉?我在田间地角扯的苦麻菜、芨芨草、马齿苋、桑叶这些兔儿草,该不会呕吐出来,脏了我一手吧?一对大红眼,该不会凸鼓出眶,爆炸,液化成血吧?还有,鼻洞、耳眼,又会流出什么气味和颜色来呢?不敢想下去了,就站了个拔河身姿,让双脚与大地牢牢焊在一起,同时伸出双手,一把捉住大白兔俩后腿。因后腿体围偏大,就让箍了兔腿的手往后梭,一直梭到脚腕与膝头间,完全妥帖了,才住手。正是这一梭的过程,让我再次触摸到了兔的柔软……父亲的老手瘦骨伶仃,却有大巴山一样的峰剑刃谷。父亲先用空荡的左手扶住大白兔下腭,再让右手松了兔耳,联盟左手抱了兔头。
万事俱备。
大白兔腾空横在我和父亲的手钳下,像一条拔河的绳。这绳,短而粗,白而柔,结构复杂,有些炙手。
这一切,让大白兔觉得反常,不寻常了。
我想最后看一眼大白兔的面部表情尤其是眼睛,但父亲的一对大巴掌遮蔽了一切。我还是清晰地听见了父亲巴掌跑出的声音,咕咕叫,尖叫,喷气声,还有牙齿错位锉磨出的声音。它们纠合一起,发出来,中心思想就一个,不要杀我,求求你俩了!但大白兔的声音太细微了,因为父亲也发声了。父亲的声音是对大白兔声音的批驳与割裂。父亲的声音是喊出来的,一二三,拉!
咔嚓一声,很轻,很秀气。世界安静了。
拔河赛,我和父亲打了平手,唯有兔是输家。
父亲一松手,大白兔倒吊在我手上,大白兔一下长高了。被拔苗助长的大白兔,都有大半个我这么高了。拔河,已抽尽了一位少年的力气,哪还有力气提溜起一条如白云重的命?大白兔滑落地上,这相当于我又摔了它一回。
大白兔从我手上滑落,还有一个原因。随着那声咔嚓的骨响,我看见大白兔短尾帘下肛门处,滚出了三五粒屎蛋子,软软的,像黑珍珠。风吹过来,一股异味杀入心脾,五脏六腑翻江倒海。
父亲一换手,把大白兔车转了方向,头上尾下地吊在一棵梨树上,稍一用力,就脱了大白兔的衣裤。脱了衣裤的大白兔,全身上下,红得人。脱衣扒裤时,父亲用他嫁接果树的锯条刀,从兔唇处下刀,一横,一竖,呈十字。父亲非常精致精美地剥开了兔脸的皮。尔后,十指环皮抓攥,身子下蹲,双手发力,皮开始一边翻卷一边向下走动。很快,一张鲜红如旗的囫囵兔皮脱了下来。父亲翻了皮,弄得里是里面是面的,抖了抖。接下来,将一把一把谷糠从大开的兔嘴处塞入,直到一只肥硕而轻捷的大白兔诞生。后来,这只重生的大白兔,成了我爷爷棉大衣上温暖软和的领子。
上一只大白兔是为了招待远来的婆婆和幺爸。这一只是为了送给我的老师。我的老师怕杀生,却最喜吃肉,她是我的班主任,又是一名政治教员。
常年写字,让我患上了颈椎、腰椎的毛病。老婆说,龙泉驿商业后街有家“太乙正骨”,专治这毛病,据说很有效。遂办了年卡,开始正骨。别说,还真有效。但我很快就不再去了。这个决定,让年卡里的一千二百元人民币打了水漂,为此,我装着没事,却心痛了好一阵。我不去,是怕那位比一头黑熊都蛮的正骨师给我端头。正骨的最后一个程序是端头。端头的时候,正骨师领我走出店门,背店面街,站在马路边,正骨师自己则站在路沿石上。大街上,车水马龙,人流熙攘。正骨师双掌环抱我的脑球,左摇右摆,右摇左摆,几摇几摆,摇摆成了滚动,且越滚越快,突然,提溜着我的脑球,向上一端。
咔嚓。
如果正骨师没有听见咔嚓的响,会非常丧气。他会让我放松身心,再来一遍,直到听见我颈骨的脆响。
正骨师哪里明白,我和父亲拔拉一只兔子,虽过去三十好几年了,我依然记得,尤其那轻微、秀气而要命的咔嚓一声。
这样的声音,让正骨师快乐,让我发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