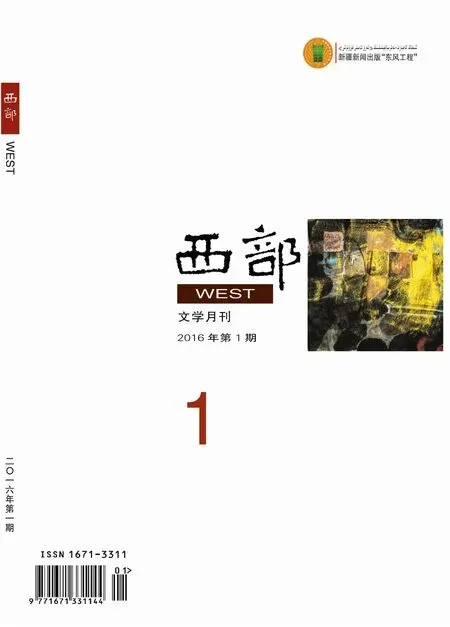七月
2016-12-07王晓燕
王晓燕
七月
王晓燕
墙上的镜子里。桌上的花。几丛兰草簇围着几大朵牡丹、百合,插在一只酒瓶子里,花瓣上的露珠还未干,娘一大早就在院子里拾掇。娘极端地爱花。
七月洗了脸,走到院子里去。娘奔来跑去,跛着脚,她的腿痛病又犯了,看了看七月身上的衣裳,让她换件新点的穿上。七月大声说:“我又不是去做戏子。”那声气儿,有金属的冷硬。娘站在那儿,愁苦地望着七月,扑打身上的土。
虽已是初夏,早晨的天气仍有点薄凉。爹去地里了,二哥还睡着,七月将头发胡乱扎了扎,匆忙奔去厨房。二嫂一边烧水,一边擀长面,七月赶紧蹲在灶前烧火。动作迟一点儿,二嫂会给娘脸色看。可这两天,二嫂对七月的态度,忽然又亲密起来了。
高压锅里炖着一只鸡,二嫂笑着说:“今儿来的小伙儿,可不能让他白吃了这只鸡。”
七月说:“你急了,你跟了他去。”对二嫂,七月又极端地克制,可对娘,却管不住自己仇人似的情绪。
二嫂娶进门有一年了,做啥活计还得娘指派。擀了面,问娘面擀好了,再做啥哩?娘说那就等会儿吧,人来了再烙葱油饼,不知他们来几个人。
客从县城来。每每有客人来,娘就特别仔细,里里外外清扫得亮堂堂的,茶杯桌椅前一天就擦洗过几遍了。菜蔬烟酒大哥前几天也托人给捎来了,杀鸡、擀长面、烙葱油饼也是最好的待客吃食了。
大哥二哥没分家。大哥大嫂在县城工作。
二嫂刚娶进门那阵,七月提出想去县城学美容美发,爹和娘都没意见,大嫂也愿意给她出钱,大嫂早就想让七月去学门手艺,但七月一直没这份心思。
“如果七月去学,我也要去。”二嫂说。
二哥立刻反对:“你去学那个像怎么回事?你去学了,地谁来种?”
“我怎么就不像回事?”二嫂马上扔了筷子,脸冲着二哥叫起来,“谁吃谁种!”娘赶紧往大哥脸上看。大哥一家人吃的从家里拿,当然,家里花钱也都由大哥管,一有空他们就回来帮着收种庄稼。大嫂脸红了红,什么话都没说。
七月觉得二嫂变得让人吃惊,女孩子一结婚就变了。七月跟二嫂是同学。一说下亲事,二嫂就退学了,穿的用的从此都由二哥给送去,隔三差五,准会指使媒人来向二哥要一样物品。一家人都会想着法子帮二哥满足人家。那可能是农村女孩子最为金贵的时期,有些人家会尽挑贵重的东西向男方要。二嫂就替她弟弟向二哥要过照相机、摩托车……大嫂每给七月买样什么,必给二嫂也买一份。
二嫂越来越有怨气冲天的话要讲。
七月突然意识到,婚姻生活也许是女人的一场灾难。
七月听见娘在喊二哥起床,太阳似乎是被娘喊过来的,一刹那间,满院子阳光。
来了三位客人。大嫂的同事吴科长已是第三次上门了,一看见七月就啧啧叫着伸出手指点她的脑门。
七月辍学,大哥大怒,等她辞掉了医院的工作后,大哥索性懒得再操这个妹妹的心了。七月也躲着大哥,尽量不到县城里去。她的事,都是大嫂在忙着张罗。
“这次再要看不上,看我不把你给卖了!”吴科长贴着七月的耳朵小声说。乱发遮住了七月的半张脸,躲避吴科长时,一个发圈甩出去,头发索性散了,她穿了件宽大的灰衬衫,衬衫的下摆包住了膝盖,脚上穿的是娘做的黑布鞋。吴科长注意到王智量自进门就一直在盯着七月看,就又冲七月挤眉弄眼了半天。
七月跟人打了个招呼,就闪进了厨房。无论二嫂怎么支使,七月就是不肯到厅房里去。二嫂自己端了一盘刚烙好的葱油饼到厅房里去,仔细看了王智量几眼,回到厨房说:“一看就是个老实人,就是个头小了点,这没什么的,你二哥还不一样是个小个子。”
七月冷笑,二嫂也不看看自己,还嫌二哥个子小,心里老大不乐意。一块儿在县城念书时,俩人什么疯话都说,可自从成了姑嫂,就变得生分起来了。
“这个人身上有股子比我们这种人多出来的东西,不像你二哥,一眼就能瞄出来,粗人一个。”二嫂还在拿王智聪跟二哥比。
厨房门口忽然黑了黑,马上又亮了。吴科长红着一张脸闪进来,凑到七月跟前来说话,一股子酒气臭。
“怎么样,七月?你可再别让我为你跑这路了。你看看,为给你找对象我这腿都跑细了。”吴科长和大哥大嫂是多年的朋友了,七月上初中时,他就是科长,如今还是科长。对七月的事,吴科长倒真是上心。
七月躲到二嫂身后去。
二嫂正在切长面,手里提着把菜刀被推到吴科长跟前。吴科长盯着那把刀,夸了几句二嫂的手艺,又回厅房去了。
吴科长给七月已经介绍过四个了。
“你这样会挑花眼的。”二嫂看出了七月的意思。“要是我,只要能生活在城里,管他长什么样。”
王智聪在乡下教书,刚考上公务员,家在县城。
大哥在电话里跟爹说,这回成也得成,不成也得成。
七月呆望着二嫂,想到人一生要度过的漫长的婚姻生活。
厨房里的光线猛又黑了黑,王智聪从外面的亮光里踅了进来。
后墙的高处有扇气窗,蒙了块窗纱,如今已是黑乎乎的,也不知当初盖房子的人为何不再给开扇窗户。虽已近正午,厨房里面仍暗昏昏的,再加上那腾腾雾气,就看不怎么真切,王智聪来得无声无息,把七月吓了一跳,这一吓,惹得她心生了厌恶,索性看也不看他一眼就出去了。
王智聪便跟二嫂扯了几句闲。
“我们姑奶奶就那性儿,你别放心上。”二嫂借机问了王智聪许多问题。
“她那个事,你晓得的吧?全县城的人都知道。哎,我们七月跟我一样,命不好。”七月那件事,本就不是什么秘密,但似乎诉说得愈多,愈能让那可憎之人承受得越多。加之,这个王智聪少言寡语,是个文化人,莫名让二嫂觉得信赖。待要说得仔细时,王智聪借口走出去了。
他望着大太阳底下的园子。满满一园子花,正是花儿们的时令。牡丹、芍药、百合、马莲。他眯着眼睛,断断续续地想到它们的名字,想到她的名字。
他把那个名字与这院子里的物什、花草一一联系在一起。这是个方方正正的四合院,房子有些老旧,但井井有条,他心里突起的怅惘像阳光洒了满院子。桌椅,窗户,她的气息无所不在,氤氲其间。
他嗅探她在这个院子里的气息,目光落在一抹月白色的窗帘上,那一定是她的房间了。她那个人,经过别人的言语,他感觉像早就认识了,他也没抱多大希望来。他母亲的院子里也种着那种花。他母亲告诉他,那叫七月花。那花极其美艳,他爱那个名字,光念着它,就有一种神秘的美感。见到她本人,他重又记起了那个名字,仿佛是听到别人说她叫七月,他一下就有了兴致,他为这个名字而来。
跟头一个女朋友分手后,他就感觉再也爱不起什么人来了。一旦想到将要与自己息息相关的某个女人,他就浑身止不住地哆嗦。那个女人真的把他整惨了。现在光是想起她的那双眼睛来,内心就涌起像海水那样多的恐惧。他很想马上对七月说说自己的这种心理。不知凭什么,他觉得七月会懂他,是能倾听他的人。七月的骄傲和冷漠,本该令他退缩的,可是很奇怪,他竟然感觉到强烈的渴望,他想接近、讨好她。
七月仅问过他一句:“来了?”这仿佛已是饱含深情的一问。当他从树荫遮蔽的巷道里走进来,他看见两边围墙下的空地上,开满了七月花,而他将要看见的女子就仿佛是花丛中成了精的一朵,七月啊。
他把自己的心封闭起来都三年了。最近,他也相过几次亲。但那些连脚趾缝里都暴露着物质欲望的女子,再也无法拨动他身体里曾经被热烈地奏响顿然又死僵僵了的弦。
他竟然会再次一见钟情,这仿佛是他的命,他那个女朋友就是始于一见钟情,他也才有了后来的下场。
他回忆起三年前那会儿,对爱情,事实上他还一无所知。他不能给人讲,他只是受到了诱惑。
他意识到,七月不可能满足于这安静又圆满的小院子的生活的。
命运会使有些事情重复发生。一种在黑屋子里孤独抽泣般的忧伤迫使他想巴结她、
讨好她。
猛听见七月的父亲在唤他。王智聪赶紧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回厅房里去了。
七月再没有出现过。吃饭时,二嫂就立在厅房不时地添茶倒水,一眼眼往王智聪脸上睃着。
七月的父母对王智聪很满意,一定要留他们多呆一阵儿。还有一位是王智聪的叔叔,这会儿已催着吴科长吃完饭就往回赶了。王智聪父亲去世得早,每有需要父亲出场的角色,他母亲就去请这位叔叔出马。王智聪很清楚,只要叔叔满意,他母亲就会以她快要老死了以及孝道之类的事逼迫他同意这门亲事。叔叔跟七月父亲拉了半天话,心已踏实到肚里去了。这么实诚人家里的姑娘,差不到哪儿去,何况七月本人那样完美,看看自己的侄子,都有些高攀的意思了。七月像某部叔叔看过的外国电影里的女子,这完全在叔叔的意料之外,以致他忘记了听来的一些闲话。
吃罢饭,叔叔倒又不催了,叔叔和七月父亲不知怎么就谈起了《周易》,谈起了军事,他们抛下其他人,自顾自往更远里说开了去。七月父亲难得找见一个有文化又乐意跟他往深里交流的人,兴致上来,俨然换了个人,头头是道,有理有据。这令七月母亲尤其是二嫂很惊异,因为父亲一年中也说不了几句话,是个极度沉默之人。说着说着,父亲忽然起身去开了炕上的一个柜子,拿出一瓶茅台,再取出一盒软中华来,给众人一一敬上烟,又敬酒。七月二哥借机去厨房催二嫂再切些牛肉,再拌一盘野菜下酒。
“把那瓶茅台都拿出来了?”二嫂抬高了嗓门。大哥拿了两条猪腿去给领导拜年,领导顺手从桌底下抓了瓶茅台给他。大哥给爹拿来,爹一直锁着。那瓶酒已放了四年了,二嫂只是看过一眼。
叔叔很吃惊,七月父亲竟然研究很广,见解一点儿也不比他差,信口道来的那些,可不正是最近痴迷研读的某位哲人的学问,他庆幸才读过那些段落,正好用得着跟这位老伯交谈,否则,输给一个农民,多没面子。叔叔一再伸出手,大声地叫着“老伯啊”,与七月父亲的手相握,对这家人,竟多了几分敬重和由衷的喜爱,情到深处,一定要请七月父亲去县城他家里做客,喝他存的好酒。虽然每日见的人很多,可真正可以无拘无束地说话的人,没一个。
“你不知道,现在这社会的人,一天到晚尽想着怎么升官发财找小三,要么就是房子汽车的事。”叔叔皱皱脸,摇摇头,“老伯啊,就是没个人跟你谈谈心哪。”七月父亲就笑,说你有空了就来,农村空气好,吃的安全,交通也方便得很,如今路都修到家门口了。叔叔拍拍大腿,说对呀,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嘛,就去望王智聪,让他快给老伯敬酒。
王智聪只得站起来,一再地端起酒杯,这不是他所擅长的,看上去就有点像老大不乐意的样子。七月父亲倒是蛮喜欢他有点呆头呆脑的样子,觉得可靠。他不由就想到另一个人来,避开七月跟老婆子一起称作“那个坏种”的人。
叔叔话越说越多,把平日里工作上无处宣泄的怨气,也一点点给七月父亲道了出来。叔叔有点看不上吴科长这个人,吴科长也不乐意让叔叔觉得自己是在跟他套近乎,便一直缠着七月母亲和二哥说话,二嫂一进来,他又将脑袋拧过去,伸着脖子问二嫂娘家是哪里的。
“那怪熟的了,前些年下乡,老住在你们家,你爸还那样爱耍牌?”二嫂脸顿时红了,嗳嗳几声,拎了暖瓶出去了。
“赌是不赌了,可那病,不喝酒才好,偏偏又好那一口。”七月母亲有点过意不去,就主动跟吴科长聊了起来,可一说就说得多了,且一下又住不了口。直到老二叫了起来:“你给人家
吴科长说那些做啥嘛。”老太太这才讪讪收住话头,发觉自己把不该说的都已说了,就连连让吴科长抽烟,让吴科长尝尝野菜。
娘坐在炕里头,爹的身后,吴科长硬拉她跟爹在上位坐了。她几次想下炕去,因为担心得让炕上坐的人给她挪地方,便忍住没动弹。她一面悬着心,生怕儿媳妇这天过后会去村里人跟前晒摆怨气:来了人,就倚老卖老不帮着她做活了;一面又惦着七月。
酒喝了一瓶又一瓶,每个人现在都扯起了嗓门说话,欢声笑语。吴科长把王智聪考上公务员的事重复说了四遍,好打住叔叔和七月父亲越来越热烈的谈古道今。说一遍,七月父母就讪讪地冲吴科长笑一下。二哥不胜酒力,又去请了庄上头的周伯来陪客,几个男人的嗓门儿快要把暗旧的屋顶给掀翻了。吴科长高声喊着,夸七月的好,又吹嘘王智聪头一个女朋友家有多富有,房子、车子有多少套、多少辆,那家的主人还出国旅游过。
“人家运气好,是借出公差去的。咳,可惜啊,他们生的那个女娃子却是个二百五。”
屋子里忽然就静了下来,众人沉默地听他说。
渐渐又听到叔叔和七月父亲压低了的交谈声逐渐地抬高了,终于压过了吴科长呀啰里吧唆的胡言乱语。
王智聪带听不带听的,处在自己的幻觉里,又一眼眼往屋里每个人脸上睃一眼,看是否漏掉了什么人冲向他的问话。
“智量你哪能找那样的!”
王智聪笑笑,并不觉得难堪,反觉得心里舒畅。众人热烈的笑谈加剧了他的幻觉。
这时吴科长又尖了嗓子转向站着的二嫂说话,再转向七月母亲。“我们七月,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姑娘,婶子,您放心,包在我身上。婶子您不知道,在大城市,七月这个年龄才开始享受生活呢。”二嫂沉着脸说了句什么,听上去像是帮着自家人在说话,二哥则听出来,她是在借机吐出那忽然被勾得分明了的怨气。吴科长再次转向王智聪。“找上七月,是你小子的福气。来,喝酒。”闷住了的空气一下又流通开来,夏日般热烈的气氛再次膨胀了。
对七月一个出身农村没工作又大龄的女子来说,能找上一个家在县城的公务员,真的是她的命好。除了王智聪和叔叔,屋里坐着的人都想到了这一点。而吴科长和七月的家人对望一阵,不由都联想到一些传言和另一个猛然让他们不得不想起来的人。
娘不时透过窗子向院子里望一眼,这场因为女儿而有的热闹到底是令人轻松和舒心的。可想到七月,娘就有些为自己没有去克制那身不由己般的快乐而又心生了歉疚。
经过吴科长不断地赞美,加之这热烈的气氛,王智聪内心里饱含了深情,目光来来回回落在沙发上、桌椅上,落在墙上的镜子里,晶亮的茶杯里,又落在七月母亲和二哥脸上。他想到七月每天会在这屋子里走动、打扫或取走什么东西,他望着墙上的那面镜子,仿佛看见她正在梳那一头黑发,心想过了今天,以后每天她都会在镜子里看见他,在做活计时想起他,会像他这样,即使眼睛里看不到,却每次呼吸都能感觉得到她。他身体里忽然有了一眼忽明忽暗的泉,暖暖的,缓缓的,不时涌出一股清亮的流水。从七月母亲和二哥脸上皆能寻到七月的影子。她的头发,让他想到某种动物的野性,她的一举一动虽有意向人暴露着任性和不满,留给人的印象,却依然是那样优雅和神秘。
他完全已是个在恋爱中的人了。
七月在北房呆了一阵。北房是二哥二嫂的
房间,她想回自己的阁房去,但那得穿过院子,会被厅房里的那些眼睛看到。七月不想被任何人注意到,宁愿那一屋子的人因为开心暂时忘了她的存在。
七月出了院门,往园子里去找点荫凉。正午的树丛间,没有一丝风,花儿草儿蔫头耷脑的。七月站在一棵樱桃树下,她心里的决定一目了然,然而,处身在被这烈日焦灼地晒烤着的园子里,身体里一股决绝的气浪忽然就像雾气,她没法去阻止,只能容忍它们无比艰难地一缕缕消散。
最为难的是娘。七月早一天嫁出去,娘就可以大大方方地去村里的人家串门,大声告诉他们,七月在县城生活得很好;再听不到大哥对她暗中的数落和二嫂含沙射影的怨气,而娘若有了怨气,可以坐班车去县城,去七月的家里轻轻松松呆两天。大哥是个爱站在人前头说话的人,他只在意亲人们每做出一件事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二哥则是个稀里糊涂的人,就像大嫂。这可能就是互补吧,大哥和大嫂,二哥和二嫂,上帝这样安排人,好让他们在这个世上活着时不觉孤单和没趣。家里少一口人,就少一份吃喝用度。房子早该翻修了。最重要的,是让那些不分青红皂白的闲话,从此不再到处流传。
在真做不了决定的时候,七月想到让上帝来帮她。上帝,是赵文轩教她认识的,但她却没有一次真正敢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一个只是有所听闻的人。
七月无意间听说,村里人如今又津津乐道于把她说成小三了。
一重重可感可触的压迫,卷着这夏日正午酷热的气浪向她逼来。这压迫到了亲人那里,他们所承受的可能还会增倍的重。
如若她离开这个家,一切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七月一度打算逃离。去新疆。那是她目前能想到的最远的地方。
今天,她非做决定不可。
客人还没到那会儿,她抽空去往阁房,在桌前坐下来,撕碎了几页纸,在十几张碎纸片上分别写下:走,不走。再把碎纸片一一揉成团,搅散了,在桌子上聚拢一处,她闭着眼睛,在心里呼喊:帮帮我,求你了。
帮二嫂揉过面的手心里沾满了面。七月把摸到的纸团捏在手心里。就在那时,客人们到了,她只好把纸团装进衣兜里,从阁房里出来,匆匆在台阶上的水盆里洗掉了手上的面。
烈日下,七月有些发晕。
走得远远的,是在失望、压迫俱来时的一点儿隐约又实在的希望。
多见一个人,家里多一次为她而有的折腾,内心里就越多感受到一重歉疚和压迫,离开的决定就又变得坚实。
她从兜里掏出那个纸团。她告诉自己,不管是什么,她都会按照纸条上写的去做。深呼吸了两口,她迅速将纸团展开,一下子看到了那个字。
她打算要全心依凭的上帝,这下告诉了她该怎么做了。
她的心彻底踏实下去。
阳光从树缝里漏洒下来,在她的鼻尖上、眼睛上,闪着细碎的光亮,几片阴影又覆盖了那光亮。
她将脸伸进樱桃树的密叶丛里。
王智聪的轻唤声从身后传来时,她来不及擦掉脸上的泪。
“对不起,我打扰到你了吗?”王智聪站在那儿,她哭泣的样子令他不忍心转身走开,他很想伸手将她揽进怀里。
“你怎么出来了?哦,没什么,我在这凉快一会儿。你不在屋里呆着,这会儿正热。”七月仓促地胡乱摸着脸,堆上笑意匆匆瞥了他一眼,马上去望远处的一棵核桃树,阔大的叶片上大大小小的光斑跳动着,随风跌落,又聚起。
“你还好吧?”
她望着他担忧的脸。“让你笑话了。”一时,她也弄不懂自己为什么要哭。
他的眼睛一直深情款款又无比忧伤地望着她。
“我想,你一定已经听说了那些事。我是说,你大老远地到这来了,我的意思是,”她忽然觉得自己要说的正是身心里一直急于要说出来的,而不是只用于敷衍他的话。反正,他不过是个陌生人罢了。
“哪些事,你想说出来吗?”他装作茫然的神情。但他马上又担心她真会说出那些事来,赶紧又说:
“我感觉自己很幸运,真高兴见到你,七月,我说的是真的。”他往前跨了一步,看着她的眼睛。因为唤出了那个名字竟然有些哽咽。她的眼睛马上垂下去。她能听到他胸口突突地跳动。
七月笑起来,看他不停地搓着手心,显得是那样紧张。七月被迫见过的那些人,第一面都不约而同地试探着,想立刻把她带到哪个房间去。
手心里,那个纸团还在。她紧握着。
他可不想听她说那些事。可是,她已经说开了。
上小学五年级时,大哥把她转到县城去读书。初中毕业,她就不想再念书了。大嫂把她留下来带小侄子,一直带到他上幼儿园大班。
那天早上,她起得迟了,肩上扛着小侄子横冲直撞过马路。赵文轩开着车差点撞上了她。
“瞎了吗?!”七月冲车窗里竖了竖中指,还用英文骂了句脏话。
那时的七月,除了找不到毒品可吸,什么都模仿外国电影里女子的作派。
送完侄子出来,七月看见赵文轩靠在车门上等在外面。
“怎么,专在这等我回头讹你?”七月莫名有些心虚,赵文轩不像是可以和她斗嘴打架的那种人。
“为什么非得跑那么急?”他笑了一气,问她。
“如果我大哥晓得我又睡过头了,会很麻烦的。”七月摸摸头上短得不能再短的发茬,老老实实回答。
“有多麻烦?”
“超出你的想象。”
“你真有意思。”
“你也很有意思。”
赵文轩一次次约七月出去时,七月不知所措,但最终还是随他去了。
“你一定晓得那种心理,有时候,只是因为好奇,或感受到某种莫名其妙的并非真的来自于对方的吸引力,我指的不是爱情。我是说,可能仅仅是我们感觉到或发现了一个被突然激活了的自我。”七月转头看着王智聪的眼睛,他点点头,又差点流下泪来。他太了解她说的是什么了。她的眼神一再地扣击着他身体里崩断了的松垮垮的弦。“当然,这些个我也是现在才弄懂了的。”
看见七月,王智聪才明白,自己就是一架琴弦需要调整、重新调音的竖琴。除了七月,注定没人能弹响他。他沉浸在自己的幻想和感觉里,对她说的带听不带听的。
赵文轩常带七月去图书馆。七月安静地坐在赵文轩对面,坐着坐着她就打起了瞌睡。赵文轩一坐好长时间,不时轻声把她唤醒。她就
不好意思再睡了。
不是为了兴趣,是为了赶上他,为了跟他有真正的交流,七月后来习惯了阅读,习惯了一个人去图书馆。
通过了职称考试,赵文轩就不再去图书馆了。
那阵儿,她过得很充实,也留长了头发,不再模仿那些外国女子。
小侄子上小学后,大哥托人让七月去县医院的门诊部做挂号收费的工作。那是自七月辍学后大哥唯一帮过她的一次,可能也是看在她突然变了个人似的份上吧。
相处日久,一种好胜心理就越强烈,强过七月对赵文轩本人的兴趣。赵文轩不让七月对任何人说起他们的关系。不管她怎么变化,仍是个来自农村的看孩子的保姆。
七月暗想,我会超过你的。强烈的自卑感常让七月找这样那样的理由主动去接近赵文轩。
那件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七月说不清具体的时间。慢慢地,她发觉自己真的陷入了爱情,赵文轩的名字、他身上的气味、衣服的颜色以及与他关联的一切,就像一种迷药,让她为之痴狂。她努力学着他的样子,学着露出他脸上的神气。在他的眼神向她投来时,她感觉到自己心底款款的深情。
七月没有固定工作,让赵文轩一直无法在她跟另一个女人之间彻底做出抉择。
他们交往了四年多,七月往图书馆跑了四年,读的书比她上学时所有时间加起来所读的都多。
那个下午,下过雷雨。赵文轩领着他真正的女朋友来医院看病。要不是七月,赵文轩早就跟她结婚了。这话赵文轩一直在说,可七月并不确切地知道那与她有什么关系。
那女人一脸喜气,紧贴着赵文轩,而赵文轩亲密地揽着她的肩。他没有跟七月打招呼,板着脸让她挂了个妇产科的号。
七月的脑袋在那一天里开了窍。
过了一个礼拜,七月辞了工作,回了乡下。
除了去地里干活,她就读书。繁重的活计和密密麻麻的书页把她脑袋里和心间的空隙填满了。
几个月后,赵文轩寻到村里来了。
他说他跟那个女人处不到一块儿,他的心一直在七月身上。
七月忘不掉在医院的那个下午,脑子里像遭受过雷击,一下开裂了似地清醒。
“有些事,放手了就再收不回来了。你不会重要到一直会被人惦记,被人怀念,被人期待。”
七月一时还无法思考一些问题。等她终于能冷静地思考了,赵文轩已结婚了。
王智聪望着远处几乎望不见的山梁。
两人从几棵白杨树下拐过去,七月推开园子的木门,走在前头。刹那的恍惚,让七月想退缩回来。赵文轩也曾这样跟她走进园子,像狗一样温顺地乞求她:
“我应该早做出选择,对不起,七月,我忽略了你的感受,我保证,我已经跟她彻底断了。我要娶你。”
“我们在一起,一定不会没趣,我们说过那么多话,你真不记得了?”
“你不是说,我们在一起,你会变得越来越好么,你真的打算不理我了?”
……
为什么王智聪会激起她如此多的回忆?
王智聪不想马上离开,回到屋里那些快乐的人中间去。他痛苦地发现,内心里,对七月竟多了一重深情。
也许,她以为已经是过去的事了,说说也无妨。他又想到,自己本也打算讲讲那个女人,对七月,把内心的伤痛勇敢地讲出来,或许可
以表明他的诚心。但又心存侥幸,但愿七月跟他是同一种心理而非别的。
可是七月抢了先,他要再讲出来,就跟交换似的。像是有自残心理的人,愿意把伤口撕裂给人看,或者,更像是一种比赛,看谁受的伤害深。
他们绕着园子里浓厚的树荫走来走去。
“你跟他在一起时,真的快乐吗?”
“有些事,回想它根本没有意义。”她答非所问,像是在自语。
“七月,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不会的。”
“你有没有想过,那会儿你刚踏入社会,也许你对那人只是单纯地崇拜、模仿以及感激。”
她吃惊地瞪大了眼睛。他大着胆子说下去:
“我也有过青春期。你渴望改变,但从来没人能够顺着你的意图指引你,然后,你遇到了那个人,他适时地激发了你潜在的那部分自我,并且,你是受了他一些诱惑——”
“求你了,别说了。”
除了她母亲,从没人会真正在乎她的情感。
否则,后来他又回来找你,你就不会再拒绝了。他没敢说出来。
“不知道。我什么也不记得了。”她努力作出已释然的表情。“说说你吧,你为什么也落下了?”
“我也不知怎么就被剩下了。”他勉强笑起来。她望着他的眼神真诚而热烈。“谈过一个,不合适,不合适的人在一起会很痛苦。”他斟酌着,慢吞吞地说。
“如果今天我不来找你,将来有一天突然遇见你了,我想我会后悔死。”
“你遇不见我的。”她似笑非笑地说,那个纸团贴着她的掌心。
“县城那么小,怎么可能呢,除非你离开这儿。”他想到,她只是在这里休憩一阵,她终会回到县城,或去别的地方。
天边隐约传来一声沉闷的雷声,他们都仰头往树梢外的蓝天望去。
那个决定仍旧握在她手里。她感觉到一阵心悸,让她发虚。她蹲下去,揪着一根草茎,等那一阵眩晕过去。
一阵猛烈的风过后,天边又安静了。
“预报说今天有雷阵雨。”他也蹲下去,跟她面对面。他的眼睛像孩童似的,半蓝半灰,她脑子里瞬间很空茫,她把那个纸团紧捏在手心。
他一直望着她。她在他的注视里。
后来,他们走出园子,顺着两道围墙夹着的小径一直往外走,从一个坡上下去,穿过一片麦地,向左边拐去。四下里全是麦地和豌豆地,他们从中穿了过去。拐了个弯,又是一个园子。树荫遍地,路边挨挨挤挤站满了白杨树和柳树,杏树、梨树和苹果树的枝条从墙头伸出来,上面缀着一串串青果,他伸手将枝条拦高了,好让她过去。坡下面的浓荫中探出几片屋瓦,她往里靠了靠,让他小心走路,不要让舅爷看到他们在此。
头顶忽然又变得开阔,他们已走到了一条大路的尽头。远处,一片片庄稼地,绿色像水一样漫透了一块块田地、山坡。蓝天正在他们头顶,又像正离他们远去,越来越远。他不大流利地说了些听来的笑话。此刻,她完全忘了她脑子里一直在想的东西。
“要是有人陪着,我愿意老死在这样的地方。”他看着她的眼睛说。也是在这一刹那,他再次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有像这样真正被一个女子所触动,一下为之倾倒,想到真要被她拒于千里时,他一定会痛不欲生。
她没说话,伸手从路边的枝上揪下一朵七月花。爹会不会对娘也说过这样的话?娘有一句贴心的话就很满足。娘给她起这么个名字,这个名字又被身边这个人深情款款地唤着。
“夏天最热的时候,七月花就大朵大朵盛放。在高而直的枝头,她是那样美艳、坚韧。我写过这样一段话。”他很惊讶,编造出这种话来。
“这是最普通的花了,事实上它在哪儿都能长。”七月接道。
王智聪等七月的目光投过来,无比忧伤地望着那张脸。“那年,七月花开的季节,我父亲去世了。我把我想说的话都写了下来,见了人,反而就不知该说什么了。后来我就一直这样,跟人不怎么会说话。”他说着突然红了脸。“我已经对你说了很多了。”
她把花捧在胸前,想着他那时的处境,心里涌起一阵怜悯的柔情。
“不会说话的人,往往最晓得怎样把话说得动人。”那阵柔情还在蔓延,她感受到季节。她一直像这荒野里生长的植物,她的精神、心灵在这季节里最自由,最平和。吴科长赞美王智聪的话,在她记忆里开始探头探脑。
风刮来刮去,他们从陡坡走下去,他伸手护着她,以防她不小心从坡上冲下去。风从抽穗的庄稼地里刮过来,在树梢的最高处喧嚣,山顶上聚积了一块块厚重的乌云。
暴雨马上要来了。
她往更远处奔跑。他喊着让她小心,不要去树底下。
“城里人,快跟上我啊。”
出了汗,她变得越发地轻松了。她一直跑到了坡底下,一条河挡住了她。
他看着天边越来越厚的乌云,让她往回走。
他们又比赛着往回跑。她问他经常跑步吗?
她很久都没这样跑过了。喘得快说不出话来。
他们提到读过的书,她像一只雀儿一样笑着。他被她的快乐所感染,一点儿也不觉得自己竟然在头头是道。他竟然还是个基督徒,因为他母亲是。她头一回听说,在县城那种地方,有人真的会是基督徒。她一下猛又感触到手里的纸团,被汗水浸得湿乎乎的,纸的棱角在她手心里变软。
说到有幸活在这个世上,真正想要做的事,两人都有些滔滔不绝起来。这出乎他们自己的意料。
“我没有工作,也没念过几天书,你真不会在意这些?”她忽然问道。
他吃惊极了,看她并不像是打趣他或有恶作剧的意思,半天都不知该说什么好。
他不就是为等这个时刻而来的吗?从辨认出她的纯真与特别那一刻起。
他望着她那头乱发,忽然咧嘴笑起来。
四周突然暗了下来,积雨的云层不知何时已将天空密密地遮盖。风从高处的树梢上刮起,也从地面卷起沙土、落叶以及草屑。一滴雨点滴落在她鼻梁上,又一滴打在她的手臂上,风湿乎乎地缠绕在他们的额头上、臂膀上。
他拉着她飞快地跑起来,雷电就在他们头顶炸响。大雨降下来,把他们困在一棵白杨树下。王智聪脱下衬衫,罩在两人头顶。他靠得太近了,她略略侧转过去,可这种姿势更像是她想要依偎在他怀里。
手里的纸团不知何时跌落在她脚下,瞬时就变了颜色,变软,变轻。
它像一团融雪似地化掉了。
闪电猛一下像剑一样刺穿了大地。她的目光追着闪电的光束,她记起摊在桌子上的那些纸团。如果客人们还没来,她就有机会做三次选择,为了不留下遗憾,她打算让自己摸三次,出现两次的纸条上写的,就是她最终的决定。
她摸到的第一张,上帝就告诉她:走。
等雨停了,他们回到屋里,她可能还会再去试探上帝的心思。
也许,那些小纸团已被苦心的娘给收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