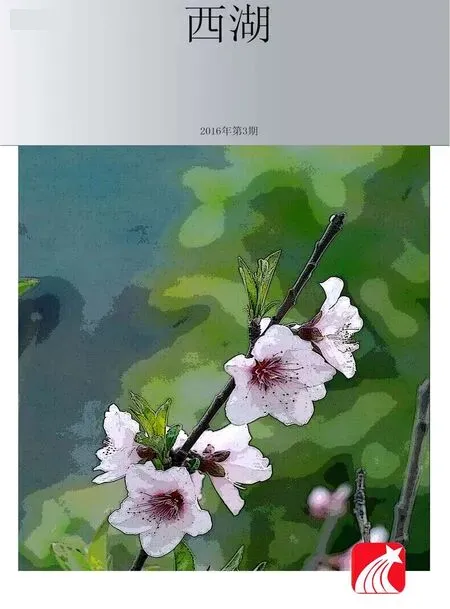自然的女儿
——草白印象记
2016-12-07王威廉
王威廉
自然的女儿
——草白印象记
王威廉
和草白认识竟然那么多年了,这让我不免感到有些吃惊。吃惊是因为,那么久的朋友,那么好的朋友,迄今只见过一面。2015年的春天,我在宁波《文学港》的办公室里坐着,远远就听见了她的声音。她的语速很快,仿佛要把一段话急切地抛出,语调又有着孩子气的尖细,在词和词的连接处,有着浓浓的江浙风情。和她通过无数次电话,她的声音,成了我最熟悉的她。声音以外的老友,又会带来怎样的惊喜呢?我飞速跳出办公室,看见她在楼道里拖着行李箱,柔顺的短发蓬松地绕成弧形,瘦弱的身体藏在宽松的麻质长衫里,活脱脱是传说中的“森女”,满是雨后森林的气息。我大声喊了她的名字,其他人哈哈大笑起来,笑我的唐突和激动,好像粉丝遇见了明星。
他们并不知道,我和草白的友谊已经有了漫长的历史,无论写作还是生活,她都是我乐于请教和交流的挚友。给这样的朋友写印象记,我总是谨慎的,因为所有的印象记都有变成漫画的风险。我最喜欢的印象记,还是《世说新语》,寥寥数笔,写一件事,一个动作,甚至,只是一句话,都极为生动传神。可问题在于,我对《世说新语》依然无法做到十分的信任,那些截取,那些塑造,无疑暗含了作者的价值取向。魏晋人充满烟火气的日常生活,是我特别感兴趣的地方,可它真的在《世说新语》中吗?
说这些,也许是我不自信的表现,我怎么能写出草白的形象呢?她是那样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她像鲁迅的野草一般在顽强和快速地生长,充满着无限的诗意和可能性。
谈及对一个作家的印象,最深的其实还是对其作品的印象,都说文如其人,人如其文也许更准确,我们不可避免,都被语言所塑造。我第一次知道草白这个古雅的名字,是因为读到了她的散文。现在的许多小说家都不愿意写散文,他们怕自己不多的人生经验在散文中被透支,也怕散文的写作干扰了小说的写作,从而便用专一代表专业。当然,从大的方面来说,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也影响到写作这个行当,作家自觉局促于自己的文体道场,本是无可厚非的。可我还是向往那种大文学的写作,就是无所拘束,只将文体当成是内心之思的某一种具体的承纳形式。因此,我也爱读诗,爱读散文,我是在网上一个“80后”散文写作群里,读到了草白的散文,眼前一亮,这文字里,诗、思、人都在了。
草白的散文并不长,都是一些错落有致、直击内心的短章,寥寥几笔,一片灵魂的风景就出现了。
印象最深的,是她一篇名为《一个懂鸟语的人》的文章,我被感动了。她写了一个哑巴与鸟儿的无碍沟通,这确凿证明世间有我们听不见却真实存在的天籁之言。我分明感到,那哑巴的形象正是她对人类存在的一种认知。人,其实很大程度上对话语交流是不信任的,尤其写作的人,更加深谙这一点,因此,作家的孤独书写,便是对回答的不抱希冀,只求心间的话语物化为文字,得以自足自立。而鸟儿作为上帝的天使,又使那不求回答的话语,获得了神秘而超越的回应。因此,哑巴又何尝只是草白?我们每个人也许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哑巴。那个哑巴的形象,从此在我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迹。
对她的散文,实在还想多说几句。
她的《消失的孩子》,不妨视为一篇小小说,他的童年怎么就不见了?童年是什么?没有童年的童年,会是如何的境地?我回味了许久。还有《听话》一文,里边的祖母形象极为生动逼真,“听话”也有了两重意思,一是听祖母说话这个行为,二是虽然听得太多而觉出了“重复的悲哀”,却还是真正听进去了,将老人的美德铭记于心。那种微妙的情愫,在草白笔下缓缓流淌,温润人心。《野果》再次证明了“草白”这个笔名绝非随意而起,它注定了作者与大自然的无限亲近。吃,是人与自然最深层的接触,是把自然请到人的内部来的过程,这其间的奥妙,已经被草白发现。体现在她的生活中,她基本上是个素食主义者,最多喝喝鲫鱼豆腐汤什么的,讲究的是从外到内的清洁。
一个同龄人,写出这么好的作品,给我的鼓舞是巨大的。写作,是一件孤独的事情,滋养我们写作的,大多是一些历史上的亡灵或是现实中的著名人物,他们离我们有时太过遥远了,因此,当自己的身边出现了优秀的写作者,那种感觉就像是暗夜中遇到了同行者,可以给荒原上踟蹰的自己以巨大的慰藉,能够让我们在脆弱与迷惘之际,依旧敢于壮胆放歌。草白那森林般的宽容与神秘,让人乐于和她一起耽于做梦,轻松自在,故而我时常把一些未成熟的想法与她分享,这也是向她学习的过程。
某个周末,我和草白在网上狠狠聊了一次,好像聊到了凌晨,那对按时作息、生活规律的草白来说,尚属首次,估计网络那头的她早已是睡眼蒙眬了,但她拒不承认,带点逞强的味道。那次聊天,终于让我们接上了头,我们很开心,就像是两个蠢蠢欲动的革命党。对于现代文学的热爱,对于写作创新的渴望,都让我们兴奋和激动。我觉得我们应该一起做点什么,思来想去,便拉她和我一起参与台湾的联合文学新人奖,我告诉她,这是王小波得过的奖,你要能得,那就厉害了。我这么热情,当然是给自己的又一次慰藉和壮胆;一起参与评奖,无疑是想把我们变成一起作战的战友。
草白一开始还有些犹豫,架不住我再三忽悠,她终于同意了,她说:“好吧,我可是陪你的。”很快,她写了一个短篇,叫《木器》,那是一个爱做木匠活的老爷爷。主题是死亡,叙述却有一种孩子气的单纯腔调。“爷爷老了,大概快一百岁了,一个人不是皇帝,却活那么久,这简直自取其辱。”开篇第一句,多好的语感。小说里有她散文的韵味,又多了想象、虚构与诗性,那个叙述的孩子,在我脑海里活灵活现的,就是童年的小草白。
几个月后的一天,草白神神秘秘地给我发了封邮件,她说有人通知她获奖了,但她觉得那是假的,是有人想骗她。我看了她转发来的贺信,上面言之凿凿地写着:“草白的短篇小说《木器》夺得了第25届台湾联合文学新人奖的首奖。”我瞬时就激动了,赶紧祝贺她。但我越是祝贺,她越是惶恐,她反复质疑这件事情的可信度,觉得也许是有人跟她恶作剧,甚至诈骗。因为那时还没到公布奖项的日子,她的那种态度,让我也迷惑了起来,现在网络骗子横行,莫不是像她说的,其中真有诈?我建议她给组委会邮箱发信确认下,然后还不忘提醒她,如果有人问她要钱说要寄证书奖杯什么的,一定不能给!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草白当然无可置疑地荣获了那个奖。她去台湾环岛了一圈,给我寄了张明信片,上面印着一片开阔的海。再回想之前我们忐忑怀疑的情形,不免可笑了。时过境迁,现在回忆起来,充满了青春的杏仁滋味。听说过许多这样好玩的故事:陪朋友去比赛、陪朋友去试镜、陪朋友去相亲……成功的似乎总是作陪的那个人,证明了“无心插柳柳成荫”才是至高无上的生活哲理。感谢草白,让我生命中也有了这样的传奇。
《联合文学》有一期获奖专刊,记录了整个评奖的争辩过程,评委们对《木器》有着一致的赞美。我想,那个奖对草白是相当重要的,因为这不仅让她获得了认可,更重要的是,这让她意识到:“我是能写小说的!”随后,她便有一系列的小说喷薄而出。像是《土壤收集者》、《惘然记》、《我是格格巫》、《热气球》、《墨绿的心事》,都得到了许多读者的喜爱。如果说她的散文展现了她静思的一面,她的小说则打开了她想象的一面,我觉得后者对她来说,可能更重要,这也是她为何向往写小说的原因。过于静思的生活,需要跳跃、飞升甚至摔碎,才能保持住生机与力量。这算是一种生命动力学的规律吗?我不敢确定,反正,在草白随后的人生选择中,印证了这个判断。
草白原本有一份特别让我羡慕的工作,好像是在嘉兴的地方网站做编辑,非常轻松,大约下午四点的时候,她就下线回家,买菜做饭去了。因为面对了一天网页的缘故,她晚上基本不上网,安安静静地读书养神。因此,要找她,必须要早。我非常羡慕这种赶早的人,我觉得个人的时间表能比社会时间早运行一会儿,就多了一份从容。但是,凡事总有例外,草白就属于这种例外。她跟我说,她不想工作了,想彻底自由,在家写作。我以为她是玩笑话,谁还没说过这样的话呢?我还专门写过一篇小说,就叫《辞职》,主人公被一个游戏弄得辞职之后,无边的自由让他感到了崩溃。所以不管她如何反复说,我都没放在心上,直到有一天,她真的辞职了。得知这个消息,我是相当愕然的,所幸,网络那头她也看不到,我心里很想说,那样清闲的工作,还需要辞职吗?也许,被无边的自由吞噬,是一种典型的男性思维吧。男人,这种社会化的动物,从社会之网中漏出来,一定会有深深的失败感。这是我从草白随后的潇洒生活中,用逆向思维得出的一点感悟。女人,并不惧怕自由,更能忍受虚无。就像草白,她不在自由的波涛上,而是在自由的深处,她的安静,她的母爱,她的沉思,她的自然,都让她可以成为自己的船锚。她有时间出游了,一时在青藏高原上驱车,欣赏天地大美;一时,又在云贵高原的洱海边独坐,感悟人生襟怀。我只能通过她的空间相册,追随她的步伐。再读到她的文字,多了复杂之美,她在变得丰富和充盈。我们,都在向人生的深流涉去。
多年的友情沉淀下来,彼此以及彼此间的交往方式,都成为了生活中的一部分,虽未谋面,却总觉得像曾为同学一般,熟得不得了。因此,似乎也没有了启程去见见朋友的动力,依旧随着生活的浪潮波动,沉溺在自己的环境里,心底倒是相信,总有一天会相见,只是早晚罢了。2015年,机会终于来了,我冲到楼道,初次见到了故人。见面虽没有生分的感觉,但毕竟还是有了不同的感受。尤其对草白的笑容,印象特别深刻。以前见她,都是在照片上,她喜欢与草木合影,双目低垂,表情覆盖着一层淡淡的忧郁,甚或忧伤,但那表情中又夹杂着笃定与平淡。于是,我想象与她见面时,她的笑一定是安静的微笑,有洞察了岁月秘密的沉稳。及至见她,才发现她是开怀大笑的人,相处时大方得体,喝酒时浅尝辄止,既有亲和力,又有正能量,毫无忧郁的影子。
知道她喜欢穿棉、麻的衣服,但没想到,她全部的衣服都是棉、麻的,连围巾也是,真是自然的女儿。印象中那些衣服似乎质朴低调,不算鲜艳,但仔细看过去,明明是很丰富的,红、蓝、绿等亮色全有。除了衣服的质料原因,更重要的是她自身的气质吧,那些颜色全都服从于她的气质表达。我们一群人在象山港坐船看海,她安静地待在船舷一侧,我时不时会想,这个女孩像是一株离开了陆地的草木,在海上她会孤独吗?我跟她聊天,她又笑了,像是一株在任何地方都能存活生长的植物。上岸后,我们在一片晾晒海带的“丛林”里照相留念,她和这些大海的头发站在一起,如同一枚别致的发卡。当镜头对准她的时候,她的笑容瞬间收敛了,那熟悉的忧郁又出现了,她甚至闭上眼睛,好像整个人退守到了自己的小天地内部,将我们撇在外边。看来,她更愿意让自己内在的一面,被呈现出来,她与世界的关系,是一以贯之、不想伪饰的真诚。
当然,她笑起来很好看的,在这里想对她说,草白,你下次多照几张开怀大笑的照片吧。
那次活动期间,还有个小插曲。某天下午,我们的参观车出发了,半途才发现草白不在,打电话过去,她说记错时间,睡过头了。那会儿,已经来不及接她了。晚上吃饭的时候,见到她,我问起,她说是因为我告诉她错误的时间,一点半出发,我说两点。我回忆起来,自己的确说了可能两点之类的话,但我午睡的时候,特意看了行程表,确认了时间,还专门调了闹钟。我下意识想,大家定会和我一样,回去看行程表的,谁想到,草白竟然对我的随口一说深信不疑,从这个细节上看出她对朋友的那份信任,这让我大感抱歉。时隔许久,我再问她,那天下午做什么了,她说还是有点儿难过的,像是被抛弃了,只好逼着自己读书,那对她,成了难熬、难忘的一个下午。我忽然感到,自己对这位老友的敏感和脆弱,所知甚少。而那,正是写作的动人之处,注定了她要独自驻守。
我从没见过一个人的网络签名,有草白这样的精确:“世界人生虽即十分实在,其托置在无可奈何的迷惘之上却是事实,只有投身自然可稍稍减轻一些这份迷惘。”人最难的就是自知,可草白是十分了解自己的,她写下的,和她体验的,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也是为什么,她的文字具备击中人心的力量。那些文字,源自她生命中的真实。真实,而不是真理,那其中有迷惘如风,让她摇曳、让她不安,但她愿意做草,最朴实最顽强的植物,从此,没有什么能阻止她的思想和自由,没有什么能阻止她的写作,没有什么能阻止她,尽情成为一名被自然宠爱的女儿。
(责任编辑: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