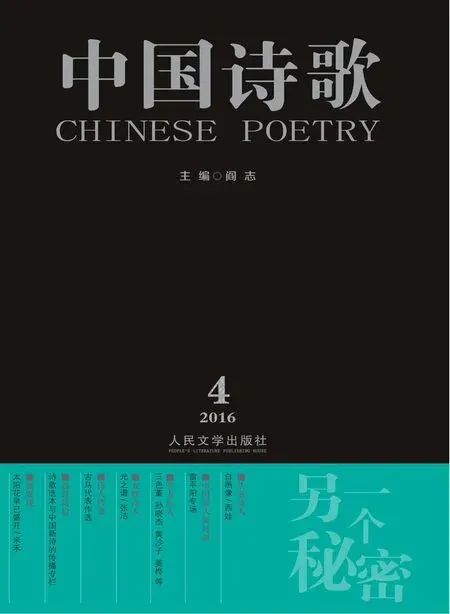自画像(组诗)
2016-11-27□西娃
□西 娃
自画像(组诗)
□西 娃
我……
我天生愚笨,爱上
阿赫玛托娃,帕穆克,布考斯基,释迦牟尼……
有时也玩一些修炼术
希望自己能脱胎换骨
却没祈望自己成为
我之外的另一个人
我长得矮小,鼻翼上留着疤痕
常常在世界各地的电影里
贪婪地看着屏幕上的俊男美女
却从未祈望自己变成
我之外的另一个人
我比“我”更清楚
这个上半身臃肿,下半身轻飘的人
失重地活在人群里
招来一些爱慕,怨恨的男女与魂灵
与之纠缠,清算,翻不了身
那些从不曾哭泣的男女和魂灵
在今生,在这样一具丑陋的身体里
把自己和我,同时哭醒
书架上的圣贤们
他们死了
并不完整的精神与魂灵
在书里
被分散在不同的书架上
部分魂灵与精神
将永久死去
我腾出大量的时间
腾空大量的心
在慢慢读他们
很多书,很多圣贤
无论我花多长时间
多少热情与温度
他们依然是死的
只有很少的一些圣贤们
在我的阅读中
慢慢活过来
他们附着在我的身心上
写一些还不曾写出的句子
发散一些不曾有过的想法与情绪
于是我从不说
通过我的手写下的这些文字
仅仅源自于我
“那首诗在哪儿呢?”
有那么一刻
它在我的房间里来过
在我的心里来过
当我从俗事中回过神来
它已离我而去
我的房间里回响着
“你从不属于我一人”
滴水观音喝完白天的阳光
又喝白炽灯惨白的光
家具门陷入死寂
我从一个屋子到另一个屋子
在心中搜寻它可能的印记
我和屋子中的一切
用了一个黄昏
又半个夜晚
供养了一首不会再来的诗
诗歌稿费
我从未乱花过诗歌稿费
它们来得这么不容易
每领一笔
我就积攒起来
去买一双绣花鞋
不同尺码的绣花鞋
从未上过我的脚
把它们摆放在书架上
无数个我
从书架上出发
去到我从未去过的地方
——这是2012年之前
之后
我把所有的稿费
用于买各种真丝裙子
我穿着它们去不同的地方
那些我从未用眼睛看清的生灵
附着在我的诗裙上
被我带回书房
第一张自画像
已经是第二个下午
已经是三十年后的北京
已经是离四川两千多公里的
一面镜子里
我举着笔却动不了笔
比我此刻样子更清晰的是
一座寺院改成的教室里
龅牙的张姓图画老师
在授课
粉笔尘与四溅的唾沫
扑向第一排女孩脸上
她用三年级图画课本
挡住脸
趴在课桌上啃生红薯
他拎起她衣领
她又瘦又黑的四肢在空中乱划
红薯掉在地上
她被置于黑板底下
于他调笑和命令声中
于52个同学眼睁睁中
沾着泥土的生红薯
被她在泪流满面中啃完
吞咽
是,这个女孩就是我
那之后,我再没动笔画过任何东西
这是我惟一的地盘了
你一次次给我讲述
你的梦
你那么多梦里
都有我
每次
我都避开你的目光
我一次也没梦见过你
我的梦
通常不接通现实
我的梦里
通常没有其他人
亲爱的
我不能责怪你
始终走不到我梦里来
我也更不想责怪自己
没有在梦里
为你开一扇窗,留一条缝
这是我惟一留给自己的地盘了
并没被睡眠与梦拐跑的人
对语言看破的能力
迫使我怀疑嘴上任何言语
迫使我通过别的途径
去寻找爱的证据
多年来,我对单人床的迷恋
使我拒绝了别的床
而现在,我躺在一张大床上
旁边是鼾声四起的你
想离开,想重新回到
我的单人床上
我无声息地跨过你的身体
这被梦与睡眠主宰的你
在这里,在别处
这也是我们此刻的距离
在我掉下床的那一刻
你一把抱住我
连说宝贝没事没事
你的反应让我吃惊
你的反应也让自己吃惊
仿佛你在睡着时也看着我
然而,你迅疾睡去,鼾声如雷
仿佛这一切本身就发生在你的梦里
轮转
我们在酒后拥抱彼此
指甲陷入对方的白肉里
我们都不出声,疼痛和红酒
把两个身体变成一个
又慢慢虚化成一个巨大的空洞
我失去身体,失去你
在失去方面,我总有多余的闲心和明智
苦痛像黑夜之中的寂静,滋生,浮游
指望在另一个身体上落地
而我希望它选择你,又希望放过你
我在自虐与虐你的臆想中
生出新的爱情,生出新的爱你的方式
你早于我醒过来,你的眼神
比我失去的身体更孤单。你再次用性爱
找回我,找回我没有声音的哭泣
剧烈的战栗中
你把被我咬破的拇指
再次放上我的牙齿
老等
你伸着长长的脖子
一只脚独立在冰冷的水里
你的身后是一望无边的盐碱地
你的前方是茫茫的水域
你一动不动
把身线拉得笔直
黑白相间的影子
在夕阳之中,在碧波之上
没有人知道你在等什么,而你在等
你自己也不知自己在等什么,而你在等
你不在乎能等到什么,而你在等
你不惜把自己等得孤苦伶仃,你还在等
你有绷直的信念——老等
你已经把自己等成一个符号——老等
你忘了自己是一只鸟,而你把自己等成了一只鸟
远道而来的我,憨痴痴地望着你
我像被水浪拍打至岸滩的鱼,喘息中
暴露了自己掩盖多年的心迹——
“吃掉我吧,老等;结束吧,老等!”
两条赤鳞鱼
它们终于又相遇了
两条赤鳞鱼
在一个女诗人的肠胃里
在泰山半山腰的泉水中
它们活着,相恋,一晃七年
极阴的水性使它们拥有小小的身体
用小小的身体捕食,用小小的身体生育
同一天,它们被捕
一条跟被捕的鱼群
送到山下的餐馆
另一条被送到山顶的餐馆
而她被当作贵宾招待
在山下吃下一条
她又爬上山顶
吃下了另一条
仿佛她从山下到山上
仅仅是为两条鱼的合葬
提供一座坟墓
梦游中的挖坟者
他痛苦得如同死去——
父亲被埋葬第五天
被人从坟墓里挖出来
暴尸荒野
他找亲戚帮忙,并发誓要杀了
这个十恶不赦的坏蛋
而父亲已经被第三次
从坟墓里挖出来
他白天埋葬父亲
有人夜晚挖出父亲
当他们抓住
这个十恶不赦的坏蛋
他被人从梦游中喊醒
惊讶地看见自己
孤零零地站在旷野中
——父亲被挖开的坟墓前
他一手拿着沾满黄土的铁铲
身上披着
父亲最喜欢穿的中山装
嘴里叼着
父亲死后才离手的旱烟斗
——活脱脱父亲,生前的模样
神灵以各种方式,让你知道他的在
她纸人一样扑倒在我床上
这已经是第几次了?
她在枯死的家庭生活里
侍候老公,做家务,在爱情故事片里度日
有两次,趁她老公出差
偷偷跑去与前情人
约会,而每次,要么在半路
要么在与情人刚见到时
她老公电话都会及时追过来
直接问她在哪里
她守在家里的所有日子
他几乎不给她任何电话
每次她受到惊吓,都会跑到我这里
一次次问:“难道真有一只眼睛在监控我
难道真有神灵存在吗?”
这个像被什么瞬间抽空的人
这个始终喜欢用“巧合”概括一切的人
这个从不相信神灵的人
她纸人一样扑倒在我床上
在一条买不起裙子的路上
每当我的女儿
用软软的声音问我:
西娃娃,我们什么时候住大房子
西娃娃,我能不能开上保时捷
西娃娃,我什么时候能当富二代
…………
我就拼命喝水
有时呛出鼻涕,有时呛出眼泪
有时,呛得什么都出不来
我不忍心告诉她
在我还是文学少女的时候
就看到作家赵枚写的一篇文章
大意是:她领了一笔稿费
去商场买一条渴望已久的裙子
她站在橱窗前,把手中的钱
拧出水来
也没能买得起那条裙子
如今的我,正走在这条
买不起裙子的道路上
女儿
她走过来
躺在我身边
“妈咪,你失恋了啊?”
她的声音愉快起来:
“你以后属于我
一个人了
你会发现
我比男人都靠得住。”
她又转变声音:
“哦,妈咪
你要对我好点哦
不然
我也会离开你
你会很可怜
更孤单。”
她的声音低下去:
“就像我……”
叮嘱——给女儿
你已到了恋爱的年龄
作为你的母亲
你嘴里的女神
惟一要叮嘱的——
你可以与色盲,傻子,精神病患者
或一切别的什么人
去谈情去说爱
但,不要去碰触
已经在婚姻中的任何男人
他们给你的所有感受
都是为了最终
用痛苦将你洗白
同时,他们还会给你
一开始就备份好的
“对不起!”
是的,你的母亲
与婚姻中的某个人
恋爱过
留下的伤口,在许多年间
除了“呵呵呵呵”的傻笑不停
今天还都发出如此之声
那么多的名字
我给你们取过名字
那些
曾在我胎盘中居住过的
孩子
你们被剥夺了
诞生者的所有权利
从而只留下名字
我文档里的诗歌
这些流产的生命
你们出现过
我却没有能力
让你们完整地诞生
而你们拥有过
完整的名字
这么多的名字啊
那么多深夜
你们不用我呼唤就跳出来
扯动着你们鲜活的五官
像一群群白色的蚂蚁
横行在我肉体里
意识和梦的能量
我对体重挑剔近乎苛刻
“连自己的肉体都没办法的人
有什么资格去过问
自己的灵魂?”
我的谬见却成为我的座右铭
最近,我的体重莫名其妙猛增
我依然日食一餐
依然每天疾走十二公里
我在四处寻找让我发胖的原因
直到这个夜晚
一个怪异的男子
告诉我
他每天晚上
都用自行车带着我
去吃他中学时代
最喜欢的排骨面
我吃得那么贪婪
吃完自己的一大碗
还把他的一半吃完
当然,是在他不停的意识里
偶尔也发生在他梦里
墙的另一面
我的单人床
一直靠着朝东的隔墙
墙的另一面
除了我不熟悉的邻居
还能有别的什么?
每个夜晚
我都习惯紧贴墙壁
酣然睡去
直到我的波斯猫
跑到邻居家
我才看到
我每夜紧贴而睡的隔墙上
挂着一张巨大的耶稣受难图
“啊……”
我居然整夜,整夜地
熟睡在耶稣的脊背上
——我这个虔诚的佛教徒
进入你最好的位置
每次你来,总有夜雨
窗外的一切在雨中潮湿
我的潮湿来自于你的轻微喘息
我有那么多哀怨
见你后却发不出更多的声音
我像游鱼,在你的身体上
游过可能的缝隙
你身体里有我正在寻找的食物
我无法确切知道,它是什么
当你用我的头死死捂住你的胸口
你以为我是一个没有五官的人
你以为我从不需要呼吸
你似乎要把整个的我,摁进你的身体里
好吧,能进入你
这可能是最好的位置
缘分
火车惊破平原的清晨。窗外
一棵大树。一抹霞光。一轮轮
五彩的花圈。一队白色的人们
又一个人,离开了人群
去到阴性的世界,享受活着时
不曾有过的安宁。我的目光
带着羡慕,送走他
与我擦肩而过的一生
我们如此确信自己的灵魂
我们如此确信自己的灵魂
比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肉体
更为确信,仿佛我们真的见过她
亲手抚摸过她,弯下身来为她洗过脚
在夜间闻过她腋窝里的汗味
在清晨听过她的哈欠声与唇语
我们如此确信我们的灵魂
确信她比我们的肉体更干净,更纯粹,更轻盈
仿佛我们的肉体,一直是她的负担
我们蔑视一个人,常常说他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
我们赞美一个人,常常说他是一个有灵魂的人
是什么,让我们这样振振有词,对没有凭据的东西
对虚无的东西,对无法验证的东西
充满确信?
如果有一天,一个明证出现
说灵魂是一个又老又丑又肮脏的寄生物
她仅凭我们的肉体得以净化,并存活下去
崩溃的会是一个,还是一大群人?
从崩溃中站立起来的人,或者从没倒下的
会是怎样的一群人?或一个?
另一个秘密
在暗处,在任何人的目光都无法
看到的地方:她绝望地看着他
——这个坐在原木堆中的雕刻师
他正一点点地雕刻她。鼻子,眼睛,唇……
她从暗物质中分离出来,被迫拥有身形
她多么恨他。宛如一首诗,她游荡
以任何形体。却被一个诗人逮住
被造物与造物之间的敌对关系
悄然形成——这是另一个
秘密:“不要以为,你给了我形体,就给了我
生命。”孩子这样告诫他的母亲
与我隐形的同居者
就是在独处的时候
我也没觉得
自己是一个人
不用眼睛,耳朵和鼻子
我也能知道
有一些物种和魂灵
在与我同行同坐同睡
我肯定拿不出证据
仅能凭借感受
触及他们——
就像这个夜晚
当我想脱掉灵魂,赤身裸体
去做一件
见不得人的事。一些魂灵
催促我“快去,快去……”
而另一些物种
伸出细长的胳膊
从每个方向勒紧我的脖子
跟失落一样无所依恃
我的身旁不仅有影子
还有上帝
他们总是在我身体的另一边
我的前面不仅有明天
还有死亡
明天和死亡都不是我的终点
我的左边不仅有你
还有心跳
有你时,我的心跳会加快一点
没你时,也不曾停止
由此我活得如愿望一样独立
跟失落一样无所依恃
灵魂
为了让我的肉体
能在这块土地上站直
我把大多数时光用于生计
灵魂像影子
斜斜地躺在地面上
与脚一样高低
我的身子拖着它
它擦着地面,流出的血
没有颜色
很多时候,灵魂
像没有光照的影子
我并不知道它在哪里
只有夜晚,我们躺在一起
如一张床上的老夫妻
在两床被子里
嗡啊呐
一条毒蛇窜进梦境里
我看到自己瘫软在地上
嘴里哆嗦出令我费解的声音:
嗡啊呐
你在冬季越过几个国度来看我
见到你的那一刻
我听见心中某个地方弹出一声:
嗡啊呐
我在深夜里静坐
当看到自己与澄明的山脉
化为一体又长出山脉时
整座群山发出同一种唱声:
嗡啊呐
“嗡啊呐”,你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总在我无意识时冒出来
它属于突如其来的秘密咒语吗?
它是我身心和灵魂遭到意外时
突然的出口么?它是否仅仅属于我?
嗡啊呐……嗡啊呐……嗡啊呐
“现在你自由了”——
当听到丽莎·凯丽的无字之歌
嗡啊呐,我不再问你到底是什么
厄瓜多尔西
她又给我取了一个绰号
——厄瓜多尔西
她说
厄瓜多尔西
你总穿一只袜子,另一只又找不到?
你腰上的肥肉,可以煸出一大碗油了
你白天泡在股市里
夜晚不是看电视连续剧
就是抱着手机刷微信
你听好了
厄瓜多尔西
中年人堕落的速度,是
皮球滚着下楼梯
见我没理会
她不停捶打我肩膀
我知道,你也写不出什么名堂
但我还是喜欢你写写写
她突然眼泪花花
厄瓜多尔西
我写作的妈咪哪里去了?
我闷声说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是:厄瓜多尔西
我的客人们
我有很大的客厅
里面有沙发
墙上挂着壁毯
几架书籍
几箱影碟与音乐碟子
几尊佛像
我从不曾在这里
迎接过现实中的客人
而我的客厅里
却有不断的客人
我从不问他们来自哪里
也不问他们的名字
我们不用任何语言
只用心交流
他们源源不断拿走我的孤独,寂寞
他们给我送来寂静与丰腴时光
使我不曾想过
去邀请或接应现实中任何人
来做我的客人
为什么只有泪水,能真实地从梦里流进现实
女儿在薄被子里
激烈颤抖
她的喊声很悲伤:
“带我离开这里
我讨厌这里,我要回去。”
我摇醒她
把她带离梦境
她在哽咽中讲述——
总梦见那个蒙面人
她也不知道他是谁
但她相信他
能把她带回去
我问她想回哪里去
她说不知道,但
肯定不是这里,不是
这个现实世界里
这样的梦境发生,已经不是第一次
“只有现实是真的
哪里都是假的,假的
包括梦!”我喊
像已经失去她很多次
“那,为什么只有泪水
能真实地从梦里流进现实?”
她指着枕头
上面湿了一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