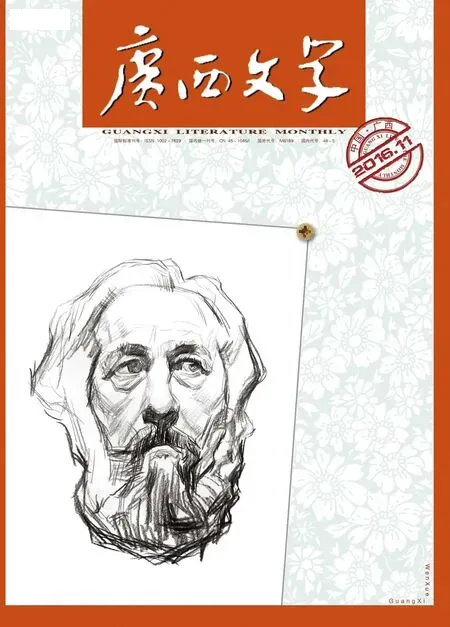经验的,叙事的,迷人的
2016-11-26陆辉艳
陆辉艳
发端于2006年的广西诗歌双年展不觉已抵达第二个十年。与往届不同的是,本届双年展规定了主题:叙事性写作。叙事性的诗歌并不好写,而对于一个有自觉追求的诗歌写作者,提高写作难度,显然是有必要的。
近两百位诗人的稿件,有一些诗作虽然也具备优秀的要素,但从叙事性写作的角度,最终筛选出目前一百一十三位诗人的诗稿。综观本次广西诗人与河北诗人“联合演练”的诗歌大展,文本在叙事性写作上所呈现的多重方向和视角,以及诗人们对叙事性写作的纷呈见解,构成了两地诗人各自丰富而又独特的话语空间。如下几个关键词可以大致勾勒它们的多彩面孔。
关于日常。生活的复杂性不得不令诗歌叙事、诗歌现场必须由叙事性来完成。它也许来自人生的某段经历,某个梦境,瞬间的记忆或经验,不论是晴朗李寒的幻觉中似曾出现过的“大雨中奔跑的男人”,黄土路笔下的“神”,还是张弓长的《当人死去,我们在做什么》中存在与遗忘的日常,都属于在具体生活中尚未轻易说出,却在一首诗中通过细节呈现的那部分。
里尔克说:诗不徒是情感,而是经验。往往是这样,一首诗中不是精致的修辞和娴熟的技艺打动我们,而是诗人表达的独特经验,和现实发生碰撞,刮擦出痕迹的那部分,给我们带来非同寻常的惊喜和震撼。
诗歌中的叙事性,还原了被修辞和隐喻遮蔽的真相和细节。对于表现现实经验和人性的复杂性,要更为可靠,准确,也更接近生活的真实。诗中呈现的碎片化经验和细节,实际上隐藏着完整的生活原型。而叙事性的想象经验,在于它高出现实的省察,如刘频的《1976年的红薯》、朱山坡的《7月4日在西贡》、羽微微的《记录》、莫雅平的《总爱瞎想我是第四只羊》、吕斐的《生活在原地》等,正是诗中脱离具体的事件而被抽象的那一部分,拓展了诗歌的空间和能指。
关于叙事的节制。相对于日常与经验的传统叙事,一部分诗人如郁葱的《忏悔录》、盘妙彬的《三江断片》、大解的《他人》、李浩的《镜子里的父亲》、《北野的《某一年》等,似乎更侧重于内心的轨迹变化,去除烦琐的细节,叙事更为节制,其视野范围向宽广的时空、历史及存在的意义辐射,使诗性多了些哲学思考和向度的延展。
美国诗人、小说家雷蒙德·卡佛在他的随笔《关于写作》中有一段关于语言的描述:“在写诗或者短篇小说中,有可能使用平常然而准确的语言来描写平常的事物,赋予那些事物——一张椅子,一面窗帘,一把叉子,一块石头,一个女人的耳环——以很强甚至惊人的感染力。”“平常然而准确”的语言更多地出现在小说写作中,但也正符合叙事性的诗歌语言的特点。一部分诗人的语言具备了这样的特点,精简,克制,诗中的叙事将我们带入及物的语境,它所呈现的是语境背后本来的生活,径直切向生活的真实,却获得了迷人的、“惊人的感染力”。
关于语调。诗人徐俊国说过大致如下的一句话:那些发着低烧和高烧的写作,都是不正常的,只有带着正常体温的写作,才能听出诗人真实的心跳。“正常体温”,说明了一首诗中用什么样的语调很重要。《叙事》(刘春)、《老约翰谈一场战事》(李南)、《霜降》(黄芳)、《儿童时代》(晨田)、《在驾驶楼顶聊天》(庞华坚)、《一个多门的房间》(陈振波)、《加班》(蓝向前)等诗作,低声调的写作,增强了阅读的在场感和亲和力,也让诗中的语调更接近写作者的体温和气息。而一首诗的气息直接呈现出一个诗人独有的精神特质,它甚至为作品打上醒目的DNA烙印,具有不可复制性。
关于抒情。叙事性与诗歌的抒情性并不构成对立。相反,叙事性为抒情提供了更为坚实和丰富的内核。霍俊明的《雅典的橘子树》,非亚的《杏仁饼》,他们一开头直接用叙事语言写天空、橘子树或某个咖啡馆,然而仅仅是在写眼前的场景吗?前者接着将镜头对焦街角的诗人、错位的生活、时空与鸽子,后者转向那块带着时间记忆与情感的“杏仁饼”,有点类似于电影的转场,诗的空间从此处拉向远处,因而前面所有的铺陈都是在为抒情而准备,叙事部分增加了诗歌的张力和弹性。因此,无论诗歌的表现手法和形式如何变化,“它的本质仍是抒情的”(孙文波语)。
或许,本次策划的主题仅是一次有意为之的集体行为,诗人们却早已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关注到诗歌写作中的叙事性。甚至,本届双年展出现的一部分90后、00后诗人,他们的写作似乎一开始就是从叙事性起步的。我们看到叙事性在本次大展诗作中的作用,同时也看到它所存在的问题,过于铺陈,沉溺于琐碎的细节与对话,在处理现实经验时流于事态的表象化,为叙事而叙事,对诗中的抽象空间提纯和省察不足,仍需引起诗人们的自我观照和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