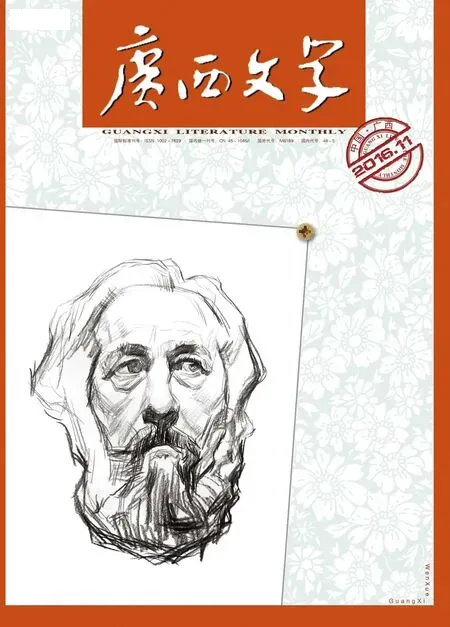诗与叙事:片面的随想
2016-11-26李浩
李 浩
1
凡墙皆是门。这漂亮的短语大约出自林白,我觉得说出这样的话的人深谙文学之道:任何一种创作都不应给自己划出“不可以”的禁忌,它需要不断地冒险,突围,以及整合,从其他中汲取。凡墙皆是门,那些伟大的作家,往往是在小作家们或者时代习惯以为“此路不通”的地方破墙而出,走成了门,直至走成了大道。“此路不通”,往往是我们被规循得太久了,是我们在不自知中画地为牢,是那种前行意识的潜在匮乏——我以为。
让叙事进入到诗歌,增加诗歌中的叙事成分,是诸多诗人们已有的成功尝试,属于它的“开拓性”其实已变得微薄,但对它的言说和梳理似乎还有相当的必要,毕竟,对它的抵御还是普遍自觉,毕竟,给诗歌加进“新的负载”并不是通识,尤其是在“叙事诗歌”一直遭受漠视、一直未充分展开的中国背景之下。
“人类社会的童年时代早已过去,那时自然和非自然,事实与想象,好像几个亲兄妹,在一个家庭里玩耍吃喝,长大成人。今天,它们发生着巨大的家庭内讧,这是连做梦也没想到的”——这是泰戈尔在谈及历史小说的时候所说的一段话,我觉得它也可应用于我们的诗歌和诗歌中的叙事:在人类社会的童年时代,叙事和抒情,和想象,和思考,好像是几个亲兄妹。但随着时代变迁,随着各文体间的慢慢长大,这个家庭里的内讧也是明显的,对立的,分歧的,甚至变得格格不入——在我看来,它们当然依然具有重新整合的可能。
2
整合,从其他中汲取,是我一向所看重的。诗歌,也应当有一个庞大的、吸收良好的胃。它不仅要从叙事的文体中汲取,也应向哲学的、社会学的、历史的政治的、心理学的……在一切人类的智慧中汲取,成为它的有机部分。
随着人类智识的不断增加,情感的不断丰富,审美的不断变化,我想,诗歌在不失自我特性的前提下应会随之不断丰富复杂,变得更有意韵也更有言外的巨大空间。这时,简抒情很可能会变得乏力,苍白。叙事性的介入应是解决简抒情问题的通道之一。叙事和叙事性,更多的是小说的——没错儿,但文学间的互通有无本来就是常态,文学的价值至少部分的价值就在于它的“拓展性”,是故,才会有人用片面深刻的方式强调:所谓文学史,本质上应是文学的可能史。任何跟在已有的习规之后的写作都是可疑的,会让自己不自觉中“渺小的后来者”。我相信诸多有野心的写作者都不甘心如此,即使这种“渺小”会带来更多的名声和利益。
小说家们早早就开始了向诗歌拓展,这种拓展是一贯的、持续的,而数量众多的小说家会把“诗性”看做是对小说的至高称颂,甚至如此宣称:小说,本质上就是诗的。在杜拉斯、胡安·鲁尔福、福克纳、马尔克斯那里,我们能够明显感受着来自诗的影响,而像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他甚至把大量的诗加入到小说中;而像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在把诗性注入到文字的同时,他还把属于话剧的、诗剧的、舞剧的言说方式融解于他的小说中,让他的小说变得丰厚有趣。耶利内克、尤瑟纳尔、赫塔·米勒……如果列举名字,我也许能把几乎所有的伟大小说家列入。他们在努力地整合。
而诗人们——为什么小说家们可以如此拓展,向诗歌“攻城掠地”,而我们诗人们就只能退守,或者偏安于抒情的一隅?
当然,让叙事进入到诗歌、增加诗歌中的叙事成分并不是诗歌“一时兴起”的诉求,它也具有某种持续性,经历着诗人们的不断调试。
3
叙事的介质融入诗歌之中。就像是——它让诗歌发生着反应,物理的甚至是化学的,让它变得——它将增加诗歌的丰厚感、浑浊感和歧义,生出更多的向度,自然其“外延”也随之拓展。这其实是一种现代性的“相称”,是艺术发展的内在动能,是诗歌自我生长和繁殖的趋向之一。我不会轻易否认艺术的生长性或“进化论”,任何一种具有伟大感的创造都应具有前人艺术经验的综合,同时,又是“对未有的补充”,诗歌当然也是如此,更应如此。
在这里,我所强调的是“叙事的介质”而非“叙事诗”,它并非惯常的“叙事诗”的完成,它也并非再次让叙事性成为核心而忽略抒情性——我看中的是前人经验之后的变化、拓展、丰富,以及重地注入。
你为什么要旅行?
因为房子太寒冷。
你为什么要旅行?
因为旅行是我在日落和日出之间常做的事。
你穿着什么?
我穿着蓝西服,白衬衫,黄领带和黄袜子。
你穿着什么?
我什么也没穿,痛苦的围巾使我温暖。
你和谁睡觉?
每夜我和一个不同的女人睡觉。
你和谁睡觉?
我一个人睡觉,我总是一个人睡觉。
你为什么向我撒谎?
我想我说的是实话。
你为什么向我撒谎?
因为实话像别的不存在的事物一样撒谎,而我热爱实话。
你为什么要走?
因为对我来说什么都没更多意义。
你为什么要走?
我不知道,我从来都不知道。
我要等你多久?
别等我,我累了,我要躺下。
你累了吗?你想躺下吗?
是啊,我累了,我要躺下。
马克·斯特兰德,《献给父亲的挽歌》节选,这一章节的题目是《回答》,他为进入到死亡的父亲虚拟了声音。巧妙的是,对同一问题的回答往往指向相悖,而它也完全可以由同一个人做出。马克·斯特兰德在叙事性中注入了撕扯的力量,从而使它更耐回味。它是对具体的“这一个”的追问,但同时又是针对所有人的,而那种貌似的不经意又能让我们进一步“感同身受”。在《献给父亲的挽歌》中,马克·斯特兰德按捺住情绪,他平静描述,却在具有叙事意味的描述中建立了层层的、旋转着的涡流。我们可以拆解诗中的每个语词并加以阐释,解析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解析它的言外之意,解析它内在的哲学思考……而在另外的诗人那里,叙事所带来歧义和丰富可那样不同,譬如在西尔维娅·普拉斯那里,譬如《珀耳塞福涅两姐妹》,譬如《锅匠杰克与整洁的少妇》(它完全由引语来完成,仿佛在诗的一侧站着一个不停诉说的人),譬如那首《与挖蛤的人一起做梦》:
这梦发芽了,边缘长出明亮叶子
它的空气被天使筛得洁净;
她回到海滨小镇上先前的家,
枯燥的朝圣之旅损伤、玷污了她。
她光脚站着,因那回归而颤动,
邻居家房子旁,
屋顶板被擦亮如玻璃
那炎热的早晨,百叶窗被拉下。
什么也没变:整个夏季
熔化的沥青散发刺鼻气味,花园的露台
向大海倾斜,深入蔚蓝;整个场景
被白色火焰喂饱,闪烁着迎接这漂泊者……
由情境开始,在这里,更属于“故事”的部分被普拉斯安置于“前史”之中,而这前史则交给了隐喻:“枯燥的朝圣之旅”。是的,这首诗充满着梦幻般的气息,它的芽茎一直在生长,即使具体化的、叙事化的情境描述也不能让梦幻的感觉有丝毫消弭。叙事性,在这首诗中建立起的是延伸通道,它延伸至语词的外面很远很远,需要阅读者调用经验和想象补充,诗中,只说她回到了小镇,“什么也没变”——谁能言说她的离开,究竟经历了什么?她返回到“什么也没变”的时间和这座称为家乡的小镇上,谁又知道她身上的变化,和她对变化的可能隐藏?隐喻化的前史有着极其模糊的指向,其中巨大的歧义性让我们无法准确确认,即使在诗歌最后突然渗透:“他们阴森如石像鬼,常年蹲在海的边界,/在缠绕的野草与海草之间等待,以便/在她首次爱的行动中诱捕这任性女孩……”情境是具体而稳固的,但她的前史和对前史的猜想则是跳跃的,未完成的。
马克·斯特兰德诗中的叙事介质使他的诗获得了丰厚,这丰厚多少来自于“思”的成分,它容纳阅读者不断向里面注入自我的生命认知,并让你审视;普拉斯诗中的叙事介质同样使她的诗获得了丰厚,不过这丰厚来自于我们对“事件”和发生的想象,它吸纳的是“体验”、感受和猜度。
4
叙事的介质融入诗歌之中,它另一显在的用意应是粘接“现实感”和“经历感”,让对它的阅读都更有身临其境的在场。它会将你吸入,让你成为参与者,甚至会调用你的相似经验以完成诗歌在言说中点到却有意不曾充分表述的“未尽之意”。谈及现实感,我首先想到的是爱尔兰诗人希尼。希尼善用叙事的辅助完成他对生活的理解和思考,他承认,他尝试“要使那种生活的真谛具有一种具体的真实性”,“最为欣慰的时刻是诗作显得最直接,成为其所参与、所辩护和所反对的世界的一种最前沿的再现的时刻”(《归功于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是的,他的诗,因由叙事的介入而生出了“日常生活的神奇”,他致力于“再现”,致力于运用把“具体的真实性”和“生活的真谛”粘合于一起的神秘药方……譬如他反复被人阐释的《挖掘》。诗中,“我父亲正在挖掘”的情境完全是现实性的,是描述,仿佛将我们的目光也吸引至窗口,和西默斯·希尼一起向窗下看去——它在把我们拉入场景的同时也把我们的情感拉入进来,让我们成为诗歌的参与者,情感的参与者。诗歌的叙事往往会把我们看成是具有参与感的“观众”,或者是经历者,它要用叙事的手段建起“戏剧”的帷布,让我们跟着戏剧的上演而不断调整自己的投入,直到阅读者和写作者悄悄地融为一体。
譬如,雷平阳的《杀狗的过程》:
这应该是杀狗的
唯一方式。今天早上10点25分
在金鼎山农贸市场3单元
靠南的最后一个铺面前的空地上
一条狗依偎在主人的脚边,它抬着头
望着繁忙的交易区。偶尔,伸出
长长的舌头,舔一下主人的裤管
主人也用手抚摸着它的头
仿佛为远行的孩子整顺衣领
可是,这温暖的场景并没有持续多久
主人将它的头揽进怀里
一张长长的刀叶就送进了
它的脖子。它叫着,脖子上
像系了一条红领巾,迅速地
蹿到了店铺旁的柴堆里……
主人向他招了招手,它又爬了回来
继续依偎在主人的脚边,身体
有些抖。主人又摸了摸它的头
仿佛为受伤的孩子,清洗疤痕
主人的刀,再一次戳进它的脖子
刀道的位置,与前次毫无区别
它叫着,脖子上像插上了
一杆红颜色的小旗子,力不从心地
蹿到了店铺旁的柴堆里
主人向他招了招手,它又爬回来
——如此重复了5次,它才死在
爬向主人的路上。它的血迹
让它体味到了消亡的魔力
11点20分,主人开始叫卖
因为等待,许多围观的人
还在谈论着它一次比一次减少
的抖,和它那痉挛的脊背
说它像一个回家奔丧的游子
它几乎全然地交给了叙事,为了强化其真实性,雷平阳甚至不得不牺牲部分的“诗意”而将时间(今天早上10点25分)、地点(金鼎山农贸市场3单元,靠南的最后一个铺面前的空地上)落实,努力让我们“信以为真”,仿佛这一过程就在眼前发生,仿佛我们是其中的旁观者,是想要抽身都有些困难的经历者——那种弥漫着的血腥气被我们嗅到了,那种痛感也因此作用于我们的神经末梢,仿佛,我们始终“看见”。这种看见的、仿佛在场的力量与一般抒情相比较,我以为它或许更有震撼力一些,也更为直接、浓厚。
5
叙事的介质融入诗歌之中,另外的用意也不应忽略:它会强化诗歌的陌生感,强化“意外”,强化具体差别——从而使写下的诗歌与旧有完成区别,生出更重的新颖感,甚至“灾变感”。求新求奇,是训练有素的阅读者普遍的心理,没有谁愿意只阅读那些已经被惯常言说过一千遍的旧识,没有谁愿意咀嚼被别人咀嚼过一小时之后的口香糖,在诗歌抒情性意味被惯常不断消耗的当下,叙事性的注入大约是让诗歌言说生出新意的有效方式。
似乎是米兰·昆德拉说过,自然主义的乡土其诗意已经被反复的咏唱所耗尽,而蒸汽时代的坚硬开启挤尽了含在自然中的最后汁液,“你无法想象自己还能像约翰·济慈或者勒内·夏尔那样写诗”——这一含有偏见和武断的论调自有其深刻性,事实上它也可应用于我们对于乡土诗歌的某种理解:新意已被耗尽,工业化改变了人与土地、夜莺和田间生物的关系,那种对自然的歌咏已无魅力可言。然而,西默斯·希尼借助“叙事性”撬开了乡土的板结。他为乡土的事物建立和他的境遇相连的故事,并填入具有深意的感吁,于是,诗歌有了陌生,诗性作为种子被重新埋入并开始新的生长,枝繁叶茂起来。譬如我随手翻到的这首《铁轨上的孩子们》:
当我们爬上铁路边的陡山坡
我们的眼睛与电线杆上的
白磁轴、发热的电线平行。
像随手画的可爱的线,它们
向东边弯出几英里又转而向西,在
燕子们的重负下垂着。
我们都很小,自认无知
毫无价值。我们以为话是装在发光的雨滴小邮袋里,
在电线上旅行
每滴都饱含着
天空的光亮和电线的闪耀,而我们自己
在天平上是如此微不足道。
我们甚至能穿过一个针眼。
我们都很小,自认无知,毫无价值——孩子们的这种想法是谁给予的?此刻,我们如何看待他们的这一“自认”?……它是有波澜的,它让人可以百感交集,然而如若没有那种“叙事的具体”,如若不提供“铁轨上的孩子们”立于电线杆下的情境,它的波澜会遭受巨大的削弱,我们的感慨也许会轻若在风里飞起的羽毛。我们再一次假设,假设希尼只提供乡间的自然场景:爬上陡坡的孩子,铁轨,电线杆和落在电线上面的燕子,细细的雨滴——那种唯美也许同样不具备感吁的波澜。
是叙事让它克服了可能的轻。是叙事,让它具体的同时又生出了陌生感,才让我们付出更多的注意,才让我们细细品啜其中含有的滋味,让我们回望自己的童年和生活。
6
叙事的介质融入诗歌之中,可以增加诗歌的丰厚感、浑浊感和歧义,生出更多的向度;可以使阅读者更具“亲历”的现实性,让阅读者有更多的身心投入;可以使诗歌样式从惯常的抒情样式中挣脱出来,从而更具新意和陌生。除此,叙事的介质融入到诗歌,还能较好地打通时间的困囿,打通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困囿,增强其自由度;它还会部分地强化诗人的个人标识。
认识叙事性对诗歌的有用并无太大困难。而巨大的难度在于,在自我的写作中完成调和。对诗歌而言,任何一首优秀的诗歌其诗性和诗意都是充盈的,必须获得充分保留,而增加叙事性则必然会对诗性构成减损,我认为它们之间的“危险平衡”需要得到反复调适。叙事成分的增加,它会增加诗歌的黏稠度,会下沉,那就要求诗人们必须在诗句中经营好凿空和留白,让它重新获得轻逸和飞翔。再一点就是,诗歌重情绪,往往截取时间片段,着力于一隅一点,而叙事性的融入则会不经意拉伸它的时间性,至少是数个片段的串联——其中的得失利弊也需要权衡。
福克纳谈到,写作,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我也深以为然。不惮试错,不惮冒险,本是写作的应有之意,无论是诗歌、小说还是言论。我的这篇拉杂的文字就含有试错的意味,它的片面性让我竟有种随时出现的崩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