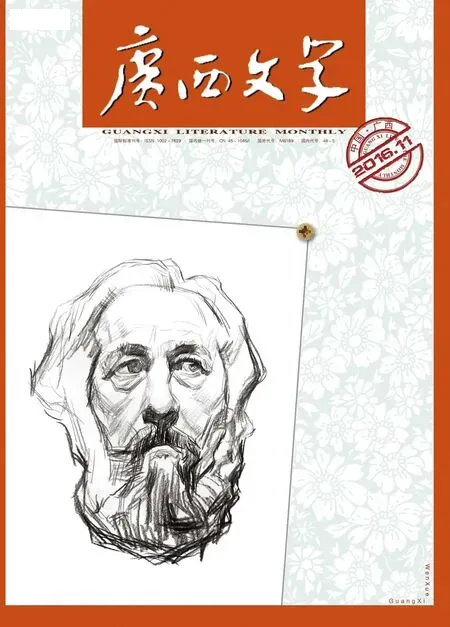膨胀的经验,微茫的诗歌
——《广西文学》诗歌双年展专号阅读札记
2016-11-26颜炼军
颜炼军
一
在上百份当代汉语文学杂志中,因偶然的机缘,我细读了这期《广西文学》诗歌双年展专刊。稍微对诗歌圈有所接触的人都会有同感:中国大,写诗的人多到认不清,光是各式各样的笔名都把人搞懵。由于我的诗歌阅读面太小,这期刊物里的诗歌作者,我大多都头一回听说。他们来自偌大中国的两个省份,广西和河北,其中许多作者不是原住民,而是从别的省份到那工作、生活或学习的。由于刊物编辑的一个策划,他们的作品被放在一起,归入“叙事性”这一主题下,但其间的差异是显然的,各篇作品与“叙事性”之间也有出入。这么说,非是怪编辑考虑不周,而是感慨,名实不对称,乃人世间常态。君不见,对于当代诗歌的有效命名,历来也是批评家头疼的填空题。
诗歌研究者对当代诗歌实况的了解,仿佛盲人摸象。可以说,想搞清自己时代的诗歌,如妄想拎起自己的头发脱离地球一样难。这么说,似乎是在指责诗歌研究者不尽职,但其实是为研究和批评开脱:历史上似乎没哪个时代的人能看清当时的诗歌,经典,几乎都是被追认的,而且还会不断变化。因此,对我而言,读这期诗歌专号,相较阅读已被不同程度地经典化,或被阐释、辨认过的作品,阅读感差异很大。一方面,我们不能期待刚过去的很平常的两年间,这两个省的诗人中就会有惊世名作诞生;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尚相信奇迹可能发生的天真读者,我依然怕错过某一行刚面世的好诗。事实上,在阅读过程中,我遭遇了众多坏诗句的“围追堵截”,许多“不成熟”甚至“失败”的文字,不断地“压低”甚至“推翻”我原有的审美标准。也由于此,若偶尔发现好的诗行——它们在此间显得更抢眼,会让我有披沙拣金的喜悦。
但随着阅读的持续和深入,上述这种带着“先见”的阅读感逐渐褪去,一种新的阅读感渐渐覆盖了我和眼前的这些作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厌烦或欣喜,也非批评家不得已而为之的挑剔,更多是一种写作社会学意义上的探视和理解,在此基础上才有审美化的拣选和辨析的混入。
二
首先引起我兴趣的,是这些作者的年龄和身份。从60后到90后,他们都属于当代中国的青壮年群体,也是社会各单元里的中坚或不久后的中坚。他们的职业几乎涵盖了我们可想到的各种行当:政府公务员、企事业员工、教师、个体户、私企老板、各类媒体从业者、自由职业者、在校大学生,等等。需要说明的是,我看到的作者名录,已经是杂志社删汰过的。我相信,倘若杂志社“放低”要求和标准,这期刊物可以变得更厚,作者的面孔肯定也更丰富多彩。换一种假设,如果哪家刊物以同样的标准选择诗人和诗作,做一次全国性的双年诗歌作品展,那么这本刊物必定会非常厚,甚至要分为几大卷装订出版。
我由此产生一些想法和疑问。多少年来,宣布和诅咒诗歌死亡的声音不绝于耳,诗歌在许多时候成为大众媒体嘲弄的对象,但它却在这么多诗人和诗作中安逸地活着。没人统计过中国到底有多少诗歌写作者,但仅从这期杂志推算,一定是个庞大的群体。为何这么多不同身份、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和出生背景的青壮年中国人,都不约而同地在写诗?照常理,诗歌作为一种个人化的、偏于精神性的表达形态,与当下中国人追逐物质化的生活南辕北辙,可为何还有这么多可能永远不会获得所谓“文名”的写作者?我想,对大多数“无名”状态的写作者而言,写本身可能比博取所谓的“文名”及其背后的象征资本更具有内在的重要性。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写作,一定与内心的某种“隐秘”需求相关。这么说的理由很简单,首先,写诗只是一种相对纯粹的特殊表达方式,在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带来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或“财富”。另外,只要看看许多作者稀奇古怪的、充满想象力的笔名,也便可揣知缘由之一二:这些笔名,很可能意味着他们对另外一种生命状态的向往,或者说,是对现有生命状态的一种象征性逃离。说得夸张一点,虽然浪漫主义语汇被各种政治和商业话语大肆利用,但这些写作者依然试图继续发明属于个人的浪漫主义语言,依然试图以写作的方式优化个人的生活世界,换言之,诗歌作为内在性的表达,无论表达技艺的优劣,都源于写作者对现有生活及其符号化方式的不满和不安。
由此出发,我想到,在目下的社会,在疯狂地追逐物质生活,追逐权力,疯狂地消费,疯狂地抬高房价,疯狂地教育孩子,疯狂地强调“正能量”的同时,人们也得以各种方式来承受从疯狂中松懈、败退下来的“自我”。社会极端的功利、势利和腐化,当然可以让许多事情由于更邪恶、更赤裸裸而富于激情和欲望,但也会滋生令人透心寒的乏味、枯燥、无望和不满。这种二律背反,也许才是这个时代的阴阳和黑白。看清如此悖谬的处境后,我们或许会惊叹人性之坚韧:我们之中只有少数人被“撕碎”,患抑郁症甚至弃世,而大多数人,似乎都找到了游刃有余的应对方式,写诗可能算是其中之一?讲到这里,我突然有一种会令许多人觉得迂腐可笑的幻觉:诗歌之于当代社会很重要。至少可以这么说,人们从疯狂中松懈、败退下来,退回自身之际,无论何种形式的诗意吞吐,都可能是治疗和修复被“疯狂”摧残的灵魂的手段,由此,或许我们就能部分地理解,为什么这个时代的青壮年群体中诗歌写作如此普遍而隐秘,因为他们大都被迫奔跑于时代的疯狂漩涡之中。
阅读这期刊物上质量参差的诗作,完全可以印证这一点。这些诗涉及当代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直接或间接的战争记忆、“文革”经验、抑郁症患者体验,到域外旅行体验;从乡村贫困场景到城市生活中“畸零”者;从被毁坏的自然到迷宫般的城市形象;从肉厂排成长队的猪头到被牵到街上挤鲜奶出售的绵羊;从弃婴到近些年发生的地震;从乡风民俗到打工生活场景;从乡土社会的溃败到个体身体遭遇的痛苦;从普通百姓的车祸到贪腐官员的被捕;从个体失控的欲望到我们奄奄一息的慈悲心肠……在这些诗作里可以看到如此丰富的内容,它们,正是构成当代中国人记忆和经验的基本零部件。按20世纪美国诗人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的话说,它们堪称当代诗歌写作者的“超级意象垃圾场”。欧美理论家强调后现代社会经验的破碎化和扁平化,其起因之一,是对前现代社会具有整体特征的社会经验的缅怀。但反过来看,现代社会经验的破碎和扁平,同样是一种整体性感受,尤其对当代中国人而言。各色相反的、相去甚远的经验与记忆,在所有个体身上的奇妙而艰难地融合,这造成的莫名的灵魂艰难,可以说是当代诗歌写作,也是当代中国人面临的整体性精神困境。如果把这种困境放到陶渊明说的宇宙天地的“迈迈时运”之中,也许只是人类这一宇宙间的生僻物种刹那间的抖动;但对置身其中的众多个体,它就是一个巨大的需要突破的长期困难。对于诗歌表达来说,它像一个复杂幽深的迷宫,所有写作者都在用词语发明各自的阿里阿德涅(Ariadne)线团,谋求突围,追寻荷尔德林说的“更高的生命”。那么这个诗歌的“线团”应如何展开?如这期杂志策划者所注意到的,当代诗歌对“叙事性”的实验和追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同时也是个技术难度很高的展开方案。
三
顾名思义,叙事就是对“事”的语言陈述。“事”天然有过去式的特征,即使是正在发生的“事”,也随着陈述而流逝成过往云烟,故东坡诗云,“事如春梦了无痕”。由于这个时代已不再有可信的先知和预言家,所以当我们说某人在讲述将来之“事”时,这个“事”只存在于语法正确的语言之中。实际上,人们只能根据已往和目前的“事”来推测将来之“事”。将来之“事”,充其量仅为过去之“事”的一部分。
人类很早就意识到“叙事”与艺术之间的关系,比如在希腊神话里,缪斯女神的母亲,是记忆女神。柏拉图也认为,人类的所有知识和艺术都产生于对遗忘的抵抗。灵魂和肉身的结合,让人类天然地会遗忘,而灵魂对自身与肉身结合之前的纯然状态的追忆或追述,就产生了知识和艺术。作为诗歌技艺之一种,“叙事”意味将个体或群体之“事”编织为语言的序列,既然是“事”后编织,就意味着遗忘、取舍和重构,就意味着对“事”本身的叛离。
作为语言陈述之一种,在许多情况下,出于写作有效性之需要,诗歌特意以叙事手段来完成自己而形成的文本特征,我们称之为叙事性。在当代汉语诗歌语境下,狭义的“叙事性”,是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诗歌里特有的抒情性而言的。简单地说,80年代诗歌里浓厚的抒情气质,是通过编织高于日常生活的主体形象,来完成社会情绪/经验的诗意转换;而90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中强调的叙事性特征,则是以编织低于或屈服于社会历史逻辑的主体形象,来完成社会情绪/经验的诗意转换。相较而言,前者是通过主体而展开世界,因此偏于抒情;而后者必须通过紧箍着主体存在的世界——社会历史、日常生活和芸芸众生,来发现和命名主体,因此叙事成为必需之重要手段。诗歌研究界对此已经有共识: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诗歌的现实对立面发生了变化。先前的种种普遍被认同的无论是作为个体的、还是集体的精神追求,已经失效或被抛弃。诗歌写作对此的整体反应,是对80年代汉语诗歌追求的崇高性进行了调整,日常经验和尘世的事物,通过叙事性写作,在诗歌写作里获得重要位置。
当然,关于当代汉语诗歌里的“叙事性”,也有需要反思的一面。它在90年代以来的当代诗歌写作中的逐步泛化,加之网络时代带来的写作的随意化,常常让有特定诗歌史背景和技艺内涵的“叙事性”,被许多写作者简化为对经验的回车—分行式的简单复制,这种不顾经验与诗歌之间巨大跨度的恶劣写作风气,其负面影响是显然的。
由于上述背景,我们今天再讨论诗歌的“叙事性”时,一般都显得更为审慎。严沧浪说“诗有别裁”。正因为一个“别”字,所以无论对任何写作观念的实践,肯定只有少数的成功者。事实上,如今再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偏于“叙事性”风格的大量作品,其中失败之作肯定远远多于好作品。而好的作品几乎对“叙事性”都抱有某种警醒,因为从根本上看,好的诗歌天生具有反“叙事”的特征。叙事,意味着有情节、有故事,但我们绝不会觉得某首好诗之好,是由于它讲了一个精彩的故事。无论是荷马史诗这样的长篇史诗,还是当代以来被认可的叙事性诗歌,其中都有诸多克服“叙事流”的“礁石”和“逆境”,叙事意味着一种经验化的词语推进逻辑,而诗歌的逻辑,却是要以词语的新锐和爆破,来超越经验秩序的束缚,这里头的区别,类似于一部差电视剧和一部好电影在镜头组接方式上的区别,看一部好电影,我们满心期待下一个令人惊异的镜头,而看一部差电视剧,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少许内容猜出后面的镜头和情节,因而生厌。直言之,在一首好的叙事性诗歌里,诗的逻辑肯定会很好地控制、化约叙事的逻辑。
四
或云,什么是诗的逻辑?我们以这期的作品为例,来展开对这一问题的辨析,看看两种逻辑之间“博弈”形态。先看有位叫六指的年轻诗人写的一首叫《上弦月》的诗:
一个卖红薯的老汉猫着腰
蹲在马路边 他没有吆喝
始终保持地里红薯的沉默
城里的夜在他的脸上洇开
又被深深浅浅的褶皱分隔
四处乱窜的风像来扫荡的城管
舔舐着他手中小半截劣质香烟
他的目光如烤熟的红薯般瘫软
呵 天有些冷了
今晚一个红薯也没卖出
他不自主地将那些冷凉的红薯
那些仿佛从他身上剥落的器官
一个挨一个紧紧地拢在了一起
而他的背后 上弦月刚刚探出头
仿佛被谁切掉了一块 切口崭新
像挖伤的红薯 淌着白色的浆液
在当代诗歌写作里,社会同情心、草根性等社会伦理层面的因素,已经很常见甚至很廉价,它们在许多时候很必要,却不能让内行人对表达它们的诗行产生敬意。要表达上述这些主题,服从于经验原则的叙事逻辑,是可以完成的。这首诗给我们留下了好的印象,原因恰恰是诗人非常好地在他的“叙事”中植入了一些反“叙事”的关键。诗人非常努力地摆脱经验逻辑的掣肘,继而上升至对编织言词肌理的实验。我可以具体看一下作者是如何努力的:在第二节里,每行诗里都有一个不错的比喻,句尾押韵;第三节中的比喻也很贴切,到第四节,起句很好,诗人有意以月亮形象打开了新空间感,且颇费心思地发明了全诗里最精确的一个比喻:刚出头的上弦月像“挖伤的红薯 淌着白色的浆液”(有乡村生活经验的人大概都知道,红薯被挖伤时会分泌出白色的浆液)。这首诗里上述这些引人注目之处,恰恰是诗人在语言形式上下的细功夫,无论是押韵,还是每节中出现的奇异比喻,都是诗人让诗歌语言形式超越目击经验的努力。对目击经验的讲述,很容易沦为单纯的叙事,而诗人不满足于此,他非常自觉地把“叙事”变为诗之“傀儡”,让叙事作为诗歌完成自身的一个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
还有一首名为《叙事:献牲》的诗。作者祁十木是宁夏的回族,1995年出生,在广西上大学。这首诗,写的大概是诗人家乡杀羊的场景。限于篇幅,我们仅截取该诗最末一部分:
这只羊像躺在手术台上一样,四蹄朝天,
余下的呼吸渴望被救,而灌进去的只有气体,
他的皮肤膨胀起来,羊皮、刀子、骨头、内脏的摩擦
清晰。肠子、肺、肝、蹄子,都遗落
在地面上,一个脚印,没有人踩得出
我们一生的忏悔和恐惧,用这只羊代替
导致我不敢看一眼,那张被褪下的羊皮
似乎要站起来,像我三天前丢了的新衣裳
整首诗写杀羊的过程,典型的叙事诗。但诗人在羊的体验与人的体验之间,建立起非常好的交织关系。每行诗里都有精雕细琢的字词,“余下的呼吸渴望被救,而灌进去的只有气体”这样的诗句很棒,它精微地呈现了包括人在内的所有动物临死的生理和心理状态。最后两行的比喻,修辞上充满了惊险,由此生发的想象空间亦十分撼人心魄。这些,都克服了一般的叙事可能导致的苍白。
此外,在张弓长、许雪萍等诗人的作品中,都有很不错的叙事克制。我很喜欢许雪萍的短诗《骤雨》,在此诗中,个体的记忆、存在,与目击景象之间生成了一种密响旁通的关系:
那团乌云,此刻正停留过窗外的天空
低沉,墨色,带着饱满的阴晦。
现在,它盘旋在我的脑海里。
那个秋天,我们就在一团乌云下。
我,妹妹,还有救护车里的爸爸。
后来,雨沿着车窗
猛然倾注而下。
痉挛的雨脚,我的眼前一片混乱。
救护车旋转的鸣笛。
妈妈尖锐的号哭。
这一切,随着时间模糊。雨声渐渐回荡
在远处的田野。
我拉上帘子。内心的静谧
近乎忧伤。
耳边回响的喧哗
近乎疯狂。
倾听,只能这样倾听
听时光——
哗,哗哗,流逝的声音。
我们可以分两层看这首诗。宏观上看,诗人非常好地把关于个体经验的“叙事”,化入对于诗歌精密形式的追求。所谓形式,就是窗外的阴晦的乌云,“我”此刻的忧伤,爸爸的重病(作者别的作品中写到了他的死亡)三者之间玲珑而隐秘的映射关系。微观上看,此诗字词、诗行之间的勾连和推进都张弛有度,每一个形象都制作得非常好:从窗外的乌云,车窗外痉挛的雨脚,到末尾对时光流逝的倾听,都有比较具体精确的呈现。读毕这首诗,我们某种意义上不仅是被诗歌的主题感动,更是惊讶于诗人为制作这一主题的而营造的语言形式感,它像一个词语做成瓮,发出的一阵阵静谧得近乎忧伤的鸣响。
总之,当代诗歌中的“叙事性”追求,的确给20世纪90年代以来诗歌写作带来了一次巨大的转变:在经历了各种必要的和不必要的高蹈之后,诗歌写作开始重新贴近个体微观经验视野中的社会历史场景。然而,“叙事性”也给诗歌写作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叙事天然地强调对经验的模仿和呈现,可诗歌天然地向往超越琐碎苍白、同质化的日常经验的牵拘,进而建立某个超验的、宇宙的、永恒的维度。后者更需要想象力,更需要“称名也小,取类也大”(《文心雕龙·比兴第三十六》)的诗歌抱负和语言才能。这些,可能是这期专刊里许多诗歌所缺少的。其实,由此也可以大致窥见当代诗歌写作面临的一些整体性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