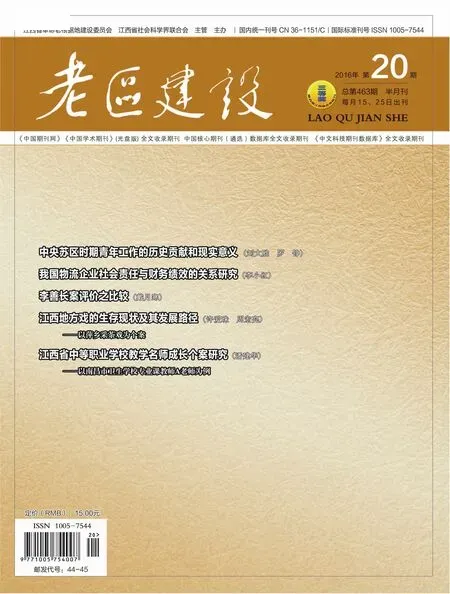李善长案评价之比较
2016-11-26戴月寒
戴月寒
李善长案评价之比较
戴月寒
[提要]李善长少年时代即随朱元璋南征北战,虽未有摧城陷阵之劳,却多运筹赞画之功,是名副其实的开国功臣。然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颁布《昭示奸党录》,李善长以胡惟庸党诛,连同其全家七十余人一并被处死。后世对于李案的评价,似以视其为冤狱者居多,但也不乏态度较为模糊、中立者。对李善长案的评价之差异,较为直接地反映出了评价者的立场和思想观念,并为多角度、全方位地看待该案提供了佐证和启发。因此本文将在梳理和比较的基础上,对评价观点进行深入探讨,并阐发相应的认识。
李善长案;朱元璋;明初政局
明初的一众功臣中,李善长以其资历之深而素有威望,他年长朱元璋近二十岁,被称为”里中长者”①。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谋反伏诛”,牵连死者甚众,而“善长如故”。时年六十余岁的李善长虽然在胡惟庸案的第一次冲击下屹立不倒,十年后却以同样的罪名结束了生命与政治生涯,这种戏剧性的跌宕不可谓不引人深思。因此李案所带来的影响不仅持续时间长,且波及范围广,从纵向上来说,在当时、在后世都未见减弱,从横向上来说,该案一直受到文人、政客等的广泛关注。经梳理,众多评价大致可分为为李氏鸣冤的“鸣冤派”和态度相对模糊的“中立分析派”两个派别,在大致叙述李善长案始末后,本文将对两个派别的代表观点进行归纳和比较。
对李善长案的探究和讨论,自明朝至今从未停止过,值得注意的是,当代对于李善长案的研究呈现出了更多新的论调和观点。后文将对明、清两朝的一些主流观点进行具体评述,就现代相关研究而言,比起过去单纯为李氏鸣不平,很大一部分学者的观点已经转向了关注君臣矛盾、利益冲突或者阶级利益等客观动因,相关文章如《胡惟庸案与李善长死因新探》②、《浅析明太祖朱元璋与李善长的君臣关系》③、《朱元璋与李善长》④等。也有支持传统观点即认为李氏案乃冤案的,如《评李善长之死》⑤。总而言之,多角度、多立场化的研究为此案的探讨增添了新的角度和启发。
一、李善长案始末概述
李善长,字百室,濠州定远人。少年时代“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⑥,朱元璋平定滁阳后,因其在乡里中有德有识,遂留用为掌书记。之后的二十余年间,李善长在朱元璋军中左右调和、掌管军资、出谋划策等,至朱元璋称吴王之后,李善长已颇受重用。从“李善长、徐达等率群臣奉太祖即吴王位”“以李善长为中书右相国”“命中书省定律令…乃命李善长、杨宪、傅綊、刘基、陶安等详定”“善长率群臣以即位礼仪进”⑦等等,不难看出当时李善长俨然已群臣之首。明朝开国大封功臣,于洪武三年(1370年),为李善长授号“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晋升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进爵韩国公,年禄四千石,子孙世袭。当时封公者六人,李善长位列第一,制词中更是将其与萧何比肩⑧,至此,可谓荣耀已极。而张廷玉评价李善长“外宽和,内多忣刻”⑨,李善长先后与参议李饮冰、杨希圣和中丞刘基发生争端,并于洪武四年(1371年)因病致仕,一年后病愈归官。从洪武五年(1372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历经李善长之子李祺尚临安公主,御史大夫汪广洋、陈宁上疏奏李善长不敬,胡惟庸经李善长推荐并与之往来甚密等事件,李善长渐渐受到怀疑和疏远。洪武二十三年四月,李善长请求赦免亲戚丁斌等,丁斌供词称李善长之弟李存义与胡惟庸往来之事,李存义父子供词又牵连李善长,加之其奴仆卢仲谦的旁证。李善长因明知谋逆而不检举之罪,应验占卜之祸事,当年夏五月,“乙卯太师韩国公李善长自杀,时年七十七”x,其妻女弟侄等全家七十余人亦被处死。明初胡蓝之狱,上至缙绅大员,下至普通官吏,虽牵连甚众,然鲜有资历深厚而获罪遽重如李善长者。因此,后世对李案的评价说法不一,认为李案仍然存疑的观点也不在少数。
二、评价之主流观点
对于李善长案的评价,大体能够划分为两个派别,其一即主要为其鸣冤,且归罪于朱元璋本性嗜杀的“鸣冤派”;其二,即态度相对中立,认为李善长案乃多方面因素结果的“中立分析派”。本文所选取的例证,除去洪武一朝,多为嘉靖、万历朝代文人的观点,现代学界观点亦有之。
鸣冤派,主要观点如其名,乃为李善长鸣不平,至于援引的证据则因人而异。同时代的代表观点,当属解缙为王国用代草的《代李善长辨冤疏》,该奏疏为李鸣冤的出发点并非建立在已成型的供词和罪状上,而是从李氏的实际地位和动机进行深入、细致的剖析,并对朱元璋加以劝诫,此处选其片段:
使善长佐惟庸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妃而已矣,宁复有加于今日?且善长岂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当元之季,欲为此者何限,莫不身为齑粉,覆宗绝祀,能保首领者几何人哉?善长胡乃身见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为此者,必有深仇激变,大不得已,父子之间或至相挟以求脱祸。今善长之子祺备陛下骨肉亲,无纤芥嫌,何苦而忽为此。若谓天象告变,大臣当灾,杀之以应天象,则尤不可。臣恐天下闻之,谓功如善长且如此,四方因之解体也。今善长已死,言之无益,所愿陛下作戒将来耳。
王国用认为,李善长事上数十年,当知天下之“不可幸取”,其本人已位极人臣,子孙亦蒙受恩德,在其晚年并没有谋逆的必要,况且即便权柄易主,李氏至多也不过当日地位而已,身份不会更加显赫,因此没有任何动机。代王国用起草奏疏的解缙,也执同样观点,“尝考大绅在河州时,曾寄贝川书,有云‘曾草谏书,为韩国公事,为詹徽所嫉,欲中以危法。’则知代草非其意也。”⑩而朱元璋对这份奏疏的反应,《明史》记载为“竟亦不罪也”,这无疑加剧了后世对李善长案中或有隐情的猜测。同样为李氏鸣冤的还有袁鄻、谈迁、赵翼等人。袁鄻认为李善长功比萧何,即便定罪为“胡党”亦不能抹灭其功绩,“李公一书生,固守根本,晏然亡虞,此与萧何何异”“其所奏定法制,纲洪目细,可法可传…岂以胡党少之哉”⑪。谈迁的评论则更为直白,“末年刑书定自家奴之口,此厮养者流,果足蔽大狱、示大信于天下乎?…史称礼葬之厚恤其家…或史笔曲为之饰耳”⑫,直接指出李善长案定罪不足以服众,更怀疑礼葬和抚恤等举动是为尊者曲笔。
至清代,为李氏鸣冤的声音仍然不减,赵翼的评论常见于史家引用:
李善长佐明祖起兵,位至上相封公,年七十有七,全家诛戮。传中既附著其锻鮻之爰书,又载王国用为之辨雪一疏,以深著其冤。…皆以见明祖之猜忌好杀,可知立传之用意也。xiv
赵翼认为,胡惟庸死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而胡党之狱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逆首已死十年,所谓“同谋之人”方才败露,实为借胡惟庸为题,牵连诸人而已。末了,赵氏将原因多归罪于朱元璋“猜忌好杀”的性格。
吴晗亦在《胡惟庸党案考》中对李善长之狱的真实性直接提出质疑,“《实录》纪李善长狱事,尤暧昧支离,使人一见即知其捏造。盖其所述谋反情事,皆援据当时狱辞,其不可信,又无待究诘”⑬。不难看出,对李善长定罪所依托的证据多来自于当世口耳相传的语言记录,缺少更多的实物证据,也是“鸣冤派”提出质疑时重要的立足点。
另一派别,即中立分析派,该派别的态度较之鸣冤派更模糊,多认为李善长案咎由自取的成分不可否认,并从多角度出发说明其历史必然性。代表例证如顾起元之评价:公尝奉诏归凤阳矣,复召理事,称疾力辞,或可以免,不见信国之休沐而安乎?信国之谨厚,上所信也;公之智略,上所疑也。疑而欲远迹以自引,则益厚其疑。…以驸马祺之亡恙,王国用之无罪知之。上临驭久,天下安慰之虑深,无将之戒,不得不严,以肃臣纪耳。此高皇帝所以独断于九重,而公之所为甘瞑于万世者矣。⑭
类似者,査继佐同样认为李善长受到朱元璋的怀疑、疏远,最终招致诛戮,虽属朱元璋刻意为之,但很大一部分仍应归罪于李善长本身识人有误、眼光不够长远,“识不足镜人,又短自全,于是惟庸之罪久而益增,而所以议韩国之同惟庸者日以益矣”“他日朝廷孱柔,或恐奸回怙势,姻娅故旧,钩引盘结,猝不可解,致成外重之势。…于是勇于一割,以应杀运,即至戚故人不恤”。值得注意的是,査继佐和顾起元都从朱元璋角度出发,认为李善长案虽为蓄意牵连,亦是人主为时代形势所迫,出于巩固统治、整肃朝纲的考虑之举动,具有其必然性。沈德符亦认为,从朱元璋的一些举动可以看出李案乃有据可循,朱元璋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诏书中赦宥胡蓝之狱犯者,对李氏之死采用了“伏诛”一词、对李氏长子李祺及公主没有任何抚恤等迹象表明,“韩公之祸似未必甚冤”⑮。
现代学界仍有观点坚持认为李善长案乃“明代最大的政治冤案”,也不乏对李善长之狱的新解读。如认为胡蓝之狱不仅是朱元璋借以铲除功臣、整肃朝纲的工具,更是阶级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洪武初年,李善长、徐达等六国公、二十八侯通过合法赏赐和非法暴力占有等手段坐拥三万八千一百九十四佃户⑯,由此使得百姓失田,加剧了阶级矛盾,威胁封建统治,因此朱元璋制造党案、打击公侯功臣极有可能乃出于打破阶级矛盾尖锐状况、巩固明朝统治的考虑。广义上说,皇权与相权、皇权与军权的矛盾致使统治者出于维护皇权的因素,采取特殊措施,诛戮大批功臣,总而言之,是为了维护朱氏的家天下。
三、观点之比较
观鸣冤派及中立分析派观点,既有相同点,又有明显分歧。相同点在于,双方都承认李善长之狱史载狱辞与实际相去甚远,即李氏之狱实为牵连附会,狱辞不足为信。两派分歧主要在于李氏获罪的原因以及其必然性大小,鸣冤派认为李氏获罪应归咎于朱元璋个人性格猜疑心重、残忍嗜杀,视开国功臣皆为“权柄之上的荆棘”,朱元璋的这一性格特点不仅是他与前代皇帝相比较为逊色之处,也从很大程度上造就了明初高压恐怖的政治环境以及明初史料记载的缺失和虚假。相应地,该派对于李案是否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缺乏讨论,这也是鸣冤派观点不够全面客观的地方。
中立分析派则认为李案并非没有冤处,而是主要“冤”在由统治者主观控制的定罪过程上,该案是李善长本人过错和统治者主观制造的结果。首先,李氏由于年长功高、缺乏洞察力、目光不够长远等个人原因,或早为朱元璋所猜忌,但未能及时引退而招致外界疑其为胡党,且猜忌日益加重,加之朱元璋本有意屠戮功臣以缓和社会矛盾、巩固明初统治,方造成该案。这一派在论及李氏之狱时从统治者角度出发、将自己置身于李案之外,认为制造党案、诛戮功臣乃明祖“驭下”的手段之一,具有一定的时代必然性,这是中立分析派的进步之处。
我们应该注意到,对李氏之狱发出评论且载于书册者,其身份多为文人士大夫,长年受到“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浸染,李善长在获罪之前近乎于完美的士大夫形象是这一批人所向往的精神偶像,因此李案对于文人的冲击是巨大的,正如《明初政治与文人心态及文学演变——以洪武文祸、党祸为中心》一文中所说,“党祸对文人的打击残害,使他们踏上了重新摸索定位自身价值的道路,这期间经历的心态变化,致使文人群体出现了几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与立命方式”。李氏的骤然倒台,使这一批人设身处地之下难免对李氏有兔死狐悲之叹惋和望沉冤得以昭雪之期冀。加之嘉靖、万历年间,政治日趋僵化和腐败,这一批文人士大夫生而不逢清明之世,其报国无门之心,恰恰催动他们往前人的案例里去寻得安慰和庇佑。因此鸣冤派的出发点,若非以现代评价标准来看,而是放在清末之前,是完全合理的。
四、余论
此处值得专门一提的是,中立分析派的观点中,对于李善长获罪的原因,除去追究其自身为人、为官之疏漏外,又从对立方朱元璋的角度出发,分析该事件的必然性,这种以维护封建统治为出发点的论调,虽然不免有正统史观的影子,但这种分析方法比之一味抒发叹惋和不忿的单纯鸣冤,已较为客观和理性。历史乃胜利者所书写的历史,明初史料记载又多隐晦和缺失,中立分析派能够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变换角度对李善长案进行历史必然性的思考,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一大进步。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后世学人才得以秉持社会史观和唯物主义史观,将社会阶级矛盾和封建权力制度矛盾等新视角纳入研究,进一步多角度、全方位地考察这一历史事件。
历史总是在惊人的相似中循环往复,距离明初大案虽已过去近四百年,其中的经验与智慧依然值得当世借鉴。李善长案背后固然有统治者强烈的主观意志影响,但从其个人角度出发,也许正是未能适时地隐藏锋芒、急流勇退,才招致不得善终的结局。从时代角度出发,不难认识到该事件乃是众多偶然因素所指向的必然结果,对历史事件认识的全面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眼界的高度,放诸其他事件而言亦是如此。
注释:
①⑥《明史》卷一百二十七,列传第十五“李善长列传”
②作者朱忠文,《贵州文史丛刊》2016年01期。
③作者要海霞,《黑龙江史志》2014年16期。
④作者张健,《明史研究》1997年00期。
⑤⑯作者梁希哲、宋鸥,《史学集刊》1999年02期。
⑦⑨《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四“开国规模”
⑧《明史》卷一百二十七,列传第十五“李善长列传”。“时封公者,徐达、常遇春子茂、李文忠、冯胜、邓愈及善长六人。而善长位第一,制词比之萧何,褒称甚至。”
⑩《国榷》卷九“太祖洪武二十三年”
⑪《罪惟录》列传卷之八“启运诸臣列传中”
⑫⑬《国榷》卷九“太祖洪武二十三年”
⑭《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胡蓝之狱”
⑮《有学集》卷一箹四
⑰《万历野获编》卷五“勋戚”
⑱《明太祖实录》卷六十八。
[责任编辑:邵猷芬]
戴月寒(1995—),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本科生。(北京100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