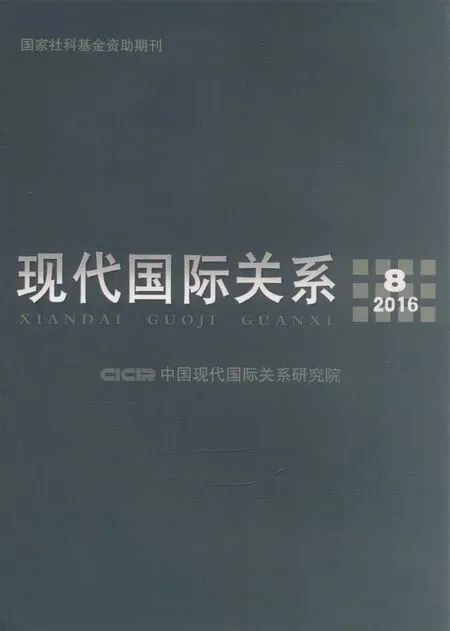美国防部2016年《中国军事和安全发展报告》评析
2016-11-26陈积敏
陈积敏
美国防部2016年《中国军事和安全发展报告》评析
陈积敏
美国防部2016年《中国军事和安全发展报告》对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国与邻国领土领海争端、中国国际战略以及影响中国领导层安全观念的主要关系变量、中国对外军事交往与海外军事投射能力、中国大陆对台战略以及中美军事交流等内容进行了分析,并阐述了美国在主权争端、台湾问题、两军交流等事务上的政策立场。“报告”显示出美国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包括军事关系,但对中国崛起持警惕态度,尤其是担心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对美国全球和地区领导地位的影响,突出反映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与重要性。因而,中美两国在推动双边关系发展上需做出更多努力。
奥巴马政府 《中国军事和安全发展报告》 军事现代化 中美关系
[作者介绍] 陈积敏,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外交与中美关系、国际非法移民问题。
5月13日,美国防部发布了2016年《中国军事和安全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6”, http://www.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6%20China%20Military%20Power%20Report.pdf(上网时间:2016年5月16日)。下文引述报告的内容不再一一列明出处。这是奥巴马政府最后一份中国军力与安全发展报告,但其篇幅超过了其任内的其他任何一份同类报告。“报告”显示出美国政府对华战略复杂而矛盾的心理:既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包括军事关系,并希望中国在当前国际体系中扮演积极的负责任角色;但又对中国崛起持警惕态度,尤其是担心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对美国全球和地区领导地位的影响,并强调要建立基于实力基础上的美中关系。换言之,美国需要在确保实力优势的前提下发展对华关系,保持对华战略主动性。该报告主要从军事角度考察和审视了中美关系,从一个层面反映出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与重要性。实际上,推动两国关系平稳有序发展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这需要两国携手并进,相向而行,共同努力。
一、“报告”的主要内容
从结构上来说,除摘要、特别主题及四个附录之外,2016年的报告主体依然分为六个部分,即年度更新、理解中国战略、军事现代化的目标与趋势、军事现代化的资源、应对台湾突发情形的军事现代化以及美中两军交流。从内容上来说,这份报告既关注了2015年中国军事发展状况,如机构改革、对外交流等最新进展,同时也分析了中国的长期军事战略,如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动因、目标等。具体来看,该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梳理了2015年中国军队建设的政策举措,如军事机构改革、裁军、反腐等内容,并且对中国与邻国的领土领海争端进展情况进行了评述。“报告”指出,中国在南沙的岛礁建设“增强了中国表面上控制南中国海争端海域的能力,加剧了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并且引发对中国长远意图的忧虑”。关于中国在处置领海争议方面的具体手段,“报告”认为,中国是以渐进的低烈度强制方式来获取对争议地域的有效控制,“在谋求自身利益时,尤其是在谋求其在东海、南海的领土主张时,中国表现出愿意容忍较紧张局势”,力避升级为军事冲突,“中国领导人懂得,动荡和冲突会破坏保障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和平环境”。此外,“报告”还一如既往地对中国各军种的力量配置、实力状态进行了评估。除对中国核战略力量、陆海空军战力等表示关注外,“报告”还以较多篇幅来分析中国在太空与反太空能力(Space and Counterspace Capabilities)、网络战等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第二,分析了中国的国际战略以及影响中国领导层安全观念的主要关系变量。“报告”关注了中国将21世纪头20年视为“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并指出中国的战略目标包括六个方面,即确保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不动摇、维护国内稳定、保持经济增长和发展、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确立中国大国地位并最终再次取得地区主导权以及捍卫中国海外利益。对于中国的外交政策,“报告”认为,“中国仍然把保持同美国和邻国的关系稳定视为其发展的关键。中国视美国为地区和全球的主导者,最有潜能支持和干扰中国崛起。”“报告”指出,中国领导人对于中国的安全现状有着基本的评估,即国内安全环境日益复杂,外部环境总体有利。这种安全观的形成主要受制于四个因素,即国内稳定、经济增长减速、影响中国利益的区域因素以及民族主义。
第三,关注中国的对外军事交往与海外军事投射能力的发展。“报告”认为,中国重视加强对外军事交往,这不仅有助于中国“加强国外存在和影响,提升中国国际和地区形象,缓解其他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忧虑”,而且还能够“通过使先进武器系统或技术采办更加便利,增长亚洲内外作战经验,接触外军做法、作战条令和训练方法”以促进并加速其军事现代化进程。从方式上来看,中国主要采用包括联合演习、军事外交、军事合作、高层访问等形式来扩大对外军事交流。值得一提的是,“报告”对中国军事的远征能力给予了高度关注,指出中国军队虽将应对潜在的台湾危机作为能力建设的一项优先重点,但“正在稳步拓展军队行动的机动性,以便能应对地区或全球焦点任务”。过去10年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和发展趋势表明,中国军队实现地区或全球安全目标的能力业已扩大。“报告”指出,在发展军事投射能力进程中,海军力量建设“处于这些努力的最前列”,并具体评估了中国海军的四项主要任务:一是保护重要的海上航线免遭恐怖主义、海盗和外国的阻断;二是提供人道主义救援/救灾;三是开展海军外交和地区性威慑;四是开展相关训练,以在台湾应急及东海或南海冲突中阻止美国等第三方妨碍中国的海上行动。“报告”认为,中国海军建设的目标是要打造一支“蓝水”(Blue Water)海军,“未来10年的目标是成为更强大的地区力量,能够在更大范围的亚太地区投送兵力,从而在长达数月时间内执行高强度作战行动”。不过,“报告”也指出,后勤和情报保障仍然是中国海军发展的主要瓶颈,尤其是在印度洋或亚太地区以外的地域。对于中国军力远程投射能力的发展,“报告”的行文之间表达了些许担忧,“解放军陆海空和导弹部队日益能够在和平时期投送力量,并在地区冲突事件中对抗美国的军事优势”。
第四,阐述了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资源与发展趋势。“报告”指出,“中国在诸多军事项目和武器系统的投入旨在增强延伸领域(extended-range)的兵力投送、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以及诸如网络、太空和电磁频谱等新兴领域的行动能力。”鉴于中国具备维持国防开支增长的经济实力与政治意愿,即“中国领导人将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视为获取大国地位和实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称的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必要前提,他们将强大的军力视为增进中国利益、防止他国采取措施损害这些利益并确保捍卫自身安全与领土诉求的关键”,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建设将会持续推进。“报告”还分析了中国进行军事现代化的几种现实动因,除了应对台湾危机以及提升中国大国地位之外,确保贸易通道安全,尤其是中东的石油供应安全,维护中国在有争议领海问题上的权益,应对朝鲜半岛不稳定局势,保护中亚能源投入,阻止民族分裂势力获取境外支持等也位列其中。为此,中国集中各种资源来保障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包括国内国防投入、自主国防工业的发展、更多的研发/科技基地、军民两用技术以及购买外国技术。
第五,评估了中国大陆的对台总体战略,并重申了美国的政策立场。“报告”指出,中国大陆的“总体战略仍然是通过劝说和强逼相结合的方式阻止支持台独政治态度的发展。”2015年两岸互动交流出现了积极态势,如习马会的实现,但“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对台军事态势有明显变化,解放军继续发展部署各种旨在逼迫台湾或必要时企图入侵台湾的军事能力”,这对台湾安全构成巨大挑战。需要指出的是,“报告”认为,中国大陆不会轻易对台湾使用武力,“只要认为从长远看统一仍有可能且战争代价超过获益,中国似乎就准备延缓动用武力”。正因如此,“报告”强调,美国将继续根据三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来指导其台海政策,其中就包括为保障台湾的自卫能力而对台出售防御性武器与服务,以便维持两岸军力的相对平衡。美国学者认为,这种“双重威慑”政策(即威慑大陆不至于对台动武,以及威慑台湾不至于走向独立)有效保障了台海和平。*2016年4月21日,笔者在美国丹佛大学与布鲁金斯学会学者卜睿哲(Richard Bush)交流中,他表达了这层意思。需要指出的是,本次报告在声明“美国反对任何一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同时,还特别加入了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一语,这是时隔10年之后美国在此类报告中首次重提这一立场,清晰表达了美国希望在台湾岛内政治版图发生变动的情形下两岸关系能平稳发展的意愿。
第六,描述了中美两军交流的现状,规划了2016年军事交流计划的重点,并明确了美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报告”援引201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中美关系的定位,指出“美国寻求同中国发展建设性关系,维持与促进亚洲和全球的安全繁荣”。*关于201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分析,可参见:陈积敏,“201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评析”,《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3期,第32~38页。但同时,中美之间确实存在着某些竞争领域。对此,“美国将根据实力地位(a position of strength)处理好同中国的这种竞争,同时设法降低误解或误判的风险”。“报告”认为,中美两军交流是实现这一路径的一部分,并坦承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和范围为两军交往提供了机遇和挑战,“解放军日益发展的军事能力促进了从人道主义救援到反海盗等领域更为深入的务实合作。不过,随着中国军事的发展和扩大,事故或误判的风险也在增加,这使得降低风险工作显得分外重要”。为此,2016年美国防部将继续加强同中国的军事交流,其重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政策对话或高层领导交往建立持续务实的交流;二是在互利领域建立具体可行的合作;三是增强风险管控以避免误解或误判可能。“报告”强调了美国在中美军事关系方面的基本立场,即重视构建两军关系的坚实基础,但同时对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保持警惕。在这一前提下,美国将对其军事战略作出调整,以确保对华军事优势,“美国将不断调整其兵力、态势和作战理念以慑止侵略、保护盟友和确保我们继续同中国交往时保持一定实力优势。美国将继续构筑盟国或伙伴国实力、加强地区合作、深化伙伴关系,从而维持稳定可靠的亚太安全环境”。
此外,“报告”还对中国的军费情况进行了说明,并指责中国发动对美网络攻击。“报告”指出,自2006年到2015年,中国的军事预算以平均每年9.7%的速度增长,并认为这种趋势将会继续维持,“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具备维持国防开支以相似水平增长的能力”。“报告”仍旧对中国军事预算的透明度进行了老调重弹的评价,强调“由于中国糟糕的会计透明度以及并未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很难估计出解放军的实际军费”。近年来,网络安全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重点议题,2016年的“报告”继续以案例列举的方式指控中国对美发动网络攻击。
二、对“报告”的评价
2016年美国防部《中国军事和安全发展报告》是奥巴马政府任内最后一份年度涉华军事报告,尽管在结构上与先前发布的同类报告无异,但篇幅上明显增多,其中反映出奥巴马政府对中国国际战略有着较为清晰的认知,同时也透露出对中国军事现代化发展的矛盾心理,并表达了对中国在领海等主权争议问题上的政策以及海外军事投射能力等方面的高度关切。
第一,美国对中国就中美关系的定位以及奉行和平发展战略有着较为清晰的认知。“报告”指出,中国重视发展对美关系,并将美国视为可以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关键影响的最重要外部因素。中国不寻求与美国之间展开战略竞争,更防止与美国出现直接的军事对抗。尽管中国在周边地区采取了一些进取性行动,但竭力防止将这种行为升级成军事冲突。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对于中国的外交战略及其限度有着深刻的认识。尽管如此,这份报告还是在极力鼓吹“中国威胁论”,如“报告”声称:“中国日益积极争取国家主权与领土诉求,强硬的辞令,缺乏透明的军事实力与战略决策,继续加剧紧张局势,造成该地区国家加强同美国的关系。随着解放军继续现代化建设,尤其是在缺乏更大透明度的情况下,这些忧虑可能会加重。”实际上,从中国强劲军事现代化建设到中国的战略意图不明朗,从中国的军费开支不透明到中国的进取性维权行动等带有明显价值判断的叙事话语中不难看出,“报告”是在刻意凸显中国军事发展对周边国家、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利益的威胁。对此,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在2016年5月14日的记者会上便批评这份报告继续渲染“中国军事威胁”、“中国军力不透明”等陈词滥调,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发表谈话”,《解放军报》,2016年5月15日。
第二,美国在应对中国崛起时秉持实力原则之上的“双保险”战略。美国是一个奉行实力至上的国家,奥巴马总统在演讲中多次提及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Commencement Address to 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Academy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Academy”,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6/06/02/remarks-president-commencement-address-united-states-air-force-academy.(上网时间:2016年6月8日)同样,美国在处理对华战略时也一如既往地将实力放在优先位置,即要确保美国对华战略优势,并进而保证其主动权。不仅如此,美国实力地位的稳固也反映到其他国家的认知上。2016年6月29日,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发布了一份关于美国全球影响力的研究报告,选取了10个欧洲国家、4个主要亚洲国家(包括中国)以及加拿大与美国作为访问对象,结果显示16个国家当中有15个国家表达了对美国领导的信心。*Richard Wike, Jacob Poushter and Hani Zainulbhai, “As Obama Years Draw to Close, President and U.S. Seen Favorably in Europe and Asia”, http://www.pewglobal.org/files/2016/06/Pew-Research-Center-Balance-of-Power-Report-FINAL-June-29-2016.pdf.(上网时间:2016年7月2日)塔夫脱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the 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 at Tufts University)国际政治学教授丹尼尔·卓泽乐(Daniel W. Drezner)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出:“如果感知本身就是力量的一种形式,那么奥巴马已经使美国再次强大了。”*Daniel W. Drezner, “Barack Obama has made America great again”,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30, 2016.
从具体的中美安全关系来说,美国采取了一种双保险战略:一方面,美国加大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保持强有力的军事存在,以便对中国军事现代化发展进行监控与防范;另一方面,美国通过构筑一个亚太安全网络来确保其对华战略优势。美国国防部长卡特(Ash Carter)2016年6月4日在香格里拉安全会议上发表的主旨演讲中提出,美国要在亚太地区打造一个“有原则的地区安全网络”,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要发挥具有相似立场的盟友和伙伴国家业已建立起来的三边机制的作用,如美日韩、美日澳、美日印三边伙伴关系;二是超越与美国有关的三边关系,让更多区域内国家参与进来,加强和发展双边关系,并进而创建三边制度安排,如发展日本与越南、日本与菲律宾的双边关系,打造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的三边机制,以及积极推动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联合海上巡逻机制的实现等;三是要通过东盟防长会议+(the ASEAN Defense Ministers Meeting-Plus)的形式来构建一个网络化、多边化的地区安全架构。卡特在演讲中表示,美国欢迎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中国在这一网络中发挥负责任作用。在他看来,所谓的“负责任”指的是中国采取的行动应当增强、而非削弱亚太国家都认可的共享原则。*“Remarks on ‘Asia-Pacific’s Principled Security Network’ at 2016 IISS Shangri-La Dialogue”, http://www.defense.gov/News/Speeches/Speech-View/Article/791213/remarks-on-asia-pacifics-principled-security-network-at-2016-iiss-shangri-la-di.(上网时间:2016年6月8日)
就中美关系而言,美国实力地位的巩固与中国的崛起并非一对矛盾体。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力量的持久性是中美关系稳定的一个有利因素。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一个基本预设就是当前霸权国家实力的衰弱并由此而产生的焦虑与恐惧。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如果美国将它的实力优势转变成对华战略压制的工具,中美关系势必将受到严重干扰。换言之,对于中美关系来说,美国应当理性而有限度地运用实力。正如《人民日报》就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偏袒与强硬行为发表的评论所言:“美国必须搞清楚,任何事情都是有底线的,一旦玩过了头就要付出代价。”*“美国不要在南海问题上冲撞底线”,《人民日报》,2016年7月6日。
第三,美国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领海争端保持密切关注,同时对中国军队的投射能力表达了高度关切。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主权争议问题上,美国一直表示其不是争端当事方,对于各声索国的主权诉求不持立场,但对于争端的解决方式有着明确的政策宣示,即美国反对在争议解决中采取单边行动,支持各方通过外交与谈判等方式,以国际标准与法治原则为基础来解决争端。*“S&ED Opening Session Remarks”,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6/06/258091.htm.(上网时间:2016年6月11日)然而,美国却难以做到超脱,而是对陷入到这些争端之中的可能性表达出些许隐忧,如“报告”称:“对美国来说,其中有些争端涉及到美国盟友,美国同其有着长期合作或安保条约承诺。”显然,这些争端为美国设置了一个难题:一方面美国需要为其盟友撑腰打气,这关系到它在盟友中的可信度,继而成为影响同盟体系存续的重要变量;*Robert Kaplan, “Eurasia’s Coming Anarchy”,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6, p.41.另一方面,美国需要谨慎评估其在争端问题上的政策张力,以免过度刺激中国,从而防止美国与中国摊牌这一最差结果的出现。*Chen Jimin, “The Crisis of Confidence in US Hegemony”, http://thediplomat.com/2014/04/the-crisis-of-confidence-in-us-hegemony/.(上网时间:2016年6月10日)
近年来,美国对于中国军事的远程投射能力表达了关切,尤其是2016年的报告更是将此列成一个部分来加以讨论。实际上,中国军力投射是其现代化进程中可预期的结果。美国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商业利益、国内公众支持以及国际形象塑造都要求中国发展某种远程投射能力,“中国全球力量投射的目标真实而温和”。*Oriana Skylar Mastro, “China Can’t Stay Home”, The National Interest, January/ February 2015, p. 43.不过,对于中国海外军事投射能力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美国却表现出较为复杂的心理:一方面海外军事投射会增强中国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从而有助于中美双方合作的进一步拓展,“一个更加积极的中国对美国而言可能是利好,特别是在能源安全、中东稳定以及气候变化方面与美国展开更大合作”。*Oriana Skylar Mastro, “China Can’t Stay Home”, The National Interest, January/ February 2015, p.44.但另一方面,鉴于中美之间存在利益矛盾、思维方式的差异以及中国军力可能会投射到美国不希望中国介入的地区等诸多因素考量,“对于美国及其地区伙伴来说,中国力量投射能力增强的意义仍不确定”。*Oriana Skylar Mastro, “China Can’t Stay Home”, The National Interest, January/ February 2015, p.45.
三、“报告”之外的思考:中美关系发展的路径
通过对“报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美两国军事关系虽取得了一定的积极进展,如两军信任机制的构建、军事交流制度化水平提升,但美国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战略防范力度在加强,对中国在维护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上的政策表现出更多的质疑与批评。*这一点还可以从美防长卡特2016年5月27日在美国海军学院的演讲中得到进一步验证。他指出美国正面临着五大安全挑战,即应对俄罗斯的侵略、应对亚太的历史性变迁、威慑朝鲜核挑衅、应对伊朗的挑战以及加速击溃“伊斯兰国”。但卡特将重点放在了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并表达出美国深刻的忧虑与防范心理。参见:“Remarks at U.S. Naval Academy Commencement”, http://www.defense.gov/News/Speeches/Speech-View/Article/783891/remarks-at-us-naval-academy-commencement.(上网时间:2016年6月8日)军事关系只是从一个层面反映出中美两国整体关系的状态。对于双方而言,保持两国关系的平稳、有序、健康发展是共同利益所在。今后一个时期,尤其是在美国政府即将换届之时,中美两国还需要为此作出更多努力。
第一,中美关系的发展离不开完善、有效、覆盖面广的战略沟通机制。中美间的战略沟通,至少能够发挥两个方面的重要功能。其一是明确并正确判断对方的战略意图。战略意图是影响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变量,但在无政府状态下,他国的战略意图既难以揣度,又不易鉴别。因此,加强战略沟通,尤其是最高领导人的相互交流便成为一条必要且有益的路径。其二是管控分歧,防止局部事态的扩大影响到两国关系的全局。*陈积敏:“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破解‘修昔底德陷阱’”,《和平与发展》,2015年第3期,第19页。2016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与奥巴马总统会晤中表示,双方应“通过对话协商积极寻求解决彼此间的分歧,或以建设性方式管控敏感问题,避免误解误判和矛盾升级,防止中美合作大局受到大的干扰”。*杜尚泽、章念生:“习近平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人民日报》,2016年4月2日。目前,中美两国已经建立了90多种交流机制,有效保障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但是,其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如美国政界对中美交流机制作用的认识不到位,仍存在一些妨碍中美沟通与交流的杂音。2015年9月习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美国部分政治人物表示奥巴马政府不应该给中国以这样的“礼遇”,甚至鼓吹要取消这次访问。*“Should Obama Cancel Xi’s Visit — Or Serve Him a Big Mac?” http://foreignpolicy.com/2015/09/21/obama-xi-jinping-cancel-visit-china-cyber-diplomacy/.(上网时间:2016年6月7日)再者是这种沟通机制不能仅体现在官方层面,也应当延伸至社会各个层面,如学术界。笔者在美国访学期间曾对一些知名的美国中国问题学者做了访谈,深感两国学术界加强沟通与合作的必要性。例如,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问题上,中美学界就有不同的观点。很多中国学者认为,这是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最新案例。然而,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教授对此难以认同。他表示,“遏制”一词有特定的冷战背景,以及特殊的对象即苏联,其基本特征是“相互孤立”。但美国并没有孤立中国,也不可能孤立中国,而是希望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的一员。*2016年2月18日,笔者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对沈大伟教授的访谈。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上也能感受到两国学者间的观点差异。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罗伯特·萨特(Robert Sutter)教授表示,这是中国应对美国的一个战术,是在“欺骗”(cheat)美国:一方面中国在言辞方面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声言不挑战美国的全球利益,但另一方面从行动上对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如恶化与美国亚洲盟友的关系,在东海、南海采取胁迫性(coercive)政策。因此,美国在亚洲实行的“再平衡”战略就是为应对中国挑战而采取的主动性(proactive)举措。尽管美国不愿与中国发生冲突,但万一冲突发生,美国需要具备掌控全局的能力。*2016年2月19日,笔者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对罗伯特·萨特教授的访谈。显然,中美之间的交流机制已经不能主要限于政府层面,尽管这一层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应该延伸至商业界、学术界等社会层面。
第二,中美关系的发展应多一些接力,少一些借力。接力与借力是两种不同的中美关系发展路径,也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接力是通过两国在共同利益领域的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的目标,不仅有助于促进两国间的战略互信,也是实现在双边、地区乃至于全球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必要路径。例如,2016年华盛顿核安全峰会期间,中美双方在气候变化与核安全领域中的合作就体现了这一点。显然,这种接力模式将会把中美关系导向一个更加健康、持久的发展前景。借力则是通过战略投机的方式来实现单方的国家利益,其出发点就带有取巧的成分,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会使其获得短期的战略收益,但却会加深双方的战略互疑,尤其是在中美两国竞争面更为凸显的情况下。例如,在东北亚安全问题上,美国通过施压中国的方式来实现其战略目的就属于此例。
第三,中美关系的发展应多一份理解,少一点儿指责。两国关系中不仅存在共同利益的一面,也存在利益矛盾,甚至冲突的一面,对于中美两个在政治制度、发展阶段、历史文化上存在巨大差异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国家间在面对共同利益时所体现出来的关系并不能反映出两国关系的全貌,也展现不了其本质,而恰恰是在两国利益出现矛盾的时候才能表现出双边关系的成熟与否、稳定与否。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已毋庸多言,但两国关系是否已经足够的成熟与稳定尚难有定论,其中一个关键的影响变量就在于每当中美关系间出现利益分歧与矛盾的时候,双方便相互猜忌、互相指责,如网络安全问题,美方始终将中国视为对美展开网络窃密和攻击的主要“嫌疑人”。美防长卡特2016年5月27日在美国海军学院发表演讲时声称:“中国网络行为者从美国公司大规模窃取知识产权,这违反互联网精神,更别说法律了。”*“Remarks at U.S. Naval Academy Commencement”, http://www.defense.gov/News/Speeches/Speech-View/Article/783891/remarks-at-us-naval-academy-commencement.(上网时间:2016年6月8日)然而,中国也是各种网络攻击的对象,也是受害者。在网络安全领域,中美之间存在诸多共同利益,本可以展开更为密切的合作,但美国对中国的种种指责损害了这种合作氛围,不仅无助于构建一个安全、共享、有序的国际网络环境,也不利于双边关系的发展。
第四,中美关系的发展应以彼此尊重取代自我优越。正如人际关系一样,国家间关系也需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种相互尊重首先并主要体现在对对方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的尊重上。然而,中美关系在这一点上还很欠缺,这主要是由美国方面造成的。鉴于当前中美关系仍存在不对称性,即美国对中国施加影响的方式与手段更加多样,美国在中美关系中仍相对占据主动地位。考虑到近代的历史遭遇与现实需要,中国将独立自主视为实现国家复兴的根本原则,把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视为不可侵犯、不容谈判的核心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95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再次强调了这一点。他指出:“中国不觊觎他国权益,不嫉妒他国发展,但决不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中国人民不信邪也不怕邪,不惹事也不怕事,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然而,仍有不少美国人以“民主灯塔”自居,以“天赋使命”的冲动来看待中美关系,不时就中国的民主、人权问题为两国关系发展设置障碍,甚至一些政治人物也希望利用这些议题来吸引眼球,如2015年2月,时为美国共和党总统竞选人的克鲁兹(Ted Cruz)就向美国参议院提交了一份议案,要求把中国驻美大使馆前面的广场更名为“刘晓波广场”。从表象上来看,这是美国国内政治的一种现象,但从根本上来看还是美国心理优越感的体现,它并没有表现出对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大国应有的尊重。
第五,中美关系的发展应当以务实取代幻想。这一点对于中美双方而言都有实际意义。从中方来说,随着总体实力突飞猛进的增长,在国际战略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急躁冒进的思想,给外界造成了一种势必要“坐二望一”的误解,这不利于中美关系的长远发展。就双边关系而言,中国首先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准确地自我定位,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过高地估计自己,更不能背弃中国一贯所坚持的外交战略,即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亚太地区是中美利益交汇最集中、互动最频繁、利益冲突最可能发生的地区,因此尤其需要慎重处理。在这方面,中国需要认识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存在既是一个历史现实,也将是一个未来趋势。中国不应有将美国势力赶出亚洲的幻想,中国不能搞也搞不成所谓的亚洲“门罗主义”。
美国也应摒弃其滞缓,甚至中断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想法。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为了寻求一条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道路而进行着不懈探索,并最终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且行之有效的复兴之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要保障这条道路走得好、走得稳,维护中国的政权稳定是首要条件。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必须要抛弃其促进中国政权更迭的不实幻想。实际上,冷战后20多年里,美国所期待的那种“历史的终结”并未变成现实,面对着一个在政治制度、价值理念、道路选择等方面存有明显差异的中国的迅速崛起,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本应该让美国人接受世界文明多样性的现实,并意识到试图改造中国是不切实际的做法,但仍有很多美国人对此念念不忘。2015年3月初,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的题为《修订美国对华大战略》的研究报告指出,“只有中国彻底的崩溃才能够让华盛顿从系统性制衡北京的义务中解脱出来,因为即便一个温和、羸弱的中国政府也不能完全消除它对美国在亚洲及其他地区所构成的威胁。”*Robert D. Blackwill and Ashley J. Tellis, “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 http://i.cfr.org/content/publications/attachments/China_CSR72.pdf.(上网时间:2016年6月8日)美国前国防部官员博斯科(Joseph A. Bosco)在《外交家》(the Diplomat)网站上撰文指出,美国需要认识到这样一个新现实,从近期来看,地区和国际安全需要美国遏制中国的扩张主义;但从长远来看,地区和国际和平有赖于在美国的支持下实现中国的政权变更。*Joseph A. Bosco, “America’s Asia Policy: The New Reality”, http://thediplomat.com/2015/06/americas-asia-policy-the-new-reality /.(上网时间:2016年6月8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主席卡尔·格许曼(Carl Gershman)也认为,“中国的民主奋斗将是国内的斗争,并将在内部获得胜利。但在我们这个相互联系的世界,有许多事情可以从外部来做,以帮助那些在民主运动前沿斗争的人们。”*Carl Gershman, “Chinese Dreams: The Fight for Democratic Pluralism”, World Affairs, Summer 2015, p.55.然而,这并不是美国思想界的主流,更不是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华盛顿时间2016年3月31日,奥巴马总统在与习近平主席会晤中重申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立场,即美国欢迎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中国崛起,并与美国一道应对全球挑战。*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esident Xi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fore Bilateral Meeting”,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6/03/31/remarks-president-obama-and-president-xi-peoples-republic-china.(上网时间:2016年6月8日)与此同时,中国也表达了与美国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意愿。习近平主席在第八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的讲话中便强调,“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更应该从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勇于担当,朝着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方向奋力前行。”*习近平:“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而不懈努力——在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6月7日。从这个角度来说,中美两国都需要以务实与建设性态度来应对分歧,并从长远和战略的视角来推进双边关系的发展。这不仅是两国利益的内在要求,也是对世界责任的必要担当。○
(责任编辑:黄丽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