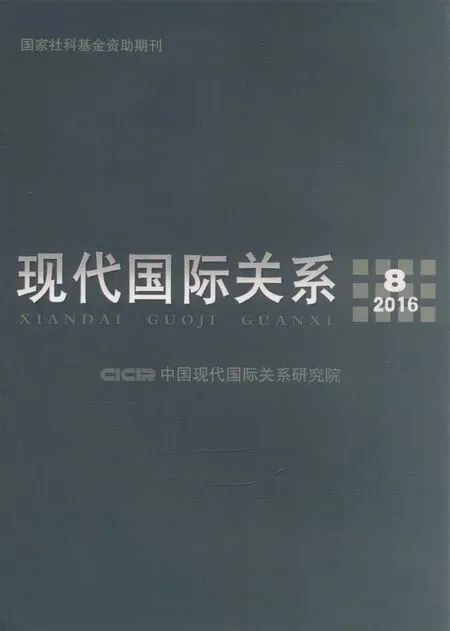处境艰难的欧盟亟须变革
2016-11-26张健
张 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所长)
处境艰难的欧盟亟须变革
张 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所长)
过去几年,欧盟一直内忧外患,近来更甚,危机叠加,问题丛生,英国脱欧、恐怖主义、难民问题、银行业危机等等,环环相扣,互为因果,复杂而难以解决。欧盟风雨飘摇,似大厦将倾,颓势尽显。
首要的问题是,欧洲一体化迷失方向,彷徨无助。二战以来,以主权让渡为主要特征的一体化成为欧洲人赖以自傲的最大成就,认为欧洲走在世界前列,进入后现代社会。客观而论,这一观点并非完全自夸。欧洲一体化确有值得肯定之处。几十年来,欧洲一体化虽迭经危机,跌跌撞撞,但总体路线是曲折向前,促进了欧洲大陆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对于欧洲一体化遭遇的种种问题和危机,包括20世纪60年代的“空椅子危机”、80年代英国的预算返还问题、90年代的“马约”波折,以及本世纪的“宪法危机”,甚至近年来的债务危机等等,多数欧盟观察家仍愿意从积极角度考察欧洲一体化,认为欧盟的问题和危机均属“成长中的问题”,危机反而会成为转机,推动一体化发展。
过去可能的确如此,但值得指出的是,欧盟当前面临的并非单一危机,而是经济、政治、安全及外交等诸多领域的叠加危机。而之所以形成当前危机叠加的局面,在于欧盟以往危机处理模式埋下的隐患,即治标不治本,得过且过,平衡妥协和稀泥。比如为解决“空椅子危机”,认可了法国的“一票否决”原则,错失了当时的欧共体联邦化的最好机会。为解决“马约”生效问题,允许丹麦享有不加入欧元区的例外权。为应对债务危机,欧盟强化了财政纪律监管,但却拒绝财政联盟、真正的银行联盟以及欧元债券,同样也错失了弥补欧元区机制性缺陷的契机。
得过且过的根本原因在于,欧盟国家在欧洲一体化的方向这一关键性问题上并无共识,一直是同床异梦。欧盟在显著发展的同时从来都没能解决自己的性质问题。欧盟内部一直存在着联邦主义者(超国家主义者)与主权主义者(政府间主义者)的争论,有些国家和民众支持将欧盟建成一个政治联盟,而另外一些国家则将欧盟主要看作是一个大的自由贸易区。因此,欧盟每项条约的签署及每项重大政策的出台,都是欧盟内部这两种观点的妥协,而每个国家也都从自己不同的视角来对欧盟的发展做出不同的解读。在一个目标差异如此之大的组织内,如果说成员国初期还能因各有所得待在一起,但随着一体化深化发展不断迫近实质性问题,比如财政联盟和政治联盟,分歧就显得难以调和,很难想象成员国会一起走到最后。
欧盟政治人物对所谓一体化模式的盲目自信也积累了各种难以化解的根本性矛盾。比如,过快扩大。不论对欧元区还是欧盟来说都是如此,希腊和意大利当初实际上都不符合加入欧元区的条件,欧盟出于政治考虑集中吸纳中东欧国家,这些均导致消化不良。过快扩大导致欧盟不但难以形成共识,反而埋下东西和南北成员国对立和矛盾的祸根。再如,精英主导,不顾民意,强推一体化。欧洲一体化是典型的精英工程,早期重大决定均未经过民众认可,甚至有违多数民意,比如建立经济货币联盟的决定就过于仓促。如今的欧元区已经成为矛盾累积、经济分化、相互猜疑、离心离德的雷区,进退两难,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比如希腊债务问题仍有待解决,意大利的银行业问题、经济长期停滞问题以及2016年10月政治改革方案公投后可能的政局动荡,法国政治分化、经济疲弱、民心不安也是较大变数,这些都会加剧欧元区内部矛盾,导致本已脆弱的欧元区更为岌岌可危,这与欧元的创立初衷显然大相径庭,不但没有团结欧洲,反而成为一颗难以排除的不定时炸弹。
一体化是欧洲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本,可以说,没有一体化,就没有欧洲二战以来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如今禁忌已被彻底打破,首次有成员国主动要求退出欧盟,而这在几年前还难以想象。欧洲一体化不再是单行线,而是一条可以倒退的双行线。欧盟和欧洲政治家也因此深受打击。显然,这反应了一个欧盟多年来不愿承认、也不愿面对的政治和社会现实,即欧洲出了大问题,不然,英国民众为何选择绝大多数分析家眼中的“自残式”脱欧决定呢?
欧洲的政治和社会新现实非常清楚,即社会民情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政治家和欧盟在民众中不受欢迎,民众迫切需要改变。而这种改变的强烈需求,可能会给欧洲一体化和欧盟带来更大的冲击。
有观点认为,英国本就是欧盟边缘国家,既未参加欧元区,也非申根区成员,脱欧就脱欧,对欧盟并无实质性损害,欧盟可能因祸得福,放开手脚大搞一体化。的确,英国有其特殊性,包括其独特的历史、地理及全球性视角和角色地位等等,这决定英国从来都不是欧洲一体化的热情、积极的参与和支持者,英国在很多情况下也的确扮演了欧洲一体化的阻碍者角色。尽管如此,英国作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和外交、军事大国,其退出对欧盟的影响是实质性的。
更重要的是,英国脱欧所反应的问题并不是孤立的。民粹主义在兴起,民族主义在复兴,这在欧洲大陆也是如此,且更甚于英国,比如法国国民阵线以及意大利五星运动的兴盛。即使是长期作为欧盟稳定锚的德国也不能幸免。德国总理默克尔民意支持率急跌,两个主要政党即中右的联盟党和中左的社民党民意支持率相加已不足五成,新兴的极右政党“德国选择党”支持率则有较大幅度上升。欧盟的很多问题特别是欧元区的问题并非英国人的过错,英国脱欧后,欧元区的问题仍在。当然,欧盟当前并无迫在眉睫的解体之虞,但某一成员国步英国后尘的风险显然是在增大。特别是欧盟的核心欧元区仍是危机四伏。如果自私自利、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成为主流,欧盟最终走向解体并非危言耸听。
追求权力和存在感的欧盟机构如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在欧盟成员国中不时成为指责和攻击对象,也并不讨欧洲人喜欢,形象每况愈下。欧盟机构当然是问题的一部分,比如官僚主义,繁文缛节,好大喜功等等,但却并非欧洲一体化和欧盟当前困局的主要原因。问题主因在成员国,各个成员国都有问题,这些问题最终都会成为欧盟和欧洲一体化的问题,并叠加放大,形成欧盟层面的危机。其中,经济是致命伤,欧洲目前的问题和危机,包括社会的激进化、穆斯林融合难、极右势力兴起、恐怖主义威胁增大、难民潮等等,都与其经济低迷、缺乏活力密切相关。经济长期停滞、民众生活水平得不到提升甚至退步,都将积累社会戾气,为各种极端思想的兴起提供沃土;而社会的激进化、极端化反过来抑制经济发展,形成恶性循环。很难想像英国人会要求退出一个生机勃勃、兴旺发达的欧盟;如果工作机会唾手可得,欧盟国家的大量中低收入者也不大可能强烈排斥移民,而移民也可能因成为有产者而更好地融入社会。
欧洲经济的僵化与欧洲政治和社会模式的僵化密切相关。从政治上看,政治人物和政党以当选为第一要务,或不作为,如不进行必要的结构性改革,在移民融合等重大问题上得过且过;或乱作为,如给选民太多难以兑现或兑现后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严重负面影响的承诺。从社会模式上看,福利制度尾大不掉,动辄得咎。近年来,欧洲重大决策出现“公投化”趋势,如英国脱欧公投,显示欧洲议会民主制已出现重大缺陷,将导致欧洲政治和社会的劣质化发展。
因此,至少目前看来,欧洲前景黯淡,债务问题、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恐怖主义以及英国脱欧等诸多问题和危机仍将持续困扰欧盟。欧盟经济很难根本性好转,欧元区危机有再度爆发的可能,乌克兰危机可能再趋紧张,难民潮可能再变洪流,恐怖袭击也仍可能再次发生。2016年10月即将举行的意大利公投、匈牙利公投、奥地利总统选举以及2017年的法国总统选举和德国议会大选也都可能出现意外,欧盟仍将生活在重压之下。
重重危机特别是英国脱欧已强烈刺激到欧盟,事实上,欧盟政治人物也都深知,必须要有大的变革,否则还可能出现更大危机。但问题是,欧盟现在能做的非常有限。原因很简单,成员国之间无法统一思想,无法沿着清晰的、共同的目标前行。重重危机分化了欧盟,也加大了欧盟的内部矛盾,德、法等主要国家之间,南、北欧之间,东、西欧之间的彼此猜疑和矛盾都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导致相互协作及危机应对更为困难。如果说精英层面对维系一体化成果尚有共识,民意则出现重大分化。民意的变化及代表这部分民意的各种极右、极左政党的兴起将极大制约欧盟解决问题及应对危机的能力,这就是欧盟选举政治面临的现实困境。
欧盟层面行动力的缺乏将迫使成员国更趋向于自行其事,正如德国财长朔伊布勒所言,如果欧盟不作为,那成员国就只好自己干。自己干的结果可能导致欧盟陷入更大的混乱,也将进一步刺激各国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抬头。如德国2015年单方面开放难民进入的做法就招致包括法国和中东欧在内的其他国家的不满甚至怨恨。
欧盟未来不容乐观,当然也不能就此断言其一定会继续没落、衰败下去。但前提是欧洲政治人物能有正确的反思和行动。其一,根本性调整一体化理念和价值观,要么更为松散化,向成员国转让权力,以包容如此不同的国家;要么更为集中化,成员国必须实质性让渡财政、税收及至外交和国防上的主权。其二,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发展,经济是基础,停滞的经济不可能有社会、政治和一体化的正常化发展。在这方面,结构性改革是正途,迎合民粹放纵保护主义则无异于饮鸩止渴。其三,摒弃价值观偏见,谨慎对外军事干预,以促发展稳定中东、非洲等大周边地区。身处贫穷、动荡甚至战乱的汪洋大海,欧盟不可能独善其身。
欧盟之所以走到如今困局,皆因无法放弃既有价值思维定式,或慑于变革之艰难不敢行动。欧盟未来是否能正确反思而有所行动不得而知,但欧盟此次面临真正的十字路口,无路可退。否则,欧盟的老问题会更加突出,新问题和新危机还会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欧盟的衰落也将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