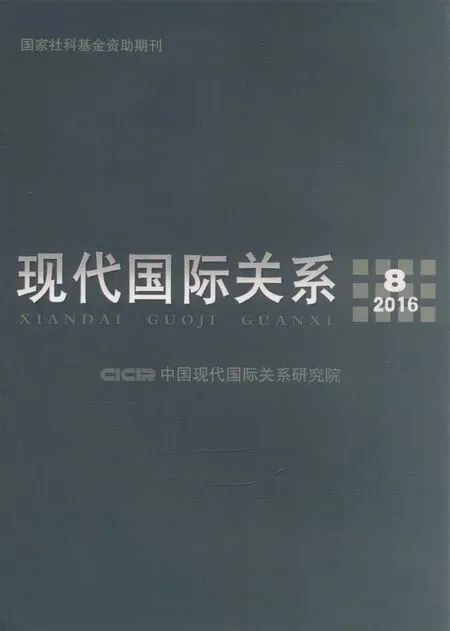西方世界的“现代国家治理难题”
2016-11-26王鸿刚
王鸿刚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执行所长)
西方世界的“现代国家治理难题”
王鸿刚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执行所长)
美国“特朗普现象”和英国脱欧等一系列令人惊诧的事件,使“西方到底怎么了”成为当下人们热议的话题。尽管西方的问题并非起自今日,西方内部各国之间的情况差别非常大,但如果笼统地概括其共同点,大致可以归结为如下几方面普遍存在的现象。一是经济不振。美欧各国虽已度过金融危机后的最困难阶段,但复苏进程并不遂顺,仍然面临“调整结构”的重任,大多数中下层民众对复苏无感,国家财政状况未有明显改观,结构性失业挥之不去,对经济全球化越来越持排斥态度。二是社会不稳。美欧各国社会正日益被愤怒、仇恨和不安的情绪所笼罩。美欧各国相继发生的一系列暴力和恐怖活动,严重削弱了民众的安全感和相互信任;同时,随着贫富矛盾、族群矛盾、新老矛盾的加剧,仇富、仇警、仇外的情绪也在快速酝酿。三是政府失能。围绕如何应对困难挑战,产生了明显对立的政策主张,并发展为高度的政治极化。在美欧不少国家都出现了极左与极右的政策主张,而且各执一词、相互否决、拒不妥协,造成严重的政治僵局。政治上的折腾大大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一些政客为博取支持,开始走上迎合民粹思潮的危险道路。这些现象其实在全球各国均不同程度地存在,但在成熟和先进的西方国家内部竟然也如此广泛,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就显得有些非同寻常。可以说,西方国家正陷入“现代国家治理难题”。
现代国家内部普遍存在着不可化约的三类基本力量:市场、政府和社会。三类力量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互动关系,构成了现代国家运行的核心机理。现代国家的治理,需要维持市场、政府与社会三种基本力量的平衡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依存与制约关系。西方国家深陷其中的“现代国家治理难题”的典型症状是:市场、政府和社会自身都出了状况,并带来相互之间的关系紊乱,因而使国家治理陷入了进退失据、左右为难的不正常状态。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极为深刻而复杂的,是多种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其中,有几个方面的因素特别值得关注。
一是经济活动的金融化趋势。无论西方各国对金融自由化持何种态度,金融资本的崛起以及经济活动的“金融化”都是无法忽视的事实。这给经济活动自身以及社会和政府都带来巨大影响。经济领域,由于金融机构沉浸于纯粹的金融套利,金融活动对实体经济支持减弱,造成经济空心化和长期竞争力下降;纵然股市一片繁荣,背后却是难以摆脱的长期停滞阴影。目前西方各国经济复苏乏力,均或多或少地与此有关。社会领域,由于富人更有能力通过投资增加收入,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各阶层收入差距扩大;而且由于资本不必寻求同社会劳动相结合便可实现增值,长期存在的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契约关系”遭到侵蚀,经济的表面增长并不能如以往那样带来更多就业岗位。失业和阶层分化,成为西方各国社会不满和社会不稳的直接诱因。
二是社会文化的消费主义倾向。自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理性主义传统,曾经是推动西方各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完善政治制度的主要思想源泉和行动依据。但资本主义要发展,必须不断挖掘人的消费需求。在感性的消费需求被不断挖掘和放大的同时,人的理性思考能力却在蜕化。“人的异化”,成为随之而来的必然结果。百年前,斯宾格勒就曾以创造力的丧失而预言“西方的没落”。如今我们看到,在消费主义文化的长期浸淫中,安于现状而不是积极进取、循规蹈矩而不是前提批判、福利依赖而不是独立自主、个人快乐而不是利他奉献,逐步成为西方社会中理所当然的生活追求。其结果必然是社会活力和长期竞争力的下降。当前西方国家内部的枪击、恐袭、排外等各种非理性行为,恰恰折射了西方各国竞争力下降的无奈现实。
三是民主体制的后坐力问题。民主体制作为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治理方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基础,并在几百年前西方资产阶级反对宗教和封建专制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至今架构已十分细致完善。在此过程中,它不仅通过民主选举较好地理顺了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解决了各国政治体制的合法性问题;而且因权力制衡而产生的天然的自我克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营造了宽松有利的国内环境。但凡事都有两面。过去几十年间,迅速壮大的金融资本悄无声息地对政府意志形成了绑架,使政府失去了决策自主性和对资本逐利本性的约束能力;政治精英们为争取上台和维持合法性而对民众诉求的不断允诺与兑现,则使政府的财政负担日益沉重。这意味着,民主体制在较好解决了合法性问题的同时,越来越难以克服缺乏远见和寅吃卯粮的弊端。就此而言,如今西方各国政府在困难面前大多表现得苦无良策,并在民粹思潮面前缺乏定力、曲意迎合,也就不难理解了。
有关西方国家的前途命运,也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对此,有人持比较乐观的看法,认为西方没事。其理由或者是“民主万能论”,认为民主制度是优越的,终究会使西方转危为安;或者是“经济周期论”,认为随着全球经济形势整体好转,或者某些技术突破带来新的经济繁荣,各类困难均会明显减轻;或者依据“相对优势论”,认为就算西方有问题,但环顾全球,其他国家的问题一点儿也不比西方少,西方国家仍将占据相对优势。同时,还有一些人持比较悲观的看法。理由或者是“长期停滞论”,认为全球和西方经济快速复苏和强劲增长恐怕难成现实,目前的经济状况不仅不会好转而且将进一步恶化;或者是“体制衰败论”,认为目前西方政治制度已严重畸形腐化,西方国家的整体衰落乃是不可避免的事。
两种看法可能都有失偏颇。乐观主义者的问题在于过于自信,没有注意到经济的空心化和社会的分化实际上已经令政治合法性和国家竞争力受到削弱,而这些问题将时时困扰西方国家。如果按目前的路线继续走下去,出现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将是非常可能的。悲观主义者的问题在于线性思维,没有意识到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是曲折和反复的。实际上,从理论上讲,西方一定程度上摆脱“现代国家治理难题”甚至实现东山再起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如果西方社会能展开一场21世纪的新的思想启蒙运动,重建理性主义传统,如果西方国家能改变对民主的过分迷信,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提升政府的执政效率和精英的责任意识,并果断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加强对资本的监管和引导,并制定着眼于重建国家竞争力而不是满足当前福利的更富远见的社会政策,西方的未来并非一片黑暗。当然,分权体制下的改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到最危急时刻,政治上的拖拉扯皮恐怕是在所难免的。
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有关西方的前途命运,更有可能的是其陷入一种上不去下不来的平庸状态。面对难题和危机,西方国家不会一动不动,会多少推进一些改革,但这些改革或者本身就有很大保守性、局限性,或者在实施过程中走了样,因而对扭转国家治理体系失衡作用有限,使现存各类问题既不会完全失控,也不会彻底解决。长此以往,西方国家将逐步失去闪耀头顶的光环衬托,从一种全球的榜样性、引领性力量,最终演变为一种平等性、参与性力量。这对西方而言也许是个退步,但对21世纪的全球秩序演进和人类社会整体而言,或许更应被看作是一个进步。
中国不应以幸灾乐祸的心态看待西方的困境。这是因为:其一,西方有问题,也可能给中国造成问题。无论经济上的保护主义、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抑或社会上的民粹主义,以及外交上的非建设性竞争,都可能给中国带来麻烦。特别是,在西方媒体中,目前已隐约形成“东升”造成“西降”的叙事话语,更容易使中国成为迁怒的对象。其二,西方的问题,也可能会是中国的问题。一定程度上,经济转型的风险、社会民粹的抬头,政治公信力的削弱,也是我们需要着力应对的问题。中国要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想到即便是建成了现代国家,也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中国必须比西方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