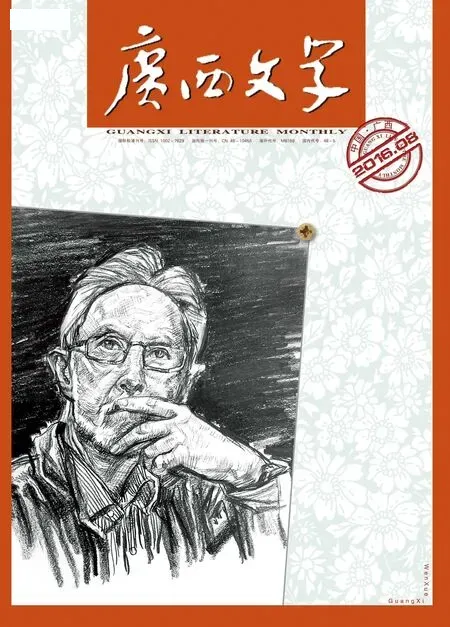带你飞
2016-11-26黄咏梅短篇小说
黄咏梅·短篇小说
在卫生间洗过澡后,严行进穿上短裤。照镜子前,他一定是要穿上短裤的,那种阔大的平角短裤。某个部位,遮起来,看不见,似乎更能体现其威武,即便那威武也许——是一种幻觉。中年以后,胸脯以下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那个隆起的地方骄傲得发亮。严行进抚了抚肚皮。镜子里,他还看到了身后那台银色的滚筒洗衣机。忽然像记起了什么,他转过身去,半蹲下来,打开舱门,将脑袋伸了进去。里边空荡荡,耳朵里满是自己喘的粗气。他艰难地把脑袋缩回,双手撑在膝盖上,使自己直立起来。有点累。他对着镜中那个胖子冷笑一声,嗨,哥们儿,你疯了吗?
早上,米嘉欣对严行进说:“洗衣机的滚筒里,一定住着一个专门吃袜子的鬼。”严行进“嚯”地笑出来。“你在讲安徒生童话吗?”他看着老婆的样子,一时间不知道怎么评价她,只是不断地摇着脑袋。米嘉欣不是开玩笑的。她指指阳台上的晒衣竿。那上边吊着两只袜子,一只长的,灰色,一只短的,紫色。“这次它吃了两只。以前它只敢吃掉一只的。”米嘉欣郁闷地研究着这两只落单的袜子。严行进一时间无语。有风吹过来,灰色长袜朝紫色短袜踢过去,紫色短袜玩花样般轻松避开了,像个神秘的武功高手。
落单的袜子总是会自己出现的。不是在抽屉里,就是在门背后,不是在洗衣篮里,就是在被褥里,总之,刻意去寻找是没结果的,只能等,等它们愿意出现的时候。严行进很清楚这一点。这就是他们家。
米嘉欣也很清楚。隔一阵,她会为那些偶然重现的东西而欢叫,仿佛她真的曾经失去过它,那种失而复得的快乐,就像赚了谁的便宜一样。只是,她的确无法解释它是如何消失的,它消失的那段时间都经历了什么。一只专吃袜子的鬼,一个专盗身份证的小偷,一个专藏皮带的变态,甚至是一个专拔U盘的神经病……
严行进反问她:“照你这么说,为什么那些东西又会自己冒出来呢?”米嘉欣想了想说:“谁知道,大概只是想借去用一阵,用好就还回来了啊。”严行进像咽下一只蛋黄,堵住了。很多话他是没办法接的,因为她的想法跟自己不在一个开关上。
年轻那会儿,严行进觉得米嘉欣很天真,中年以后,他死死地认定她其实是个傻大姐儿。好在米嘉欣是一个旅游博物馆的解说员,每天像复读机一样,并不需要什么心机,要是换作其他单位,像米嘉欣这种女人,“死”好几遍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他总是对那些爱上他家聚会的同事说:“我娶了个奇葩老婆。”好在,这个奇葩老婆不怎么管他,出入自由,花钱自由,仿佛她知道,他是这个家的一件东西,就算哪天被借去用了,用好自然就还回来的。
周末,严行进约单位几个哥们儿来家里玩牌。玩牌一贯是严行进交流工作的一种工具,他们一边玩,一边讲单位的人事。其中,那个人事处的副处长梁力和办公室的副主任邱天是常客,严行进往往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额外的消息。最近,单位里进驻了巡视组,有消息传,第三把手怕保不住了,贪污,养情妇。严行进想八卦一下,那个第三把手到底是怎么被搞“死”的。
作为主妇,米嘉欣像往常一样给他们沏茶,切水果,还用烤炉烤了些简单的曲奇饼干。在他们礼貌地夸奖饼干好吃的时候,米嘉欣忽然说:“我吃过一种太空饼干。在阿姆斯特丹。味道很奇怪的。”
副处长梁力拿了一手好牌,稳坐,等赢,他顺便搭了一句话:“嫂子,太空饼干,是给太空人吃的吗?”
米嘉欣说:“不是的呀,是吃了之后,人就像飞进了太空一样。”
“噢,是用酒做的吧?”
“大麻。”
台面上几只手顿时停下了。他们都看着米嘉欣,包括严行进在内。
“真的是大麻做的。反应没那么大就是了。吃过之后,我们玩一种游戏。一个人闭上眼睛,其他人就做一些动作,看那个人是否能看见。我闭上眼睛,看见一个人和一个人拥抱,一个人捏了捏另一个人的左耳朵。她们说,没错,她们就是这么做的。”米嘉欣的语速很快,就像她平时在博物馆里讲解一样。“不过,有的人闭上眼睛,什么也看不到。”
男人们都愣住了。
副主任邱天将手上的牌一把倒扣在桌面,他请米嘉欣多讲一些。
米嘉欣将那次阿姆斯特丹的奇妙之遇大致讲了一下。
“不是说会产生幻觉吗?怎么会看到真实的东西?”邱天兴致最浓。
“嗯,我查过一些书,对有的人,它会延伸神经长度,或者说感知范围。有的幻觉是真实的,只是你并不相信。不是这样吗?不肯相信的东西你们都会说成是幻觉。”米嘉欣正儿八经的样子,令他们不忍质疑。
“打牌,打牌,别听她瞎掰,我这个奇葩老婆,一天到晚净说些奇葩的话,亏你们也信。”严行进狠狠地甩出了一对红心2。“这一把,我必须管住你。”他指着梁力咬牙切齿地放话。
米嘉欣独自离开了牌桌。
那几个人又开始叫嚣,甩牌。听起来,严行进居然干掉了一手好牌的梁力。
“你怎么知道一双黑桃K在我这里?他妈的,莫非吃了太空饼干?”
“哼哼,我就是吃了太空饼干,牛逼大了。”
于是,他们稀里哗啦重新洗牌,一边洗,一边“太空饼干”地说个不停,无非就是总结失败教训和获胜经验。
“妈的,以后跟你打牌,看来得先来两片太空饼干。”
米嘉欣在卧室听到那些狂放的笑声。她认出了严行进的声音。印象中,他好像只有在这些时候才笑得那么忘我,以至于她有点恍惚,平日里那个乏味、沉闷的严行进究竟是不是她的一种幻觉?
对于米嘉欣来说,阿姆斯特丹的确是一次很奇妙的旅行。她是跟几个闺蜜一起去的。风景倒没多吸引她。最后一晚在酒店里,杜倩倩在阳台抽了一根烟之后,回到房间,忍不住从旅行包里取出一个五颜六色的盒子,对正在喝啤酒聊天的她们说:“妈的,来荷兰不尝尝这个,你们是来干吗的?”米嘉欣接过盒子。她刚在coffeeshop的菜单上看到过,在卖啤酒的路边小店里也有,她还以为是巧克力,拿起来仔细读过上边的字母。杜倩倩是她们当中唯一的女烟民,逛街的时候,她偶尔会消失一阵,她们就知道她找地方买烟去了。就像嗜酒的人喜欢猎土著酒一样,她喜欢抽当地烟。昨天逛性博物馆的时候,杜倩倩就曾经脱离过队伍。赵杨说,我就知道这家伙去买这玩意儿了,跟抽烟一样嘛。
“哼,她终于憋不牢了,在coffeeshop吃饭的时候,她就一直在说,这种奇怪的香味,你们肯定第一次闻到,猜是什么?切,这用猜吗?”李素岚是五人当中的老大,心思最缜密,每次出门都全赖她做攻略,路线、酒店、交通工具,妥妥的打印在A 4纸上分给大家。
“抽了会有什么反应啊?怪好奇的。”米嘉欣忍不住问了出来。
“抽一口就知道了呗。在这里是合法的。”杜倩倩热烈响应米嘉欣。
于是,她们就学着杜倩倩的做法,各自卷了一根。一口、两口,赵杨和乔珊珊就先后嚷嚷:“不行了,不行了,晕。”赵杨揉着凸起的小肚子哼哼:“怎么这里热乎乎的。”米嘉欣什么感觉都没有,她只是觉得那些香味很特别。刚才在coffeeshop一直都坐在这种香味里。
杜倩倩抽完了一根。米嘉欣抽掉了三分之二。
接下来,她们几个人,一声不吭,等反应。山雨欲来的紧张兴奋。
米嘉欣的反应最慢。她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躺在了地毯上,当地毯从她的脊背开始下陷的时候,她的脑子出奇地清醒——嘿嘿嘿,现在开始。她听到自己兴奋的声音——地板凹下去了,柱子斜了,噢天啊,整个房间都偏离了,大约有七十厘米的样子。
后来,米嘉欣完全不清楚其他人怎么样了,世界只剩下她一个人。在她的眼前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画面。金色的教堂,教堂里的壁画,教堂里的展厅,展厅里的浮雕,画面不断转换,却无比清晰,仿佛身处其中。
“是卢浮宫。”米嘉欣笃定地对严行进发誓。“我真的看见它了。”
第二天她们又一起吃了太空饼干。要不是没法通过机场安检,米嘉欣都想带回来给严行进尝一尝。做完那个闭眼睛的游戏之后,她当时就想,闭上眼睛的严行进到底会看见什么?
严行进听米嘉欣说起这次经历,倒吸了一口冷气。“下次不能再跟她们出去了,尤其是那个杜倩倩,男人婆一样,难怪会离婚。”
米嘉欣没接话,继续跟严行进讲:“真的是卢浮宫,我回来查过百度,一模一样,那些壁画,蒙娜丽莎的微笑,穹顶的图案……就像我真的去过一样。”
“你又没去过卢浮宫。教堂都长得差不多。”
说来惭愧,严行进没出过国,也没有到外面的世界看看的愿望,他每天从单位到家,从家到单位,也不无聊。他觉得单位就是一个有趣的世界,在他看来,人和人的交往就是从最远的地方旅行到最近的地方,或者反过来。所有的风景,如果没有人和故事,有什么看头?
米嘉欣不一样,她喜欢出门走走,看看风景。女儿考上大学之后,他们终于得以脱身,小长假她约严行进出去旅行,但严行进总是懒得动,他们为此不时生气。
“山山水水,我们这里多的是,节假日就连你那破博物馆也人挤人。风景哪里都一样的嘛。”严行进就用这样的话来搪塞。
“饭饭菜菜,怎么吃都是吃,在哪吃都是吃,那你为什么还要奔东奔西参加各种饭局?”米嘉欣这样堵回去。
“吃饭的人不一样,怎么能一样呢?”
“你是吃饭还是吃人?”
一度,严行进认为米嘉欣喜欢出门旅行,大概跟她的职业有关。在仅有的几次一起出行之后,他又觉得她并没那么喜欢看风景,在跟导游听讲解的人群里,她总是会忽然消失。有一次在一个寺庙里,严行进以为米嘉欣掉队了,给她打手机,原来她压根就没跟着大部队停在半山腰的那个寺庙里,而是一个人爬到了山顶上。严行进生气地在电话里吼:“不来这个寺庙你来这个地方干吗,莫名其妙!”静穆的庙宇里回荡着严行进的吼叫声,所有人都看向他。他不得不灰溜溜跨出寺门。后来,他在山顶一个僻静的地方,找到了自己的老婆——她坐在一块石头上,盘着腿,眼睛闭着,很享受的样子。
“神经病!如果这样的话,小区里任何一张石凳上,你爱坐多久就坐多久,跑大老远干吗。” 他们总是不欢而散。
最后一次他们是去青岛。那一年,结婚纪念日遇上中秋小长假。朔望月一点点积攒,如同他们的婚姻,自转、公转,各种转动,竟然踩中了某个点。就连严行进这种早被米嘉欣判决为——身体里没有一粒浪漫细胞的人,接受这种命运的暗示,也生出了一些浪漫的想法。他们决定去青岛,看海上生明月。
他们提前一天到。途中因为预订的酒店并没能像广告上说的那样——窗边能看到海,严行进在总台跟人家大闹了一场。好不容易换到了一个能在窗边看到海的酒店,已经错过了饭点,饥肠辘辘,又不想出去觅食,只好叫了两碗海鲜面,为了区别平常生活,他们额外点了一瓶红酒。
落地大窗,窗外有海,总算很合意。海的舌头卷动着,一下一下地舔在米嘉欣的心里,不是咸的,而是甜的,像膨胀起来的棉花糖。
他们看过气象预报,如果明天天气晴好,十九点三十八分,最大最圆的月亮将会准时出现在这扇窗前。此刻,他们坐在窗边,对饮,话虽不多,但跟平时还是不一样的。米嘉欣望望远处的海,又望望近处的那个人,陷入了一种幻觉,仿佛自己是个小姑娘,那小姑娘脸上有着青春的光和微笑,她想跟对面那个人谈谈——爱情。有点困难,但她竟然说出了口:“你还有多爱我?”她连自己都被吓住了,尴尬得脸红。对面的那个人也是被唬住了,看起来有点不知所措。如果,这个慌乱的局面是因为紧张,米嘉欣会做出轻松的样子,替他解围。然而,他并不紧张,他左顾右盼地压抑自己,生怕笑出来,结果他失败了——他哈哈哈地笑着,仿佛听到了一个放屁的声音,忍不住笑了,只好尽力笑得欢乐一些,以期越欢乐越能解除对方的尴尬。如果,那个天真的小姑娘,会在这种笑声里撒娇、撒蛮,强迫他投降——爱死你了,爱死你了,够了吧,她便会原谅他。可是,她四十六岁,他四十八岁,他们默契的步伐不包括月亮这次踩下的那一步,那是宇宙的规律,却是他们的一次节外生枝。她的理性只够她在心里把那点红酒泼到他的脸上,然后让自己体面地转过身去。
电视的声音,很快掩盖了窗外那些不知内情的海的欢唱。那是一档法制节目,严行进每个晚上准点必看。无所事事,他们各靠在床的一边,看那个囚徒声泪俱下地忏悔,拖着脚镣,领着警察到他抛尸的现场——那是一个礁石凌乱的海边,海水混浊,凶猛地拍着礁石。“一个花季少女就是在这里结束生命的。”解说员惋惜的腔调,为这场悲剧谢幕。
第二天,他们在八大关转悠,视野都离不开海滨。海几乎没什么变化,严行进很快就腻烦了。然后他们购物,在摊档上买海贝饰品。米嘉欣找到了点乐趣,对比那些蜡染的裙子和琉璃手串跟她们博物馆纪念品超市的价格相差多少。午饭就在海滨一个饭馆吃,为点四个菜还是五个菜,一扎啤酒还是两扎啤酒,他们争论了几句。“两个人,就是很难点菜。”严行进其实还想吃一盘冰浸海螺肉,但,两人位的桌面显然已经摆不下了。
在吃饭的过程中,严行进开始弄手机。先是短信,几个来回,电话就响了。
米嘉欣心里一沉。知道他最终还是忍不住。他告诉过她,在青岛有几个大学同学,已经多年没联系了。出发前,米嘉欣特别强调了一下,她只想两个人,看海上生明月。
一个电话进来,严行进就眉飞色舞,仿佛孤岛求生者遇见了一艘船。两个电话,三个电话,严行进就嗨起来了。米嘉欣没法多说什么,她只是很好奇,那些已经多年没见面的朋友,是怎么被严行进搜索出来的。
十九点十分左右,他们看见了月亮,大得有点虚幻。米嘉欣觉得很失望,月亮并没有在设定的时间和地点出现。他们一大堆人,在一个安静的海角,升起篝火,搭起帐篷,月亮就在他们背后的那堆礁石间升起来,而不是那扇落地窗前。
严行进跟那些老同学坐在沙滩上,叙旧、喝酒,扯官场八卦。米嘉欣跟几个太太一起,负责烧烤,将那些牡蛎一只只撒上蒜蓉,滴上香油,然后一只只摆在烧烤架上。那几个太太都相互熟络,跟米嘉欣却是第一次见面。她们客客气气地交流着养生的方法。后来,她们提议煮点姜汤喝,要加点木柴把火烧旺。米嘉欣看到远处的沙滩边上有一丛小树林,便积极地说去那里找找看。其中一个太太执意要陪着一起去,米嘉欣拒绝了。朝小树林走去的时候,她发现那个太太一直跟着,她只好转过身去,礼貌地说:“请别跟着我,我想自己一个人走走。”那个太太愣在原地,不知如何作答。
米嘉欣顾不了为自己的失礼道歉,她只想藏进那堆黑乎乎的小树林里,就算那里边有老虎有豹子有豺狼,她也想待在里边。
是海边那种矮矮的红树林,因为台风的原因,长不高。米嘉欣钻进去,勉强藏身。从树枝间看天上月亮,并没那么大那么圆,顿时真实了许多。海风徐徐,吹来了远处围在那堆篝火边的人们的说笑声。她想退得更远一点,就像浪潮翻身那般绝情。可是,很快她就不能再待下去了。距她左侧不到二十米的地方,钻进来一对情侣,他们那么忘情,竟然没发现她,他们那么迫切,连明亮的月光也不害怕,发出一些模糊的气息和字词。她只好匆忙扯了几根枯枝败叶,落荒而逃。
那几个太太已经离开烧烤炉,各自回到自己丈夫的身边。米嘉欣只好朝严行进身边的空位走过去。他在讲着一个什么事情,大家都很感兴趣地在听,几乎没有人发现她。她并没有坐下,只是脱掉鞋子,站在细软的沙子里,抬头向海的方向看去。礁石的阴影很浓郁,这里一堆,那里一堆,在火光的映照下,凌乱而狰狞。她忽然想到了什么,大声打断了兴致勃勃的丈夫:“严行进,你看那里,那里,我们见过的,那个抛尸的现场。”她用手指着他们身后那堆礁石。
等那些突然安静下来的人回过神,那几个年轻一点的太太们发出了惊悚的叫声,她们纷纷躲到男人的怀里去了。只有米嘉欣还站在原地,她脚底那些细软的沙子仿佛开始松动。如果继续这样站着,她不知道会陷进一个什么地方。
青岛回来之后,他们各自暗暗发誓,不再一起出门旅行,就像圆月不再会准确地照在他们某一个应该纪念的日子上。
吞下几片太空饼干之后做的那些游戏,使米嘉欣重新认识了一下自己。与自己平淡的人生相比,她觉得自己多少有些不平凡。她对自己敏锐又奇特的感觉有了些挖掘。她第一次知道,自己能看到的比别人都多,尽管闭上眼睛,她也能看到。她甚至决定将那次所“看见”的画下来。
小时候,她跟随外公学过一些绘画,也算是有童子功。外公是村庄里的秀才,擅长画年画。过年前,村里人会拎一块猪头肉来排队讨年画。抱着鲤鱼的大胖小子,戴着官帽的财神爷,甚至复杂的八仙过海图,外公都能画出来。外公去世那年,她跟严行进抱着四岁的女儿回村庄过清明,她一户一户地去看外公的年画。那是2 0世纪9 0年代,一阵风似的,村里忽然开始流行一种三维立体画,几乎每家的厅堂中央都挂着一幅,他们告诉米嘉欣,往左侧一点看,那画中人的眼睛是闭着的,往右侧一点看,眼睛就是睁开的。外公的年画保留下来没多少,在暗绰绰的偏房,在油腻腻的厨房,甚至在冷飕飕的柴房,米嘉欣找到了他们从客厅转移过去的十来张。总体来说,外公画得还是很逼真的,就是脸谱过于单一,无论男人女人,只要笑得喜庆一点,左边的脸颊都会挂起一只长长的酒窝。
祭祖结束后,老舅公拿一只陶瓷碗送给米嘉欣。外公给外婆画过唯一一张肖像,他们将肖像烧制在陶瓷碗上,留个纪念。米嘉欣从来没见过外婆,可她在陶瓷碗上一眼就认出了她,跟那些年画一样,她的脸颊上有一个美丽的长酒窝。外公把外婆画在每一张年画上,这个秘密恐怕无人发现。米嘉欣对严行进说,原来,我是见过外婆的。
米嘉欣一点一点、细细密密地将她“看见”的那些部分画在纸上。局部的浮雕,展厅的角落,教堂的穹顶……她们单位资料室有很多关于卢浮宫的旅游手册,可她根本就不想借来临摹,那一次看见的那些画面,就像印刷一样牢牢印在她的脑中。外公说,画画的逼真,主要是神态的逼真,而一件东西的神态,是印在画家脑子里的。外公说不上是什么画家,但米嘉欣相信外公,他在年画上画的那些酒窝,每张都像印出来的一样。
严行进庆幸米嘉欣选择了画画。到了她这个年纪的女人,琴棋书画或者养鸟养生,总归会要捡起一样的。他单位很多女同事,凑在一起就交流她们的“兴趣班”。除了把自己的书房霸占掉——事实上,严行进更多的时间是待在客厅的沙发上,画画并不是件惹麻烦的事情。跟他一个办公室的陈曼丽,每天下班回家做饭后又跑回办公室,吹葫芦丝,据说她丈夫只要在家听到葫芦丝的声音,就像低血糖发作一样手脚发软。
“画画好,安静,养心,说不定还能让你,呃,有收获。”
“收获什么?”
严行进一时说不上来,他摆出一副家长的样子说:“肯定会有收获,总归比跟那些乱七八糟的女人出去疯好。”
米嘉欣撇了一下嘴。自从开始画,她的确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跟闺蜜联系了。她们给她打电话:“你在忙什么呀,那么久都不给我打电话,太过分了。”米嘉欣说:“我给谁都不打。”
画出来的都是局部,如果不是米嘉欣在旁边指指画画地解说,严行进根本不能确定她画的就是卢浮宫。不过,用色的基调倒是很有整体感的,是那种金黄色,很明亮,看久了,严行进会觉得那是一幅幅梦境。米嘉欣说,那好吧,就把它们命名为:米嘉欣的梦境系列。
整个夏天,米嘉欣都在书房里画她那些“梦境”,有时候连饭都懒得吃,就像上瘾一般。
严行进并不介意老婆沉迷于画画,他一个人占据客厅。有的时候,米嘉欣画得太晚了,就跑到女儿的房间睡,他一个人占据卧室,靠在床上,手指划拉几下ipad,头一歪就进入梦乡,美美地睡一大觉。更多的时候,他是在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跟同事通电话,哇啦哇啦地讲单位那些鸡零狗碎的事情,低声说,大声笑。遇到同事想聚会了,他也不拘什么时候,就张罗他们过来喝酒。反正,米嘉欣只要一进书房,就像从这个家里消失掉了,偶尔看到她从走廊尽头那个厕所里出来,他会轻松地跟她打个招呼:“嗨,老婆,又画多少了?”
直到老孙打电话来。
老孙是严行进过去的同事,调离之后,严行进跟他的联系不多,因为业务上并没多少交集,在严行进的通讯录里,他把他仅仅归在朋友一类,在这类之上,是亲人、死党、好友、同事。有时候,他跟米嘉欣没话聊了,也会心血来潮问:“你们孙馆长最近怎么样?”不用问,严行进都知道,老样子。管理着一个风景区里的历史博物馆,自己肯定都快成老古董了。他曾经在一次聚会上遇见过老孙,穿着复古的立领唐装,干瘦的身体在里边晃晃荡荡,让人联想起他那个没有油水的单位。
“老严,你做做你老婆工作,再这样下去,我也保不住她了。”
严行进吓了一跳。这种话他也说过,他警告自己手下——你再闯祸,到时连我也保不住你。
老孙叨叨地列举了些米嘉欣的工作错误,严行进都没记住,历史朝代、人文典故这些,他是外行,他对风景没兴趣,除了可数的几次接米嘉欣下班,他都没正儿八经到过老孙管辖的地盘。不过,白塔那件事情,他听明白了。
在他们生活的这个城市,一段古运河穿城而过,从严行进办公室的窗子看出去,如果没有雾霾,能看到运河边上那座白塔。对于白塔的来历,全城妇孺皆知:当年乾隆下江南,行至这段下榻,忽发感叹:此地与京城北海相似,可惜差一座白塔。次日清晨,乾隆推开窗,只见对岸一座白塔耸立,以为是从天而降,身旁的太监忙跪奏:是当地盐商为弥补圣上游湖之憾,连夜赶制而成的。乾隆龙颜大悦,赞赏有加。原来,当地盐商闻到风声,用万金贿赂乾隆左右,将京城白塔画成图,然后用盐包为基础,以白纸按图扎形速成。一夜造白塔,赢得了皇帝的欢心,更体现了盐商的机敏。
后人用汉白玉建起了白塔,尽管它与这里的南方古建筑风格很不搭配,但它曾为这个地方赢得圣上的赞扬,它是一个“功臣”,百姓歌颂它,也歌颂圣上。
在很多工作间隙,严行进会端杯茶,靠着窗户,呆呆地看着那座遥远的白塔,心里充满对古代盐商五体投地的佩服。
可是,现在老孙告诉他,米嘉欣不再背那些解说词,她指着博物馆里那座一比十比例的白塔模型,对跟着父母来观光的孩子们说:“这座白塔,是我们这里的标志性建筑。相传,清代一个商人,不满官商勾结,不愿同流合污,被扣以莫须有的罪名,贬至此地,因怀念京城,他跟妻儿一起在运河边用雪堆了一座白塔,与京城北海的白塔相似,以慰思乡之情。那年冬天,江南遭受百年难遇的极寒,白塔成冰,经年不化。奇怪的是,在他郁郁而逝的那一天,白塔忽然一夜之间融化了。后人为了纪念这位商人,用汉白玉建造了这座白塔,通体洁白无瑕,以喻其清正的一生。”
“胡编乱造!”老孙在电话里扯着尖嗓子吼。由他主编的那本本城《风物志》,其中关于盐商一夜造白塔的故事,占据一个章节,图文并茂,是他亲手执笔的。
根据严行进的了解,米嘉欣虽然一贯奇葩,但对待工作还是认真的,不该做出这么、这么——惊世骇俗的事情来,是的,刚才老孙在电话里,不断地提到了这个词。
米嘉欣并没有否认篡改解说词这件事。
“谁能证明他们说的就是正确的?”米嘉欣一副轻描淡写的样子,让严行进很不满意,难道她竟然意识不到,这样下去,她在单位会被搞“死”的。
“历史记载是这么说的,你就该这么说。”
“历史是谁记载的?”
严行进对历史没研究,没法跟米嘉欣就正不正确这个问题再扯下去。“随意篡改历史名胜故事,是,是违法的。”他不得不搬出老孙的话来。
“违的是哪条王法?”米嘉欣毫不示弱,都有些刚烈了。她的这个样子让严行进有点心虚。
“几百年都这么讲,人人都这么讲,有什么不好的?”
“有什么好的?我就不乐意那样讲,我就乐意跟小孩子这样讲。”
“你是在讲安徒生童话吗?”
“没错,我就是讲安徒生童话,有本事开除我。”米嘉欣身体薄薄的,敏捷地闪进了书房。
严行进愤怒地伸脚踹了一下书房门,他想跟进去,看看那个消失在门背后的老婆,看看她到底在搞什么鬼,看看她那些乱七八糟的“梦境”,而这些“梦境”看起来很可能会将他们的生活搞得乱七八糟。
可是,那扇门被米嘉欣反锁了。
严行进没想到老孙那么容易就能搞定。三个人,菜一千多,酒一千多,加上给老孙带走的烟酒、红包,小一万,他就答应把米嘉欣调换到档案室去。她再也不需要每天都做一只复读机,事实上,这是一台需要维修的复读机。
在饭局上,严行进和老孙之间并没有多少共同话语,把以前的旧同事讲过一遍之后,他和老孙就剩下一杯杯地干酒了。很快,他们就喝到门了。老孙那张干黄的脸,现在红彤彤地放着光,立领唐装的扣子已经脱到了第三颗。酒已经让老孙失去了端庄,看上去就像一个牢骚满腹的落拓文人。严行进酒量好一些,但也醺了,话特别多。要不是米嘉欣下手把他们的分酒壶都夺去,他们估计很快就会钻到桌子底下。
“我这个老婆啊,就,就是个奇葩,老孙啊,你不知道,我得有多操心啊……”严行进舌头有点大了,他一边说,一边用手将米嘉欣鬓边散落的一绺头发,轻轻地拨回她的耳后,最后将手搭到她的肩膀上,笑眯眯地看着她。他那么旁若无人,快要把头凑到米嘉欣的脸上了。实在太近了,米嘉欣本能地闭起了眼睛。
闭着眼睛,米嘉欣却还能看到严行进,他并没有坐在椅子上,而是在助跑,准备翻越对面那扇铁门,那是米嘉欣读大学住的女生宿舍铁门。他向里边的米嘉欣招着手,一气呵成地征服了铁门,顺利地站到了她眼前。年轻、清瘦、拘谨,压抑着荷尔蒙的热气。他跌落在二十多年后,米嘉欣闭着眼睛的这一刻。
米嘉欣吓得睁开了眼睛。她看见了严行进。他已经走到老孙的座位边,情绪高涨,正激动地要求跟老孙拥抱。老孙也激动了,他摇晃着刚从位置上站起来,马上就被严行进紧紧地抱住了,那干瘦的身体被挤得一句话都放不出。
饭局最终被米嘉欣强行结束。走出饭店门口,严行进和老孙还在拉拉扯扯,又被米嘉欣强行分道扬镳。跌跌撞撞的老孙被塞进出租车,手里还紧紧牵着那些烟和酒。
“没问题,老孙没问题,他还能拽着东西,就能安全回家,老婆,你放心,没问题。”严行进脑子很清醒,嘴巴已经管不住了,不断在重复地讲。
他们没有打车,也没商量过,就相互搀扶着朝南面走。沿着那条运河河堤,大概走十五分钟就能到家。他们走得很慢,因为没能走成直线,不断要矫正脚步。
这段运河,白天里人是很多的,市民都喜欢来这里走走,岸上桃花、梨花、梅花、樱花,种了一路,河面上铺着荷叶,他们把这段运河当作一面大湖,就像是某个皇家后花园,各个季节都来赏。这是一个夏季的夜晚,荷花的暗香和浮影,荷叶下蠢动的蛙噪,却让人心里分外宁静,静得米嘉欣只能听见严行进酒气的声音。
他们就这样走走停停,好像走到了很远的地方。当这段美好的景致就要结束的时候,严行进忽然摆脱了米嘉欣的手臂,他圆滚滚的身体一路朝前小跑,一边跑,一边喊:“米嘉欣,来,我带你飞。”他跑得竟然很稳当,几乎能跑成一条直线。没跑多远,他又停下来了,转过身去喊米嘉欣:“米嘉欣,快来,我带你飞!”话音未落,他像一只猴子,连爬带蹬,敏捷地攀上了停靠在路边的那辆叉车上。
等到米嘉欣走近,严行进已经稳稳地坐在了那只向上举着的货叉架上,就像他是这个庞然大物的某块零件。他两只凌空的脚踢来踢去,一边喘气,一边笑喊, “米嘉欣,我带你飞,我带你飞。”
米嘉欣抬头看着严行进,慢慢地笑了起来。刚才落入胃里的那点酒,也慢慢地升腾了起来。她一直抬着头,看天空那一团黑黑的影子,她几乎认不出他来了,好像某样东西,丢失了很久很久,猛然冒出来的那一刻。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米嘉欣觉得自己背部开始下陷,那感觉就好像在阿姆斯特丹的酒店,她陷入地毯之前,忘乎所以地大叫:“嘿嘿嘿,现在开始。”只不过,这一次,她觉得并不是陷进去,而是,被谁连根拔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