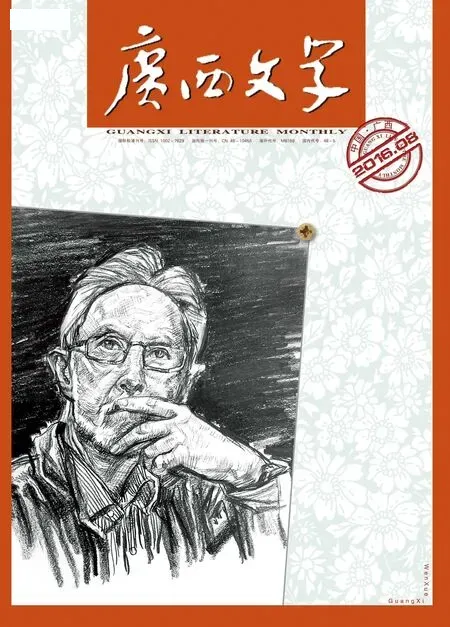我的开山祖婆
2016-11-26彭喜媛
彭喜媛/著
引 子
父亲死了,祖母活着。
2013年中元节前一天,祖母九十岁生日,我回乡为老人祝寿。
祖母这个月轮到四叔家赡养。去看她时,她坐在床头,裸露的手脚活像干柴棒。自去年跌了一跤后,她再也没有站起来。
我心情复杂地望着她。近在咫尺,却感觉和她隔着一座山,横着一条河。在她眼里,我有她年轻时的模样,她在我眼里,我预见自己将要老去的容颜。
怀念早已作古的祖辈。少时,曾听父亲不止一次谈及我家的开山祖婆,印象中,那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真实故事。
能为长眠于地下的祖先们做些什么呢?我惶恐地搓着手……
他们既非官宦巨贾,又非社会名流,也没有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压根儿没必要浓墨重彩。然而,终身守寡的开山祖婆贞洁如玉,宅心仁厚!她调教出来的子孙亦勤劳善良,造福一方。她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一颗微弱的“星星”,和她当年同呼吸共命运的不计其数,他们共同照亮温暖了那个特殊时代漆黑的夜晚。
先人已作古,唯一的家谱又太抽象,而眼前活着的,能开口说话的,还有精气神的祖母让我心里一喜:这一刻,我感谢祖母还活着!
祖母作为生活在新旧社会交替的平民百姓,耳闻目睹了近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虽说大字不识一个,但作为彭家的童养媳妇,对我们彭家的家史好歹也能说出个子丑寅卯吧。
人生有太多的不可预测,有时一转身就是永别,抓住现在才是永恒。
我请祖母从我家的开山祖婆讲起,她说:“要得,黄土垒到我脑壳顶上了,把这么好的故事带到棺材里去太可惜了!”
我将手机录音打开,放在她面前……然后搬了条板凳,坐在床尾,开始聆听……
一
清朝同治年间。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在湖南省祁东县,一个腆着大肚子的年轻孕妇,颠着一双三寸小脚,手里举着一盏桐油灯,跌跌撞撞地行走在乡间小路上……她——就是我的开山祖婆。
她的身后,跟着一名小丫鬟,丫鬟身上背着个大大的碎花布包袱,里面装的是她主人的全部家当。
这不是一次普普通通的夜行,而是一个家族的历史性转折!
我的开山祖婆二十一岁那年嫁入马埠村一个彭姓大户人家,那儿门前有一条清澈的小河,还有一望无际的田野。她丈夫排行老四,新婚后夫唱妇随,感情笃厚,孰料命途多舛,她身怀六甲时,彭公暴病身亡。
树大分枝。分家产时,接连抓了三次阄,我的开山祖婆分的都是深宅大院的偏房;田呢,分了三十丘(一丘为三十担谷地),是三里开外名叫红砖的小山冲。我的开山祖婆心里头明镜似的,眼泪只能往肚里流,她知道族人防她改嫁,胡乱敷衍她罢了。痛定思痛,她决定离开这个大家族,离开马埠,去那个偏僻的小山冲开始新的生活。
那时我们农村走夜路,通常用麻秆蘸桐油做火把照明,但我的开山祖婆在迁移的那个晚上,却偏偏选择一盏微弱的桐油灯。因为啊,她早已打定主意:今晚点灯走路,一不用灯罩,二不用手挡风,一切顺其自然,如果灯熄灭了,她就带着遗腹子改嫁;如果灯一直亮着,那肚子里怀的就是崽(儿子)了,她要把崽生下来,守一辈子寡!
当她们主仆二人走到红砖村时,手里的桐油灯光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她心里悲喜交加:看来老天爷是不让我改嫁了。
就这样,她在这个小山冲里草草安下家来,不久,生下儿子,取名彭金元。
二
红砖村三面环山,南面为出口,呈凹字形,交通闭塞,却也山清水秀,土地肥沃,随便丢些小麦、红薯等类的种子都有收获。
自从生下儿子后,我的开山祖婆心里有了舵,每天扭着她那双可以在量米筒管里打转转的三寸小脚,白天出去侍弄菜园,回来的时候割一把青麻秆,放在盆子里用水泡着……
晚上,我的开山祖婆给我的曾老祖父喂饱了奶,哼着童谣,哄他睡着了,放到脚边的一个木摇篮里……这时,她的脸上就露出微笑,笑着笑着,泪也跟着往下淌。她叹口气,然后坐在蚂凳上,就着一盏桐油灯,将一块旧布铺在膝盖上,将泡软的青麻秆从水里捞出来放在膝盖上,开始熟练地剖麻秆皮……
那时在我们当地,为了弄点油盐钱,有手工纺麻纱的习俗。我的开山祖婆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这如豆的灯光下,纺麻织纱,纳鞋底,做肚兜,常常熬到鸡叫才肯歇息。
都说寡妇门前是非多。
这时,本地一些单身的男人总想方设法接近她,抢着帮她挖地犁田、挑粪沤肥……
我的开山祖婆不恼不喜。一天下来,等到收工的时候,就当着第三人的面,大大方方塞给对方工钱,客客气气把人打发走,既不驳别人面子,自己也问心无愧。就连那些有家室的男人,平时有事没事也喜欢找她搭讪两句,走远了还要回头瞅瞅她那高挑的身材、动人的模样。其中有个叫三猴子的单身男人暗恋她不是一两天了。一天,我的开山祖婆在田边摘葱花,三猴子见了,径直走过去想套近乎,脚下不懂得拐弯,结果一头栽进水沟里……惹得在田里做事的长工们笑弯了腰!
尽管群蜂乱舞,我的开山祖婆还是行得正、坐得稳,平时讲话做事,样样拿捏得很到位,她甚至连一件捕风捉影的事儿都没有。
但媒婆对她这种人是不甘心的。那段时间,她家的门槛简直快被媒婆踏平了,她们介绍的都是大户人家,说不嫌弃她有个拖油瓶,只要嫁过去,保准坐在家里呼奴唤婢,吃香的喝辣的。
她用手指拢了拢鬓角的发丝,微笑着说:“找个肩膀靠一靠,我是舒服了,可我的崽就遭罪了,做人家继子,在人屋檐下,哪能不低头?!人家有金山银山,我不稀罕,我崽才是我的命根子!这一辈子,我就带着我的崽,帮彭家四房续香火,天皇老子都不嫁,吃糠咽菜也心甘情愿。”
媒婆不可思议地朝她翻了两眼,嘴里咕噜着:哎哟,有福不享,造孽哦!然后就抖一抖手中的手帕,撅起嘴,一扭一扭地走出去。
三
就这样,我的曾老祖父彭金元在我开山祖婆的哺育下,茁壮成长,他读完私塾后,开始学医。
我的开山祖婆勤俭持家,孤儿寡母的生活倒不至于很窘迫。有时见左邻右舍缺衣短食,还常常给予帮助,因而乡亲们都很敬重她。
一天中午,一个白胡子老头经过这个村庄。走到枣子塘的时候,脚下一滑,落入水中。老人不懂水性,在水里挣扎了好一阵,眼看就要沉下去了。恰巧我的曾老祖父从外面学医回来,看到有人落水,身上的长衫都来不及脱,不假思索地跳下去,将老人捞了上来,又把他背回自己家。我的开山祖婆连忙找出我曾老祖父的干净衣衫让老人换上,又叫丫鬟烧火做饭,还特意炒了几个好菜,给老人压惊。
说来也怪,老人在她家里白吃白住了三天,并没有要走的意思。我的开山祖婆和我曾老祖父对他一直敬如上宾,好吃好喝地侍候。
第四天早上,我曾老祖父一早醒来,发现老人不见了,枕边留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个医药秘方。他本来就是学医的,当时看见这个秘方笑了笑,不以为然。
孰不知,正是这张秘方,改变了我开山祖婆的命运,以至让子孙后代受益百年。
一日,隔壁院子李奶奶背着她的小孙女来我的开山祖婆家串门。孩子显得很烦躁,老是哭,李奶奶一边哄,一边骂。
我的开山祖婆抻长脖子去看那妹仔,发现她脸上、颈子上长满了红红的疹子,便“哟”了一声,说这妹仔怕是要出麻疹了!
那天,刚好我的曾老祖父也在家,她便叫他过来看看。
我曾老祖父仔细看了看,皱起眉头说:“怎么现在才晓得?麻疹现风了。”
李奶奶一听,脸吓得煞白,说:“我原来以为是长痱子,完了,我这妹仔小命难保!”
这时,我的开山祖婆说:“我崽晓得治麻疹,要不要他帮看下……”
李奶奶像不认识我曾老祖父似的说:“以前没听说呀!”
当时,我曾老祖父有点怪他娘多事,他知道他娘是急别人之所急,他临时想起了那个白胡子老人留下的秘方。
我的开山祖婆当场拍着胸脯说:“李奶奶,你放心,治得好治不好,都不收你一个铜板。”
十天后,李奶奶领着她的崽和媳妇,提着鸡蛋、米酒、白糖到我的开山祖婆家道谢,说是她孙女已经出完麻疹,从此算个正常人了。
接下来,我曾老祖父为周围的乡亲们治小儿麻疹,治一个好一个,一时名声大噪。
话说本县有个富甲一方的张员外,晚年得子,视若掌上明珠。小员外七岁那年出麻疹,老员外遣人抬轿子进城,请来最好的郎中,一连请了七个,银子花费不少,可小员外的麻疹没出齐,昏迷了好几天,眼看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老员外心如刀绞,哽咽着叫下人准备后事。
这时,在座的一位老医生说:“听说红砖出了个后生郎中,喊作彭金元,治麻疹蛮厉害的。”
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老员外打发一个家丁到红砖村来,请他走一趟。
“快去吧,崽,救人要紧!”我的开山祖婆催。
赶了十多里山路,来到老员外家。
张员外府上的人见我曾老祖父是个十七八岁的后生仔,身着粗布长衫,脚穿一双落满灰尘的布鞋,便露出轻蔑的眼神,待他的言行举止就难免怠慢。
我曾老祖父并不计较这些,直奔小员外床前。
小员外躺在雕花牙床上,我曾老祖父用手翻开病人的眼皮,发现他双眼紧闭,眼珠子已经不会动了,接着又探了探他的脉搏和气息,转头对老员外说:“张员外,您家有没有糯米酒酿和麻秆蔸蔸?”
“要好多有好多!”老员外说。
“还要水中的红浮萍……”
“这好办,好办呀!”
“赶紧用大锅烧开水,两床草席…… ”
一切材料准备就绪,我曾老祖父叫人把门窗关好,找来一个大洗澡盆子,往里面倒满药汤,又命人将两床草席立起来,严严实实围住洗澡盆子,一丝风都不要透进来……
他把病人抱进去熏,然后用力帮他擦洗……
屋子里围满了人,连咳嗽声都没有。
一袋烟的工夫后,又重新换上热药汤。这时,我曾老祖父扒拉小员外的眼珠子,发现会动了。
府中人奔走相告。
熏第三次时,小员外在水盆子里“哇”的一声哭出来了!
城里那些老医师面面相觑,脸上哪挂得住?他们用长袖子擦擦额角说:“张员外,恭喜贺喜!令郎福大命大,你们忙,先行告退。”
老员外哪还顾得上理那些人?他不停地朝我曾老祖父打躬作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临走时,老员外亲手用银盘托着金银珠宝要送给我曾老祖父。他目不斜视,只拿了一点点出诊费就告辞了,因为他牢记我开山祖婆的家训,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张员外命人用轿子送我曾老祖父回家,另打发两个家丁挑了两担箩筐悄悄跟在身后,一直送到他家里。家丁把箩筐往堂屋里一放,只说是张员外对彭郎中的谢意,便一溜烟跑了。
我的开山祖婆不知张员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揭开箩筐上封好的红纸一看,一担是酒、肉、布匹、面条等五色礼,另一担是满满两箩筐银元!
四
我的开山祖婆用这一担银元,在这个小山村大兴土木,盖了一座三进院墙、两千平米的大宅子。院内前后各建了一个大粮仓,可储存一千担谷子。一米多宽的屋檐,两手合抱不过来的木柱子,两米长的石码头,可谓气势庄严,在我们当地盖过好几条山冲。因我曾老祖父的父亲排行第四,于是将此院命名为“四房冲”。后来,这个村子就以四房冲命名,沿叫至今。
一夜暴富后,我的曾老祖父并没有沉迷于享乐。在我开山祖婆的指导下,他在本乡镇开了三家诊所。
每天,我曾老祖父的诊所门庭若市,他对待病人一视同仁,凡是贫苦人家前来医治的,往往分文不收,他的医德和医术在当地成为美谈。
成家后,我曾老祖父共育有六子二女。他的长子就是我的曾祖父——彭修德。
为避免吃没有文化的苦,我曾老祖父在自家祠堂开办私塾学馆,请先生授课,学馆有二十来个学生,极大地方便了本村及邻村的孩子学习。
做长辈的用心良苦,可我的曾祖父并不买这个账。作为大少爷的他,几乎没有认真听过一堂课,没有学会写几个字。我的曾祖婆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先生更是拿他没办法。他能把死的说成活的,能把圆的说成扁的,且性情豪放,不拘小节。有文化的人叫他“铁齿铜牙”,人们背地里给他取了个绰号——“白舌子”,这是我们那儿的土话,含有贬义,指不识字,大话飞上天的意思。
岁月荏苒,祖上的血脉一代一代相传。我曾祖父长得高大帅气,长衣白褂,脚穿我开山祖婆精心制作的软缎子鞋面,从头到脚都是清清爽爽,一尘不染,方圆十多里都知道他的大名。他揣着金怀表,胸襟前的表袋里常年挂着一支自来水钢笔,一根两尺来长的和田玉烟杆不离左右,他走到哪儿,哪儿的气场就截然不同。
我曾祖父二十岁那年有了儿子,他就是我祖父。后来曾祖母的肚子一直没有响动,当地人都说我祖父是个“秤砣儿”(绝无仅有的意思)。
我曾祖父深知自己吃了没文化的亏,但嘴上从来不说,他送我祖父念书,从几岁一直读到二十岁。
民国十七年(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保甲制的基本形式已有了具体规定:十户为甲,十甲为保,十保以上为乡镇。
其时,我曾祖父被选为我们当地保长。
一次,乡里开会,上头有份报告,需要记录,别人都在认真阅读,唯独我曾祖父叼着长烟斗咝咝地抽。这时,有个人调侃他,说:“彭保长,您天天戴着根那么高级的钢笔,怎么不用来写字呀!”
“哎呀,老兄,你提醒得好,今天走得匆忙,忘记带眼镜了,这样,麻烦你给我读一下呗。”
那个人原本想让他出一下丑,没想到弄个虱子到头上抓,没办法,他只好乖乖地念了一遍。我曾祖父的记性极好,轮到他发言时,他几乎一字不漏地讲出了会议纪要。
作为保长,当地群众若有什么纷争,需请保长或族长去评理,有理没理,关系到一族人的颜面问题。而我曾祖父,凭着红唇白齿,不知帮多少人扳回了理!在当地享有很高威望。
有个嫁到石家的彭家姑娘,一天跟石家人发生了纠纷,有人抬着轿子来请我曾祖父前去评理。
在石家祠堂里,围满了前来看热闹的人。
那时,石姓人家在当地是一个大族,族里也出了一些能人,因此不怎么把彭家人看在眼里。
我曾祖父是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人。他先把彭家姑娘叫到面前,问清了缘由,心下明白,她是受了别人的欺负,她是有理的。但他先不论理,而是当着众人劈头盖脸地将那彭家姑娘教训了一通,弄得她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哭哭啼啼地说:“彭保长,我是彭家姑娘,您怎么不帮我撑腰,反倒帮别人骂我?”
石姓人家一阵哄笑:“哈哈,还是彭保长识抬举,你们哪个敢跟我石家屋里的人过不去,那就是拿鸡蛋往石头上碰嘛……”
我曾祖父低头佯装用手帕擤鼻涕,悄悄对那彭家姑娘说:“蠢婆,我在打开台锣,骂给别人听的。”
我曾祖父的脑袋转得何等之快!不等石家人笑完,他把长烟杆往桌子上一拍,震得桌上的茶杯跳了起来。他脸色铁青,眉毛倒竖,冷笑一声:“哈哈,蚂蚁子打哈欠,口气大得很!没错,茅坑里的‘石’头固然又硬又臭,但是……”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们彭家屋里右边有三把凿子,凿起石头来,要你圆就圆,要你扁就扁!”
他的一席话,硬邦邦的,砸在地上鸡都啄不动。全场人瞠目结舌,有一下子没反应过来的,悄悄问:“哪来的三把凿子?”另一人就没好气地回答:“蠢呀,‘彭’字右边不是有三撇嘛!”
“哎哟!也亏他想得出!”
石家族长听了他这番话,早惊出了一身冷汗,老花眼镜差点掉到地上去,心想讲理哪是他彭修德的对手?这个“铁齿铜牙”一句话就能把活人噎死!
最后,石姓人家给那个彭家姑娘当面赔礼道歉,保证以后不再欺侮她,还买来鞭炮燃放,一来除晦气,二来为她恢复名声,并且大鱼大肉款待彭保长。
五
其实,评理这碗饭并不是那么好吃的,要是评不好,那轿子坐起来要烙屁股的。
有一回,我曾祖父又被人请到五里外的地方去评理,请他讲理的是另一个彭家姑娘。
到了那边,他先从旁人那儿调查了解纠纷情况,又从彭家姑娘那得到了证实,知道这彭家姑娘的确蛮泼辣过分的。
评理开始,对方族人在众人面前客观公正地把双方争吵的事实摆在桌面上。很显然,这场理,彭家姑娘输定了。
众目睽睽之下,我曾祖父慢悠悠地点燃他的烟斗,深吸一口,吐出一个长长的烟圈,他在思量,如何力挽狂澜……末了,咳嗽一声,提出要向对方当事人了解一点情况。
那个女人不知是计,自认有理,便在我曾祖父面前手舞足蹈地学起来。我曾祖父说人多太吵听不清,那女人便靠近他面前,说到彭家姑娘如何如何撒泼,越说越激动,唾沫星子溅了彭修德一脸……
我曾祖父侧耳倾听,听到关键处,打断她的话,问彭家姑娘是哪么子(如何)撒野的。
那女人突然劈开双腿,撩起上衣,露出白花花的肚皮,两个手板心一边拍打她的生殖器,一边朝我曾祖父作泼水状,嘴里放鞭炮样骂一些不堪入耳的脏话……
“反了,反了!大家快看……这个女人对我耍流氓!”我曾祖父腾地站起来,勃然大怒,话音未落,抡起长烟杆,敲在那女人的额头上,女人的额头顿时起了鸽子蛋那么大的包块。
全场鸦雀无声。
我曾祖父气咻咻地对众人说:“看看,这样一个泼妇,还说她有理,现在事实胜于雄辩!就她这副德性,我们彭家姑娘还能欺侮得了她?你们刚才都亲眼看到了,说说……该怎么办吧?”
对方族长哪料到会平地起风波?气得脸都绿了,一边朝那女人翻白眼一边小心翼翼地给我曾祖父赔笑脸……
那个女人在我曾祖父面前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哀求:“彭保长,刚才在您面前失了态,您大人大量,莫往心里头去啊……”
“蠢婆,我们族人的脸面全给你丢尽了!还不快滚回去杀鸡煮蛋给彭保长赔罪……”族长呵斥她。
生活中,我曾祖父是个千金散尽还复来的主。
作为保长的他,经常深入老百姓家里,哪家没油,哪家没盐,他就带那人回来,但不敢惊动我的开山祖婆。他叫人在耳门等着,自己蹑手蹑脚去厨房翻碗柜,把油盐酱醋夹在腋窝下,藏在衣袖里,悄悄塞给来人,也不图谢,手一挥,让他走人。
一来二去,我的开山祖婆发现家里油盐短缺,吃饭时就嘀咕:“厨房的油盐酱醋好像有人动过,莫不是屋里头进贼了?”
我曾祖父打个哈哈:“哪个贼吃了豹子胆,敢到我家来偷东西?可能是猫或老鼠啵。”
为了防偷防盗,我的开山祖婆一天到晚拄着把自制的竹筒扫帚,从后院粮仓到前院粮仓,一路“嚯啰嚯啰”敲过去,一路喊:“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一日,我曾祖父又领了两个家里没米下锅的人回来,发现我的开山祖婆在祠堂门口前院巡察,他便支使其中一人跟她扯白话。他呢,带着另一人,偷偷溜到后院仓库,支开下人,撬开仓库门,让人只管往箩筐里舀谷子。舀满了,就叫他挑起从后门溜走,然后大喊:“阿节(祖母),有人偷谷子了!”等我的开山祖婆颠着双小脚气喘吁吁地从前院赶到后院来时,早不见那人的后颈窝了。
六
在那时,我目不识丁的曾祖父,只有他想不到的,没有他做不到的。
乡亲们遇上什么难事,都会想到他。
一回,邻村的二柱来找我曾祖父,吭吭哧哧的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曾祖父两眼一瞪:“什么事,你痛快点儿。”
原来,二柱在外村某大户人家当长工,三十多岁了还没讨上老婆,他东家的儿媳妇荷花怀了崽,却传来她男人在外打仗战死了的消息。
二柱一直暗恋着荷花,荷花觉得他勤劳能干,平时对他也是高看一眼,两人一商量,愿意结为夫妻。
荷花婆家知道后,气得暴跳如雷,非要荷花守一辈子活寡。
我曾祖父听完后,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第二天夜晚,我曾祖父、二柱还有几个年轻力壮的男子前往荷花婆家。
按照事先约好的暗号,荷花悄悄从窗户里爬出来。当时的她即将临盆,而她家离四房冲又有七八里路,山路太窄,不能坐轿子,走路又行动不便。我曾祖父想出一个好主意,让壮汉将孕妇反身背起,疾步如飞……
荷花的婆家人发现后大喊大闹:“抢人啦,快给我追呀!”
等到了山顶,回头一看,山脚下舞动的麻秆火把像条火龙,照红了半边天……
翌日,荷花生下一个大胖儿子。后来,又和二柱生了三儿两女。直到现在,荷花近一百岁,她还活着。
我曾祖父此举,在当地已成佳话。
我的曾老祖父晚年时将家产分给六个儿子,每人五十担谷地。我曾祖父作为大房,分得祠堂左右两边最好的正房。不久,我曾老祖父与世长辞。
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民间疾苦。我曾祖母念及她的亲侄女两岁没了爸,七岁那年便把她叫到四房冲来做丫鬟。后见她做事勤快,又出落得眉清目秀,身高一米七三,便把她收为童养媳妇。她就是我的祖母。
我曾祖父二十岁做父亲,三十六岁做了爷爷,眼睛眉毛笑到一堆去了,放话出去,说要从县城请人来唱花鼓戏,宴请所有亲朋好友。我曾祖母听了,心里叫苦不迭,脸扭得比苦瓜还难看,悄悄拉了拉我曾祖父的袖子说:“家里都快没米下锅了,还唱哪门子戏啰!”
我曾祖父的二弟没有成家,三弟、小弟婚后没有生育。我曾祖父便建议将我祖父过继给他三弟做儿子,将我祖母给他二弟做儿媳。不久,我曾祖父的二弟三弟相继暴病而亡,他三弟媳改嫁。后来,那两份家产均由我祖父祖母继承。
我曾祖父另外三个弟弟都循规蹈矩,把田地都经营得很好。但到了我曾祖父手里,由于他的开销巨大,常常瞒着家里头把田当了,曾祖母敢怒不敢言,我的开山祖婆用手指戳他的脑壳,嗔道:“你呀,你古家(这个)败家子,一个人败了三家人的家当啊!”
“老人家,你哪晓得外面有好乱哦!我办了十条枪,准备打强盗(土匪)。”
我的开山祖婆颤抖了一下,身子往前倾斜,压低声音说:“崽(对晚辈的一种昵称),你晓不晓那强盗头子‘大嘴巴’是我们家亲戚哩!”
“晓得,按辈分喊他表叔,但他祸害我们四房冲的人,我就不能由着他胡来。”
“崽,你得注意自家安全,炮子铜管(子弹)冒(没)长眼睛哩!”
民国二十年(1931年)左右,中华热土内忧外患,土匪猖獗,连我们这个小山冲也时常有土匪出没,一下山就一窝蜂地拥到老百姓家里大扫荡。
作为保长,我曾祖父并没有光顾着自个儿吃喝玩乐,逍遥自在。其实这个时候的他,已经捉襟见肘,就连买酒买肉的钱都没有了。有时打发那个绰号叫“白毛”的亲信去赊猪肉,屠户割下一块上好的瘦肉,称都不称,直接给来人拿走,连账都不记。年尾了,我曾祖父家门口聚集了卖猪肉的、卖酒的、卖烟的人来收账,我的开山祖婆叫我的二祖婆弄几个好菜,招待那些收账的人,又赔了些好话。人家一分钱没收到,二话都不说,吃完饭抹了嘴巴就抬脚走人。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我曾祖父在家翻箱倒柜找了半天,问我曾祖母:“我那些放在橱柜抽屉里的炮子铜管哪去了?”
我曾祖母一听,头都懵了!原来她不知那些东东为何物,早让我父亲和二叔当玩具拿去耍丢了。我曾祖父气得脸色煞白,抬手就是一巴掌,我曾祖母用手捂着脸,吭都不敢吭一声。
当时,我父亲和二叔在床上睡觉。
外面有人喊:“不好了,强盗来了!”
我曾祖父一听,明白那个强盗头子是冲他来的,连忙叫我祖父朝后院跑到山上躲起来。
这时,一大群土匪杀气腾腾地冲进我家祠堂!“大嘴巴”高声吼:“白舌子,你给我滚出来!听说你办了三十条枪要办我们,今天,老子不但要办了你,还要绝你的种!”
我曾祖父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再说家里已没了子弹,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一闪身跨出门槛,刚好屋檐下垒着一墙土砖,他脚步太急,摔了一跤,把膝盖碰烂了,裤子也穿了个洞眼。土匪一进屋,不见我曾祖父,一把掀开麻纱帐,鼓起眼睛,恶狠狠地问我曾祖母:“这是什么人!是不是白舌子孙子?”
我曾祖母战战兢兢地说:“老侄哎,这两个奶崽是别人家的,来我屋耍,睡觉了,他们爷爷奶奶都在祠堂门口石凳上坐着呢,不信你去问。”
“白舌子,你平时不是牛皮哄哄嘛,今天怎么做缩头乌龟了!看你往哪里逃?快追!”
看见窗外有个影子闪过,“大嘴巴”手一挥,跳出门槛,抬手就是“砰砰”几枪。子弹打在砖头上,砖头被打得粉碎,火花溅得老高,吓得屋里的女人和小孩哭都不敢哭!
土匪们追不到我曾祖父,他们就挨家挨户抢老百姓的东西,揭锅盖,翻粮仓,折腾得鸡飞狗跳。直到天黑了,土匪们才打着麻秆火把上山,走到对面红旗岭上,忙着分赃。
这一夜,我曾祖父没有回家。他生死未卜,全家人惴惴不安。
直到第二天黎明,我曾祖父才全身湿漉漉地溜回家里来。他脸色苍白,全身瑟瑟发抖,三床棉被压他身上都喊冷!
他牙齿打战咯咯作响。他断断续续地告诉家里人,昨天跑出去后,他就在家门口的枣子塘尾头的芦苇下泡着。为了不让土匪发现,他全身淹在水里,只露出嘴巴和鼻孔以上的出气……
深秋的水已经很凉了,何况又受了伤,泡在水里一天一夜,伤口已经感染,不到三天,我的曾祖父含恨离开人世。我的开山祖婆哭晕了过去!
出殡那天,刚好是他四十岁生日,为他送行的人排成了长龙。据说四房冲下雨,七天七夜不见天。
七
人生三大不幸——幼年丧父,中年丧夫,晚年丧子,全给我祖婆赶上了!
我曾祖父死后,我的开山祖婆带着儿媳和孙媳,三代寡婆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在一个鼎锅里吃饭。一餐煮三升(筒)米,通常是给这个盛一碗,那个盛一碗,自己没餐饱饭吃。
在那个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年代,可能听说我们四房冲杂粮多,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混口米饭吃,所以外地讨饭的一天要来三五拨人。
我的开山祖婆每餐吃饭时,舀一碗白米饭,压得紧紧的,堆得高高的,夹几块茄子鲊、萝卜干之类的腌菜埋在饭尖尖上,佝偻着腰,颠着小脚走到祠堂大门外的石凳上坐下,捧着香喷喷的饭菜,光是闻闻,却舍不得动筷子。等讨饭的领头人往她面前一站,把手一伸,她就把碗里的饭全部倒给别人,也不转回去添饭,端个空碗在手里,待上一餐饭的时间才回家!
一次,我的开山祖婆把饭倒给叫花子,刚好给我曾祖父的五弟看见,于是就过来告诉我曾祖母说:“大嫂,大嫂,老祖婆把早饭送给上头屋里人吃了,又把晌午饭倒给外地的叫花子,看来她自己要饿到天黑了。”
由于年事已高,我的开山祖婆不再管粮食收租的事。有时在外面和别人扯白话,一双手也从没空闲过,不是搓麻绳,就是做布鞋。听说这家没腌菜吃了,那家没盐巴了,回家讲给我的二祖婆、曾祖母听,劝她们气量大些,接济乡里乡亲。
1950年冬季开始,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国农村拉开了帷幕。我的开山祖婆被戴上地主婆的高帽子,推上历史的舞台批斗,工作队的人拿鞭子抽打她。她一双三寸小脚顶着衰老而羸弱的身躯,犹如狂风暴雨后坠落的枯叶。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部分受过她资助的乡亲认为她是一个宅心仁厚的人,联合起来出面反对,极力保她。
传说中有一种无脚鸟,因为没有脚,不能停歇,只有选择飞翔,累了的时候也只能在风中歇息。无脚鸟一辈子只能落地一次,那就是死的时候。
我的开山祖婆就是只无脚鸟!她在这场运动中倒下了!
她在那个每天不知饿死多少人的非常时期,将自己保命的口粮施舍给认识或素不相识的人,自己随时准备饿死!
她守寡六十七年,一辈子冰清玉洁!绝不做男人的附庸!
她自嫁到我们彭家就从来没有停歇过!她脚跨两个世纪,活了八十八岁,生不逢时,死于运动,家里连副棺材都没有。乡亲们念及她的好处,凑了副薄棺给她,葬于离家八里外的中心塘的老祖山上。
打我记事起,从来没有人给我开山祖婆上过坟。守了六十多年寡的她,在生受够了寂寞,死后又是多么的冷清!
此刻,我想净身,素手,焚香……双手合十,虔诚地跪在我开山祖婆的坟前,三上香、三叩首,我想对她倾诉历史的变迁、时代的进步,以及她的品德成为子孙后代的楷模……
传说大寿星彭公活了八百岁,他的豁达和乐观可见一斑!自古以来,姓彭的人才辈出,铁血柔肠。
而今,我的祖屋早成了一片废墟,昔日的石狮石凳也不知跑到哪个旮旯角去了,徒留下祠堂门口几级裸露的石梯,无言地诉说岁月的沧桑。少时,我总嫌它破旧和残损,嫌它禁锢了理想和自由。
长大后,不管游子飘多远,才知道水有源树有根,才明白祖辈们的勤劳、仁慈、睿智是我们一生最大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