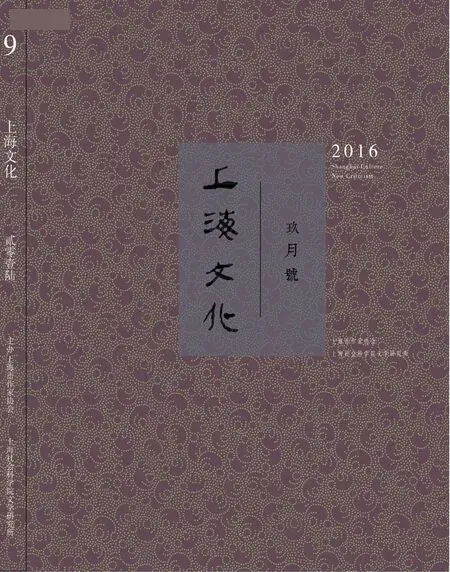芥川龙之介来到中国以后
2016-11-26东君
东 君
芥川龙之介来到中国以后
东 君
芥川与中国文学
永井荷风的《断肠亭日志》1927年7月24日一节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归途于电车中不时见有乘客捧读《东京每日新闻》的晚报,中有小说家答芥川龙之介自杀的新闻。说是患神经衰弱症而服毒自尽的,终年方三十六岁……我内心悄悄地追想我三十岁的往事,对自己无事活到今天感到不可思议,唯此而已。”
在日记中感叹芥川之死的永井荷风活到了八十余岁,在芥川去世前一阵子曾就“没有情节的小说”与之发生过笔仗的谷崎润一郎也活到了八十岁。而芥川龙之介,这位日本大正时期的鬼才、20世初的短篇圣手在人世间仅仅活了三十六个年头。
芥川去世那一年写的两部重要小说《某傻子的一生》与《河童》都谈到了自杀这一话题。《某傻子的一生》中有两句话让我记忆犹新。一句是:“人生比不上一行的波德莱尔。”照我的理解,这句话可作如下两种解释,一是:人生像波德莱尔的诗一样短;另一种解释是:人生湮没无闻,到底还不如一行波德莱尔来得有名。如果把这句话跟芥川短暂一生联系起来,那么我更倾向于前一种解释。可以说,《某傻子的一生》通篇氤氲的一种颓废、虚无、甚至绝望的气息就是从这一句话里面生发出来的。写到第四十二节,小说里又冒出了一句充满反讽意味的话:我最同情的是神不能自杀。这话与其说是跟神开玩笑,不如说是一种自嘲。口吻清淡,内心也是一片通透。生呀,死呀,反正就是这样子过来的。彼时的芥川氏,于死,无所畏,无无所畏;于生,无所恋,无无所恋。大致如此。
另一篇小说《河童》简直就是一个厌世者的叙谈。芥川在一次虚构的对话中借幽灵之口,提到了德国作家克莱斯特、哲学家迈兰德、奥地利思想家魏宁格尔等。如果再稍加注意的话,就会发现他们都是自杀者。从芥川的小说里可以见出其性格峻烈的一面:一个终日被创作激情驱策的天才作家无法容忍一个被疾病拖垮,连“动物的本能”都没有的病夫苟活于世。
我在各种版本的芥川文集里面见过芥川不同时期的照片。其相貌,可谓清瘦,带着病态的脸窄而长,眉头总是紧锁,表情总是忧深郁结。他那只细弱的手要么支着下巴,要么撑着脑门,仿佛他那脑袋里有什么沉重的东西需要一只手来支撑。他若是穿和服的话就会露出一副窄肩膀来,一根岌岌可危的细长脖子使他的肩膀与脑袋一直保持着一种脆弱的关系。我在芥川一篇介绍自己的小文章里看到,他一般来说每隔三个月理一次发,因此他的乱发就像是一团黑色的火焰,而他那双眼睛如同燃烧之后行将熄灭却又犹带火星的炉炭。芥川的形象在黄昏时分看来定然是十分清苦的,也很容易让人想起中国唐代的苦吟诗人,想起“郊寒岛瘦”四个字来。
芥川是受中国古典文学影响颇深的一个作家,反过来说,他的文学作品对中国现代文学也带来某种程度的影响。我们现在谈到芥川,就会有一大群日本近现代作家连带而出:泉镜花、国木田独步、夏目漱石、菊池宽、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便是:自幼就经受过汉文学的陶冶。中国作家读他们的作品往往会有一种微妙的既视感。
古代日本引入汉语,始有丰赡、典雅的书面语。但明治维新之后,西风东渐,日本开风气之先,自铸新词,这就有了语言文字的“返流”现象——日本文化输入中国之后,大量日语词汇随之返流,也融混到汉语词汇的长河之中。我们现在所用的汉语词汇据说不下三千种来自日本,只是百姓日用而不知。藤井省三所著的《华语圈文学史》在前言部分即指出:“现代汉语中的‘文学’一词,借用的是明治时期日本译介‘literature’时所创造出来的译语。”事实上,“现代”这个词何尝不是从日本引入?
有时我想,没有我们这位东邻,中国的现代文学也许要滞后许多年才会散枝开叶。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的作者鲁迅曾留学日本,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集《沉沦》的作者郁达夫也曾留学日本,中国第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新感觉派的催生者刘呐鸥也曾留学日本。他们通过日本接触西方现代文学,正如日本人当年通过荷兰接触西方文化。
然而,有时我又想,如果没有汉文学的滋养,明治以来的日本文学恐怕又是另一番景象。我很喜欢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所写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对中国文化的乡愁。这种乡愁,恐怕是浸透在骨子里、流入血液里的。在吉川幸次郎看来,明治以降,日本作家中汉文学造诣最深的,首推夏目漱石,其次是永井荷风(也许还要外加一个森鸥外)。夏目漱石之爱陶渊明、王摩诘,谷崎润一郎之爱高青丘、吴梅村,永井荷风之爱香奁体诗人王彦泓,都不是摆摆样子的。他们不仅爱读中国古诗文,也都能写一手不输中国诗人的汉诗。现在看来,日本大正时期出道的作家在汉学功底方面虽则不如明治时期的作家,但他们的汉学毕竟也是幼时习得,终身受用的。如果说芥川曾经在文章中对中国古典文学有过什么不敬的说法,那也是爱之深责之切。正如谷崎润一郎所言,他们的血管深处有一种被称为中国趣味的东西,因为浸润太深,也就难免有了恐惧。这种心理有时候会让他们在本能上做出一种排斥汉文学的姿态。无论怎么说,日本作家仰承中国古典文学的沾溉与中国现代文学接受日本现代文学的反哺都是不争的事实。
我把日本明治、大正时期的作品一路读下来,居然发现那个时期的日本作家好像都有一种写作历史小说的偏好。有学者认为,这跟日本当年发生“大逆事件”之后形成的紧张的政治气氛有关。森鸥外本人就承认,他是受此事件影响转而着手写历史小说,其中有一部分是直接取材于唐传奇的;而芥川刚出道的时候就直奔这条路子,其中一部分也是取材于中国的笔记小说。现实的逼仄,带来的是想象的自由。芥川来到中国之前,对中国的想象大概还附丽着唐诗宋词、明清小说里所描述的诸般风情。每每有朋友自中国归来,他就喜欢打听一些带有异域风情的故事,以便铺衍成小说中的某个情节。据说他的《杜子春》就是根据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提供的素材写成的。还有一篇《南京的基督》,发表于芥川中国之行前一年。他本人在文末附记中特地作了说明:起草本篇时,仰仗谷崎润一郎所作的《秦淮一夜》之处不少。也就是说,他写了那么多中国题材小说均非来自现实生活的体验,而是通过二手材料获取的。及至他来到中国,处处但见灰暗、破敝的景象,脑海里原有的唐风宋韵一下子就给搅散了。这情形颇有点像多情公子跟一个姑娘家隔海通信多年,一直以来为之魂牵梦绕,待到真正见了面,却发现对方是个粗皮糙肉的老姑娘,扫兴的话自然难免。芥川对中国的好恶,主要反映在中国题材的小说与一本《中国游记》的纪行文里。尤其是《中国游记》,谈得更直观。这一点,芥川跟夏目漱石、谷崎润一郎一样。漱石谈满州见闻,谷崎谈中国饮食,芥川谈中国人文,虽然各有侧重,但从总体来看,他们对中国的现状有诸多不满,文字里时常出现“肮脏”、“愚昧”等刺目字眼。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芥川未到中国之前,写了十几篇中国题材的小说,但到中国走了一大圈之后,除了一部《中国游记》,我们几乎没有看到他再写这类小说了。时隔五年,他写了一篇小说《湖南的扇子》,其中一些情节大概是他在湖南亲历亲见的。光是从题目来看,就很容易让人回想起他之前所写的《南京的基督》——这也是芥川喜欢干的一件事:在不同的小说之间开凿一条秘密通道,以供细心的读者去发现。
《南京的基督》与《湖南的扇子》
大正十年,也就是1921年3月下旬,芥川龙之介受大阪每日新闻社之命,坐船赴中国,作了长达一百二十天的考察。其路线与谷崎润一郎之前的中国之行大致相仿。此次中国之行,他走了很多大城市,看了不少场戏,还拜访了诸如章炳麟、郑孝胥、辜鸿铭之类的名人。在他眼中,章炳麟“那个突兀高耸的额头,直令人觉得会否长了个瘤”,“不知出于何种爱好,壁上趴着一条硕大的鳄鱼标本”;辜鸿铭有一张“酷似蝙蝠的脸”,留一条“灰白的长辫”,言辄“大骂基督教,大骂共和政体,大骂机械万能”。总之,这些人在他眼里都仿佛是些畸人异士,言语间也颇多谐谑。有些中国作家或学者觉得芥川为文近于猖狂,但我以为,这正是他一惯的文风,譬如他写自己的老师夏目漱石时,就用一种调侃的口吻说,他一点儿也没感觉漱石先生的书房有多“宏伟”,诸如“天花板看得出有耗子洞”,“那高窗户很像监狱或精神病院的窗户,有很粗很粗的栅栏”之类的话,他都不加掩饰地写出来。这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对待中国的鸿儒宿耆也像老朋友一样坦诚、率真。很奇怪,芥川拜访的人物里面大多是一些深谙国粹、精通国学的学者或诗人,没有一位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另一份资料显示,他跟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主将胡适博士也见了面,大致了解了一些小说和诗歌创作的状况。可我在《中国游记》(陈生保、张青平译)里面不曾见过这方面的文字记载。那本书里,也没有提及鲁迅其人及其小说。在胡适还没有发表第一首诗、鲁迅还没有发表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之前,中国文学与日本现代文学相隔着一座欧州。
通过史料,我们或可发现,就在芥川访华那段日子里,鲁迅翻译了他的两个短篇《鼻子》和《罗生门》发在北京《晨报副刊》上。芥川即便没看到那份报纸,也当有所耳闻。当时,芥川知道作为译者与同行的鲁迅?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鲁迅在1918年之后就已经写出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风波》、《故乡》等短篇小说(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译者之一陈生保在他的导读一文里面罗列得更仔细,把创作时间都标上,仿佛是一件彰彰可考之事)。我翻看了一下《鲁迅全集》,《故乡》这篇小说的创作时间是1921年1月,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时间则是1921年5月,也就是说,芥川龙之介来到中国后,如果留意当月的《新青年》杂志,就能读到鲁迅的《故乡》。事实上,芥川访华之后也应该知道鲁迅其人。《华语圈文学史》有这样一笔记载:“一九二○年代初期,中国以言文一致为目标而创制的‘国语’,借以现代文学为教材的国语课程而得以普及,日本的芥川龙之介、佐藤春夫及武者小路实笃等著名作家对于已开启了现代化进程的中国都抱有浓厚的兴趣,开始介绍作为同时代的中国文学旗手的鲁迅。”因此,以我的推测,芥川来到中国之后,或许读过鲁迅的小说。不过,鲁迅出版第一部小说集《呐喊》要比芥川的中国之行晚两年时间。因此,也可以推断,芥川当时即便读过鲁迅小说,也是极其有限的。时隔多年,芥川写了一篇短文《日本小说的中国译本》,提到了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文中一段话是对鲁迅——他的记忆有误,翻译芥川氏作品的应该是鲁迅,而非周作人——的赞赏:“至于翻译水平,以我的作品为证,译得十分精准,且地名、官名与器物之名均附注释。”写下这段话,也算是跟鲁迅隔海握手吧。
芥川写作《湖南的扇子》是1926年1月。距他访问中国已逾五年。有人从这篇小说里面读出了人道主义思想,而我却读出了一种宗教感。关于这个话题我会在后面谈到。
1921年5月30日,芥川从汉口出发,去湖南长沙走了一圈。长沙城比他想象中还要破旧,跟长江沿岸的一些城市几无二致。在芥川的《中国游记》里面,他是这样描述长沙:“这是一座在大街上执行死刑的城市,一座霍乱和疟疾肆虐的城市,一座能听得见流水声音的城市,一座即便是入夜之后石板路上仍暑气蒸腾的城市,一座连公鸡报晓声‘阿苦塔额滑丧’(与日语‘芥川先生’发音相近)都像在威胁着我的城市……”《湖南的扇子》从表面上看像是一篇纪行文,实则是小说。里头的叙述时间亦作调整,变为1921年5月16日。从开头部分来看,他对长沙这座城市照例是没有一点好感,在他眼中“除了猪以外就没有什么可看的东西了”,在这种近乎嫌恶的语言氛围中他讲述了一个貌似风雅、谐谑却暗含残忍与愚昧的故事。长沙之行接待“我”的,是一位曾留学日本的中国医生谭永年。谭指着狗走过的一块地方告诉“我”,之前本城有五个人就在这里被砍了头,外国人没有见识这一场景的确可惜。因为,谭说,唯独斩首杀头在日本是看不到的。而后谭带着“我”乘坐汽艇饱览了湘江、橘子洲,以及岳麓山的风光。那天晚上,谭还带“我”进了一家妓馆。与三两妓女聊天时,谭从老鸨手里接过一个小纸包,打开一层又一层,里面便露出一块巧克力色的脆薄干点一样的东西。“我”问这是什么。谭说,是一块饼干,上面沾了几天前一个被砍头的土匪头目的血。又问,作什么用?答道:吃了可以除病消灾。座中的妓女玉兰与含芳都曾是那个土匪头目的情人,此时见了这饼干,虽说反感,却不敢表露出来。谭把人血饼干递给大家吃,无人敢接。最后,谭把它递给了一直不动声色的玉兰。玉兰说了几句话,就接了过去。谭把玉兰的话翻译给“我”听:“我非常高兴地品尝我深爱的……黄老爷的血……”
读到“人血饼干”,我们或许会想起鲁迅早年的一个短篇小说《药》里面的“人肉包子”。这篇小说写于1919年4月,同年5月发表于《新青年》杂志第六卷第五号,两年后芥川到中国访问,这个时期即便没有读过鲁迅这篇小说,至少在之后几年里应该也曾与闻。《药》里面有这样一个情节:“他的母亲端过一碟乌黑的的圆东西,轻轻地说:‘吃下去罢,——病便好了。’小栓撮起这墨东西,看了一会,似乎拿着自己的性命一般,心里说不出的奇怪。”而在《湖南的扇子》里,老鸨手里那个小纸包里包着的,便是“已经发干了的巧克力色的奇怪的东西”。不同的是,小栓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人血包子,而玉兰明知这是人血饼干却依旧吞了下去。芥川写到这个细节时,一种宗教感就出来了。这是在鲁迅的小说《药》中所没有的。谭把饼干递给了一直微笑动也不动的玉兰,原本是要羞辱她的,但玉兰却像领取圣餐一般领取这份羞辱。她还怀着敛抑的语调对众人说:“但愿你们也像我一样……把你们所爱的人……”恕我在此重复引用这句话,因为它让我忽然想起《哥林多前书》中谈到圣餐的设立时所说的一段话:“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劈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他来。”因此,就凭这一点,我以为,芥川的《湖南的扇子》与鲁迅的《药》走的是全然不同的路子,倒是跟他自己之前所写的《南京的基督》有一种暗在的精神联系。这种精神就是芥川一直寻求的宗教精神,更深入一点说,这种宗教精神跟他受西方作家影响,“从艺术的角度喜欢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不无关联。
我们都知道,芥川跟其他一些和洋汉三才兼备的日本作家一样,在创作上奉行的是“拿来主义”,无论东方西方,明着借鉴,暗中较劲。毫无疑问,鲁迅作为同时代作家,曾进入芥川的视野,但尚未触及他的思想内面;芥川对鲁迅小说的素材有无借鉴尚难论断,即便有之,也只是一两个情节上的相近——有些作家就是这么奇怪:他们相隔迢遥,生活中没有交集,精神上没有共振,但就在某个点上突然相遇,彼此欣赏,点头致意,然后迅速分开,各走各的路。鲁迅与芥川之间的关系大概就是这样的。
芥川自杀那年,也就是1927年2月,他完成了一部重要的作品《河童》。这部小说的开头部分,极像鲁迅写于1918年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两篇小说前面都有一篇小序,讲述的都是一个精神病人的简单病况。这一段文字如果不能视之为巧合,那也是一种向鲁迅——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的拓荒者致敬的方式。《河童》中这名“第二十三号病人”大概有三十多岁,而《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不能简单地归类于精神病患者当中)从年龄来推算,也有三十多岁。《狂人日记》第一章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日本学者伊藤虎丸注意到了“三十多年”这个时间点。他认为,如果作者文中使用“三十多年”这个数字具有特别意思的话,那么中华民国成立那一年,鲁迅刚好三十。这样的推论也许不无道理。在《铸剑》里面,鲁迅曾十分明确地告诉我们:眉间尺背着宝剑踏上复仇之路的年龄正好是十六岁。为什么鲁迅要凸显这个时间点?有考据癖的人认为这个数字之于鲁迅别具深意,十六岁,正是他离开绍兴去南京洋式学堂读书的年龄。三十,是而立之年,有所作为的年龄。但鲁迅笔下的狂人与芥川笔下的“第二十三号病人”非但一事无成,在外人看来他们的脑子也是一塌糊涂的。芥川写这篇作品时,精神状态已经越来越糟糕,他常常担心自己会像母亲那样疯掉。因此,内心那一点稳静失去后的茫然不安在他的文字间随处弥散着。
《某傻子的一生》从表面(包括题目)来看有点近于《狂人日记》,但细读之下,就会发现二人的叙述风格与路数都不一样。芥川这篇小说虽然没有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但仍然带有“私小说”的某些特点。《某傻子的一生》散漫写来,都无伦次,却又仿佛有一根线把散乱一地的珠子串了起来。他所写的大都是日常生活中属于个人的一种寂寞的心境、无聊的状态和厌世的情绪。他就这样无所忌畏地写出来,也不管读者能否懂得。芥川自杀前一个月写给小说家久米正雄的一封信中就曾不无审慎地写道:“稿(即《某傻子的一生》)中所出现的人物你大概都知道。但是发表之后,希望你不要加上注解。”为什么“不要加上注解”?因为这一类文字很可能会坐实自己或别人的隐私,于人于己,都不太好。
我以为,作为小说家,芥川作品里面的成分似乎要比鲁迅复杂。他总是能从“瞬间危机”发现人性的暗区,从现实的缝隙切入一步步迫近事物的本质,因此,他那种近于幽暗的叙述里面总有什么东西如同水光一样微微晃荡着,使人产生隐约不安,却又仿佛有所期待。芥川小说的魅力,大概就在这里。
芥川与鲁迅
把中国作家来跟国外某位作家作比较研究,是批评家们通常喜欢干的活。依例,把芥川与鲁迅放在一起谈也能谈出一些话题来。但这样做就好比早些年周作人把郭沫若拉来跟谷崎润一郎作比较,把郁达夫拉来跟永井荷风作比较,只能是就某一相似点而论。夏目漱石有两撇胡子,鲁迅也有两撇胡子,但我们不能就此说,鲁迅像夏目漱石;芥川一生只写短篇小说,鲁迅一生也只写短篇小说,但我们也不能就此说,鲁迅像芥川。鲁迅终究是鲁迅。就像芥川终究是芥川。
芥川年龄比鲁迅小十一岁,小说创作的起步时间却比鲁迅早四年。芥川着手写小说之前,日本现代文学已经走过了近三十年的历程,在芥川之前,有夏目漱石、泉镜花、国木田独步、谷崎润一郎等,他们都给芥川带来了或多或少的影响。而鲁迅不同,在他之前,中国现代文学的园地还是一片荒芜。他所能参照的,大多是日本或西方的小说家。因此,鲁迅在尚未找到小说叙事方法之前,他一直不敢轻易下笔(这就是他早年写过一篇文言小说之后难再赓续的一个原因)。鲁迅做什么事,都是十分谨慎的。他要看了百来部外国小说,翻译一些域外小说之后才敢动手。可以打一个或许不太恰当的比方:芥川就像一个带足了本钱杀入赌场的赌徒,因此他可以放开手脚赌一把。而鲁迅不同,他口袋里的本钱不多,因此他赌得格外小心翼翼。在鲁迅那个年代,现代派小说已经在西洋与东洋大为盛行,但鲁迅的创作多取现实主义修辞,其态度也是多取传统的人道主义精神。这条路子已经在此前被西方作家视为正途,而他循此走下去不会因为陷入旁门左道而人仰马翻。
多年前,我曾与研究中国现代海派小说的日本学人木村泰枝聊起过鲁迅与芥川。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在日本,没有像鲁迅那样的作家;在中国,同样也没有像芥川那样的作家。可是,我们为什么能从芥川身上发现鲁迅的影子,从鲁迅身上同样能发现芥川的影子?
我以为原因有三:
其一是影响过鲁迅的作家也曾影响过芥川。反之亦然。像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日本“国民作家”夏目漱石,都是影响过他们的诗人与作家。鲁迅的《野草》与芥川的小说中不乏对人性之恶的书写,从中能感觉到他们或多或少受到波德莱尔的影响。波德莱尔在《恶之花》的题辞中说:你如果没有从撒旦那里学过修辞,你就扔掉此书。鲁迅早期有一篇雄文《摩罗诗力说》,可以直译为:论撒旦派诗歌的力量。他也正如波德莱尔所说的那样,试图从撒旦派诗歌那里获取一种反抗的力量。而芥川无论在文章或书信中都曾谈到过波德莱尔,也曾借他的诗引申开来,抒发一些对善与恶的看法。他的《蜘蛛之丝》、《烟草与撒旦》、《地狱图》写到了撒旦、地狱,说到底写的就是人性之恶,因此也不免带上一种“波德莱尔式”的阴冷调子。至于说到夏目漱石,更是他们二人无法绕过去的一位前辈作家。芥川与鲁迅虽然未曾谋面,但他们的文字因缘说起来与夏目漱石不无相关。1908年4月,鲁迅曾租住夏目漱石住过的老宅。1915年12月,芥川由一位同学介绍正式成为夏目漱石的入室弟子。从这两件事来看,夏目漱石都是他们内心追摹的作家。周作人说,鲁迅日后所作的小说“虽然不似漱石,但嘲讽中轻妙的笔致实受漱石的影响”。我们再来读芥川龙之介的小说,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漱石先生也曾如此这般写过”的感觉。
其二是鲁迅翻译过芥川小说,由于个人风格过于强烈,就易使读者脑子里早存了一个“鲁迅味的芥川”。如前所述,中国最早把芥川龙之介作品翻译成汉语的是鲁迅。不过,除了《罗生门》与《鼻子》,鲁迅似乎再也没有译过芥川其他作品,但因为译笔好,人们提起芥川小说,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鲁迅的译作。有人据此认为,鲁迅的《故事新编》有几分芥川的笔调。这实在是一种误解。鲁迅当年翻译芥川用的是自己的笔调,这就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芥川的小说风格就是这样子的。因此鲁迅那些从古代神话或史料中拾取的小说也自然被人误读成了“芥川味的鲁迅”。事实上,二人的心眼手法大不相同。鲁迅早年也曾用自己的笔调翻译过契诃夫的小说《省会》,也有人据此断定,鲁迅的《故乡》模仿了契诃夫的《省会》。现在我们把两篇作品放在一起就可以发现:鲁迅的确从自己翻译的《省会》中得尝异味,但他所写的《故乡》却散发着浓重的“鲁迅味”。
其三是芥川与鲁迅都读过大量中国与日本的古代典籍,善于从旧书里面获取写作资源,他们的来路与去向都是历历分明的,其间或有重合也是难免的。芥川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的历史小说。就题材而论,主要分三部分:日本古代的、中国古代的、西方古代的。本国的题材大部分取自《古事记》、《今昔物语》之类;中国题材则大部分取自唐传奇与明清笔记小说,在他的小说集里面所占份额较大。鲁迅也写历史小说。在题材上,鲁迅显然是要故意避开芥川驾轻就熟、“老手气息太浓厚”的那类东西。他给自己设定了一道门槛,仅限于秦汉以上的神话与历史。而且,他也没有像芥川那样拾取别国历史或神话入小说,他还是写中国,不及其余。这跟他写《中国小说史略》时只关起门来谈自家古代小说拒绝跟外国小说作比较研究的作风大致相同。鲁迅翻译芥川的历史小说时,曾在附记中十分坦率地谈到两点不满之处,其中一点便是“多用旧材料,有时近于故事的翻译”。这也恰恰是后来文学史家夏志清诟病《故事新编》的地方:“说的有现代白话,也有古书原文直录”(见《中国现代小说史》)。较之于鲁迅其他小说,《故事新编》的写法就更自由了,有些地方或许还保留了早期小说的阴郁气息,但从总体来看,它有一种现代小说的“自在性”,心中无碍,文字间即是一派水流花放,白云涌现。它不是什么“主义”或“流派”所能框得住的。这一系列作品虽然不讨周作人、夏志清等学者所喜欢,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它是有“新意”的,甚至是可以与芥川的历史小说并称于世的。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芥川是写了一系列历史小说后,转而在私小说的影响下写起了一些现实题材的小说;而鲁迅则是写了一系列现实题材的小说之后,开始写一系列历史小说。他们取道有别,但通过这两类小说呈现出了各自的历史意识与现代性,以及现代作家不可或缺的个人主体精神。
芥川与鲁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芥川是一个急迫的天才型作家。他出生于1892年,卒于1927年,而他真正开始小说创作的年龄是二十二岁。在短短的十三年间,他居然发疯般地写了一百五十余部中短篇小说(其中不少短篇放在当下依旧粲然可观)。鲁迅于1923年出版第一部小说集《呐喊》的时候,他已经出版了第六本小说集《春服》;鲁迅于1926年出版第二部小说集《彷徨》的时候,他已经在两年前出版了第七本短篇小说集《黄雁风》;而他的第八本小说集也将在次年出版。
相比之下,鲁迅应该算得上是一位从容的学者型作家。在小说家鲁迅尚未诞生之前,他已经不声不响做了十几年的学问,日本学者伊藤虎丸称之为“原鲁迅”,这个“原鲁迅”就是写《中国地质略论》、《中国矿产志》的科学者鲁迅,写《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的思想者鲁迅,翻译《地界旅行》、《域外小说集》的译者鲁迅,地方志研究者鲁迅,文学者鲁迅,诗人鲁迅等等。他身上有着多重方向,但真积力久,最终还是选择小说创作作为爆发点。这个爆发点是在他三十六岁那年方始找到的。这方面,鲁迅倒是有点像另外两位日本作家夏目漱石与森鸥外,他们都是早年留学,知识结构庞杂,文学储备也足,从事小说创作的年纪也相对较晚。换一种说法,如果鲁迅只活到芥川那个年纪,我们就无法看到他那些最为后人称道的小说了。因此,我们也可以为之捏把汗说,幸好鲁迅能活到五十六岁。
芥川龙之介好像就是为写小说而生的。他生前出了八本小说集,三本随笔集。此外,还有若干小品、游记、日记、书信、俳句等零星作品。之于他,小说最为倚重。而鲁迅去世后整理出版的二十卷《鲁迅全集》中,只有二卷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创作,这里面自然包括他为数不多的短篇小说。从二人的作品类型来看,芥川一生,几乎是以写小说为志业的,而鲁迅的小说创作则是阶段性的。有一段时期,兴致来了,就写上几篇。鲁迅第一本小说集《呐喊》的写作时间集中于1918年至1922年间,第二本小说集《彷徨》的写作时间在1924年至1925年之间,中间有十年,他几乎没写什么小说,《故事新编》里面的作品大多是晚年写的。鲁迅研究中国古籍所耗费的时间与精力,远远在芥川之上。周作人把鲁迅的作品分为甲乙两部分,其中甲部大部分为古代典籍的搜集辑录与校勘研究。由此可见,鲁迅在三十六岁之前是没有想过做小说家的。
芥川的目标是很明确的:不停地写,做一个世界一流的小说家。不幸的是,芥川在前半程用力过猛,以至健康问题出来后影响了创造力,反过来说,创造力的衰竭对一个作家来说是最为致命的。疾病带来的痛不欲生往往会伴随着写作过程中引发的力不从心。问题就在这里,芥川是靠创造力写作的作家,一旦无所依恃,他就会生出一种毁灭感。芥川研究者发现:芥川在最后几年里,虽然有作品不断问世,但从总体质量来看大不如前了。别人可以感受的,芥川本人当然是比任何人都更为敏锐、也更为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鲁迅不同,他身上固然有创造力,但这种创造力之外还有一种他早年所信奉的“摩罗诗力”。从鲁迅晚年所写的文章来看,虽说是满纸凄凉,但骨力依旧,他的创作欲丝毫未见衰竭,且不说他去世前一年完成的《故事新编》,单是像他后来病中所写的《女吊》,也还可以看出他写《朝花夕拾》时的平和心境。不过,即便如此,夏志清教授还是迫不及待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个时期的鲁迅“显示出一个杰出的(虽然路子狭小的)小说家可悲的没落”。
事实上,写作就像是跑步。跑步的能量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肝醣,一是脂肪。有些人一开始就跑得快,是因为调用了肝脏里的肝醣带来的能量,但这种能量在短时间里很快就耗掉了;而另一些人不然,他知道肝醣转换成能量比脂肪转换的能量更大,但持续时间不长,如果要跑马拉松,就得均衡地分配二者,尤其是增强脂肪转换为能量的效率。像芥川这样的作家显然属于前者,他更适合做一名短跑运动员。鲁迅没有芥川那样的爆发力,但他有一种持久的耐力。他原本是可以做长跑运动员的,但很可惜,他也只是比芥川多跑了一程路就倒下了。
如果非要说鲁迅与芥川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我以为,那就是体质。我们甚至还可以比较一下鲁迅与芥川身上的疾病。
芥川在自杀那一年身上有多种病症:肠胃炎、神经衰弱症、心悸、失眠、痔疮等。对芥川而言,神经衰弱症是最为致命的,他的老师夏目漱石也一直为此病所苦。一位翻译家谈到夏目漱石时说,神经衰弱症能导致精神绷紧,触发创作激情。这实在是站着说话腰不疼。神经绷紧,在短时间内可能对写作者有所助益,但长此以往,神经就会变得像拧了又拧殆无余沥的毛巾一样,激情既告汩没,灵性亦告销歇,给生活与写作带来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芥川所忧者,正是这一点。因此,我们可以说,芥川不是死于神经衰弱症,而是死于对创作欲衰退的恐惧。
鲁迅身上的疾病有以下几种(这是一位日本医生在他临终前诊断的):胃扩张、肠松驰、肺结核、右胸湿性肋膜炎(其弟周作人也得过此病)、支气管喘息、心脏性喘息及肺炎(详见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对鲁迅来说,病痛自然难免,人之将死的预感也曾有过。但他似乎没有像芥川那样想到以自杀的方式终结自己的生命,相反,他每每在深夜醒来之际,还会打开电灯,要看来看去看一下。看什么?看人世间但凡能看得到的与看不到的一切。鲁迅说:“外面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鲁迅的笔调是冷的,但对这个终将告别的世界始终是深爱着的。
在芥川晚期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创作欲日益枯竭之后,他的厌世情绪也日甚一日。1927年6月,也就是离芥川服药自杀只有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完成了上面提过的那个短篇小说《某傻子的一生》。在结尾处,他这样写道:“他执笔的手颤抖起来了,甚至还流口水。除非服用0.8毫克的佛罗那,他的头脑没有一次清醒过。而且也不过清醒半小时或一小时。他只有在黑暗中捱着时光,直好像将一把崩了刃的剑当拐杖拄着。”
这一段话大概就是芥川在生与死之间苦苦挣扎的写照了。芥川去世时,枕边放着一本打开的《圣经》。他很想借助宗教信仰化解内心的苦闷,然而,他一直未能如愿。芥川氏若能奉神之召上天,那么,我想,他大概会坐到神的左边吧。
初稿写于
2016年7月24日芥川龙之介忌辰
7月30日深夜改讫
编辑/黄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