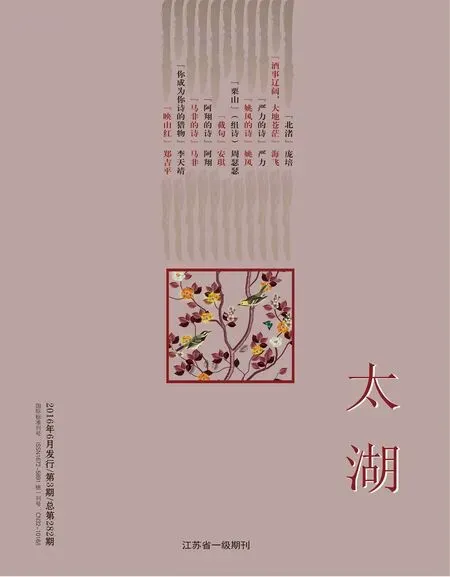回望塔山
2016-11-26周其伦
周其伦
回望塔山
周其伦
果然此地绝风尘,几欲相求已暮春。
竹里遗孙摇凤尾,溪边小浪织龙鳞。
到来恰见如珪月,坐久浑忘卖药人。
却忆当年杜陵老,寒山无伴语津津。
这是一首不算太古的古诗,诗歌的名字叫《溉澜溪访友》,作者是清代诗人程衡 (字公权,重庆市江津人)。诗歌的创作背景,我们现在已经无从考证,唯一能够知道的是,这是诗人在很偶然地游历了一次我的家乡溉澜溪后,留下的如许赞美。
我最早读到这首诗还是在25年前。那年为了修地方志,我们特地出差去了位于两路镇的江北县档案馆查询资料。在那本印刷粗糙,书页已经发黄的 《江北厅志》上,我读到了这首关乎我家乡的诗歌,兴奋之情顿时溢于言表。前不久,我参加了江北作家走进寸滩活动,猛然间又触动了我对这首诗歌难以抑制的怀想。回到家后,我又兴味盎然地翻阅了姜孝德先生精心编撰的 《江北区历代文学作品选》,在这本装帧大气到无以复加、资料浩繁到宽广深厚的县区级文学 “大书”中,又读到了这首曾经让我以意情牵的诗作,这就让我觉得有话可说了。
客观地说,我的生长地溉澜溪不算名胜古迹,也不是特别有那种温润色彩的小镇。我们上面读到的这首诗,几乎就是目前我们唯一能够拿得上台面来的文学作品,这让我在兴奋之余又有些不甘。对此,我还专门向现任的江北区作协主席,被称为江北区文学史档案活化石,当然也是好朋友的姜孝德询问,平时一谈起同类话题,常常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到刹不住车的他,对此也有些默然。据他的研究得知,现在流传于世间的,也只有这首咏叹溉澜溪的诗歌,他说他也特别喜爱诗里意蕴中饱含着的那样一种质朴的纯美。专家如是说,我们权且如是听了。
位于重庆市江北区的溉澜溪,是一个有溪流、有山峦、还有文峰古塔的小镇,“溉澜溪”既是街区的名字,也是那条横贯小街曲曲折折流向长江的溪流的名称。溪水是从邻近的渝北区 (以前叫江北县)流过来,远远看去,若隐若现的溪水高高低低潺潺流淌,但它具体源自哪里,我们无从知晓,只是看着它逢山开路曲折迂回而来,流经此处便与闲适地居住在小镇上的人们短暂地亲热一番,就义无返顾地扑向山脚下那一日千里的长江。
“溉澜溪”这名字不论是地名抑或是水流名称,都显得独特。这三个字都沾水,而且都是偏正组字的左偏旁沾水,我对地名考究不多,对文字学也荒疏得很,仅就我现今所积累的知识来看,像有这种特点的地名或者是溪名,即便是在全国也不多见。据说一开始人们把这里叫做灌篮溪,因为灌和溉同义,而 “溉”读起来似乎更为朗朗上口,因此古人就把它改为了溉澜溪。街道傍水而设,溪水顺街而淌,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无缘无故就多了几分惬意。
溉澜溪旁边有座不高的山峦,山峦上有建于清道光年间的文峰塔,当地人大多叫这座山为塔子山。俗话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这座矗立在长江北岸的古塔,这里的历史文化传承才开始闪耀着片片光泽了。说起这文峰塔的年代,算不上久远,但因为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刚好位于长江的寸滩至朝天门这两个水码头的江岸线上,所以从水系的角度看,就有了非常独特的韵味。
我读过一篇文章,记不住篇名了,说的是早年间从远方乘坐渡船回渝的游子,当船舶慢悠悠舒缓缓地逆江水而上,过了寸滩就望得见文峰塔了,而远方归来的游子一望到此塔,那就意味着回到家了,就可以大起胆子去怀想父母的期盼和妻儿的温暖;假如人们从朝天门顺流而下出外闯荡,一过寸滩,文峰塔就立马会消失于人们的视野之外,好多铁骨铮铮的男儿此时都会心里发酸,有的还禁不住掩面唏嘘。如此说来,这座古塔倒还真不是摆设,至少让我们觉得它有那么一点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意思,这也为溉澜溪这个质朴的小镇平添了万般风情。我的这篇文章围绕着溉澜溪街区、溉澜溪流水和塔子山这样一路走来,似乎就有了一种悠远清越的人生况味。
从前这里是一个颇为恣意的微型水陆货物集散场镇,我们现在肯定是很难去考证这个场镇的具体兴起时间,但它的日益衰微我是亲眼见到的,不过那是一种非常缓慢的时光流连,几乎伴随了我的大半生。
广义的溉澜溪街道应该说地域是相当广阔的,就城市居民这个层面来讲,它可以从江北嘴旁边的青草坝铺展到茅溪、寸滩、黑石子,洋洋十余公里,人口也就是两三万的样子。而在这几个城镇居民点的周遭又 “农村包围城市”般地密布着几万寸滩乡以种蔬菜为生计的农民。当年的溉澜溪街道和寸滩乡两个基层政权的管辖范围呈现出犬牙交错的状态,这是非常独特的,当然这也为今天的执政者把这里统一为寸滩街道奠定了地名沿革意义上的基础。
据我目前尚且健在的哥哥姐姐们讲,我的实际出生地还不在溉澜溪,那时我们家还住在溉澜溪最下端的黑石子朝阳河,大约是我两三岁的时候,我大哥被招工到了位于青草坝的四川省重庆船厂,船厂在溉澜溪有面积不算太小的家属院区,我父母都是纯粹的城市居民,也没有正式的工作单位,无从分得住房,等我大哥一转正分到了住房,我们一大家子就呼天抢地地尾随着已经成为公家人的大哥,搬到了溉澜溪塔子山下的五零八村。从此我就开始与这个小街,和塔子山,和这条溪流有了亲密到几十年不离不弃、欲说还休、欲罢不能的零距离接触。
以前生活在溉澜溪的人有两大乐趣,绝对是今天的人们,尤其是今天的年轻人根本无法体味到的。当年我们可以很舒爽地登上不高的塔山,“欲穷千里目”地眺望无尽的远山近水,“离散两依依”地饱览身边的桃红柳绿;我们还可以在漫长的长江沙滩上抑或是江水退却后裸露出来的石滩上玩水嬉戏。爬山和观水相比较,我个人是不太喜好去江边玩水的,直到现在我都常常暗自纳闷,从小就生活在长江边,为何我却成了极个别不会游泳的人呢?
登塔山是我的乐趣,有时候呼朋唤友,有时候也独自徘徊。高兴了还会钻进塔楼,透过塔楼窗户往外打望。那时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奢求,也就是把这种玩耍当作娱乐,这与我后来做了街道文化站干部去考古和再后来的文学写作无关。站在山顶,连天接地的长江从脚下流过,江面上永远都是上上下下穿梭不息的大小船舶,偶尔还听得到一两次突然鸣响的汽笛声,徜徉之余兀地会心下一惊,竟也乐得自在,我的这个喜好几乎延续到现在。
即便后来我每次外出,都会更多地选择爬山。来到一风光绝佳处,最愿意去的地方,也是观摩那山峦顶端大小不一、风姿各异的古塔庙观。我和许许多多的考证癖或者是求神拜佛者有些差异,我更在意这种身心的 “抵达”,这种亲眼观摩亲耳聆听,我甚至很少在这些地方去摄影以作留念,我觉得人到这里了,心也就到了,我的这种固执的 “抵达”感觉和 “到过”的心理,让我在失去了很多很多的同时,也实实在在地得到了很多很多。
溉澜溪街面由一条条完全不规则的长条石铺就,它从高高的半坡上扑面而下直抵长江。上接古代的驿站头塘,下连当年可以假通商之利的船运码头石垭子青草坝。我们已经从程衡的 《溉澜溪访友》里,感受到了人们与溪水的密切亲和关联。有人说 “溉澜溪”流了那么远,你咋就敢肯定他说的就是现在的溉澜溪呢,我注意到诗句中有浪花的描写还有古石桥的神韵,而我的家乡溉澜溪就与此有着很多相通的意蕴,比如朝阳桥的霸气,偃月桥的委婉,再往下数还有茅溪桥的阳刚和至善桥的清丽,小桥流水绿树掩映,再加上塔子山上开阔旷达的视野,我以为当年的程衡没有理由不是在这里唱和的,而当年诗人游览时的溉澜溪,一定是一处妙不可言的好地方。
我的儿时,溉澜溪水留给我的记忆就是欢乐。
我记得溪流蜿蜒曲折,水源并不是很丰富,只有在夏天洪水泛滥时,溪水才会有放荡的咆哮。绝大多数时候,这里就是儿童们欢愉的天堂。我们在溪边捉迷藏,在溪水石头缝里掰螃蟹,还在水里嬉闹着打水仗。因为溪流不深,平时最多只能淹过大人的小腿肚,那个时候家家的娃儿都多,家长们 “抓革命,促生产”都搞不赢,一般都没有闲心来干涉我们在溪里玩耍。有一次我在溪里掰螃蟹,忘记了回家时间,天都黑了,才扑爬跟斗赶回去,被我的家人好一顿臭骂,还被罚抄写作业五遍。
这还算是轻的,记得还有一次就严重了。这条溪沟虽小,看着水也不深,不知何故,溪沟里也时常会隐藏着深浅不一的深水凼凼,有一次我就差点中招。远看着是一片离岸边不远的草笼,有几只青蛙在上面匍匐跳跃,心想可以捉回家用南瓜叶子包起烧来吃,再撒几颗盐味道一定鲜美无比。哪晓得我几脚窜过去,陷进了一个深坑里,溪水很快漫过我的腰杆,心一慌就手忙脚乱,用力反而感觉使不上劲,越陷越深,最后跌倒在溪水里大声呼救,手里还牢牢地抓着岸边的茅草。一个已经读高中的邻居不晓得从哪里找来块木板,才把我拖上岸来。这个记忆相当深刻,到现在我都能够回想起那天我父母的气急败坏,他们威胁我再敢下水就不给饭吃。我估计这也许就是造成后来我一直都不太亲水的性格的原因,也是家乡留在我内心深处的一道印痕。
我们家乡还有一个特别怪异的现象,从我记事起,溉澜溪就从未发生过一起火灾,连未遂的都没有。记得有一年我在街道工作,陪同区里来的领导去社区,领导告诫居民要注意防火,说这些居民点都不通公路,失火了连消防车都开不进来。我记得好几位老人家都抢着给我们说,溉澜溪这个地方从来没有失过火,还真是沾了这名字的光。“溉澜溪三个字都沾水,那火还燃得起来吗?”尽管他们言之凿凿,其理由也太牵强了,不足为凭,但就我的记忆来看,这里的确绝少有火患。这不用去考证,权且作为一个说法。
我还小的时候,是无从知道清代的程衡专门为家乡这溪水写过一首这么美丽的诗篇的,后来长大了,读到这首诗了,再回头去看那溪水,却渐渐地发现,我们已经很难寻觅得到那它潺潺的芳踪了。重庆人的天性就是伴水而生以水为乐的,居家休闲都与水有关联。所以这些年城市的壮大与发展,也为溉澜溪这块既可以乐山又可以乐水的地方注入了飞扬跃进的元素,海尔路的横贯东西,江北区政府迁居此地,为这里带来新的希望新的商机的同时,也让无数闻风而动的开发商心驰神往,各种品质的高档楼盘和鳞次栉比的别墅群,都以乐山亲水作为噱头看好这块地方。
目前仅在溉澜溪的就有保利观澜、万科微澜、都市美邻、瑞同优米四大高档楼盘,扩展到寸滩地区那就更加多了。这些高调宣称要给生活最自由的尺度,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意欲重新定义重庆城市生活范本的大楼盘,其气度品相闪耀和超拔的宣示,无疑为即将旧貌换新颜的溉澜溪带来更为亮丽的明天。
我们一行到寸滩采风,出面接待我们的是寸滩文化站的敬相安先生。他、我和姜孝德,我们三人曾经是在同一天被江北区文化局招聘为乡村文化站干部的,自然格外随便;以至于随便到敬相安非要在我们面前显摆一下他今天打理的寸滩综合文化站,号称这个文化站设施硬件一流,达到何其了得的地步。老实说,这些年我走南闯北,还是见了一些世面的,我开始想笑敬相安有点自恋,觉得不妥,硬是压下了我的念头;心想,你一个街道文化站再 “一流”,又能 “一流”到值得在我们面前炫耀吗?
一行人走进了寸滩街道港安三路附二楼月光丽苑小区里的寸滩综合文化站,这下倒令我一下子目瞪口呆了,这绝不是夸张。一个街道文化站,煌煌四五百平方米的面积,装修到如此绚丽的程度,确实让我很振奋。音乐舞蹈辅导室、讲座报告厅、能够在全市内通借通还的图书馆,棋牌室,初级健身机械和电脑查询系统,不由得让我一阵阵发蒙。想想当年我在这里做文化专职干部时,我们文化站的规模,也就仅仅限于有一张办公桌。这才过去二十多年吧,怎么就让我有了恍若隔世的感觉了呢?
时代的进步和城市的巨变,每天都在创造着我们过去难以想象的奇迹,这也是今天的江北区和今天的溉澜溪能够骄傲地崛起,能够在那些挑剔的财大气粗的开发商面前扬眉吐气的主要原因。我估计这些开发商恐怕不一定知道曾经有一位古代的诗人,为溉澜溪写过那样一首清丽纯美的赞美诗,如果他们知道了,会不会更加窃喜于自己的明智选择呢?这些看似不经意山水、不流连人文的开发商们,他们最先看重这里的,一定是 “溉澜溪”的秀丽和 “文峰塔”的婉约,这里不那么显山露水,却能够让每一个与它擦肩而过的人忘不掉,或许这就是文化的魅力吧。这也是一种品相,也是文化传承,开发商有理由把这里装点得更美,志得意满的敬相安也可以文化站的豪迈在我们面前显摆,今天的溉澜溪让我刮目相看。
回程汽车到了五里店,我回头望去,过去心中伟岸挺拔的文峰塔看上去很小很小,远远望过去,那塔子山已经和塔子山周围的那些建筑物接成了一片,显示出一种更为壮阔壮丽的景象。
周其伦,重庆市作协会员,现供职于 《重庆商报》。在国内报刊发表文学作品数十万字,小说、评论见诸于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文学报》、《北京文学》、《莽原》、《湖南文学》等多家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