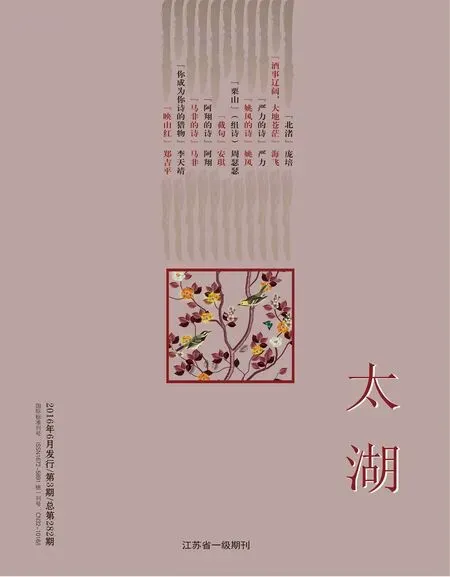策马执戈唱大风
——简析茂戈诗歌
2016-11-26史映红
史映红
策马执戈唱大风
——简析茂戈诗歌
史映红
写评论的人都知道,对作者和作品太陌生的话,往往不知从何下笔,相反,对作者和作品太熟悉的话,也不知从何入手。对于茂戈和他的诗歌来说,就属于第二种情况。先说作品,他的第一本诗集 《雪域兵谣》数年前我从西藏的一个文友那里讨要到了,时常翻阅,现在又得到他的诗集 《西藏在上》。如果说把他所有的诗当作一首歌的话,哨所、界碑、军旗、巡逻、钢枪、战士、演习等就是歌词;雪山、冰川、草原、河流、玛尼堆、经幡、玛吉阿米、仓央嘉措等藏地符号就是曲谱;南昌起义、抗战风云、长征艰险、乡土离愁、人生感悟等方面的吟诵就是主唱了。其次是对茂戈的熟悉,说是熟悉,既未谋面,更未深聊,似乎谈不上;说是不熟悉,又对他经历如数家珍:出生农村,十八当兵,由于工作勤奋踏实,军政素质过硬,组织推荐考军校;军校毕业后,主动申请进藏,既在基层带过兵,又在机关搞过宣传和文化工作。我又知道,无论那个岗位,在把工作任务完成的同时,夜深人静的时候,节假日、双休日和八小时以外,其他人打扑克、喝酒侃大山、外出之际,他忙里偷闲,在军营一隅,读书、看报、写作……在领导周围前呼后拥的队伍里没他,在削尖脑袋、用尽计谋要当官的竞争中没他,但时常在 《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西南军事文学》《文艺报》《诗歌月刊》《星星》等军内外六七十家报刊上有他。
今年五月初,我在他博客上留言:“请把已出版的诗集 《西藏在上》寄我一本,我会把拙作 《西藏,西藏》呈送”,没有多余的话,像一位多年交往的朋友。没过几天,就收到他快递来的 《西藏在上》和长篇小说 《雪葬》。这段时间一直在阅读他的诗,准备写个评论,因为我清楚,在近十年以来的西藏文坛,在诗歌创作方面,茂戈不能不写。
下面从五个方面对茂戈诗歌作简要赏析。
边关的颜色
把评论的第一部分定名为 “边关的颜色”是有原因的,祖国陆地边境线长达2.2万公里,在这漫长的第一道大门上,无论白天黑夜,无论刮风下雨,眼睛不停扫视的,是战士;双脚无数次丈量的,是战士;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石一砾,用手抚摸的,还是战士。战士是和平的守望者,是主权的捍卫者,是正义的象征者,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和平的颜色,是边关的颜色。作为戍边22年的老兵茂戈,作为一个从懵懵懂懂战士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老兵,他笔下很多次出现可亲可敬的战士,战士的喜怒哀乐,战士的摸爬滚打,都描写得生动活泼。来看 (《紫外线灼伤我的脸》):“紫外线灼伤我的脸/我发现我的脸皮/起了一层又一次/之后,一种叫高原红的颜色/皴裂地烙上我的脸∥紫外线灼伤我的脸/一如年深日久的化石/任高原风雪吹打/与我的迷彩服和黑色的钢枪/吹打成雪域中铁血的雕像∥紫外线灼伤我的脸/老兵们说,灼伤/是一种洗礼的过程/灼伤后绽放的高原红/是雪域中的荆棘之火”。一个个在父母精心呵护下的 “小皇帝”,一个个刚走出校门的学生娃,或者一个个不谙世事的社会青年,到一名合格的共和国战士,这个距离是显而易见的。要经过紧张、严格、甚至苛刻的综合军事训练,要经过诸多繁复的政治学习和教育,当然更要经过严格的考核,才能成为一名列兵。对于戍守雪域高原的战士,还有一点,必须适应严酷的高原生存环境。我刚入伍时,我的四川自贡籍班长黄柳生用川味十足的口音说 “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天上无飞鸟,四季穿棉袄”,这是西藏的真实写照。到部队的前三天,已有7人因为高原反应住进医院,黄班长又说:“这就是高原,你们现在申请回家还来得及,因为新兵训练期间允许退兵。”而当时我们驻地海拔还不到3600米,没有拉萨高,对西藏来说,这个海拔是相对偏低的,说明白些,就是西藏的 “宜居环境”。诗中的高原红是雪域高原给战士们的第一份馈赠。
接着看诗人笔下的战士 (《梦见李班长》):“那一年,西藏高原夏天的演习场/那一天的阳光伸手一抓就是一大把/现在想来,我仍觉得是那颗导弹/在出筒的刹那就被高原可怕的阳光灼伤了/像一位刚上高原的毛头小伙儿/摇晃几下一头栽在距你五米远的距离里/你迅速跳进掩体,等待爆炸……/十五分钟后,导弹没有爆炸/上级命令:引爆/导弹静静地躺在那里,像阴谋家一样/随时蓄谋着撕破高原的一次声响/你主动站出来,只一句 “我行”/大家就看到你坚毅而果断的目光∥当兵那些年,我第一次碰见生与死的抉择/当时,大片大片的阳光砸在地上/砸在你宽阔而厚实的肩膀/你带着雷管走向导弹,走向/你的战场”。茂戈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壮阔的画面,字里行间鼓荡着恢宏的气势、惊心动魄的情境:骄阳之下,演习场上,一枚导弹没有像预料的那样直刺苍穹,而是 “摇晃几下一头栽在距你五米远的距离”。众所周知,当下很多人都麻木了,满脑子除了金钱和无穷无尽的欲望,对什么都无所谓,往往也是这些人,炒菜时锅里溅起几滴油就手足无措;家里有一点点煤气味就如临大敌;偶尔的敲门声让他心跳加快。试想一下,一颗未能射出的巨大导弹躺在我们五米处,我们又是什么感受?当接到上级命令之后,李班长 “主动站出来,只一句 ‘我行’”,就 “带着雷管走向导弹,走向,你的战场”。把一名技术能手、一名优秀战士的果敢、自信、担当描写得淋漓尽致,让人印象深刻。
再欣赏 (《我从边防走过》):“——祖国,这里是西藏边防/我站在狂劲的边防风中念着这句话/体内骨骼开始铮铮作响∥从昆木加哨所到乃堆拉哨所/从塔克逊哨所到查果拉哨所/一路上,十八岁的高原红竞相绽放/我重新认知到他们站立的海拔高度∥走不出的边防线,走不出的喜马拉雅/老兵们深情地告诉我/雪是 ‘喜玛’,家乡是 ‘拉雅’/他们在这里种下了一路的太阳花∥请允许我执意走下去/像一朵雪花投入雪域的怀抱/为此,我决定这一生/把整个西藏比作我痴痴的爱人”。这是一首典型的边关诗,茂戈作为雪域高原的一名普通军人,没有刻意歌颂和任意拔高,而是用亲身经历、亲身感受来诉说雪山哨所的艰辛,守边战士的不易和巨大奉献,从平凡中发现艺术之美,在真真切切的体味中升华诗意和美感。自古以来,军旅诗总是贯穿着一股苍凉之美、阳刚之美,比如横槊赋诗的王昌龄的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比如沙场秋点兵的辛弃疾的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比如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的岳飞的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同样在茂戈作品里,我们读到了雪峰的高寒,剑光的凄冷,骨骼的坚硬,战士的忠诚。
定格的面孔
我与茂戈一样,在西藏高原服役20余年,青春和 “世界屋脊”产生了完美对接,在这说长也长说短也短的军旅岁月中,随着兵龄增加,对脚下这片高天厚土的了解也就多一些,不知不觉就感到肩上使命的沉重:1903年至1907年,英国侵略者从亚东等地入侵西藏诸多地区,他们凭先进武器,一路烧杀掠抢,西藏地方政府派兵抵挡,在曲米辛果隘口,侵略者诱骗藏军谈判,待藏军放下武器时,英军突发猛击,700多名藏军顷刻牺牲。在宗山保卫战中,侵略者攻城近三个月,后因山上军火库不慎爆炸,弹尽粮绝,加之侵略者猛烈进攻,宗山失陷,军民大部分牺牲,少部分跳下悬崖,无一人投降。后藏门户失守,不久拉萨失陷,数个不平等条约签订。1962年下半年,印度军队不顾我国多次警告,悍然从东线、西线入侵,我新疆、西藏驻军被迫还击,痛击印军。但双方争议领土仍有约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浙江省,或者两个半台湾省面积。据不完全统计,数十年来,我驻守西藏解放军,近2万官兵由于种种原因不幸牺牲。
走在这样一片土地,任何人都深有感触,茂戈多次写到这些牺牲的军人,想用文字定格他们的容颜,我只列举三人,其中一位是将军,他是西藏军区司令员张贵荣,来看 (《一条生命铸就的路》):“你衰弱的肌体/能完成几次痛苦的孕育∥你的体内,涌动一种骚动/倚靠一个永恒的无雪的日子/你走向你永无止境的行程/确切地说,你是要爬上山巅/沿着脚下这条路,走向/另一条路/尽管你50年的身躯/压得大山颤抖∥伸手的瞬间,你/碰痛了一块青石岩/你扶着青石岩伸向前方的手/永恒地,昭示你生命中路的/方向和力量∥你用倒下的身躯,为这条路/铺就一段铁血的路基/这就是你滚烫的墓志铭/这就是你石化的骨头/20年后,200年后/你的血拍打路基的声音/在高原祥和的风雪中,仍会止不住/激情,昂扬”。张贵荣司令员1984年在勘探国防公路途中,因高原缺氧,长时间劳累引起心脏病复发去世。广袤的西藏,特别是当时的西藏,有多少以藏族为主的各族群众生活水平亟待提高,发展缓慢的西藏经济亟待插上腾飞的翅膀,特别是国防,雪峰林立,山高水长,很多边防哨所给养基本上是马驮牛拉,战士肩扛手提,制约这一切一切的,是路。将军心里比谁都清楚,他要修路,他要把尽可能多的边防哨所用路连起来,与拉萨连起来,与北京连起来,却不幸倒在勘探的路上。我常常这样想,青藏铁路通了,拉日铁路通了,拉林高速通了,就连 “高原孤岛”中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县墨脱也通公路了,如果戎马倥偬的张将军活着,该有多么欣慰。
再来看一位普通的军官吴敬泉 (《你生命的爱系于一种高度》):“5000米的高度/雄鹰飞不过/生物学家 “生命禁区”的学说/骡马和牦牛,被5000米/嚼成一堆尸骨/军用汽车和直升机,被5000米/咬成一堆废铁/只有背枪的你,20年如一日/在爱激起的风雪中/融化,上升∥你铁血的身子,用爱的豪迈/盛下7200个日头/盛下7200场冰雹和雪/你 “用特殊的材料制成”/你和你的爱,都交给了/ 5000米的风/5000米的雪/5000米的岩壁/ 5000米的哨所/你的身后/雪莲花在盛开美丽∥离开高原,500米的高度/怎能托起你的爱/你最终不可避免地睡在平原/弥留之际,你告诉平原上的爱人/说你真正的爱人是高原/还坦荡地说出当初的/相约和誓言”。一边是海拔500米的成都,被誉为 “天府之国”,一边是海拔超过5000米的雪山哨卡,吴敬泉营长舍小家为大家,在这里一干就是20年,患上严重的高原心脏病,转业回成都不到半年,病情复发去世。一个人的信念到底有多坚定?一个人对边疆的爱到底有多真诚?无数边防军人半个多世纪用行动在证明,用意志在诉说,但更多的人默默无闻,一些军人牺牲后由于条件所限,遗骨无存。茂戈用平铺直叙的方式,用看似波澜不惊的语句,却载涌着浓浓的感情,句句带血,字字含泪,疏朗有致,给读者一种震撼,一种痛惜,一个敬意。
另一个是战士彭洪奎,茂戈在 《雪中,用生命丈量信念》中写到:“倒下了,三天三夜的行程/你绝不甘心倒在距哨所十公里的路上/爬,你也要爬回去/你把意念托付给你的手/在雪地,拖出一条/长长的路/此时,你的目光穿透雪雾/你难道看见哨所的战友/在雪中等你归来的期盼/你的耳旁是不是还响着未婚妻/喃喃述别的馨香∥那场罕见的大雪,注定了/你一米八几的身躯要倒在雪中/在一个士兵至高无上的职责面前/你用双脚/在弥漫雪域丈量你的信念/你的信念高于生命/发现你时,你的手仍坚定地/伸向哨所的方向”。在广袤的西藏,有很多座军营,每天都有很多很多官兵出差、学习、演习、休假,他们一离开军营,总会把一个叫 “军纪”的东西带在身上,彭洪奎就是这样一个兵。1993年4月探亲归队途中,遭遇暴风雪,造成大雪封山无法通车,为按时归队,他依然冲进狂躁的暴风雪的世界,从世界第一高镇——帕里镇 (海拔约4300米)向更高的查果拉哨所 (海拔约5300米)迈进,倒在离哨所不到十公里的路上,牺牲时头朝哨所的方向。在当下,很多人没有信仰、没有敬畏、更没有悲悯之心,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有的是没完没了的欲望,当官了,还盯着更大的官,赚钱了,想着赚更多的钱,在名利场上,六亲不认者有之,父子成仇者有之,过河拆桥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有之;心里装着国法党纪、装着师长家长教诲的到底有多少人?记得在2015年9月2日,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习主席向30名抗战老兵颁发 “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时强调:“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真可谓“思焉而得,故其言深,感言而得,故其言切”。
历史的回音
茂戈的诗作,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再现历史,把我党我军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压迫的漫长斗争中的一些故事,一些人物,一些足以改变历史的大事写出来,那段荡气回肠的岁月就呈现了,那些惨绝人寰的暴行就还原了,那些不忍去看、不忍去揭的伤痕就出现了,那些为了民族大义英勇献身的先烈就有音容笑貌了。大家都知道,在日新月异的今天,在媒介极度发达的今天,不难发现,网络、影视上到处充满了奢靡享受的画面,一些下三滥的这样或那样的明星从恋爱、到多角恋、到怀孕生子、跟谁生、甚至生三个四个的消息总有人乐此不疲地关注和报道;很多电视节目玩穿越,颠倒黑白,丑化英雄模范人物;很多电视频道持续播放 “天天美食”和 “舌尖上的中国”的时候,军旅诗人茂戈的作品无疑让人眼前一亮。
让我们一起回望那段国破家亡、任人宰割的岁月的诗作 (《南京大屠杀 77周年祭》):“七十七年前,准确地说/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在第一场雪还没到来之前/寂冷的太阳,与30万无辜的生命/展开一场腥红的角力∥我白发苍苍的爷爷奶奶,罪恶的子弹/射穿他们一辈子都忠厚老实的身体/我朴实而善良的父母,没有躲过/一层一层从土地上犁过的炮弹/我娇小而可爱的妹妹,赤裸裸地/被奸杀在那群疯狂的淫笑里/我那只会哭泣的孩子,恐怖地/被挑在一把刺刀的疯狂之上/我呢——也被鬼子们绑着/我早就不奢望还能活着!那一刻/屠刀可以砍掉我的头颅/却永远也砍不掉我——我们的仇恨∥六个星期,短短四十多天/30万白骨堆积的历史/比黑夜更黑,比深渊更深∥面对屠杀,面对灾难/这一辈子,我执意选择从军∥……今天,我流下诗人的泪水/伴随七十七年来的自我祭典/安慰一首诗歌的诞生”。读这首诗,我首先读出了凄惶,仅仅过去77年,很多人,很多年轻人甚至不知道抗日战争,不知道南京大屠杀,不知道卢沟桥事变,我们教育的失败到了何种地步?读这首诗,我读到了愤慨,就在当初日本鬼子屠杀的重灾区大连、上海等地,一些人竟然邀请日本AV女优堂而皇之进行性表演;读这首诗,我读到了仇恨,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咬碎钢牙的仇恨;读这首诗,我读到了疼痛,是对积贫积弱之国任人宰割的无奈;读这首诗,我读到了沉,感到作为一名军人手中钢枪的分量,重如山,沉如山。诗人时而尽情想象、天马行空,时而不温不火,娓娓道来,强忍泪水,几度哽咽,像一位大屠杀的见证者,让人印象深刻,过目不忘。
再看同样写历史的诗作 (《追寻长征》):“沿着那条被红军踩出的路/我在寻找七十年前的那片红色∥我首先寻找的是那面红色的旗/我一直感叹旗凝聚的力量/召引着一群头顶红五星的战士/在饥饿与寒冷以及炮火的边缘/义无反顾/与死神打着游击战∥我听说那面的小土包上/栖息过一群很漂亮的女战士/有一位红色的孩子/诞生在她们温暖的怀抱/还有那片向阳的坡地/有七名红军的鲜血染红了半边天∥那片沼泽也七十年了/水纹起伏着历史苍老的情节/我无法从野草旁边/找到一只草鞋,更无法/沉默在小战士牺牲后/仍坚定指着的方向里∥我追寻长征,继续长征/我想知道:我的017600号手枪/曾留有哪位长征战士的体温/是哪位长征首长传给我的/坚硬而红色的铁”。这首诗,诗人把可载入史册的历史事件,没有刻意拔高,也没有用豪健旷达的词语来吐纳风云,反而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以一个长征将士后人的身份,慢慢追忆,边走边看边思考,“沿着那条被红军踩出的路,我在寻找七十年前的那片红色”;“我听说那面的小土包上,栖息过一群很漂亮的女战士”,作者不伪造,不矫饰,看似无憎无爱、无喜无悲,却营造了作为后来者对先辈浓浓的情感和敬重,质朴自然,直抒胸臆,反而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感染力。
接着欣赏写历史的诗作,诗人没有按常规出牌,而是以梦的方式入手 (《梦回南昌起义》):“那一夜,我听到了/周恩来与贺龙两位伟人的对话/吹响了冲锋的号角/那一夜,我看到了/一群热血男儿,在夜的静谧中/积蓄呐喊的力量/那一夜,我知道了/有一场翻天覆云的壮举/将在八月一日黎明前的黑暗里/用血的热度,洗礼革命的/镰刀、斧头∥中弹的瞬间,我的血/喷洒而出,立即/染红天边最初的那朵朝霞∥我露出欣慰的笑容/黑夜……黑夜/正被透明渐渐消溶/又一颗子弹击中了我,我使劲/将军旗插牢在南昌城门∥我不倒。我努力/以站着的姿势牺牲”。茂戈在作品里运用了形象、排比、拟人等修辞手法,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把南昌起义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描写得如闻其声,如见其境;运筹策划时的高度紧张,枪林弹雨中奋不顾身的冲锋,炮火连天中震天的呐喊,残破但又顽强挥舞着的军旗,让我们又听到了历史的跫音。真正明白了为什么近百年之后,那一夜诞生的人民军队,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直至现在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道理。
天上的西藏
茂戈从军22年,在西藏服役15年,这15年,是一个人心性相对成熟的时段,西藏的雪山、冰川、湖泊、寺庙、经幡、玛尼堆;高原以藏族为主的各族人民虔诚的宗教信仰、奇特的风俗习惯,厚重璀璨的传统民族文化、敬天悯人的宽广胸襟,都给诗人巨大的影响和心灵上的震荡,现在,就在我的案头,放着他的三本书:《雪域兵谣》《西藏在上》《雪葬》,从三本书的命名上,就能看到高原的元素;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他的很多作品标题都有青藏的元素,比如《雪莲花》《玛吉阿米》《雪花的表白》《雪花飘飞》《放飞一朵雪花》《倾听雪域》《雪山的秘密》……不管他承不承认,西藏已经融入他的血液。我们先来赏析诗人写西藏的水 (《坐看雅江》):“我在河岸看雅江/雅江在历史里看我∥好一条英勇之江/敢在云霄里奔腾/敢在寒冰与寂孤中/傲然穿行/赋雪山以活泼/赋岁月以血性/ (藏人说,我们的体内奔腾着雅江潮声)∥雅江之上,是一年四季/冻僵了的山/其实,高原里的故事/是雪冻不僵的/许多感人的故事/都在雅江的浪花里跳跃/ (藏人说,雅江的每一朵浪花里都孕藏着一个动人的传说)∥大峡谷是雅江隐居在历史深处/雄浑激情的千古绝唱/像一位高傲绝色的少女/只等她的英雄来找她/(藏人说,你听雅江日夜不息地唱着 《格萨尔王》)”。这条天上的大河,这条云中的大河,这条在西藏境内长达2057公里的大河,数千年前藏族先民就繁衍生息于河的两岸,并创造出了绚丽灿烂的藏民族文化。诗人没有写雅江巨大的峡谷,没有写惊天巨浪,没有写吼声如雷,也没有写峰回路转,却以轻盈的笔调,婉约的氛围,写出了雅江在西藏各族人民心目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看了诗人写水,再看他写山 (《西藏归去不看山》):“千万年前,它们不经意的崛起/提升了祖国在世界的高度/这个意境告诉我:平均海拔4200米/种下诗歌,长成云彩∥到哪里?再去找这种传奇的山/猕猴与魔女,是它们创写的神话/它们挺起这个民族的脊梁/浑身流淌的血性/沸腾喜马拉雅∥到哪里?再去找这种雄壮的山/耸立,是它们在岁月的灵魂/它们对谁都不低头/而明天的雪花/会摸到它们的心跳∥到哪里?再去找这种神圣的山/纯雪素身,是它们超凡脱俗的姿态/这个世界最亮丽的太阳/每天由它们托捧而出/引来一群神鸟的翅膀∥到哪里?再去找这种高远的山/白云,是它们放飞的梦想/它们也随着梦想在飞/那一朵白云正飘向远方/那一朵白云正抵达天堂∥西藏归去不看山。归去/一马平川”。很难说西藏的山属于天空还是大地,也分不清西藏的群峰起点在哪?终点又在哪?西藏的山,是一个民族的图腾,是中华民族的骨骼,它支撑着星云,它紧握着太阳。我不止一次去各地旅游采风,一些地方称作 “山”的东西,其实就是微微凸起的土包,如果有一把足够大的铁锨,几锨就铲平了。每每此时我就想,这里的人们好可怜,把土块当山,竟然当了很多年,真应该去西藏看山。茂戈在诗中,一口气写下了 “传奇的山,雄壮的山,圣洁的山,高远的山”,最后一句尤其精彩:“西藏归去不看山。归去,一马平川”。精彩到任性,精彩到许多人不服,却又不得不服。
温暖的家乡
与很多远离家乡的人一样,与很多漂泊的游子一样,茂戈在两本诗集中,多次写到故乡,写到父母,写到老婆孩子,这让我们看到了作为军人的他柔情的一面,自古以来,没有国,哪有家?一个正常的人,肯定既爱家,也爱国,一个不爱家的人,说他爱国,那是扯淡;同样一个不爱国的人,说他爱家,也是痴人说梦。来看茂戈笔下的亲人 (《给妈妈》):“妈妈,儿当兵/到很高很高的地方/儿伸手/可以摸到妈妈望见的月亮∥妈妈,儿可以/描述这燃烧的一切/雪飘飞的日子/那是高原血液的澎湃/妈妈,儿用流着血的身体/认真地靠近每一场雪/以及,风雪中/迎风盛开的雪莲花/因此,妈妈/儿脸上盛开的高原红/在守着高原的日子里/是种安宁与幸福/令儿的追求/更为热烈与忠诚∥妈妈,儿当兵到很高很高的地方/每日的平凡依然,内心/飘荡着火焰一样的旗帜/那是因为,我总是/想着您念着您嗬,妈妈”。时而滚烫,时而沉重,时而揪心,用“月亮、雪花、旗帜、忠诚、安宁、幸福”等词语,用 “妈妈,儿当兵到很高很高的地方”,“妈妈,儿可以描述这燃烧的一切”,“妈妈,儿用流着血的身体,认真地靠近每一场雪”,层层推进,步步为营,母子隔空对话,满含深情,铿锵有力,我们听到茂戈泪水与笔尖落地的轰鸣,我们看到炊烟与雪花相互碰撞,相互交织……
再看一首同样感人至深的作品 (《老婆来信》):“老婆来信,很准时/一周一封∥开端提起一件惊喜的事:她/这次西藏探亲后/终于有了我们的孩子/老婆说,她希望/我们今后的孩子/只要不跟我一样黑就好∥紧接着,老婆说/是沉痛的笔调:父亲的关节炎重得厉害/我的泪水滴在信纸的 ‘父亲’上/父亲是继承了祖辈血液的老实农民/他对有我这个西藏军官儿子感到骄傲/老婆说,父亲不让/把他病重的消息告诉我∥信的最后一段提到,老婆每天/教完书,就看着/变幻的柳树想没出世的孩子/老婆说,她和没出世的孩子/都很挂念雪域高原的我/并给我一个甜甜的吻”。诗作中,“提起一件惊喜的事:她,这次西藏探亲后,终于有了我们的孩子”,“老婆说,是沉痛的笔调:父亲的关节炎重得厉害”,“老婆说,父亲不让把他病重的消息告诉我”。一位可亲可敬的军嫂就出现了,一位既照顾老人又忙于事业的女强人就出现了;一位淳朴老实、勤奋一生的父亲就出现了,一位文化不高却鼎力支持孩子保家卫国的长辈就出现了。整首诗没有高大上,没有风花雪月,没有矫揉造作。诗人从家长里短中、从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叙述中,让我们感受到了真实,感受到了妥帖,感受到了清风拂面般的温馨,感受到了赤脚走在海边沙滩上的细腻。
茂戈与我的经历基本上一样,他写的很多素材,其实我也写,我写的,他还写;给他写评论,其实对于我,是进行一次再学习、再创作,把他没有写到的,我用评论的方式补充上去。做这件事的时候,我总在兴奋之中,我明明知道诗歌、甚至文学在当下的诸多尴尬,但是对于一个真正热爱文字的人,社会如何看待,周围的人们如何看待,这些都并不重要,这也是他多年坚持的原因,也是我多年坚持的原因。现在,茂戈与我一样,刚刚自主择业,有了更多的时间思考和创作,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我们殷切期待着他更出色的作品。
史映红:笔名桑雪,藏名岗日罗布,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于甘肃庄浪县,九十年代入伍进藏,服役21年,已转业;居山西太原。在 《诗刊》《解放军报》《文艺报》等发表诗文950余篇 (首)。著有 《西藏,西藏》等诗集4部;曾就读于鲁迅文学院第十九届高研班。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