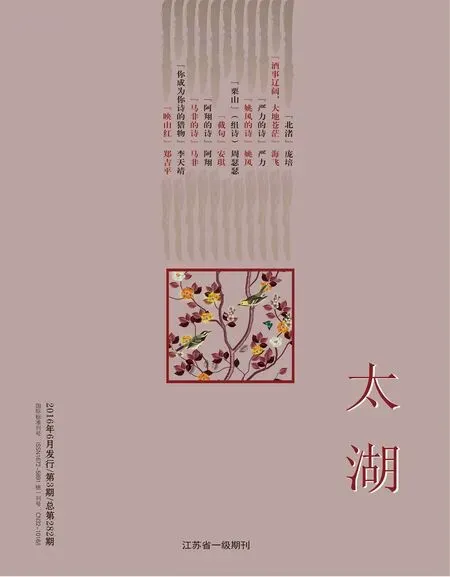惑·祸
2016-11-26竞舟
竞舟
惑·祸
竞舟
如同灯灭,世界突然退回到黑暗的奇点。
我在哪里?
钟表上指针慢下来,所有的运动轨迹都被拉长。飞溅到空气中的意识,以极慢的速度下沉,汇聚,重新进入我的身体。随同意识进入身体的,还有路面上数不清的灰尘,我甚至嗅到汽车轮胎与柏油路面摩擦时产生的焦糊味。
时间从上一秒向下一秒过渡时,在交界处颠簸了一下。
一切都还原成先前的样子。
行人、车辆,速度快得令人心惊,仿佛是在弥补刚才的停滞。凉悠悠的风从对面吹来,伴随呼呼的风声,空调挂机上绿豆大的灯亮着,家具显示出简单而模糊的轮廓。
我从生死临界点上退回来,身体和意识都像窗帘上的褶皱,越来越清晰。刚才那种弦断前的紧绷,原来是在梦里。我躺在床上,怎么会去杀人呢,又怎么会自杀。
但是刚才,梦醒之前,我是默认自己杀了人的。并且在极力掩饰。至于为什么杀人,过程是什么,还没来得及考虑清楚。
几个穿便服的年轻人涌到我家,询问一些简单的问题,比如我的地址,昨天在哪里,与某某人的关系怎样等等。我想起那句著名的台词:你可以保持沉默,否则你的每一句话将做为法庭证词。从他们之间的对话我知道,是在调查一起谋杀案。
这些人似乎太不专业了。据我从影视剧里面了解到的知识,他们首先应该是穿制服的,在提问之前,还应该出示自己的证件,否则我可以拒绝回答。不过,我与许多人一样,对所有声称执行公务的人,本能地怀着敬畏,还没有学会拒绝。我受的教育也告诉我,配合他们执行公务,是每个公民必须履行的义务。
退一步讲,据说他们在办案过程中,有充分理由穿便服。他们假装当事人或者证人,以便更接近事情真相。这种执行公务的方式,用在敌我矛盾中被称作卧底,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被称作钓鱼执法。我是个被调查对象,没有资格要求他们穿什么衣服。
那些人说,作案者是个女人。
至于为什么,我不敢问。在破案过程中使用什么样的逻辑,总有他们的道理,这些我不懂。我能做的,只是在配合他们调查的同时,保护一下自己而已。
可是,我真的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吗?
他们已经在几个可能的嫌疑人中,确定我的作案可能性最大。这种可能性是从逻辑上判断。谢天谢地,我还有机会。
那么,受害人是男人还是女人?一点想不起来。有一种遗忘被称作选择性遗忘,是指当事人受潜意识驱使,把一些无法承受或不愿面对的记忆屏蔽掉,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
我突然意识到,主动做出这些解释,其实是在默认那些没影子的推测。人们常说水到渠成。事实是,水到不一定就有渠,而渠成了必会有水。几个陌生人的突然造访,无异于在我心里扒开了深深的沟壑,思维正沿着这个沟壑,一泻千里。如果不想随波逐流,承认自己有罪,必须得把这个沟壑堵上。那就必须动用对抗性思维,告诉自己,是他们弄错了,这个混账世界使用的逻辑,全都错了。可这,可能吗?
我无法想象,是什么样的事情才会最终导致一个人走上杀人道路。财产,荣誉,或者一时的激愤?都有可能,又不全对。电视新闻里说,一个流浪汉,为了入室盗窃,有时候仅仅是一两百元钱,他可以接连用电击的方式杀人。近期新闻中又说,发生在美国电影院里的枪击案,作案人甚至什么也不为,只为模仿电影中的某个角色,那么多人就死在了他的枪口下。杀人,我原以为那是需要非凡激情的,堪比火山喷发或山洪暴发。但从警方提供的罪犯照片看,他们表情都很平静,甚至很温和。这是怎么回事?
看起来这个世界已经先我而崩溃了。
可怕的能量迅速在我体内聚集,就像地壳板块下的岩浆,随时有爆发的可能。我确定,那不是愤怒,而是完完全全的恐惧。
他们说除了我,暂时没发现别人有明确的作案动机。
也许他们是对的。连我自己都不相信这起案件会是别人干的。如果是别人干的,为什么我会有惊恐万状的感觉?我留意自己的一举一动,全都是在强作镇定。
我开始担心自己撑不了多久。心里素质这个词清晰地出现在脑海里,那是我的短板。但同时,我又侥幸自己到目前为止,表现得还算无懈可击,没有当着这些来路不明的陌生人,哇哇大哭起来,并承认自己就是案犯。
那些人走后,我把桌上的纸杯拿出去扔掉。
他们的手很脏,在纸杯壁上留下了清晰的指纹,令人生厌。是的,指纹。他们一定是循着这条线索找到我的。我一直以为,自己从未在这个世界上留下过任何痕迹,是个透明的可有可无的人。偏偏还会有人循着蛛丝马迹找过来,把他们充满敌意的目光投向我。
褐黄色茶水冲出纸杯,在空中划出闪亮的弧线,我从那道弧线上嗅到一股血腥味。又一阵莫名恐慌。这么说,人已经死了,流了很多血。通常情况下,流那么多血,一定是动脉血管被割断了。
在电动剃须刀流行之前,男人们普遍使用装有锋利刀片的机械剃须刀。那种刀片,我每次看到都有种不祥的预感,好像再看下去真会发生些什么。据说只要把头发放在上面轻轻吹口气,头发就断了。过去很多人都拿这种刀片自杀。自然,用这种刀片杀人一定也是很容易的。
要是对方反抗呢?像我这种胆小如鼠的人,只要别人一反抗,立刻吓得半死,然后落荒而逃。逃不掉的话,最后被杀的一定是我,而且是用我自己手上的刀片。
显然,这个人没有反抗。
茶叶和纸杯散落在坑坑洼洼的泥巴地上。烂泥地被弄得更加肮脏不堪,我想,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
所有事情都在按部就班地发生,而我却什么都不知道。真相被包裹在重重迷雾中,视觉,听觉,触觉,全部主动缴械。只有恐惧像泥石流,向我碾压过来。
又一个疑问升上心头。
那几个调查我的人,到底是不是警察?如果不是,他们只是物业保安人员来走访业主,或者派出所的人来查人口,我是不应该慌张的。也就是说,别人是不是警察,这是次要问题,我干了一件不该干的事情,这才是关键。否则他们何以嗅觉如此灵敏地认准了我,而不是其他嫌疑人?做贼心虚,这话一点没错。一心虚就会露出破绽。
不过,有时候也未必。据说有些案犯在杀人之后,居然能隐藏在人群中,泰然自若生活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想,他们的心脏一定是像机器一样强健和冰冷。从今以后,我也必须这样。
尽管很慌张,也从没想过主动伏法,我还是愿意活着。我想我能做到,只要不说出细节,他们就不能怎么样,这样我就能继续苟活于人世。
赎罪是必须的。是的,不顾一切。这是苟活之人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选择。
我承认从没有大张旗鼓去帮助过别人,除非从众,或者当面遇见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现在走到无路可走,也只好采用这种大开大合的方式,更深地介入生活,告诉大家,我在做好事,我用实际行动洗刷身上的血迹。我是多么不情愿这样,甚至看到别人赫然在镜头前做善事,就觉得深深的疲倦。无声无息活过这一世,才更符合我的心意。
不过,我也暗暗企盼,如果头上有神灵,做那么多善事,总该会获得一些良心上的安慰,要不,就让我遇到一些意外好了,以某种善终的形式结束自己。我从不祈求表扬,也不想逃避应承担的责任,只希望能体面摆脱罪恶感的纠缠,安安静静地离开,不要掀起轩然大波。
可惜这样的机会不是想有就有的。
我住的是一排平房中的一间。所有的门都朝向南面,门前有一条青砖铺成的小路。家家门前都用芦席、毛竹等物支出一块雨棚,雨棚延伸到路的那一边,邻居之间没有秘密。雨棚之外,以及平房的后面,都是无边的寂静和黑暗。平房像一只破舢板,漂浮在墨蓝的大海之中,一转身就可能再也找不到。
安全是暂时的,或者说,危险也是暂时的。
女邻居乳房硕大,怀里抱着一个小孩。烫过的披肩发使她的头部看上去几乎占据了身体比例的一半。我冲她笑,她目光淡淡的,绕道走开了。她的神情告诉我,大家已经知道我的事情。他们知道我正受到良心的谴责,并最终会受到法律制裁。
她把孩子留在门口。让一个孩子站在我面前,这是为什么?我将如何去面对一个孩子?
那孩子拖着鼻子,脏兮兮的小脸蛋像气球一样膨胀出来,把五官挤在缝隙里。他的眼神清澈,眼白发蓝。他东张西望,然后向我走来。他用手指着烂泥地和茶水杯同我说话,口齿不清。我不明白孩子在说什么,听上去像一段追问,或者指责。
我有种担心,警察会从这个孩子身上寻找突破口。比如问孩子,我在某天的某个时段,在不在家等等。孩子也许不理解,但他可以随意地点点头,或者摇摇头,那么所有的证据就都有了。接下来,警察只要审问我作案的具体细节就可以了。
细节。
是割腕,还是割喉?自然是割喉,一般割喉才是他杀,而自杀多半采用割腕的方式。但不管事实怎样,我是定不能承认的。我愿意用后半生赎罪,但万不能承认自己是杀人犯。这一点很重要。我不可以是杀人犯,这个身份远远超出了我的心理承受力。
可我究竟是怎么做的呢?
在警察到来之前,我得想想清楚。如果语无伦次,警察会更加穷追不舍,说不定还有更惨烈的情况发生,直到我的交代能让他们满意为止。他们代表权力,代表法律,那他们一定是对的。这是大多数人的思维定式。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困扰着我。
即使警方查不出来,我真的就能一直坦然活下去吗?会不会最终发疯而死?发疯会死吗?要是那样,我连发疯的权力都没有。因为那样,即使我不承认别人也会想到,我是因为承受不了恐惧和自责才死的。也就等于向世人宣布,这件可怕的事情是我做的,我是个可耻的罪犯,名字里带着永远洗不去的污点。
这是我到现在为止最不能接受的。对我来说,不明不白地死比不明不白地活更难以接受。活着,至少还有洗刷自己的机会。
又回到那个终极问题上,我为什么要杀人?
并没有什么忍无可忍的感觉,哪怕是被生活击打得遍体鳞伤,压得喘不过气来,也没有想过那是别人的错。只是有时候会想,命运何以偏偏对我如此紧追不舍,如果生活的轨迹不是这样,而是另外一种柳暗花明的境况,那该多好。这种想法每天都会在竞争激烈、气氛压抑紧张的环境里出现,何至于就会导致杀人事件发生呢。
空气变得越来越稀薄,时间分分秒秒地流逝,墙上的挂钟随时面临着停摆。我用越来越大的力气来保持心理的平衡与平静。
突然,毫无征兆地,我放弃了。突然,风轻云淡。
死也挺好的。不是吗?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还有什么可说的。我很累,太累了,不想再挣扎。于情于理,我都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也不想等着别人动手,还拖累他们挖空心思去寻找证据。真所谓一了百了。
一想到我竟如此迅速地摆脱了纠缠,那些人的脸上失落甚至恼怒的表情,我笑了。就像两个搏击运动员,刚上场,其中一个突然选择退赛,把另一个怀着必胜信心的赛手晾在赛场上。我让他们所有的工作显得可笑而毫无意义。这是我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叫太极。
久违的轻松。
无牵无挂的感觉真好,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是值得的。想起那句诗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直到今天,我才真正理解它,认同它。
重新打量破旧的平房,扁平的家具,觉得它们不再那么面目可憎,我会想念它们的,尽管它们很脏很阴沉。
有风从面颊上掠过,门吱吱呀呀地打开。外面一片漆黑。随时会有不速之客从黑暗中走出来,走进房间,向我宣告他们的新发现。
我梳洗打扮,换上干净衣服,走上乌烟瘴气的街头。车辆行人横冲直撞,呈现出奇特的生机勃勃。我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存在。
太阳低低悬挂在道路西头。金黄色的光线顺着道路一直铺过来,像一条温暖的地毯,一条通道,等待嘉宾入场。很快,我将与落日上方的夜晚一起降临。
站在路边,观察哪辆车速度比较快,车身比较重,这样不容易刹车。一定要看上去像是一个意外事故。我愿意偿命,但不愿背负杀人犯的丑陋名声,那比杀人本身更可怕更无法面对。我接受命运安排,但要体面,至少表面上是这样。这是我对这个世界,对我自己唯一的要求。
一辆大货车从闷黄色的落日里面冲出来,带着杀气,一路呼啸而来。它的速度和体量都让我满意。目测大货车到跟前的时刻,我向马路中央走去,像一个走向祭坛的人,我看见自己全身散发着一层淡淡的光晕。
大货车碾过的瞬间,我的身体像羽毛一样飘起来,意识也随之在四周腾起,又带着优美的韵律,先后落下,与身体重新凝聚,定型,散发出微光,微热。
我的手试着在身边摸索。指尖触到凉席的质感,尽管床有点硬,但可以肯定不是柏油马路。
窗外微弱的曙光穿透窗帘。那帘子与我白天看到的不太一样,更像是电影或者油画,层次、明暗都显出刻意的精致。我不愿睁开眼睛。半睡半醒之间,淡淡的悲哀传遍全身,我想哭。
刚才,为什么就那么肯定自己杀了人呢?
我这个惯于自责的人,却同时习惯于相信、顺从这个混乱和任性的世界。梦还不远,我记得清清楚楚,从头至尾没有一次反抗。像只羔羊,默默地、委屈地承受着,哪怕是我根本无法承受、不该承受的。曾子的母亲因有投杼之惑,后人觉得曾母对自己儿子信任不够。可不管怎样,对曾母来说,儿子毕竟是他者,她不可能了解他每时每刻的心理和行为。而现在,我却连自己都不相信,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会做什么,是怎样一个人。一个人既然不能为自己命名,那么世界将按照它的逻辑为你命名,而它的逻辑就是荒谬。
我告诉自己,应该立即醒过来,离开床,走出房间,彻底摆脱这个噩梦。可是夜那么静,深沉的舒适感,房间里均匀的呼吸声,都让这个决心显得同样荒谬。
身体的存在感越来越清晰,那是身体与环境相抵触所导致的觉醒。侧身时间太长了。我把身体放平,意外地,手臂打在一个硬物上。平整,冰凉。
这一发现都太奇怪了。床应该是放置在房间当中的,怎么会有墙?
窗外,天并没有比刚才更亮一点,也许窗外的光线不是来自晨曦,而是月光。我注意到,窗帘每隔十公分左右,暗影就格外清晰一些,像窗户栏杆。不会啊,我们家的窗户,什么时候装了栏杆?
我不能确定是又一个梦境,还是正面对一个更大的现实。抑或这就是世界本来的模样?也怪不得别人,每个人的处境都是自己协助他人构筑起来的。
左手顺着冰冷的平面,向头顶上摸去,触到铁质的坚硬棱角。我推测,还有一个上铺。摊平右手臂,手背挂在了床沿外。床大约一米多宽。这里倒是很像一座监狱。
浑身一激灵。我在哪?
浓稠的昏暗中,一个声音从房间某处传来,缓慢、疏松,仿佛从梦中逃逸出的一缕烟——
你以为呢?
竞舟 女,某杂志社编辑,中国作协会员,文学二级,发表小说、散文八十余万字。小说曾获江苏省首届期刊优秀作品奖、金陵文学奖等。现居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