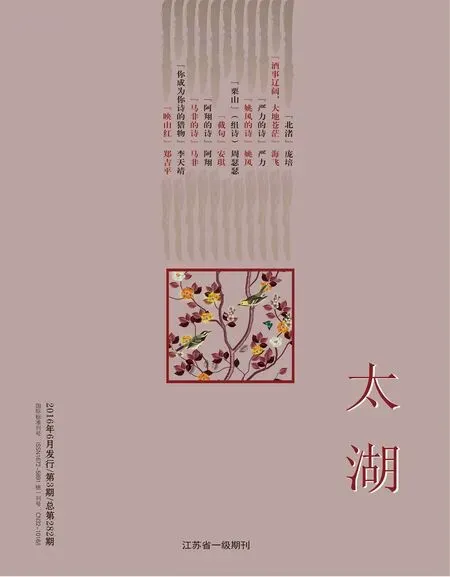石 碑 巷 (外一篇)
2016-11-26褚福海
褚福海
石碑巷(外一篇)
褚福海
故乡那条狭窄弯曲的巷子,一直铺陈在我记忆的显眼处,始终不曾黯淡,不曾消隐。那巷子叫石碑巷,横卧于故乡桃溪镇的东侧,宽仅丈余,长约百米,因地面均用宽厚的青石墓碑铺就,故此得名。
巷子两旁,清一色的二层砖木结构建筑,楼上住人,楼下开店,凸显清末民初风范,气度不凡。石碑巷里,商号林立,布幡飘曳,人声鼎沸。开设的店铺,除了有钱记布庄、彭家粮行、汪氏秤店、光明理发店、怡春浴室,还有发财园茶馆、地产竹器店、阿根南货店、一品香酒楼、尝尝看小笼包、哑巴馄饨铺、十里香烧饼油条店等等,愣是把整条巷子塞得满满当当,鼓鼓囊囊。
拂晓时分,星星尚在清辉遍洒的穹顶眨着眼睛,家住巷子两侧的人还神游于温柔梦乡,却时不时传来了 “轱辘轱辘”的声音。我知道,那是山农推着装满毛竹、松枝、茅柴等山货的独轮车轮碾压在石板上所发出的清晰摩擦声。间或还可听到农人挑着各式时令菜蔬担子有节律的 “吱呀吱呀”声。他们瞄准巷子两旁的空隙处,停车歇担,或蹲于街沿,或斜倚车边,各自忙碌着,做着开市的准备。石碑巷东端紧临桃溪河,湾兜里筑有个用大条石垒砌的石码头,宽敞,铮亮,不时有居民披着晨曦前来浣衣洗菜。铿锵的棒槌声,邻居间的攀谈声,奏响了山镇和谐曲,彻底扯破了黎明的宁静。水汽缭绕、晨色迷蒙的河湾里,渔舟云集,桅灯闪烁,渔民们正争先恐后地提着网兜木桶,有的或干脆捧上脚盆,将夜里捕获到的大鱼小虾、螺蛳蛤蜊拿上岸去交易。倏忽间,沉寂了一夜的石碑巷扭动了几下纤细的腰肢,揉了揉惺忪的睡眼,骨碌碌地醒来了。鳞次栉比的店堂里渐次亮起昏暗的灯光,一户紧挨一户的住家中忽闪出绰约的人影。没过多久,巷子里弥漫的油香味、水蒸气,轻飘慢浮;远处近旁此起彼落的吆喝声、讨价还价,以及烧饼店鼓风机的嗡嗡声,茶馆里壶杯碰擦的叮当声,不绝于耳,构成了山镇原始而赏心悦目的晨景。
我家就住在巷子东端的河埠畔,前门朝巷,后墙临河。每日清早我背着书包,踩着湿漉漉的石板去上学时,都会欣赏到这番生动有趣的景象。偶尔,甚或会傻傻地静默着伫立于一旁,看上一会儿热闹。桃溪镇虽不大,可石碑巷却是闹猛的,也是有灵气的,山镇人在安逸与恬静中循环往复着岁月,度过了一个个春夏又秋冬,我也在温馨庸常的日子里一天天拔节茁长。
石碑巷里的人家世代经商,故相对其他地方而言,家境普遍要宽裕殷实一些,肚子里的墨水略多一些,见识也更宽泛一些。不起眼的巷子里,倒是实实在在走出过三位四品官员,诞生了数位教授与两个海归。光环耀眼的石碑巷,着实让四邻八乡的人歆羡煞,众口一词地皆夸石碑巷是块精致玲珑的风水宝地。
我从小是听着石碑巷的韵律、嗅着石碑巷的气息长大的。抑或是 “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故,我素未觉得她有多么神奇,也没见她有何别样。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才彻底扭转了我对她的认知。那年黄梅天,天似乎被谁捅破了,没完没了地下着滂沱大雨,使三面环山的桃溪很快就被咆哮的洪水包围,顷刻间成了汪洋泽国。令人惊诧与大开眼界的是,竟然街上可划船,巷里能逮鱼,镇上居民家少有幸免进水受淹。而稀奇的是,唯独石碑巷人家毫发无损,安然无恙。事后,甚觉奇怪的我曾不解地问起过父亲,父亲呷了一小口酒,略显神秘地说,石碑巷是永远都淹不掉的,因为巷子的石板底下是架空了的,当初铺筑时设计者就考虑到了泄洪防汛。闻之,我心底惊叹,前辈们真是太有智慧、太具前瞻性了!从那一刻起,我便怀着敬畏的心情,注视起石碑巷来。
石碑巷人家的民风,就像山泉那般清澈,淳厚,简单,纯净,绝无自私狭隘的市侩气,彼此间和睦相处,有难时彼此帮扶。通常最易见的是,哪家包了馄饨,或是烧了红烧肉,哪怕是炒了一碗蚕豆,也总要拿上一些送给左邻右舍分享,用最古老朴拙的方式传递着暖意,延续着友情。夏日里,如若翻脸不认人的天公冷不丁来场雷阵雨,邻里晒在外面的衣物没人收时,总有菩萨心肠的阿婆笑哈哈地跑出去帮忙收回家,一件件整理好,待主人回来后,悉数送去。有一年深秋,天刚蒙蒙亮,勤快的刘阿婆拿着箥箕出门倒炉灰,颤颤巍巍挪动着的小脚,不经意间踢到了揉成团的手帕。弯腰捡起,打开一看,里面还有个小布袋,袋子里塞着一卷脏兮兮、软乎乎的毛票。质朴敦厚的刘阿婆心里寻思,这钱袋估计是哪位买卖人丢掉的,此时肯定焦急万分。于是,老人家手握钱袋,在熙来攘往的石碑巷里边走边柔声问,谁遗失了东西。刘阿婆差不多跑了大半条巷子,好不容易找到了满脸惶恐的失主,经核对无误后,愉悦地将带着体温的钱袋交还给了那个卖山芋的农村老妪。这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后来竟成了桃溪镇上街头巷尾争相传颂的话题,也成为石碑巷人最津津乐道与值得自豪的美谈。
石碑巷人的胸襟,如石板宽厚敦实,石碑巷人的良心,像山泉鲜活透明,石碑巷人的灵魂,似银月纯净透亮。我曾多次为自己是石碑巷的一员而自豪!长大后,我告别了朝夕相处的石碑巷,成了一个远离故土的游子。可家乡的变化与发展,无不触动着我的神经,牵动着我始终放不下的心!
去年阳春,我抽空回了一趟多年没回去的桃溪。车抵郊外,马路边原有的一座山丘与几家工厂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成排连片的新颖楼群。进入镇区,原先那杂乱低矮的街巷已销声匿迹,拔地而起的是整齐有序的崭新小区。目睹此景,我既喜亦忧,喜的是,家乡的面貌天翻地覆,日新月异;忧的是,那条四处烙满我身影的巷子如今可安在?
翌晨,我默然无语地独自踱步而去。让我喜出望外的是,我日夜惦记念想的石碑巷还在,且保护得堪称完整。随着城镇管理的加强和经营方式的转型,巷子里的店铺大多板门紧锁,人影稀疏,已难觅当年的繁华印迹,显现出乎意料的冷落萧瑟。但我想,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无须心存遗憾,毕竟,石碑巷还在。
石碑巷镌刻着历史的印记,已然嵌进我生命的缝隙,融为一体,无法抹去!
掏雀窝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桃溪镇上粮库的仓房里有堆积如山的粮食,场地上晒满了稻谷、麦子或各种豆类,丰盛的食物吸引着成群结队的麻雀来此觅食筑巢,因而粮库也成为我们这帮淘气鬼寻乐的园地。
粮仓高大,我们矮小,自然够不着,于是我们去围墙边找来长长的竹梯,“哼哧哼哧”扛至屋檐下满是鸟粪的位置,轻轻架好,蹑手蹑脚地快速爬上去,至能够掏得到的高度,利索地将手伸进雀窝,待到麻雀发现险情,为时已晚,只能乖乖束手待擒。麻雀在窝里乱作一团,有的边 “叽叽喳喳”边扑腾,有的甚至用尖嘴来猛啄你的手,但一切皆是徒劳,都成为我们的战利品。初夏的一天,我们一连掏了五六窝,逮到大小麻雀三十多只,四个人均分战果后,得意地回家去了。次日,当母亲把鲜美的清炖麻雀塞肉末端出锅时,一股浓郁的香气顷刻便在屋内弥漫开来,让家人在一饱口福之前先在嗅觉上得到了享受。
有一回,我掏到一只幼雀,嘴尖嫩黄嫩黄的,身上的羽毛尚未长全,有的部位裸露着皮肉,浑身毛绒绒、热乎乎的,煞是可爱。我小心翼翼地用手捧着,捂在胸前,到家后找来只纸盒,四周开了几个小孔,再垫上些棉絮,给它安好了窝。自从那幼雀进入我家后,我放学后便去捉青虫给它吃,实在捉不到虫子时,就给它喂饭粒。刚开始小家伙有些胆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拼命躲避我。久而久之,见我丝毫不曾伤害它,便逐渐放弃了戒备,慢慢跟我亲近起来。
看着它一天天长大,嘴尖由嫩黄变成浅灰,羽翼渐丰,我由衷地高兴,将它迁进鸟笼里,给它更舒适宽敞的空间。做完作业,我便抓紧工夫驯化它,用手托着它抛向空中,再接住,锻炼它的胆量与双翅;以口哨作号令,训练它的配合度与执行力。每次要反复训练上十来个回合。小家伙虽是一未成年的麻雀,但也鬼精鬼精的,偶尔还会装腔作势着学偷懒,不过,它那样只能吃饭粒。当然,它飞得起劲卖力,我肯定要奖赏它几只虫子,以示激励。
经过反复不断的调教驯化,那只幼雀长至三四个月时,就像信鸽一般能够独自飞翔了,而且令人称奇的是放飞出去竟认得回家。每每只要听见我逗引它的口哨声,立马停止玩耍动作,扭转头对着我凝视,判断我口令的含义,再作出恰当的回应。有时轻轻挪着碎步半信半疑地步行过来,有时急吼吼扑着翅膀灵巧地飞来,相当聪颖机敏,简直就像个听话的孩子,给我枯燥乏味的童年带来了铭刻于心的乐趣。
精心伺养到七八个月后,那麻雀基本成熟了,处于青春期的它食量倍增。时值盛夏的某日上午,我正埋头做着功课,母亲在忙着做饭,那麻雀便在家里自由活动,欢快地飞来飞去,扑腾着,玩乐着。当母亲朝着汤锅里倒豆腐时,不料被眼尖的小精灵瞟见,只听耳畔 “呼啦”一响,它迅疾飞扑过去,我和母亲猝不及防,眼睁睁看着它把一小块豆腐叼走了,飞至挂在半空的竹篮上,伸长脖子,眨巴着眼珠吞咽了下去。
这事唤醒了我木然沉睡的意识:它已具备了独立生存的技能,是该回归大自然的时候了!尽管有万般不舍,可我还是在那个闷热的夏日清晨,默默拎着鸟笼,独自来到郊外,毅然打开了那扇囚禁它许久的笼门。霎时,嗖的一声,它纸片般轻盈地飞向了碧蓝、辽阔的苍穹。凝眸它渐飞渐远的身影,心底蓦然滋生出些许欣慰,犹似清泉潺湲流过。
褚福海 中国散文诗作家协会常务理事,《散文选刊》、《海外文摘》签约作家,苏州市作家协会会员。已在 《人民日报》、《中国报告文学》、《北方文学》、《散文百家》、《鸭绿江》、《青年文学家》、《散文选刊》、《散文诗》等报刊发表150余篇。《小镇轶事》获“文华杯”全国短篇小说大赛三等奖,《大爱孝女》获2014中国散文年会奖,《四季素描》入选 《中国散文诗》2015卷,《童年趣事》获中华文学奖,并入选散文卷。出版散文集 《掬水闻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