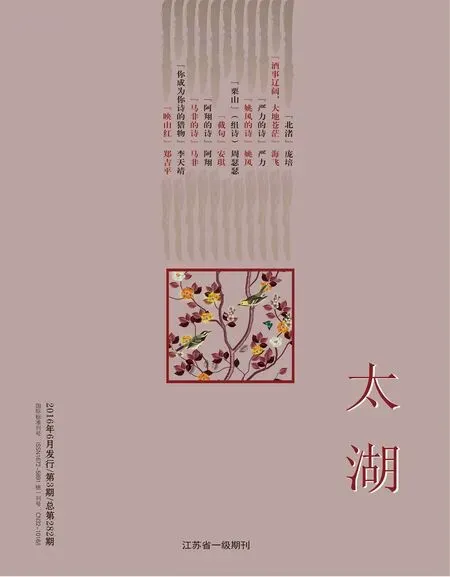北渚
2016-11-26庞培
庞培
北渚
庞培
1
镇上有一户出殡的人家,在暗黑的厅堂板壁前用长凳和门板隔起来,上面放了很多厨房用的菜肴。切碎的猪肚,整只煮熟的肝,蜷曲在盆子里的烧鸡和豆制品,百页 (千张)、菠菜、粉丝、笋片、黑木耳。我探头过去仔细看,还有炖烂泡热的蹄筋,像发白的鱼肚,也像煮熟后剥开的蛋白。
街巷的颜色,却没有这样刺眼,都是一式的高大砖墙,墙头排列陈年的瓮缸。墙头草遮没了门牌号。临街是一式店铺的排门,雨天的色泽被保留在青砖和麻石条铺设的弄堂各处。合作社木头铺面的门上仍画有巨大的向日葵图案。一行 “毛主席语录”的暗红色字样,像死去很久的人留在那儿的淤血。而向日葵的叶子是绿色的,一种非常稀奇,使人惊诧莫名的绿漆颜色。
有一家做塑料粒子的化工厂,仍有人做活计,都是四五十岁的妇人,系肮脏的围裙,一个由昔日大祠堂改建的厂房,只剩下家庭作坊式的角落还有些人气,其余的机器全都停掉了,蹲伏在房子的黑暗里,跟镇上街区的命运一样溺死着,锈烂、落魄。我循着那股刺鼻的化学塑料味,走进玻璃钢瓦盖顶的大院子。那些妇女们都围坐在机器旁一张临时搬来的工具箱边上吃夜饭。脸是绿色的。饭是各人从家里带来蒸热的,没有几样菜。有一盆大家一起喝的热汤。她们中间的一个人在做着殷勤的手势,示意身边的工友多喝点汤。没有人注视我这个贸然闯入者,在场的人大概把我当成了近年来云集到江南各乡镇的外地打工者中的一名。仿佛,我刚拣完垃圾,收拾完田地各处的矿泉水可乐瓶经过镇上 (此外再没有别的身份的外来者进入此类被遗弃的乡镇)。我不知道他们那餐夜饭,除了气味难闻的塑料味外,还能吃出别的什么味道。那整筐整筐的成品就堆放在她们的“饭桌”旁边。一种鸽子粪似的硬黑粒子,我不能够叫出它们的名字。
我原来想和她们闲聊,因为都在忙着吃饭,只好作罢。我把镇上的街道全都走完了,只有这一块地方,似乎可以找到人说说话。
画家梵高再世,一定可以画一幅 《塑料厂工人写生》这样色调阴郁的画作,像画他那幅1886年著名的 《食土豆者》。
有一个瘫痪在藤椅上的老太太,常年坐在房子靠街的窗户边上。那窗户是一个可以朝上掀起的老式活动窗板。老太太用一根拐杖柄顶住窗板缝,从那条细小的缝隙里默默无声地朝外张望——而她自己呆着的屋子,则是暗黑一片;所有的家具、蚊帐顶上,全积满了灰尘。老太太自己的样子,也仿佛是一团活动着的立体的灰尘——深埋在这一片荒芜的灰尘堆里——甚至包括她脸上的表情。我初次从她窗下经过时,没看见她的人,竟只注意到撑牢在窗板缝里,古藤制的那一根拐杖柄。我循着那团古色古香的东西往屋子里一看——老太太隔着墙,竟直接就坐在我的眼前……
窗外,又一个春天的节气,一个春光明媚的江南的早晨。从黄昏到第二天上午,我逗留在这破败的古镇上,仿佛一名四乡漂泊的寻梦者——也有可能,我要寻访的梦境,已经不大可能再有了。
两天前,蜜蜂嗡嗡嗡开始从蜂箱肚里,飞进刚开的油菜花田那一团团晕黄的花粉丛里去。从北渚镇清洌的小河畔,一只纯白的蝴蝶向我飞来,那是那年春天里我遇见的第一只蝴蝶。我在日记本上记录下这件事情。蝴蝶的翅膀纯白纯白,宛如一小片从水面上剥离的太阳光斑,一颗放大镜下的露珠,一只新造的浆。其娇媚的色泽介于初绽的梨花和新雪之间,不禁使我想起古诗里描写农家春天的篇章。
所有镇上的店铺、木头排门、板壁、房顶、房梁、暗黑肮脏的家具,包括田里的菜蔬,全都在一夜之间脱掉了身上的衣裳,像一个长久不落热水洗澡的人,开始进入其节日盛典般的沐浴。古镇生活的暗旧气息,藉着天地间万事万物在这一个季节苏醒的早晨悲喜交集的心情,像蒸气一样弥漫到了街巷和田野各处。但路上行人的鼻子眼睛,仿佛都在说,澡堂里里外外,脱下来旧的脏衣裳实在太多了!新的替换衬衣,倒没几件……几件像样的……;惟有镇头头上出殡的那户人家,拿出来的花圈是新的,崭新的纸花,在浩荡原野上吹来的缕缕暖风中,像河上的涟漪,像河上的白云,像老年人眼里的泪花,惊颤不已、簌簌发抖……
2
而穷的地方,水总是很清。
北渚镇上就有这么一片清清的河湾。
但是整个镇子现有的格局,却已倒坍败落,像一张翻倒在地大户人家旧式的八仙桌,一派萧条肃然的景象。犹如盲人的眼窝对外界的光亮没有反应,镇上的居民也对屋门口那条光亮的小河神情木然。昔日傍河而筑的江南市井,再也唤不回往年繁华的幻景。古诗里优游了千年的河中之洲,颓变成了田埂上一个病倒的老农姿式——甚至再也没有对孝道略知一二的亲人,能够把他从辛劳了一辈子而潦倒半生的稻柴捆边边上慢慢搀扶起来——吹来的田野浩荡的春风里,惟余他孤零零一个人,瘫坐其中。他的身底下是一个往昔四海通达的大河浜——河道在十米开外的平原上,已遭堵塞。镇上的房门一样朝南的河滩边,堆满了各式各样的生活垃圾,其中包括镇上的小工厂里倒出来的废品铁屑。整个大白天里,镇子的街道有时竟看不见一个仍安居在当地的年轻人,只有年纪大的老人,坐在光线暗旧的房门口,坐在某处被岁月熏黑了的马头墙底下;沐浴在早春阳光里的那一双双老眼睛,仍残余着一汪冬天的水——镇子的左右两侧不时游荡而过的全是外省来的小贩、季节性短工、拣垃圾者。陌生的眼瞳深处有一种迅速巡逡向四周乡里的无望的觊觎,犹如饥饿的秃鹫在荒原的风中围绕一名尸骨未寒者的耐心的盘旋。中国南部的拣垃圾者,近两年发明了又一种新式的形体语言,用丢弃的可口可乐瓶子作为走街穿巷搜索买卖的信号,而代表了昔日的小风铃或拨浪鼓形式——每天太阳一出来,一直到太阳落山,镇上人家空荡荡的侧厢和走廊过道、院子天井上空,就不时地回响起这种空可乐瓶子做的摇拨声音——一切都成了被遗弃者的可怕征兆和信号:不再通船的水域,人去楼空的商店,镇办企业或乡政府财政赤字,地势下陷的货运码头,老鼠们逃遁一空的镇属大粮库,花圈和寿衣店(生意呈平稳上升的趋势),拆空了的茶馆、祠堂、书场、老房子、影剧院。理发店内歪斜到一边去的铁制旋椅。养老院门前被漆成了绿色。昔日大街上伶俐而逗人喜爱的小黑狗变成了一只大肥狗,一只专拣垃圾为生的邋遢丧家犬(半个镇子以内,人们就听得它吭哧吭哧沿街走来的声音)。发了霉的阳光和河对岸那片田野……一枚家长们丢弃了的儿童口琴在其中呜呜吹响……
北渚镇的东首,有一座清代石拱桥,则是地道乾隆年间的老货色。长满荒草的桥背桥身,左右两侧的石头栏杆分别镶嵌有四枚工艺古朴精细的小石狮。那狮子的造型格外稚朴有趣、逗人眼亮。四只小狮子的头竟一式一样做成罕见的平顶。近乎四方形的狮子头上,不知有过多少路人的手掌因为油然而生的欢喜亲昵而把它们当成了悠长岁月遗留下来的活物。他们轻轻地将之抚摩。抚摩过它们的那些过路人的手掌都已在桥上桥下消逝不见;雕塑成宠物形状的四只石狮子那副伶俐可爱的憨态却至今犹在,在老桥的两侧傲然而活泼地蹲立,用它们的八只石头眼睛和四张呲笑的嘴巴,给邻近乡里的农人带来了多少年华似水的吉祥欢喜——给镇上的少女们带来蝴蝶翩飞的回眸一笑;给孩子们,老娘姨们,四方的手艺人带来一个往昔浩瀚年代的信物。雨天路滑,过路人还可以用手捏住桥栏上的石狮——只比人的拳头大一点点——一副憨厚气的硬头,以防脚底下滑倒。年复一年,这桥上的石狮石栏杆、石板心的八卦形图案,就成了这个古镇历史的匿名见证人。小石狮子的耳朵向着四面八方张开,在岁月的风雨中始终镇定自若,微微翕动——比一切古镇上活人们的耳朵都听得更多,更加真切管用……这四头石狮,好比一把名贵提琴上的签名,而这把提琴,已经衰老到了破损不堪、不能够再用的地步。琴盒、琴肚上的签名部分,却依然熠熠生辉。那制作这件工艺品的工匠的心血;那演奏者的精湛琴艺……在周围皲裂了的面板上嗡嗡作响……
桥的名字叫青龙桥——有一则过分华丽的相关故事,我在此省略掉 (江南乡间的古桥多有一二则大致相仿的故事传闻。一名中国人如若坐下来听它,多半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小时候曾在哪儿听讲过)?
与别处的古桥略略不同的是,北渚的青龙桥有一个向前跃起,蜿蜒着的弧度,非常优美,在造桥工艺上也非常神奇。也就是说,从桥的此岸这个点到达彼岸的那个点之间,桥砌筑的走向不是直线形的,而是在路人不易察觉、走过桥去的身背后,形成一个雨虹般的弯弧,宛如游走的龙蛇——故名 “青龙桥”。
桥面生满了苔藓。桥墩、桥侧垂挂着茂密的藤蔓。雨天里走过,晴天里憩息,桥面各处,都散发出一种古式古香的青石气息。整个桥身已不见其它文字 (铭刻在石梁石板上的,也早已被苔藓荒草湮没),惟独桥首两侧的石梁,不久前竟有当地好事者用红漆涂上 “雨天路滑、行人小心”八个蹩脚的文字——这青龙桥的衰老败落,可见一斑!
3
桥对过,是一排正念着唐宋古诗的岑寂的旧房子,是一式的曲尺形走向、旧式平房、薄的青砖地。露天的庭院和天井。十几个窗洞都已被砖石堵死的侧厢房,宛如春天寂寞的坟场。
那排房子,是昔日古镇的大粮库。运粮码头、晒场、打谷场的规模仍在,但整个场地已完全荒芜。
一年一度的荒草萋萋,正无情地吞噬那里的每一条砖缝,每一眼窗洞。藤蔓和爬山虎像传说中的穿墙而过者,在暗黑光线的各处,展露出它们攀援的绝技和人世沧桑无情的变颜术——昔日粮库成了古镇草木和植物们的最佳竞技场。
粮库前面一片空地,一排数株的樟树和梧桐树高高矗立在古镇的上空,成为方圆几十里以外就能够被人看见的一处绿荫。悠远的年代在那些落叶残枝上哔剥作响,根本无视房子本身低哑的男中音念出的那些字句:
“过十里春风,尽荠麦青青……
渐黄昏,青角吹寒,都在空城。”
——姜白石:《扬州慢》。
“春风桃李花开日,
秋雨梧桐叶落时。”
——白居易:《长恨歌》。
天空的繁花簇拥到这些荒凉的房顶和树荫之间。早晨的空气像刚捻出来的棉线一样洁白、嫩爽。河水本身也很清洌,因为附近的工矿企业,全都凋落颓败,无法再倾倒出那些卑劣地利用泡沫垃圾计算着利润的可恶的污水了,此乃不幸中之大幸。但粮库本身的四进身房子,终于在盘踞着蛇蝎们的荒草丛中,在断墙残檐间,偿付清了它早年一直拖欠下来的冒牌丰收年代的孽债。
房子的喉管仍旧被一只饥饿的手掌紧紧攥住,被一只仇恨而削瘦的膝盖,抵着它满面无辜、惊恐外突着的胸脯——粮库的外墙上留有一条当年刷上去的斗大标语,黯淡地醒目着: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念出来的古诗声音不时被口号声音打断。——在这中间是一座千年古镇裸露在蓝天白云之下最近五十年的沧桑……
4
“帝子降兮北渚……”
屈原在 《九歌》里说。
5
——我眼睛看见的那户农家的葬礼,也许延亘了千年。也许在我脚下这块土地上,从未中止过,停息过。招魂的旗幡,祭祀用的酒水,永远飘荡在这土地上空,洒落在庭院深深的小巷石板弄堂。没有一个活过、活着的中国人,曾经走出过这俭朴葬礼的乡间隆重行列。我们全是其中迎风哭泣的扼腕者,是白色挽联上书写着的沙沙声。我们的身体上有丧葬用的纸钱的一部分,泪水、烛焰的气息——是其中默然哀痛着的亲人们,那一大群黑压压的沿公路送葬者队列里大放悲声的部分。死者姓氏的喑哑无声,正是这田野上浩荡而歌的春天的嗓音——一个古代的、长长的歌队。
庞培 1962年12月生。诗人、散文作家。主要代表作有 《低语》、《乡村肖像》、《五种回忆》、《四分之三雨水》、《母子曲集》、《谢阁兰中国书简》、《西藏的睡眠》、《童年册页》等著作二十余种;获得的主要奖项有:1995年首届刘丽安诗歌奖,1997年第六届柔刚诗歌奖和2014年第四届张枣诗歌奖。现居江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