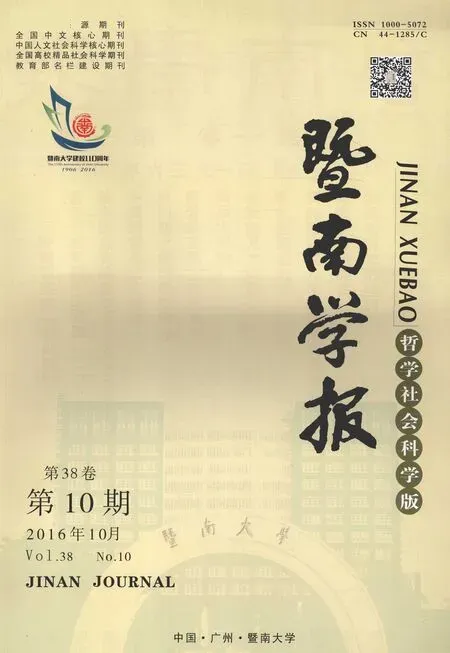老子思想的符号逻辑及其传播伦理
2016-11-26李红
李 红
(西北师范大学 传媒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老子思想的符号逻辑及其传播伦理
李 红
(西北师范大学 传媒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从符号论的角度去考察老子思想,将能有效审视老子思想的内在逻辑。这种逻辑深刻地影响到中国文化的某些独特实践,成为中国人传播观念和传播实践的重要理论来源。老子通过“否定”“二分”“反”和“去”等符号逻辑的运作,将其思想建立在对传统价值形态批判的基础之上,以建构“贵无”“欲望批判”“收敛”“圆满”“贵身”等新的伦理价值,成为中国人处理传播问题的新的思想形态和观念形态。
老子; 道; 符号; 传播伦理
在中国文化中,“谦虚谨慎”、“韬光养晦”、“内敛”、“少说话多做事”、“自然而然”、“涵养”、“枪打出头鸟”等等,无不体现了某种独特“处下”、“内敛”和“自然”的逻辑。当我们从传播伦理的视阈去审视老子思想的时候,中国人的某些传播实践可以从老子《道德经》里找到理论逻辑。当然,中国人的传播实践不仅仅是纯粹文本逻辑,而是会根据文化实践对文本进行选择并内化为心灵,从而形成不同的思想延伸,比如形成法家、玄学、道教等文化实践,从而形成不同的思考逻辑、行为逻辑和处事逻辑。要完整探讨中国文化的全部传播伦理是本文力所不逮的,所以,本文暂不理会《道德经》的历史实践,而仅就文本展开挖掘,探索其中的符号逻辑。在皮尔斯那里符号学是作为逻辑学的同意语来使用的,在其学科分类图表中标示“逻辑学[=符号学]”①皮尔斯著,赵星植译:《皮尔斯:论符号 李斯卡:皮尔斯符号学导论》,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1页。;在结构语义学那里也试图将符号的二元逻辑建立成一个符号矩阵,有学者将其用来分析网络“图像事件”中的“视觉抗争”②刘涛:《视觉抗争:表演式抗争的剧目结构与符号矩阵》,《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由此可见,符号是建构逻辑关系的重要载体,从符号过程的角度来审视《道德经》的书写逻辑,将能透视其中传播伦理的逻辑结构,避免对《道德经》的误读。
一、“否定”符号:“道”的超越与贵“无”伦理
《道德经》的开篇,老子就强调“道”的超越性,即“道可道也,非恒道也”(一章),即“道”不是语言符号所能把握的,它是不可名状的,故“道常无名”(三十二章)。不过,人类不可能没有符号;正是因为有了“名”,才有了对世界的把握,世界才呈现在人类的面前,因此老子说:“有名,万物之母”。“有”与“无”、“有名”和“无名”始终成为老子思想中相互依存、不可化解的对待关系。“有”是一种当下的存在者或者是对存在者的把握,这种把握是具象的、有限的,因此是易逝的;相较之下,“无”是根本的,是“有”的源头,它又蕴含在“万有”之中。按照老子的逻辑,“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十章),即“无”是最根本的实在,它产生了“有”和万物。与“无”具有家族相似性 (family resembalance)的概念有虚、空、冲、玄牝、渊等,它们都具有抽象性、根本性,因而能含纳万物,万物以其为归依。因此,老子说“渊兮似万物之宗”(四章);“玄牝之门,是谓天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六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十六章)。
“无”是一个否定词,根据语言的否定性原则,“必须有对于实在的企图,欲加以修饰而不得,然后才产生否定”*布拉德雷著,庆泽彭译:《逻辑原理》(上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2页。,实在与修饰的属性之间,首先存在一种正面关系,然后才是排斥关系,也就是说,虽然是排斥的关系,但是修饰的属性为抵达实在做出了部分贡献。比如,老子说到“道”的时候,说:“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十四章),即没有形,没有象,不可捉摸,但是它又确确实实在那里。为什么能够在那里?是因为“状”和“象”这样的否定在那里牵引;通过否定性描述,它呈现出了某种可想象的特质。没有否定的“属性”,对“道”也就没有言说,“道”也就处于无法想象的虚无状态。对于极具抽象性的“道”,虽然老子只是“强为之容”(十五章),“强字之曰道”(二十五章),但是“道”已经“始制有名”(三十二章),可以想象、运思和体验了。
老子常常通过“否定”的方式超越规定性,《老子》5 000余字,否定词如“不、弗、非、勿、亡”等字出现了258次,其中“不”字就用了238处。*李战奎:《老子否定式思维的现代意义》,《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8期。正是通过否定词的使用,“道”的超越性得以建立。也因为有了“道”的超越性,认知、体验和实践才会有一个指向性,那就是追寻“道纪”(十四章),以超越“有”,超越当下,从而获得作为人的超越性。这种超越是一种“内向超越”,是通过“心”对“道”的把握实现的,与西方客观外在的“外向超越”根本不同。*余英时:《论天人之际》,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24页。老子这种“内向传播智慧更倾向于消融社会性对自我超越的干扰,注重自我内心通过向‘道’的复归而实现自我升华”*谢清果:《内向传播的视阈下老子的自我观探析》,《国际新闻界》2011年第6期。,这就导致了魏晋玄学、道教、宋明理学中浓重的“神秘主义”的心灵取向,从而为哲学的开放性提供了基础。在老子的思想背景上,仍然具有浓厚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以及巫岘传统,并且巫史不分,因而儒、道、墨三家都体现出“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余英时:《论天人之际》,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70页。老子思想的逻辑前提是建立在对天、对“道”、对自然万物的信念基础上的,没有这种原初的(先验)信念,思想的起点将无法展开,也就无法获得超越性。
从老子思想的终极追求来看,不能简单地将其归于“权谋”(韩非)、“军事”(毛泽东)、理性*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77页。,“君人南面之术”*《汉书·艺文志》。。毋宁说它是一种“反思”或批判,是从相反视角展开的,始终保持在“反”的状态,即“反者道之动”(四十章),“正言若反”(七十八章)。但是这个“反”必须跟“复”和“归”联系起来思考,是对某种根本之“道”的“复归”,即“复归于无物 ”(十四章);“复归其根”(十六章);“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二十八章)。没有这个根本的超越之“道”的指引,所谓的“反”不过就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一种具有进取目的的“谋划”和“有为”,这与老子“无为”“自然”的理念背道而驰,也是对老子“无为而无不为”观念的一种功利化理解。从思考动力的角度来看,没有“反”,反思也就无法展开,这种“反”是符号切分的“反”,而非对象本身的反。“对象”本身无所谓正反,它就是“一”。当然,这个“一”不是数量而是本体,即“道生一”(四十二章);这个“一”也是“道”的本质特征之一,也是根本的。因此,老子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三十九),“一”支配着世界为万物。
世俗社会是一个祛魅(disenchantment)的社会,神秘力量和超越想象逐渐失去,人类被置于理性和世俗的旋涡之中,人类理性的无限膨胀,反而将人类置于无所归依、无限追寻的循环状态中。因而让社会充满了纷争、让人类疲惫不堪,最终,人与人、人与心灵、人与社会、人与神、人与自然等都出现了严重的传播伦理问题。老子思想也正在走向理性化的路,但是它仍然坚持“道”的超越性和神秘性,并且它明确地将批判的视角指向世俗的“利”“礼”“智”“学”“仁”“誉”“有”等社会价值,从而让人们警惕世俗的价值对人类构成的压迫。
老子通过“否定”的方式掏空“道”的确切内涵,以获得无限的意义含纳能力;这也就是“指的空洞化”,即扬弃或隐退“指”自身的存在,经历“指非指”的转换,*屠友祥著:《言境释四章·序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明确地让人意识到符号与其对象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实体,从而避免符号的片面性遮蔽对象的完满性,让人性在完满的世界面前展开其无限性。这可以分为两方面来讲:一方面就是主体(个体)通过“否定”的反思性超越,克服自我的局限;另一方面是通过“否定”剔除符号对客体的超越,从而让主体进入完满的客体中。这在传播伦理当中体现为对主体的反思和对客体的去蔽同时展开,并做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五章)的价值无涉状态,由此才能体现传播关系的“和合”状态,而不是“分”或者“析”的切割状态。
二、符号二分:价值批判与欲望批判
在老子的思想预设当中,始终有一系列世俗的社会价值作为批判的靶子,而世俗价值的代表就是儒家的观念,比如儒家的“仁”“孝”“礼”“忠”等,都是老子批判所针对的社会价值,因此,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十八章);“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十九章)。这看起来很激烈,其实是因为老子采取的是完全不同的价值批判逻辑。老子不再像孔子那样,觉得天下混乱是“礼崩乐坏”的结果,从而试图恢复周礼,恢复传统的社会价值以拯救社会;相反,老子采用的是釜底抽薪的办法,觉得社会混乱是世俗价值所带来的,这些社会价值的形成恰恰是社会混乱的根源。其解决之道是取消符号的价值切分,以回归“素”“朴”状态。
从传播问题的角度来看,社会、行为和人心常常存在如下的混乱状态,那就是人际的“争”“夺”“盗”“怒”“怨”“敢”“杀”等;外在的“妄作”“执”“强”“华”“多”“上”“恃”“持”等;内在的“躁”“轻”“患”“离”“狂”“惊”“迷”“畏”等。这些行为或状态都具有某种意向状态,也就是心灵的相关性或指向性,即“关于或者指向某事物”*约翰·塞尔著,文学平、盈俐译:《人类文明的结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6页。。实际上,这种意向状态是关于或指向世界的,只不过世界被把握为符号(表征),那么间接地,意向状态也就指向符号(表征)。语言符号在对世界进行切分的时候,基本采取的是二元的方式,老子对此看得很清楚,所以认为美丑、善恶、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等(二章)是相对而立的。但是这种相对不是平均对等,而是有所偏向,通常偏向强、大、多、上等主流价值,相反的一方即弱、小、少、下等则是负价值。当正价值都成为欲望的或者意向的对象时,这种欲望或者意向就具有扩展性,由此便会引发社会、行为和内心的冲撞,引起不安或危险等社会传播问题。
实际上,世界本来是一体的,所有的文化都是符号切分的结果。没有切分,就没有文化,人类也就可能会处于另外一种生存样态,那就是“小国寡民”的状态,即不被物役、不奔波、没有争斗、没有文字烦扰、快乐无忧、没有人际冲撞(见八十章)。文明社会的冲撞,很多时候就是符号的冲撞。从社会层面讲,老子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五十七章)为什么呢?因为“禁令”、“用具”、“奇货”、“苛法”等皆是符号切分的结果,其中蕴含了深刻的价值评判的意义;价值在此无疑就成为世俗人等追求(正价值)或回避(负价值)的目标,人就成为价值的奴隶,而不再“淳朴”和“自然”,社会也就纷争不止。
在老子看来,“上”、“强”、“阳”等常规的正价值是有问题的,这些正价值的问题也正是文化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总根源。原因在于,世界充满了辩证法,那就是“弱之胜强,柔之胜刚”(七十八);“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四十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五十八章)。老子始终告诫说“不敢以取强”“物壮则老”(三十章);“强梁者不得其死”(四十二章);“勇于敢则杀”(七十三章)。这些正价值很容易导致“满”、“过”、“多”,会造成对固有秩序的一种破坏,正如物理学中的“熵”,它因更多增加而带来“无序”。当然,老子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不是抽象出来的,而是通过对世界的观察后通过“比拟”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是“道法自然”的结果,比如“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九章);“企者不立;跨者不行”(二十四章);“信言不美”“善者不辩”(八十一章)。这种对日常现象的观察总是被置于二元对立的视角中,并通过否定词“不”的方式展现出某种悖论,由此获得辩证的逻辑,常规的正价值也就变得不那么绝对了。
社会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乱”?人心为什么不能“静”?老子进一步探索了其中的动力之源,那就是欲望。在老子看来,欲望的产生是跟文化符号的切分密切相关的,没有这种切分,欲望也就无从产生。所以,他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十二章)”,即没有“贤”与“不肖”的区分,没有“贵”与“贱”的区分,没有“好”与“坏”的区分,就不会有欲望,也就不会有“争”、有“盗”、有“乱”。雅克·拉康认为欲望(desire)不同于需要(need)和要求(demand),它是“要求减去需要所得的差”*吴琼著:《雅克·拉康 阅读你的症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83页。。“要求”是一种语言表述出来的“请求”,它跟生物本能的需要是不一样的,总是体现出某种匮乏和欠缺(lack),因此,欲望不可能达成。通过能指替代的方式,欲望被安置在象征秩序内,但是能指又不断漂浮或滑行,欲望只是闪烁隐现的意义碎片,是超越象征秩序之外的。欲望总是通过语言展开,但是又指向语言之外,具有侵凌性,社会纷争的根源在于“欲望”,“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四十六章)。
固有的文化在不断地制造欲望,所以解决社会问题就需要“知止”,防止对“名”的过度追逐,“知止所以不殆”(三十二章);只有“镇之以无名之朴”,才能做到“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三十七章)。老子提出了一种极端的处理问题的方式,那就是“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三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也就是去掉价值切分,最终做到去掉“欲望”,做到“见素抱朴,少思寡欲,绝学无忧”(十九章)。
价值和欲望的消解,其实就是需要通过透视符号的二元本质,勘破文化的幻象,消除意向性的偏执,以回归根本之“道”。就社会和人际关系中的传播实践而言,从主体角度来看,皆是“自心”在作祟。勘破符号的二元,便能勘破“自心”,勘破自心的欲望,由此获得“静”“重”“定”“无尤”“明”“正”“真”“自然”等伦理特质。由此,在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中体现出“挫锐解纷”“和光同尘”(四章)的特质,并在传播实践中体现出某种超越性的心理的稳定性、对客体的洞察力和关系上的亲和力。
三、“反”的逻辑:“守弱”中的收敛伦理
如上所述,在常规的文化逻辑里,对二元对立的选择总是倾向于“强”的一边,但是老子的选择却与此相反,他始终坚持“守弱”的姿态。根据其“道法自然”的思维方式,“守弱”的结论来自于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和思考,比如“玄牝”、“水”、“溪”、“谷”、“婴儿”、“户牖”、“车辐”、“飘风骤雨”、“曲”、“枉”、“洼”、“张弓”、“盈缺”、“建造”、“用兵”、“草木”等,其中虚无、柔弱的特质正是其生命活力的重要前提。在此“天道”、“世道”、“人道”的相互勾连中,“天道”成为“人道”的理性依据和思维起点,其逻辑是内心体验(而不是实验)、想象(而不是分析)和推衍(而不是归纳),*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5页。由此获得了形而上的哲学原理。另外,胡孚琛先生还解释说,道家源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原始宗教,其中最具特色的就女性崇拜,包括女始祖崇拜、女阴崇拜等,也就养成尊重阴柔、守慈、好静、谦下等品质的传统,贵阴贵柔的道家哲学显然是对这一传统的哲学抽象。*牟钟鉴、胡孚琛、王葆玹著:《道教通论——兼论道家学说》,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14—17页。老子始终强调“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二十八章),无论从宇宙生成,还是从“道”的特征,以及日用的生存状态,都从“守弱”阴柔姿态切入,这种哲学特质体现在“始”“母”“玄牝”“渊”“冲”“中”“根”“溪”“谷”等关键概念中。
具体从效果的角度来讲,这种阴柔姿态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七十六章);具有强大的容纳能力,即“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四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八章);展现出强大的生成能力,即“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六十三章),“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十一章);能提供强大的能量,即“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五章)“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七十八章);柔弱本身也能展现出强大的力量,即“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四十三章)“柔弱胜刚强”(三十六)。对这种效果的指向性(用)选择,就会变成一种功利主义哲学(法家);对这种价值的偏向(负项)选择,就会造成一种消极退让的隐者哲学。不过,这些都不是老子的初衷,因为从老子思想整体的逻辑来看,其最终指向是超越性的“道”,是反功利、反切分的。但是老子为什么要这么处理并采取“反”的逻辑呢?
首先,老子始终认为弱与强是辩证转化的,即“守弱曰强”(五十二章)“强大处下, 柔弱处上”(七十六章)。这种转化的动力在哪里?那就是“向上”的动力,也就是前面所讲的欲望。故而,他采取的是“正言若反”的言说方式,因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四十章),没有守弱处下的姿态,也就不会有向上的势。当然,守弱处下的姿态并不是客观位置,而是一种符号位置,是一种心理的姿态。从最终的目的来看,这仍然是“取强”,这与老子强调的“不敢以取强”“果而勿强”(三十章)相背离,处于“强”“弱”的二元倾轧之中,指向“强”这个老子所批判的价值逻辑。毋宁说,老子的目的是为了展示二元切分在时间上的暂时性,即“不终日”、“殆”、“失”、“败”、“已”、“死”等;在空间上的有限性,即“弊”、“穷”、“死地”、“拔”、“脱”等;在关系上的脆弱性,即“亲”、“疏”、“伤”等。
其次,只有采取“并”的方式,在二元基础上才能超越二元,才能参透“道”。老子在做了那么多的二元对举之后,总是会强调“无为”,也就是说,在符号价值上不做选择,没有选择,也就无所谓“二元”。所以,老子说“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十六章),并举之后,才能看到根本;否则单方面就是一种独白思维而不是辩证思维。最终,老子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不做刻意选择、展示和作为,即“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五章);“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三十六章):“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三十七章)。这样,“二元”对举的问题就被自然消解了。老子所说的“无不为”,从他的论述逻辑来看,并不是如后世之人那样的“用”的功利逻辑,而是始终强调“自然”,即“希言自然”(二十三章)“百姓皆谓我自然”(十七章)。因此,“无为”是指不刻意妄为以保持“自然”的态度;“无不为”不是意图性的,而是状态性的某种“结果”而已。
再次,老子他所讲的“反”,不仅仅具有相反相成的二元切分的含义,而且具有“还”与“回复”之意,也具有本体的“复归”之意。张岱年说“老子所谓道之主要内含,可以说即是变与反”*张岱年著:《中国哲学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1页。。老子说,战争不是个好东西,因为“其事好还”(三十章),对“价值”的争夺必然导致彼此压制,是传播危机的总根源。“玄德”的状态是“深矣,远矣,与物反矣”(六十五章),这是一种“大道”,故“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二十五章),最后达至和顺圆满的状态。老子也称之为“复归”,即“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十六章),并且“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朴”“复归于无极”(二十八章)。因此,老子思想超越了简单的二元对立及其转化,将“守弱”的姿态与“返”的逻辑结合起来论述,从而获得了一种超越符号能指的视角,并指向形而上的不可言说之“道”。这种“道”的“大”、“反”和“归”,所体现的类似于一种整体性符号逻辑;数字时代的确需要一种大尺度的“宏文本”思维,以实现碎片化传播的意义整合。*胡易容:《宏文本:数字时代碎片化传播的意义整合》,《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钱钟书认为“‘正言若反’,乃老子立言之方”,正是通过“正-反”的不断组合,形成悖论(paradox)与矛盾(oxymoron)修辞逻辑。对此,钱钟书引用神会《语录》:“今言中道者,要因旁义;若不因旁义,中道亦不立”;施彦执《北窗炙輠》记录一僧说“佛法”,说是东边倒东边扶,西边倒西边扶,中间立则推一推。*钱钟书著:《管锥编》(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717—718页。没有可言说之象,也就没有不可说之“道”,故“道”必有所“因”;不过是通过“反”的方式来“因”,应该是东边倒西边推,是反着来点醒的,也就是佛教所说的“遮诠”。因此,“反”的逻辑实现的是对玄妙之道的把握,这不但体现在思考当中,而且体现在传播实践当中,从而采取“守弱”的收敛伦理。
世俗的价值危机在于其进攻性和进取性,但文明社会的诸多伦理原则,却具有某种收敛的特质,比如爱、宽容、礼貌、谦逊、反省、公正、诚实等;很多宗教里也有很多戒条,比如摩西十诫、佛教的五戒十善等;中国文人特别强调日常斋戒仪式,以此获得身心的洁净精微。这在庄子那里发展为“心斋”“坐忘”等修养功夫,由此通过对“心”的修炼实现自我修养,以避免认知的偏执、锐化主体间关系。“守弱”的伦理特质,其实是勘破了对“物”的偏执,由此获得了解脱,也就不用“取强”了,非此即彼的冲撞也就消弭于无形。
四、符号的消解:复归“道一”中的圆满伦理
符号化之后的文化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割”、“散”、“裂”,即老子所反对的“圣人方而不割” (五十八);“大制无割”“朴散则为器”(第二十八章);“天无以清将恐裂”(三十九章)。《庄子·天下》篇也提到“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应帝王》讲了关于“浑沌”的寓言故事:“倏”和“忽”为了报答浑沌的恩情,说人都有七窍,那我们也给你凿上七个窍,于是每天凿一个窍,到第七天,浑沌就死了。浑沌为什么会死?问题在于“凿”破坏了它的完满性。浑沌其实就是“道”的状态,是“朴”和“一”,所以《淮南子·诠言》说:“洞同天地,浑沌为朴”;王充《论衡·谈天》说:“元气未分,浑沌为一”。庄子在《天下》篇中说“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也就是说,人类对于世界的判断、分析、考察只能是片面的,无法把握“天地之美”“神明之容”。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始制有名”(三十二章),即对世界加以符号化处理之后,世界被裁剪了,“析、断、判,为此处之制的涵义”*屠友祥著:《言境释四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随之而来的后果就是王弼《老子指归》里所说的“名必有所分,称必有所由。有分则有不兼,有由则有不尽”;庄子在其《齐物论》里也说“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所以,最终的结论就是“道通为一”,因为符号化的“分”就是对“道”的破坏。
老子不断地提到“一”,以描述“道”的状态,并且认为是根本的实在,即“道生一”(四十二);“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二十二章);“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候王得一以为天下贞”(三十九章)。这个“一”跟“道”一样,也是恍兮惚兮的,抽象而微妙的,即“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并且强调“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十四章),也就是不可言说的;“道”的状态也可称为“大”,“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三十四章),“大”到极致就是无法言说,即“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四十一章)。老子多次提到“不言之教”(二章、四十三章),“贵言”(十七章)“希言”(二十三章),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减少语言符号的干扰来追求“自然”“自化”“自定”“自正”“自朴”的状态,即“道法自然”(二十五章)。要达此境界,则需“镇之以无名之朴”(三十七),并且回归婴孩的状态,即“圣人皆孩之”(四十九),以避免“名”的干扰。
实际上,老子所主张的是一种“复归”,这种复归是辩证转化并扬弃之后的复归,是一种反思之后的提升;他所推崇的“赤子”“愚”“拙”“昏昏”“闷闷”等,不是“自然决定的”,而是“心灵经过努力而达到的成就”*冯友兰著,赵复三译:《中国哲学简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36页。,这跟通常所说的“傻”是有本质区别的。老子对于思维和世界的演进过程,抱持的是一种圆圈的逻辑,即“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二十五章),并且始终相信,通过努力,人能“复归”某种“根”、“常”、“无极”、“朴”等,而这些状态所描述的也就是“道”。
这种反思之后的提升,老子提供了一系列功夫,即采取“去”“损”“涤”“挫”“解”“塞”“闭”等方式保持“守弱”姿态,通过守弱而做到“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二十八章)的“二元”对举并参透“二元”。老子的目的并不是要坚持“守弱”姿态,而是为了取消姿态,从而达至“道”“天”“自然”的状态,即“合”与“一”。这种状态没有价值区分,没有极端选择,没有内心的纠结。表面上看,老子是试图取消符号,取消文化的反智主义,比如他说“绝圣弃智”(三十九章);“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六十五章);“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三章),让老百姓吃饱喝足就行,即“甘其食,美其服”,退回到“结绳记事”(八十章)的文化之初。但是老子的反智反文化只是一种姿态,而不是实质,追求的是不停地“反”和“损”的状态,从而达至“玄德”“玄同”“大道”的超越状态。
具体来讲,老子的任务就是通过克服“多”而达至“一”,因为“多”是危险的,会带来极大的干扰和混乱,即“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五章);“少则得,多则惑”(二十二章);“多藏必厚亡”(四十四章);“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泫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五十七章);“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六五章)。所以,老子主张“为道日损”(四十八),其目的其实就是为了“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三章),做到“寡欲”(十九章),以达到“我无欲,而民自朴(五十七章)”。需要做的就是去掉“多”,回归“俭”,即可避免干扰和妄为,“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二十九章);“治人事天,莫若啬”(五十九章);“治大国若烹小鲜”(六十章)。另外,还需要“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五十六章),消除符号的价值切分,通过“涤除玄鉴”(十章)的澄明方式,最后参透到“复归”根本性的“道一”。实际上,“《老子》五千言反复申论就是一个道理,那就是道的世界是一个不能断分、宰割、对立、相待的圆满的世界”*徐小跃:《对老子思想的现代价值的几点思考》,《安徽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道一”的圆满性,用老子的术语来说就“和”“浑”“公”“自然”“愚”“昏昏”“闷闷”“朴”“拙”“讷”“玄同”“大顺”。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道”的世界不仅仅是一个外在的世界,更是一个内在的世界,即心的世界。在老子的《道德经》中,有十处讲到“心”。其中谈到对“心”的警惕,即“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虚其心,食其腹”(三章);“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十二章);“心使气曰强”(五十五章)。谈到“心”的理想形态,即“心善渊”(八章);“愚人之心”(二十章);“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圣人……为天下浑其心”(四十九章)。按照符号学的观点,心的世界也是一个符号的世界,即人是一个符号,心灵是符号,思想也是符号。*卡西尔认为:“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载于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拉康说:“无意识是像语言一样被结构的”,载于吴琼著:《雅克·拉康:阅读你的症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4页;皮尔士说:“每当我们思考时,我们都有某种作为符号加以使用的情感(feeling)、意象(image)、概念(conception),或者其他表象(representation)呈现于意识”, C.S.皮尔士著,涂纪亮、陈波译:《对四种能力的否定所产生的某些后果》,载苏珊·哈克主编:《意义、真理与行动——实用主义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69页。通过“心”的修炼所获得的,其实就是对符号的反思和运作,由此实现老子所强调的“虚其心,实其腹”(三章);“心善渊”(八章);“浑其心”(四十九章)的修养目标。这样,修养就通过对“心”的作用而有了着力点,传播问题就变成了自我“心”的修养的问题,由此获得了一个新的起点。其核心就是“无为”“不敢”“不争”“不有”“不恃”“不宰”,以避免与世界形成主客二元的对立关系,并通过不断的符号消解实现与世界同一和圆满,做到“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五十四章) 的现象学还原。
五、“心”的消解与“身”的完满:“贵身”伦理
老子说“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十三章),是说很多人把荣辱看得跟身体一样重要,假如没有身体,这些感觉又从何谈起。在此,身体获得了一个根本性的存在,这种存在具有不可否认的客观性。老百姓为什么不怕死?是因为“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七十五章),只有用身体去冒险才能获得生的机会,最终还是指向身体的存在;当身体存在的机会渺茫,那就会没有畏惧感,恐惧和威胁将失去威慑力,即“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七十四章);更有甚者,“民不畏威,则大威至”(七十二章),假如老百姓不怕死,那么对于统治者来说才是真正的危险,因为老百姓在此对身体似乎已经满不在乎,他就会极具攻击性和破坏性。“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十三章),对身体的充分重视,是天下国家的基础;这种基础不仅仅是能力层面的,也是心理和伦理层面的。
如果我们从身体与认知的关系的角度去看,身体与对象的关系是一种直接的接触关系,包括眼睛的看、耳朵的听、触觉的摸、味觉的嗅等等,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老子的主张,即“虚其心,食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三章),这种直接的接触比符号所带来的要丰富得多。但是,身体的感官分割不等于身体,毋宁说,感官只是身体的一部分,它的感知仍然是割裂的,是需要警惕的,所以老子说“圣人之治,为腹不为目”(十二章);“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四十九章)。从心灵的角度来看,耳目又与心灵密切相关,耳目扰动又会带来心灵的扰动,从而让心灵处于分、杂、乱的境地,让人处于一种“多”而不是“一”的状态,这就是圣人需要像婴儿一样整体感知(即“圣人皆孩之”)的原因所在。
直接接触的感知所获得的还只是一种表象,这种表象不具有永恒性和抽象性;相反,思维是超越于当下身体感知的逻辑连接,不是“视”“听”“捪”(十四章)所能捕获的,它是一种抽象的运作过程。人类对于世界的认知,不一定需要身体的在场,只需要心灵的介入即可。“古代世界,很多大智慧,都是躲起来悟道,不是坐在树下,就是钻在山洞里,还有的对着墙壁发呆,除了化缘讨吃喝,或取经传教,根本不出门。不但不出门,连书都不读”*李零著:《人往低处走——〈老子〉天下第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54页。,所以老子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这就叫“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四十七章)。很多人不但不能做到超越身体去认知,而且试图扭曲身体,过度使用身体,这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即“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这是一种“余食赘形”(二十四章),是建立在不牢靠的反自然的基础上的,这反而会带来更多的遮蔽。
实际上,对于老子来说,“道”的最高境界就是“无我”,也就是试图对“心”的消解实现身体的隐藏,从而避免身体有限性对世界的遮蔽。所以老子主张“后其身”“外其身”(七章)“功遂身退”(九章),反对“以身轻天下”(二十六),最终消解自我,让世界呈现“自正”“自朴”“自宾”的状态,即“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五十一章)。自我及其身体作为一种视角,总是具有极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首先就体现在身体的空间有限性(视野、触觉、听觉)和时间有限性(死亡);人类所要努力的,不是取消这个有限性,而是承认这个有限性,并回归这个坚实的基础,即保持“小国寡民”(八十章)的身体直接性。现在所要做的,是超越身体的有限性,站在一种“无我”的“心”的消解的立场看待世界,如此才不会有视阈的局限性,即老子说的“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二十二章);并由此获得认知的遍在性,即“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十六章)。
最完满的身体就是“赤子”“婴儿”的身体,即“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猛兽都不能伤害它,它浑身充满精气神,因为“和之至也”(五十五章),这是与天地和合,不受世俗侵扰的状态。同样,善于养生的人也能做到不怕猛兽,不怕战争,因为压根就没有“死地”,所以“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用其爪,兵无所容其刃”(五十章)。这些现象看起来很神秘,其实逻辑上很好解释:因为孩子不懂得恐惧,毒虫猛兽即不容易攻击它;你不到危险的地方去(死地),怎么可能遇到毒虫、猛兽和战争呢?如此,便通过消解前提的方式,消解了问题;将身体置于恐惧和危险之中,想要没有恐惧和危险,怎么可能呢?退一步讲,即使处于危险的境地,也能通过“心”的消解而使危险不被察觉,身体也就会处于安全之中。
从符号的角度来看,人对自我的重视,往往跟“自我”概念范围有关系;消解了概念,也就消解了自我,同时也就消除了“外物”对于身体的束缚。《吕氏春秋·孟春纪·贵公》讲了“荆人遗弓”的故事:一个楚国人,把弓丢了而不肯寻找,说:“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听了后说:“去其‘荆’而可矣。”老子听了后说:“去其‘人’而可矣”。在此,孔子通过地点概念“荆”的消解而消解问题;老子则通过消解“人”这个概念消解问题,将人置于一种纯粹的身体状态中,以获得一种“公”的视野。无论是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论”,还是巴赫金和马丁·布伯的对话理论,都是以“主体”的存在作为前提。而在老子这里,主体试图被消解,以回归身体的完满性,避免主体视阈的局限性,从而进入与万物同一的“无我”境界。老子并没有以人类为中心来思考问题,而是将人放入宇宙秩序中进行思考;一旦将人类的“主体性”偏执去除,人类也将获得广阔的视野。因此,老子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二十五章)。在此,人被置于宇宙中一种微不足道的地位,只是宇宙中的一元,并不具有主体的地位。同样,庄子所采用的“寓言”“重言”“卮言”修辞,看起来“汪洋恣肆”,不过是以视野无限超拔的方式,超越主体视野的狭隘性,以获得“以和天倪”的境界。所谓的“道一”“以和天倪”等道家观念都是试图获得身体的完满性,以与天地和合的方式充分敞开人的精神和灵魂。
在西方传播学的传统中,人都是一个核心主体,而人的存在又是通过他人或世界而得以形成的,他人或世界就成为讨论的重点;这看起来试图确立主体的地位,主体其实以不可追问的方式被隐藏了起来。但是,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自我”反而是思考的重点,在努力修身的过程中,指向的是个体的完善,并通过个体完善实现社会的善治。在老子的观念里,主体在修身过程中,需要通过一系列自我批判性的道德实践,以获得身体的完满性,并由此敞开精神和灵魂,从而在实践层面展开“传播问题”的思考和解决,而不是仅仅在外向、他者和认知层面展开。因此,看起来试图隐藏主体,实际上是实实在在地指向主体,以消解主体的方式实现主体的完善;在此,主体是生成性的而不是自明的,唯一自明的是身体。
总之,通过符号论深入审视老子的《道德经》,我们发现,无论是价值批判、收敛、圆满、贵身,还是“贵无”,都体现了某种内向超越的特质,即将传播的问题置于生存论的伦理角度进行反思,并将“道一”作为最终的形而上的指引。在此,无论是与内心、与自然、与他人、与社会,都获得了敞开的特质,在认识论、伦理学、生存论、本体论等层面都建构了新的前提,从而对传播问题的思考获得了形而上的视野,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伦理原则。
[责任编辑 王 桃 责任校对 李晶晶]
2016-08-20
李 红(1977—),贵州黔西人,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网络舆论和传播符号学研究。
G206
A
1000-5072(2016)10-006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