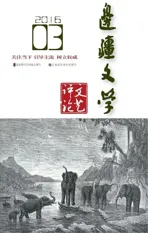解不开的峡谷情结
——读李四明的诗集《躲不开的夏季》
2016-11-25密英文
◎密英文
解不开的峡谷情结
——读李四明的诗集《躲不开的夏季》
◎密英文
解不开的峡谷情结 ——读李四明的诗集《躲不开《躲不开的夏季》是李四明创作、出版于上世纪80年代的诗集。全集分“唱不息的童年”、“躲不开的夏季”、“走不出的山路”三辑,共60首。这些诗作以饱满的创作激情,热情讴歌了怒江大峡谷和大峡谷两岸的傈僳族同胞的生产劳动、爱情及生活。整部诗集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风格;历史与现实纵横交错,激情和理性相互交融;诗风清新、朴素、淡雅,如山间清澈的小溪,如林中明净的湖水,令人心旷神怡,又发人深省。读它,一种浓浓的峡谷情结萦绕在我的心头。
童年的淡淡愁绪,回报母爱的拳拳之心
“童年/奔驰在八月的田野/啃着包谷杆/甜蜜/流进心里//童年/横在回归的老牛背上/挥一挥牧鞭/太阳/吆下山去”(《童年的记忆》)。童年,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值得记忆的,但每个人的童年又不尽相同。李四明和许多傈僳族青年一样,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但由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落后,地理环境的险恶以及当时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作者的家庭被划为富农,父母被批斗,给他幼小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
“给父母/播种和收获的白昼/一个安祥的夜晚/她舂着/比她身躯还粗的木碓。”(《舂碓的小女孩》)、“从捉迷藏的笑语中/也会遗落几滴泪。”(《牧童》)、“从母亲/遥远的惨叫声中/悄然落地/光着脚丫/裸着肚皮”(《火镰》)、“看见父亲酒醉的模样/我就想起过去的日子”(《过去的日子》)……
从以上这些诗句中,我们不难捕捉到作者童年的不幸和艰辛。当然,诗人也是幸运的,故乡的山坡不仅长满青青的野橄榄,也生长着一种传说中的“幸运草”,让人神往、蕴满希望。更重要的是,诗人有一位善良、慈祥、勤劳、伟大的母亲:
“母亲/为了我,不再是/挎着长刀、扛着弓弩、吹牛角号的汉子/被喝酒的父亲打骂//为了我,不再是/背着大篮,握着犁头/喘吁着粗气的父亲/您托出了您的太阳……//那是寒冷的早晨/您为了不让幼小的心灵受冻/把全部的爱蕴世故在心底”(《母亲》)、“晶莹、透亮/该不是泪珠吧/母亲说/她生我的时候/掉落了好多好多的泪”(《野橄榄》)……
就因为有这么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使诗人的童年不仅不因艰辛而酸涩,反而有了“野草莓”的回甜。于是,在许多诗作中,诗人情不自禁地注入了他对童年的追忆之情和对母亲的拳拳回报之心以及对不懂事的岁月的追悔:
“我知道我的过去/只会吮吸母亲的乳汁/在母亲病难之时/也只会躲在一旁悄悄哭泣……”(《故乡的河》)。
当然,追忆童年,诗人也不仅仅只有叹息和忏悔,童年生活的艰辛也使诗人和千千万万的傈僳族少年一样,过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并拥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坚韧之心,他和他们一样“不愿用眼泪/换取母亲的宽容/他们需要笑/笑也应该属于他们”(《割猪草》)。
需要指出的是,诗人在作品中常以“母亲”作象征,使作者的峡谷情结有了两股剪不断、理还乱的金线——童年和母亲。其实,这里的母亲已不仅仅为诗人的母亲,她是千千万万峡谷母亲的化身,也就是说,她就是祖国母亲。难怪作者的思念“是缠绕的线团/怎么也滚不出/阿妈温柔的手心”(《故乡的路》),也使作者的这些诗作,有着浓浓的真情、淡淡的愁绪,读来亲切、感人,很容易打动人心,让人潸然泪下。
歌吟爱的失落与收获
“一切皆流、无物常驻。你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为新的水不断流过你的身边”(赫拉克利特《古希腊罗马哲学》)。这是指事物在不断地推陈出新,旧的东西失去了就永远地失去了;而爱情,或者说,曾经有过的初恋,是难以忘怀的,这样,爱情就成了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从事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
“等到有一天/我俩擦肩而过/蓦然回首/已过了收获的季节”(《重逢的日子》)“我俩时常相见/又时常分离/那古树下的叠影/那小站里的挥泪/如今,偶然碰在熙攘的街市/火辣辣的眼睛/仍是躲不开的夏季”(《躲不开的夏季》)……这些诗作写出了爱的无奈和对初恋的情想,写出了爱的“失落”感。因此,对已获得的爱,诗人也曾充满恐慌和紧张:“这个季节/天空是善变的无赖/烈日炎炎/别贪恋异乡的风景/旋即倾盆大雨/会淋湿你的美丽”(《夏》)、“那强劲的音符/是我声嘶力竭的呼喊/旋转的霓虹灯/是我紧随你的目光。”(《你是否感觉》)。当然,我不是说诗中的“我”就是作者本人,但它毕竟是作者个人生活经历、生命体验及积累的结晶,与作者的感情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其实,作者是爱神的宠儿,自从“她”“第一个闯入”作者的门“轻轻的揉搓/那皱巴的记忆/月光下/晾晒发霉的日子”(《洗衬衣》),他就获得了与那些幻想的“初恋”有着截然不同又相吻合的爱,或者说真正拥有诗一般美好的爱情生活,它拓宽了诗人爱情诗的题材:女儿的生日、晚饭后的散步、妻子一个爱昵的动作……都能触动诗人的灵感,写出一首首看似随意道来,其实满含激情的诗作: “好动的小女跑前跑后/甜甜的笑声/抒写黄昏的可爱/妻子低头不语/像一朵开放的睡莲/不忍惊动她的温柔”(《散步》)。
美,不仅包含了审美客体本身的性质,也包含了审美主体对客体的感受、认识、理解和评价。李四明的许多爱情诗,就是作者本人对审美客体的独特感受、认识、理解和评价,使原本平谈无奇的人和事,被他诗化,如“在雨中/一位带伞的女子/和她走一段/难忘的路程”(《总是……》),本是一段平常的在雨中共走的路程,却被诗人渲染得如此美丽;而那首《冬》中,“那个玩雪少女/那声甜甜的微笑”在我们看来不过是位少女在微笑着“玩雪”,而诗人却从中浮想联翩,企盼“它”永远“还那么真实/温暖一生的冬天。”这正如老诗人艾青所说:“诗人只有丰富的感受力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丰富的思考力、概括力、想象力。”(艾青《诗论》)。
真诚地歌哭,激情地呐喊
“诗文随世走,无日不趋新”(赵翼),“如今,作一个诗人——意味着用诗的形象去思索,而不是像小鸟一般以美妙的声音去鸣啭的。要想作一个诗人,不需要那炫耀自己的琐屑的意愿,不需要那无所事事的幻想和梦、陈腐的情感和华丽的忧郁,需要的是与当代现实问题的强烈的共鸣……”(别林斯基《1845年的“流星”》)。与写童年、写爱情的诗相比较,李四明写民族、写历史和现实的诗,更趋成熟、更有价值,是真正的“真诚地歌哭,激情地呐喊”。
诗人对党是充满感激之情的,他和生活在怒江两岸的各族人民有着血肉交融的关系。这不仅是因为党给了作者和他的民族以新的生命,同时,在党的领导下,怒江这块贫瘠的土地发生了跨世纪的飞跃,激发着作者的创作激情。而更主要的是,诗人把自己的根紧紧地扎在时代和社会的土壤中,所以,他的呐喊是真挚的。
“面对党旗/在铁锤和镰刀/不断的撞击声中/我举手宣誓/这是多年的心愿阿”(《面对党旗》)、“拓宽的山路/把山里人/多年的愿望驮在车上/如车轮飞旋”(《乡村公路》)、“这是在朦胧的黎明/母亲挑着启明星/微笑着向前、向前/担回金黄色的秋色”(《小路》)、从“故乡那块土地/不生长庄稼/有种草长得很旺”到“故乡那块土地”/不再生长草/庄稼却四季长得很旺(《幸运草》)……这些诗作,不仅抒发了诗人对党的感激之情和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责任及荣光。同时,也讴歌了故乡日新月异的变化,一步步来临的好日子。
和故乡的山水和发展变化相关联的,那就是故乡的人和事,诗人真诚地扎根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努力感受着他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在建设新生活、创造宏伟事业过程中的思考、劳动、汗水以及他们的彷徨、向往和追求。他的以《山汉子》为题的诗作写得流畅、自然,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选入《躲不开的夏季》的几首诗也不例外,他写山汉子是“从江中峭岩中崛起/就已注定你的一生/与江水作伴/和浪花为伍”(《浪里松》)、且“耕耘悬崖/收获峭壁”。他写道班工人“年复一年/地老天荒。你拉长了路的寿命/路延伸出你的价值”……这些诗作,把物和人有意识地融为一体,以物托情、借物写人,真实地写出了山里汉子的粗犷、洒脱。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傈僳族的历史和现状的忧虑和思索以及对未来的向往、憧憬,使他的一些诗作有了一定的历史厚重和份量。
“山里人爱喝山里的酒/抛向蓝天的唠叨/落在山野也能抽芽//山里人爱唱山里的歌/一心想/捕捉岁月/却反被岁月捕捉”(《山里人》)。
“傈僳人/一个骚动的民族/一群初生的牛犊/刀山敢上/火海敢下/吼一声/轻松地走出阿爸的篝火/挣脱阿妈的麻线/牵着山野的朝阳/赶着大山的粗犷/我们来了/重重地敲开/城镇紧锁的黎时”(《傈僳人》)。
是的,“我们来了!”,带着父辈的呼吁、渴望和企盼,背负时代的重托,盈圆大峡谷千年的梦幻,因为“想哭就大声地哭/想笑就尽情的笑”(《那时,我们还小》)的日子是属于我们的,这是一个充满和平、自由和希望的时代。
艾青说过:“一首诗是一个人格,必须使它崇高与完整。”“诗人必须说真话”,《尚书·尧典》:“诗言志、歌咏言”。“诗者,志之所至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绪于中而形于言” (《诗大序》)。这些大师和经典中谈到的诗言志,其实指的是诗人的志向和诗作所要表达的意向。诗品和人品融会贯通,使诗人的诗作更具有了诗格的提升,从而使人们有了拜读的欲望,并欲罢不能。
(作者系怒江州文联副主席)
责任编辑:程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