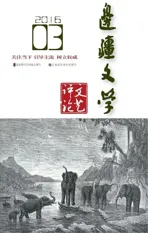新世纪文学场域中的云南青年写作
2016-11-25黄凤玲
◎黄凤玲
新世纪文学场域中的云南青年写作
◎黄凤玲
新锐批评
主持人语:本期新锐批评推出的是两位大学校园内的青年批评家的作品,他们同时对云南的文学现象投予关注的目光。黄凤玲对云南的青年文学创作进行了有自己发现的扫描,她所注意到的一些云南青年作家、诗人,可能是我们没注意到的,或者是没太认真对待的,黄凤玲在她的评论中,抓住特征进行了介绍,这对今后进一步的评论是意义的。谢轶群对云南作家黄玲的散文作了自己的解读,文章有对其中篇章的赞赏,也有对一些篇章不足表达的遗憾,这才是评论应具备的态度。散文是一个易写难工的文体,对散文的研究也有相当的难度,它不像诗歌和小说有大致的研究路径和丰厚的理论积累,海一样宽广的散文创作领域,也给散文研究带来没边际的可能性,这又恰好又成为散文研究的难度所在。本文中关于散文的几段文字是很有见地的。(宋家宏)
一
“新世纪文学”是涵盖2000年以后的中国文学概念。在新世纪文学语境中,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是一个标志性特点,20世纪中国新文学传统中那些最伟大的作家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偏重于乡土生活的书写。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新成长起来的“70后”、“80后”作家几乎很少涉及农村题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专注于对城市生活的描写。到了新世纪,这种状况更是越来越强势。与城市生活相关的视野、趣味、习惯的强化,已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学书写中的一股强势力量。中国文学从乡土世界转向城市生活,这是20世纪与21世纪之间的一个根本区别。
云南地处边疆,但我们对文学的钟爱和坚守并不边缘。“70后”,这是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型后产生的第一个代际作家群,其生长的特定背景,决定了这个作家群体形成特殊的生存观、价值观、艺术观,也使他们的小说创作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审美格局。在“美女作家”和“下半身写作”这些看上去炫幻的光环之下,遮蔽着一群有着独特个性和审美风格的作家。
“承前启后”的70后作为在云南写作者中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创作近几年正逐渐步入黄金时期,他们的作品再一次向我们重申文学对世界的意义:传达何为生活,生命的真实,存在的价值以及时间的轮回。
陈鹏 1975年生。这是一个对生活和自身有着深刻洞见的小说家,他把如何超脱于庸常凡俗之上,作为对自己写作才能的考验——抑或是自我救赎?《长江文艺》2015年第8期登载了陈鹏的短篇小说《礼物》,几乎完全运用对话推进叙事进程,一个青春叛逆的16岁女儿,一个人生破败的中年父亲,支离破碎的生活与青春的疏离静静地晾晒在主人公和阅读者的眼目之下,不免让人想起《麦田里的守望者》里那句话“长大是人必经的溃烂”,作家将主人公自身挫败沮丧的生活同女儿迷惘尴尬的成长经历缝合在一起,成为作家指涉无常命运的一道黑色抛物线。整篇小说有一种强烈的分寸感,这一直是陈鹏写作坚持的叙事节奏,笔触间不断闪现一个优秀记者的冷静和细腻,语言洗练节制,叙述干净精准。但一种塞林格式的渴望与失落,困惑与忧伤早已默默地潜伏在故事的周遭,看似冰锋般锐利的文字之下,一股沉寂的激情在情节之下的暗格里聚集。阅读陈鹏小说的体验不会轻松,但却自有一种冒险的惊异和刺激,因为在他的小说中,命运仿佛一个耐心的狙击手,隐藏在生活的暗处,伺机而动。
同为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诗人爱松和影白,他们一同参加《诗刊》主办的“第三十届青春诗会”,骨子里涌动着一样的对传统经典文学的热情,不同的是,爱松将典雅化为了充盈在他醉心的如歌诗意里,浅酌曲觞,低吟高唱。对爱松来说,诗歌写作成为他精神怀抱中的乐器,而不是随身携带的兵刃。而影白则酷爱古典诗词中的鲜活意象,辅之以西式现代主义的反讽意味,睥睨纵横,慷慨悲歌。尤为难得的是爱松近年绽放出在小说创作方面的才情,令人欣喜。
“70后”文学创作是一个始终全力表现都市生活的写作群体,以一种完全脱离了乡村的都市性写作姿态,以前所未有的自己的都市生存经验为场域,内在化的展示自我的生命在现代城市文明中的挣扎和突围。
雷杰龙 一个写小说、散文和评论的70后作家。2013年2期《人民文学》发表的《归宿之地》是小说形式大胆实验的成功范例。小说的语言优雅而冷静,幽默的亮色在阔然无垠的叙事场域中时时律动,纪事、评析、随笔,交错叠加,现代感十足的小说。
尹马 2010年尹马凭着小说《朵儿的诅咒》入选第二届高黎贡文学节的参展作家。诗人尹马的小说处女作,语言清晰简洁,和他刚直率性的诗歌语言相比,甚至可以说是雅致流丽了。小说可读性很强,娓娓讲述的感伤爱情如同童话里的捕鼠人一样迷住了读者,而人心和人性的迷幻和暧昧让人怅然。
近年来,在一些作家以及那些与文学无关的人身上,我们越来越频繁地看到,他们改变信念,就像更换戴旧了的手套一般无忧无虑和漫不经心。但同样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巨大变革中成长,在一个异常活跃和饱含激情的变化时代里从青春渡向中年的作家吕翼,却是一个文学信仰的坚守者。
吕翼 2011年6月,吕翼小说创作研讨会在鲁迅文学院召开,1971年的昭通作家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这是一位以自觉的担当和坦荡作为对“良心”尊重的作家,吕翼的小说在呈现强烈的地域色彩的同时,又能塑造具有普遍人性特征的典型人物,语言绵密机警。他秉承着与生俱来的坚韧气质,张扬根性写作和血性写作的两面猎猎旗帜,扎根于深切爱恋的土地,紧握时代写作的核心(历史和大地),在时间和空间的隧道里执着探究时代的信仰,追问人性的隐疾。
各种观念和文化的多元“叠加”,构成了“70后“的基本特征。他们的文化展现出一种过渡性的特质。这使得他们的写作呈现出来的,其实是一种很复杂的状态。
红布条儿 问鼎第六届高黎贡文学节“文学奖”的网络女诗人。“故乡对于诗人来说是另一个我的存在。”这是一个和故乡杳杳相思的女子的倔强。着一袭棉布红袍的女诗人红布条儿,神情肃穆,皈依佛教的壮族女子在欲望都市的深圳流浪。打开她的诗歌,一瓣宗教的自律和自然“隔着一座空山”与世间万物相连共存。漂泊异乡的忧惧给韦红霞以切肤之痛,而诗歌是红布条儿的救赎方舟,在月华如水的夜里带她回家。
唐果 1987年,少年唐果跟随支边的父亲举家迁入云南德宏。从此,山水田野,鸟语花颜走进了唐果的诗魂,这个用树叶染绿手心的女子,唤意抒情,风情万种又稚语天然。她用透亮的文字同世间万物、生命尊严交言,倾身谦恭是她的身姿,清新恣意的诗歌语言自有一脉凌厉的思辨之气。意象飞动,澄明亮丽又峰回路转,总是让那些阅读者在与她的诗歌不期而遇时怦然心动。
庞德说:“诗人是一个种族的触角”,在云南,让人不由想起小凉山彝族诗人阿卓务林。
阿卓务林 至今仍然住在泸沽湖畔的宁蒗县城,这是一片他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土地。以一种彝家人的热情和沉实撰写一部小凉山的《瓦尔登湖》。与梭罗不同的是,阿卓务林的诗歌更加自觉地关照族人传统文化和信仰体系与生存地域的联系。阿卓务林对本民族文化执着的挚爱与坚守,正是诗人令人敬重的品格。
在70年代出生的人身上普遍地有一种焦虑感,他们在时间中穿梭,如同穿过漫长的荆棘林,那种刺伤不重却很疼、持续时间长,虽可愈合,但是精神的恐惧却难以忘记,这种焦虑几乎是积重难返。
徐兴正 他没有像普希金那样陶醉地欢呼“我渴望生活,为的是能思考和受苦。”但对社会中边缘、琐屑、灰暗生存的近距离观察,让那些混沌、暧昧、模糊、歧义的生活在他的小说里找到了恰当、妥帖的流动和张开的方式。中篇小说《马贤对是谁》正是作家鼎力之作。作家描写的是一种生动具体的,有血有肉、有滋有味和充满着过街楼般喧闹的生活。小说摆开的是一桌麻辣火锅的架势,小说语言组成的热气在空气中漂浮着一种让读者兴奋的味道,幽默、俏皮的世俗话语透着生活的鲜香辛辣,在这场似喜而悲的宴席中,世情和人性成为作家啼笑皆非的安排下展示的五彩拼盘,时代的暗疾和存在的忧伤被正面迎击。另外,对于写作散文的徐兴正,其倔强又淡然的笔调也值得注视。
这是一群很执拗的作家,很多人坚持写作都在十年以上,从事纯文学创作,拒绝商业化写作。从九十年代到新世纪十多年的写作道路中这群踽踽独行者经历了遮蔽以及遮蔽之后的重塑进入了创作的高峰期。他们用作品修正了大众对“70后”作家的偏见,他们省察人情世事、灵魂隐痛,他们的文字不仅有正面塑造人的灵魂的能力,更给人直面现实人生直抵精神深处的勇气。
二
如果说新世纪文学中最为轰动的文学现象,当然要数“80后”文学了。“80后”文学是对新世纪出现的青少年写作的命名和概括。 “80后”在网络这个崭新的场域建立了他们表达自己、指认同类的领地,并且面对社会共同发出质疑或申诉,从而彰显他们的文化权利。
在“80后”文学(主要是所谓偶像派在聚光灯下走秀时)集体强势登场,抓取大众狂热眼球的彼时,或许我们曾叹息文学的荣光远离云南的村寨。但现在恐怕是要暗自庆幸当初那场都市的狂欢我们并未入场。正因如此,云南的写作群体中,那些自觉规避了代群陷阱的作家,正以寂寞却顽强的探索,建构自己独立的文学空间。
2013年,《格兰塔》杂志评选的英国青年作家二十佳,大多毕业于名校。他们在哈佛、牛津等名校拿到高级学位后,又转向各类创意写作班学习,进而开始他们的文学写作生涯。相比之下,云南文坛的青年作家们真正来自各高校中文专业的比例远远低于此,至于还拥有所谓的创意写作班的经历者,更是寥寥可数,甫跃辉便是这可数之一。
甫跃辉 云南保山的80后小说家,复旦大学首届文学写作专业研究生,中短篇小说登载在《中国作家》、《文汇报》(香港)等文学期刊。甫跃辉小说多以并不确定的南方农村生活为题材,故事构思新颖别致,将自己细腻而不琐屑的感觉和对生活的思考揉进主人公的命运书写中,叙事简约而又意味深长。对城市寄居者、灵魂漂泊者以及存在焦虑的现实凸显,作家并未采用叩击和拷问的激烈方式,相反有一种张爱玲式的精致和苍凉。不同的是,甫跃辉的感伤虽然舒朗但却出自悲悯。2013年4月甫跃辉以作家身份参加了“第一届全国青年作家批评家主题峰会”。云南的甫跃辉已经走向当代文坛的前沿,对中国文学的未来显示了自己的存在。
甫跃辉成长的历程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持续写作,并照着自己的内心写作。惟有如此,你才能找到属于你自己的话语方式。
通常的写作者能做到的只是用文字打开人类世界中的一扇又一扇虚掩的房门,让阅读者看到敞开的门内所发生的一切,至于门后的光景,恐怕多是“难以描述”的。只有数量不多的作家,努力将写作的笔触探向那些隐秘的幽深之处,让人的存在露出凌然的真相。包倬就是其中一个勇敢者。
包倬 一个出生在大凉山生活在昆明的80后小说家。在汹涌巨大的生活浪潮里,包倬并未竭力赞颂那些高高在上的崇高与黑暗抑或如铁般坚硬冰冷的规律,他始终保持着持续关注的是个体的存在,或许是欢笑,忧伤,或者是狡憰、迷糊,在他看来,平凡的生活存在比海洋中所有的沙子更沉重,普通人的生命状态比任何所谓的客观规律价值更高。在包倬的笔下我们看到放纵的物欲刺激掘空了的人的内心,不断溢出身体的灵魂被挤压到了城市的阴影下,疲劳和麻木像潮水一样漫过广阔而虚弱的肉体。或许有人会质疑其中人物的浑浑噩噩,没有鲜明而坚定指向的信仰,但这正是包倬小说置予这尘土飞扬的俗世一个隐秘的通口。舍斯托夫说“只有当人们看不到任何可能时,人们才去信仰。”包倬小说中的主人公,几乎都是晦暗而令人窒息的人生,然而恰好击中了生活的暗面,那么深刻精辟。没有夸张,也不搞笑,在他平缓从容的叙述中,一群无法逃脱自己生活境遇的孤独者,单薄的灵魂漂浮在命运之海,无所依托,最终湮没于社会生活的的诡谲与悲凉。正如美国华裔女作家李翊在其新作《比孤独更温暖》中所言:“生活是一场战斗,那些平凡卑微之人并不能奢望中途的退出。”包倬的人生经验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一种与生俱来的艺术敏感并没被他曾经匿名的生活消解,而是更加凸显。对于身外的这个世界,包倬有清晰而坚定的认识:生活的喜悦和苦难都是现实存在的,回避或者粉饰都不能从生活中赶走悲剧。包倬写作的小说语言是朴素可信的,并没有同龄人易于陷入的华丽矫饰的泥淖,以一种令人着迷的真实性将那些夜色的人生照亮。
在创作上,对青年作家来说还是一个文学资源的问题,我们经历的时代是相对平和的时代。在写作资源相对匮乏的时代,就需要作家具有更强的洞察力,更多的包容心。
王单单 2012年10月王单单参加《诗刊》第28届“青春诗会”,2013年4月获首届“人民文学·新人奖”,仅仅相隔数月,王单单就给云南的诗坛带来了两次不小的震动。对于拥有雷平阳和樊忠慰的“昭通文学”来说,欣喜的是诗歌血脉又有了可以与之相配的继承者。
生长在大山深处的王单单,血液中便流淌着生活的苦和痛,沉默的煤和陡峭的崖赋予诗人隐忍和坚毅的姿态。他的诗歌像他日夜守望的家园:淳厚骁勇的峰峦,野气血性的飞瀑,是他诗歌语言的刚直站立;而那热烈得令人窒息、瑰奇得让心眩晕的火烧云就像他诗歌里的意象,风流倜傥,恣纵宕跌。自称狂狷之徒的王单单其实并非快意人生的剑客,他的诗歌确有刀锋,但,此锋却插入自己的肩头,“为睡着的白骨/洗净来生的痛苦和悲悯”。王单单的悲痛里有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骑士精神,唐吉诃德式的疯傻与哈姆雷特般的癫狂也难掩饰的生命的力度和灵魂的高度。从《晚安 镇雄》到《车过高原》,王单单无疑是云南当代青年诗人中最锋锐的声音。
东巴夫 80后丽江作家。《丽江笔记》诗意的景物描写,单纯却颇有张力的叙事,现实和虚构在其中亲密无间,沉稳和轻灵精妙融合。作家在诉说着一种记忆的语言,向心灵的幽微之境探觅,这是一路丰沛悠远的漫游,也是将丽江还给丽江的漫游,空气中有一缕湿润的干草味儿,仿佛屠格涅夫的“白净草原”。年轻的东巴夫,有着真诚低调的抒情气质,既非狂欢式抒情的七彩乌托邦,也绝不是赞美诗般的感伤沉溺,而是带有底色和个人化的长久凝视,一种鲜活茁健的原创力。东巴夫,一个知道自己写作方向的作家,他的未来,值得期许。
李达伟 1986年生于大理。李达伟的散文是特别的。他并不沉溺于童年记忆的想象和田园飘忽的期望中,他的目光深邃悠远。长篇散文《隐秘的旧城》,在作家如江河一般畅流的叙述中,透过或旖丽或斑驳的景象,作家的笔触在寻找,寻找在日趋匿名化、表面化和短暂化的人类社会关系中,承载着城市和乡村人格印记的文化界碑,思索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我的关联和精神图像。作家由心而生、以情入笔,深沉厚重的宏观视角与细腻温润的微观视角相得益彰,仿佛影视中长、短镜头和空镜头的循序变换,各种景象一一呈现,又渐次隐没。语言纯净富有质感,淡淡的感伤中充盈着理性的思辨色彩,李达伟的散文,一种有着强悍内在驱动力的智慧书写。
2012年,80后周明全登上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舞台,这是第一位站在云南边地发声,引发公众倾听的80后批评家。三年过去了,周明全的声音并未减弱,而是更加响亮,充满自信。他在《当代作家评论》等国内重要理论杂志和报刊发表了近百篇文章,并获得包括“第十四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在内的多个奖项。同时,他还策划了国内首套《“80后”批评家文丛》、《“80后”批评家年选》等丛书,其文学批评著作《隐藏的锋芒》表现出一个青年文学批评家的学养和抱负。周明全是一个有自觉的问题意识的批评家,他的批评不仅思辨性强,视域深阔,而且能在喧闹纷繁的文坛坚持独立理性的姿态,发出有温度、有血性的声音。或许,如今已昂首进入中国80后批评家前列的周明全会成为云南乃至全国构建新的文学格局的推手之一。
2014年8月,杨荣昌参加第八届全国中青年文艺评论家高级研修班学习。他在《文艺争鸣》等刊物发表了专业论文数十篇。读着杨荣昌的批评文章,更感觉到他的朴质心性和对文学批评的热度和信念。杨荣昌的文学批评保持着一种强势的理论敏感和人文情愫,并对云南的文学批评地域格局产生积极的影响。杨荣昌的脚步稳健昂扬,踏实地磨练着艺术感受力,锲而不舍地蓄积着文学批评者的理论学养,假以时日,他们定能够担当起整理混沌中具有创造性的文学秩序的重任。
从2006年10月起,稳居福布斯财富排行榜的“80后”偶像作家郭敬明,以出版人和成功商人的身份主编《最小说》,发行量一直高居不下。而由主流文学刊物和名校共同主办的文学赛事,仍然还停留在“寻找90后的韩寒郭敬明!”的窠臼中。或许对媒体和公众来说,“80后”留下的印记太过深刻,一时之间恐怕很难忘却。再加上人们在识别一个新事物时一种惰性心理在作祟,会依赖于对既有的知识和经验进行惯性的连接,从而导致对事物的标签化现象。
云南90后女孩李涵淞,诗歌带着一种边地的热烈和孤癖杂糅的气质,坚硬生疼的语言将这一代人内心暗处的渴望刺破。富有异禀的《孤决》追求着大气之悲与细碎柔美两种风格。
宋耀良在1982年《人才》第11期写过《文学创作的最佳年龄》,其结论是:“一个作家往往需要十年左右的创作准备期,才能达到他的创作高潮和顶峰。”视之当下的云南,90后作家中尚未能够在文学界产生足够影响力的重量级作品出现,他们需要的是更长的时间以及更多的阅历来使得自身有所沉淀,而产生质变。我们要做的,也不仅仅是夹杂期盼的等候,更应该是主观上对当下这个时代里文学环境进行反省,探讨,批评。一直到90后作家的作品能够凭借其自身的文学实力而步入图书出版业的主流。
这是个现实,年轻是他们的资本,未来也由他们把握,但要想集体爆发,仍需磨炼和沉淀。明媚文字下的寂寥,恰如风华青春,艳丽中带点凄清。
三
每个时代会有不同意味的诗歌,因为时光给人同样思考的权利和机会,而思考的结果的不同源自各个代际的写作者有着迥异的生存境遇。挣扎在现实和理想之间,是每一代作家的心灵困境,也是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
让人欣慰的是云南青年作家对纯正文学立场和高贵文学理想的坚守,对艺术个性、原创性、思想深度的持续追求。在这座由26个民族环绕的清亮高原上,从来就不缺少文学的灵魂歌手,前面介绍的只是他们中的一部分 ,还有同样出色的他们:写入中国作协2014年度“白皮书”的“云南青年诗人群”,除前面提到的诗人,还有泉溪、芒原、吴佳琼、祝立根、老六、胡正刚、张伟锋、哥舒白、杨红旗和艾傈木诺等诗人;获第十届骏马奖的傈僳族诗人李贵明、获边疆文学奖的藏族作家央金拉姆、获滇池文学奖的诗人铁柔、博士诗人符二、获“2014年度华文青年诗人奖”的冯娜、彝族诗人李玉超,新锐诗人杨碧薇、“文学之新”李茜、布朗族“90后”诗人郭应国、高中生诗人李空吟······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云南文学的青年写作是一个不断惊喜绽放的存在。
每一个时代都会寻找属于自己历史和生活的最好书写者,作为候选者和预定代言人,青年作家们必须把自己的生活和更多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在全球化语境下成长起来的一批年轻作家,不应过分的陶醉于当下的感性欲望的潮流中,应寻找灵魂栖居的精神家园,思索新的精神生长点。对于日常经验深度和多元意义的发掘,对于现代人个体灵魂的审视和反省,对自我、他者和整体性社会经验的整合,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进一步反思,以及如何以一种世界视野在自己的作品中灌注更多的自主意识,并积极寻求新的文本叙述方式和表达形式。这些都是青年作家可以思考的层面和拓展的空间。
对于云南当代作家尤其是年轻作家而言,要在绵延的文学链条上获得自己的位置,就应该具备尼采所说的重新发现历史的能力。我们不要局限于“躲进小楼成一统”的闭塞,而是“常怀千岁忧”的担当,开放包容的博大情怀。将文学的“代数与火”(博尔赫斯语)完美结合,真正实现文学作品结构的精巧和触动人们情感的因素的双剑合璧。
在浩如烟海的人群之中,如何才能让一个微小的个人可以通过自己一己之力绽放绚烂的文学才华呢,平台的搭建是有益也是必要的。不过,媒体在这其间的引导作用和社会责任应当是要强调的,韩寒《他的国》中左小龙那样的悲剧原本是可以预防和避免的,这也是大众传媒时代,媒体和公众要一同面临和必须具备的媒介素养。
当然,云南当代文学批评家应当主动承担自己的职责,在一个更广阔的文学场域内持续观照当下青年人的文学创作与文学现象。除了登上主流媒体为青年作家的发展提供宽容空间而大声疾呼,也要发表文章竭力引导公众对青年作家和作品作有效关注。能身处文学的现场,在市场化的一片芜杂当中仔细分辨那些向上成长的创造力。让不同代际、不同群体的人都能在中国当代文学场域内获得发声的机会。
云南当代青年作家心智早熟,一直做着文学的梦,并在抵达灵魂的旅途已经摒弃了雕琢粉饰,自怨自艾的小情致,而不乏带着那么点凌厉和荆棘。虽然,他们的作品还时显稚嫩,作品的语言和技巧还不很娴熟,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文学殿堂执着的信徒,在不远的将来,是一定能够抵达庄严的圣地的。
(作者系昭通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杨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