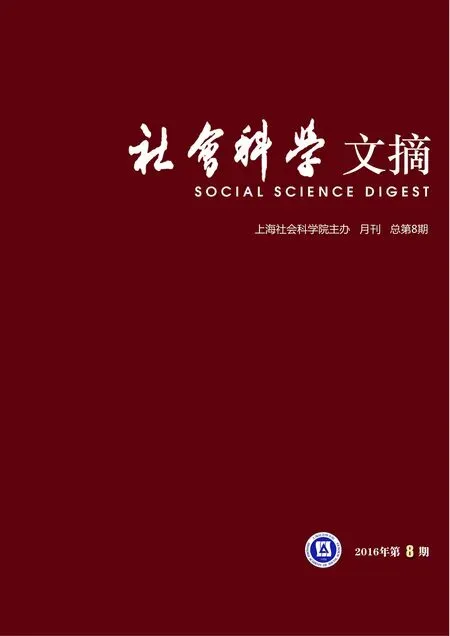《制止核恐怖行为国际公约》与我国相关立法的协调研究
2016-11-25王文华
文/王文华
《制止核恐怖行为国际公约》与我国相关立法的协调研究
文/王文华
国际公约对核恐怖犯罪的规定
2015年7月13日施行的《国家安全法》第31条规定:“国家坚持和平利用核能和核技术,加强国际合作,防止核扩散,完善防扩散机制,加强对核设施、核材料、核活动和核废料处置的安全管理、监管和保护,加强核事故应急体系和应急能力建设,防止、控制和消除核事故对公民生命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危害,不断增强有效应对和防范核威胁、核攻击的能力。”
核恐怖主义是最大的核威胁,它是指国际恐怖分子利用核扩散从事恐怖活动。198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Convention on the Physical Protection of Nuclear Material, “CPPNM”)于1987年2月8日生效。“9·11”事件后,国际社会面临的核恐怖主义的威胁加剧。2005年4月13日,第59届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的修正案——《制止核恐怖行为国际公约》(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Suppression of Acts of Nuclear Terrorism, “NTC”,以下简称《公约》)。这是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13项反恐公约,也是第一项明确旨在打击核恐怖主义罪行的国际公约,该公约于2007年7月7日生效。目前已经有99个国家批准、16个国家签署了该公约。我国于2005年9月14日签署,2010年8月28日批准了该公约,同时也声明对有些条款作了一些保留。
《公约》由序言和28条正文组成,对“放射性材料”“核材料”“核设施”等术语进行了界定,并要求缔约国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将核恐怖主义行为规定为刑事犯罪,规定各缔约国应当开展引渡和刑事司法协助等司法合作,共同打击核恐怖主义犯罪,同时对以收缴等方式获得的放射性材料、核设施或者装置的保管、储存和归还作了具体规定。
《公约》第2条规定,“核恐怖犯罪”是指任何人以制造伤亡、损坏财产或破坏环境为目的,拥有或使用放射性物质或放射性装置的行为。此外,破坏民用和军用核设施,或威胁使用放射性物质或核装置的行为,也属于核恐怖犯罪。《公约》规定的核恐怖犯罪行为主要为3大类:一是以危害人、财产和环境为目的,拥有放射性物质或核装置;二是出于同样目的,使用放射性物质、核装置或破坏核设施;三是为达到这些目的,威胁使用或企图拥有放射性物质和核装置。
《公约》第5条要求,各缔约国应酌情采取必要措施,在国内法中将第2条所述犯罪定为刑事犯罪,并根据这些犯罪的严重性质规定适当的刑罚。对于第1、2项,即使未遂也构成犯罪。此外,上述行为的组织、教唆、帮助行为也构成犯罪。在程序上,对于涉嫌制造核恐怖行为的个人,各国政府必须起诉或将其引渡到别国受审。各国应该为打击核恐怖行为加强情报交流,并加强对本国放射性物质的监管。
我国刑法有关惩处核恐怖犯罪的规定
我国一向重视履行包括国际安全在内的各项国际义务,对所批准或签署的公约严格遵循“条约必须遵守”的原则。从罪名设置看,我国刑法涉及或包含核材料作为犯罪对象在内的罪名,主要规定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只有走私核材料罪规定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2001年12月29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三)》对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有关条文进行了补充修改,其中与核恐怖相关的有:(1)将刑法中原有的投毒罪修改为投放危险物质罪、过失投毒罪修改为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2)对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的犯罪人根据他们在犯罪中各自所起的作用分为3个层次,分别规定了不同的法定刑;(3)将非法买卖、运输核材料罪修改为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4)将洗钱罪的犯罪对象由修改前的3种扩大为现在的4种,即在保留了原有的犯罪对象基础上又把“恐怖活动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作为洗钱罪的犯罪对象;(5)将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罪修改为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6)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修改为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7)增设了3个有关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新罪名:资助恐怖活动罪、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此外,《刑法》第151条第1款“走私核材料罪”、第130条“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危险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第136条“危险物品肇事罪”、第338条“污染环境罪”、《刑法修正案(九)》第120条之二增设的“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等罪尽管本身不属于核恐怖犯罪,然而,由于犯罪对象包括核材料,在研究核恐怖犯罪时,也应当对这些罪名给予高度关注,以利于刑法的整体协调。
刑法修正案(九)对第151条第1款“走私核材料罪”取消了死刑的规定。核走私主要指的是走私可制造核弹的主要材料——铀和钚。走私核材料罪本身不必然是恐怖犯罪,但是可能会被恐怖组织、恐怖分子所利用、对公共安全造成很大威胁,然而该罪首先是侵犯经济秩序的犯罪,即使危及公共安全,也只是造成公共安全的危险,属于危险犯而非实害犯,因此,不能因为对恐怖犯罪的恐惧而将恐怖犯罪泛化、将与恐怖犯罪可能有关联的犯罪都予以严惩。
进一步与《公约》相协调,强化刑法的预防犯罪功能
(一)增设“非法持有核材料罪”或“非法持有危险物质罪”。从刑事政策角度出发,对核恐怖犯罪的治理同样需要“严而不厉”——严密法网、全面构筑刑法防线、增加前端、上游犯罪的规定,不可一味依赖死刑。未来可以考虑在《刑法》第130条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危险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刑法修正案(九)》第120条之二增设的“为实施恐怖活动准备凶器、危险物品或者其他工具罪”以外,增设“非法持有核材料罪”或“非法持有危险物品罪”。因为前者需要证明非法携带危险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情节严重的行为,或者需要证明行为人具有“为实施恐怖活动”的目的,而涉核材料的犯罪因其极大的危险性,需在罪名设计时考虑到降低司法证明的难度,将刑法的防线提前,严密对涉核材料犯罪的刑法规制,强化刑法的预防犯罪功能。况且,刑法第128条第1款早就规定了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刑事立法的逻辑是——出罪“举重以明轻”,入罪则应当“举轻以明重”。那么,在核恐怖已引起世界各国高度警惕的今天,增设“非法持有核材料罪”就有很大的必要性。
(二)增设危害“核装置”的相关罪名。《公约》第2条规定的“核恐怖犯罪”的3大种类所指向的犯罪对象都是“放射性物质和核装置”,因为“核装置”是制造原子弹、氢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必需。我国《刑法》第2章、第3章、第6章的涉核罪名都不包括核装置,有关“危险物质”“危险物品”“有害物质”等犯罪对象的罪名,其实都只包括核材料等放射性材料,并不包括核装置,只有在第7章危害国防利益罪中涉及“武器装备”的几个罪名中包括核装置,显然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主观方面都受到很大限制,难以有效规制涉及核装置的核恐怖主义犯罪。建议未来可以考虑在刑法第2章增设危害“核装置”的相关罪名。
(三)将核恐怖犯罪列入“国际犯罪”,专章加以规定。联合国先后制定的反恐13个公约充分说明,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所普遍关注、重点预防和打击的犯罪。例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2编将本属于国际犯罪的“破坏人类和平和安全的犯罪”作为独立的一编加以规定,该编第355条为“研制、生产、储存、购买或销售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罪”。实践中,恐怖犯罪越来越呈现出跨国、有组织等特点,犯罪主体、犯罪手段、犯罪后果常常具有国际性。在理论上,恐怖主义更是早就被视为国际犯罪的一种,因为它“违背人类基本价值”,“震撼人类的良知”。未来我国有必要考虑:一是单设“国际犯罪”一章;二是将核恐怖犯罪列入其中,突出对其严重的谴责性、否定性评价。
(四)取消“运输、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的死刑。《刑法修正案(九)》取消了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的死刑,考虑刑法典的整体协调性,未来还应考虑取消《刑法》第125条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中的“运输、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的死刑,因为其危害性与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相当——“运输”是在一国境内运输,“走私”是跨越国境或者在界河、海、湖泊运输。简言之,走私的本质就是逃避海关监管的“跨境运输”。同时,“储存”的危害性也并不大于“走私”或“运输”。也可以说,走私的危害一般大于运输、储存。那么,既然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都已经取消死刑,那么运输、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自然应当取消死刑。
《公约》与我国其他法律的协调
我国新颁布的《国家安全法》、《反恐怖主义法》以及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反洗钱法》、《人民武装警察法》都在基本面上与《公约》协调对接。然而,在实体、程序上仍需要对核恐怖作出更为专门、专业的系统规定,逐步形成更完备、全面、深入的核反恐法律体系,有效促进我国在反核恐怖犯罪方面与《公约》的协调对接。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摘自《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