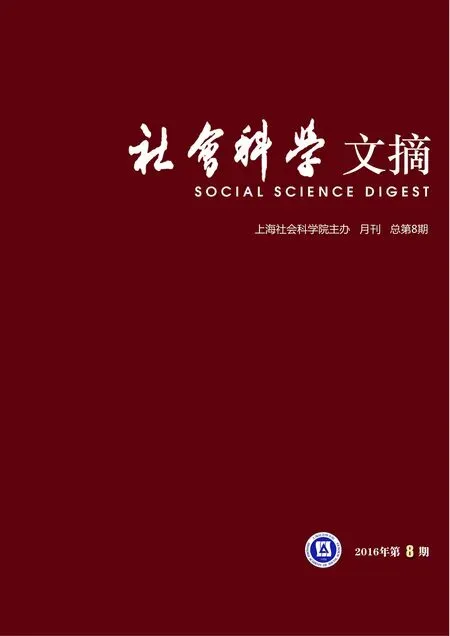政府信息公开的宪法逻辑
2016-11-25秦小建
文/秦小建
政府信息公开的宪法逻辑
文/秦小建
在宪法体制的组织和运行逻辑下,政府信息公开不能为一个单维度的“政府—公民”关系所涵括,公民知情权所对应的“国家”义务,也不能被狭隘地理解成“政府”的公开义务。同时,“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限制性框架,只能置于宪法体制的组织和运行逻辑中,结合各个国家机构与公民的关系进行具体化的理解。否则,这一原则及对应的政府公开义务就是空洞的,空洞的原则当然无法约束政府。宪法体制的组织和运行逻辑,决定了信息公开国家义务的具体类型和体系结构。只有在此视野下,才可领会以公民知情权为基础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所具有的重大宪法功能,而不是局限于一种以公开促进自我规约的狭窄认知。
主权逻辑与治理逻辑
依据《宪法》第2条、第3条、第三章,宪法体制的组织和运行逻辑以公式表达为“人民—人大—国家机构(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公民”。“人民—人大—国家机构”是主权逻辑的彰显,“国家机构—公民”是治理逻辑的体现。二者耦合成我国宪法实施的两个互动层次。其一,基于人民主权,作为主权者的人民选举产生权力机关,产生国家机构,并制定法律,从而组织和规范国家的整体运行。主权逻辑构造了国家的主权结构,这一主权结构,既保证主权权威的恒在,又以制度化的方式抑制主权者出场所不可避免的无序和激情。其二,包括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在内的国家机构在主权逻辑构建的宪法体制中各司其职,遵守和适用法律,以强制性的权力为保障,通过授予权利、赋予义务具体调整个体公民之间、个体公民与国家机构之间产生的法律关系。所谓治理逻辑,是通过法律的宪法实施,即由人大产生的国家机构遵守和适用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实现人民意志。主权逻辑为治理逻辑输送正当性,治理逻辑为主权逻辑实现价值理性。
在这一宪法逻辑中,政府承担的信息公开义务可对应分解为两个层次。一是在“人民—人大—政府”的主权逻辑下,政府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向人大报告工作。据此,政府应当向人大主动报告信息,而人大作为人民意志的代议机构,有权代表人民要求政府公开社会大众所普遍关注的信息。二是在“政府—公民”的治理逻辑下,政府因职权行使与公民形成行政法关系,公民的权利义务因此受到影响,行政行为与公民个体之间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利害关系。此时,遵循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要求,有关行政行为的信息,应当向公民公开,公民亦有权向行政机关申请公开。依据宪法体制的职权配置关系,如果政府公开义务存在偏差,那么公民有权向上级政府举报、申请行政复议,并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两种逻辑的混淆及其后果
现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赖以建构的“知情权—政府信息公开义务”逻辑,混淆了作为主权者的“人民”与作为政府治理相对方的“公民”,因而也混淆了有关宪法体制组织和运行的“人民—人大—政府”之主权逻辑与“政府—公民”之治理逻辑。
这一混淆,漠视了“人民—人大—政府”的主权逻辑,忽略了政府与作为权力机关的人大在信息公开领域的职权关系及义务配置,致使现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与整体宪法体制相脱节,难以形成制度合力。同时,由于无法受到宪法体制的有效规约,政府的信息公开职权极易僭越宪法体制的职权配置,违反国家机构分工原理。其后果是,既可能因其职权所限而无力满足民众信息需求,也可能因越权而陷入恣意,更可能将蕴含于分工背后的制约和监督消解于无形。
这一混淆,还为本不应在代议政治中直接出场的“人民”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使得“人民”超越人大而直接与政府形成关联,从而与主权逻辑相抵牾。由于缺乏代议制的整合和过滤,有关信息公开的“民意”在“沉默的大多数”的映衬下,本源是少数群体和精英阶层诉诸抽象的“人民”概念所进行的单方面“加工包装”,看上去拥有强大的道义力量,实则难以将多元认知下的分散民意诉求汇聚成绝大多数所认可的体制性共识,更无法转换成实质性的制度压力,自然难以有效施压政府。与此同时,忽略代议渠道而动辄诉诸主权者的民意号召,常常掺杂着民粹倾向的非理性指责,掷地有声的建设性讨论和诉求主张淹没其间。加之政府治理(尤其是基层)受制于压力机制而难以保持常规化运作,信息公开底气本就不足,民意回应体制还不健全,正常的民意表达和沟通交流管道由此不断窄化。以主权者身份自居所发出的指责,一旦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宽容和理解丧失了土壤,交流和沟通没有了意义,结果被提前预设,本意在于强化沟通的公开不免演化为情绪化的对立。
这一混淆,还干扰影响了治理逻辑下“政府—公民”的知情权实现,而这恰恰是公民需求最为迫切、利益关联也是最为直接的方面。由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下称《条例》) 对主权逻辑和治理逻辑的混淆,没有意识到不同逻辑下信息所具有的不同性质及其功能,也无法体会到不同性质的信息对不同逻辑下的公民的不同意义,因此没有设置有针对性的制度对其予以区分。而笼统的公开义务,虽增大了那些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获取信息的机会,但降低了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获取相关信息的公开强度,乃至于发生错位,冲淡了直接利害关系背后的合法性关联,使得那些关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信息,得以借助《条例》中有关例外事项不公开的制度管道从容规避。当下土地规划开发项目中涉关公民利益的信息公开不足,很大程度上正是利用此种混淆获得极大的义务豁免空间。
这一混淆,还可解释当下行政诉讼针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救济实效不足的困境。行政诉讼是宪法在治理逻辑下对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监督的制度设置,它理所当然地遵循与治理逻辑相对应的以直接利害关系为基础的合法性审查模式。仅仅通过人为主观定性,就将某个与公民无直接利害关系的行为认定为具体行政行为,实际上等同于将主权逻辑硬性塞入治理逻辑,行政诉讼无法接纳,基于“特殊需要”的不设限申请模式和泛化的知情权需要,遭遇了行政诉讼围绕“法律上直接利害关系”的合法性审查框架的抵抗。
政府信息公开是防范行政专断的一种具体方式,可谓扣在政府头上的“紧箍咒”。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兼具议会控制与公民参与两大制度方案,既基于主权逻辑向代议机构报告工作,接受代议机构监督,又顺应治理逻辑下的公民知情权诉求履行公开义务。二者本应有序分工,协调并致。然而,我国的这一制度设计,却人为割裂了上述逻辑关联。《条例》一方面通过自我立法全然超脱人大控制,无视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的既定人大体制安排;另一方面则曲解了行政过程中公众参与的应有定位,透射出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合法性悖论”:以鼓励公众参与为初衷的政府信息公开,本意在于矫正行政过程的“民主赤字”,但由于与作为正当性来源的主权逻辑的自我割裂,以及自身的运作偏差,陷入一种更深刻的合法性危机中。
对应制度构造
有鉴于此,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应当回归宪法体制的运作逻辑,分别对应“人民—人大—政府”的主权逻辑和“政府—公民”的治理逻辑进行制度化构造,实现其在宪法体制中的特殊价值和功能承担。
基于主权逻辑,对于那些与公民个体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信息,政府信息公开的首要维度是向人大公开,而人大作为人民的意志代表,经过是否属于“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权衡之后,向人民公开。这一方式,可借助于人大权威回应实践中以“公共利益”为由的义务规避困境。另一方面,在“政府—公民”治理逻辑中,区分直接利害关联的三层次,确证信息与公民个体的利益关联程度,据此分别构建公开模式。具言之,在基于“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具体行政行为下,信息是行政主体做出行政行为的基本依据,直接关系到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基于正当程序原则,行政行为的所有信息应当全部向行政相对人公开,至于其中可能存在的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问题,应当通过《保守国家秘密法》《档案法》及相关保密协议等配套制度予以解决。在基于“大范围法律上利害关系聚集并与公共利益共存”的土地规划开发等职权行为下,涉及行为合法性的信息也应完全公开,但如与公共利益形成冲突,应对接主权逻辑交由人大平衡。在基于“公共利益的反射关系”的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监管、产品质量监管等情形下,如反射关系可落实至特定时空的公民个体,则采取“聚合型法律上利害关系与公共利益并存”模式;如不能落实到公民个体,则回归主权逻辑的公开模式,并在治理逻辑下借鉴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模式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申请。
现行《条例》作为行政法规,是行政机关为执行法律规定或履行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事项而制定的,尚可对应于传统的以公开促进规范的制度定位。然而,作为行政法规的《条例》显然无法包容主权逻辑,因为这一关系已经涉及宪法体制安排。并且,公民知情权与政治权利的密切关联,决定了以行政法规作为规范载体,不符合法律保留原则。此时,有必要向作为宪法性法律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升级。但需要补充的是,如果没有特别的需要,其实并没有必要专门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来规范这一关系,因为在既有的组织法体系和《监督法》中,已经对这一关系做出了具体的制度安排。尤其是《监督法》规定的专项工作报告制度,实际上就是这一逻辑的制度化表达。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摘自《中国法学》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