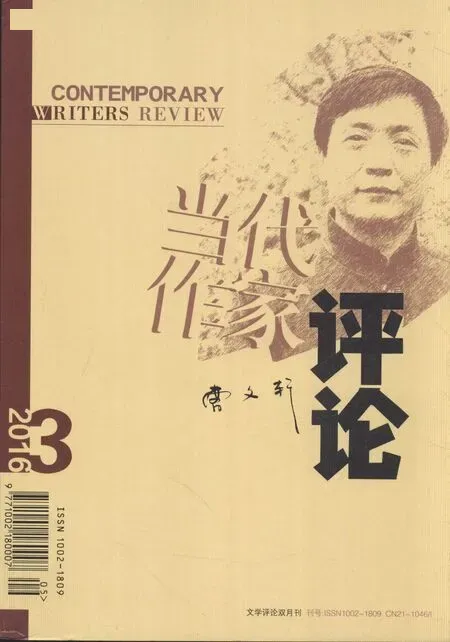陈超与海子诗歌死亡意识之比较
2016-11-25段曦
段 曦
诗歌研究
陈超与海子诗歌死亡意识之比较
段曦
死亡是海子诗歌的核心主题,据西渡统计“‘死’在《海子诗全编》中出现五百四十八次”,*西渡:《灵魂的构造——骆一禾、海子诗歌时间主题与死亡主题研究》,《江汉学术》2013年10月,第32卷,第5期。海子对死亡的倾心自不必说,其前期诗歌中的死亡往往带有一种独特的美感与诗意。纵观陈超的诗歌作品,“不少诗作均藏有或浓或淡的死亡情结与或强或弱的死亡意识”,*谭五昌:《陈超:死亡幻象的审美书写与精神超越——对陈超诗作〈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的解读与阐释》,《文艺争鸣》2015年第1期。尤其是八九十年代的作品中死亡经常出现,这些死亡诗充分体现了诗人精神上的高蹈。相比海子对死亡作更多形而上的思考,陈超涉及死亡主题的作品类型更加丰富,既有对死亡的理性思考,也有富于日常纹理的生活化书写。陈超与海子的诗歌创作都始于八十年代(陈超于一九七九年开始写诗,海子从一九八二年左右开始写诗),他们年纪相仿(陈超比海子大六岁),两人都有着大学毕业后留在高校任教的经历。二者的诗歌中明显存留着属于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情怀,字里行间都充溢着对诗歌的无限深情与热爱。
自从海子离世,他的诗歌就一直受到自杀的影响与干扰,常有论者由海子的死逆推其诗歌,以诗人之死验证诗歌,对此陈超提出应该直接面对诗人提供的文本世界,“这不仅是对诗人对文本的尊重,也是对诗人个人秘密的尊重”。*陈超:《海子论》,《文艺争鸣》2007年第10期。如今本文讨论二者的死亡意识更应如此,关注文本,理解诗人所构筑的诗歌世界,这是对诗人的尊重,尤其陈超生前尤为看重自己的诗人身份,但他的诗歌才华常被卓著的诗歌评论成就所遮蔽,其诗论家的身份较之诗人更为学界所熟知。再者,诗人在诗歌中谈论死亡,更多的是对有限生命的自我思考及以死亡意象完成对该思考的审美表达,并非把死亡作为一种实际行动付诸实践。
陈超与海子都以死亡观照世界,观照个体的存在,将二者诗歌作品中的死亡意识作比较,不难发现他们都直面死亡,海子笔下的死亡是个性化的审美书写,既有对死亡不遗余力的赞美,亦有激烈的形上思辨,而陈超对死亡的认识更趋于冷静客观。陈超与海子都不惧怕死亡,在陈超的诗歌中,可以为了诗歌为了理想而死,这种精神向度上的超越,于海子诗歌中也处处可见。由于海子对死亡的亲近,他视死如归,陈超则以诗歌为信念向死亡宣战。
一
陈超说:“讴歌死亡的诗人,不一定受动于自毁激情,恰好相反,他祈祷的是烈火中钢的轮回。”*陈超:《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第177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这种精神上的高蹈与超越,让陈超发出“让一个书呆子同命运交锋!”的宣言(《博物馆或火焰》),他还写道:“从未有过自杀念头的人是颓废的也是可怕的人”(《流水38行:愚人初级读物》)。诗人看似轻松的语气,却是真正对人生的有限性与无限性展开思考,恰如诗人自述:“我的每一个句子想说什么是很清楚的。”*陈超:《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第38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所谓自杀的念头并非平日里因为烦闷、苦恼而发出“想死”之类的抱怨与牢骚,而是对个体生命有限性的自我意识,在当下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强迫自己忘记人的生命会中止这一事实,有些人,连一分钟都没活过”,*格非:《春尽江南》,第199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生活的重压使得被物化的人眼里只有实利,他们拼命生存,奋力拼搏,内心却一片浑浑噩噩,这如同行尸走肉般的人生,难道不可怕?同样可怕的是对死亡避而不谈、不想,选择自我逃避,沉溺在日常生活中渐渐麻木,不愿意面对终有一死的真相。自杀对人而言是可以自己决定生命终止的时刻,这使人超出了动物的受动状态,“这种能力演绎成了人的意志力的最高表现”,人意志力所依据的信念“为个体的人生提供了世界的某种意义,这些意义最终决定着人的生死存亡”。*刘小枫:《拯救与逍遥》,第44、45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对陈超而言,这信念就是诗歌,“诗就是信仰”(《马拉美,水波》),“诗是语言的金链,会代代相传”(《青铜墓地》),“诗歌以雪的方式超越杀戮,她们清澈,陈静/普照事物在冬天的根”(《荷尔德林,雪》)。诗歌以语言的力量重新建构了世界的意义,陈超正是在此基础上针对“死亡”所带来的虚无感,提出“诗歌不死”的信念,探索人生的有效性与无效性。
陈超自觉而强烈的死亡意识集中体现在长诗《青铜墓地》中,该诗由“序曲”、“第一歌:我说”、“第二歌:众诗人亡灵的话”、“第三歌:合唱”及“尾声”形成多声部结构,自《第一歌》开始,每一章的最后一节采用整齐划一的形式,着重体现了诗人对死亡的诗性思考的逐渐展开与深入:
烘炉默默奔流,地轴款款转动
活着看见死亡后,死亡是否不像是死亡
……
烘炉默默奔流,地轴款款转动
诗歌深入死亡后,死亡已不能再重复死亡
……
烘炉默默奔流,地轴款款转动
诗歌一息尚存,死亡已不再骇怖
……
江河汹涌奔流,地轴隆隆转动
我们穿越死亡后,死亡是一个人生还的起点
在陈超看来,死亡不可避免,即便是被耶稣复活的“拉撒路先生”现在“也不能跃出/青铜墓地”。人纵使有着“活着的欲望”,最终还是要面对“医院的白墙”。陈超是主动思考死亡的,“活着看见死亡后,死亡是否不像是死亡”,他从死亡的角度出发,即“站在生者的反面来观照世界,这种意识使他的诗篇厚重而有风骨”。*刘涛:《时间的重负与自我心灵影像的回放——读陈超的诗》,《西部》2015年第11期。陈超自觉的死亡意识,不仅仅是对死亡的客观承认,更是对死亡发出“而死亡也不得统治万物”的宣言,陈超引用了英国诗人狄兰·托马斯的诗句,这是一种向死亡宣战的态度,他告诉世人“这才是为诗者对死亡高傲的寓言”,“比青铜刀锋更犀利的/不是肉身而是诗魂”。即使死亡意味着肉体的消失,但诗歌的精神会一直延续下去,因此死亡“不再骇怖”,甚至成为“新价值的起点”。死亡意识促使人的价值意识觉醒,死亡使人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并促使人主动创造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人选择了诗歌,不论是死亡还是“生存的乌云”都不能阻止抑或控制“诗歌自由的暴雨”,诗歌向诗人敞开了一扇大门,诗歌既是诗人获得价值与存在的方式,也使得诗人自身获得了无限发展与可能性。
同时,诗人在此承认了死亡的“骇怖”,这是人类面对死亡的正常心理,但诗人并未选择逃避,而是直面死亡,积极地思考生与死,并意图超越死亡。诗歌正是其所选择的超越方式,当“诗歌深入死亡后”,诗人所看重的“生死转换”的主题,即“生命轮回的死亡和死亡轮回新生命的胜利”成为可能。因着“诗歌的金链一代代承传”,亦因着“死亡不能结束的东西”还可以“留给诗歌的镇守去生长”,诗歌战胜了死亡的骇怖,超越了死亡留下的虚无,“不死的诗魂”成为一代代诗人坚定的信念和信仰,“人类诗歌共同体”在象征着死亡的墓地上空“亲睦地闪耀在一起”。在这里,诗歌“不可抗拒”,也“没有什么力量能让它返回死亡本身”。在诗人看来,诗歌使人获得了生存的意义,并创造了一种永恒价值,这种价值排除了死亡的影响,也赋予了个体生命一种永恒性。诗人指出“是死亡之手/在赐予生命”,当我们以诗歌的方式“穿越死亡后,死亡是一个人生还的起点”。这种对生与死的转换与交替的思考与浪漫派诗哲是一致的,即“只有在生与死的永恒交替中,才有不断超升的生的永恒之流”。*刘小枫:《诗化哲学》,第250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生与死的创造性关系在于,死是生的前提,死也同时为生的超越提供了可能。
《青铜墓地》一诗在标题之下引用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名言,“先行到死亡中去”,以及英国诗人迪兰·托马斯《我梦见我的创生》中的诗句:,“在死亡的大汗中我梦见我的创生”,已然预示着这是一首“向死而生的诗,是通过诗歌穿越死亡并使得死亡得以重生的哀歌”。陈超认为“这是自己第一首充满了光明的诗篇,而它却是地狱的赐予”,*霍俊明:《“梦有故人来”:诗人陈超》,见陈超:《无端泪涌》,第8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光明由地狱/黑暗赐予,这个悖论其实诗人在诗中就已提出:“心灵的丰稔不正是来源于永劫轮回的黑暗之途?”恰如靡菲斯特说自己是产生光明的黑暗,诗人得到光明的启示也来自于对黑暗,即对死亡的严肃思考。同样的悖论也存在于海德格尔的死亡哲学中,“死亡是黑暗,然而它却是给此在之存在以光明、给此在之存在以意义的黑暗”,*段德智:《西方死亡哲学》,第24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这是海德格尔重视死亡问题的缘由,也是众多诗人关注死亡的原因。
陈超对死亡的自觉思考是从人文精神的角度出发,寻求一种精神向度上的超越,他肯定了诗歌及诗歌精神在这个时代的价值和意义,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对个体对时代的关注。面对自九十年代开始的商品经济大潮,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的甚嚣尘上,陈超讽刺道:“这个时代不屑原谅落伍者”,“‘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有钱就不怕谁’/请听广场上欲望和利润在吹哨”(《凸透镜中两个时代的对称》)。他喜爱自然与乡村,认为城市充满了“令人讨厌的贪婪、算计”(《登山记》)。面对不可阻挡的现代化趋势,陈超充满冷静与反思,坚守着心中的诗歌理想:“实用时代一个人还写诗,就不失可爱。/请相信我们那时鄙薄过世俗的名利之心。”(《“所有朋友都如此怪僻”》)在诗歌中他反复怀念着一切“老派”、“老式”的事物,怀念着“逝去的年代”、“充满活力的八十年代”,因此,陈超诗歌中的死亡还暗示着一个理想主义时代的结束:“博物馆在夕光中倒影渐行渐远——/一个时代的眼睫缓缓合上……”(《博物馆或火焰》)诗人对逝去时代的怀念也深深饱含着对人文精神消亡的忧虑,作为“旧时代的幸存者”,一个与命运交锋的“书呆子”,他对精神的坚守,即体现为对诗歌的坚守,惟有诗歌让他的内心充实。诗歌是他的理想,为了诗歌他甘愿牺牲,乐于赴死:“诗歌的叶脉在祖国的晨空伸展/他甘愿以热血灌溉沙原”(《飞翔》),“桃花刚刚整理好衣冠,就面临了死亡;/为了理想他乐于再次去死,/这同样是预料之中的事”(《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这种为理想而死的气魄,既体现出陈超死亡意识中注重个体选择的倾向,更彰显了诗人固有的心灵深度与精神高度,正如诗人自己所说:“你的心似乎没变,老派如既往模样。”(《停电之夜》)
值得一提的是,“书呆子”在陈超的诗歌中反复出现,“他”从“逃亡时/被踩碎的眼镜片在火灾反光中发抖、屈服”,逐渐“挥别青春/是因为一个中年人的知性/已变为平稳墨迹的持久阵痛”(《艺徒或与火焰赛跑者之歌》)。当陈超写下“岁月的流逝已教会我平静地面对写作的,无用”、“书呆子巨大的奢侈。柔情侠骨两消融/我不可能生在一个比诗歌无用的时代更美好的时代!”(《天道远,吾道弥》)我们看到诗人与世界的和解,然而字里行间那股无以名状的心酸却又久久不能消散。诗歌,或者说诗歌精神,一直是陈超抒情的对象,他恰如“乌托邦最后的守护者”,守护着关于诗歌与理想的家园,“我热爱在希望和流血中轮回的精神/对于乌托邦贫困的留守者/纯洁的写作是恰如其分的财富”(《飞翔》)。对精神乌托邦的坚守,很大程度上构成了陈超诗歌中死亡意识产生的深层动因。
在陈超的诗歌作品中,对死亡的书写既有如《青铜墓地》、《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等直接进入精神世界的探索,亦有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的有感而发,如《与西西逆风骑车经过玉米田》,诗人看到“金红头发童子军在风中集合/绿领带系得潦草而飘逸/腰身一齐弯向东方/金子的心,无辜闪亮”,突然“想加入这单纯的绿色集体!/谢谢天,一切最终都会如愿/拜托你那时将我撒入这绿吸墨纸的大地”,诗人对自然对大地的喜爱由此可见一斑,陈超对死亡如此淡然写意的感觉,更体现了诗人看待死亡的平常心态。又如《沉哀》一诗,诗人悼念英年早逝的友人,然而整首诗并没有过分外显的悲伤,诗人平淡地写道:“太阳照耀着好人也照耀着坏人”,“从吊唁厅到火化室大约十步/太阳最后照耀着他,一分钟”。诗人看待死亡是冷静而客观的,既没有将死亡任意地夸大,也没有把沉重的心情肆意抒发,在诗人看来,死亡是一件极其正常的事,有生便有死,就如太阳一如既往地照耀着,世上的死亡也一如既往地发生,恰恰是这种平常的语气,却举重若轻般地把“沉哀”凸显了出来。陈超另一些涉及死亡的作品,如《夜和花影》、《早餐》等,则是由回忆入手,把对往昔时光的怀念抒发得淋漓尽致,死亡作为抒情背景中的一部分融入了诗人的脉脉温情之中,重新唤醒了记忆的力量,极易使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这也是陈超抒情的成功之处。
二
相较于陈超看待死亡的冷静与客观,海子对死亡则充满向往。在《春天,十个海子》一诗中,海子如此写道:“这是一个黑夜的孩子,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不能自拔,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的确,黑夜、死亡和乡村在海子诗歌中大量出现,尤其是死亡,在海子二百余首抒情短诗中,涉及死亡的诗作约有七十首,长诗中的死亡书写与思考则更为集中。海子对死亡的倾心,仿佛将死亡变为一种与生俱来的抒情方式,无论面对任何抒情对象,海子都能以死亡呈现出别致的诗意。因此在海子笔下,尸体、棺材、骨头等与死亡相关的意象也被赋予独特的美感,如“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是我的棺材,我是你的棺材”(《葡萄园之西的话语》)、“美丽在水里/鱼是草的棺材”〔《燕子和蛇(组诗)》〕、“我的自由的尸体在山上将我遮盖 放出花朵的/羞涩香味”(《在家乡》)等。即使名为《爱情诗集》,而海子写的却是:“坐在烛台上/我是一只花圈/想着另一只花圈/不知道何时献上/不知道怎样安放”,死亡依旧出现在海子抒写爱情的情思中,烛台与花圈是祭奠时的常见物,在这里,海子敏锐地洞察到死亡与爱情之间的某种内在一致性,即不确定性。人终将面临死亡,但并不能确切地预知死亡到底在哪一天降临,爱情亦如此,人并不知道爱情会于何时何地发生,这种不确定性恰恰也是爱情神秘而美好的所在。
海子诗歌中有不少以死亡为主题的作品,如《死亡之诗(之一)》《死亡之诗(之二:采摘葵花)》《自杀者之歌》等,与普通人对死亡的惧怕和回避不同,海子对死亡感到亲近,他常在诗歌中想象死亡的降临:“有人在头顶扔下/一匹蓝色大马/就把我埋在/这匹蓝色大马里”(《春天(断片)》)、“请在麦地之中/清理好我的骨头/如一束芦花的骨头/把它装在琴箱里带回”(《莫扎特在〈安魂曲〉中说》)、“在七月我总能突然回到荒凉/赶上最后一次/我戴上帽子 穿上泳装 安静地死亡”(《七月的大海》)等。在海子早期的作品中,对于死亡的想象是轻松自在的,如《死亡之诗(之二:采摘葵花)》一诗,海子讲述梵高的自杀,将死神比喻为“雨夜偷牛的人”,死亡的过程则是被死神“采摘葵花”:“那双采摘的手/仍像葵花田中/美丽笨拙的鸽子”,整首诗的基调欢快明朗,不乏美好的感觉,这种美好与我们所能想到的死亡之诗大相径庭,海子这般歌唱道:“如果我死亡/我将明亮/我将鲜花怒放”(《太阳·土地篇》)。海子早期抒情短诗中书写死亡的轻松态度在之后的写作中逐渐产生一些变化,如《马雅可夫斯基自传》一诗已经显露出修辞的坚硬与形容的可怖:“在我弃绝生活的日子里/黑脑袋——杀死了我/以我血为生 背负冰凉斧刃/黑脑袋 长出一片胳膊/挥舞一片胳膊/露出一切牙齿、匕首”,直至一九八九年的晚期作品,如《春天》《月全食》《春天,十个海子》等诗,死亡的书写呈现为“鲜血淋淋”般猛烈而锐利的痛苦。总体而言,这种转变,与海子由“水”性进入“火”性,即进入《太阳·七部书》的写作有关,也显示出海子不同的人生境遇与心境的变化,海子的死亡观念有其复杂性,但他对死亡的热衷却从未改变。
海子并不是分离地看待死亡,事实上,在海子的诗歌中,生与死是同构的:“左边的侍女是生命/右边的侍女是死亡”(《抱着白虎走过海洋》)、“生命和死亡宁静的声音/我在倾听……不要说死亡的烛光何须倾倒/生命依旧生长在忧愁的河水上”(《月光》)、“大黑光啊,粗壮的少女/为何不露出笑容/代表死亡也代表新生”(《传说》)。在海子看来,死成为了生的前提,生是从死之中衍生出来的:“受孕也不是我一人的果实/实在需要死亡的配合”(《吊半坡并给擅入都市的农民》)、“死亡金色的林中我吹响生育之牛”、“尸体是泥土的再次开始”(《太阳·土地篇》)。海子受到藏传佛教轮回观念的影响很深:“这轮回/这在骨殖泥土上不断变换的生命”,“日夜的轮回/是我信奉的哲学”(《太阳·断头篇》)。海子认为“死就是生”(《太阳·断头篇》)、“死去多少回又重新诞生”、“一切都可以再生”(《但是水、水》)。因此,“死而复生”在海子的诗歌中十分常见。生与死的对称出现,生与死的轮回在《太阳·弑》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绿马:我是生育之马。
红马:我是死亡之马。
绿马:我很快就要衰老。
红马:我很快就要从火焰和灰烬中再生。
绿马:我是生命之马。
红马:我是超越生命之马。
海子坚信,死亡并非一种终结,死亡甚至是对生命的超越,他将死亡视为生命的延续,“我延长着死亡就是延长着生命”(《太阳·断头篇》),因此“我就是死亡和永生的少女”,“死亡之马”也是“永生之马”(《太阳·土地篇》)。海子倾心死亡,但海子也同样热爱生命,在《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一文中,海子说:“要热爱生命,要感谢生命。这生命既是无常的,也是神圣的。要虔诚。”生命的无常确定了死亡的存在,当海子写下“活在这珍贵的人间”时,他对生命的热爱与感恩是真诚的,只是当他吟咏生命中的美好时,也不忘与死亡携手,他说:“我无限地热爱着新的一日”,“幸福找到我”的时刻是“在劈开了我的秋天/在劈开了我的骨头的秋天”(《幸福的一日》),对他而言“死亡是一种幸福”(《太阳·弑》)。
死亡,或者说是死亡本能构成了海子思考世界的方式,海子将诗歌的形成也归于死亡的原始力量的催动:“泥土反复死亡 原始的力量反复死亡 却吐露了诗歌”、“土地的死亡力 迫害我 形成我的诗歌”、“土地的死亡力正是诗歌”(《太阳·土地篇》)。与其说死亡形成了他的诗歌,毋宁说死亡促进了海子自我意识的深度觉醒,这意味着诗人“将真正开始其精神受难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迸发“对人的生命存在的强烈的终极关怀意识”。*胡书庆:《大地情怀与形上诉求:对海子〈太阳〉七部书的阐释》,第100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先验的死亡力吸引着海子,对海子而言,“死亡比诞生更为简单”,海子对死亡本能毫不抗拒,从这个意义上出发就可以解释海子诗歌中不时弥漫的悲观色彩,如《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诗,在温暖的表象下,始终有一股悲伤的暗流,这是一个无法面对今天只能“从明天起”才能“做一个幸福的人”的诗人,他祝愿陌生人,“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而“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孤独于众人的他只愿如此,也只能如此。又如,在《太阳·诗剧》中,海子发出“与其死去!不如活着!”的呐喊,表面上看,这与他主动赴死的情结多少有些矛盾,然而联系上文“我走到人类的尽头”细细体会则悲哀尽显,“人仅靠本能就在实施的‘活着’的状态,诗人海子却需要拼命全力喊出”。*陈超:《海子论》,《文艺争鸣》2007年第10期。海子相信“我们活到今日总有一定的缘故”,于是他问:“是谁活在我的命上”、“每个人都有一条命/却都是谁的命?!”海子对存在意义的追问是由死至生的思考,活着是需要理由的,于是他“成为一个诗人”,以诗歌创造价值,赋予存在意义,赋予世界意义。
海子对死亡最集中的思考体现在《太阳·断头篇》中,在这首长诗里,海子塑造了一个反抗的英雄,断头的战士。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反抗,但他的头颅成为了太阳,拉开了人类精神苏醒的序幕。诗人说:“这一次,我的诗,出自死亡的本原,和死里求生的本能,并且拒绝了一切救命之术和别的精神与诗艺的诱惑。这是唯一的一次轰轰烈烈的死亡。”*海子:《动作·〈太阳·断头篇〉代后记)》,西川编:《海子诗全集》,第1035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在强烈的形而上的激情叙述中,海子对死亡的认识却异常清醒:“死亡是事实/唯一的事实。”在这里死亡具有双重含义,其一,作为反抗的战士,海子非常清楚死亡是唯一的结果,唯有死亡,这位失败的英雄的反抗才最终完成;其二,死亡一直存在抑或“悬临”(海德格尔语),这意味着“死亡是一种一直渗透到当前现在里来的势力”(雅斯贝尔斯语)。于是,海子说:
来吧,死是一直
存在的逼视
死是一堆骨肉
我像奇迹一样
每天每天
住在她身上
生命就是奇迹!
死,
怕什么
难道死亡会伤害生命
难道死亡会使我胆怯
前文已提及,海子认为死亡是对生命的延续,因此死亡不会伤害生命,而面对死亡的“逼视”,每天活着的“生命”才是“奇迹”般的存在,由此可见海子对生命的敬畏,亦可反观生命带给海子的负重感。生存对海子而言是有难度的,这就不难理解海子所说:“生存是人类随身携带的无用的行李/无法展开的行李”(《太阳·土地篇》)。海子并不惧怕死亡,一方面缘于他对死亡的亲近感,另一方面,海子选择为一种精神信仰而死,所以他并不胆怯,“除了死亡/还能收获什么/除了死得惨烈/还能怎样辉煌”。与陈超一样,海子为了诗歌理想也甘愿赴死,海子把诗歌当作“永恒的事业”,他相信“一些不朽的嘴唇睡在九泉之下/叩动,一些诗歌不朽”,这与陈超坚信“诗歌不死”的信念是一致的。在理想主义的驱动下,海子也在寻求精神上的超越,他主动迎接死亡:“除了主动迎接并且惨惨烈烈/没有更好的死亡方式”,甚至把死亡当作了一种使命般的担当:“如果毁灭迟迟不来/我让我们带着自己的头颅去迎接”,他要“轰轰烈烈地生存/轰轰烈烈地死去”,恰如诗人在序文中所说:“在一个衰竭实利的时代,我要为英雄主义作证。”这是一个无头的英雄,以太阳之名创造新的价值,这是一个“以行动定生死”的英雄,他的宿命是“反抗的宿命”,他主动向着毁灭向着死亡出发,直到“拖火的尸体倒栽而下”,他仍在高呼:“必须行动”、“必须决一生死!”这个英雄就是诗人自己,尽管诗中出现了多个人物形象,但他们都是海子的化身,都指向精神的超越,最终诗人以自我牺牲的行动意志完成了这一超越。
海子说:“在中国,必有一次伟大的诗歌行动和一首伟大的诗篇。这是我,一个中国当代诗人的梦想和愿望。”*海子:《诗学:一份提纲》,西川编:《海子诗全集》,第1048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太阳·七部书》正是他“一次性诗歌行动”的展开,他设想自己“在幻象和流放中创造了伟大的诗歌”(《太阳·土地篇》),也正是幻象与流放让他走向了拥抱太阳的燃烧之路。在对死亡的思考中,海子意识到诗歌也是“幻象之一种”,其本质上是虚无的,但它却提供了一个精神救赎的彼岸:“幻象是人生为我们的死亡惨灭的秋天保留的最后一个果实,除了失败,谁也不能触动它……幻象则真实地意味着虚无、自由与失败(——就像诗人的事业和王者的事业:诗歌),但决不是死亡。死亡仍然是一种人类经验。”*海子:《诗学:一份提纲》,西川编:《海子诗全集》,第1053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海子企图超越人类经验的形而上渴望十分强烈,在此基础上他创造了以太阳为核心的乌托邦,他试图建构一个新的价值体系,重新阐释世界,他以诗歌完成这些构想。海子选择了诗歌,他相信诗歌也选择了自己:“人类是人类死后尸体的幻象和梦想”,于是“诗歌执笔于我”(《太阳·土地篇》)。在诗歌理想的感召下,海子不仅自诩为“指路人”,在“在沙漠里指引着大家,在天堂里指引着大家”,更将自己比作“一个黑暗而空虚的王”,他走过全部天堂和沙漠,独自忍受着空虚和黑暗,忍受天堂的寒冷,却始终矢志不渝地坚持着诗人的事业,王者的事业,一如无头英雄一般甘愿牺牲,他不惧死亡与孤独,他以诗歌超越了世俗意义上的存在与时间,在精神世界里完成了自我升华。
三
理想主义气质浓厚的海子走向英雄主义顺理成章,他与陈超一样敏感于时代的变化,在“衰竭实利的”时代,在“物质凶相毕露”、“物质要了人命”的时代,海子宣扬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海子有感于土地的丧失,精神家园的沦丧,于是他以乡村生活经验为基础创造了大地乌托邦,村庄、麦地等田园意象在海子的诗中比比皆是,一如死亡意象,但正如崔卫平所说:“海子从来不是一位田园诗人”,他笔下的土地是“一个巨大的隐喻,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崔卫平:《海子、王小波与现代性》,《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2期。陈超也有此共识,他认为海子的诗是“反思现代性的现代性”。*陈超:《重读海子》,《名作欣赏》2009年第18期。这一评价是极其准确的,海子对现代性的反思体现为诗歌中强烈的精神危机意识,如《太阳·土地篇》中:
现代人一只焦黄的老虎
我们已丧失了土地
替代土地的是一种短暂而抽搐的欲望
肤浅的积木玩具般的欲望
过去的诗歌是永久的炊烟升起在亲切的泥土上/如今的诗歌是饥饿的节奏
饥饿中我只有欲望却无谷仓
海子仿佛已经预知诗歌时代的终结,置身于欲望遍地的时代,现代人的精神呈现为一种“饥饿”状态。土地的丧失以及精神的空虚令海子感到焦虑,于是他渴望诗歌和远方,他“呼唤着一只盛满诗歌的敏锐的角”,然而家园已然“脆弱”,远方也只是“一无所有的家乡”,“天才和语言背着血红的落日/走向家乡的墓地”。曾经那个“珍藏着诗歌 和用来劳动的斧头”的家园已逐渐消失,海子的反思也最终退回到自己的内心,“我是在我自己的故乡/在我自己的远方”。
陈超所面临的现代化进程更为深入,因而他的反思更加贴近现实,如《大淀的清晨》:
哦,星期天的白洋淀清晨
显得不真实。它让我忘记了生活重压的焦虑,
有如天涯归客恍惚于故乡久别的美。
如果不是抬眼望到那些旅游者在玩飘伞,
我就将一步跨出“现代化”的时间。
陈超渴望远离城市,远离“‘现代化’时间”,他喜爱自然与乡村,无奈“现代化”已经深入生活的方方面面,令他无处遁逃。在《北郊景色,或挽歌》一诗中,诗人由纪念车祸身亡的友人而将视线转移到“撞坏的汽车堆积场”,在这里陈超对现代化的批判与嘲讽呼之欲出:
下午五点半,北郊的天空又受到化工厂浊黄的控制。
冬青枯萎,如垂暮者抱头趺坐。
远处有三三两两遛着脏狗的“现代化”娘儿们。
提前到来的有夜晚,
废车堆积像水泥的蛾巢,
亮起冷冷的荧光。
伴随着工业现代化而来的污染,是人们在享受现代化带来的便利的同时相应承担着的风险,当天空变得“浊黄”,废车堆积在土地上成为“大地无法消化的/起瘤的钢铁橡胶面包”,污染已然成为现代人心头的“毒瘤”,而且随时可能因为污染引发人体生理性的病变,冬季的田野上已没有往日的风景,只剩一派“现代化”光景,这仿佛才是诗人心底真正的挽歌。相较于海子笔下的土地所具有的精神隐喻,陈超笔下的土地的现实意味更重,毕竟进入新世纪以来,土地丧失的问题更为严峻,在《推土机和螳螂》中,陈超有感于郊区农田被划作高尔夫球场,他的焦虑隐于其中:
一个农妇无端地斥骂
朝推土机欢呼的孩子们
她的双眼哀怨而无告
一只螳螂
在抖颤中挺起身
不屈地迎着推土机方阵
它锋利的双臂合十
像最后撤退的修士
在无助地抗议入侵者
还是在为土地做最后的祈祷
推土机的推进好似商品经济的步伐不可阻挡,一切都以经济利益为中心,不论是城镇化还是各种经济项目的开发,土地失去了本身所具有的自然生命气息,更多变成水泥地,抑或人为的绿地,而承载着东方文化传统的乡村也正在消失。面对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切,有人欢呼,有人抗议,尽管这抗议是多么无助,而更多时候,只能叹息,甚至连叹息都来不及,天翻地覆的变化就已经发生。陈超对现代性的反思也触及文化领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对“后现代”浪潮持审慎的态度,他说:“朋友们,让我们谈点逝去年代的人与事/与我们记忆中珍存的青春原浆酒相比/‘后现代’鸡尾酒又算什么?”(《红黄绿黑花条围巾》)面对学界中对“后现代”的盲目跟风现象,他讽刺道:“一卷儿豆腐丝嘟囔/诗要浑不吝/严谨也太老土/都‘后豆腐’时代了”(《论战试解》)。陈超是为“自己的心写诗”,他看重个人心灵的观照,即“笔随心走”,不盲随各种主义。作为一个诗人,他坚持:“人,该说实在的话”(《“点彩”画家》),这样的坚持难能可贵,陈超肯定“从来就在的诗”,他以心灵和个人体验为准,而海子更注重对诗歌真理的追求。
陈超与海子一样,坚持诗歌信仰,坚守精神的乌托邦,二者都是具有理想主义气质的诗人,很大程度上,两位诗人对死亡的关注以及愿为理想献身的情怀都源于此。陈超与海子“在灵魂方面基本是属于同一精神型构的人,他们天生就是理想主义者,或者说,他们完全是人文理想主义精神塑造出来的人。一位纯粹的理想主义诗人,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位怀有死亡情结的诗人。”*谭五昌:《陈超:死亡幻象的审美书写与精神超越——对陈超诗作〈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的解读与阐释》,《文艺争鸣》2015年第1期。陈超与海子的死亡情结和乌托邦情结相互缠绕,理想主义色彩在诗歌中尽显无疑。二者既属同一精神型构,也有着共通的知识背景,陈超在访谈中提到八十年代的两套书对他影响很大,即“三联出的四五十本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上海译文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属于现代人本哲学的,比如海德格尔、尼采、萨特、本雅明、胡塞尔、伽达默尔,以及‘西马’诸人的著作”,*陈超:《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第38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海子也不同程度受到八十年代出版的这些西方译本的影响,*参见金松林:《悲剧与超越——海子诗学新论》,附录三“海子藏书目录”尤其是存在主义及生命哲学。可以说,陈超与海子的死亡意识形成于较为一致的文化基础上,他们以死亡观照个体反观时代,寻求精神上的超越。海子一步步上升到抽象的精神世界,走到了精神乌托邦的极端,陈超则在精神的高蹈中逐渐增加对日常生活的关注,有时甚至是对现实的一种逼视,这种尖锐和勇气是《青铜墓地》中对死亡宣战的态度的一以贯之,也避免了耽溺于精神乌托邦的危险性。
陈超与海子十分欣赏荷尔德林,二者都写过以荷尔德林为题的诗作,当荷尔德林问道:“在这贫困的时代,诗人何为?”*海子:《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西川编:《海子诗全集》,第1069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这令很多人深受震动。对陈超而言,在物质丰富而精神贫乏的年代,保持精神的追求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对世界的期待,于海子更是如此,他上升到人类的高度,企图以诗歌唤醒人类的精神觉醒。海德格尔说:“这个时代是贫困的时代,因此,这个时代的诗人是极其富有的。”*〔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第52页,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这句话也适用于陈超与海子,正是拥着一份永不磨灭的诗歌理想以及勇于坚持的信念,他们富有于人文精神的勃发,富有于灵魂的充实安定,最重要的是,诗歌完成并传达了这一切。更可贵的是,两位诗人构筑的精神乌托邦在当下的现实语境中,特别具有启示意义。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物质文化消费文化盛行,人更多地看重当下,追求实利注重物质享受,理想主义仿佛已随着远去的八十年代一并消逝。伴随着现代技术发展而来的工具理性使精神与理想更显失落,这种失落表现为人们“对于精神、灵魂、意义或超越问题的冷漠,对一切人文价值的冷漠”*陶东风:《中心与边缘的位移——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结构的变迁》,陶东风主编:《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第276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精神与理想的缺席成为当代人的精神常态,这是十分可怕的。两位诗人在诗意世界中创造了精神乌托邦,它指向人可达到精神高度,避免人成为物化的人,并赋予人永恒的价值,这一精神超越的要求隐含在诗人对死亡的哲理思辨之中。乌托邦或许具有某种危险性,但作为一种精神指向有其存在的必要,否则“达到了理性支配存在的最高程度的人已没有任何理想,变成了不过是有冲动的动物而已”。*〔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第268页,黎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责任编辑李桂玲)
段曦,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