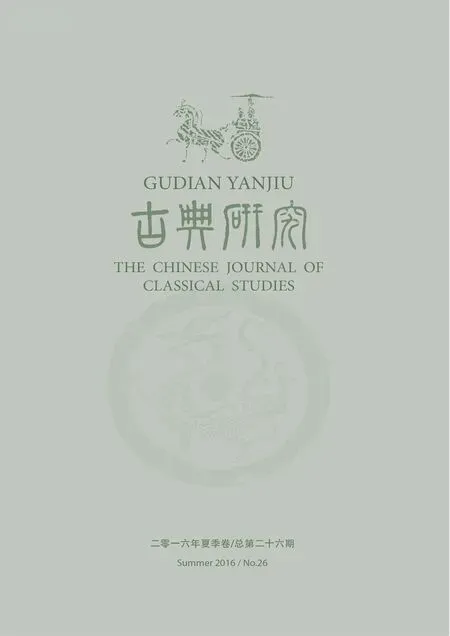柏拉图笔下的城邦與護衛者
—— 《王制》第二卷374a-376c發微
2016-11-25王進
王進
(貴州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
柏拉图笔下的城邦與護衛者
—— 《王制》第二卷374a-376c發微
王進
(貴州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
在《王制》第二卷中,柏拉圖把哲人、護衛者與狗等同起來,認爲三者的品質是一致的。在啟蒙哲學盛行的今天,要想理解其原因顯得頗爲困難。對於蘇格拉底把哲人與狗類比是否嚴肅這一問題,同爲施特勞斯學派中人的布魯姆與尼柯爾斯的不同解讀必定隱含著重大問題,思考二者對於“哲人”的理解和界定亦是另一難點。蘇格拉底將三者等同並不是隨意爲之,而是因爲他懂得哲學與政治之間的衝突與矛盾。哲學的天性是追求真理,但哲人面臨現實政治時,必須克制自身追求普遍性的哲學衝動,以免破壞政治共同體的現實基礎。若不安於這種“意見”而醉心於“真理”,任憑理智和情感狂奔湧流,則將破壞人間基本常識。護衛者必須拒絕以哲學上的抽象判斷作爲最高準則,才能承擔起保衛政治共同體的職責。失去節制的哲學心性終將自甘墮落,喪失對常識的判斷能力而淪爲政治共同體的叛徒。
Author:W ang Jin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Guizhou University of China(Guiyang 550025,China).E-mail:phihwang@163.com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
兵者,國之大事……不可不察也。(《孫子兵法》)
愚兵之耳目,使其無知…… (《孫子兵法》)
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淩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漢書》)
柏拉圖-蘇格拉底在《王制》①本文引用的《王制》中譯本爲王揚譯本《理想國》(北京:華夏出版社,2012),同時參考了郭斌和、張竹明譯本 (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和英文本,Allan Bloom,The Republic of Plato.Translated With Notes and an Interpretative Assay,New York:Basic Books,1968。中談到城邦護衛者應該具備何種品質之時,將城邦的護衛者比喻爲狗,甚至很多時候相提並論,直接將兩者等同,並且進而認爲狗象哲人一樣“愛智慧”,狗也是哲人。在今天看來,護衛者——狗——哲人這三者差距大矣,豈容混淆?但問題是:作爲哲學奠基人之一的蘇格拉底-柏拉圖,怎麼就將三者等同起來呢?其間之深意何在?在本文看來,蘇格拉底-柏拉圖如此作爲,其實蘊含了重大的政治哲學問題。
一、問題的回顧及其疑惑
首先讓我們來回顧一下該問題。
蘇格拉底-柏拉圖在與格勞孔討論城邦護衛者應該具備何種品質時提出這個問題:“一條品種優良的狗在看守一事上和一個出生高貴的年輕人有甚麼區別?”(375a)在此,蘇格拉底-柏拉圖第一次將狗與護衛者相提並論,接著認爲兩者具有相同的天賦才能。首先是身體方面的:“兩者都必須有銳利的目光,追蹤目中的獵物行動輕快,並且還要擁有力量,如果有必要和被抓住的東西鬥爭一番”(375a),並且還需要“勇猛”;其次是心靈上的“充沛氣魄”。但是問題在於:“他們怎麼能不蠻橫地對待自己的同行、對待城市裏的其他公民,如果他們的本性就是如此?”(375b)假如不能避免的話,那麼護衛者不僅盡不到護衛城邦和其國民的天職,還會養虎成患,反過來成爲禍國殃民之徒。這種情況,古往今來,比比皆是,所以,爲了避免這種情況,護衛者和狗除了上述的品質外,“他們一定對自己家裏的人溫順,對他們的敵人兇狠,否則,不等別人來消滅他們,他們自己將搶先做到這一點”(375c)。
但是,問題到了這裏,蘇格拉底-柏拉圖與格勞孔都犯難了,“因爲溫順的氣質和勇猛的氣質大體上相反”。相反的東西怎麼能夠統於一身呢?同時問題又在於:對於城邦的護衛者來說,如果這兩種品質“缺乏兩者中任何一種,他就不能成爲優秀的衛士” (375c),那麼,從“理論”上來說就根本找不到合適的城邦護衛者。但是,眾所皆知的是,護衛者對於任何一個現實、具體的城邦來說都是不可或缺,所以還必須克服這個理論上的困難。最後困難也確實得以克服。原來,“真是活該,朋友,這下我們可陷入了困境,因爲我們把先前提出的那個比喻給拋下了”,“我們沒有考慮到這一點,一些氣質,我們認爲不可能存在,可它們的確存在,自身擁有對立的性格特徵”。在哪里呢?
在其他動物中,某人也能觀察到這一現象,然而,在我們把牠比作衛士的動物中,這尤其顯而易見。其實,你也許知道,在品種高貴的家犬中,這就是牠們的本性,牠們對自己家裏的人和熟人可謂溫順至極,對生人則相反。(375d)
也就是說,狗的天性裏面就存在“溫順”和“兇狠”兩種相互矛盾的天賦品質,這是狗的天生、自然的品質。“我們並不需要跨越自然去尋找一個這樣的衛士”(375e),理論困局就這樣在事實面前得到了自然的解決。“牠 (狗)的脾氣總是對熟人非常溫順,對陌生人卻恰恰相反”(375e)。並且,“每當看到陌生人,牠就生氣,儘管牠事先並沒有受到任何傷害。看到熟人,牠就歡迎,儘管牠從來沒有從他那裏得到過甚麼好處”(376a)。而且最重要的是,對於城邦護衛者來說,區分敵友是最重要的——不能像抗戰時期的漢奸偽軍那樣槍口對內——狗在這方面做得最好:“牠辨別友好與敵對的形象不憑別的,就憑自己熟悉前者,不認識後者”(376b)。簡單明瞭,無需思量。
至此,城邦護衛者“彼此之間發生衝突,或者跟其他公民發生衝突”的重大問題得到了解決。但是,這說的是狗啊,並沒有說城邦護衛者啊,難道城邦護衛者也應該象狗一樣?答案當然是肯定的——“我們並不需要跨越自然去尋找一個這樣的衛士。”由此,護衛者的問題得以解決。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到,這裏隱含的問題是:“溫順”與“兇狠”兩種相反的品質是“在別的動物身上找到,特別是在我們拿來跟護衛者比擬的那種動物身上可以找到”的,而不是在人身上找到的。那麼,現在說護衛者具有這樣的品質並不違反事物的天性,就暗含一個潛在的要求——護衛者必須下降爲動物,否則無法履行保家衛國的重任。換言之,也就是將狗與護衛者等同起來,認爲護衛者應該具有狗一樣的天性。表面看來,這不是侮辱同樣爲人的護衛者嗎?這確實是一個問題。
最後,護衛者“還需要具備這樣一種特徵,除了具有充沛的精力,他還需要哲人的氣質”(375e)。這個說法相當令人震驚,連當事人格勞孔都困惑了(“怎麼會呢?……我不懂”)。爲甚麼呢?因爲雖然說了護衛者與狗的共同性,但是那始終屬於身體和精力等自然方面,而哲人的氣質卻是一種相當高妙的東西啊,這怎麼可能呢?換句話說,哲人是愛智慧的人,難道狗 (護衛者)也“需要有對智慧的愛好”?智慧?——這不是哲人的專利嗎?狗需要智慧,哲人是愛智慧的人,這難道不是說,哲人就是狗?天啊!並且最爲令人震驚的是,蘇格拉底-柏拉圖做出這一判斷的根據是:
(狗)每當看見陌生人,牠就生氣,儘管牠事先並沒有受到任何傷害。看到熟人,牠就歡迎,儘管牠從來沒有從他那裏得到過甚麼好處。
可是,
我這樣想的根據是:狗完全憑認識與否區別敵友——不認識的是敵,認識的是友。一個動物能以知和不知辨別敵友同異,你怎麼能說它不愛學習呢?
然而,“愛學習和愛智慧是一回事”(376b),所以,狗才是真正愛智慧的哲人。對這一點,我們今天的人會感到非常的震驚。我們今天判定一個哲人的標準是看他能否思考一些普遍性的、根本性的全人類問題。一個哲人應該是超越了國家、民族的界限的人。對他們來說,萬國爲一國,眾人爲“一人”,其愛是普遍的,沒有差等的。反觀蘇格拉底-柏拉圖的話,居然將區別敵友、並且是根據認識與否來區別,將對敵人兇狠、對朋友溫順這些凡人、俗人的行爲作爲智慧的表現,這難道不是……並且,尤爲嚴重的是,這還是“一種對智慧有真正愛好的表現”。換句話說,狗是對智慧有真正的愛好,狗才是真正的哲人,反過來,許多平素說愛智慧的、現代的具有普遍性追求的哲人,搞得不好並不是真正愛智慧,而是假的哲人。孰對孰錯?這值得我們深思。
二、“哲人”問題
相關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哲人與狗的比較上,這些討論及其所包含和所引發的問題值得我們重視和思考——特別是在今天國朝學界和現實生活之中。
在布魯姆看來,“把像狗那樣對熟人的情感與哲學等同起來,當然不是嚴肅的”。①布魯姆,《人應該如何生活:柏拉圖〈王制〉釋義》,劉晨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9,頁 77。筆者同時參看了該書英文版,Allan Bloom,The Republic of Plato。Translated With Notes and an Interpretative Assay,前揭,1968。對此,尼柯爾斯針鋒相對地說:“與此相反,我認爲,哲人與護衛者之間的比較並無不妥”。不僅如此,她還進一步指出:“也許這比較實質上比看上去還要‘認真’”②尼柯爾斯,《蘇格拉底與政治共同體:《王制》義疏,一場古老的論爭》,王雙洪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7,頁91注1。——如果稍微瞭解一下這兩位教授的學術背景,或許對我們不無益處。布魯姆教授師從古典政治哲學名家施特勞斯,被認爲是其“門下最有名氣和成就的弟子之一”,其主要學術成就之一就是在英文世界重新翻譯了本文所討論的《王制》,因爲布魯姆教授卓越的古典學修養,該譯本廣受尊重。在翻譯該書後,他爲之撰寫了解釋性文字,③該解釋性文字附錄於英文版《王制》之後,參看Allan Bloom,The Republic of Plato,Translated With Notes and an Interpretative Assay,前揭,1968。劉晨光將之獨立出來,單獨成書,譯爲中文,另名爲《人應該如何生活》。參看布魯姆,《人應該如何生活:柏拉圖〈王制〉釋義》,前揭,頁77。被認爲“別具一格、極富魅力”,“每一個見解、每一處論斷都是他深思熟慮、反復孕育的產物,故如河蚌煉珍珠,滿篇皆珠璣”。①布魯姆,《人應該如何生活:柏拉圖〈王制〉釋義》,前揭,“中譯本說明”。尼柯爾斯教授則師從施特勞斯的芝加哥同事克羅波西 (Joseph Cropsey)教授。克羅波西曾與施特勞斯共同主持編寫《政治哲學史》,在施特勞斯去世後,他被指定爲其遺稿保藏人。所以,布魯姆與尼柯爾斯可謂“同門”。同門相爭,其中必定蘊含重大問題,不可小覷,值得我們關注。扯遠了,話說回來——布魯姆與尼柯爾斯產生分歧的原因何在?
布魯姆爲甚麼認爲“把像狗那樣對熟人的情感與哲學等同起來”不“嚴肅”呢?這個問題暫且不說,我們先來反問一下:爲甚麼蘇格拉底-柏拉圖要進行這個“不嚴肅”的比較呢?原來,它“只爲第五卷中哲學的真正出現開闢道路,以及加強哲人與戰士之間的區別”。哲人與戰士之區別何在?布魯姆告訴我們:
哲人是溫順的人,因爲他們追求知識而非獲益;他們的目標不需要損害別人。對這個城邦的統治者而言,對知識的熱愛是一種必要的動機,以便調和他們對勝利和財富的熱愛。但是,哲人是狗的對立面,因爲哲人總是尋求認識他們不知道的東西,而狗必須使自己與未知事物斷絕關係,並對外來的吸引懷有敵意。狗熱愛牠們自己的東西,而非好的東西。而且必須如此,否則牠們將不能在牠們的羊群與那些可能攻擊羊群的敵人之間做出必要的區分。戰士原則上是幫助朋友和傷害敵人。誠然,對已知事物的熱愛,使他們的情感超越自身而延伸至城邦;它帶有哲學的普遍化或世界主義的效果。但是,這種愛在城邦的邊界處終結。戰士仍是非理性的野獸,既喜歡那些友善對待他們的人,又喜歡粗暴對待他們的人。……狗的天性使狗向哲學的指令敞開,但並不使狗成爲哲人。②布魯姆,《人應該如何生活:柏拉圖〈王制〉釋義》,前揭,頁77。
布魯姆之所以認爲狗與哲學等同起來“不嚴肅”,是因爲“哲人是狗的對立面”。哲人基於自己求知的本性,對未知的、陌生的事物具有濃厚而強烈的興趣,在此興趣面前,沒有城邦的存在——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沒有國家、民族的界限和其存在,沒有家國鄉邦故土的概念。因爲哲人求知的本性會“自動”地破除這些實際的界限和抽象的概念。在哲人的面前,只有“甚麼是好的”的問題和意識,換句話說,他們只追求普遍性的“真理”,凡事只問“對不對”,而不是問“是否是我們的”。狗則不同,狗不思考“甚麼是好的”這類普遍性的、抽象的哲學問題,也不熱愛這些問題,而只是熱愛“自己的東西”。在狗面前,城邦、家國、故土、鄉邦都存在,並且牠只熱愛屬於這些領域內的東西,反之則是陌生的,就是敵人。如果狗企圖讓自己的愛超出這些範圍,那就非常危險了,因爲如此一來,狗看護家園、保家衛國的神聖職責將失去根基和理由。此種情況正如古典政治哲學名家施特勞斯所說:
作爲理論家,他就要站在優異性的一邊,而不管它是在何時何地被發現的,他要在好的與他自己的這兩者之間無條件地選取前者。而行動的人主要關心甚麼是他自己的、甚麼對他而言最親近,不管它多麼缺乏優異的性質。①施特勞斯,《自然權利與歷史》,彭剛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頁316。
同時,狗“對已知事物的熱愛,使他們的情感超越自身而延伸至城邦;它帶有哲學的普遍化或世界主義的效果”,那麼怎麼辦呢?布魯姆的辦法是:強制“這種愛在城邦的邊界處終結”。申言之,哲人基於求知之“知”和“甚麼是好的”之“好”的普遍性、抽象性和超越性,超越了國家和民族的界限,同時也“抽象”了具體的國家和民族,這樣一種超越、抽象的思想和泛愛眾生之博愛,使國家和民族在面臨外來侵略時喪失抵抗的理由和力量。而狗則與之完全相反,儘管狗所具有的“溫順”天性也使牠們潛在地具有上述哲人的性質,但是,狗的“愛在城邦的邊界處終結”,它不會象哲人那樣對普天之下的人一視同仁,博愛無別,而是僅僅熱愛自己人、熟人。那麼當外來之敵——陌生人——前來侵犯之時,狗 (護衛者)會“不問是非”地加以反擊和抵抗。關鍵的問題就在於,對於保家衛國的護衛者來說,就需要這樣的“不問是非”而只問陌生與否……
對此,尼柯爾斯表示不同意見。在正式表明她的看法之前,她簡單陳述了布魯姆的觀點:
布魯姆注意到,蘇格拉底的哲人與狗之間的比較並不“認真”,但他認爲在有限範圍內蘇格拉底的比喻是成立的,即護衛者對熟人的愛可以推延到他們對城邦的感情;這種感情超越了自我,與哲學的普適性是相通的。
接著,她表明看法:“與此相反,我認爲,哲人與護衛者之間的比較並無不妥,不是因爲護衛者的開放性,而是因爲對統治城邦的哲人是有嚴格限定的。也許這比較實質上比看上去還要‘認真’”。①尼柯爾斯,《蘇格拉底與政治共同體:〈王制〉義疏,一場古老的論爭》,前揭,頁91注1。尼柯爾斯認爲哲人與護衛者的比喻“並無不妥”,其原因並不在於布魯姆所說的“護衛者的開放性”,而是從對“統治城邦的哲人”的“嚴格限定”這個角度來說的。假如從此出發,那麼結果不但不是布魯姆所說的不“認真”,相反是“還要‘認真’”。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布魯姆與尼柯爾斯之間的重大差別在於對“哲人”的理解和界定。在前者看來,哲人是無限開放的,而在後者看來則是有限封閉的。問題至此,那麼我們就要考察“哲人”到底意味著甚麼?恰好,蘇格拉底-柏拉圖接下來就談到狗的愛智慧的問題。
儿童肥胖已成为全球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目前,中国儿童肥胖发展速度快于欧美发达国家[1]。且呈现城市高于农村的特点,尤其是在经济发展快的大城市,儿童肥胖已成为影响儿童健康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2]。儿童时期肥胖不但增加多种疾病的发病风险、影响心理健康和学习能力,80%肥胖儿童还可延续至成人肥胖,与成年期许多慢性疾病如高血压、高血脂症、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脑血管疾病及成人期癌症有非常密切的关系[3-5]。预防和干预儿童肥胖的流行已刻不容缓。
三、護衛者、哲人與狗
眾所周知的是,哲學是“愛智慧”,是智慧之學。但我們需要弄清楚的是:第一、蘇格拉底-柏拉圖所謂的“智慧”是甚麼?第二、其所謂的“哲人”又何謂?
甚麼是“智慧”?蘇格拉底-柏拉圖說,他們所假定建立起來的城邦“一定是智慧的”,“因爲它有很好的謀劃”。好的謀劃源於護國者所擁有的知識,這種知識不是像木工那樣的生產性、實用的知識,“而只是用來考慮整個國家大事,改進其對內對外關係的”知識。這種知識“是深謀遠慮的”,蘇格拉底-柏拉圖稱之爲“真正有智慧的”。由此我們可以知道,“用來考慮國中某個特定方面事情的”知識不是智慧,真正的智慧是治理政治共同體的:
由此可見,一個按照自然建立起來的國家,其所以整個被說成是有智慧的,乃是由於它的人數最少的那個部分和這個部分中的最小一部分,這些領導著和統治著它的人們所具有的知識。並且,如所知道的,唯有這種知識才配稱爲智慧,而能夠具有這種知識的人按照自然規律總是最少數。(《王制》429a)
柏拉圖這裏反復說到“智慧”,但甚麼是他所說的“智慧”呢?有學者認爲,
柏拉圖所說的智慧不純粹是形而上學的思辨性能力,而是關切現實的幹練安邦之才。關心城邦、立足現實、憫懷生民,這就是古典政治哲學的特色。所謂‘智慧’,在柏拉圖看來,就是從事政治,爲老百姓的生活編織一張足以安居樂業的社會經緯。①程志敏,《從“高貴的謊言”看哲人和城邦的關係:以柏拉圖〈王制〉爲例》,《浙江學刊》2005年第1期,頁88。
由此来看,智慧是關於人間事務的知識,它與關於自然界的知識大相徑庭。一個僅僅對自然界的知識有著精深廣博瞭解的人,並不能夠說他有“智慧”。以此觀之,今日之所謂科學家、工程師無論知識如何,在本質歸屬上還是屬於木工、瓦匠等技工之範圍。如果讓這些人來治理國家的話,恐怕難免“國破家亡”。②415c:“銅鐵當道,國破家亡”。郭斌和、張竹明譯本,前揭,頁129。這一點可從古典時代對政治家的教育和培養中窺見端倪:
在過往時代,通過傾聽睿智長者講話、閱讀優秀史家的作品,通過遊歷和投身公共事務,有才智的人能夠獲得政治知識以及他們所需要的政治理解力。③施特勞斯,《甚麼是政治哲學》,李世祥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1,頁6。
在過去時代,政治家獲得治國安邦的政治才能的方法,一是傾聽飽經人世滄桑的睿智長者的談話,二是閱讀記載人世經驗而又充滿史識的史家著作,三是親身投入人世間去瞭解世態人情。三種方法的共同特徵是:都是強調對人間事務的瞭解和認識,其中沒有自然界知識的位置。以此古典觀點來看,今天的政治家就無需去學習水電知識、或者去學習如何辨別雲母石等地質知識等等,而是——就中國政治家的閱讀範圍來說——應該去認真研習《二十四史》。那麼這一觀點是否已經落後——就象施特勞斯說的那樣,“在過往時代”呢?此點暫且不論。
具有上述“智慧”的人被稱爲“哲人”,他與我們現在所謂的“哲人”有著很大的不同。嚴格來說,後者僅僅相當於蘇格拉底-柏拉圖嚴厲批評的“智術師”。如同木工所有的是如何進行木料加工的知識一樣,智術師所擁有的知識也只是推理、邏輯等思維技巧而已;木工依靠木工活謀生,智術師則依靠生產和出售知識謀生,至於宗教信仰、社會倫常、家國秩序則甚少考慮。但是問題在於,宗教信仰、社會倫常和政治秩序對於現實政治共同體來說,無論對於個體還是群體來說,恰好又是必須的。這就在哲學與政治之間產生極大的衝突和矛盾。所以,“平庸的民眾對哲學和哲人並無同情之心。正如西塞羅所說,哲學對許多人而言是可疑的”。①施特勞斯,《自然權利與歷史》,前揭,頁145。民眾對哲學、哲人的懷疑具體體現在雅典民眾對蘇格拉底的死刑判決之中。實際上,對於現實具體情況來說,民眾如此作爲又是可以理解的,畢竟,要像啟蒙哲人康德那樣不信神而依然能夠過有道德的生活,對於心智一般的普通人來說,可能相當困難甚而完全不可能。今天,依然作爲“平庸的民眾”的普通大眾已經完全不再懷疑哲學及其哲人了,這只是因爲“在十九世紀,此種情形才有了深刻而明顯的改變,而這一改變要歸因於哲學的含義的完全改變”(同上,頁145)。今天,通過啟蒙哲人的不懈努力,普通民眾已經完全受到啟蒙,像哲人那樣完全忽視了哲學與政治的尖銳對立與衝突,也完全忽視了自身作爲普通民眾與哲人心性上的天然差異。
由於古典哲人深刻明白哲學與政治之間的對立和衝突,所以,當哲人從思想的天空被迫下到凡間 (政治共同體),輪流擔負治國安邦的義務時,他們不得不謹言慎行。由此他們的觀點就一定具有僅僅屬於這個共同體的“狹隘”性和“局限”性,也就是僅僅屬於局部的“意見”而非普遍的“真理”。從天性上來說,他們也具有普遍性的情感衝動和理智天賦,但是,現實治國者的職責壓制了他們的這份衝動和理智。正是在這一點上,他們與狗的天性取得一致。或許正是如此,所以,蘇格拉底-柏拉圖說,狗也是哲人。而現代的哲人已經不再懂得哲學與政治之間的尖銳對立與衝突,同時也由於不再擔任政治共同體實際統治者和領導者的社會職務,所以他們言說行事不但全無顧慮,相反還視之爲“勇敢”和“真誠”,任憑自己的理智和情感狂奔湧流,所以,他們不再是狗。與此同時,當他們對一個政治共同體發言之時,政治共同體可能也就岌岌可危了,因爲他們的普遍性的情感和理智會衝破政治共同體的立體性的、現實的存在。但是,問題的關鍵在於:
儘管科學本質上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社會卻必須由一種愛國主義的精神、一種與民族的仇敵勢不兩立的精神來激勵。政治社會乃是一個要針對別的國家來防衛自己的社會,它必須培養尚武的美德,而且它通常養成的是一種好戰的精神。相反地,哲學或科學是要破壞好戰精神的。(同上,頁262-263)①施特勞斯,《自然權利與歷史》,前揭,頁262-263。
餘論
忘記了古典哲人的深切教誨,各種奇怪的言論就會層出不窮,比如近來,國朝某年老經濟學人發表高論,爲大漢奸汪精衛進行辯護,說汪精衛是“真正的英雄”。以此論之,那些浴血沙場、捨生忘死抵抗外敵入侵的抗戰英雄則是狗熊了。也有國朝某年少經濟學人爲英國發動的對華鴉片戰爭進行辯護②吊詭或者說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相對於中國這位自由派經濟人對英國發動的對華鴉片戰爭的頌辭,一百多年前,“英國自由主義史上閃耀著兩個偉大的名字”(參見霍布豪斯,《自由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頁50)一語所指的二人之一的英國前首相格萊斯頓也曾對英國議會發表演說,但不同於前者的是,作爲戰爭發起國的首相先生卻強烈譴責這場戰爭。……是甚麼原因使這些聲名遐邇的公共“知識分子”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出此言論?又是何種原因使得媒體人敢於傳播此種言論?它們又將產生何種民眾影響?此種問題,值得我們深思、反思。回顧蘇格拉底-柏拉圖的上述言論,想來會有助於我們的思考。考察上述經濟人的理論基礎,我們會發現,它們就是某些所謂的“普世價值”,換句話說,就是一些最爲基本的“自然”權利。這些基本的“自然權利”在層次上與哲學上的終極探問具有相似性,它們的共同特徵都在於去除了家國、民族等社會性。立足於這些不具任何社會性的“赤裸裸”的“真理”,當然就會得出爲漢奸進行辯護的結論。但是問題的關鍵恰好在於,以此抽象的“赤裸裸”的“哲學的”“真理”來要求和改變具體而又現實的政治問題,是否尊重了政治本身所具有的屬地的特性?它又將對政治共同體產生何種影響?這些都值得我們深思。注意古典政治哲學所強調的政治與哲學之間的緊張關係,如果忽視了這些緊張關係,將導致我們對基本常識的忽視。而問題恰好在於,
有些事物只有用肉眼來看才能看到它們的本來面目;或者更準確地說,這些事物只有從與科學觀察者截然不同的公民眼中來看,才能看到它們的本來面目。①施特勞斯,《甚麼是政治哲學》,前揭,頁17。
或許也正是因爲這樣,所以蘇格拉底-柏拉圖含蓄地指出:城邦護衛者應該像狗一樣。追求普遍性的哲學應該懂得在他們面前止步,或者說,城邦的統治者應該拒絕對護衛者進行哲學教育。這一點在《王制》接下來的討論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初稿於二○一二年“九·一八”國恥紀念日,二稿於二○一二年國慶前夕,三稿於二○一三年元旦,四稿於二○一五年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周年紀念日
參考文獻[References]
Bloom,Allan.The Republic of Plato,Translated with Notes and an Interpretative Assay.New York:Basic Books,1968。
布魯姆,《人應該如何生活:柏拉圖〈王制〉釋義》,劉晨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9。[---.The Republic of Plato,Translated with Notes and an Interpretative Assay.Trans.Liu Chengguang.Beijing:Huaxia Publishing House,2009.]
刘小枫,《施特劳斯的路标》,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Liu,Xiaofeng.Leo Strauss als Wegmarke.Beijing:Huaxia Publishing House,2011.]
尼柯爾斯,《蘇格拉底與政治共同體:〈王制〉義疏:一場古老的論爭》,王雙洪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7。[Nichols,Mary P.Socrates and the Political Community.Trans.Wang Shuanghong.Beijing:Huaxia Publishing House,2007.]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張竹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Plato.Republic.Trans.Guo Binghe and Zhang Zhuming.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1986.]
柏拉图,《理想国》,王揚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2。[---.Republic.Trans.Wang Yang.Beijing:Huaxia Publishing House,2012.]
施特勞斯,《自然權利與歷史》,彭剛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Strauss,L.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Trans.Peng Gang.Beijing: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06.]
施特勞斯,《甚麼是政治哲學》,李世祥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1。[---.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Trans.Li Shixiang et al.Beijing:Huaxia Publishing House,2011.]
施特劳斯,《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郭振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sm.Trans.Guo Zhenhua et al.Beijing:Huaxia Publishing House,2011.]
The Polis and Its Guardians:A Reading of Republic II 374a-376c
In the second volume of Republic,Socrates identifies philosophers and guardianswith dogs in that they share the same quality,that is,they show a real love for wisdom based on common sense by which they distinguish enemies from friends.Bloom and Nichols,both of whom are members of the Straussian school,stand in sharp conflict concerning whether Socrates is serious in his comparison of philosophers to dogs.For all those difficulties,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ers'precious teaching should be kept inmind thatonemustgive up ultra-secular speculations and examine texts with a classical sight to find out implications in their subtle expressions.With the help of precedents'annotations,a close reading of Socrates'texts shows that he is serious in identifying philosophers and guardianswith dogs,who knowswell that the solution to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philosophy and politics,between“mildness”and“fierceness,”forms the premise of the existence of political communities.The nature of philosophy is to seek truth,but a philosopher must convert from philosophy to political philosophy to overcome his impulse of pursuing universality and to prevent himself from damaging the real foundation of a political community.Guardiansmust possess both“mildness”and“fierceness”to defend his compatriots and fight his enemies.This contradiction is reconciled in a dog,who treats enemies ruthlessly and fiercely but remainsmild to his friends-hemakes stark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friend and the enemy by judgingwhether they are acquaintances or strangers.Therefore a dog is not only a guardian possessing both“mildness”and“fierceness,”but also a philosopher with a true love for wisdom.This interpretation leads to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first,narrowness and limitedness is imposed by the polis on a philosopher when he turns his sight from the sky to the earth,therefore he will damage fundamental common sense of human society if he can't get along with such“opinions”and let his intellect and passion flow freely indulging in truth;second,to take on the duty of defending the political community,Guardians should take“acquaintances or strangers”as a criterion to distinguish enemies and friends and reject any superb principles based only on abstract philosophical claims; third,enlightenment philosophers'abstract considerations ignoring any concrete distinctions between nations or stateswill deprive the community of will and courage to resist aggression.This philosophy without any self-moderation will lose both courage and wisdom and accept its own digressions.People with such a“enlightened”mentality will also be unable to distinguish the enemy from the friend according to the common sense of“acquaintances and strangers.”They are doomed to become traitors against the political communities in the confusion of thought and the lack of courage.
Republic;state;philosophy;politics
關鍵詞:《王制》 國家 哲學 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