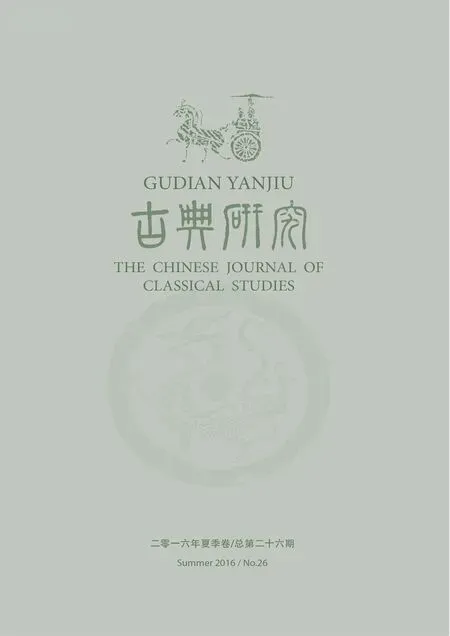早期儒家與神秘主義
2016-11-25陶磊
陶磊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
早期儒家與神秘主義
陶磊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
借助靈知主義的“神性自我”觀念,可以很好地闡釋從孔子到孟子儒家學說的發展。孔子的克己復禮,是克去多餘部分獲得完美自我的意思;慎獨是完美自我的成立;孟子的良知良能說是對“神性自我”的祛魅。爲了解決“神性自我”祛魅後堯舜天生爲聖人的問題,孟子將通常所理解的性與命作了角色變換,其良知良能說就成了性善論。伴隨著神性自我的祛魅,早期儒家的修養學說經歷了從主身向主心的轉變。基於這個認識框架,一些蘊含神秘主義的早期儒學文本可以獲得更準確的定位,《大學》、《中庸》都應是孔孟之間的文本,郭店楚簡《五行》不能稱其爲思孟五行。《易傳》與孔孟一系的儒家,在性、命、天的關係的認識上,看起來很相似,但一以性中蘊含理爲基本預設,一以心爲理的根源爲認識基礎,二者屬於不同的心性學範疇。儒家的神性自我是神與人的綜合,此觀念植根於古代神道立教的宗教政治文化土壤中,早期儒家對於“神性自我”的嚮往,與宋明理學所追求的內在超越,不能相提並論。
Author:Tao Lei is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Humanity,Zhejiang University(310028 Hangzhou,China).E-mail:tao11@zju.edu.cn
早期儒家學說中有無神秘主義的內容,是一個難以講清楚的問題。基於宋明理學的闡釋,早期儒學中很少有神秘主義的成分,①陳來《宋明儒學與神秘主義》論述宋明儒學中的神秘主義,其中提到早期儒學文本的一些敘述,但這不代表宋明儒學對早期儒家文本中的基本概念與範疇以及一些命題也是作神秘主義的理解。陳文收入其著《宋明儒學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頁99-127。而若依據《莊子》所記述,孔子、顏回有心齋、坐忘之術,則早期儒學中又存在神秘主義。然《莊子》所述,一般將其視爲寓言,並不作爲早期儒家中存在神秘主義的確切證據。筆者過去對此曾有少量討論,②關於早期儒家中的神秘主義,筆者撰寫過《〈內業〉與〈大學〉》、《〈五行〉與神秘主義》;對於“慎獨”,筆者亦以爲當從神秘主義的角度去理解。這些文字均見於拙著,《思孟之間儒學與早期易學史新探》(上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然未能通貫。早期儒學中的神秘主義,依然是一個有待證實的問題。本文擬借鑒西方靈知主義的“神性自我”的概念,③關於靈知主義,筆者主要參考張湛,《神性自我:靈知的理論、歷史和本質》(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7)。張湛論文中引述約納斯的論述,認爲靈知主義理解的人包含血氣、靈魂與靈,靈即神性自我,又稱“普紐瑪”(pneuma),見其論文頁100。其中有一點非常關鍵,即靈知主義認爲靈魂之中又有靈,這與中國早期神秘主義的心之中又有心的講法,在形式上非常類似。也就是說,如果作形式類比,早期儒家文本中講的與心並立的意或內心,就是早期儒家神秘主義中的神性自我。這個神性自我同樣具有類似靈知主義的神性自我的內包與外融的結構,意之內包,即所謂“身所以主心”(《性自命出》),即《大學》講的“身有所憂患,心不得其正”;意之外融,即儒家的修身,內容當爲人之儀表,《詩》所謂“人而無儀,不知其可”。通過內包與外融,事實上構建了更大的神性存在,也就是聖人。聖人是神道立教者,是內外兩方面的完美存在。聖人是儒家的典範之人,具有神性,早期儒家中的神秘主義派別實際上正以其爲研究和追求的對象,神秘主義實踐服務於成聖。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援用“神性自我”的概念,並不意味著中國古代的意或內心可以等同於靈知主義的靈知;並且,因爲早期儒家中意、心、身體,並不像靈知主義中那樣是對立關係,而是一體關係,因此早期儒家中的神性自我存在一個從意到意心身體合爲一體的放大。也就是說,文中使用的神性自我的概念,是在兩個意義層面上使用:一是與靈知主義的神性自我對應的心中之心,一是心中之心內包、外融後形成的神性存在。而後者可以早於神秘主義派別出現而存在,當時還沒有心意分疏。這樣看,早期儒家整體都具有未祛魅的特徵,而其中進行神秘主義修煉實踐的則是子思、孟子之間的儒家,《大學》、《五行》是他們的作品。討論早期儒學中的神秘主義,並進而討論與之相關的一些問題,不妥之處,請方家批評。
一、神性自我與早期儒家
儒家文本中有神秘色彩的內容是不爭的事實,《中庸》講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而爲參,都具有神秘色彩,而所謂聖人至誠,誠者天道,同樣具有神秘色彩。“誠”是《中庸》的核心概念,沒有“誠”,就沒有君子所貴的“誠”之。在天道與人道之間,有共通的內容。既然涉及天人相與的問題,便不能說早期儒學中沒有神秘主義。关切神人相與或天人相與问题是神秘主義的共同特點。
以靈知主義爲例,他們認爲,每人都有一個神性的自我,修煉的目的就是要讓神性的自我呈現,從而成爲神。《中庸》當然沒有談修煉,而是講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講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所謂雖愚必明。顯然,君子想達到聖人之境界,可以通過學習實踐實現。这裏就有一個有趣的問題,儘管《中庸》不是通過神秘修煉達到聖人境界,但其所達到的境界與神秘主義者所要達到的境界沒有本質區別。“明則誠,誠則明,天人一也”,張載的解釋實際指出了《中庸》君子成之的方向。准此,認爲《中庸》的作者同樣持有人皆有神性自我的觀點,應該並不爲過。對於聖人來說,他的整個存在就具有神性,所以能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而對於君子來說,他以聖人所制定的禮樂爲學習對象,勤學苦思篤行,最終也能達到聖人的境界。換種表述方式,君子成聖的過程,其實可以理解爲神性自我不斷呈現的過程,是神性自我走向自我實現的過程。
理解了這一點,對於早期儒家的一些論述,就可以獲得更準確的把握,比如說孔子講克己復禮爲仁,一般理解就是克制自己恢復禮,仁就是用禮來約束自己。學者或據此得出人是禮儀性存在的認識。這個解釋顯然很難與孔子講的人而不仁如禮何融會貫通,按照後者的意思,仁的品質是禮具有意義的前提,僅僅是禮儀性存在,本身並不具有價值。而如果仁就是用禮來約束自己,這似乎陷入了邏輯悖論。仁意味著接受禮的約束,而沒有仁的禮又沒有價值,邏輯上究竟誰在先,成了說不清楚的問題。如果接受人具有神性自我的講法,這個地方就不存在邏輯悖論了;當然,禮也不是對人的約束,復禮也不是恢復禮。人具有神性自我,克己只是克去現實自我中多餘的部分,使神性自我呈現出來。這個神性自我便是真正意義上的人,也就是仁者人也的基本意旨。復禮之復,應該理解爲合,克去多餘的部分,使自我存在符合禮的要求;而禮原是聖人所作,符合了禮的要求,就意味著自己也近於聖人。克己復禮的過程就是神性自我的呈現過程。這樣理解,與人而不仁如禮何就不存在衝突了。不仁而有禮恰恰是前一種理解所導致的,是仁的喪失,而非成仁的過程。如果那樣,禮就沒有任何意義了。
禮表面看起來是一套規範,其實質卻是神性自我存在的範型,所以孔子講爲仁由己。仁人的建構不是從禮開始,而是從己開始,從吾欲仁斯仁至矣的心境開始。郭店楚簡《尊德義》有一句話很難理解,“學非改倫也,學己也”,學習自己,從存在神性自我的角度就很容易理解,神性自我的存在有一套範型規定,學習的目的就是習得這種存在的範型。這個過程中,學習與呈現共存,是不斷認識自我同時又是自我不斷呈現的過程。
如果這個闡釋思路可靠,早期儒學與神秘主義存在相似背景這一認識,應該可以成立。只不過儒家沒有選擇神秘主義的修煉方法,達致理想的彼岸,而是通過理性的學習實現這個目標。孔子用親身實踐走出了一條通向彼岸的道路,所謂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不過,儒家的這個成聖過程過於漫長,《中庸》的道路也非一般人所能堅持,對於期期致天下太平的儒家來說,這不是一條現實的道路,轉而求助於神秘主義,應該是一種可能的辦法。
儒學的早期文本《大學》,筆者判斷就運用了神秘主義的學說。其所謂格物,筆者理解就是來精氣,神秘主義文本中本有天仁地義淫然而自來的話。筆者過去討論《大學》中的神秘主義,有一點沒有特別關注,即慎獨與誠意的聯繫。《大學》在討論誠意時引出慎獨的話題,二者間必有關聯。前面討論早期儒家承認存在神性自我,這個神性自我存在於哪裏?有沒有辦法將這個神性自我有意識地引導出來?這是早期儒家關切的問題,也是早期儒家不同於其他學派的神秘主義的地方。
自我一定存在於意識之中,只不過,意識有有意識與無意識之分。按照神秘主義的看法,普通人的意識被物欲污染了,所以他們不能發現真實的自我,只有去除物欲,進入無意識狀態,才有可能意識到真實自我,意識到神。早期儒家的高明之處在於其將意識分爲意與心兩個層面,神秘主義文本《內業》中講的心之中又有心焉,也是這個意思。通常講的意識就是心,而無意識就是意,所謂真實自我就存在於意中。①有一點要說明,筆者過去以爲《大學》中的“意”是潛意識或者表層意識,這個判斷不完全可靠,二者不能完全等同。當然,真實自我也不等於神性自我,神性自我是神與人的結合體,不是今天人格心理學中講的本我。嚴格地講,慎獨與神秘主義中內包的修煉不完全等同,內包是指向與本體融合,不過,思孟將性與良知良能都訴諸天命,慎獨也就有了這個意思。自我形成也就是作爲本體的天之誠。《中庸》的誠或誠之,應該都是指向意中的真實自我,與《大學》的誠意具有對應關係。
《中庸》也講慎獨,其語境是“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見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不睹、不聞應該就是無意識境地,後面的隱、微之說,筆者理解是在講人心道心。無意識中也有心,所謂隱微之內心,就是指無意識狀態下的意識活動。這樣看,《中庸》的慎獨確實與無意識之意聯繫在一起。筆者已經指出,獨與神秘主義文本中講的精則獨是同一種狀態,這在《大學》中比較容易解釋,因爲其前的格物即來精氣,精氣充盛,獨自然生。問題是獨究竟是甚麼,用神性自我來理解也許是一個比較好的講法,慎,前人已指出可以讀爲誠,②郝懿行、王念孫據《爾雅·釋詁》讀“慎”爲“誠”,見王先謙《荀子集解》卷二,上海:上海書店,1986,頁29。慎獨就是使神性自我成立。
慎獨在早期儒家心性修養中的意義,筆者理解應該是服務於未發之中發而皆中節這一目標。孟子四端中有禮,是神性自我的組成元素,如果神性自我呈現,發而皆中節自然不是問題。《大學》的致知,所致應即明乎善之知,而神性自我中應該包含善的因數,沒有善,談不上神性自我,至少不能說是儒家的神性自我。仁義之善存在先天性,後來孟子講仁義禮智根於心,也是先天的。《中庸》講,明善是誠身的前提,所以致知必須在誠意之前,不先致知,無法明辨何謂善,也就不能成其獨,亦不能明乎神性自我。而神性自我不立,就不能保證未發之中發而皆中節,更不能保證後面的修齊治平的實現。
二、孟子的祛魅
孟子的四端是對神性自我祛魅的結果,試詳論之。
神性自我的呈現,不是單純的善的發用,孟子講的政治上惟善不可以獨行,在这裏同樣成立。善必須依附於性、依附於禮才可以表現出來。这裏很容易犯一個認識錯誤,即認爲性中本有善,宋儒將性區分爲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系在子思、孟子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來,而孟子的思想是對早期儒家中的神秘主義背景進行揚棄的結果。
從孟子開始,早期儒家的神秘主義背景已經很難看清。《中庸》講天命之謂性,郭店簡《性自命出》講“性自命出,命自天降”,將性視爲天之所命,而對心之善否並未加以規定,所謂“心無定志”,“君子逮其心爲難”;孟子將性與命作了分疏,通常講的欲望,他認爲是性;而仁義禮智聖,他認爲是命。但前者君子又謂之命,後者君子又謂之性,這樣他就將善心的問題帶入到了性命的思考中。他講盡心、知性、知命、知天,心與天聯繫在了一起,有了所謂天爵,有了所謂良心。這些論說的出現,是揚棄神秘主義的結果。此前的論說中沒有良心之說,但善心有可能會生成,即神性自我中存在善心,只不過神性自我非一般人能夠使之呈現,必須達到聖的境界方可以呈現。
郭店簡《五行》中將仁義禮智四行和謂之善,是人之道,可以不形於內,人可以去實踐。四行必須加上聖,才能轉化爲德之行,而聖無論是形於內還是不形於內,都是德之行。這個德非一般人可獲得,必須是能夠得天德的人才可以謂之爲聖人。而只有成爲聖人,才可以使神性自我呈現。這與一般神秘主義理論一樣,神性自我的被意識,本身以修煉者成神爲條件,神性自我與成神,二者互爲條件。在孟子之前,君子成聖與獲得聖德也互爲條件。《大學》的格物同樣是這個思路,不能格物來精氣,後面的過程都無法展開,但能夠格物,則意味著已經成聖成神了。
孟子揚棄了這一切,在他看來,過去人講性,講的都是故,也就是《五行》中講的不形於內的四行,而他講的性,則是良心,是根於內、形於內的。他祛除了聖作爲神性自我呈現的前提,當然同時也就祛除了自我的神性,他的良知良能是神性自我的人格化的結果,是人的完全的道德覺醒的結果。所以他有人皆可以爲聖人的論斷,當然他已將聖人作了祛魅,還原其爲人。在馬王堆帛書《五行》中,聖不形於內也是行,聖德人人可以踐履,這應該是孟子之後的講法。
關於古代聖人,孟子有一個講法,“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這個分疏筆者以爲就是《五行》德之行與行的分疏的祛魅後的形式。因爲他將神性自我祛魅,並以之爲性的構成。堯舜之爲聖人,自然是天性如此,湯武之於堯舜,相當於君子之於聖人:聖人爲誠,君子爲誠之,身之即爲誠之。《五行》中的德之行是誠,行則是誠之。这裏我們也可以理解,孟子講的明明是良心,可他偏偏說是性善。因爲神性自我不能再講,若是不這樣講,古代的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他也無法講清楚,現實中的人並不是按良心來行爲的。把良心歸爲性,這個問題就解決了,這應該是他將通常講的性命分疏顛倒過來的問題意識。
孟子的良心說,意味著早期儒家思想進入了世俗化的階段,與過去的宗教思想劃清了界限。神性自我的存在與宗教上的神道立教聯繫在一起。神道立教的要旨是在神與人之間安排一位中間人的角色,一般人以其爲模仿的對象,服從他的教化。他既有神性的一面,同時又有人性的一面,神性自我因之而出現。這是人的自我意識最初的萌芽,其至少在商末周初已經出現了。《易經》講的“有孚惟心”,“有孚惟我德”,說明那個時代人已經意識到自我的存在,德已經內化,只不過,那個時代的自我意識應該是基於神性自我而提出的道德自信,還不可能達到孟子的認識水準。而這個觀念應該就是孔子到孟子之前的儒家心性道德學說展開的前提,孟子的道德學說則是對其祛魅的結果。
祛魅,使得心性修養方法發生了變化,心的作用佔據了主導的地位。孟子講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講心志集於義,然後得浩然之氣,都是強調心在心性修養中的作用。氣對應的是性,是身,過去《大學》講格物致知,講身有所恐懼憂患則心不得其正,以及《性自命出》講“君子身以爲主心”,都是強調修身對於養心的意義。所以,孟子以前的儒家都強調禮的重要性。從孔子到子思,都強調學習,學習的內容主要是禮,所謂學而時習之。禮的最直接的作用是規範人的肢體動作,動作得度,心氣也正常。《中庸》講“明哲保身”,應該也具有提示身對於心性修養的重要性的指向。到了孟子,身的地位顯然退居次要地位,心成爲心性修養的主導力量。他講的養浩然之氣,主要辦法是心集於義。當然,這不意味著身不重要,惟善不可以獨行,心的追求需要通過身去實踐。孟子說,天下無道,以身殉道;天下有道,以道殉身。有道無道,由心決斷;以身殉道還是以道殉身,也是基於心之決斷。
身心在心性修養中的地位轉換,發生在郭店簡的時代。郭店簡一方面講身以爲主心(《性自命出》),另一方面又講心爲身之宰(《五行》);告子也講不得於心,勿求於氣,都早於孟子。如所周知,郭店簡的“仁”字從身從心,這應該是個會意字,意指身心合一爲仁,或主身,或主心,主身者不能忘心,主心者不能忘身。這一點今天很容易理解,肉體與靈魂相結合,才是完整意義上的人。
筆者曾判斷,郭店《五行》不能稱其爲思孟五行,①參拙著,《思孟之間儒學與早期易學史新探》(上編),第五章,“‘思孟五行’辨析”。因爲它既不是子思的思想,也不是孟子的思想,裏面講心爲身之宰,筆者判斷是講外心爲身之主宰,這不見於子思的論說;其承認神性自我又不見容於孟子,將其置於思孟之間應該是合適的。不過,需要解釋的是,荀子明確講子思倡之,孟軻和之,思、孟的思想中應具有與這個神秘主義派別相似的內容。這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一是思、孟的思想中都存在所謂天人結構,都要略法先王,旨在成爲聖人,《五行》德之行與行的分疏,在《中庸》《孟子》中都有反映。二是兩人都重視意識中類似意的東西,思、孟都不是明確的心、意二分說者,但他們的論說實質上都有對意的重視與關切。《中庸》講的誠,沒有明確講是誠意,但對照《大學》,可以判斷其講的是誠意。所謂“至誠如神”,與神秘主義文本中講的“意行似天”內涵相近。孟子講的良知,意涵也接近於意,所謂仁義禮智根於心,心弗思弗得,實質上是將四端置於心中之心的位置。這些內容,構成了思孟學說的基礎,倡和之義,當在於此。
然思孟並不主張通過神秘主義實踐成聖。《中庸》主張通過學習達到“明”,“明”指向對神性自我之明,是對善的明。能明乎善,則能誠乎身,自我之明即自我之成。孟子雖講心志集於義,但他也講反身而誠,而他的良心之論,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理解爲包含了兩重心的結構,即本然之心與實然之心。他們都不明確劃分心與意,意、心、身的結構在他們那裏只是心、身結構,即身心合一爲仁。所謂思孟學派大致可以成立,但主張神秘主義修煉的應是其中的亞派別,《五行》自然也不能稱其爲思孟五行。
三、《易傳》的性理觀
早期儒家中的神秘主義線索不限於《大學》《中庸》這一系,事實上還存在另一路的神秘主義,即《易傳》。
《易傳》的有些論述,與孟子的思想很容易混淆,《說卦傳》講的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這與盡心盡性知命知天的路徑很相似,但仔細區分,二者其實不同。《繫辭傳》講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天下之故即孟子講的天下之言性者。也就是說,《易傳》講的性還是孟子之前的儒家談的性,還沒有達到孟子對性命交替的認識水準。其與思、孟的性、命、天的路徑相同只是形式上的,實質內容並不相同。
《易傳》的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窮理不是要求個體生命積極地去探索求知,而是要求人洗心、退藏於密,以實現感通。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易簡本身不包含積極探索的意思,相反是要求人澄心靜慮,從聖人所作的易象中悟得天下之理。①《朱子語類》卷124:“先生謂祖道曰:陸子靜答賢書,說個‘簡易’字,卻說錯了。‘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是甚意思?如何只容易說過了。乾之體健而不息,行而不難,故易;坤則順其理而不爲,故簡。不是容易苟簡也。”朱熹將易簡之義與《大象傳》聯繫起來思考,有其合理性,但問題是他將知與能理解錯了。這裏的知與能,筆者判斷是與孟子的良知、良能相對應,先於行爲而存在。要獲得這種知與能,就《大象傳》講,也要先退藏於密,進行冥想感通,然後付諸實踐。所謂與太極合一,無往而不合於天下之故。因爲言不能盡意,聖人作象以盡之,真正能夠窮盡理的是易象。天下之故雖包含理,但不是周延的理,只有窮盡易中所蘊含的理,才能與太極合一。六十四卦來自八卦,八卦來自四象,四象來自兩儀,兩儀來自太極,由六十四卦層層上溯,最終一定能夠達於太極。與太極合一,意味著從根源上掌握理,感通天下之故只是其自然結果。因此必須先窮理,然後才能盡性,先精通易,然後去實踐人生。朱子將窮理理解爲一個求知的過程,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弄得很支離,其實不符合《易傳》的思想。《易傳》的窮理是與本體合一的過程,只有與本體合一才能無往而不合理。《大象傳》講君子視乾,則自強不息,視坤,則厚德載物。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對於君子來說就是所謂命,易象中蘊含的理在人性中有其對應的存在,視易象,則可以激發人性中固有之得。這個所得由天所命,激發出這個所得,就是盡性,也就是踐履天命。
需要要說明的是,这裏不是說君子占卜遇到甚麼卦,然後採取相應的行動。六十四卦是一個整體,表現的是太極,太極不可見,君子常存六十四卦於心,也就相當於常存太極於心。六十四卦象對應的天下之理,是作者認爲的君子所當具的全部,本身是一個整體,也就是聖人的德行才能的全部。
孟子的知性知天,其前提是盡心。天下之理根源於心,盡心表面上看也是窮理,其實是心創生理。理不是固定的存有,《內業》講日用其德、日新其德,在孟子这裏,就是日用其心、日新其理。同樣的理,在不同的語境中有不同的表現形式。日新的基礎在於心,不同語境中有不同的新理闡釋需要,這需要時時用心。
孟子不講盡性,也不講至於命,因爲性命之能否實現有環境的因素。心生出新理,但因環境的影響,理卻未必能夠得到實現,盡性而至於命就成了空話。孟子講立命,其意是追求心中所認同的理,但能否追求到是另外一個問題。他講盡其道而死者爲正命,但這只是在獨善其身的意義上成立,是與桎梏死者相對應而講的,本身是保守的,不能說已經盡性。盡性不完全是仁的問題,還有智的問題,所謂成己成物。因爲對於孟子來說,仁與智都是人所固有的,這是他與《中庸》的不同。《中庸》中成己成物在邏輯上分離,實踐中盡性與盡人之性、盡物之性也分開。《中庸》沒有良心說,而是神性自我,人性與神性自我是分離的。孟子的良心與人性交織在一起,在他的邏輯中,盡心可以做到,但盡性則很難,脫離了神性的支撐,人只能成爲獨善其身的聖人,卻很難成爲兼善天下的聖人。①嚴格地講,孟子的思想模式與《中庸》是相似的,只是對神性自我進行了祛魅。不過,因爲所處時代話語的不同,他們的論說即不相同,因爲政治變了。《中庸》還處於德禮政治的語境中,而孟子則處於從德禮向道法轉變的過程中,儘管他立足於古典的儒學,面對的卻是世俗的政治,他處在固有的學說已完全無法實現的時代。孔子、子思面對的其實已是理想不可能實現的時代,但孔子、子思的時代思想語境比孟子好。
《易傳》所謂感通論,與良心說也不在一條線上。孟子的良心之說不需要費心去感,是因物自然而生;其言萬物皆備於我,所謂物備於我,當是指的萬物之理備於我,說的是存於我心,萬物有理,但這個理的根源在於我心,所謂理由心生。後來陸象山講我心即宇宙,是從孟子發展出來的,但不完全相同。①關於孟子的萬物皆備於我,學者有不同認識。牟宗山認爲這裏講的就是心即理,與陸九淵的心體論相同 (見其著,《宋明理學演講錄》之二,“不同層次之‘理’的簡別”,收入牟宗三,《宋明儒學的問題與發展》,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勞思光認爲是指心具眾理 (見其著《新編中國哲學史》一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頁146)。筆者贊成勞思光的見解,如果心本身就是理,就不存在人心、道心的分疏了,而偽《大禹謨》說要“允執厥中”,也就是人心、道心執其中。並不是唯道心是求,這不符合儒家的中庸之道。且不論這種認識是否可靠,其與《易傳》不是同一條路徑當可以肯定。對於《易傳》來講,天下之故與人性是並行不悖的關係,人性之善不妨天下之故自有其理。理學之超越的理實際上系基於此提出,人性與天下之故均有理存在,理是二者共通的基礎。所以理是本源是本體,宋儒講太極即理。並且在《易傳》中,天下之故具有命的特點,是先在的,人之心性是後在的,人性之理不外於天下之故。這也與孟子不合,孟子講人皆可以爲聖人,天下之故本身需要接受良心的檢驗,理的根基在於良心,而不在於天下之故。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文王的言行是天下之故的組成部分,但對於豪傑來說,沒有這些故,一樣可以擔當天下的道義。
很顯然,《易傳》與孟子不是同一條思想路線,一從窮天下之理出發以至於命,一從盡良心出發,以知命。兩者都有性善論,但孟子的性善論其實是心善論,只不過他也認爲是自然的,具有性的特徵。《易傳》的性善論,主體不是心,而是踐履天下之故的血氣之性。宋儒的性即理的講法與其更接近,只是將氣從性中剝離開來,性成爲純粹的理。孟子的性善論是從神性自我祛魅後得來,由《易傳》得出的性即理卻不存在神性自我的預設,相反很容易通向未發之中本身蘊含理的認識,通向對《中庸》的誤讀。對於《易傳》來講,只有性中本有理,才可以與天下之故相感通。對於《易傳》來講,心對於性氣發抒的規範作用並不明顯,本身並不具有道德價值。其所以能盡性,不是對於性的發抒實現合目的的規約,而是基於對性中之理的揭示,窮理後循理而動就是盡性。
四、內在超越
與早期儒家的神秘主義認知背景密切相關的一個問題,是所謂內在超越,追求內在超越被部分學者認爲是中國文化的基本特徵。據論,這是與西方宗教對照的結果,聖人天德,性理是天命之內化,從而達到內聖境界,超越自我,即爲內在超越。①內在超越的典型表述是牟宗三在《中國哲學的特質:天命下貫而爲性》中提出的,所謂“天道既超越又內在”,轉見崔大華,《儒學引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頁849。關於這個論斷,學者有不同的認識,或贊成或反對,贊成者居多。從宋明時代人的精神追求看,這個判斷是可靠的。不過,這個基本特徵是否真是中國文化的基本特徵,或者說,這種內在超越是否應當如宋明以後所表現的那樣,則需要思考。
宋明以後的新儒學的基礎,筆者判斷是《易傳》,②參拙文,《〈易傳〉〈中庸〉與宋明理學》,刊於《古典研究》2015年第2期。而這恰是基於與早期儒家不同的神秘主義背景而提出的性命學說。以此爲背景,經過宋明儒的提煉,確實很容易出現內在超越,但這種內在超越是否合乎早期儒家的宗旨,值得反思。孔孟無論如何不可能接受以理殺人,當然也不會接受無條件地服從於所謂理,因爲這在根本上背離了早期儒家仁民愛物的宗旨,背離了中國文化講求公平正直的精神。孔子講殺身成仁,孟子講捨生取義,表面上看很符合爲道義可以不惜生命,但這種獻身精神只是特定歷史場景中的抉擇,不是日常之道。如果對道義的暫時背離不危害到他者的生命,即便孔孟恐怕也不會選擇放棄生命。背離不等於違反,儒家就贊成在亂世選擇沉默,孔孟都主張窮則獨善其身,有明哲保身的追求,③後人用“明哲保身”傾向於貶義,這其實是誤解。明哲保身有求正命之義,不是相對於追求道義講的。孟子既講捨生取義,又講不立於嚴牆之下,後者便是明哲保身。這其中蘊含對自我價值的肯定。自我不保,中正之道何以傳呢?
就早期儒家來講,與其講是內在超越,不如說是對神性自我得以呈現的追求,而在其呈現的過程中,也很難用超越這個詞來形容道的追求者。神性自我是神與人的綜合,以神道立教模式下的聖人爲典範。這種自我的呈現,既不是完全的神,也不是完全的人,而是神與人的綜合,綜合的結果就是眾所周知的中庸之道。儒家希望達到的只是中道,取得人心與道心的平衡,而不是超越於世俗,成爲純粹的神性存在。然達到中道本身並非易事,對善的洞察也非唾手可得,所以從孔子開始講學習,希望從學習中獲得對善的領悟,實現中道而行。孔子講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或者進取,或者有所不爲;總之,不能流於凡俗,流於凡俗的結果必然是自我的喪失。追求恰到好處地表現自我,顯然不能算是一種超越。當神性自我被祛魅,良知登場,人的道德實踐根本談不上甚麼超越;如果算是超越,也是對凡俗鄉願的超越,對於小人的超越。
內在超越常常與內聖聯繫在一起,然內聖不是儒家的詞彙,而是出自《莊子》。事實上,從神性自我的角度觀察儒家,其並不存在內聖的問題。儒家之聖合內外之道而成,孟子的仁義禮智也是合內外而成,仁義本於內,禮智主於外。①這個判分基於《孟子》未對禮智根於內進行論證而提出,是權宜劃分。筆者理解,禮義都兼具內外;而明乎善之智則更多基於內,同時又運用於外;仁指向成己,但又包含愛人之義,也是內外兼具。儒家講的德大多內外一體,但發端存在內外先後的問題,而不同的思想家有不同的認識。比如智,子思那裏可能首先是明乎善,孟子則主張善根於心,智主要指向於外,所謂是非。孟子之所以講都是根於心,是因爲其原先本於神性自我,還未得以進行內外的分疏。這中間已經包含了外王的向度,禮與智主要服務於外王,古代的聖人,是內聖外王的統一。神性自我、良知良能都不是單純的內聖問題。內聖外王命題的出現是與政治轉型聯繫在一起的,是聖與王不能統一的結果。在上古德禮政治中,聖與王可以統一,內外的價值統一於神性自我之中,孟子做祛魅的工作,也將其完整接受下來。隨著德禮政治向道法政治轉變,內聖與外王不再能實現統一,從內聖中不再能開出外王,超越的話題也因之而出現。
德禮政治是基於神性自我的政治,是基於聖人天德的政治。“德也者,得於身也”(《禮記·鄉飲酒義》),某種程度上可以理解爲自我之得。偽古文《大禹謨》講“惟精惟一”,《大學》《中庸》講慎獨,《五行》講能爲一,君子可以慎其獨。用哲學語言表述,獨或者一,其實是自我的同一性,得一、誠獨,意味著獲得了自我,而這種獲得與神秘的精聯繫在一起,天德者,天賦其精,《大學》講格物,是通過神秘修煉使精來,精來則能一,則能誠其獨,使自我呈現。在神秘主義語境中,禮智都本於內,致知所致的即是明乎善的能力;禮同樣如此,是自我的呈現。內聖與外王在其中是統一的,或者說內外之分並沒有意義。
道法政治不是基於自我的政治,而是基於公義的政治,是從天下之理出發的政治。內聖之中固然有對理的偏好,但內聖並不能開出完整的天下之理。禮有文質,是非難言,這都是世俗政治中內聖無法通向外王的障礙。由內聖得出的外王必然是威權主義,而這是道法政治所欲盡可能排斥的。真正的道法家都排斥聖人,他們將法治理解爲民之命,這是從編戶齊民社會的角度提出來的,更強調平等。儒家的由自我出發,親親然後仁民的差序格局無法滿足人民追求平等的願望,由儒家的觀念出發建構的道法政治模式,並不是理想的政治模式,所以,在世俗政治中,內聖很難開出真正的外王。
但莊子後學提出內聖外王自有其價值。真正的道法政治要求爲政者摒棄私心,完全從公義出發制定法律,某種程度上可以認爲,爲政者只有排斥了自我才可以制定出好法律,而莊子學說正好可以滿足這個要求。莊子講吾喪我,喪失自我恰好可以用來制定法律,這樣制定出來的法律才能真正合乎公義,合乎天下之理。內聖的主要意義指向正在於此,當然還同時包含神性之知,對於天下公理的知。
這種分疏在講神性自我、講良知良能的儒家中建立不起來,引入這種分疏的結果,必然產生自我與公理的衝突。孔子特別強調自我的界限,己所勿欲,勿施於人,自我的不恰當運用會導致公理的損害。西方學人討論自由,主要關切點亦在於此。但儒家顯然重視自我,儒家的道,如綱常倫理,原是從自我出發的。郭店儒簡《六德》區分門內門外,講爲父絕君,不爲君絕父;爲昆弟絕朋友,不爲朋友絕昆弟,這都是重視自我的體現。而對於宋明儒學來說,他們強調天理,則又必然帶來對於自我的損害。因爲他們的天理是建立在不合理的政治秩序上的天理,是三綱五常,其中又以君臣倫理爲重,在這種天理之下的內聖必然是滅失自我的內聖,這可以講是內在超越,但不符合孔孟儒家的宗旨。
綜上所述,借助靈知主義的神性自我觀念闡釋早期儒家學說,可以獲得更貼切的理解。基於聖王神道立教的觀念,早期儒家的成德學說中蘊含神性自我的預設,孟子對其進行祛魅,提出了良知良能之說。基於早期儒學中神秘主義的線索,《大學》、《中庸》應該是孔孟之間的文本,而郭店簡《五行》則處於思孟之間。另外一種具有神秘主義背景的文本《易傳》,在性、命、天的關係的認識上,與思孟很相似,但二者屬於不同的心性學說,《易傳》是性善論,孟子是心善論。早期儒家蘊含神性自我預設的學說,不應該用內在超越來描述,所謂內聖外王也不適合用來描述這種學說。後世儒家表現出的所謂內在超越存在學派理路上的紊亂,背離了早期儒家的宗旨。
參考文獻[References]
《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The Bamboo Slips of the Chu Tomb at Guodian.Beijing:Cultural Relics Press,1998.]
《周易》,《十三經注疏》影印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The Book of Change.Photomechanical printing edition of the Annotation of the Thirteen Classics.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1980.]
陶磊,《思孟之間儒學與早期易學史新探》,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Tao,Lei.A New Studies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Yi-ology and the Confucianism between Zisi and Mencius.Tianjin:Tianjin Ancient Book Press,2009.]
張湛,《神性自我:靈知的理論、歷史和本質》,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7。 [Zhang,Zhan.The Divine Self:the Theory,History,and Essence of the Gnosis.Diss.Fudan University,2007.]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Zhu,Xi.The Collected Annotation of the Four Books.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1983]
Early Confucianism and M ysticis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rly Confucianism between Confucius and Mencius could be demonstrated better with the help of the concept of the Divine Self of Gnosticism.The topic that Confucius advocated,restraining ourselves to conform to the etiquette,means eliminating the superfluities and preserving the perfect self.Be careful of the solitary selfmeans to set up the perfect self.The concept that held by Mencius,the innateknowledge and ability instinct,is the result of getting rid of the charisma of the Divine Self.To ague in favor of Yao and Shun as the born sages when the Divine Self had been disenchanted,Mencius changed the connotations of Nature and Mandate each other,which was exactly contrary to the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these two concepts.So his idea of the innate knowledge and ability instinct was usually believed to be the proposition that the human nature is good.In the course of being deprived of the charisma,the basis of the theory of the early Confucianism to become a sage had been changed from the body to themind.Based on this epistemological frame,those early Confucian textswhich contained themysticism could be locatedmore exactly.The Great Learning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should be composed between Confucius and Mencius.The FiveMoral Conducts,one of the bamboomanuscriptswhich excavated at Guodian in 1993,could not be defined as the theory of Zisiand Mencius.The Commentary of the Yi has the similar idea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basic concepts such as Nature,Mandate,and Heaven,with the orthodox Confucianism.But they have different premiseswith their theories,the former believes that reason is contained innate in Nature,while the latter believes that reason is originated in themind.So they belong to different theories of themind and nature.The concept of the Divine Self of the early Confucian is synthesized with gods and human.It originated from the ancient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culture,which based education on the divine.Compared with the pursuit of the realization of the Divine Self of the early Confucian,the pursuit of the intra-transcendency of Neo-Confucian in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is quite another story.
early Confucianism;mind and nature;Divine Self;education based on the divine way;intra-transcendency
關鍵詞:早期儒家 心性學說 神性自我 神道立教 內在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