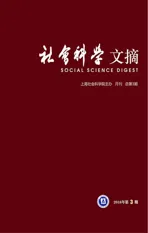顾颉刚的古史与民俗学研究关系再探讨
2016-11-25袁先欣
文/袁先欣
顾颉刚的古史与民俗学研究关系再探讨
文/袁先欣
“故事”与“古史”关系再考
顾颉刚以“古史辨”研究最负盛名。为人广泛注意的是,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与其对民俗学的开拓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向来,“用故事的眼光解释古史”这一“古史辨”的特殊视角,常被理解为顾颉刚的民俗学视野单向影响到其历史研究的结果。然而,事实是否尽然如此?
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顾颉刚自述其 “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念得益于青少年时对民间故事、戏曲、传说的关注,这种关注在胡适历史演进研究法的刺激下,启发他产生了“一种新的眼光”。这个由顾颉刚自己建立的“从故事到古史”叙述影响颇大,其真实性甚少有人质疑。然而,若我们将《古史辨》的相关论辩以及同时期顾颉刚关于歌谣、戏曲、故事、民俗的研究观点,与《〈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对比阅读,却会发现另一个“从古史到故事”的时间序列:顾颉刚虽于1923年即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但此一时期他着重阐发的并非史事的流变样貌,而是上古史的真伪考辨;其故事学研究的思路此时也未成熟。顾颉刚的侧重态度在1924年前后经历了微妙变化,不仅影响到顾氏此后继续讨论古史的态度和视角,还直接左右了他1924、1925年“孟姜女故事研究”的方向。
“层累地造成的古史”完整表述最早出现在1923年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其中从一开始即已包含了两个不同的方向:其一,是通过对比古今,辨别历史叙述中的真伪;其二,是注目历史叙述在传播流变当中的差异变化。对这两个方向的不同侧重实际形塑了顾颉刚后来的古史及民俗学方法。
《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发表后,立即引发顾颉刚、钱玄同与刘掞藜、胡堇人的论战。论战焦点集中在禹是否存在、禹之神圣性的问题上,其中作为反方的刘掞藜凭借严谨的经学与小学功底,对顾氏文字考辨和逻辑推衍展开批评。顾氏后续讨论中虽对禹为九鼎上“虫”的观点有所退让和保留,但仍不遗余力地论证禹之天神性、《尧典》之晚出等观点,刘掞藜则对此展开了巨细无遗的批驳。
1924年2月,胡适为这场辩论写了一篇总结性文章《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胡适不满于顾与刘的争论陷入琐屑枝叶,大力重提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当中自叙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见解的三个意思。胡适认为,顾颉刚所谓“我们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史事,应看他最先是怎样,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意见,实际上构成了“顾先生这一次古史讨论的根本见解,也就是他的根本办法”。
通过大力表彰顾颉刚的“根本见解”和“根本方法”,胡适将注意力从顾刘其时汲汲于的“微细的错误”,转移到了宏观史学理论和方法论问题上。这一方面是救顾颉刚于刘掞藜穷追猛打的高招,另一方面,胡适将顾氏方法论的侧重点放在“每一种传说的‘经历’与演进”上,也是对顾氏本人在论战时具体实践其“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的隐微批评。事实上,顾氏之所以陷入枝末的字句争执不能自拔,正在于其不能放弃从真伪角度来辨正禹之存否。如顾氏能以较为彻底的“传说的‘经历’与演进”方法来讨论,则禹之存否本来是可被回避的话题。遗憾的是,1923年论战时的顾颉刚并未想到这一层。对于真伪的执着最终将顾氏拖入了细节阐释的泥潭,而胡适正是不满于此,才感到有必要拨正讨论方向。
导师提点的作用不言而喻。胡文发表后一个月,顾颉刚即写作了《我的研究古史的计划》,清晰展现了古史研究思路的转变。该文中,顾颉刚首次明确提出了民俗学在古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顾颉刚举古史中姜嫄“履帝武”而生后稷一事为例,指出学者对此种史事的态度一般可归纳为“信”、“驳”、“解释”三种。这三种态度都不可取,顾颉刚的自我期许则是“能处处顺了故事的本有的性质去研究,发见它们在当时传说中的真相”。从《我的研究古史的计划》开始,上古史事真伪的问题被搁置,顾氏关注的中心转移到古史/神话如何在流变中构成了如今的形态,“神话”也从“伪史”的同义词,转而成为一种民间信仰的传说故事。这一转移的基础正是胡适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中对“经历与演进”方法的表彰。由是故事的观念被引入,“故事的眼光”开始正式成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的一个重要面向。
“不立一真,惟穷其变”
胡适读后感对顾颉刚产生的另一个重大影响,是促成其酝酿已久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写出。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顾颉刚将自己最近两年孟姜女故事的研究整理也放在古史研究范畴下来叙述。这种“用故事的眼光来看古史”独特视角的产生,应当说仍是胡适读后感影响的后续,而非如顾氏自陈一般,是幼年来一直关注戏曲、民间故事的自然结果。顾颉刚当然对孟姜女故事早有关注,但值得注意的是,1923年10月,也即是顾氏与刘胡二人进行第一场古史辨论战之时,顾氏甚至曾经将已经搜集到的孟姜女故事材料交托表弟吴立模,由吴写了一篇同名论文发表。其时顾氏并未试图将孟姜女故事研究与正在进行的古史争论联系起来,甚至不甚重视地将材料交给他人作文,恰好说明他当时还执着于真伪史事之辨,未尝注意到孟姜女故事流变中蕴含的方法论突破。胡适读后感发表后,顾氏一个月后马上表示要重视民俗学在古史研究上的意义,当年秋天,在写作《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同时,开始将故事学方法引入古史研究,这些事件当然并非巧合。
现有的学术讨论中,吴立模的孟姜女研究同名论文常被忽视。然而,吴文虽非顾颉刚亲自写作,但主要论点、材料基本来自顾氏本人,应当说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1924年前顾氏对该话题的思考进路。对比吴与顾的两篇《孟姜女故事的转变》,更能看清胡适推重“经历与演进”对顾氏产生的影响。
吴文以时间轴上的流变为中心,描述孟姜女如何从杞梁妻变为哭倒秦长城之孟姜女。但吴文最后暗示,孟姜女的流变实为对作为“真相”之杞梁妻的偏离,其内在思路因而与顾氏此时论禹之真相问题时所循逻辑相同。
与吴文相比,顾颉刚的写作则更像是对胡适读后感中提出的一整套方法的实践。顾文中,“杞梁妻就是孟姜女”这一吴文中反复强调的关系被轻轻带过,文章主体着重铺陈了战国、西汉以前、西汉后期、唐朝这几个故事中心元素发生转变的时间点,注重的是从不同时段社会生活的具体状况,来解释故事元素转变的原因。有趣的是,摆脱了对溯源性真实的执着后,顾颉刚反而找到了另一种达致历史真实的方式:孟姜女故事的真相并不在其最早形态,而在于民众接受这一故事时,因时势、地方性、流传方式等原因,如何对其进行自发自愿的改造。这变动不居的流变中蕴含着最为普遍和真实的民众心理,而这部分“历史真实”却长期在经典历史叙述中被忽略掩盖。在《答李玄伯先生》一文中,顾颉刚用“不立一真,惟穷其变”八个字,来概括自己的古史和民俗学研究方法。
“民众”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悖论
以“不立一真,惟穷其变”为中介,顾颉刚得以从追寻溯源性真实,转向对另一层面历史真实的追问:后世人们出于种种因素,愿意以什么方式来接受历史并视其为“真实”?而要追问这一接受层面上的历史真实,又必须引入作为接受主体的“民众”。
自晚清以迄民国,“民众”概念自政治而入文化,一直是思想讨论的核心话题。顾颉刚对“民众”概念的理解和接受也在此潮流之中。与胡适大力推行的科学方法同调,顾颉刚表示他研究歌谣故事不在致用,只在求真,这就使得他与其他要在“民众”概念中注入价值因素的学人拉开了距离。歌谣运动初期,《歌谣》周刊上曾有真假歌谣之论,这一看法实际反映出知识分子对纯粹民众与民众之声的浪漫主义想象。其时许多论文皆提醒歌谣采集时不可窜入文人创作或修改的作品,最好自民众口中直接采来,其中又以不文之农民、妇女、儿童所唱为上。有文本依据的弹词小曲等则被目为文人模仿之作,已失天籁。然而事实上,处在文化和社会阶梯下层的民众艳羡并主动模仿上层文化形式,本极自然,并不全待文人“假作”。《歌谣》同人固然试图以眼光向下的方式颠倒传统的雅俗之辨与阶层对立,但他们构想出的民众形象又饱含理想色彩,与现实相去甚远。相较而言,顾颉刚在搜集民歌时,欠缺此种预设的理想民众观念,反而得以跳出流行的框架,呈现出另一幅色彩杂糅、更近真实的民众画卷。
然而,以客观知识的方式介入“民众”,并不代表这种操作本身能够完全摆脱政治性。以中立、客观为目的的现代科学知识带有自身的意识形态特征,在有关“民众”的客观知识被生产的过程中,“民众”依然难逃被定义、被观看、被书写的命运。与浪漫主义式的“民众”类似,顾颉刚的“民众”概念也诞生于文人贵族与民众的断裂和对立中,但与浪漫主义者将追求的终极价值放置于“民众”身上不同,顾颉刚的“民众”一方面对传统社会和文化体系构成了挑战,另一方面,又须最终臣服于科学和现代理性。在此意义上,顾颉刚对于民众较为客观的呈现,成为了启蒙政治合法性必不可少的一个论证过程。然而如此启蒙,又在不知不觉中再一次形塑了上下分离的阶层关系。这种一方面要接近民众、一方面又以知识方式异化和疏离民众,并在此之上再度无意识地建立现代式样的层级的方式,不仅仅存在于顾颉刚身上,甚至可说是包括民俗学在内的现代学术以及操弄现代学术知识的知识分子难以摆脱的悖论。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博士后;摘自《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