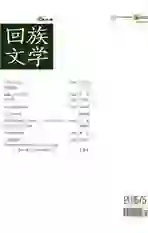在大理
2016-11-23叶多多
叶多多
每年都会到大理小住一段,有时候是春天,有时候是冬天。说大理诱惑,不免矫情。大理之于我,其实仅仅是一种习惯,过上一段时间,就想去走走转转,本不需要什么理由的。
懒洋洋的老墙,躺在角落里的小石磨,几方扎染的桌布,荡漾的云朵,小桥流水,苍山洱海,小溪里不时弹起一条小鱼,我垂着的手随时都可以触碰到路边的花花草草,绚烂而美丽。蓬勃,呼唤,沉默,沸腾,小片小片连在一起的菜地,大树,水源,神灵,满眼是我熟悉的风景。
很长时间,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基本上是马锅头、扎染、海菜花之类毫不相干的事物,微风,细碎的阳光,烤乳扇的小摊,小溪边的樱花,小院里的日子。那些井。
经常会想起那些场景。
还有那位做彩扎的老人赵云鹤。他能用帛或者棉纸扎出栩栩如生的彩轿、喜亭、高头大马、大红灯笼、龙凤呈祥、金童玉女、白鹤宝船、祥云缭绕等彩扎。白族人笃信神灵,无论红白喜事都要用到彩扎,有时候,仅仅是不顺、“撞着鬼了”,也要扎个彩扎把“鬼”送掉,病才会好起来,日子也才会顺起来。而赵老的绝活就是扎什么像什么,只要你能说出的鬼,他都能扎出来。
神秘的事物是很难用理性说通的,我相信神秘事物的存在,相信每个彩扎,每一道符号都凝聚着不朽的箴言。
很多时候,存在是相对的,正因为有了这些荡漾的缤纷、色泽、花瓣的出现,我才看到了焰火的升起,听到了骨朵绽放的声音,才触摸到了最真实的存在。
我从小就是个容易紧张的人,因此,心底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忙乱焦虑的间隙,在内心疲惫的时候,能够住在一个既舒适又朴素的地方,读读书,喝喝茶。于是,多年前我便辞去了工作,过着一种行走写字的简单生活。
我喜欢这种生存方式,松弛、自然,为内心的安静和成长而活着。也许我做不了什么大事,但我有勇气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
记得陪喇嘛华尔丹到大理崇圣寺时曾问过他,二十多年的寺院生涯,由一个小喇嘛成长为格西,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他淡淡地说,不断地学习,管住自己的心。我微微怔了一下,时间的力量是强大的,有时候,孤独与自由,真的很难说谁更好。
喇嘛华尔丹六岁出家到拉卜楞寺,这次专程到鸡足山拜谒了达摩祖师的修行之地后,又来到崇圣寺。
华尔丹的父亲当年也曾到过鸡足山朝山,不同的是,华尔丹的父亲是磕着等身长头一步一步从遥远的甘南走过来的,从第一年的春天走到第二年春天,整整用了一年的时间。如今的华尔丹是坐飞机来的,在华尔丹看来,虽然行走的方式完全不同,但宗教意义上的传承是一样的。
曾作为南诏古国、大理古国时期皇家寺院的崇圣寺不仅金碧辉煌、气势恢宏,也是中国南方最著名的佛教名刹,历史上曾有九位大理国国王在此出家为僧。然而,华尔丹千里拜谒,吸引他的偏偏是离崇圣寺仅仅几百米的枯木庵,这里是开山祖师义存最初栖止念禅之地。随华尔丹进到庵里,满庭寂寥,唯有来自唐代的两尊枯木兀自岿然。义存圆寂时说:“双柽扫地,石卵开花,我会再来。”当我双手合十的时候,我看到了时空中最华丽的不弃不离,无关繁华或者悲凉。
下山入城,我推荐华尔丹入住玉洱客栈。理由是这家客栈的店主是古城的土著,温良而宽厚,装修也朴素而舒适,门前有繁茂的花草,有小溪流过,老房子重新翻修过,楼梯有依稀的木纹,我不仅住过多次,也推荐不少朋友住过。果然,店主为僧人华尔丹专门安排了幽静的房间和打坐的卡垫。盈盈在握的暖意,记得我说了很多感谢的话。
喜欢随意走,出了客栈,路过首饰店、饼铺,现烤的大理粑粑,糖馅的,在清凉的空气里咕嘟咕嘟冒着热气,亦是我最喜欢的点心。拐个角就到了喜子的手工作坊,老远就能看见暖暖的灯光下,那张不饰脂粉的脸,那么好看。每次到大理都会去小店转转,挑选几件自己心仪的衣服。喜欢喜子的创意,她的优越之处在于化繁就简,看似普通的服饰,不经意就穿出了万种风情。再往前,就是一个叫“惑”的小酒吧,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在喝咖啡,声色迷离里,他们指尖的味道,该是相同的吧。我看到了大理世俗和娱乐的一面。现在的大理,生活成本也比过去高出了许多,原本一百元左右的房间,现在得一百五十元以上,旺季还得往上翻许多。
早些年去的时候,那些老房子改成的客栈里面还不能上网,读书便成了最快乐的事情。
在一个叫“藏客”的小酒吧里,我翻开了来自么卓本和他弟弟的唐卡画集,么卓本是个严格遵循传统的画师,诗性是他笔下最显著的特点,因而对他的画一直有着很大的期待。酒吧很复古,有一些茶马古道上的老东西。墙上,密密麻麻贴着一些流水账一样的客户留言,我喜欢平铺直叙的表达方式。
当然,看到古城的铺面大都由外地人经营,心里也不免怅然。
我觉得古城面临的新问题是如火如荼的旅游已经使这座千年古城不堪重负,商铺密布,人头攒动已经成了这里的常态。嘈杂的环境使古城里的土著越来越多地选择了搬离,我不由得想到,不远的将来,如果古城没有了原住民,将是怎样一番可怕的景象。
喜欢那些老字号店铺的银器,闪烁着寂静的光芒,犹如古莲,盛开于当下的日子里。我的手一遍遍地抚摸着那些银器,由此也认识了银匠董育才,禁不住诱惑,请董银匠专门为我打制了一对厚重粗犷的錾花手镯,心仪那种戴在手上沉甸甸的感觉。在另一间老银铺里,买了一只纯银的簪子,经常用它给自己在脑后绾一个松松的髻。
流连忘返。在我的梳妆柜里,大理淘到的银饰已经多到了让闺蜜眼红的地步。一件喜欢的银饰,犹如一场美丽的邂逅,至今记得那个四十多岁的手艺人,话不多,默默干活的那种。见我喜欢,便随手递了一个镂花的吊坠给我,微微一笑:“花开富贵,意思好得很。”当时,我并没有注意到它的花纹,只是被那种古朴和手艺所深深吸引。“花”与“华”谐音,在银饰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银饰并不仅仅是一种装饰,更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与幸福的向往和祈诵,在大理,银匠们都喜欢选择这类吉祥的花样与图案。
随手把一张碟放进光驱,盘坐于毯,镂花的银坠,无声的视觉盛宴。
喜欢有岁月感的东西,收藏纯手工的银饰,高超的技艺,一气呵成,令人叹为观止。夏天,配上简单的T恤,尽是风情。冬天,作为毛衣吊坠,亦很特别。明朗,汹涌,激荡,惶惑,艰难,黑暗,裂纹,都已经不再重要。在大理,很多时候,心情像是立于杯沿的一滴透明的水。
喜欢素未谋面,喜欢陌生的感觉,相信在连接着过去时光的巷子里穿行,自然会拥有真实的世界,很多看不开的东西自然也会放下的。
冬天的大理,阳光美好而轻盈。大片的老宅,我沿细细的甬道穿过去。对于我来说,有足够的诚实善良就可以,鲜有精力去计较太多的事情。
年复一年,不知不觉间,我发现自己竟然已经适应了波澜不惊的生活,那些细微的日子,久久地感动着我。
温暖常在。让内心慢慢结实,慢慢生长。
在大理,我遇到了很多同我一样选择了简单生活的人,不少艺术家买下院落隐居于此。安静,朴素,传统道德在古城里有普遍影响。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过上心满意足的日子,但清除身心里多余的东西确实是可以做到的。
选择大理,我们都是一致的。
彝族青年曲果在北京、上海、杭州、重庆和昆明都做流浪歌手,喜欢过居无定所的日子,而做原创音乐则一直是他峥嵘的告慰与依附。为此,他那个远在山村的母亲以为他中了邪,三番五次请当地最有名的毕摩为他安魂,希望他能够定下心来,踏踏实实过日子。其实,做自己喜欢的音乐,于曲果而言,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他沉迷其间不能自拔,以为一辈子都会这样过下去了。直到有一天他来到了大理,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阿莲。
现在,他在大理开了一间茶店,给自己的茶店取了个很文艺的名字:云上的日子。他的妻子,那个纤纤的广州女子,总穿着蓬蓬的棉布裙子,仔细地擦拭着陶制的茶壶和茶具,每天的日子具体而充实,他向着世俗的日子又迈出了一大步。
生存的过程或许就是自省的过程,他终于明白,没有精神和经济的自立与独立,漫游,不过是茫然与脆弱的真实写照。
如今,他们的女儿小豌豆都已经两岁了。我相信,他们会一直带着小豌豆在大理静静地成长。
许是大理的山水启发了我,我在大理完成了大型系列纪录电影《迁徙——在寻找幸福的路上》的策划和文字稿。里面的故事是我,又不是我,可这有什么要紧的呢。曲果成了影片第三集中的男一号。原来构思是以一个流浪的音乐人定居大理的故事来展开,基本上以曲果的真实生活为原型,讲述那些循着生活与自身节奏做力所能及事情的人们的故事,讲述他们鄙视庸常幸福的勇气,即使生活已经到了真正的无可去处,也依然能够看到安慰,依然希望拿出自己最好的,然后带着体温去贴近每一个具体的日子。
然而,拍摄的过程并不顺利,多少次,重复多条也得不到一个满意的镜头和满意的细节,于是明白真正的不“做作”有多难,有时候,动机过于强大,未必是好事。
我对命运的理解是,它是羊群,既可以走向风和日丽、水草肥美的广袤草原,也可以走向电闪雷鸣的悬崖绝壁,而自己,就是那个握着羊鞭的人。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难以启齿的黑夜和孤独,释放不仅是灵魂卸下重负,肉身也得卸下重负,虽然这种选择未必真的能够让人脱胎换骨,但我相信,内心的安静,是真正的安静。
我的选择似乎越来越逆向了,一年中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乡下,滇东南、普洱、南腊村和滇西北、中甸、从古龙村,是我交替常驻的地方。婆家在南腊,一个汉族和哈尼族杂居的山村,迪庆高原的从古龙村则是儿子的出生地。
这些乡村之所以吸引我,不是因为古老,也不是因为诗意,恰恰是这些村庄里每个人对改变的期待和为此所付出的努力。
而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应该得到尊重。
一个地方的建筑之所以源远流长,必定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与众不同之处。大理不过是众多幸存下来的古镇之一,何至于让我经年不息地辗转于此呢?
那些实际上已经日渐热闹的小巷子我已经不知走了多少回,衰老,斑驳,大多数的格子门窗虽然依然保留着原来的模样,但经年累月的擦拭,尘埃拂去,岁月安详。这样的老宅子,大多被租给外地人开客栈了,翻新的房子也不少,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是每个人本能的需求,一成不变未必就是好。白族是个无比崇尚传统的民族,走在大理的街上,身着白族服装的本地人比比皆是。这种现象,即使是在多民族聚居的云南,也是不多见的。盖房子是白族人一生中最隆重的事情之一,自然也是绝不会马虎的,因此,即便是把老房子拆了重建,也依然是传统的三房一照壁围成一个院子,中间种植着茶花和珠兰,安详的气质里有着截然的现代结构。家境殷实的人家,也有建成四合五天井的,这种结构较之三房一照壁,气势更为恢宏华丽。然而,无论是老宅还是新居,每家的照壁都会精心题书家风祖训、祥瑞诗词。门楼则采用大理石、青砖、花砖、木雕等精雕细琢,共同组成斗拱重檐,振翅欲飞的气势令人惊叹。建筑是文化的碑,白族人对精神和文化的专注令人肃然起敬。
然而,不论承认与否,其实每个人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着,时尚、潮流不可避免地要渗透进每个人的生活和精神,非要把眼前的一间老屋看作是坚守传统的象征是不足取的。
我理解,所谓的坚守,更应该体现在精神和道德的层面上,回归,更应该指向精神层面的回归。
当我从乡下重新来到大理时,不可避免地有了一种深刻的陌生感,这是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情绪。显然,很多人享受着现代的生活,却不愿承认眼前的现实,我再一次意识到仅仅看到大理古朴传统的一面是狭隘的,不应该的。文化的传承与进步,首先体现出来的就是复杂性、独特性、多样性,应该承认,所谓古老的生活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如果略过满眼的繁华往古城的深处走去,小巷窄门,另有一番景观。
在南门农产品市场旁一间专卖土产的小店驻足,店面不足十平方米,狭小的空间里倚墙竖着两架碗口粗木头榫卯的结实货架,上面依次摆着笼头、缰绳、马蹄铁、马嚼子、鞍垫、马镫、马鞭、马掌钉、军用背壶、铜制水瓢等二十多种马牲口用具,门口是两副结实的马鞍子,一架是普通松木的,另一副的鞍桥、前叉、后叉都是用一种叫泡木的珍贵木材制成,这种木材韧而不硬,制成的鞍子架到马背上会随着马儿的走动产生弹性,从而不易磨伤马背。店主段毓华做了三十多年的马店生意,在他看来,做生意其实就做两个字:独特。如今虽然汽车满街跑,但在农村,马驮依然还是实惠而又实用的。“不过,要筹齐这些马具越来越难了,比如马镫。以前骑马的主要是马帮的马锅头,所以用得着镫子,现在的马匹都是自家的,除了用来驮点东西,很少有人舍得骑,用得少了,做这项手艺的师傅也就越来越少了。”段毓华有些担忧地说。尽管如此,段毓华的小店每天都还是能卖出一两件物品,一个月下来也能卖出五六套鞍具。段毓华对小店的业绩很满意,对于很多人鼓动把铺面租出去获得更大收益的想法并不认可,他笑眯眯地说:“我虽然七十五岁了,但身子骨还硬朗,闲不住。房子是自家的,开店图的是个热闹,儿女们都出去工作了,我要那么多钱做什么呢,够吃够喝就行了。”
没有触目惊心,没有对峙,即使内心充满着最彻底的孤独,也依然能从这些平静的人们身上吸取强大的力量。
漫长的时间里我毫不掩饰对这里的喜爱。
段家马店的斜对面,是一间卖草药的铺子,同样七十多岁的店主赵老是个民间郎中,在这一带很有名气。除了绝症,赵老几乎是看一个好一个。我曾介绍朋友的妻子到赵老的药店看过病,那女子某日发现自己的乳房上骤然长了一个包块,惊惧之下连忙到医院做了各项检查,被确诊为乳腺纤维瘤,虽然医生告知没有生命危险,但除了手术,要消除瘤子也并不容易。从此,她踏上了遍访省城名医之路,中西医结合药吃了不少,瘤子却不见缩小,更没有消失的迹象。女子逐渐变得紧张而神经质,疑神疑鬼,心病大于体病,我便把赵老介绍给他俩。许是赵老的草药确实有独到之处,许是大理好山好水的滋养,夫妻俩在大理住了两个月,瘤子竟神奇地消失了。其实赵老看病的秘诀重在治心,相由心生,病由心治,道理是相通的。至于说到药物,赵老说,一点也不夸张,整座苍山都是我的药库,我家从爷爷那辈人就在苍山采药了,好用的药大都长在向阳岩子缝里,即使是同一剂药,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采的药效都有很大的差别,每年秋季采的药最好,吸足了阳光的药力最足。以前山里随便都可以采到两三百种药,现在不行了,能采到的不足一百种,很多药都绝迹了。说到那些永远消失的物种,赵老沉默很长时间,他的话本来就不多,平日里,那些神奇的药香,就是他的语言。
在喜洲,我目睹了一场惊艳的魔法,那是扎染的过程。
一种开着白花的绿色植物被剪断了枝叶投入滚沸的锅里,一边加盐一边添火,经过一个夜晚的熬制,便可以得到鲜亮如树叶的绿色染料,要想得到土黄色,则用一种叫黄色的小果子熬制,熬制黑头草则可以得到墨汁般的黑色。每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火候和密码,所以,得到的效果是千差万别的。
扎染过程大致这样,先用铅笔在生白布上绘上自己喜欢的图案,经过扎缝、染漂、折花、碾平几道工艺,一块漂亮的扎染便完成了。喜州扎染的优越之处在于针法,能够数得出来的就有龙卷、单针、双针、合缝、城墙、小七针等。
很长一段时间,我沉浸于这种神奇的魔法中。每次回家,都会买上几条用棉纱织成扎染的围巾,质地极为柔软,无论鲜艳还是素淡都有一种异质的风情。
白族女子向以勤劳著称,也很有侠气。天麻麻亮的时候,大部分男人还在梦里神游,而女人们早已把院子打扫整理干净了。天色渐亮,清晨的阳光和小鸟一起出现在屋顶的时候,早餐已经做好了,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饵丝,汤里飘着红红绿绿的辣椒、葱花,浓香扑鼻。与早餐同时端上桌子的,是一罐翻滚沸腾的浓酽烤茶,男人们吃完早点,再神闲气定地喝上一盅烤茶,便心满意足地出门,该上班的上班、该种地的种地去了。白族女子的拿手绝活在于自制小点心,平底的双面烤锅,放入用核桃仁、芝麻、花生、红糖、橙皮揉成的有馅的面饼,烤得两面透黄的时候起锅就成了。讲究一点的人家,还要在上面压上牡丹、芍药、菊花、南瓜、葡萄等吉祥图案。既不暴烈,也不挣扎,敞开自己,接纳对方,是这些家庭真实的写照。
在一个巷子里,一位容貌高贵的老人对我说,他们是细奴逻的后代,我怔了一下才反应过来,这是一位彝族人。尽管她的脸上和手上都布满了属于老年人的斑点,可安详的气质依然赋予了她一种稀罕的美。一千多年前,她的祖先建立了强盛一时的南诏国,首府就是现在的洱海地区。大理的彝族人至今还保留着祭祖的习俗,缅怀是为了激励,焰火中的烟花,仪式,神灵,我曾目睹过那种被伤痛浸润过的美。
有一年冬天,我在大理双廊的洱海边整整晒了一个星期太阳。迷离的阳光下,我反复听着一个专辑《哭泣的阿拉伯沙漠》。淡淡的忧伤,磁性低沉的男声,总让我想起杜文秀兵马元帅府,那个大理古城中的城中之城。整个冬天,庭院里的茶花火焰般开着。清末城池中那位率领各族人民起义的回族人已经远去,只有从融合了自由与血性的墙壁里,能够看到回族人的坚韧与抉择,看到这片土地曾经的创伤与痛苦,微笑与咆哮。
我看重《哭泣的阿拉伯沙漠》里那种坚持与坚决,它让我看到了大理的另一面,柔软背后沉甸甸的重量。
我想,这才是真实的大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