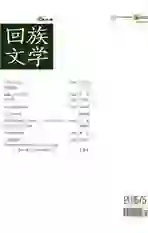花狗时代
2016-11-23马瑞翎
马瑞翎
祖父并不赞同养狗。他说养狗的人家,天仙不肯进门。我想象裙带翩跹的仙女们一听见狗叫,立马就吓得从屋顶上飞掉了。但是祖父告诉我,天仙不是这个样子的。猜测议论天仙的外貌是大不敬,因此谁也不知道天仙长什么样子。天仙不喜欢狗,可问题是,老百姓——尤其是我们那地方的老百姓,不养狗似乎不行。我们家也养狗。养过的狗不是英年早逝就是少年夭亡,仅有一只花狗从满月直到寿终正寝,在我家走完了它的一生。它生平因为爱咬人而出名,受到畏惧和尊敬。我曾在记忆中搜索,想找出一个对它不恭的记录,想了半天,好像有一次父亲骂过它:“你眼睛瞎了?你这个瘟狗!”
父亲在水井的四角栽木杆,搭架子。不久架子上就爬满藤蔓,绽放白花,毛茸茸坠下许多葫芦来。幼年的花狗就拴在葫芦架子下面。中饭和晚饭前,整个村的人家都来担水。撞桶、泼水、说话、狗叫,乱成一团,够热闹的。花狗在这样人来人往的环境中,居然成长为一只爱咬人的狗。它出名以后,村里人谁也不敢擅自进我家门。他们总是站在大门外,紧紧拉住门的两个铁扣环,大声喊话,主人答应以后,才一伸一缩地进来。花狗凶猛地挣铁链子,冲客人狂吠。来者一边说话一边紧张地望狗,赶紧说完事走人。不过,花狗不咬担水之人。于是村人每到我家说事,都故意扛扁担、拎桶,假装担水的样子来掩护。也许花狗已经识破,只是假装不知道而已。
宰牛的时候,满院子腥味、烟火味和烫洗肚肠的味道。我永远记得这场景:牛皮剥开,垫在地上,牛的内瓤还在牛皮上白花花地竖着。卸开以后,肉就变成红色的了,大块大块地晾在竹席子上。女亲戚们在厨房里做菜和讲话。父亲独自蹲在墙角,用一把尖刀刮牛脑袋和牛脚。弟弟把牛膀胱吹成气球;两个亲戚家的孩子在拖牛的肩胛骨,他们说这是车。所有亲戚都似乎忘了怕狗。花狗此时不能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它也不注意任何人,有时从桌凳的空隙间穿过,或者干脆外出,过一阵又回来,在院子里随便找个地方趴着。我母亲的堂兄是哑巴。他以为今天是同花狗改善关系的好机会,就拿盆盛了一些碎肉去贿赂。花狗站起来,精神抖擞地、毫不客气地在拿盆的那只胳膊上咬了一口。手飞快地缩了回去,盆咣当一声掉在地上。花狗慢条斯理地把东西吃完,扬长而去。哑巴的母亲,也就是我祖母的老嫂嫂,对花狗十分不满。她本人也吃过花狗的苦头。某天她从我家大门外路过,花狗突然跳出去将她扑倒。她坐在地上拖声曳调地叫唤,我还以为有人在大门外唱歌。而后老太太住进医院,耷拉着脑袋,半靠半躺,一边哼哼一边同亲戚说话。我祖母背地里似乎有点高兴,说花狗咬人必有道理。因为她同老嫂嫂关系曾经很不好。在旧社会的大家庭,我祖母不善讨好婆婆,没有生儿子,在妯娌斗争中时时处于下风,受到欺负和压制。难道我祖母和母亲谈论这些陈年旧事的时候,花狗在一边听见了?于是它就以它的方式替主人讲了一回道理?
斋月伊始,祖父把堂屋洒扫干净,点燃檀香,摆好油香和糕果,请阿訇来念经。祖父本人也是阿訇,他同别的阿訇都坐上首的椿木凳子,满拉坐的是下首的长条凳。他们赞圣的声音神秘、动听、真挚、庄严而坚定。我从小就爱听这个。不知花狗怎样想,反正它也站在檐坎上听,神情非常专注。有个学生不专心念经,拿一只纸折的三角板,在花狗耷拉的耳朵上挑逗了一下。花狗不耐烦地一摆脑袋,喉咙里发出警告。这位又往花狗的脸上挑逗了一下。花狗怒不可遏,在他的大腿上狠狠地咬了一口。直到今天我还记得,这位小叔在医院里被大人摁住,他死死抓住自己的裤腰,不准人脱他的裤子,号得比刚被狗咬时还要厉害。他的母亲,就是祖母的娘家弟媳,我称她为舅奶奶的,在当地赫赫有名,吵起架来,十个婆婆也不是她的对手。她为这事骂了好几天。祖母说,花狗当初满月之时,正是这位舅奶奶把它从窝里捉出来的。谁从狗窝里捉狗,狗长大就会像谁。“倘若花狗是大华捉来的……”母亲说了半句话。大华就是哑巴伯父的妻子,是个大好人。倘若花狗是她捉来的,那一定会是一只不咬人的老实狗。
随着咬人次数的增多,花狗受尊敬的程度也在增长。奇怪的是,它有时连小孩子也咬。我家老宅院子类似于古代的后花园,不是落满叶子,就是一地花瓣或熟烂的果子。这是孩童的乐园。我的玩伴阿碧,还有她的小五妹,我们三人站在石榴树下。小五妹脑袋上罩一只发卡,发卡上顶着一团用纱巾扎的大红花。这种打扮是从画上学来的,名曰“祖国的花朵”。突然一声啊呜,伴着尖叫,小五妹捂着屁股大哭。原来花狗咬了她一口,不过咬得并不重。小五妹扬言要回去告状。阿碧害怕挨大人骂,就拿东西讨好她。我也拿了东西来哄她。又玩了一阵,小五妹把告状的事忘了,我和阿碧就一样一样地把东西又给拿了回来。这个阿碧,在十七岁去世。我对她的怀念和回忆,总是与花狗、与故乡、与往事牵连——写到这儿,我满眼都是广阔、炎热、富庶的故乡。田埂上蓝色的打碗花——谁摘它,谁吃饭的时候就会把碗打碎;荒地上匍匐的藤萝;山岗上温润的野百合……唉,我们背着竹篮,以割草的名义,在田埂上游逛,一直玩到太阳落山。我们常常吵嘴。阿碧总是拍着口袋大声说:“你管得着吗?自由权利在我包包里头揣着!”这句话总能使她占上风。我以为“自由权利”是一种硬纸片样的东西,可以随身携带。我非常想得到自由权利。有一天终于鼓起勇气去问母亲。她正在踩缝纫机,成批地缝制一种布帽子,忙发家致富忙得不得了,没好气地把我赶了出来。
花狗咬过的另一位孩童是弟弟的朋友,名叫四红。男孩子们在院子里玩得正高兴,突然听见哭声,四红被花狗咬了。他跌倒在地,一边哭一边用手和脚逃跑。花狗跟在后面,在他撅起的屁股上又咬了一口。花狗为什么要这样?也许四红冒犯了它。也许花狗咬人不需要任何原因和理由,谁侵入了它的领地它就咬谁。因为它是一只真正的狗。现在城里的那些狗,不是娇滴滴的小型玩赏犬就是艳丽肥硕的大型观赏狗,它们有些不太像狗。就如同现在的苹果又大又红,可是吃起来却没什么苹果味那样。
是的,花狗是一只多么好、多么真的狗啊!它的毛又长又亮,背上的花纹就像黑白相间的奶牛。父母带我们姐弟三人去山上割茅草,花狗同我们一道出门,迈着细碎的步子,严格地保持着既不超前也不落后的状态。当走进田野,我们就一起撒起欢来。花狗腾跃着,飞驰着,花尾巴在绿色麦浪中欢快地摇曳。我们高高兴兴,走向广阔的荒地,一直走到山脚。在弯弯的山道上爬啊爬啊,前方豁然开朗,展开一片山洼。荞子正在开花,整片洼地像是铺满了雪。四周坡上全是茂密的茅草,吹风的时候整座山都在波动。花狗像白色闪电在波浪中消失,片刻以后又在彼岸出现。有时在奔跑中它会突然停下来,像在倾听或者沉思,而后又突然调转身子朝另一个方向飞奔。它认真地嗅闻,把头钻进茅草,那丛草乱动起来。而后花狗就向我们奔来,嘴里衔着一颗香喷喷的野葡萄。我们欢呼着朝那个地方跑去。
“你家的狗真听话,真有本事!”同样去割茅草的那家妈妈说。
其实花狗还有更厉害的本事呢!它曾经在贸易站的一大堆废甘蔗叶里找到一块红糖,而后跑了很远的路衔回家来。
“我家的小花爱干净,从来不吃屎。”母亲说,“再饿,它也不吃桌子上的东西。”
花狗确实严格地恪守着规矩。我们吃饭的时候它站在不远不近的地方,期待地看着,等待着。尽管十分垂涎那些放在桌子边沿的、啃过的牛骨头,它也绝不伸嘴,非要等主人把骨头抛给它不可。
黑夜追赶着白昼。月亮像一条细线挂在我的闺房之外。光秃秃的无花果树,剪影是黑色的,背景是灰亮灰亮的。这些景物嵌在我的窗框里,像一幅画。唉,那时候我的心情总是怪怪的。我的感觉会像针一样,在静夜中越磨越尖,能够一下子觉察出那些微妙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气味和声音。叶子在发芽,花瓣簌簌落下,一切都如诗如画。这些有时使我愉快,有时又使我惆怅。其实,这些都是恋爱造成的感觉。同我谈恋爱的那个人,年龄大我许多,而且是汉族人。这遭到全家反对。但是花狗却从一开始就不咬他。有一回我与他吵架,将他赶了出去,而后关掉大门。这个家伙在大门外咳嗽和唱歌,折腾一阵子,他居然爬到墙上去了。事后他告诉我,骑在墙上的时候他怀着一种“别无选择的悲壮”。花狗呜呜地冲过来,仰头审视他,他也低头看狗。而后花狗就理解了他,转身走掉了。于是,他马上把墙外那只脚移到墙里,咚的一声跳将下来,跌在一丛红薯藤上。祖母专程跑到新宅去反映这一事件。于是母亲就专程跑到老宅来骂我。骂了几回她就不管了。祖父也不再干涉。父亲则从一开始就不予理睬。
谈恋爱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花狗居然老了。它很少出门了。皮毛暗淡无光,腰身圆滚滚的,走路的时候臀部一扭一扭,非常沉重迟缓。它成天蜷在我的闺房门口,后来又蜷在我的书桌底下。有一回我正烦着,朝它大声嚷嚷,赶它走。它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看着我,那衰弱疲惫的神情,哀伤留恋的眼睛,简直同人一模一样。而后它就一步一步地走出去了。我不该呵斥它。直到现在,我还在后悔。
有一天父亲对我说,花狗死掉了,在门外的水塘子里。我的胸腹簌地一空,有一些东西飘走了。我跑到大门外。花狗的上半身静静地搁在岸上,下半截身子泡在水里。父亲把它拖回家,埋在柿子树下。花狗成了老宅院子里最好的肥料。那一年柿子树上成团的果实把枝条都压断了,父亲插了一些木棍来撑着。麻雀一群又一群,飞来啄果子吃。它们的肚子里都有花狗的营养。鸟儿会把花狗的分子带到很远的地方。也许,鸟粪中的一粒种子会在异国他乡发芽。
后来我离家去外地工作。有一次回老家,发现柿子树已经换成一棵桃树。过了几年又变成一棵新品种的无花果树。不知以后还会换成什么树。这些年中,家乡的狗升级换代(恐怕应该是降级换代才对),全换成了小型犬,其血统乱七八糟,杂到了极点。它们的优点是爱叫和吃得少。它们无疑都很平庸,很不理想。我的花狗成了永远的绝唱。
春节回老家,祖母已经老得成天坐着或躺着,对社会上的事情一无所知。祖父倒是仍然关注外界,常常拄着拐棍出去逛街。他老人家一生对狗不感兴趣,直到现在,他仍然认为,养狗的人家,天仙不肯进门。但是家里庭院广阔,房子多而人少,夜里需要响动,所以还得养狗。母亲告诉我,如今遍地都是流浪猫和流浪狗,谁要是想养,只管到干河里去挑一只回来。我路过干涸的河床,果然被抛弃的猫和狗都集中在那一带,它们可怜兮兮地在垃圾堆里找吃的,叫得呜呜咽咽。记忆中,像花狗那样优秀的本地犬们,悠闲地在大路上、在村庄中行走,想躺在哪里晒太阳就躺在哪里晒太阳。它们在河床上、在荒地中打仗,一群狗与另一群狗拼个你死我活,厮杀声惊天动地。它们在色彩缤纷的田野中奔驰、恋爱、结婚,在生产队保管室的草堆里生下优秀的后代,而后像我舅奶奶那样的厉害媳妇,或者像大华一样的老实媳妇从中捉出一只,抱到某户人家去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