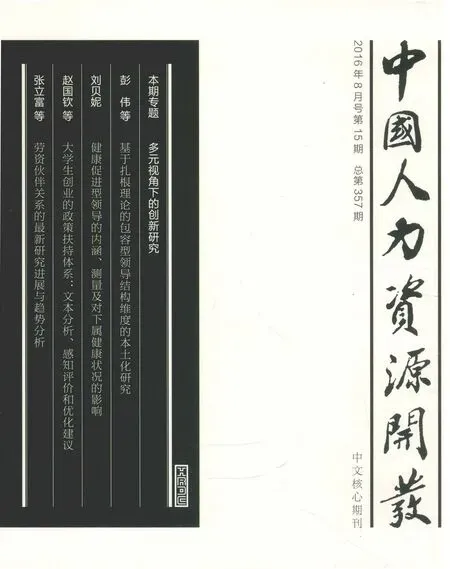健康促进型领导的内涵、测量及对下属健康状况的影响
2016-11-23刘贝妮
· 刘贝妮
健康促进型领导的内涵、测量及对下属健康状况的影响
· 刘贝妮
本文从特质观、行为观和权变观三个视角对健康促进型领导的特点进行梳理,提出健康促进型领导的内涵包括健康观念、健康知觉和健康行为三个维度。通过对493名企业员工进行调研,得出如下结论:健康观念、健康知觉和健康行为是三个对于“下属健康关心”和“下属自我健康关心”具有区分效度的结构维度;下属健康关心与工作特征、工作环境和工作氛围显著正相关,下属自我健康关心与过度承诺显著负相关;在下属健康关心对员工健康状况起作用的过程中,下属自我健康关心起到了中介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领导者需要从健康观念、知觉和行为三个方面实践组织健康管理,承担下属健康关心责任,通过“仪式性”活动推进企业健康组织的建立。
健康促进型领导 下属健康关心 下属自我健康关心
在众多决定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因素中,“健康”作为与“教育”同等重要的人力资本形式,一直被认为是决定地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健康、高素质的劳动力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健康除了与员工健康意识、健康投资和自身健康状况有关以外,还与组织层面的因素相关,工作场所的物理环境和社会心理环境同样可以影响员工健康。已有的研究已经证实,组织社会支持、工作控制和角色冲突等与员工因病缺勤、职业倦怠、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等有明显联系(Piko,2003)。然而,有效的组织员工健康管理不仅需要相关的组织文化、组织制度和工作设计等,还需要好的领导者,尤其是对“健康”敏感的领导者。于是,学者开始将研究视角转向领导者的健康促进管理角色上,并提出了健康促进型领导的概念(Health-promotion Leadership)(Dellve et al.,2007;Franke & Felfe,2011)。
健康促进型领导活动主要表现在,领导者通过制定组织政策和制度、优化工作设计和流程、营造工作场所健康促进的组织环境等方式去激发和鼓励员工积极参与到健康工作场所的开发和管理中,提升组织中员工的健康意识和健康行为,最终达到工作场所健康促进(Andrea et al.,2010)。可见,健康促进型领导在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和运作、员工个人的健康管理和健康促进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纵观国内外研究现状,健康促进型领导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内的研究更是处于空白状态,健康促进型领导的概念内涵、测量以及对下属产生的影响等方面的问题都亟待解决。鉴于此,本研究在梳理国外文献的基础上,综合提出健康促进型领导的内涵和结构框架,并验证其测量内容的建构效度,探究其对下属健康状况的作用机制,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管理建议,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视角,为企业建立和推进健康型组织提供思路和借鉴。
一、健康促进型领导内涵和结构
(一)健康促进型领导内涵的演化过程
健康促进型领导的概念的提出是由一系列相关的概念和研究演化而来,其形成和发展的路径大体遵循:领导者健康观——领导者健康管理角色——健康促进型领导。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有学者针对领导者的健康意识与员工健康状况进行了实证调研,结果显示,员工自我报告的健康状况和他们感知到的领导对他们健康的重视程度显著相关(Gavin & Kelley,1978)。然而,就组织而言,员工个人的健康状况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组织能够有效的对员工的健康进行管理,营造良好的健康促进工作环境,使得每个员工在这样的环境中可持续的发挥自身的价值和潜质,更为优化的进行人力资本的配置,为组织创造出更大的竞争优势。因此,领导者的健康管理角色逐渐成为学界较为关注的研究议题,有的学者指出,领导者可以通过制定明确的工作目标、合理的工作流程、与劳动付出相符合的薪酬回报体系、尊重和关心员工健康状况等方式增加员工健康感知,降低因病缺勤率(Dellve et al.,2007),这其中已经蕴含领导者工作场所健康促进的涵义,即领导者通过营造健康的组织物理环境和组织心理氛围来增加员工健康意识,促进健康状况。
目前,国外已有部分学者对健康促进型领导进行了探索,健康促进型领导的概念也不断得到拓展,但总的来讲还缺少共识的标准定义。鉴于此,本研究先从特质观、行为观和权变观三个经典领导研究视角对健康促进型领导内涵进行梳理,并综合提炼出本研究对其的定义。

表1 不同视角下健康促进型领导内涵梳理
(二)健康促进型领导的内涵梳理
特质观视角下,领导者对健康的敏感程度和健康意识是健康促进型领导的关键特征。领导者对健康问题的敏感程度越高,越能更敏锐的发现下属健康方面可能存在的风险,有意识的去关注下属健康状况,并且传递重视健康的观念(Franke & Felfe,2011)。每个员工都有自己的价值观,组织也有组织的价值观,当员工感觉到自身价值观和组织价值观存在差异和冲突的时候,如员工更倾向于追求工作——家庭边界的分离,但组织的政策和工作方式渗透到了员工的家庭层面中,就更有可能给员工造成身心上的不适(Leiter et al.,2009)。因此,健康促进型领导能够秉持增进员工健康和福祉的价值观,拥有促进下属健康的意识,通过了解员工的需求和意愿,与员工积极沟通和解释组织相关制度,增加员工工作任务和个人价值观的一致性,努力减少员工价值观和组织价值观之间的鸿沟,从而减低员工的健康风险(Dunkl et al.,2015)。
行为观视角下,健康促进型领导的核心要素是其健康管理方式或促进组织成员健康的一系列行为。领导者持续关注并提供工作环境的改善、给予员工足够的权利跨度去获得完成工作要求的相应资源、不断对工作场所质量进行提升、为员工提供个人健康发展计划和机会等(Anderson et al.,2005)。领导者和下属之间积极的沟通关于健康方面的话题,关心下属健康状况,制定工作场所健康促进政策和制度,鼓励员工积极参与到组织健康管理中(Gurt et al.,2011)。领导者致力于推进积极的健康促进行为、提供必要的上级支持、促进工作场所环境的改善,如设计清晰的岗位职责、界定明确的工作角色、提供给员工足够的工作资源以平衡工作要求、在非办公时间不侵扰员工生活、关心员工健康状况并给予改善建议、鼓励员工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办公物理环境的舒适和心理环境的和谐等(Eriksson et al.,2015)。
权变观视角下,健康促进型领导的主要表现为根据不同的组织环境与氛围采取不同的健康管理领导方式,如当员工面临较为严重的工作压力时,领导者具有促进员工健康的意识、设置适当的工作压力、建立合理的报酬体系、采取民主的管理方式、提供支持性的卫生服务信息与资源、营造舒适的工作物理环境等,帮助缓解员工工作压力,并监控和支持员工的生理和心理健康(Gregersen et al.,2014)。在工作的物理和心理氛围都相对舒适的工作环境中,健康促进型领导的关注重点将会放在促进员工健康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提升组织的健康状况,如组织效率、生产力和竞争力等,主要包括领导者实践健康行为,通过榜样机制促进和提高员工的健康生活方式,对员工尊重、信任并保持持续开放的沟通渠道与方式,持续维护已有的工作物理环境和组织社会心理环境(Andrea et al.,2010)。
表1梳理了不同视角下健康促进型领导的内涵,虽然学界对健康促进型领导的内涵界定还没有达成共识,这与该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有关,但通过梳理仍然可以归纳出学者们观点的相同之处:首先,健康促进型领导是以领导者自身对于健康的重视度以及价值观作为基础的,领导者致力于为组织成员在健康生活方式上树立行动榜样;第二,健康促进型领导对健康具有较强的敏感度,努力建立和营造对员工健康有促进作用的工作物理环境和组织社会氛围;第三,健康促进型领导善于采取一系列支持性措施或影响策略来激发组织成员的健康行为,避免工作外的干扰和超时劳动,鼓励员工参与到组织健康管理中,从而为提升组织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基于前文的分析,本研究认为权变观能更好的诠释健康促进型领导的内涵,即对领导现象的解释需要综合领导者个人特质、领导行为以及组织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健康促进型领导指领导者基于自身的健康观念和健康意识,通过行为模范作用和健康管理行为来激发组织成员的健康生活方式和健康行为,从而营造出健康促进的组织氛围,以提升组织竞争力并实现组织的可持续发展。

图1 健康促进型领导结构框架图
(三)健康促进型领导的结构
由于健康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较为私人的事情,健康是员工自身要对自己首要负责任的事情(Daniels,1996),因此工作中员工自发的健康行为需要被重视,也就是说,应该在健康促进型领导的结构框架中增加领导者如何培养下属健康行为的内容 ,根据社会认知学习理论(Bandura,1969),当下属意识到领导非常重视他们的健康问题,并且鼓励他们积极的参与健康实践中,给予他们更多的权限,敏锐的察觉到他们什么时候、因为什么而感到压力,同时被领导更为认真的对待和照料时,这些行为会进一步刺激下属关注自身健康(Goetzel & Ozminkowski,2008)。
根据资源保存理论,人们有一种获得、保存和保护各种资源的基本动机。人们总是在积极的努力维持、保存和建立各种他们认为宝贵的资源,这些资源的潜在损失、实际损失或者投入资源后无法获取资源作为回报时,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威胁(Hobfoll,1989)。资源在个体健康领域指的是个体特征(如:身体状况)、条件(如:工作环境)、能量(如:工作控制能力)等让个体觉有能力去促进和保护自身健康的东西,资源可以被分为两类,一类的是内在资源,一类是外在资源。内在资源可以被描述为认知方面的或者行为方式上的资源,如健康知识、健康的生活方式等;外在资源可以被描述为组织或者社会方面的资源,如组织的健康促进氛围、社会支持环境和条件等。“下属健康关心”主要是领导改善或提高促进员工健康的工作条件的行为措施,并且支持员工去保护、保持自身健康状态的观念和意识,因此可以将领导的下属健康关心视是一种外部资源;“自我健康关心”是个体通过恰当的方式,如正确的看待工作压力、处理工作任务、平衡工作要求、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等去保护或者促进自身健康状况,因此可以将自我健康关心视为一种内部资源。
图1总结了健康促进型领导的结构框架,包括基础、核心内涵、影响以及后果。在框架中,领导者的自我健康关心是健康促进型领导的基础,领导者关于自身健康状况的思考方式、认知程度和行为策略为下属健康关心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作用,并且能够作为指导、调节等角色帮助下属处理他们的健康问题。同时,领导者的自我健康关心和下属健康关心也会影响到下属的自我健康关心,领导者在健康行为方面树立行为榜样,并且通过传递健康观念、意识和促进健康行为等方式对下属进行健康关心,下属的自我健康关心意识和程度会有所提高。
领导者的下属健康关心是健康促进型领导的核心内涵,包括观念、知觉和行为三个方面,下属健康关心中健康观念包括了领导者对下属健康的关心程度以及对下属健康的负责程度。负责程度指的是对于职业压力和工作潜在威胁的适当的感知,并且认为需要采取行动去避免下属遭遇这些压力和威胁。下属健康关心中健康知觉包含了领导者对于下属健康状况、工作相关的压力和环境的注意度和敏感度,领导者能恰当准确的评估下属压力水平的能力和对下属压力先兆表现的识别。下属健康关心中健康行为包含了领导投入到健康实践中的频率和程度,包括领导为下属提供健康的工作条件、鼓励和帮助下属参与到健康的工作行为中并且提供健康和安全事项资源和信息。
在梳理了健康促进型领导的内涵、结构框架之后,下文主要通过实证研究探讨健康促进型领导中观念、知觉和行为的结构维度、领导对下属的健康关心与下属自我健康关心的影响因素以及健康促进型领导对下属健康状况的作用机制等。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的提出
健康观念、健康知觉和健康行为是健康促进型领导的三个构成方面,是健康促进型领导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关键,因此理论上讲,这三个方面应该同时满足。比如,下属也许会感受到:(1)他们的领导对下属的健康是负责任的(观念维度);(2)领导能够感知到下属的压力和健康风险(知觉维度)以及(3)领导有意愿促进下属的健康状况(行动维度)。然而,下属有时会感觉到三个要素不能同时满足,比如他们也许能够感知到领导是重视他们的健康状况的(比如在会议上强调工作场所健康促进的行为有哪些、公开场合鼓励和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等);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真正的对下属健康负责(比如领导者可能会认为健康是个非常私人的事情)。这样,下属可能会认为他们的领导行为符合规定,也可能会认为他们的领导没有真正关心和在意他们的健康状况。另一方面,下属可能认为他们的领导对于他们高水平的工作压力有感知,并且积极努力的去减少他们的工作要求,但是并不能真正改善环境(比如缺少决策权力等)。或者下属根本感觉不到领导对他们的健康状况的关心,更感觉不到领导有任何促进他们健康状况的行动和措施。这些例子都说明,三个健康促进型领导的结构维度是缺一不可的。
因此本研究的第一部分就是要验证这三个结构维度的效度,并且验证健康观念、健康知觉和健康行为是即有区别性又互相联系的三个成分。假设下属能够区分他们自己和领导的健康观念、健康知觉和健康行为。因此提出研究假设:
假设1:健康观念、健康知觉和健康行为是三个对于“自我健康关心”和“下属健康关心”相关但又具有区别性的组成结构维度。
因为健康促进型领导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要验证是否自我健康关心和下属健康关心是健康促进型领导力的特征。如前文所述,下属健康关心是一种外部资源,应该和工作任务特征或者工作环境相关;而自我健康关心是一种内部资源,应该更普遍的和下属个人工作行为相关。下属健康关心检验工作特征、工作氛围和工作环境三方面:(1)工作特征:良好的工作设计,包括员工的工作控制能力、工作资源获取能力和工作要求的平衡水平、角色清晰程度和工作意义等,都可以降低员工面临身心健康问题的风险,这些方面在之前的研究中被认为是领导在工作设计上关心下属健康的主要方面(Arnold et al.,2007);(2)工作氛围:包括领导在促进组织和谐氛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而增加了下属之间积极的社会互动,因为工作场所中的良好组织氛围和员工关系是员工健康心里知觉的重要因素(Haber et al.,2007);(3)工作环境:工作氛围可以理解为工作的社会心理环境,而工作环境则指的是工作的物理环境,身体要求是除了心理要求以外另一个可以预测健康的重要指标,舒适的办公环境对员工健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Canjuga et al.,2010)。综上所述,高水平的下属健康关心意味着领导通过优化工作设计、完善组织政策和措施、营造对员工健康有促进作用的工作物理环境和社会心理环境等来影响员工健康。因此可以假设,下属健康关心与工作特征、工作氛围和工作环境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
过度承诺可以被描述为个体过度追求工作上的认可和赞赏而表现出来的一系列态度、行为和情绪。过度承诺指出,员工过度承诺会使他们超过适当的努力程度、过于频繁的把自己暴露在更高水平的工作要求中,并且做一些超出他们工作资源范围的工作。所以结果往往是,这些努力减少了他们从高工作要求中恢复过来的潜在可能性,并且当预期回报不是即时到来时,增加他们的易受挫折感,最终会导致个体健康状况的恶化(Preckel et al.,2005)。尽管也受到领导和工作要求的影响,但是过度承诺是一个更容易受个体工作风格影响的因素,因此将过度承诺作为一个内在特征。过度承诺的员工比其他员工更容易超时超强度工作、忽视休息、将工作带回家等,因此有更高的频繁和更容易遭受工作压力的风险。因为自我健康关心包括对自己健康负责任、对威胁自身健康的信号有清晰的意识、更积极的投身到健康促进的行为中去,因此个体有较高水平的自我健康关心可以减少过度承诺。基于此提出假设:
假设2:下属健康关心与工作特征、工作氛围和工作环境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自我健康关心与过度承诺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
更进一步,假设领导提供下属健康关心能够让下属有能力去保护他们的健康资源,从而进行自我健康关心。当领导积极调动、鼓励下属参与到健康促进方面的行为和实践中,并且提供更为适宜的工作环境,下属就会更有健康意识并更积极的进行自我健康关心。相反,如果领导不实践下属健康关心,这意味着下属将失去很多实践自我健康关心的机会和能力。因此可以预测,领导对下属的健康关心显著影响着下属的自我健康关心,而作为一种内部资源,下属的自我健康关心程度与下属实际的健康状况密切相关。下属如果能够意识到他们的健康风险信号,并且具有强烈的动机去关注自身健康,同时实践促进个体健康的行为活动,那么他们就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健康资源并且平衡工作要求,这些因素又会反过来促进下属更好的健康状况;另一方面,下属如果不积极实践自我健康关心,忽视自身健康问题,就有更大的风险面临健康资源的丧失和匮乏,更少的机会去获得工作资源和处理工作要求,健康状况就会受到损害,遭受更多的工作压力和更多的工作家庭冲突问题。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3:在下属健康关心对员工健康状况起作用的过程中,下属的自我健康关心起到了中介作用。
(二)调研数据收集和基本情况
本次调研采取线上线下两种方式发放调研问卷,匿名填写,共发放问卷535份,回收535份,按以下标准筛选有效问卷:(1)漏答题超过4项(10%);(2)有明显不认真作答的倾向,如都选统一选项或答题呈现“Z”字型,最终获得有效问卷493份,问卷回收有效率92.15%。调研对象来自各种类型的企业,其中公共服务类企事业单位占63%、IT类企业占17%、高校占12%、医疗服务类企事业单位占8%;调研对象中女性占58%,男性占42%;36%的调研对象年龄在30岁以下,20%的调研对象年龄在30到40岁之间,24%的调研对象年龄在40到50岁之间,20%的调研对象年龄在50岁以上,年龄分布比较均匀;工作年限从6个月到28年之间不等;平均在现在的直线领导下工作的时间为5年(SD=4.99)。
(三) 变量测量
下属健康关心测量采用Franke等人(2011)的量表,包括11道题目,所有的题目采取五点量表形式,从1-非常不符合到5-非常符合。其中反映健康观念的有3道题,如:我的领导认为降低我工作中的健康风险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的领导在处理工作的时候,员工健康问题的优先级比较靠前等;反映健康知觉的有3道题,如:当我的健康状况出现问题时,我的领导能够立即察觉到等;反映健康行为的有5道题,如:我的领导会要求我及时汇报工作中有关健康风险的问题等。问卷信度从0.84到0.88。
自我健康关心测量采用Franke等人(2011)的量表,包括10道题目,所有的题目采取五点量表形式,从1-非常不符合到5-非常符合。其中反映健康知觉的有3道题,如:当我的健康状况出现问题的时候,我能够立即感受到;反映健康观念的有3道题,如:对我来说降低工作中的健康风险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反映健康行为的有4道题,如:我尝试去减低自身的工作要求,最大化的达到工作生活的平衡;我会按时休息,避免对工作过度承诺等。问卷信度从0.73到0.80。
外部工作特征测量量表采取的量表,包括8道题目,所有的题目采取五点量表形式,从1-非常不符合到5-非常符合。其中反映工作任务的测量采取Arnold等人(2007)的量表,包括4道题,如:有趣的工作内容、较高的工作自主性、清晰的工作角色和目标、丰富的工作资源;反映工作环境的测量采取Haber(2007)的量表,包括2道题,如:舒适的办公环境、便捷的现代电子设备;反映工作氛围的测量采取Canjuga等人(2010)的量表,包括2道题,如:良好的组织氛围、和谐的同事关系。问卷信度从0.68到0.77。
过度承诺测量量表采取Preckel等人(2005)的量表,包括6道测试题,所有题目采取五点量表形式,从1-非常不符合到5-非常符合。如:我倾向于承担超过我所掌握的工作资源之外的工作任务、我早上一起床就思考工作相关的事情、我周围的人都认为我为工作牺牲太多等。问卷信度0.87。
健康状况采取单一问题测量形式,询问调研对象对自身健康状况的总体感受并打分,10分表示健康状况非常好,0分表示健康状况非常不好。
三、结果与分析
(一)变量区分效度检验
为了检验下属健康关心中健康观念、健康知觉、健康行为和自我健康关心中健康观念、健康知觉、健康行为六个变量之间的区分效度,本研究采用SPSS 20.0和AMOS 16.0进行统计分析处理,首先进行CFA验证性因子分析。在六因子模型、四因子模型、双因子模型和单因子模型之间进行对比,模型参数如表1所示。其中,六因子模型由下属健康关心的三个因子和自我健康关心的三个因子共同构成;把下属健康关心中的健康观念和健康知觉合并为一个潜在因子,把自我健康关心的健康观念和健康知觉合并为一个潜在因子,加上下属健康关心中的健康行为和自我健康关心中的健康行为,共同构成四因子模型;把下属健康关心中的三个因子合并为一个潜在因子,那自我健康关心中的三个因子合并为一个潜在因子,构成双因子模型;把所有条目归并为一个潜在因子构成单因子模型。结果显示,健康促进型领导影响因子的四个验证模型的拟合指标χ2/df值,依次为M1>M2>M3>M4。并且六因子模型中χ2(334)=879.00(P<.001),χ2/df=2.63,CFI=0.92(大于0.9),RMSEA=.05(小于0.10),说明六因子模型拟合较好,显著优于其他模型,表明主要研究变量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证实了健康促进型领导的影响因子模型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验证了假设1。

表2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二)相关性检验
表2列出了主要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信度和相关矩阵。结果显示,下属健康关心中的健康知觉、健康观念和健康行为分别和工作特征、工作环境以及工作氛围呈现显著正相关(r值从0.17到0.44,P<.001)。自我健康关心中的健康知觉、健康观念和健康行为则与工作特征、工作环境以及工作氛围呈现的相关性相对较弱(r 值从0.05,P>0.5到r值为-0.22,P<.001);自我健康关心中的健康知觉、健康观念和健康行为与过度承诺呈现显著负相关(r值从-0.10到0.30,P<.001),下属健康关心中的健康知觉、健康观念和健康行为与过度承诺之间也呈现负相关,但程度较自我健康关心稍弱(r值从-0.14到0.15,P<.01)。结果证实了假设2 ,即下属健康关心与外部工作特征,如工作任务、工作氛围和工作环境有显著的正相关性,自我健康关心与个人工作方式,如过度承诺有显著的负相关性。
(三)中介效应检验
中介效应存在的前提是确定自变量与因变量显著相关,经分析发现,下属健康关心中的健康知觉、健康观念和健康行为与下属自评健康状况显著相关,r值分别为0.24、0.24、0.29,P值均小于0.01,说明存在中介效应。Bootstrap方法是一种重复抽样技术,抽取大量的Bootstrap样本并获得其统计量的过程,该方法实质上是模拟从总体中随机抽取大样本的过程。本研究采用偏差矫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方法计算多重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水平,求取95%的置信区间,对下属自我健康关心的观念、知觉、行为三方面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如下表3所示。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均大于0,表明中介效应显著,效果量采用间接效应与总效应之比,即ab/c表示。可以看出,领导者下属健康关心的健康观念对下属健康状况影响过程中,下属自我健康关心的健康知觉起到的中介作用最大,达到69.7%,这说明领导者对下属健康状况的重视程度以及员工健康在管理中的优先级会通过影响员工的健康知觉(如员工对自身健康的敏感程度)从而影响员工总体的健康状况;类似的,领导者下属健康关心的健康知觉对下属健康状况影响过程中,下属自我健康关心的健康行为起到的中介作用占47.6%,这说明领导者对下属健康状况的敏感程度会通过影响员工的健康行为实践从而影响员工总体的健康状况;领导者下属健康关心的健康行为对下属健康状况影响过程中,下属自我健康关心的健康行为起到的中介作用占51.2%,这说明领导者积极在工作场所推行健康实践活动会通过影响员工自身的健康行为从而影响员工总体的健康状况。

表3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4 多重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的Bootstrap分析
四、管理启示
通过实证分析,理论推理得以印证,健康促进型领导的包括领导者的下属健康关心和领导者的自我健康关心两个视角,每个视角包括健康观念、健康知觉和健康行为三个结构维度,这三个维度对反映健康促进领导力的区分效度较好。领导者的下属健康关心与工作特征、工作环境和工作氛围显著正相关,下属自我关心与过度承诺显著负相关,领导者下属健康关心的健康观念对下属健康状况影响过程中,下属自我健康关心的健康知觉起到的中介作用最大,也就是说领导者的健康观念会影响到下属对健康的敏感程度从而影响员工的健康状况。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以下三点管理启示:
首先,领导者需要从健康观念、健康知觉和健康行为三个方面实践组织健康管理。健康促进型领导是以领导者自身对于健康的重视度以及价值观作为基础,领导者致力于为组织成员在健康生活方式上树立行动榜样;对健康状况、工作相关压力和工作的物理、心理环境具有较强的敏感度和负责态度;善于采取一系列支持性措施或影响策略来激发组织成员的健康行为,下属提供健康的工作条件(如:通过工作设计、工作氛围改善等),鼓励和帮助下属参与到健康的工作行为中(如:遵守健康规则、避免过度劳动等)并且提供健康和安全事项资源和信息(如:实施工作场所健康促进计划,支持员工参与行为等),从而为提升组织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其次,领导者需要承担下属健康关心的责任。要建立健康组织,提升企业整体健康水平,领导者需要对健康管理赋予优先级。领导者下属健康关心程度越高,下属越能拥较强的工作控制能力、良好的工作设计、较丰富的工作资源、较高水平的工作要求平衡、较清晰的工作角色和富有价值的工作意义等;自我健康关心程度越高,过度承诺的工作状态发生的可能性越低,员工面临过度劳动、职业倦怠、健康状况受损的风险也越低。
最后,健康组织的建立需要“仪式性”活动进行推进。研究表明,领导者的下属健康关心中健康观念对下属健康状况起作用的过程中,下属自我健康关心中的健康知觉起到的中介作用最大,这说明在认知层面上宣传健康价值观、促进健康意识、提高健康敏感性等对推进企业健康组织的建立起到了作用。正如早期的制度主义学者认为,组织为了应对制度体系的要求而采取某些仪式性行为,形式和内容会产生“说做两张皮(de-coupling)”的状态;但近期的制度主义学者研究发现,这些仪式行为会对企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并最终由“形式”变成“现实(Tilesik,2010)。因此领导者可以采取一些仪式性的健康实践互动,如为每名员工设计健康计划、进行每日健康打卡活动或企业健康之星评选活动等,来推进企业健康组织的建立。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所采用的是横断面研究设计,无法具体揭示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虽然研究发现下属健康关心通过自我健康关心对健康状况产生影响,但现实中这种影响的方向可能是双向的,这也是杜班拉的社会认知的交互决定论观点中早已强调道。因此今后的研究可进一步考察健康随时间的系统性变化以及在此过程中领导者下属健康关心与自我健康关心之间的因果关系,确定变量间的关系机制,为健康促进型领导的研究提供更丰富的实证研究支持。
1.Anderson D, Plotnikoff R C, Raine K, Barrett L. Development of measures of individual leadership for health promotion. Leadership in Health Services, 2005, 18(2): 1-12.
2. Andrea E, Runo A, Susanna B A. Development of health promoting leadershipexperiences of a training program. Health Education, 2010,110 (2): 109 -124.
3. Arnold K A, Turner N, Barling J, Kelloway E K, Mckee M C.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meaningful work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 2007, 12(3): 193-203.
4. Bandura A. Principles of behavior modifica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69.
5. Canjuga M, Laubli T, Bauer G F. Can the job demand control model explains back and neck pain? Cross-sectional study in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Swiss working popul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Ergonomics, 2010, 40(6): 663-668.
6. Daniels K. Why aren’t managers concerned about occupational stress? Work & Stress, 1996, 10(4): 352-366.
7. Dellve L, Skagert K, Vilhelmsson R. Leadership in workplace health promotion projects: 1-and 2-year effects on long-term work attendance. Europe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07, 17(5): 471-476.
8. Dunkl A, Jimenez P, Zizek S S, Kallus W.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health-promoting leadership and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Naše Gospodarstvo/our Economy, 2015, 61(4): 3-13.
9. Eriksson A, Axelsson R, Axelsson S B. Health promoting leadership-different views of the concept. Work, 2015, 40(1): 75-84.
10. Franke F & Felfe J. Instrument health oriented leadership. Heidelberg: Springer, 2011.
11. Gavin J F, Kelley R F. The psychological climate and reported well-being of underground miners: An exploratory study. Human Relations, 1978, 31(7): 567-581.
12. Goetzel R, Ozminkowski R J. The health and cost benefits of work site health promotion programs. Annual Review of Public Health, 2008, 29(6): 303-323.
13. Gregersen S, Vincent S, Nienhaus A. Health-relevant leadership behavior: A comparison of leadership constructs. Zeitschrift Für Personalforschung, 2014, 28(1-2): 117-138.
14. Gurt J, Schwennen C, Elke G. Health-specific leadership: Is there an association between leader consideration for the health of employees and their strain and well-being? Work & Stress, 2011, 25(2): 108-127.
15. Haber M G, Cohen J L, Lucas T, Baltes B B.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reported received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 meta-analytic review.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007, 39(1-2): 133-144.
16. Hobfoll S E.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A new attempt at conceptualizing stress.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89, 44(3): 513-524.
17. Leiter M P, Frank E, Matheson T J. Demands, values and burnout: relevance for physicians. Canadian Family Physician, 2009, 55(12): 1224-1225.
18. Piko B F. Psychosocial work environment and psychosomatic health of nurses in Hungary. Work & Stress, 2003, 17(1): 93-100.
20. Preckel D, Kanel RV, Kudielka B M, Fischer J E. Over-commitment to work is associated with vital exhaustion. International Archives of Occupational & Environment Health, 2005, 78(2): 112-122.
21. Tilcsik A. From ritual to reality: Demography, ideology and decoupling in a post-communist government agenc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0, 53(6): 1474-1498.
■ 责编/王震 Tel: 010-88383907 E-mail: hrdwangz@126.com
Health-Promotion Leadership: Its Definition, Measurement and Effect on Employees’ Health
Liu Beini
(School of Labor Economics,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Combing the concept of health-promotion leadership from characteristic perspective, behavior perspective and contingency perspective, put forward the definition of health-promotion leadership is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contains the views of leaders and followers, including health value, health awareness and health behavior. Through the survey of 493 employees, fin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health value, health awareness and health behavior are three distinguish and validity structural dimensions of health-promotion leadership concept. Leaders’ staff care h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to task characteristics, work environment and working climate, self care h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relation to over commitment, in leaders’ staff care play a role in the process of health state, self care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Based 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we put forward that leaders need to practice the organizational health management from three aspects: health conception, consciousness and behavior, take responsible for staffs’ health care, through the "ritual" activities to promote establishment of a health enterprise organization.
Health-promotion Leadership; Leaders’ Staff Care; Staffs’ Self Care
刘贝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电子邮箱:liubeini818@126. com。
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我国劳动者过度劳动问题及其政府规制研究》(14CJY07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高校教师工作时间分配、隐性过度劳动及其干预机制》(16BSH007)、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术新人项目(CUEB2015003)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