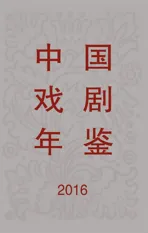对京剧发展的点滴思考
——上海京剧院的启示
2016-11-20马也
马也
二十多年前,上个世纪后半,当全面深重的戏剧危机来临的时候,很多人以为京剧这种经典传统的艺术形式已经过时了枯萎了,她也将同昆曲一样退出艺术史舞台而走进博物馆;但是《曹操与杨修》的横空出世,以及《狸猫换太子》的“轰动京师,技压群芳,艺覆歌楼,戏馆一盛”,却给萧条的京剧艺术带来了希望和亮光。上海京剧院向时代证明了:京剧艺术,依然有着很强的艺术生命力甚至是很强的艺术成长性。
适逢上海京剧院60大寿,对上海京剧院60年来的发展路程,确实很有必要进行阶段性的理论梳理和经验总结了。我以为,对这种梳理与总结应该强调两点:一是,必须将其置入中国戏剧发展史甚至是文化发展史的历史平台和理论框架之内,二是,注意找寻一些艺术史中带有规律性和真理性的东西;否则我们就既看不清它的来龙去脉更看不清它的真实面目,当然也难以发现其价值与意义。这种总结和梳理不止对上海京剧院来说是有意义的,对京剧本身甚至对整个中国戏曲的健康发展也是有意义的。
来沪开会前,我还是认真地做了些功课,想对海派京剧以及上海京剧院的发展经验做点儿新的表述;但是想来想去,还是回到了“概念化”的老套表达上——我以为上海京剧院给京剧的最好的也是最大的启示就是“创新求变”。周传家先生总结的海派京剧发展的四个阶段,很有水平。我想做一点儿感性的罗列,周信芳及其以前的时代不说了,只说样板戏之后的一些重点剧目:《龙江颂》、《海港》、《智取威虎山》;《曹操与杨修》、《贞观盛世》、《廉吏于成龙》(龚和德先生称之为“尚三部”);《狸猫换太子》、《成败萧何》、《金缕曲》(龚和德先生称之为“陈三部”),其他的也不说了。戏迷和专家们能说出京剧的大体脉络,但是年轻观众甚至大学里的学者,未必都了解:当今时代,只一个上海京剧院就守住了中国京剧的“半壁江山”——要我说,从京剧发展史的角度看,上海京剧院,大于半壁江山。我不知道中国有多少个京剧院,几十个总是有的。但是大多数京剧院并没有几个优秀的新编新创剧目。很多青年观众甚至大学教授,未必知道上海京剧院,但是可能知道前列剧目。我可能研究得不够,我找不出来,再有哪个京剧院团有如此辉煌成就。
问题来了,这些成就是怎么成就的?会上很多专家从各个角度做了很好的分析,演员优势、管理优势、团队优势、领导优势、地域优势等等,我都赞成。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创新求变”。周贻白先生很早以前的话,我认为还很准确:“实则京朝派和海派,各有其独擅剧目和著名艺人,两者颇难轩轾,如目京朝派为近于保守,则海派实以京朝为其基础;如认为海派过于火野,则京剧实由此而获得一些新的发展”(请注意,周先生这里强调的是“新的发展”)。20世纪初的海派京剧,和京派京剧相比,大体有如下几个特色:一是唱腔灵活流畅,善于变化,能及时适应上海观众的欣赏趣味和审美需求;二是剧目比较追求情节性、新鲜性和趣味性,例如海派京剧首开京剧演出连台本戏的先河;三是演出形式善于花样翻新,舞台布景追求时尚新奇,如海派首先使用灯光布景,舞台装置首先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四是能较快地接受西方的新思维新思想。上海是近代中国最早得西方资本主义风气之先的大城市,一批具有改良改革精神的新型京剧艺术家,如汪笑侬、潘月樵、夏月珊、夏月润等都出自上海,他们思维活跃,思想进步,甚至直接投身于资产阶级革命;这批海派艺术家身上有很强的革新精神,创作上不拘陈规,表演真切率直,是近代戏曲改良运动的中坚力量。当然,早期的海派京剧也有过火和恶性发展的时候,但是其核心精神是创新求变,是创造性发展。说到创新发展,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创新和传统的关系。近几年来,对于京剧创新问题,有很多反对的声音,例如说:“世界上的事物都在变也该变,唯独京剧是个例外”;“京剧应该退回到一百年前”;“京剧创新是个伪命题”,“京剧压根儿就不需要创新”;要挽救京剧应该“向后看”,眼睛要盯住传统,要坚守传统、坚守本体、回归传统、回归本体、回归古典;京剧乃至文化,根本就不需要创新,等等。
“五四”文化论争时,一些文化虚无主义者,从内容到形式,全盘否定中国戏曲;张庚先生总结他们的观点是:戏曲(主要是京剧)“要不得”。我闹不明白的是,一百年前的“要不得”,到今天怎么就突然“动不得”了?“动不得”观点的具体展开是:“改不得”、“变不得”、“碰不得”、“新不得进不得”、(“进不得”是说话剧导演进不得,因为他们“祸害了”戏曲。);更有甚者是要“原汁原味儿”地模仿和继承。
这类观点目前正在强有力地扩散着、弥漫着。我认为,发展下去,在理论思维上会带来混乱,在戏剧创作上,会窒息扼杀创新创造。我这里既不是猜测臆断也不是危言耸听。近一两年来,我已经很多次听到一些年轻的理论家(有的还是戏曲理论的学科带头人)向我问起:到底是发展创新正确还是回归传统正确?他们自己经常处于一种犹疑摇摆之中。有学者前几年在《文艺研究》上发文称,梅兰芳从来就不承认他演戏(京剧)是在塑造人物形象;戏曲(尤其是京剧)也从来不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主要目的。有的戏剧专家,一会儿反对这种观点,一会儿又觉得这种观点是对的。我有个很有成就的剧作家朋友,动手写京剧,当看到一些专家说京剧“动不得”的观点后,竟然说,我不敢动笔了。不少人在这些似是而非的观点面前,糊涂了;更有甚者问:是不是上面的政策导向又有变?
“动不得”理论,其来头都不小,这是其弥漫扩散,产生较大影响的原因之一。从我看到的文章来说,有资深戏曲专家、有身处一线的戏曲表演艺术家、有学者、有戏剧界的领导、有媒体记者。我得罪不起这些人(当然,也怕误解了误读了他们的观点)。这里我只能举一个例子,那就是昨天上午会上发言的傅谨先生。我之所以敢于在这里表明我不同意他的观点,是因为我们是多年好友,不会得罪他。这两天微信和网络上很多人在传他的文章。他说,戏曲界的创新创造,多年来如同狗熊掰棒子,最后只剩下一个,还未必是最好的。这个观点我基本同意。但是,他说“文化需要保守,不需要创新”;说“戏曲创新多半只是一种对传统不知不懂的掩饰”,我无法苟同。傅谨先生有很深厚的学术背景和理论话语权;我周边的学生及一些年轻的专家学者,多为他的“粉丝”;他的观点虽不至一言九鼎,但影响很大。
京剧的存在,我以为,起码可以有三种方式,这也就提供了我们观察研究的三个角度三个层次或称三个维度:一是“非遗”角度,二是剧种角度,三是具体剧目也即“艺术品”角度。作为“非遗”(或传统),应该完整保留保存保护,甚至是抢救;哪怕现今不用的“跷功”等等过去的技术绝活,这些东西多存在于老艺术家身上,也应该作为遗产保留。这类工作主要应该由“非遗”部门去做。京剧院团,不是“非遗”司,它的第一任务是出人出戏出好的艺术作品;第二,是肩负着剧种发展的使命(其实这第二点已经天然地被第一点涵盖);第三,剧院剧团如果有能力有条件(当然也有义务有责任),不是不可以做保护“非遗”工作,而是说那不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作为京剧院团,我以为,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创造优秀作品:剧种的发展,剧团的生命,演员(角儿)的前途,多半依赖于好剧目——伟大的戏剧作品。大师的诞生,也要靠好作品说话。
一个剧种,“兴盛还是衰落”,“生存还是死亡”,关键或根本问题,是能否创新创造、能否表现新的时代和新的人物。地方戏的“兴”和昆曲的“衰”,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自身生命力的兴和衰。但是昆曲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不能与时倶进,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变革创新,脱离时代脱离大众。张庚先生说:“昆曲有一个与生倶来的致命弱点,即对农民的生活与斗争,缺乏了解,有些人还对农民存有偏见。当梆子、皮簧兴起,在舞台上创造了许多吸引观众的农民起义人物的形象时,昆剧却对之一筹莫展,它的演员连表演这些新人物的基本功都没有。由于昆剧演员对新兴的地方戏在艺术上存有偏见,他们甚至还对之进行抵制。在苏州这个昆剧的故乡,演武戏的戏班是不许进老郎庙的不许进城演出的。这种固步自封的态度,使他们更加脱离群众。与当时的地方戏舞台上的一股新鲜空气相比,昆剧舞台上那些人物和他们的生活就显得陈旧,大多数群众对昆剧的兴趣也就减弱了。加之,昆剧的艺术表现风格,轻歌曼舞,也很不合这个时期广大观众的口味。这时期新兴起来的地方戏,大多是急管繁弦,慷慨悲歌,唱得人们耳热心酸,因为不如此就不足以表现金戈铁马的内容和叱咤风云的人物”。上世纪初,戏曲改良时期大量的时装新戏,虽然很少有成熟的或可以保留的,但是这对古老的传统戏曲如何表现现实生活及其人物却做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中国传统戏曲艺术如何表现新时代的生活和丰富多彩的新人物,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课题。……戏曲艺术经过千锤百炼,已经形成精致的独特的艺术体系。而要让这样一个已形成完整体系的传统艺术去表现崭新的生活内容,的确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回顾近百年来戏曲发展的历史,从辛亥革命前夜提出戏曲改良,经过多次失败,几乎失去信心,认为旧戏根本不能表现新生活……这段历史表明:戏曲在新时代是不可缺少的;它在表现现代新生活方面走过一段漫长崎岖的道路,戏曲家们从根本不知道如何表现到逐浙懂得如何表现,一点一滴地积累着经验”。
《曹操与杨修》虽然不是现代戏,但它所塑造的曹操,在戏曲史的画廊里是个全新的人物形象。关于这—点,在以往的研讨中很多专家都做了精彩的评论:有人认为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曹操;有人认为是一个新的活曹操;有人认为不只是“活”而且在形象深度上超过了《三国演义》及以往所有同类作品的曹操;有人认为是戏曲史上京剧史上无数个曹操中最新最好最成功的曹操形象。同时我认为,这一个曹操也更是一个高难度的人物形象。难就难在曹操人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深刻性和玄妙性。“三杀”,尤其是灵堂杀妻,情节的玄妙性和人物的复杂性简直是超乎人们的想象。如此复杂深刻丰满的形象,单凭感觉来说,话剧似乎可以塑造完成,京剧能吗?能。《曹操与杨修》从剧作到表演都证明了京剧艺术的表现力。凡是(人性)复杂深刻丰满的高难度艺术形象,离开心理深度的开掘和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看到,“三杀”的每一杀,包括雪夜巡营曹操与杨修性格冲突的升级,都有极为丰富的心理内容。错杀孔闻岱后的极度惊恐和追悔,杀倩娘时的万分痛苦和无奈,杀杨修时的矛盾、犹豫和煎熬。尚长荣淋漓尽致的表演,扎实严密地揭示了曹操悲剧性格的心理历程。龚和德先生说,这是心理现实主义在京剧表演艺术上的胜利,此评甚为精准。
京剧的当代发展,发展不顺利是一回事,要不要发展是一回事,怎么发展又是另一回事;创新创造,成果不丰厚是一回事,要不要创造创新是一回事,怎么创新创造又是另一回事。这是三个层面的事情,不能混淆,不能代替。有些眼花缭乱的甚至是胡作非为的创新不应该成为倒退(京剧回到过去)的借口。这些都是艺术发展史中的根本性问题、真理性问题、原则性问题;我们不该在理论逻辑上出现混乱。
顺便碰一下“禁区”。我不同意彻底否定样板戏的艺术成就和创新经验(十年间,八部革命样板戏,上海京剧院有二部)。我认为我们今天的很多剧目与样板戏相比,是大踏步倒退。把样板戏当成某种工具,政治上另有目的,可作别论;但是从唱腔设计、音乐设计,到表现现代生活的程式创新,到整体舞台呈现的完整性,多半应该肯定。对样板戏的评价应持一种全面的客观的分析的态度,那不是几个人的事情,那是全国之力(多少剧团,多少优秀作家艺术家的艺术积累、智慧和才华)的合力与结晶。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彻底否定样板戏),起码是一种政治的不自信,更是一种文化的不自信。当今年轻一代,很多人不懂京剧,不爱京剧,但是他们不讨厌样板戏;有些年轻人的京剧启蒙,也来自于样板戏。
傅谨先生坚持“保守”,反对“创新”,是错把艺术生产部门当成了非遗保护部门;或者以为,既然创新没有创好,还不如回到过去,也是逻辑上有问题。另一些人的主张,我有些理解不了:怎么“原汁原味儿”地继承?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原汁原味儿这码事儿。你娘生下你之后,就永远回不到娘胎里了;过了此刻的你,也不再是原汁原味儿的你。还有,什么是“坚守本体”、“回归本体”?本体是什么?本体在哪里?“前三杰”是本体?“后三杰”是本体?徽汉合流是本体?传奇杂剧是本体?还是金院本、唐大曲、秦汉百戏是本体?做个假设:假如今天的京剧没有了“京胡”,还是京剧吗?肯定不是了。但是,京胡这种东西,根本就不是京剧与生倶来的东西。早期京剧(徽班进京直到徽汉合流)的胡琴与后来的京胡,天壤之别。京胡是在梆子胡琴的基础上,经全面改造创新而成。
一部戏剧发展史,就是:“变”的历史。
把京剧只是当成“国粹”、当成文化、当成绝技向世界去展示展览,京剧可以不用动,可以“原汁原味”地晒出。同样可以晒出的还有“小脚”、“三寸金莲”、“烟枪”、“鼻烟壶”等等。但这些未必是艺术,未必是真正意义的戏剧艺术。西方人的好奇和“惊呼”,并不代表我们艺术上的伟大。
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关于“传统”。我同意安葵先生的意见,传统和创新的关系,早就讨论得很清楚了,只是现在又弄乱了。
传统需要尽全力保护保留保守。但是,我们保留传统,干什么?这是个问题。有些人说要“坚守传统”、“回到传统”。我以为这个观点不是似是而非,而是完全错误。你“坚守”这些传统干什么呀?你又不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今天,无论是从中国梦的实现动力还是从中国梦的重要目标而言,都离不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些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是传统只是“根基”,是发展的前提。对于京剧的健康发展、对于伟大作品的创造,传统是必经的路径,是丰厚的滋养;传统必须要经过创造性的转化,要经过创新性的发展,才能体现其重要重大价值和意义。对于剧种来说,传统是基础,创新性发展是目的;对于剧目来说,传统是手段,伟大优秀是目标。继承传统、借鉴传统,本来就是发展、创新、创造的题中应有之意;换句话表达就是,你离开传统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对于剧院和艺术家来说,单独强调“坚守传统”,这种表述本无意义;加上反对创新的意思,就有了意义——是倒退的意义。艺术实践中,确实有不懂传统、丢弃传统,甚至是破坏传统的先例;但是我敢断定,他们一定不会成功。这不能成为反对创新创造的理由。一部《曹操与杨修》,从剧作到表演,既是借鉴传统的最好例证,也是创新创造的最好例证。尚长荣先生说所谓创造就是:熟知传统又不被传统所拘束,掌握技术又不被技术所拖累;要“激活传统”,“巧用程式”;对传统要有“创造性”发展、“灵活性”把握、“生活化”体验(“拨动当代观众的心弦”);行当、程式、传统”要为塑造人物服务”。我以为,他把传统与创新创造的关系说透了。多年来,我爱读的一部书是龚和德、黎中城先生主编的《京剧<曹操与杨修>创作评论集》(推荐一下: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5月版)。此书我每读一遍,都有新的收获和感悟。关于戏剧创作中,传统与创新的关系,此书已经讨论得非常透彻了;由于是对一部具体作品的分析研究,就更具有说服力;我以为,此书可以作为京剧院团和戏曲艺术家的教材。
会议结束时又重看《曹操与杨修》演出(青年版),虽非尚长荣登场,但仍感慨良多,回家整理发言稿,有些话不吐不快。文艺座谈会上习总书记说我们的文艺“有高原缺高峰”;现在“高峰”一词就成了避讳,不大敢有人用了。他只是说“缺”不是说无。多高是高峰?8848米?我以为,比高原高的就是高峰。在当代戏剧发展史上,上海京剧院就是高峰,在30多年来数以千计的新创戏曲剧目中,《曹操与杨修》就是高峰,在京剧的表演艺术和艺术家中,尚长荣就是高峰。别处的高峰,虽然可能不多但可能还有,只是在这个发言中我没有顾到。
窃以为,我们还是低估了上海京剧院和《曹操与杨修》在京剧发展史上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