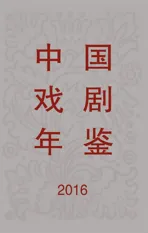如果只有模仿,戏曲终会怎样?
——就“张火丁现象”与傅谨先生商榷
2016-11-20张之薇
张之薇
在今天这个时代,戏曲式微,所以话题极少,能真正把这个圈子搅动,并让人兴奋异常的人和事更是凤毛麟角,而张火丁却称得上是戏曲圈一个令人亢奋的话题。这不仅是由于作为一名京剧旦角,但凡有她登台的戏票都能迅速售磬,甚至黄牛票都能炒出数十倍的价钱,而且由她搬演的戏,虽然以传统戏居多,竟然也不乏收获无数戏迷们的狂热追捧。早已被大众艺术边缘化的戏曲,而且还是所谓的与当下时代疏离的经典老戏,只要假以“张火丁”这么一个金字招牌,立马拥有了必胜的市场保证,不仅不是票卖不出去,而且还是以最快的速度售罄,这着实让众多戏曲圈内人匪夷所思,也不由令人恍惚:戏曲到底是真的衰微了,还是我们的戏曲没有把准观众的脉,或是舞台上演的戏不是观众真正想看的戏?这些问题的确值得我们思考。但要命的是,一些理论家却从这并非具有普遍性的“张火丁现象”生发出去,偏激地把对经典传统戏的模仿和重复视为戏曲发展的正道,反之,则把创新精神视为当下戏曲发展的畏途。
一、京剧的历史是由无数极具创新精神的伶人书写的
且不说,张火丁的表演到底是不是对经典老戏的模仿和重复,到底是不是对程派艺术原封不动地继承,先说中国戏曲,或者说以京剧为代表的戏曲艺术,在它的发展历史上似乎谁也不会,同时也不敢这么武断地给“创新”判了死刑,因为无论是从京剧孕育萌芽的阶段还是京剧成熟繁荣的时期,吸纳与变化都是它赢得观众,赢得市场的关键,而京剧的历史,一言以蔽之,也可以说是由无数极具创新精神的伶人写就的。
前有魏长生,这个在京剧真正形成之前无法被人忽视的秦腔花旦魁首,为了把女人的俏和妖展现在戏台上,除了大胆改革足底的跷功,还把从前旦角以网子盖头的“包头”改为了梳水头,也就是用假发梳成了一个坠髻,并以云鬓珠翠装饰,这种装饰在今天的戏曲舞台上已是司空见惯,但是在乾隆年间却无疑是大大的创新,并引得京城花旦争相仿效。中有谭鑫培,这个京剧历史上首被称派的创始人,逆老生行的洪钟大吕而上,打破行当界限、创造新声,将青衣、老旦、花脸行当的唱法,以及昆曲的咬字方法都被他拿来融化在了自己的唱法中。他的标新立异使得当时投向他的唾沫星子从没少过,但是就是这种清醇流利、余音绕梁的新式老生腔,成就了“满城争说叫天儿”的地位。后又有梅兰芳,这个早年被无数新文人围绕的旦角,在新旧思想撞击的大背景下也曾着意革新,更留下了众多时装新戏、古装新戏等异于传统剧目的作品。也就是说,无论是在装扮上,还是在唱腔上,抑或是在剧目的内涵上,在京剧发展的不同阶段,都经历了伶人们顺应时代的变革和创新。也可以说,没有一位永载史册的京剧名伶是靠模仿或重复而成就自己的,这在过去是如此,现在是如此,未来也必然是如此。
那么为什么到了今天,就可以有理论家如此高调地标榜模仿和否定创新精神呢?我要说,这只能算是今天这个时代的悲哀,但这绝非是值得宣扬的真理。若是搁到程派初创的那个旦角繁华的民国季,面对市面上你追我赶的新戏编排,程砚秋也如是标榜自己,那恐怕跻身“四大名旦”之列是永世无缘了。谁都知道,程砚秋的嗓子由于变声期没变好,遂独辟蹊径,打破旦行旧制,把旦角的高音和脆音向宽和厚发展,创立独具特色的“鬼音”;谁都知道,程砚秋曾经专门赴欧洲考察西方音乐,无论是发声方法还是唱腔设计,甚至是唱词都有向西方音乐借鉴之处,最终成为了他在后来唱腔编创中的营养源泉;谁都知道,“模仿”这个词在程砚秋看来绝对不是后辈继承程派技艺的上佳之选。
二、京剧的“传统”究竟是什么?
实际上,在今天这个年代,戏曲作为边缘艺术,风光不再的现实无可否认,而戏曲界的创作者们就像被豢养的动物般早已失去了求生的技能,他们也失去了在老祖宗留下的玩意儿面前创造它和超越它的能力,于是一些走极端的理论家们觉得退而求其次,能够模仿和重复好前人就已经很好了,仿佛前人、老戏就约等于传统。听起来,这话似乎有些道理,甚至很能俘获一批戏迷的心,但是细究起来却发现问题很大。
首先,持此言论的都是立志要宗法传统的,而持这般言论的理论家也毫不讳言自己是保守主义者,因为据说他们对“传统”充满敬畏。但是,我想问的是,传统究竟是什么?可以简单而模糊地界定为旧戏吗,或者是过去的名角儿演的传统戏?那些让今天戏迷们高山仰止的传统老戏或经典老戏又是怎么来的呢?
实际上,事物一旦降生就走在了“变”的路上,也走在了变成“旧”的路上,京剧当然也不例外。所谓京剧的传统不是今天有今天的传统,明天有明天的传统,而是像人的骨骼一样,世世代代生长在伶人心中的,这根骨就是京剧中的“三级韵”和“身段论”。“三级韵”管的是唱念,“身段论”管的是做打,这些均属于京剧这门艺术形式的规律法则,而京剧的延续、生长也正是由这些颠簸不破的规律构成的。不过,京剧不是只有骨,它也是有肉的,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肉对骨的充盈,才有了京剧的美妙和博大精深。它的“肉”就是角儿们在艺术法则中注入自己的风格和个性,注入了自己的体验和创造。京剧流派纷呈的原因大抵如此。所以,所谓“宗法传统”说出来是件多么可笑的事情,如果真的京剧历史上伶人都标榜自己只宗法传统,那么结果很容易想象,就是京剧演员们仿佛是一个模子刻出来,舞台上只有干瘪的程式,不仅看不到演员的个性,也看不到演员所塑造的人物,于是形式也失去了意味。这时传统倒是有了,可也只剩下传统了,京剧还能有它的魅力吗?这里我们又提出一个问题,京剧是仅有形式就可以了吗?虽然在今天,很多专家也是持如此观点,代表性的是武汉大学的邹元江教授,曾以梅兰芳的“表情”为切入点对此曾经有过慷慨激昂的长篇论文。虽然,此问题并不属于本文探讨范围,但我以为如果仅有形式,没有意味,没有意境,京剧绝不会出现数个高峰。
那么,京剧的传统究竟应该如何对待才是正确的呢?真的是复制和模仿吗?京剧历史上的大家很多,无一不是海纳百川,并专注于将“传统”拿来为我所用的。杨小楼、尚和玉同是师从俞菊笙,然尚和玉却在之后的声名远远没有杨小楼响亮;余叔岩和王又宸也是同宗谭鑫培,而王又宸在京剧的历史上能被人记起的机会也是少之又少;梅兰芳与王琴侬均在陈德霖“六大弟子”之列,王琴侬在嗓音条件更是深得陈老夫子赏识,而王琴侬在京剧旦角中的地位却根本没法和梅兰芳比,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无他,一言以蔽之,都是模仿惹的祸。说的更明确些,就是缺乏自己的独创性。从上面的例子看得出,伶人如果没有创造性,一味模仿别人,后果将多么可怕!对于京剧艺术来说,在像与不像之间权衡,也许某种继承基础上的太过相像反而会葬送一个伶人成为大师的可能性,就更别提百家争鸣,开宗立派了,最终的结果是也无法推动京剧艺术向前发展。
所以,创造性地继承传统是句金句,创造的意义决不能抹杀。“传统”在过去科班出身的京剧伶人中都是刻在他们心中的,只是有些人把它当成了不容撼动的铁律,而有些人则把它变成了可随自己需要变化的金箍棒,匠人和大师的区别恐怕就在于此。正如子舆在《京剧老照片》中所说的:“匠的手是自己的,心是别人的,所以技术再高,描摹得再像,活儿做得精细,还是个匠人。而家则不同,有时他的手或许是别人的,但心永远是自己的,所以无论他随意举手也好,任意投足也罢,表达的都是自己的思想”。这就带出了京剧表演的几个境界的问题。下级表演,只演程式,对人物仅仅进行类型化的表现;中等表演,只是追求演好剧本中的人物性格;而上乘表演则是能够把人物性格与程式技艺结合,再通过自己的体验运用个性化的条件进行创造的表演。显然,京剧的上乘表演是一场心与技的最佳融合。这就要求在表演的过程中,如何能够从人人皆烂熟的一招一式中表现出伶人自己的“表情”,才是最重要。这个“表情”则是伶人将技艺与剧中人物性格结合后的个性化表现,而非如邹元江教授所说梅兰芳的“表情”是沾染了西方思潮之后的话剧表演方法。
三、“应不应该创新”和“如何创新”是两个问题
其实,除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对京剧的“新旧”之争外,在京剧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把“新”与“旧”分得如此泾渭分明。不同的是,“五四”时新文人嫌弃的是“旧”,推崇的是“新”;而如今,在一些理论家看来,“旧”总归是好的,正宗的,甚至上升到了对“旧”的模仿与复制都比“新”高级;而所有“新”的自然就是低级的,经不住时间考验的。而实际上,在京剧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旧”并不一定意味着就是传统,“新”也并不一定就是意味着打破传统的。清朝光绪年,老生腔相对于程长庚的洪钟大吕来说,谭鑫培略带甘甜的“柔靡之音”就是新,而到了民国初年,相对于老生谭鑫培,那拥有无数倾慕者的旦角梅兰芳就是新的。一代有一代之“旧”,一代有一代之“新”,新陈代谢规律不能避免。但“新”与“旧”从来就不是衡量伶人优劣的标准,相反倒是模仿和创新始终是让伶人们高下自现的试金石。然而,今天,难道一切都颠倒了?
当然,理论家坚持认为文化需要的是保守,而不是“创新”,可能是被流行在今天我国戏曲舞台上胆子过大的“创新”给伤着了。但是不能因此而混淆“应不应该创新”和“如何创新”两个问题。回答前一个问题,一定是肯定的,毋庸置疑的,因为京剧,乃至于戏曲发展的历史就是创新的历史,改革的历史。而回答后一个问题就成了值得每一个当代戏曲人思考的重点。
在谈这个问题前,我们首先需要厘清创新主体的问题,也就是什么样的人才能担负得起京剧创新这个任务。今天这个时代与曾经京剧鼎盛的时代完全不同,今天是个谁都能谈几句京剧,但谁都对京剧的规律所知甚少的年代,所以,与民国时围绕在名伶周围的众多文人献计献策实践京剧不同,创新,这个技术活儿现如今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承担的,更不是一些光说不练的理论家所能够承担的。值得信赖的人,恐怕必须是戏曲艺术创作一线的艺术家,尤其是对“场上”的规律极为熟稔的人,特别是能够通晓并有能力进行剧本创作与舞台创作的艺术家。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创新不至于丧失京剧本体,是基于他们对传统有效地继承,对其他剧种和艺术有效地借鉴融化、对戏曲人物深入通透的理解和对时代审美变化的敏锐感知。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这样的人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少了,不仅如此,更令人尴尬的是,在我们戏曲创作人中还有些本来拥有一身的手艺却对自己的手艺自卑而摇摆的人。这是今天戏曲,也是今天京剧的现状,但并不能因此就否定了创新这回事。面对京剧这门古老艺术,我们需要检讨的是今天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在尊重它一以贯之的吸纳、包容的本来特质下,去创造它,发展它,让今天的我们依然能够穿越几百年的光阴而能够发现它的美好,缔造它的经典性,而不是奉行文化保守主义,使创新成为今天戏曲发展的禁忌。
四、多师之徒张火丁果真只有忠实继承吗
再回到文章开头的张火丁,我们可以大胆假设,像张火丁这样出色,并已具盛名的演员,她既有对舞台的熟悉程度,又有对艺术的极致要求,假如周围拥有像梅兰芳时代那样极具传统文化素养和京剧艺术素养的多个而非一个捧角家们,那么张火丁必定是发扬程派艺术当之无愧的人选。可惜的是,张火丁目前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与民国时期,名旦们在舞台技艺的精研之余,他们还对琴棋书画等文人修养方面也是多多研习不同,今天的戏曲演员多面临文化知识欠缺的尴尬,就更别提文人修养的境界了,民国时的名伶们得益于在他们的周围簇拥着一大批深谙其道的文人,可今天这个社会的文人们不仅已难有旧文人的学养,甚至连对戏曲艺术的本体和规律或许都模棱两可,所以即使有文人充当名伶们的顾问,对名伶们进行指点,演员也应该谨慎地听,文人也应该谨慎地说,否则,可能就会错误百出,不仅误导了演员,也误导了观众。像张火丁这样的演员,一定是渴求有文人给她指点的,可惜的是,她的文学顾问傅谨先生给她定下的基调似乎有悖一个戏曲名伶正常的发展规律。那就是“忠实地继承”,“原汁原味地继承”,所谓“老戏老演”,不谈超越,只谈模仿。如果一个还没有达到一定高度的演员正走在学习程派的路上,那么她谈忠实地继承或许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对一位业已成名的演员来说,始终在强调她的继承,甚至是模仿地继承,那或许就显得缺乏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因为,无论是对于京剧的发展来说,还是对于一个演员的发展来说,传统永远只是他们的必经之途,是丰厚的滋养,是桥梁,是过程,而非终极目标。任何一位演员只有能做到创造性地继承才能发挥其更大的意义和价值,才能在戏曲史上留名,否则,也许就是沧海一粟。所以,对于张火丁来说,如果真的止步于继承和模仿,那将是件多么遗憾和可悲的事情。
然而,张火丁果真如她自己和她的文学顾问所说,没有创造吗?其实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她的程派成长史,就可以轻易地否定此种说法。和京剧历史上很多大家一样,张火丁也是多师之徒,她少年时学习过评戏,15岁改学京剧,以梅派、张派起家,启蒙老师王兰香,后又是从渠天凰,张芝兰、李近秋等师,后由于她对程派的喜爱,向程派第三代弟子李文敏,也是程砚秋门下重要弟子赵荣琛的弟子学习程派重要剧目,奠定了扎实的程派基础。但是,张火丁似乎最为著名的老师还是赵荣琛,1993年,张火丁正式拜在了赵荣琛门下,成为关门弟子,得其亲授。赵荣琛去世后,张火丁又南下拜在了程派著名演员新艳秋门下,后来还曾向程派名家李蔷华、王吟秋学过戏,像这样的多师之徒,不知如果要“忠实地继承”该如何继承,该继承谁?是继承她的师爷程砚秋,还是继承她的师傅赵荣琛,还是其他谁呢?因为这些程派艺术的传承人绝非一个模子,完全一致。一个并非悟性很差的多师之徒,必然是综合的,融会贯通的、博彩广纳的,而绝非固步自封、亦步亦趋的,又怎能丝毫没有自己的创造呢?至于张火丁是否能够在名声上还是在技艺上超越她的诸位老师们,则只能留待时间来评判了。不过,如果她依旧一味标榜自己没有超越,只有继承,而她也果然是这么做的,恐怕她也真的不会有超越的那一天了。
京剧研究专家刘曾复先生曾经说过:京剧艺术从“大老板”程长庚,到后来谭鑫培、杨小楼、王瑶卿、余叔岩、梅兰芳等诸位前辈,他们的一生,走的都是继承创新的路,有关他们的历史经验需要认真研究,认真学习,从中对京剧的历史优越性和局限性得出正确的认识并总结经验,对今天的京剧无疑大有益处。我就拿这句话作结,也与今天的理论家们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