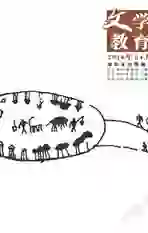平民的“江湖”
2016-11-19曹霞
自从《老炮儿》“火”了以后,“江湖”一词又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道出了古代文人进退之间不改其心的情怀。在金庸、梁羽生、古龙等人的小说里,它指的是刀光剑影、侠义道术、爱恨情仇交织的“武林”。在《老炮儿》里,它指的是80年代的民间“英雄”、草根“大哥”们自我打造和口口相传的规矩道义。虽然电影表现的是“老炮儿”在以“金钱”为唯一衡量标准的当下社会的隔膜与失败,但他们的热血情义、恩怨道德,以及他们在新旧世界、贫富悬殊、代际隔膜等一系列冲突与裂隙中辛酸难忍的“解决之道”,都使之成为生活中典型的精神症候群:进而不得,退之失据。
我从“江湖”说起,为的是引入王手的《阿玛尼》。王手的小说素有“不离生活事实”之名,他写底层,写平民,写地位和身份低微的普通人在尘世间的煎熬和挣扎,但那煎熬里并无怨意和恨意,而是视其为正常的际遇、平常的生活,这使他的小说在平静阔大之余,同时提供着关于“民间”生存样态的如实摹写。《阿玛尼》以第一人称视角、通过一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赌场“抽头薪”者(实为维护赌场秩序的打手)的讲述,对平民的“江湖”做出了作者的理解和阐释。这个“江湖”有别于传统修辞和武林逻辑,在这里:1、贫弱者相助——开赌场的人并非一方霸主或权贵,而是家境困境的寡妇金龙妈,她的两个儿子金龙是傻子,银龙因聚众赌博被捕,刚释放出狱。金龙妈和无业游民“我”合力把赌场撑起来,也无非是生活贫困者在窘境里的相互体恤和救助;2、赌场的生态很“和谐”——虽然打赌人五花八门,不乏争端,但“我”的维护最“狠”的也只是用螺丝刀扎出一串血珠就足以解决。这里看上去不像为了利益而拼命的赌场,更像是人们在无聊得发苦的尘世里打发时光的“游戏场”;3、“民间”强韧的生存伦理:赌场最后被联防队端掉了,“我”靠给人调解矛盾为生,金龙妈靠做散活养傻儿子,银龙又被捕了。他出狱后的社会,“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曾有坐牢“污点”的银龙脑子灵活,人脉广阔,不仅“生意”做得相当成功,还能不时甩出几百万响应地方政府的救灾号召。
说起来,这是平民的“江湖”,它既没有与“庙堂”相对立的粗砺暴烈,也没有自轻自贱的卑微低视。李云雷在评价《老炮儿》时,指出“老炮儿”们并没有建立起“属于他们这一代江湖的独特价值观”。和管虎相比,王手不是在为草根“英雄”悼挽、唱叹和追忆,他只是以一种“平常心”、“自然理”贯穿起一个时代的变迁。从70年代末到今天,世易时移,人世变幻,但王手依然平静而坚定地以平民的伦理、平民的精神贯穿着这巨变,支撑着破碎的人生和时代。他不以傻痴者为耻,也不以强健者为傲;不以贫困者为低,也不以钱权者为高。在他那里,两者并无高下之分,他唯独对“人”在世间的辛苦、奔波、劳作持以敬意,这是“世界”得以存在和运转的基础。在小说的结尾,一世辛劳的金龙妈八十多岁还脑子清醒,身手敏捷,堪称“仁者寿”,这也巧妙而隐在地呼应了小说的题目“阿玛尼”——一个从电影《奇袭》里提取出来的关于“苦难大妈”的原型。
如果我们了解王手的生活经历和创作理念,我们对他笔下的平民“江湖”就不以为异了。普通人的出身和有做生意传统的温州环境使他的血液里自带着对“平民”、“劳作”的亲近与暖意,而他年轻时爱看的《三国演义》和《水浒》潜在地塑造了他的“江湖”伦理,这些地缘、文学、职业等元素使他不仅下意识地赋予了小说里的社会、工厂和人际关系以江湖的意蕴,也向着“简单、实用、有人情味”建构他的江湖游戏规则。他用平民的“江湖”柔化着坚硬的现实,抵御时世的艰难和无常。
关于70年代末80初的“历史叙述”,我们不缺乏宏大的、“革命”的、“文化溯源”式和意识形态的讲述,但从平民的角度、普通人的视角进行的讲述,还是相对匮乏,即使有,也可能易于掺入和堕入历史的“控诉者”或“清算者”的怨懑窠臼。《阿玛尼》的不同之处在于作者对平民“江湖”的平视、平静、平常、平淡,它绵密而结实地呈现出了一个时代万花筒般的镜像。对于王手来说,无怨恨,无要求,这是一种世界观。我以为,这更是“活着”的坚韧和蓬勃。
曹霞,著名文学评论家,现居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