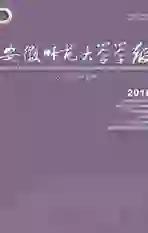老人自死习俗:“鲧复生禹”神话与历史背后的真相
2016-11-19徐永安杜高琴
徐永安 杜高琴
关键词: 老人自死;鲧复生禹;天问;巫术思维
摘要: 依据爱德华·泰勒的“万物有灵观”、弗雷泽的原始巫术思维原理、范热内普的“过渡礼仪”等人类学经典理论,剖析“鲧复生禹”神话,鲧-禹部落(家族)具有雨师职能。去掉神话历史化、历史道德化的迷雾,鲧的被杀背后真相是自死。“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是老人自死之后的“三年之丧”的仪式。仪式中鲧向禹转移的“神灵”形象、仪式的空间特性都体现了源自祖先颛顼的部落传统。“鲧复生禹”神话具有老人自死习俗与成人礼仪双重意象。以禹为核心,颛顼-鲧-禹部落在三代史的开端具有特殊地位与重要性,老人自死是那个时代的敬老、孝道的重大仪式。
中图分类号: G112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6)04049710
Key words: the elders' lone death custom; Gun died and was reborn as Yu; Tian Wen; magical thoughts
Abstract: Based on Edward Taylor' s animalism,Frazer's theory regarding the primitive magical thoughts and Gennep's classic theories on anthropology in his book Les Rites De Passage,analyze the famous mystery—“Gun died and was reborn as Yu.” It turns out the Gun-Yu family plays a role as the rainmaker in the tribe.The real reason behind Gun's death is that he chose the way of lone death.The poem “why not release Gun after imprisoning him for 3 years in Yu Mountain” suggests the custom that after the parents' death,the offspring has to be in mourn for 3 years.Both the “God image” Gun transfers to Yu and the spatial features of the ritual indicate the custom has been passed from the tribe whose ancestor is Zhuan Xu.There are traces of coming-of-age ceremony and the elders' lone death custom in the “Gun died and was reborn as Yu” mystery.With Yu as the core,the Zhuan Xu-Gun-Yu tribe plays a special and important par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hree Dynasties.The elders' lone death custom is regarded as a way that people shows their respect to the elders.
关于老人自死传说的研究,我提出解释理论是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中的“万物有灵观”与詹·乔·弗雷泽《金枝》中的原始巫术思维原理(即老人自死习俗的本质是民俗信仰),并结合范热内普的“过渡礼仪”理论,解析了典籍中“尧舜禹禅让”的真相是老人自死习俗,周期三年,并在商末周初,演化成“大夫七十而致事”的官礼、“三年之丧”的丧礼。①本文在此基础上,继续依据上述经典人类学理论,旨在论证,“鲧复生禹”(《天问》中“伯禹愎鲧”)的神话背后,包含着老人自死习俗的内涵,同时进一步对尧舜禹禅让真相进行解析,并赋予这段历史以新的解读。
“鲧复生禹”出自《山海经·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1]536对该神话最早着迷的古人就是屈原。他在《楚辞·天问》中问道:“鸱龟曳衔,鲧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 伯禹腹鲧,夫何以变化? 纂就前绪,遂成考功,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阻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伴随疑惑与探究,几千年无定论,究其原因,还是人们的思想跳不出神话历史化、历史道德化的藩篱。
弗雷泽指出,在未开化的野蛮社会中,巫师“最首要的是控制气候,特别是保证有适当的降雨量。水是生命之源……因而在原始人社会中,祈雨法师是位极其重要的人物。”[2]95“因为人们既笃信巫师拥有使甘露降临、阳光普照、万物生长的力量,因而也就很自然地会把干旱和死亡归咎于他的罪恶的玩忽职守和存心固执己见,并相应地给他以惩罚。因此,在非洲,国王如果求雨失败便常被流放或被杀死。”[2]132白尼罗河流域的丁卡人,“正由于他享有崇高荣誉,丁卡的雨师们一个都不允许自然地老病死去……所以,一个雨师感到老了,体力不济了,就告诉他的孩子们说他想要死了。在阿加的丁卡人中,做法是挖一个大墓穴,雨师躺在里面,他的朋友和亲戚围在穴边。他断断续续地向人们说话,回忆本部落过去的历史,提醒他们他过去是如何统治、如何教导他们的,并告诉他们将来如何行动。教诲完毕之后,他就吩咐他们把他盖起来。他躺在墓穴里,土就抛到他身上,他立即就闷死了。”而“他的可贵的神灵就立即传给了适当的继承者——他的儿子,或其他近亲。”[2]398我们将从这里入手,通过多角度分析,证明“鲧复生禹”具有类似的历史真相与文化内涵。
一、 关于鲧-禹部落(家族)的性质
第一,他们属于黄帝的世系。《山海经·海内经》:“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1]503《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引《世本》:“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鲧。”[1]528《史记·夏本纪》也选择了“黄帝-昌意-颛顼-鲧-禹”这一世系说法。
第二,颛顼-鲧-禹部落具有“酋长与雨师兼具一身”的特殊身份。《大荒北经》曰:“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间,附禺引郝懿行解云:“《海外北经》作务隅,《海内东经》作鮒鱼,此经文又作附禺,皆一山也,古字通用。”之山,帝颛顼与九嫔葬焉……丘方员三百里,丘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为舟。竹南有赤泽水,名曰封渊。有三桑无枝。丘西有沉渊,颛顼所浴。”[1]478《海外北经》曰:“務隅之山,帝颛顼葬於陽,九嬪葬于隂。”[1]291《大荒西经》中记载:“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及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1]476颛顼所居之地多水,多渊,有山,这最雨师所心仪的风水宝地;“颛顼死即复苏”,说明颛顼有巫术变化能力;巫术变化形象为蛇与鱼,都与水有关。所葬之地亦以神名命之(“附禺之山”即“鮒鱼之山”。“鮒鱼”与“鱼妇”音同而字颠倒,或是传承记忆出错所致,实为一名)。这一段文字,以诗歌节奏读来,可能就是祈雨仪式中的咒语,此段文字稍作调整,即是两段语义清晰的歌词:“风道北来,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 天及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表达了祈求枯鱼—鱼妇—蛇—颛顼四位一体(包含巫师与图腾动物之间的灵魂转移)的“复活”仪式的内涵。
颛顼作为部落联盟首领时期,已经存在禅让不传子的传统,他的部落后代就在其后的部落联盟首领之下专门职掌水旱之事,这就是为什么尧舜时代治水的大任会由颛顼的后代鲧、禹承担的原因。《列子·杨朱》:“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体偏枯。”[3]213《庄子·盗跖》:“尧不慈,舜不孝,禹偏枯”[4]197即传说禹治水时,身体“偏枯”,俗称“半身不遂”,走路也跛了,称为“禹步”。其实背后是禹实施继承于祖先颛顼的巫术通神仪式。
确认以上两点,在后面论证“鲧复生禹”背后的老人自死内涵时,就可以明了这的确就是在传说中的炎黄时代的原始社会普遍存在的习俗。
二、鲧的事迹争论背后的神话历史化、道德化的逻辑剖析
鲧的事迹以《山海经·海内经》中记载的神话为最早。神话中的英雄被杀,是可以杀而不死,或死而变形,死而复生的,鲧作为巫师身份尤其如此。由此“杀鲧于羽郊”之后,又有“鲧复生禹”就是都是很自然的事情了。然而随着后人以理性思维取代神话思维,而将神话历史化、现实化,在这二者之间就必然存在逻辑上的矛盾了。于是人们按照各自理解的需要,出现了重新“解构”神话材料的两种逻辑。第一种是,认同神话中鲧被杀是历史事实,那么其后的“鲧复生禹”就是无稽之谈。《尚书》中记载:“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佥曰:‘於,鲧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勿成。”[5]26-28“(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5]56-57“鲧陻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5]293-294《史记》进一步综合表述:“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尧曰:‘鲧为人负命毁族,不可。四岳曰:‘等之未有贤于鲧者,愿帝试之。于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于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6]11二者都采取了绕过“鲧复生禹”内容的思路,建构了一段影响深远的“信史”!这种处理也无意中包含了神话中的合理成分,即禹继承鲧的治水事业时已经是成人。
然而,神话中鲧是正面的英雄形象,鲧的被杀,是“不待帝命”。与其舍命为天下相比,“帝”因此杀他,显然过分。鲧的事迹中的确包含有功于民的一面,从民的立场看,鲧的死充满悲剧性的崇高感,而“帝”的形象反处于其下,甚至对立。《天问纂义》毛奇龄注曰:“大抵鲧治水随地筑堤,今河北清河、广宗、临河、黎阳等界,所在皆有鲧堤可见。”[7]11说明鲧虽未能根治水患,但毕竟减缓了洪水的危害,百姓是将鲧和禹一样纪念的。《国语·鲁语》曰:“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扞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8]166鲧能够与黄帝、颛顼、帝喾等相提并论,作为郊祀王城外百里之内为郊。祭天地在郊,皆得称郊。《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鲧至少是以雨师的身份配祀天地。对象延续下来,说明他不仅有功,也不可能存在与尧舜争天下的大罪。
这样的对比显然与尧舜二帝一贯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历史观相冲突。于是,在《尧典》中,鲧与“帝”的位置完成了转换,且从尧帝的口中否定他“方命圮族”。虽然不知四字具体所指,但已经定性,只是罪不足诛。鲧治水,“九载,绩用弗成。”按说罪加一等,尧既然没有因其治水无功而杀之,舜又何必“殛鲧于羽山”?
从维护部落联盟首领或帝王道德正统出发,《尧典》与《史记》都将鲧的事迹予以反道德化改造,是别无选择的选择。此后的典籍中,鲧的罪更是被提升到与帝王争夺天下的高度,“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为帝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比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召之不来,仿佯于野,以患帝。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副之以吴刀。禹不敢怨,而反事之。”[9]267“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10]243
如此,帝王杀鲧不仅顺理成章,也造就了自己政治与道德上的正统形象,“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就被包装成了合乎后人道德观的正版历史。但是,这种处理方式,不仅对“鲧复生禹”避而不谈的本身就是留下了一个对神话结构解释上的缺陷和疑问,同时带来了另一个难以解释的人性问题,如后文的“若以为杀人父用其子,而舜、禹何以忍乎?”还有,作为父子,为何鲧的道德这么低下,而禹的道德那么高尚?从文献来看,人们也只能用禹就是天生的道德高尚的原因来解释了。
第二种重新“解构”神话的逻辑是,倾向于“杀鲧于羽郊”与“鲧复生禹”都是存在的,这就必然导致对鲧先被“杀”的真实性的疑问上,集中在对“殛”字的理解上。将鲧反道德化者持“诛杀说”的居多,但也有持“流放说”的。《尚书今古文注疏》引疏云:“云‘殛,诛者,《释言》文……‘诛,责遣之,非杀也。《汉书·鲍宣传》云:‘昔尧放四罪而天下服。是殛即放也。《祭法》疏引《郑志》答赵商云:‘鲧非诛死,鲧放居东裔,至死不得反于朝。禹乃其子也,以有圣功,故尧兴之。若以为杀人父用其子,而舜、禹何以忍乎?……案:舜之殛鲧,方将使之变和东夷,必非置之死地。箕子云‘殛死,亦谓殛之远方而至死不反,故《楚辞·天问》云:‘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言久遏绝之,不施舍也。”[5]57屈原《天问》中的记载为流放说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就“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 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四句, 陈远新曰:“乃帝遏之不杀而用其子,且知其子不以父故避嫌,而不蹈父故辙,亦可深思鲧之为鲧矣。为鲧出脱,即是为尧舜出脱;不然,弃父用子,终是千古疑团。”[7]97可见,解“殛”为流放,很大程度上也绕开了前面提到的人性的障碍。“流放说”的另一个证据,是《天问》中解释“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两句的文献支持。
(唐)杜佑解《舜典》“鲧殛于羽山”曰:“按司马迁曰:‘舜流四凶于四裔,以御魑魅。此一明四凶不死也。又,《舜典》云‘流宥五刑者,五刑中有死,既以流放代死,此二明四凶不死也。又《舜典》言,舜美皋陶作士曰:‘五流有宅。孔安国注云:‘五流有宅者,谓不忍加刑,则流放之,若四凶。此三明四凶不死也……所以辨鲧至羽山而自死者也。”[11]2219首次明确提出了“自死说”,看似即将破题。
第二种逻辑毕竟仍然是以神话历史化为目的,而不是对神话思维的恢复,更没有可依据的解释神话思维的理论(那是19世纪以后的产物)。因而即使杜佑提出的“自死说”,其认知的本质与老人自死习俗真相之间仍然隔着一堵厚厚的墙壁,并且他们必然陷入一个新的逻辑矛盾之中,那就是如何解释“鲧复生禹”的内涵!
三、 后人对“鲧复生禹”的世俗化解释
由于对老人自死习俗的遗忘,不理解这里的“复”乃是“重”的意思,“复生”乃是神灵“重生”,包含继承者是直系血缘亲子关系的特定内涵,这与“颛顼死即复苏”是一脉相承的。当然,“复生”的意义是双重的,它既是鲧的神灵重生,也是禹的重生(接受了鲧的神灵,其生命结构改变了,具有神性)屈原最先发出这样的疑问:“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 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引出了历史上延续两千多年的“猜谜”活动。
《天问》有“启棘宾商、九辩九歌,何勤子屠母,死而分竟地?”王逸解为禹母生禹之事。[7]201-212《吴越春秋》曰:“鲧娶于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壮未孳,嬉于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为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肋而产高密(禹)。家于西羌,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12]239《帝王世纪》亦谓:“颛顼生鲧, 尧封为崇伯,纳有莘氏女,曰志,是为修已。山行,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于石纽。”[13]21这样的感生神话,由于《天问》的记载,说明在屈原之前已经存在。女嬉生禹与伯鲧愎禹在《天问》里同时存在,正好说明,后者应该是“复生”,换言之,此时的禹不是婴儿,而是成年人。
屈原疑问的原意是:鲧是男人,如果禹是在鲧的腹中孕育,那是怎样在他的身体里变化的呢?这已经是“看呆神话”,即用生活经验向神话发问(这是《天问》的一个基本逻辑出发点)。后人还是围绕男人生育的矛盾绕圈子,一些解释反而跑的更远。
解“愎”为狠者,如王逸:“言鲧愚狠,愎而生禹,禹小见其所为,何以能变化而有圣德?”王夫之曰:“鲧之愎,禹之圣。”解“愎”为怀抱者,如洪兴祖曰:“愎一作腹……《诗》云,出入腹我。腹,怀抱也。”林云铭曰:“禹固出于鲧之怀抱也,乃变障隄而为疏导。”指出语法结构问题者,如夏大霖曰:“禹腹鲧是倒装句法,谓禹乃鲧所怀抱。”而他们对“夫何以变化”大多作禹为何德行比鲧高的解释。[7]9697本来《山海经》神话中就是“复”生,为何还争相在《天问》这里解作“腹”生呢?就是因为都不明白“鲧复生禹”是鲧-禹之间神灵转移,是鲧在禹身上的“重生”。
闻一多解释曰:“腹原作愎,鲧禹二字互倒……《广雅·释诂》一曰:‘腹,生也。……《海内经》曰:‘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复生无义,复当读为腹,亦谓鲧化生禹耳。”[14]23他虽然也解作“腹”,但是解释“鲧化生禹”更合理了,也接近了神话内涵(闻一多时代,西方神话学理论著作原著、译作他是能够看到的)。但是闻一多认为鲧既被杀,“复生”就没有意义,却又是在拿生活的逻辑看神话。“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两句相连,正是包含了鲧的死亡所体现的悲剧性内涵,即有辱使命,杀而不死,非生禹不能寄托未竟事业。其神话情节就是“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1]537然后才有“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因此,“复生”不是没有意义,而是有重要意义。从被“杀”到“复生”,完全符合神话的文学特征,夸张,浪漫,诡谲,凸显了鲧在这个神话结构中所处的悲剧性地位与内在精神的冲突。前人解释的“伯禹愎鲧”都应该回到“鲧复生禹”神话语源上,“愎”“腹”都应该回到“复”字上。这与从母亲腹中出生是完全不同的。
依据《天问》文献存在的时间顺序,后人对“鲧复生禹”的理解原本应该不会和禹母生禹混淆。而袁珂认为:“神话中‘鲧腹生禹的情节,带着父权制氏族社会男人乔装生子风习的痕迹。”[15]29他解释以“产翁制”,是和禹母生禹混为一谈了。神话学专家尚有如此解释,对古人的模糊理解也就不必苛求了——古人对“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的解释(以王逸注为代表)包含了以下的理解和暗示,即鲧生出一个小孩的禹(不妨就将他们的理解视为“产翁制”的转述),再长大成人;或者虽然鲧生不出禹,但鲧被杀之时,禹还是一个小孩的禹(这样,“鲧复生禹”被赋予生离死别以及父命子承的悲壮也无不可),经过十几年,而为成人的禹。中间可能经过高尚的母亲或托孤者的教育,品德智慧远超其父,并被舜授命治水。这样神话中后三句“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不就完全符合时间逻辑而成为一体,前面提到的人性障碍不也迎刃而解了吗?
假如我们如此理解,作为部落首领,鲧应在30岁之前就要成婚,为何却很晚得子?如果这点说不清,那么在禹的成长过程中,至少在其童年和少年时期,一定要有一个过渡性的部落首领来领导全族,但是神话和史书都没有任何的相关材料。而禹至少要长到20岁(也就是舜至少要等20年),才能受命继承鲧治水的事业,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我们来看《尚书》,假定尧帝启用鲧治水与求贤于舜同时,舜经历3年考验(实际为“殡”之“三年之丧”),至鲧治水9年时,舜即位6年。又假定舜次年“殛鲧于羽山”,其时禹由母而生,至《大禹谟》中舜与禹言:“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载”时,禹治水13年已经成功。即便对话就在成功之时,则舜用禹治水在继位20年时,推知禹应为13岁。如“殛鲧于羽山”与舜禹对话时间都更晚,推算出禹的岁数更小,治水是不可能的。因此“鲧复生禹”时禹应该是成人。
由此,“鲧复生禹”包含两种仪式,一方面,“鲧复生禹”是发生在父子之间的老人向年轻人的神灵转移仪式,是鲧的重生,“复生”。另一方面,则是禹完成成人礼时的重生——成人礼仪中包含死亡与再生仪式,他们家族有“颛顼死即复苏”的传统。在这个意义上,说“鲧腹生禹”是合理的。马林诺夫斯基论述原始民族成人礼仪,“所历试验,常使被试者装作当场死亡旋又复活的样子。”同时,还要“将神圣的神话与传统有系统地教与青年,渐渐使他知道族中奥秘,使他见到神圣的事物。”有一种形式是:“主宰将青年吞下,使他死亡,然后使他复活,以成戒行圆满的成人。”[16]22这其实是一个“感生神话”在成人礼仪中的表现形式。与之相似,“鲧腹生禹”很可能先有一个“鲧吞禹”的前奏,与禹第一次孕育时,女嬉“得薏苡而吞之……因而妊孕”相对应;而“剖之以吴刀”“大副之吴刀,是用出禹”,又与禹第一次出生时“剖肋而产高密(禹)”相一致。亦即禹的成人礼中的再生部分重复了他过去第一次孕育出生时的感生神话形式,只不过是载体变成父亲鲧。通过仪式,禹才能够有资格接受鲧的神灵,承担部落首领与雨师的职能。可以说,舜在等待合适的时间,即禹的长大成人,先举行禹的成人礼,接着举行鲧的老人自死仪式。(禹的合理年岁,鲧复生禹时应在进入20岁后的青年期,《仪礼·士冠礼》中“年二十而冠”或源于此。)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鲧在尧帝用舜之前即治水已久,其岁数当在尧之下,但至少比舜大不少。尧帝所言“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此前必有洪水由起到盛的过程,其间鲧带领所部以筑堤堵水的方法,终不能有效根治,有辱使命,此乃“方命圮族”的内涵。尧帝第二次启用鲧治水,鲧不变其法,九年无成效。至舜帝时代,仍未成功。鲧背着“方命圮族”的压力,殚精竭虑,心力交瘁,身体衰老明显超出实际年龄,治水已经有心无力。为天下大计,舜或命令鲧提前实施老人自死仪式,尽快将神灵转移到继承者禹的身上,以免神灵的衰老将部落带入颓败的危机之中,而不能完成治水大业。
如此解释“鲧复生禹”,即可理解“帝令祝融(笔者按:或舜)杀鲧于羽郊”与“鲧复生禹”并列出现,也能解释屈原“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的疑问。
四、“三年不施”中的“神灵”转移仪式、形象及空间特征
(一)对“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的仪式性解释
王逸注曰:“言尧长放鲧于羽山,绝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也。”后人多解为尧、舜囚而不杀、不赦。如周拱辰曰:“曰三年何也?《公羊注》:古人疑狱,三年而始定,三年不施,永不施矣,惟有永遏之已耳。”[7]92-95人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尧舜与鲧的关系上了。他们不解“鲧复生禹”的真相(包括错误理解鲧生出一个小孩的禹,再长大为成人的禹)。自然也就不能理解“三年不施”的背后,是指鲧的一点神灵完全转移到禹的身上需要经过三年的“过渡礼仪”,即经历“分隔——边缘——聚合”三个阶段,在以成人兼巫师的新身份完成聚合到成人群体的仪式之前,禹还不能开始进行治水大业。以天下当时的水患之严重、舜帝与百姓对禹的期待,三年的等待太漫长了!因而“三年”在此是一个被强调的数字,而“三年不施”的疑问则表明在神话的流传过程中其内容与对象都被误读了。
在很大程度上,“三年不施”与“三年不腐”(从神话角度也可理解为“三年不死”)存在着对立关系。前者包含了天下治水需要的紧迫性,而后者包含着鲧-禹之间的神灵转移仪式特殊的重要性。第一,它不是一般70岁,而是提前了许多岁数(但至少在禹成年礼之后)举行的。对鲧而言,是迫不得已的;第二,比之尧禅让于舜,鲧是以失败者的身份,带着巨大的遗憾、羞耻,背负命运的不公和对命运的抗争而进行禅位的。为了完成未竟事业、重振部落荣誉,必须保证自己的生命在禹身上“复生”!不可因为治水的急迫而有任何懈怠。他内心世界的一切禹必定清楚。大禹治水,正是因为肩负双重的使命,他的奉献才超常彻底,他的事迹才如此感人,《庄子·天下篇》引墨子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如此。”治水才能“纂就前绪,遂成考功。”
(二)“神灵”转移仪式中的图腾形象分析
形象之一,龙。闻一多引古籍“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与“大副之吴刀,是用出禹”两句曰:“或曰化龙,或曰出禹,是禹乃龙也。剖父而子出为龙,则父本亦龙,从可知矣。”[14]23(以刀“剖父而子出”显然是嫁接了女嬉“剖肋而产高密”、 修已“胸坼而生禹”的情节,并与后来的启自母腹“破石而出”相类。)依此,转移的神灵形象首先是龙。它赋予鲧-禹家族掌控水旱的智慧与灵验。大禹治水有龙相助。传说夏后氏之王多乘龙。《海外西经》曰:“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儛《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1]253《大荒西经》曰:“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珂案:开即启也,汉人避景帝刘启讳)[1]473活脱脱一副大巫师的形象。张光直说:“夏后开无疑是将天上的乐章与诗歌带到人间的英雄,此时他便是一个巫师,得到两蛇和两龙的帮助。龙与蛇可能与他们为上帝沟通人间的使命有关。”[17]46-47龙蛇能助巫师升天。龙成为中华民族之象征,鲧-禹部落的龙图腾影响深远。
形象之二,熊。《史记》对“黄帝”的注释:“[集解]徐广曰:‘(黄帝)号有熊。[索引]案:注‘号有熊者,以其本是有熊国君之子故也。”正文有黄帝“教熊罴貔貅赤貙虎,以与炎帝战于版泉之野。”[6]6从排序看,熊图腾的部落是最具战斗力的,而他们很可能就是颛顼-鲧-禹部落的源头。《山海经》中多处记载了多位帝王(包括颛顼)陵冢前的神兽,熊列于其首,显然与其力量和勇猛的特性有关。
《左传·昭公七年》记晋平公梦熊问韩宣子,对曰:“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18]429(《国语·晋语》略同)《汉书》颜师古注曰:“禹治鸿水,通轩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事见《淮南子》。”[19]385联系二者,可见转移的神灵也有熊。它赋予了禹领导治水、筑城等工程所需要的力量和勇气,也是重大工程开工仪式上所请之神。
形象之三,鳖。《史记》曰:“舜……乃殛鲧于羽山以死。[正义]:鲧之羽山,化为黄熊,入于羽渊。熊音乃来反,下三点为三足也。束皙《发蒙记》云:‘鳖三足曰熊。”(笔者注:原文能之下为三点)[6]11《经典释文》解释《左传》化熊之说释“黄能”云:“如字,一音奴来反;亦作熊,音雄,兽名。能,三足鳖也。解者云:兽非入水之物,故是鳖也。一曰:既为神,何妨是兽。案《说文》及《字林》皆云:能,熊属,足似鹿。然则能既熊属,又为鳖类,今本作能者,胜也。东海人祭禹庙,不用熊白及鳖为膳,斯岂鲧化为二物乎?”[20]1089 美国新墨西哥的祖尼印第安人认为“人死之后灵魂转生为乌龟……死者的魂魄就是以乌龟的形体聚居在另一个世界里。”(见弗雷泽著,徐育新等译,《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81页),二者或有某种内在联系。鳖或“黄能”,常居于水底,稳健有力,代表雨师部落在水下疏浚、治理河道的工程能力。而熊也可以入水,文献中关于鳖、“能”、熊的混杂性解释,恰好反证了那不过是雨师部落在水下和陆上治水、开路、筑城等多种能力相互统一的图腾化表现。
形象之四,玄鱼。《拾遗记》卷二谓:“尧命夏鲧治水,九载无绩。鲧自沉于羽渊,化为玄鱼。时扬须振鳞,横修波之上,见者谓之‘河精。”[21]33“鲧”字为鱼类,与“颛顼死而复苏”的形象“鱼妇”(实际上是“鮒鱼”)有传承关系。蛇、龙、鱼、鳖,形象虽有变化,但皆不出水族之物(古人或鱼蛇混同,《海外南经》曰:“南山在其东南。自此山来,虫为蛇,蛇号为鱼。”),可见模拟或相似巫术思维的痕迹,自颛顼而传之。
仪式中转移的图腾“神灵”包括上述四种(熊兼有鳖、“能”的属性)。其中,“熊和龙的母型蛇、蜥、鳄,都要冬眠——惊蛰,这在初民看来,也是一种死与不死、生与再生的辩证运动。鲧禹的化熊、化龙,就昭示着他们的生命只能转化不能毁亡,他们的业绩只会断续而不会中止。”[22]5-6鱼和鳖、“能”(龟类)则代表着雨师所拥有的最元初的生命创造力和生不息的生命延续力。在“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的祈雨仪式里,鱼甚至是最重要的神灵。
(三)“神灵”转移仪式中的空间特征分析
《山海经·南山经》曰:“又东三百五十里曰羽山。其下多水,其上多雨,无草木,多蝮虫。”(羽山之下注:“今东海祝其县西南有羽山,即鲧所殛处。”)这里倒是很合乎雨师的环境特征。《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对“羽山”的注疏:“《史记》[集解]马融云:‘羽山,东裔也。[正义]《括地志》云:‘羽山在沂州临沂县界。‘云‘羽山,东裔者,《地理志》:‘东海祝其,《禹贡》羽山在南,鲧所殛。山在今山东郯城县东北七十里,江南赣榆县界。”[5]57《天问纂义》中,“蒋骥:‘羽山在今淮安府赣榆县。又登州蓬莱县亦有羽山。游国恩按:‘羽山见《离骚》,当以在今蓬莱县者为鲧殛处,他所传同名者非也。”[7]95
闻一多将神灵形象与空间地点统一起来:“《中山经》曰:‘從山多三足鳖。從山即崇山。乐府古辞《董逃行》‘吾欲上谒從高山,谓從高山,可证。《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注曰:‘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案当即传说中鲧所封崇国之山(《周语》下又云‘有崇伯鲧)崇山为鲧所居地,而云多三足鳖,是亦主鲧化为能鳖之说者也。”[14]21
丁山在《古代神话与民族》中进一步论证:“《山海经·中山经》云:‘青要之山,实惟帝之密都。是多驾鸟。南望墠渚,禹父之所化。毕沅《校正》云:‘渚,在今河南嵩县。”丁山考证:“今嵩县……因崇山为名。崇山,《诗》言嵩岳,卜辞曰岳,为殷、周祷雨胜地……则鲧化羽渊,宜在崇山附近之禅渚;所谓羽山者,羽之为言雨也,雩也,即谓祷雨之山矣。”鲧称崇伯,羽山即为崇山。[23]231
闻一多、丁山所言似更为合理。《大荒北经》所载颛顼所浴沉渊,所葬附禺(鮒鱼)之山,《海内东经》言“汉水出鮒鱼之山,帝颛顼葬於陽,九嬪葬于隂,四蛇衞之。”[1]385“鮒鱼之山”是颛顼-鲧-禹部落在汉水的发源之地。比照羽山与附禺(鮒鱼)之山、羽渊与沉渊,显示出具有传承性的对应关系。换句话说,鲧进行的老人自死仪式,是在类似于祖先颛顼所居住的有山,有水,有渊的自然环境中,这种巧合显然包含了精心安排的目的性。亦证明舜“殛鲧”,实质是舜命令鲧提前完成“鲧复生禹”的仪式,而不是直接被诛杀。
《天问》曰:“阻穷西征,岩何越焉?”王逸注曰:“言尧放鲧羽山,西行度越岭岩之险,因堕死也。”[7]227其包含的仪式是:鲧身处于羽山(崇山),或天然洞穴中,完成神灵与肉体分离(自死)后,神灵以图腾形象回归祖先故地,以获得祖先的认同与庇佑,并通过接触巫术得到祖先赋予的强大力量(这是一个精神的而非身体的历程);然后再返回羽渊,完成神灵向禹的转移,开始“颛顼死既复苏”的仪式。对照《大荒北经》颛顼葬附禺之山,浴沉渊的描写,鲧完成神灵与肉体分离后,进入丧礼阶段,葬于羽山。禹则进入三年守丧即神灵转移的过渡礼仪阶段。羽山、羽渊二者距离相近,其间,禹或有在羽渊沐浴,通过水的媒介,与神灵——龙、熊相互融合的仪式。这大概就是“焉有虬龙,负熊以游”的真实涵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则从反面说明在神灵转化的三年仪式中,一切都有专门的巫师主持,即《论语·宪问》中孔子所言“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
水,是雨师进行通神或实施神灵转移仪式的必需要素,故《山海经》《天问》中的颛顼-鲧-禹神话都与水密不可分,由此也揭示了现存的自死窑遗址大量分布于河流两岸或朝向沟谷这一空间特征的秘密所在。
《后汉书·张衡传》注引杨雄《蜀王本纪》故事曰:“荆人鳖令死,其尸流亡,随江水上。至成都,见蜀王杜宇,杜宇立以为相。”[24]972闻一多《天问疏证》所引本故事曰:“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令)决玉山,民得安处。”且以为“此亦主鲧化为能鳖之说者”。[14]22有当今学者以为乃是有附会“阻穷西征”与大禹治水之功的色彩。[25]47-53若是如此,则证明鲧完成神灵与肉体分离后,肉体死亡(尸),而神灵开始回归故地(是汉水而非长江)楚民族与颛顼有族源关系,《天问》说明楚人保存了对鲧做为治水英雄的神话情感。随着楚民族从汉水流域进入到江汉平原,鲧治水神话演变出新的鳖灵文本,背景被置换为长江流域。鳖灵的故事结尾:“(望帝)乃委国授之(鳖灵)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鲧终于在另一个空间获得了英雄应有的尊严与王者的地位,这也体现了道统与民间对鲧的评价的不同。之说可成立。这里言“尸随江水上”,是为满足后面鳖灵“遂活”的需要,作“借尸还魂”的载体。
至于后人从维护尧舜道德正统的需要出发,把杀鲧的羽山描绘成十分荒凉、恐怖的面貌,是最自然不过的了。如闻一多所引证:“《地形篇》又曰:‘北方曰积冰,曰委羽,注曰:‘北方寒冰所积,因以为名。委羽,山名。在北极之阴,不见日也。委羽山一曰羽山,即帝所刑鲧处。而《墨子·尚贤中篇》曰:‘昔者伯鲧,帝之元子,废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乃热照无有及也。”[14]36
五、结论
尧舜禹禅让和鲧复生禹两个神话中都包含老人自死习俗。禹在其中具有特殊地位与重要性。在禅让的神话背后,禹与前任有不同之处,是经历了两次老人自死仪式,一是“鲧复生禹”,一是“舜-禹禅让”。在他的身上,既延续了本部落禅位于子的传统,又承载了部落联盟禅让于外的传统;他的体内,既有祖上颛顼-鲧的神灵,也有帝王尧-舜的神灵;他治水,既是要解天下之灾,也要重振家族荣耀。他要与天斗,与地斗,与命运斗,与自己斗,“生于忧患”的大禹真是压力山大!所以他治水的神话事事动人,又处处沉重,特别是他变熊开山,妻子见而化石,儿子启破石而出的神话,折射出禹的内心深藏的孤独、无助、悲凉,以及些许的迷惘,甚至他的下一代的出生也打上了家族悲剧的烙印,与他那化身为熊的孔武有力的形象形成强烈的对比与反差。然而他以超出常人的意志坚持着,以熊的力量继续着,终以成功而告慰祖先与天下。
相比《尚书》中尧、舜作为帝王的道德化形象,典籍中禹的形象更加有血有肉,更加丰满生动,由于受到道德史观的强大影响,后人更看重尧舜禹禅让神话,而忽略甚至贬低了鲧复生禹神话所隐含的历史信息,以及鲧-禹部落对中国历史的重大影响。因为他们的部落不仅是宗教知识(雨师·巫师)的掌握者,也是当时科学知识的掌握者(如以《禹贡》、夏小正为代表的系统的地理知识,天文历法知识);具有能征善战的军事能力,还掌握着最先进的工程技术和工程建设能力——除了水利工程,他们还是城市的建造者。《吕氏春秋·君守》曰:“夏鲧作城。”《淮南子·原道训》曰:“昔者伯鲧作三仞之城。”《吴越春秋》:“鲧作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汉书》臣瓒引《世本》曰:“禹都阳城。”还有可以与尧舜比肩的各种美德:忠诚,奉献,天下为公,勤劳(《大禹谟》中舜赞其“克勤于邦,克俭于家”), 自我牺牲(三过家门而不入),隐忍,谦逊(《大禹谟》中舜、禹的对话)等;他们也吸收融合了其他部落与部落联盟中的优秀文化与先进技术,逐渐成为当时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代表。舜禅让天下于禹,这是鲧、禹都不曾奢想的事情,却是天命和历史给予他的最公正的回报,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鲧-禹部落成为天下正统,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也开创了中华文明的崭新时代!而这一历史开端追溯到“鲧复生禹”的神话,就必然和老人自死习俗联系到一起。
1960年,英国学者李约瑟在《现代中国的古代传统》一文说:“关于中国官僚封建主义的起源,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论点,认为那和中国古代水利工程超越一切的重要性是有关系的。我认为这种说法很有道理。”[26]35今天,他引述并赞同的这一观点也在解剖老人自死习俗与尧舜禹禅让、鲧复生禹神话关系的论述中找到了源头。
分析尧舜禹禅让与鲧复生禹同时,关于老人自死习俗与孝道的关系也水到渠成。两个神话不仅包含了老人自死习俗的内核,而且老人自死在彼时彼地都是事关部落兴盛的神圣的神灵再生仪式,根本不存在野蛮、不孝的问题。孝道的观念不是凭空存在的,不是抽象的概念,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存在于每个时代的现实生活中,其内涵与形式是会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而有所改变的。从彼时彼地的观念(巫术思维·民俗信仰)本质看,老人自死反倒可以说是彼时彼地的对老人的最大的孝,最隆重的孝,是孝道的重大仪式。老人自死习俗与后来的某些礼制(“七十致事”“三年之丧”)的形成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从原始社会的巫术思维,经过夏商时期的过渡,进入周代的礼制,这一漫长的演进必然伴随着观念的转变,也必然伴随记忆的丧失,解释的讹误,并长期影响后人的认识。所以,我们运用辩证唯物史观去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并结合人类学、民俗学(包括神话学)的理论深入解剖,才能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而仅仅站在后来以家族血亲关系为核心的孝道观念的角度,包括从某些口传文本的叙述导向上,看待老人自死形式上与后来孝道的冲突,判定前者是野蛮、不孝,甚至将老人自死习俗的消失看作是从弃老到敬老,社会从野蛮进入文明的标志,所持的是静止的、割裂的、片面的历史观;是历史道德化的思维惯性的表现,所得出的结论当然也是值得商榷的。
日本学者伊藤清司说:“我们可以推定,舜经受考验的传说,在流传过程中有了很多变异,所以给内容带来了一些混乱。其中最大的混乱也许来自古代执笔的的那些文人学者。他们也许把舜经受考验的传说看做‘不雅驯,于是根据儒教的思想意识,对其内容巧妙地作了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然后,根据封建孝悌道德观念,加以粉饰,致使传说的原来面貌有了明显变化。就这样,故事中出现了理想的圣天子像(这是捏造的),还出现了名为禅让,实则架空的所谓理想的王位继承的范例(这是创作)……可能不管他们怎样乔装怎样粉饰,传说的真面目却不可能全部被掩盖。我们很幸运,在人民的创作中还有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民间故事,这些民间故事就是我们据以摸清传说之本来轮廓的线索。”[27]433-434他的观点对我的思考是有力的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否定融合了儒家思想的老人自死传说对传播孝道观念具有的积极意义。
总之,以禹的事迹为核心,老人自死习俗为纽带,与正统信史、上古神话、民间传说、汉水流域区域历史与文化遗存等,建立起了跨越时空的文化联系。认同尧舜禹禅让与鲧复生禹神话的背后隐藏着老人自死、成人礼仪习俗,以及伊藤清司解析的婚姻难题考验的风俗,那么我们确信并传承至今的这一段历史中,有关人物、事件内容、结构关系与语言表述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要重新改写。
参考文献:
[1]袁珂.山海经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3.
[2]詹·乔·弗雷泽.金枝:上[M].徐育新,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3]王强模.列子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4]王先谦.庄子集解[M].上海:上海书店,1991.
[5]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4.
[6]司马迁.史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94.
[7]游国恩.天问纂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2.
[8]左丘明.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9]吕不韦.吕氏春秋[M].高诱,注.上海:上海书店,1991.
[10]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上海:上海书店,1991.
[11]杜佑.通典[M].颜品忠,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1995.
[12]赵晔.吴越春秋[M].张觉译,注.长沙: 岳麓书社,1994 .
[13]皇甫谧.帝王世纪[M].济南: 齐鲁书社,1998 .
[14]闻一多.天问疏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5]袁珂.中国神话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16]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M].李安宅,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17]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
[18]宋元人.春秋三传 [M].北京:中国书店,1990.
[19]班固.汉书:武帝纪[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94.
[20]陆德明.经典释文:中册卷十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1]王嘉.拾遗记[M].萧绮,录.齐治平,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
[22]萧兵.《天问》难题一则[J].云梦学刊,2004(6): 56.
[23]丁山.古代神话与民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4]范晔.后汉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94.
[25]李修松.“鳖灵”传说真相考[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4754.
[26]李约瑟.四海之内:东方和西方的对话[M].劳陇,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27]伊藤清司.难题求婚型故事、成人仪式与尧舜禅让传说[C]∥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汪效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