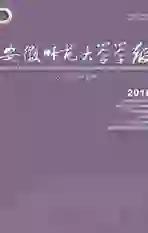依违于儒与佛、道之间的心路嬗变轨迹
2016-11-19郭应传
郭应传
关键词: 王阳明;九华山;圣贤志向;释老之学
摘要: 王阳明于弘治、正德年间曾两次游历九华山。游历期间的具体境遇虽然有所区别,但基于儒者情怀的圣贤志向追求与学术传承的使命担当意识却是一以贯之的。王阳明兼摄佛、道思想所折射出来的归隐倾向以及对超迈洒落的精神生活的向往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种交织不仅铸就了王阳明亦显亦隐的丰实人格,也展现出王阳明依违于儒与佛、道之间的心路嬗变轨迹。
中图分类号: B82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6)04046708
Key words: Wang Yangming;Mount Jiuhua;the ambition for sages and men of virtue;the doctrine of Buddhism and Taoism
Abstract: Wang Yangming had two trips to Mount Jiuhua in Hongzhi and Zhengde years of the Ming Dynasty.Although the specific situations during two tours were somewhat different,of ambition for sages and the pursuit of academic heritage mission consciousness based on Confucian feelings were consistent.Wang Yangming's seclusive tendency reflected in the Buddhism and Taoism was interwoven with his yearning for spiritual life of transcendence and freedom.The intertwinement not only shaped both explicit and implicit abundant personality of Wang Yangming,but showed the spiritual evolution of Wang Yangming vacillating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Taoism.
王阳明一生对于佛、道①之学的态度呈现出阶段性的复杂变化。大体上来说,于中岁“龙场悟道”之前,经由听闻、涉猎再到一度沉溺于其中。其在悟得圣人之道而归正于儒学以后,则以反省与批判为主,其后又逐渐转向在对释、老之学的重新诠释中选择性的吸收,在对释、老之学的儒学化改造中寻求同圣贤学问的会通与融合。对待释、老学说态度的这一变化过程既与王阳明跌宕起伏的人生磨砺难以分开,更是与其圣贤志向孜孜不倦的追求以及儒者使命意识的不断自觉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弘治、正德年间两次游历九华山,折射出王阳明于匡时济世的关切,又难以割舍归隐情结,并表现出对于超世洒脱生活的矛盾心态。
一、第一次九华之游:为学之方的困惑与志向难酬的怅然
王阳明思想的转变历程,大致可以将正德三年(1508)在贵州龙场证悟圣人之道而渐入圣学门径作为分水岭。对于龙场悟道以前的学思经历,王阳明于正德十年(1515)在《朱子晚年定论》自序中曾作过这样的概述:“守仁早岁业举,溺志辞章,既乃稍知从事正学,而苦于众说之纷扰疲病,茫无可入,因求诸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1]卷3,139虽然自幼就确立起读书学圣贤的志向,亦曾深契前辈学者娄谅视“圣人必可学而至”[1]卷32,1228的鼓励,但在较长时期内,却一直难入圣学之堂奥。这期间他曾广泛地涉猎道教养生之说、程颢和朱熹等宋儒的学说、诸子经史以及韬略兵法等,然而却深切地体会到辞章艺能之学难以通达圣贤之道,从而陷入困惑之中。为了摆脱这一困惑,一度寄希望于朱熹曾经提出的为学之道,即将居敬持志的内向工夫视为读书的根本,而将循序格物、精思穷理作为读书的方法,结果仍然是“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2]卷10,201,无法将物事之理与心性之体融贯统摄起来,这使得他更加坚信圣贤自有定分。内心的苦恼引发他再次转向释、老的方外之学,甚至“偶闻道士谈养生,遂有遗世入山之意”[1]卷32,1229。第一次游历九华山就是在难寻圣学之门而不得已暂时“求诸老、释”的困惑心境下发生的。
《年谱》记载,弘治十四年(1501),王阳明奉命审录江北并在多数囚狱案件得以平反以后,“遂游九华,作《游九华赋》,宿无相、化城诸寺”[1]卷32,1230。此次九华之游对于王阳明第一次游历九华山的具体时间,大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张立文、陈来认为应在弘治十五年,钱明、尹文汉则认为应在弘治十四冬至弘治十五年春。参见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60页;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4-315页;钱明《阳明学的形成和发展》,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68页;尹文汉《王阳明游九华山综考》,《池州师专学报》2006年第2期,第46-47页。根据王阳明《游齐山赋》自序、《九华山赋》自序以及王阳明最为重要的弟子之一邹守益所作《九华山阳明书院记》等相关资料,推定王阳明于弘治十五年游历九华山,似乎较为妥恰。参见《王阳明全集》卷四十三《游齐山赋并序》、《九华山赋小序》,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册,第1759、1760页;《邹守益集》卷六《九华山阳明书院记》,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321页。,从《九华赋》等词赋对于九华景观描述细致的程度来看,真可谓“穷秘密于崔嵬,极玄搜而历考”[3]卷9,九华赋。在涉险寻幽、探奇揽胜的同时,王阳明也追思凭吊了前贤名士、道士仙人在九华山留下的古迹遗踪,“吊谪仙之遗迹”,“访王生于邃谷”,“悯子京之故宅”,“有感于子明之宿要”,“款知微之碧桃”。[1]卷19,696-698这里涉及到九华山诸多遗迹,包括唐代诗仙李白的太白祠、唐代隐士王季文临终前舍为无相寺的书堂、北宋滕子京谪居九华的的旧宅、西汉陵阳县令窦子明修炼成仙的传说以及唐代道士赵知微留下的遗迹。
领略九华的自然景观,追怀先贤名道的古迹遗存,并不能消解王阳明这一时期究心圣学却不满于辞章记诵的学风,寄情释道却又信疑参半的矛盾心情。据《年谱》载,此次游历九华山期间,“是时道者蔡蓬头善谈仙,待以客礼。请问。蔡曰:‘尚未。有顷,屏左右,引至后亭,再拜请问。蔡曰:‘尚未。问至再三,蔡曰:‘汝后堂后亭礼虽隆,终不忘官相。一笑而别”[1]卷32,1230。可见,“终不忘官相”一语点破了王阳明此时虽欲游心于方外,却又难以弃置圣贤情结于不顾。在向仙道虚心求问的同时,王阳明亦乐于涉险而造访高僧,《年谱》云:
闻地藏洞有异人,坐卧松毛,不火食,历岩险访之。正熟睡,先生坐傍抚其足。有顷醒,惊曰:“路险何得至此!”因论最上乘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后再至,其人已他移,故后有会心人远之叹。[1]卷32,1230-1231
虽然都是点拨语,但与道士蔡蓬头稍带讥诮的语言风格有所不同的是,地藏洞异僧则从正面加以开示,将宋明理学初创时期的两个重要人物周敦颐和程颢视为“儒家两个好秀才”,真可谓一语点醒梦中人。
对于王阳明来说,寄心于方外之学,既是难入圣学门径的权宜之计,也是位卑而无法施展其济世抱负的无耐之举。一方面,即景生情,任由想象以抒发一时的避世之念,“每逢山水地,便有卜居心”[1]卷20,761,“仙人招我云,挥手青云端”[1]卷19,708,“苟长生之可期,吾视弃富贵如砾瓦。吾将旷八极以遨游,登九天而视下。餐朝露而饮沆瀣,攀子明之逸驾”[1]卷43,1759,“世外烟霞亦许时,至今风教后人思。却怀刘项当年事,不及山中一著棋”[1]卷19,706,“逝予将遗世而独立,采石芝于层霄。虽长处于穷僻,乃永离乎豗嚣”[1]卷19,698。圣贤之门难入,经世之志难酬,对于具有浓郁儒家情怀的士人来说,内心的纠结与精神世界的焦虑在所难免,然而,据此就真正地放下,“遗世而独立”,也未免不是一种艰难而痛苦的抉择。正因为如此,另一方面,这种“放下”的不易也在此次游历九华的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青壁须留姓,他时好共寻”[1]卷20,761,“岂尘网之误羁,叹仙质之未化……君亲不可忘兮,吾安能长驾而独往兮”[1]卷43,1759,“彼苍黎之缉缉,固吾生之同胞;苟颠连之能济,吾岂靳于一毛!矧狂胡之越獗,王师局而奔劳。吾宁不欲请长缨于阙下,快平生之郁陶?顾力微而任重,惧覆败于或遭;又出位以图远,将无诮于鹪鹩。嗟有生之迫隘,等灭没于风泡;亦富贵其奚为?犹荣蕣之一朝。旷百世而兴感,蔽雄杰于蓬蒿。吾诚不能同草木而腐朽,又何避乎群喙之呶呶”[1]卷19,698。
游心方外、寄情仙释,虽能一时“欣然有会于心”,但终究同自己的儒者情怀、圣贤志向龃龉难合,“然于孔子之教间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无归”,因此,即便出入于佛、老之中,但其中的依违之处却不能不让王阳明“且信且疑”[1]卷3,139。由疑虑而渐悟仙、释二氏之非,直至批判“老、佛害道”[1]卷32,1232,似乎就不是一种偶然的激愤之辞。
从释道二教抽身而重新回归圣学之域,却仍要面对热衷于辞章记诵、注释考辨的僵化学风;虽殷殷倡言为学之志,然而却应者廖廖,甚至受到立异好名的误解;抗疏直言,陈说利害,结果却招致下狱谪官。这就是王阳明远谪贵州龙场驿之前不得不直面的境况,这种境遇使得王阳明的为学之路和仕宦之途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二、第二次九华之游:危困处境的磨砺与进退行止的释然
因伸张正义而遭受系狱贬谪,即便在赴谪途中也受到监视甚至加害,这一系列险恶境遇的打击与磨难,使得王阳明刚到贵州龙场这一生存条件恶劣的偏僻之地,也能够以超然的心态看待眼前的荣辱得失,不过,“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1]卷32,1234,一时却难以破解生死的念头王阳明后来在回答弟子“夭寿不贰”的问题时,曾这样说:“学问功夫,于一切声利嗜好俱能脱落殆尽,尚有一种生死念头毫发挂带,便于全体有未融释处。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若于此处见得破,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方是尽性至命之学。”参见《王阳明全集》卷三《传习录下》,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册,第119页。。他于动心忍性之余,通过日夜端居默坐以求静一澄心,尤其是在玩味体悟《易》理的过程中,王阳明深切地体认到,“此古之君子所以甘囚奴,忘拘幽,而不知其老之将至也夫!吾知所以终吾身矣”[1]卷23,940。受到《易》中蕴涵的古代圣贤君子随遇而安、与时消息的生存智慧的启迪,王阳明领会到人生的进退之道和生命的安顿之法,从而能够真正地放下生死的牵挂。正是在对人生的进退和生死问题透悟的基础上,王阳明终于悟解格物致知的要旨,“始知圣人之道,吾性具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1]卷32,1234。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龙场悟道”在王阳明思想演进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标志着其致思路径发生了明显的转向,即由此前一直纠结“物理吾心终判为二”,对于物事之理与心性之体终究难以通贯为一深感困惑,转向摄物以归心,心又涵具众理,而心与理之间的内在张力又通过作为本体之心的“性”得以消融,“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理”[1]卷1,26。这样,不仅提升了心的形上地位,也极大地凸显了心的本体意义。这种以形上的本体之心统摄性与理,心、性、理三者融通无碍的致思取向为王阳明心学思想的进一步展开并最终在心学理论的形上学建构层面趋于完善与圆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王阳明“龙场悟道”以后的思想转向及其归趣,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曾作过这样的总结:
自此以后,尽去枝叶,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为学的。有未发之中,始能有发而中节之和。视听言动,大率以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2]卷10,201
自“龙场悟道”以后,王阳明尤为注重心性的磨练,强调“须于心体上用功”[1]卷1,16,主张通过静坐涵养的工夫正德五年(1510),王阳明离开贵州龙场赴任江西庐陵知县的途中,与门人冀元亨、蒋信等谈及“兹来乃与诸生静坐僧寺,使自悟性体”,后又寄书补充说:“前在寺中所云静坐事,非欲坐禅入定也。盖因吾辈平日为事物纷拿,未知为己,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功夫耳。”参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二《年谱一》,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册,第1236页。以复归心体虚灵不昧的本然状态,通过扫除涤荡私意私欲以存养扩充至善的本性。因为在他看来,若仅仅着力于事事物物,容易造成本体之心的放逸而不能持守,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支离决裂的为学方法也难以避免私意气习的缠蔽,往往逐物而难返。正是有鉴于此,他明确地提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1]卷2,46的“知行合一并进”之说,突出知行在心性本体意义上交融互具的不二关系,进而将体与用、本体与工夫打成一片,反对将知行割裂为两截所导致的或重行而轻知的“冥行妄作”,或重知而轻行的“揣摸影响”。
从正德三年(1508)“龙场悟道”起直至正德十六年(1521)“始揭致良知之教”[1]卷33,1287这一段时期,王阳明思想的旨趣主要聚焦于如何通过省察克己的工夫,操持涵养本体之心,反对外心以求理,因为“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以何物邪?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君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君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邪”[1]卷2,47?心体虽赅备众理,但并不意味着只能通过静修“硬把捉着此心”[1]卷1,26,如果那样的话,“是徒知静养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临事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1]卷1,13-14,这是承继程颢所倡导的动静皆为定性的修养路径,只是王阳明更为重视于事事物物上历练这一实践工夫的重要性。这种注重“须在事上磨”的克治成己工夫在王阳明第二次游历九华山期间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诠释。
正德十四年(1519),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之后,为了避免节外生枝,王阳明连夜赶往杭州将朱宸濠交给提督军务的太监张永,然后得旨返回江西,却又遭受张忠、许泰等佞臣的谗言陷害和百般刁难。《年谱》记载,正德十五年(1520):
忠、泰在南都谗先生必反,惟张永持正保全之。武宗问忠等曰:“以何验反?”对曰:“召必不至。”有诏面见,先生即行。忠等恐语相违,复拒之芜湖半月。不得已,入九华山,每日宴坐草庵中。适武宗遣人觇之,曰:“王守仁学道人也,召之即至,安得反乎?”乃有返江西之命。[1]卷33,1277
因谗阻滞留于九华山期间,虽然蒙受幸臣的恶意毁谤和皇上的无端猜疑, 王阳明并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悲观消沉,而是以“毋为尘所萦”[1]卷20、811、“视此琐屑真浮沤”[1]卷20,805的豁达胸怀,在注重磨砺自己心性的同时,又以超然的心态,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与士子、寺僧酬唱答和,观赏、品味着九华山幽静秀美的自然景色与融洽和谐的人文环境。
为了砥砺心境,淡然地应对险境,王阳明选择壁立千仞的东岩作为自己晏坐的地点。明末贵池诸生刘城在其《游九华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上东岩,窥阑悚仄。僧曰:‘阳明先生来此时,未有阑,履前出岩外者出三分,诸从游学生,皆变色战战。又曰:‘焚香之众,誓舍身于兹者,岁数人,多不及防,或损肌肤,卒不得死,亦有失足损躯者。因募十方甃石以干之,乃至今。”[1]卷7,301-302同样如此,惟有以淡定自若的心态方可处变不惊,才能从容地面对仕途的风浪与险恶的处境。
视险若夷心境的磨炼并没有影响王阳明赏景酬答的兴致。“九华之山何崔嵬,芙蓉直傍青天栽。刚风倒海吹不动,大雪裂地冻还开。夜半峰头挂明月,宛如玉女临妆台。我拂沧海写图画,题诗还愧谪仙才。”[1]卷20,806“瀑流悬绝壁,峰月上寒空。鸟鸣苍涧底,僧住白云中。”[1]卷20,806奇峰、流瀑、白雪、明月、飞鸟、僧寺,王阳明已沉浸在九华山的空灵妙境之中,无怪乎他坦言,“当年看不足,今日复来看”[1]卷20,806。在尽情地赏玩九华胜景的同时,王阳明也与当地的儒林士人、方外释子交游酬答。在《江施二生与医官陶野冒雨登山人多笑之戏作歌》的古风中,王阳明写道:
江生施生江生施生是指江学曾和施宗道,二人皆是青阳县人。二人都曾与王守仁有过交往。参见(清)华椿 等修,(清)周赟 纂:光绪《青阳县志》卷四《人物志·理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172173页。颇好奇,偶逢陶野奇更痴。共言山外有佳寺,劝予往游争愿随。是时雷雨云雾塞,多传险滑难车骑。两生力陈道非远,野请登高觇路歧。三人冒雨陟冈背,既仆复起相牵携。同侪咻笑招之返,奋袂径往凌嵚崎。归来未暇顾沾湿,且说地近山径夷。青林宿霭渐开霁,碧巘绛气浮微曦。津津指譬在必往,兴剧不到傍人嗤。予亦对之成大笑,不觉老兴如童时。平生山水已成癖,历深探隐忘饥疲。年来世务颇羁缚,逢场遇境心未衰。野本求仙志方外,两生学士亦尔为。世人趋逐但声利,赴汤蹈火甘倾危。解脱尘嚣事行乐,尔辈狂简翻见讥。归与归与吾与尔,阳明之麓终尔期。[4](卷7,332
阻留于九华山虽属“不得已”,然而,“我本无心云自闲”[1]卷20,812的释然心境,却使得“静听谷鸟迁乔木,闲看林蜂散午衙”[1]卷20,811的兴味并没有消减,甚至在这种志趣相投的交往游历中,王阳明发现自己并不“狐独”,而是有着一批不愿被声色货利、尘嚣世务所累且可以与之偕行的友人。同样如此,与寺僧释子的交往酬和也是闲适而惬意的。《归途有僧自望华亭来迎且请诗》曰:“方自华峰下,何劳更望华。山僧援故事,要我到渠家。自谓游已至,那知望转佳。正如酣醉后,醒酒却须茶。”[1]卷20,808不难体味出,诗作的字里行间呈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
然而,在悠然闲适的游历交往中,他却能体会一种超脱于尘世之外的自在与清新,由此而萌生“暗然避世不求知”[1]卷20,807的憧憬,表现对归隐生活的向往。这一向往在此次顺路游览贵池齐山的过程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
即看花发又花飞,空向花前叹式微。自笑半生行脚过,何人未老乞身归?江头鼓角翻春浪,云外旌旗闪落晖。羡杀山中麋鹿伴,千金难买芰荷衣。
倦鸟投林已乱飞,林间暝色渐霏微。春山日暮成孤坐,游子天涯正忆归。古洞泄云含宿雨,碧溪明月弄晴晖。桃花不管人间事,只笑山人未拂衣。[3]卷8,游齐山二首
诚然,对于王阳明来说,这种“避世不求知”的归隐生活更多地指向精神世界的洒脱与自在,并不意味着消沉厌世,也不仅仅只是“有如智者深韬藏,复如淑女避谗妒”[1]卷20,807。因为,在阴长阳消之际,“小人之朋日渐以盛,苟一裁之以正,则小人将无所容,而大肆其恶,是将以救敝而反速之乱矣”[1]卷26,1027,因此,明智的做法是“遁其身以亨其道”[1]卷26,1027。诚然,“君子虽已知其可遁之时,然势尚可为,则又未忍决然舍去,而必于遁,且欲与时消息,尽力匡扶,以行其道。则虽当遁之时,而亦有可亨之道也”[1]卷26,1027。遁身归隐虽为形势所迫,却并不只是为了一己的自全保身,而是“与时消息”地弘道济世、匡时救弊。在王阳明看来,这种“可亨之道”即是圣贤之道、圣人之学。当然,王阳明认为圣贤之道的现状却是令人堪忧的,这从《登云峰二三子咏歌以从欣然成谣》中能够得以体现:“淳气日凋薄,邹鲁亡真承。世儒倡臆说,愚瞽相因仍。晚途益沦溺,手援吾不能。弃之入烟霞,高历云峰层。开茅傍虎穴,结屋依岩僧。岂曰事高尚?庶免无予憎。好鸟求其侣,嘤嘤林间鸣。而我在空谷,焉得无良朋?飘飘二三子,春服来从行。咏歌见真性,逍遥无俗情。各勉希圣志,毋为尘所萦!”[1]卷20,811诗中不仅体现王阳明对于圣人之学深沉的忧患意识,也展现了强烈的使命担当。
似乎可以这样说,圣贤志向乃王阳明一生孜孜以求的人生理想,这一理想的追求开显了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也铸就了良知本体的实践品格,同时,王阳明也向往超迈洒脱的精神追求,这种超脱境界的追求充盈润泽了生命的情调,丰富了心学的思想内涵。圣贤志向的追求与超脱境界的向往决定了王阳明的良知心性之学具有儒与佛、道相融互渗的特质,也塑造了王阳明亦进亦退、亦显亦隐的丰实人格。
三、批判与会通:释、老之妙与圣贤之学仅毫厘之间
在王阳明跌宕起伏的人生中,曾于弘治十五年(1502)和正德十五年(1520)两次游览九华山,而这两次九华之游都处于其思想变化的重要时期。王阳明的得意门生之一钱德洪曾略述其师的学思历程时说:“盖师学静入于阳明洞,得悟于龙场,大彻于征宁藩。”[1]卷29,1089在第一次游历九华山前后的这段时间内,王阳明虽有圣贤志向却苦于不得其门而入,虽与李梦阳、顾东桥等曾为显扬才名而学习古诗文,却又叹悔“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也”[1]卷32,1231,于是,就在家乡会稽山阳明洞修习道教的静坐导引之术,从而转向对仙、释之学的探求。后来于龙场困厄处境的磨砺,始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自此渐入圣学之门。成功地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却陷入谗陷毁谤的峰口浪尖之上,终以“自信其心”化解了这场无端的凶险。王阳明另一位得意门生王畿在《先师画像记后语》中曾引述其师对于这件事的解释:
先师尝语人曰:“吾于平濠之后,致知格物之学愈觉明彻。良知不学不虑,天植灵根,无间无圣凡,人人所同具。但不能实致其知,牵泥搀和,自滑其灵,所以失之。大都世间毁誉利害,不过一身荣辱,一人得丧。吾所遭谤,构以党逆无将之恶名,蒙以灭族无辜之隐禍人,几微倏忽之际,间不容发。若不能自信其心,略为形迹所滞,机稍不密则失身,根稍不真则偾事。晦而明,曲而理,种种苦心,只好自知自信。意之微妙,口不能宣,而况于人乎?”[5]卷15,410-411
第二次登临九华山就是在平濠之后遭受佞臣张忠、许泰等人陷害阻挠的情形下所作出的无耐之举。虽然如此,暂离构陷的漩涡,投入宁静秀丽的九华山中,在与士人释子坦城无忌的交往过程中,王阳明不由得感叹道,“痴儿公事真难了,须信吾生自有涯”[1]卷20,811,从而再次萌发了归隐之念。如上所述,对于王阳明来说,这种归隐并非是消极遁世的逃避,而是于阴长阳消之际委曲周旋地“遁其身以亨其道”的生存智慧与儒者使命担当。
纵观王阳明的一生,浓烈的圣贤情结贯穿于王阳明的学术生涯与生命旅程的始终,并由此而勾画出王阳明的学思主旨和人生基调,虽然如此,我们也不可忽视佛、道二教对于王阳明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谪官龙场之前的求学问道历程中,即使在悟得圣贤之道以后,释、老二氏之学对于王阳明心学体系的建构、身心的安顿以及进退的抉择也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对于王阳明于正德初年在贵州龙场悟道之前的为学次第及其思想嬗变轨迹,挚友湛若水在《阳明先生王公墓志铭》进行了颇为清晰的概括:“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原文将“正德丙寅(1506)”误作“嘉靖丙戌(1526)”。参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七《世德纪》,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册,第1409页;黎业明《湛若水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始归正于圣贤之学。”[6]王阳明之所以一度转向于仙、释之学的探求,究其原因,既受有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时代思潮之影响,亦与家族的文化传统、师友潜移默化的熏染难以分开关于家族文化背景、师友等对于王阳明仙道情结的影响,参见钱明《王阳明的道教情结——以晚年生活为主线》,《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第2429页。,更主要的缘由似乎还在于,王阳明对于当时的士人学子“溺于词章记诵,不复知有身心之学”[1]卷32,1232的学风颇为不满,但他自己一时却也难以找到进入圣学的门径。归正于圣贤之学以后的王阳明,对于这一段出入于佛、道的经历,时常加以反省或用来警示弟子,“某幼不问学,陷溺于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于老、释。赖天之灵,因有所觉,始乃沿周、程之说求之,而若有得焉”[1]卷7,246,“吾亦自幼笃志二氏,自谓既有所得,谓儒者为不足学。其后居夷三载,见得圣人之学若是其简易广大,始自叹悔错用了三十年气力”[1]卷1,40。这种自我解剖式的反省或警示,某种意义上隐含着在当时朱子学独尊的学术氛围中另辟蹊径的苦衷,亦是通过现身说法以开示如王嘉秀、萧琦、滁州从游弟子等拘泥于养生、慕禅、骛奇的良苦用心,并不意味着王阳明已将释、老之学视作无用的学问而彻底抛弃了,相反,王阳明不仅以一种颇为幽隐的曲折方式将释、老二氏的心性学说融入到天理良知的本体论建构中,同时亦通过借鉴和吸收佛、道注重静定的修养方式,将其与儒家省察克治的涵养修为工夫结合起来,从而熔铸为一种“动静合一”《传习录》记载门人黄直所录的一段问与答:“问:‘儒者到三更时分,扫荡胸中思虑,空空静静,与释氏之静只一般,两下皆不用,此时何所分别?先生曰:‘动静只是一个。那三更时分,空空静静的,只是存天理,即是如今应事接物的心。如今应事接物的心,亦是循此天理,便是那三更时分空空静静的心。故动静只是一个,分别不得。知得动静合一,释氏毫厘差处亦自莫掩矣。” 参见《王阳明全集》卷三《传习录下》,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册,第107页。的工夫论,并最终以“一循天理”的良知心体统摄动静合一、动静皆定的工夫论。这一致思理路于1521年在回答伦以训“学无静根,感物易动,处事多悔"的疑问时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
惟学而别求静根,故感物而惧其易动;感物而惧其易动,是故处事而多悔也。心无动静者也。其静也者,以言其体也;其动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学,无间于动静。其静也,常觉而未尝无也,故常应;其动也,常定而未尝有也,故常寂;常应常寂,动静皆有事焉,是之谓集义。集义故能无祇悔,所谓动亦定,静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静,其体也,而复求静根焉,是挠其体也;动,其用也,而惧其易动焉,是废其用也。故求静之心即动也,恶动之心非静也,是之谓动亦动,静亦动,将迎起伏,相寻于无穷矣。故循理之谓静,从欲之谓动。欲也者,非必声色货利外诱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虽酬酢万变,皆静也。濂溪所谓“主静”,无欲之谓也,是谓集义者也。从欲焉,虽心斋坐忘,亦动也。[1]卷5,195
从这里能够看出来,在遵从宋明儒学严分循于天理与从于私欲的时代主题下,王阳明不仅将先秦儒家思想与宋儒思想互释贯通,还将动与静、体与用、内与外、寂然与感通、本体与工夫融合起来,并将其收摄于本体之心。同时,王阳明又承袭了宋代周敦颐、程颢等儒家学者的做法,批判性地改造了佛、道二家的静定、无欲思想,并明确地以“纯乎天理”之心体将其统贯起来。
正德初年回归儒学以后,在批判的基础上选择性地加以改造和吸收,这是王阳明对于佛、道之学所采取的基本态度,而这又是与他基于儒家立场对佛、道所作的判定分不开的。王阳明依据《大学》“亲民”意旨将儒与佛、道区别开来,“只说‘明明德而不说‘亲民,便似老、佛”[1]卷1,28,“自从悟得亲民宗旨,始勘破佛氏终有自私自利意在”[5]附录2,702。“亲民”之所以被王阳明视作儒学与释、老之学根本区别之所在,其原因在于:
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体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秘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父、人之父与天下之父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孝之明德始明矣!亲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兄、人之兄与天下人之兄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也,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夫是之谓明明德于天下,是之谓家齐国治而天下平,是之谓尽性。[1]卷26,1015-1016
在王阳明看来,“亲民”乃是“明明德”的落点与归宿,是实现儒家“天地万物一体”的生命关怀与价值诉求的必要前提,亦是达至“仁”之境界的必然体现。正是从儒家“亲民”立场出发,王阳明对释、老之学提出了批评,“专事无为,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学术”[1]卷1,10-11,“禅之学非不以心为说,然其意以为是达道也者,固吾之心也,吾惟不昧吾心于其中则亦已矣,而亦岂必屑屑于其外,其外有未当也,则亦岂必屑屑于其中。斯亦其所谓尽心者矣,而不知已陷入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人伦,遗事物,以之独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家国天下。” [1]卷7,274
王阳明即使在苦于难入圣学门径而究心于释、老之际,却时常感受到“二氏之学未尽”[1]卷40,1606,认为其与“孔子之教间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阙漏无归”[1]卷7,256,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王阳明回归于圣学之域的探求。
在对佛、道二教进行批判的同时,王阳明亦从儒学角度对二教的相关思想加以诠释与融通。在与陆澄讨论养生问题时,王阳明指出,“京中人回,闻以多病之故,将从事于养生。区区往年盖尝毙务于此矣。后乃知养德与养身只是一事。元静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谨恐惧而专心于是,则神住、气住、精住,而仙家所谓长生久视之说,亦在其中矣”[1]卷33,1290-1291。对于陆澄颇为困惑禅宗不思善恶与儒家随物而格两种修养工夫的区别时,王阳明解释说:“‘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此佛氏为未识本来面目者设此方便。‘本来面目即吾圣门所谓‘良知。今既认得良知明白,即已不消如此说矣。‘随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来面目耳。体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个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1]卷2,73
如果说对于释、老学说的批判主要基于儒家“亲民”的宗旨,那么,对于二氏之学在重新诠释中加以吸收,在改造中加以融通,则源于王阳明视释、老之学也是“求以自得”的身心之学。诚如其言,“世之人苟有究心虚寂,学道德性命而不流于俗者,虽其陷于老、释之偏,犹将以为贤。盖其心求以自得也”[1]附录2,697,“居今之时而有学仁义,求性命,外记诵辞章而不为者,虽其陷于杨、墨、老、释之偏,吾犹且以为贤,彼其心犹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后可与之言学圣人之道。”[1]卷7,246这不仅仅是对释、老之学的肯定,更是对“有训诂之学而传之以为名,有记诵之学而言之以为博,有词章之学而侈之以为丽”[1]卷2,61这种空疏浮泛的时代学风之自觉反省与深沉忧思。
正是有鉴于释、老之学亦为注重身心修养和精神境界提升的“自得”之学,王阳明指出,“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1]卷32,1243。这种“毫厘之间”的妙处与差异,王阳明曾有一段颇具代表性的阐述:
仙家说到虚,圣人岂能虚上加得一毫实?佛氏说到无,圣人岂能无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说虚,从养生上来;佛氏说无,从出离生死苦海上来:却于本体上加却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虚无的本色了,便于本体有障碍。圣人只是还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些子意在。良知之虚,便是天之太虚;良知之无,便是太虚之无形。日、月、风、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虚无形中发用流行,未尝作得天的障碍。圣人只是顺其良知之发用,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碍?[1]卷3,117
仙、释的“虚”、“无”之境,超然于世累之外,是王阳明所欣慕的。然而,如果仅仅将这种境界拘限于对遁世离俗生活的醉心,限定于个体生命长生久视或超脱生死的追求,这却是王阳明难以接受和认可的。因为,“与物无对”[1]卷3,115的良知必然发用流行于万物,这是良知本体之“用”在伦常日用中的自然呈现。这与王阳明基于“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旨趣而对“明明德”与“亲民”所作的体与用关系的阐述,在致思路向和思想意旨上是一致的。
佛、老学说与圣贤之学的相通之处与毫厘差异使得王阳明自觉地意识到融会儒、释、道三教的必要性。诚然,这种融合会通是从儒家立场出发并对佛、老二氏之学重新加以诠释的前提下展开的。晚年的王阳明曾这样说:“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尽性至命中完养此身谓之仙;即吾尽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谓之佛。但后氏儒者不见圣学之全,故与二氏成二见耳。譬之厅堂三间共为一厅,儒者不知皆吾所用,见佛氏,则割左边一间与之;见老氏,则割右边一间与之;而己则自处中间,皆举一而废百也。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之谓大道。”[1]卷34,1298-1299这里不仅彰显了一代大儒对圣贤之学的学术坚守与使命担当,亦充分表现了王阳明对于三教合一这一时代思潮的积极回应与理论自觉。
参考文献:
[1]王阳明.王阳明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2]黄宗羲.明儒学案[M]∥黄宗羲全集:第七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3]王崇.池州府志[M].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2.
[4]释德森.九华山志[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
[5]王畿.王畿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6]湛若水.湛若水先生文集:第五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马陵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