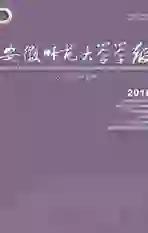形式因与目的因的统一
2016-11-19谭善明
谭善明
关键词: 叙事理论;形式因;目的因;美;善
摘要: 无论是对叙事技巧的揭示还是对叙事语法的描述,都让人觉得文学世界与审美世界的传统关系不复存在了,这是因为文学的审美维度从两个方面被缩小了:一是将审美性等同于文学性,又将文学性定位于形式技巧层面;二是为了维持文学的本体性而排除了社会性和读者的主体性,从而使得形式因与目的因相分离。为了理清文学形式的审美之维,有必要借助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论重建叙事中形式与目的、美与善的联姻。
中图分类号: I01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6)04044706
Key words: narrative theory; form; purpose; beauty; goodness
Abstract: Either revealing the narrative techniques or description of the narrative grammar, it makes us feel that the tradi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terary world and the aesthetic world no longer exists, because the aesthetic dimension of literature has been reduced from two aspects. On the one side, the aesthetic character is treated as literariness which focuses on the techniques of form; and on the other side,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ontology of literature, the social nature and the subjectivity of readers are excluded so that the form and the purpose become separated. To research the aesthetic dimension of literary form, it is necessary to resort to Aristotle's poetic theory to rebuild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form and the purpose, beauty and goodness.
当马原在小说中声称“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子”的时候,读者一下子从那个近乎真实的世界中清醒过来,“叙事”的突然降临改变了通往文学意义的审美之途。在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中,内容在认识论上的优先性引导着文学意义及其审美意蕴的生成,形式则以感性显现的姿态小心翼翼地配合内容的表演。20世纪形式主义文论转向包括叙事理论的出现使人们对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重新定位:真实与虚构、内容与形式、作者与文本等等,于是“讲什么”不再重要,“怎么讲”才关乎作家的创造性和作品的艺术性。
即便是在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人们也无法回避“怎么讲”的问题,文学要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必然要经历一个“赋形”的过程。正如席勒所言:事物的实在是事物的作品,事物的显现是人的作品,“不论我们对历史追溯到多么遥远,在摆脱了动物状态奴役的一切民族中,这种现象都是一样的:即对外观的喜悦,对装饰和游戏的爱好。”[1]133形式创造既是一种审美冲动,也是至关重要的生命冲动,是人性对动物性的超越,也是从人的基本需求向高级需求的提升。于是在传统形而上学体系中,一方面是形式作为思想内容的辅佐而服务于某种文学意图,另一方面形式也同时不断地尝试突破内容的束缚而获得自由,这后一方面的努力在20世纪文艺领域终得以实现,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无不是将文学的外部研究转向内部研究,从对内容的偏重转向对形式自律性的考察。但是,这一转向是否使文学的审美价值得以凸现仍然是成问题的,本文尝试借助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对文学形式问题进行美学反思。
一、形式的危机:从审美性到文学性
对于一般的文学研究者来说,形式问题的分析会和特定的审美取向相联系,但是当谈到形式主义文论时,无论是对形式技巧的揭示还是对叙事语法的描述,都让人觉得文学世界与审美世界的传统关系不复存在了,这也是俄国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被人们所诟病之处,当文学不再是美的、或者不止是美的,还会是什么?为此,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形式文论语境下,“审美性”发生了什么变化。
在“陌生化”这一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关键词中,我们无论如何是能够感受到一种审美意味的:陌生化通过文学形式上的改造拯救了逐渐陷入认知的事物,以审美偏离所带来的愉悦终止审美疲劳所造成的对世界的冷漠。我们在陌生化中所见到的那种力量,是对感性的引发,是对事物本身及对审美感受过程的密切注视。什克洛夫斯基那段关于“陌生化”的经典阐释:
正是为了恢复对生活的体验,感觉到事物的存在,为了使石头成其为石头,才存在所谓的艺术。艺术的目的是为了把事物提供为一种可观可见之物,而不是可认可知之物。艺术的手法是将事物“奇异化”(陌生化)的手法,是把形式艰深化,从而增加感受的难度和时间的手法,因为在艺术中感受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应该使之延长。艺术是对事物的制作进行体验的一种方式,而已制成之物在艺术之中并不重要。[2]10
从中可以看到,陌生化的手法使事物从现实性、认知性走向艺术性、审美性。雅各布森认为,审美功能是文学的主导功能,因为文学具有多种语言功能,它们是主从关系:“在语言信息中,如果美学功能是主导成分,那么这种信息当然可以采用表现的语言的多种方法;但那样一来,这些部分就从属于作品的决定性功能,也就是说,它们依主导成分而变更。”[3]11穆卡洛夫斯基也认为:“在艺术领域内,审美评价必须处于作品中所包含的价值等级的最高级。”[4]24
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俄国形式主义始终将“审美性”作为文学研究的关键,毋宁说,对审美功能的关注只能看作是形式主义文论的出发点,在批评实践中,他们更多地谈及“文学性”而非“审美性”,原因在于他们不关注这种“审美性”是怎样,而是要进入其背后去研究意义的生成机制,这些机制当然会导致审美意蕴的产生,但它是“前审美性”的。雅各布森对此看得非常清楚,他指出:“随着形式主义的发展,把一部诗作看做是一个结构系统,看做是一套艺术手法的有规则有秩序的等级系统的精确概念产生了。”[3]12于是,科学主义迅速取代了审美主义,各种修辞技巧、艺术成分的变形、转换成了形式主义研究的中心问题。
这是形式文论研究的第一重危机:“审美性”被“文学性”所取代,而文学性又被限定为语言技巧层面的运用。随之而来的第二重危机是文学活动被视为文本内部的语言游戏,即便这种研究有审美的考虑,也是将情感性、社会性等因素排除在外。无论是托洛茨基言辞激烈地指责形式主义把词语作为上帝的赐物加以盲目崇拜,从而剥离文学的社会语境将之孤立起来;还是巴赫金从语言的意识形态性角度提醒形式主义者们,如果将形式同贯穿于其中的社会联系分割开来,那么形式本来也将荡然无存——都揭示了这种内部研究的有限性:固步自封必将陷入“语言的牢笼”。由于种种原因,俄国形式主义者们后来也开始反思,如雅各布森在回忆中认为当初包括穆卡洛夫斯基、什克洛夫斯基以及他自己,都并不想建构一个封闭的艺术王国,艺术作为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部件与其它部件密切关联,“我们所强调的不是艺术的分离主义,而是审美功能的自主性”。[5]但正是对这种自主性的强调使他们的研究最终走上了一个极端,在客观上导致了艺术的分离主义。
同样的,英美新批评的“细读法”也是执着于文本得以组织的技法和修辞,这是文学语言区别于日常语言和科学语言、文学性区别于非文学性的关键所在。新批评和俄国形式主义都试图重建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和现实的世界、科学的世界等是完全不同的,正如前述什克洛夫斯基所言,这个世界“正是为了恢复对生活的体验,感觉到事物的存在”,兰色姆也认为“诗歌旨在恢复我们通过自己的感觉和记忆淡淡地了解的那个复杂难制的世界”[6]82,这表明他们一方面要维护文学的自律性和本体性,另一方面又强调文学的使命,希望通过文学来唤醒沉睡的世界。但这毕竟只是一个文学的世界,而且是文学的“形式”世界,它以割断文学的社会性为代价构建起一个纯粹“审美性”的世界,正因为这种分离,使文学活动被孤立,从而其强调的文学性或审美性就成为片面的了。就像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那有名的“意图谬误”和“感觉谬误”理论中所表明的,为了达到真正的本体批评,作者和读者必须从文学批评中被去除,于是文本就被架空了,文学活动也成为静态的,最终文学成为与个人性和社会性无关的“语言乌托邦”。
在形式主义文论中,审美性就是这样从两个方面被缩小了(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叙事理论中同样如此):一是将审美性等同于文学性,又将文学性定位于形式技巧和修辞手法层面;二是为了维持文学的本体性而排除了社会性,以及作者和读者的主体性,从而使得审美性脱离了情感性。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谈论叙事的审美维度时,我们需要作出抉择:是应当继续坚持文学的审美自律性,还是应当冲破形式文论的局限重新对待审美问题?无论是从形式理论本身的发展状况,还是从文学活动的完整过程来看,毫无疑问当是后者。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探讨审美问题就可以避开形式技巧,而是应注意到形式本身的张力。一方面叙事毕竟是关于“怎么讲”的问题,形式本身的审美意味是不可忽视的;另一方面叙事活动不能脱离语境,更不能脱离文学活动,其审美意味要通过具体的修辞“表演”才能成为“活生生的”,这也是文学的生命所在。
二、文学叙事中的形式因与目的因
研究叙事问题,首先就要分析作品中作者与叙事者的关系,叙事者与作品中人物的关系,作品的人物构成、叙事视角、叙事方式和结构等等,我们将其统称为叙事技巧。从俄国形式主义到法国结构主义,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无不对技巧问题作过深入细致的剖析。叙事技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源于“故事-情节”的二分法,这是传统形而上学思维在语言和叙事领域的又一次显现。这一二分法使人们相信有一个原初的故事,它是叙事的材料正如亚里士多德的“质料”,当故事进入到文学话语中时就涉及到“怎么讲”的问题,这就要通过叙事技巧而赋予其“形式”,使之成为情节。这一划分与后来叙事理论的危机有着最直接的关系:那就是将叙事技巧与叙事美学、叙事语法与叙事修辞相分离,而将叙事研究定位于前者,最终使叙事学丧失了活力。因为按照这一二分法,情节如何得以编织是叙事文学的关键所在,而至于这种编织究竟带来什么样的美学效果倒在其次,这样一种先后或因果关系,逐渐将审美与形式分开,从而使形式纯粹化、结构抽象化。于是,叙事理论貌似是要深入揭示文学话语的秘密,其结果却是对文学的缩小。
技巧与审美应当是一体的,但对形式的过分衷情则有意无意地遗忘了审美。叙事技巧的运用直接决定着情节的表现形态,当人们转而关注“怎么讲”的时候,叙事话语的生成和转换取代了故事内容和意义的优先性。这就是要考察文学作品的动词形态、句法形态和语义形态(或者叫文体、构成和主题),它们分别对应于古代修辞学的选词、布局和创意[7]45,这在修辞学领域涉及到的乃是如何遣词造句、谋篇布局、表情达意这样的语言使用技巧,也正因为对技巧的专注使得修辞学长期以来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
但是在叙事理论中,技巧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它是文学成为自足客体的基础:叙事技巧的揭示和总结凸显了叙事文的虚构性,这拉开了文本与世界的距离;叙事技巧自身的规律性和客观性使文本又凌驾于作者和读者之上。这样一种分析显然是要刻意避开文学的社会性和情感性因素的,因为必然性或可能性的形式规律是要超越偶然性的,相对于技巧和结构的普遍性,社会性和情感性无非是其具体的“感性显现”。以托多洛夫为例,他划定了结构主义诗学(叙事学)的研究范围:“结构主义者的研究对象并不在于文学作品本身。他们所探索的是文学作品这种特殊的话语的各种特性。”[8]190因此结构主义关心的不是“现实的文学”而是“可能的文学”,研究的是“可能的文学”中带有普遍性的形式技巧和抽象结构。然后他论述了叙事作品分析由小到大的几个层次,并对每个层次中的叙事技巧问题进行了总结。在第一层“语域”中涉及的是叙事话语的意义实现,包括讲述的指称意义、话语的字面意义和言语行为的进程。第二层“视角”包括叙事者本人是否介入作品、叙事者和人物之间的关系(由此可以区分内视角和外视角)。第三层“文本结构”包括逻辑顺序、时间顺序和空间顺序。第四层“句法”涉及命题得以被实现、情节得以被编织的具体技巧,如插入、连环、交替。在这样一种叙事理论中,托多洛夫对技巧和结构等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而对于审美问题是搁置的,这一点他也是心知肚明的,以至于他在文章的最后强调:“通过对一部或几部著作的分析,不管分析得多么精辟,也不可能提出一些普遍的美学法则。”[8]254关于叙事技巧的法则与审美的法则无关,可以说,叙事技巧的确应具有审美价值,但这种价值仅存在于作品内部,只有当读者阅读时,审美价值才真正体现出来。他还看到,结构并不是评判作品的唯一要素,叙事技巧的分析也不能穷尽作品传情达意的一切手段,同样,出于对文学审美价值的重视,结构主义叙事理论也不能是文学叙事研究的唯一标准。
“故事-情节”的二分法导致了叙事技巧被孤立出来,割断了文学形式的审美之维。要从叙事技巧走向叙事美学,就必须超越形式主义而恢复叙事与世界、读者和作者的联系。我们这里重点谈前者。后一问题的讨论参见拙文《论叙事修辞对叙事语法的超越》,《外国文学》2009年第2期。建立叙事与世界的关系并不是要返回摹仿与再现的文学传统,衡量文学是如何对现实世界进行真实性摹写的,而是要将叙事技巧放在叙事行动中进行动态考察,将叙事技巧与叙事目的和效果相联系。对叙事技巧的这样一种理解,是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因”一致的。亚里士多德确立了事物产生、变化和发展的“四因”: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其中质料因是指事物的最初基质,是事物得以形成的原料;形式因是事物的限度,用以指事物“是什么”,它是事物的本质规定;动力因是指使一定的质料取得一定形式的驱动力量;目的因是指具体事物之所以存在所追求的目的。从这四因的内在关系来看,“目的之达成也就是本质的实现,即形式被确定”,目的隐含于形式中并通过形式得以实现,因此目的和形式是“一码事”,而动力则“是事物的本质和目的实现过程中的张力,因此与形式也属于同一类原因”,这样,“四因”就成了“二因”,即“质料因”和“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都归属于“形式因”。[9]82叙事关涉的是特殊的文学形式,它也应当包含动力因和目的因,叙事美学研究的形式技巧也应是处于话语活动中、并朝向某一目的运动的。
于是,作为美学范畴的“形式”除了具有“和谐”的含义——“秩序,匀称与明确”[10]266,还应当包括“完善”——质料形式化的过程要趋向善的目的。以此审视结构主义叙事理论可以发现,叙事技巧的强调只顺应了目的因中对“和谐”的要求,而有意放弃了善的目的论,希望以此方式通达文学的“本质”,却不曾想恰恰是分割了“形式”本身,从而远离了文学本身。
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为何再次将“道德”问题置于叙事研究中。一方面从话语活动本身来看,“在人物身上,许多看起来是纯审美或纯智力的性质,可能事实上都有着道德的层面”,道德因素是叙事本身无法避免的;另一方面,从目的因角度来看,“善”不只是以其自身为目的,它也是形式之“美”的必要成分:“小说的结构本身,因而连同我们对它的审美理解,就经常建筑于这种实用,就其本身来看是‘非审美的材料之上。”[11]138-139我们不必担心这样会导致狭隘的道德主义,价值实现是人类活动不可或缺的部分,通过艺术形式而获得的审美快感中必然会有某种善,在这种意义上,道德无非是指一个追求完整的人对作品所进行的价值判断,这涉及到作者的责任问题,也涉及到读者的责任问题。这一完善本身就是具有审美意义的,因而建基于“形式”范畴之上的叙事本质上必然是形式和目的、美与善统一的。这一点无论是在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还是《诗学》中, 都是很明确的。他认为修辞学技巧的运用涉及人的性格和美德的分析、人的情感及其产生原因和方式的分析,所以修辞学“也是伦理学的分枝”[12]25。这种理解对文学叙事中的形式问题进行美学反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审美快感:美善一体
强调叙事中的形式因和目的因、审美与道德、美与善的统一,绝不是意味着再一次回到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在“形式”范畴中的叙事毫无疑问关乎技巧的安排和情节的设置,目的因是内含于形式因的,道德因素不是外在的,而是叙事本身的逻辑,亚里士多德这样一种形式理论在文学叙事中是尤为明显的。具体说来就是将审美原则和道德原则共同贯穿于叙事技巧中,当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论及史诗和悲剧的情节安排时不是孤立地对待形式,毋宁说他面对的是“有意味的”形式。所以我们不能片面地理解他关于美是整一的观点,当他谈到史诗情节中“事件的结合要严密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若是挪动或删减其中的任何一部分就会使整体松裂和脱节”[13]78,这里的情节安排不仅仅是指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中那种文本层面的话语编织活动,而是通过对行动的摹仿使艺术具有美的结构和善的情感,也就是说,情节和行动的结合是美善统一的关键所在,所以他说“悲剧摹仿的不仅是一个完整的行动,而且是能引发恐惧和怜悯的事件”[13]82。恐惧和怜悯正是内含于形式因的目的因,这并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道德,其中虽然包括善恶观念,但准确地说它即是一种审美层面的快感。正如朱光潜所言,“亚里斯多德是最早的一个替快感辩护的哲学家”[14]81,这是与柏拉图针锋相对的,因为柏拉图既批判现象世界,也限制人的情感和欲望,而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则通过将审美和道德相联合,恢复本能、情感和欲望之于人及其艺术活动的重要意义。
此外,亚里士多德还从动力因的角度强调情节安排与审美快感的关系:“既然诗人应通过摹仿使人产生怜悯和恐惧并从体验这些情感中得到快感,那么,很明显,他必须使情节包蕴产生此种效果的动因。”[13]105从动力因来看,情节的组织安排、故事的叙述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恐惧和怜悯的情感应该是出自情节本身,而不是由作者强加进去的,也不是通过某种怪诞可怕的“戏景”,所以,“组织情节要注重技巧,使人即使不看演出而仅听叙述,也会对事情的结局感到悚然和产生怜悯之情”[13]105。将目的因和动力因内含于形式因之后,悲剧中的审美原则与道德原则也就统一了。这样,当我们在理解“情节是悲剧的根本,用形象的话来说,是悲剧的灵魂”[13]64这句话时,一定不会再将情节的安排看成是纯粹的形式技巧。结构主义叙事学所总结出来的技巧运用的规律与亚里士多德说的情节的编织要符合“可然律”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种“可然律”体现的正是“怎么讲”故事的动力因和目的因,无论是要求情节的连贯和整一,还是突转和恍悟的发生,都是为了悲剧中恐惧和怜悯之快感的发生,这才是称之为“悲剧的灵魂”的情节。亚里士多德同样谈到在史诗中叙述与快感要统一:“显然,和悲剧诗人一样,史诗诗人也应编制戏剧化的情节,即着意于一个完整划一、有起始、中段和结尾的行动。这样,它就能像一个完整的动物个体一样,给人一种应该由它引发的快感。”[13]163总之,在任何需要合理安排情节的场合,都应保持审美原则和道德原则的统一。
按照这种理解,在叙事中形式与目的、审美与道德的联姻就是非常必要的了。叙事中的道德不是一种说教,也不是指某些固化的价值观念,而是由作品激发起的某种情感,而这是审美快感的必要成分。也就是说与道德性和情感性是相联系的,这是超越叙事技巧而走向叙事美学的关键之处,文学不可能是一堆冷冰冰的技巧拼凑起来的死物,它以“活生生”的面目建立起人与世界、人与人的联系,叙事若抛弃了道德性和情感性也就沦为抽象的数学公式。
换一个角度看,审美原则与道德原则的统一其实仍然是审美本身的问题,这无非是美的情感性与善的情感性的合一,前者直接呈现为审美形式,后者则内在于审美形式。即使亚里士多德从善的角度谈快感,这也是一种与现实的、功利的快感相区别的、带有审美距离的快感,比如他强调最好的悲剧选取的主角都是少数几个著名人物,悲剧的时间也选取遥远的古代,这都是注意到现实与虚构的区别。当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试图拯救形式主义文论的危机而重提道德的时候,也是基于审美意义。查特曼就认为布斯在书中常常提到道德价值,实际上是似是而非的,他强调的不过是美学价值,因为该书考虑的是道德价值如何为某部作品服务,而非将道德价值与真实世界中的行为相联系。[15]布斯所关心的是如何通过各种叙事技巧建立起作者、叙述者、人物和读者等之间的关系,并由此达到某种特殊的效果,所以他才强调作者的介入和控制,作者或叙述者对读者情感的干涉和影响。这样就回复了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叙事技巧与道德判断之间的联系,将动力因和目的因内含于叙事活动中。同样,布斯也强调叙事活动中的审美距离问题,作者可以通过控制距离来使读者接受其特定的信念和规范,而不是通过审美距离来孤立“情节和情感”,所以距离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使读者和某些趣味、某些价值增加联系,从而增加情感效果,最终达到叙事中美善的统一。
不过要想总结出道德因素作用于叙事进程的规律绝非易事,同样叙事中的美与善究竟该如何统一也是不会有定论的,因为这是由作者、叙述者、读者等在一定情境下共同作用的结果,于是我们看到布斯对小说叙事的研究不像结构主义者们那样急于一劳永逸地抽象出程式和规则,而是借助具体作品深入考察情节的展开及其审美效果的实现。这就表明,作者在创作叙事作品时,来自隐含的读者、叙事者、人物的声音,推动和影响着作者的创作,这使得叙事技巧中充满着丰富的意识观念和情感色彩;而读者在阅读叙事作品的时候,形式技巧所造成的审美光晕不是超凡脱俗的,而是要让读者注入自己的价值判断,这样才能真正地和文本展开对话,才能获得审美的享受,情感与形式的统一构成了阅读活动的完整内容。卡西尔在《人论》中写道:“人类文化并不是从它构成的质料中,而是从它的形式,它的建筑结构中获得它的特有品质及其理智和道德价值的。”[16]46几乎所有的语言符号及其组织结构都带有特定的情感或情绪的色彩,我们没有理由将符号、形式与情感、道德分离。在叙事理论中被强调的那种强大的“文学性”冲动,并非某些理论家们所认为的是对永恒秩序的回应,而恰恰是某种强烈情感的体现,卡西尔指出了这种形式冲动背后的美善统一的情感意义:“审美的自由并不是不要情感,不是斯多葛式的漠然,而是恰恰相反,它意味着我们的情感生活达到了它的最大强度,而正是在这样的强度中它改变了它的形式。”[16]189
动力因的加入使形式成为具有生命的形式、饱含美善统一的情感形式,这乃是形式最本原的审美维度,特别是在叙事过程中,形式是于叙事行动中被唤醒和照亮的,这本身就是形式和目的的统一。即使在叙事中存在着某些较为明显和固定的基本规则,作家也不是为了这些规则去创作,而是借助它们来完成特定的叙事活动,从而为规则增添了新的生命,这也正是作家肩负的审美使命。对叙事的研究更不能停留于对形式技巧的抽象上,而是要从审美角度确认美善的统一,这正是苏珊·朗格在那本书中所极力强调的,“那些做艺术鉴别的人(只有他们才能发现感性形式何以令人激动)知道情感原本就以某种方式蕴含在每一种想象形式之中”[17]66,那种斩断形式中任何价值判断和情感色彩的作法,只能使我们在文学活动中朝向“子虚乌有”。
参考文献:
[1]席勒.美育书简[M].徐恒醇,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
[2]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M].刘宗次,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
[3]雅各布森.主导[M]∥赵毅衡.符号学文学论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4]穆卡洛夫斯基.标准语言与诗歌语言[M]∥赵毅衡.符号学文学论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5]本奈特.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J].张来民,译.黄淮学刊,1992(2):104111,121.
[6]兰色姆.征求本体论批评家[M]∥赵毅衡.新批评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7]托多罗夫.文学作品分析[M]∥张寅德.叙述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8]托多洛夫.诗学[M]∥赵毅衡.符号学文学论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9] 赵宪章.西方形式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10]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11]布斯.小说修辞学[M].付礼军,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
[12]亚里士多德.修辞学[M].罗念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13]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14]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15]申丹.修辞学还是叙事学?经典还是后经典?——评西摩·查特曼的叙事修辞学[J].外国文学,2002(2):4046.
[16]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17]朗格.情感与形式[M].刘大基,傅志强,周发祥,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凤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