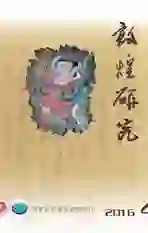P.2569背面两首傩歌的校补定名及相关问题
2016-11-10任伟
任伟
内容摘要:敦煌文献P.2569背面《儿郎伟》之前的文书,黄征先生视其为两首诗歌作品,拟名为《银歌》、《金歌》,并未进行释读;张锡厚先生主编的《全敦煌诗》(第12卷)首次释录了该作品,题名为《儿郎伟》驱傩词,但仍有未尽之处。结合图版再次释读,确认该作品是两首与驱傩有关的诗歌,并从几个方面厘定为可能反映敦煌西汉金山国时期宫廷驱傩活动的儿郎伟作品。
关键词:傩诗;金吾将军;儿郎伟;西汉金山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6)04-0074-06
Abstract: Dunhuang academic Mr. Huang Zheng previously regarded the texts written on the reverse side of P.2569 as two poems and named them Silver Song and Gold Song, but he did not interpret or collate them. Mr. Zhang Xihou was the first to collate the poems, and he entitled them ErLang-Wei under the category of ancient sacrificial ceremony words in Vol.12 of his Compilation of Dunhuang Poetry(2006), but his interpretation is not sufficient. Combining the plat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llate the document again, confirms that both poems are about ancient sacrificial ceremonies, and concludes that they are likely works on the activities of exorcising evil spirits and welcoming gods held by the Jinshan Kingdom court at Dunhuang.
Keywords: Nuo Poems; general of imperial guard troops; Erlang-Wei; Jinshan Kingdom under the tile of Western Han;
一
敦煌遗书中王重民先生编为P.2569的文献是一个汉藏文文献杂抄的写卷,正面全为藏文、背面也有20余行藏文而被抽归法藏藏文文献,编号为P.T.113。该写卷背面抄录了多首题为“儿郎伟”的汉文作品,已由黄征先生辑录校注,收入其所编《敦煌愿文集》[1]。在《儿郎伟》之前还抄有两首作品,黄征先生在《敦煌文学〈儿郎伟〉辑录校注(P3552、P2569)》校记中拟名为《银歌》、《金歌》,认为非《儿郎伟》,与驱傩无关而未作校录[2]。张锡厚先生主编的《全敦煌诗》第12卷首次释读并收录了该作品,题名为无名氏《儿郎伟二首》[3]。兹先将张先生的释文抄录如下:
(其一)
银山银带关。银坡银岸□。银□□欲多。银门银户坐。银树银花。银叶银□。银河银樽必酒成。银□银铛如酒著。银鹅袍袴。总继银做。□已带车乘。庄铰钉丛多。总市买卖将银针。小儿游去掷银锁。坐卧常向南岳界。澡浴常用银娑罗。大富大贵总如此。今宵故此来驱傩。
(其二)
金庭金阙,金柱金门。金鞍金马,里有金人。东厨金釜,百燃金薪。金盘九阙,金盏金樽。饮者金酒,食者金珍。仓置金粟,出乘金轮。金枝簇从身,是金吾将军。荣华富贵如此,纳庆且寿新春。
该写卷纸张破旧,纸质粗糙,多处有褶痕,其上汉文文书皆为竖写,书法粗拙。这两篇作品残存九行,历时久远,漫漶过甚,且多处墨痕洇染、墨迹变淡,点画不清,很难释读,仅后半部分四行半勉强能够识别。虽经张先生首次释读,但录文读来依然难明就里,与原卷图版覈校,仍有未妥之处。
因此本文拟在张先生成果的基础上结合IDP图版再次对原卷进行释读,并就该作品谈点拙见,以求教正于方家。
1. 银山银带关。银坡银岸□
此处“关”字仔细核对原卷图版,似是“闺”字,类似的写法还见于P.2058背面《水则道场文》:“……乃仙娥化质、素玉同芳,长播淑德于宫园,永传嘉猷于闺阁……”[4]但“闺银坡”显然不通,应是“围”、“闺”形近致误,故校为“围”。
原卷“银岸”后“银”字隐约可见,后一字细勘图版,隐约能看到“水”字,“银岸银水”可以解释得通,古人诗词中就见。如《全唐诗》卷七百零九徐夤诗《白酒两瓶送崔侍御》就有“几夕露珠寒贝齿,一泓银水冷琼杯”。宋人钱惟演《七夕》诗中也有:“紫天银水渡辛夷,藻帐雕屏解佩时。”[5]
2. 银门银户坐。银树银花
“银门银户”后一字原卷为“坐”,但联系诗句来看,抄者可能“坐”、“生”不辨、形近致误,且“坐”不能解,当校改为“生”。敦煌文书的创作、抄写情况比较复杂,写卷的抄者未必就是作者,抄写者水平不高、抄录粗疏,因而致误的情形很普遍。从内容上的多处错误看,本卷应该也如此。
此字既释读为“生”,则当和后面的“银树”连读,即“银门银户生银树”合为一句。张先生把“银花银叶”分开,实际上此句意为“银花银叶”点缀在银色的树枝上,形容装金点银的美丽景象。“银叶”后一字虽漫漶不清,但能看出是上下结构,上部左半部看隐约像“爿”或“月”字,右半部和下部十分模糊,多处褶皱,不能辨识,姑且根据句意释读为“装”字。
3. 银河银樽必酒成
原卷为“银柯”,先生释为“银河”,并出校记曰:“伯本原作‘银柯,‘柯、‘河形近致误。”[3]5691
按:此处原卷“银柯”不误。“柯”,《说文》解为“斧柄也”。《广雅》解为:柯,柄也。后引申为“树枝”,如南朝梁吴均的名作《与朱元思书》中就有:“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银柯”意即“银色树枝”。且上文有“银花银叶”,则此处“银柯”亦通,两句似在描述节日里装金点银的盛景,故不烦改。改为“银河”,反而不合诗意了。
“银樽”后一字较模糊,张先生释为“必”字,细勘图版,似非,但难以释读,故暂付阙如。
4. 银□银铛如酒著
此处“如”字,因原卷漫漶过甚,无法释读,但从残留笔画痕迹看并非“如”字,故亦暂阙。
5. 总继银做。□已带车乘
核对图版,“银”字下并无“做”字,系张先生误校,故删去。“已”前一字无法辨识,细校发现,“已”误,似“包”,且该字和缺字应该合为一个字,但实难校读,故阙。
6. 庄铰钉丛多
“庄”后一字,张先生校为“铰”,殊难理解。图版极为模糊,复核原卷彩色照片,时间久远,墨痕洇染,该字所在纸张位置处有较多褶皱。法藏原卷是粘贴在一张蓝色衬纸上的,该字右半恰有一处破损,露出下面的蓝色背景,看上去颇像“交”,但仔细辨识,并和本篇其他“金”旁字相较,该字左半并不是“金”旁,右半边一字也非“交”。全字更像书写潦草的“严”,且“庄严”一词可解,故暂释读为“庄严”。
7. 坐卧常向南岳界
原卷“南岳”勉强可以看出,“界”字下半较为模糊,“南岳界”可解,兹从张先生所校。
中唐以后,佛教律宗颇为兴盛,南岳衡山即为当时的毗尼中心,名德辈出,如智俨、希操、弥陀和尚承远、云峰和尚法证、大明律师惠开、般舟和尚日悟等,形成刘禹锡《唐故衡岳律大师湘潭唐兴寺俨公碑》中所云“言律藏者宗衡山”[6]的局面,著名诗人柳宗元亦撰有《南岳弥陀和尚碑》、《南岳云峰和尚碑》、《云峰和尚塔铭》、《南岳般舟和尚第二碑》、《大明和尚碑》、《衡山中院大律师塔铭》等数篇碑铭[7]。此处“坐卧常向南岳界”结合下文“澡浴常用银娑罗”似说一位持守戒律、严洁修行的高僧大德,亲自参与驱傩活动,也暗示出敦煌岁末傩事活动得到普遍重视。
8. 澡浴常用银娑罗
原卷为“澡洛”,张先生校为“澡浴”,是。“澡浴”一词为“洗浴、沐浴”之意,佛经中常见。如《大楼炭经·忉利天品》:“郁单曰天下人。食净洁自然粳米。是为见取食及澡浴。龙及金翅鸟食鱼鳖。及食提米提历大鱼。是为取食及沐浴。阿须伦食自然食及衣澡浴。四天王诸天。食自然食衣被及澡浴。忉利诸天。亦食自然食衣被及澡浴。”[8]又如敦煌写卷S.3872《维摩诘经讲经文》中:“……是身虚伪,虽假以澡浴衣食,毕归磨灭……常将世间清冷之水,澡浴磨灭,只是洗得外边尘垢,心中诸恶,不能去除……此个色身何准则,澡浴之时如洗墨。”[9]
“娑罗”,此处疑为“婆罗”(即颇罗)的误写。“颇罗”,亦写作“叵罗”、“破罗”等,是中古时期西域传入的一种酒器。《隋书·西域传》中记载:
曹国,都那密水南数里,旧是康居之地也……国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东诸国,并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焉,金破罗阔丈五尺,高下相称。[10]
蔡鸿生先生认为,“破罗”一词源自伊朗语的音译,此处“金破罗”当为祆教祭拜得悉神的酒器[11]。余欣先生则联系库车和法门寺地宫及西安东南郊沙坡村出土的相关文物专门对“银颇罗”做了考证,认为是与祆教有关的礼器,虽然与史书所载大小有别,但其性质和形制应该相同,大小不同大概是适用于不同的祭祀场合之故[12]。“颇罗”作为酒器,屡见于唐人诗句,如敦煌写卷P.2555刘长卿《高兴歌酒赋》:“珊瑚杓,金叵罗,倾酒漴漴如龙涡。”[13]岑参的诗作《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14]另外,宋人撰《邵氏闻见后录》卷八记:“近世以洗为叵罗……”[15]
邵氏虽有质疑,但可见时人已有此称。结合上文“澡浴”一词,“婆(颇)罗”作为礼器,亦可用于洗浴,此处作“婆罗”当更为妥当。“银颇罗”、“金颇罗”都是名贵的礼器,在此显然不无夸饰之意。
9. 今宵故此来驱傩
谛视图版,“宵”原卷为“消”,当为“宵”的误写,兹从张先生径改。“傩”字墨色很淡,但前面“駈”(“驱”之俗字)清楚,故“傩”不误。
综观第一首作品,全篇共有4行半,每行25个字,加上残字共有112个字,每句刚好7个字,且句尾“坡”、“多”、“柯”、“鹅”、“锁”、“罗”、“傩”等可以清楚释读的字均协韵,似可认为该诗是完整的一首七言之作,试移录如下:
银山银带围银坡,银岸银水□□多。银门银户生银树,银花银叶装银柯。银樽□酒成银□,银铛□酒著银鹅。袍袴总继(係)银□带,车乘庄严钉丛多。总市买卖将银针,小儿游去掷银锁。坐卧常向南岳界,澡浴常用银婆罗。大富大贵总如此,今宵故此来驱傩。
第二首原卷清晰度尚可,文字大多可以辨认,张先生释读得基本无误。但“金枝簇从身。是金吾将军。”一句张先生断为“身”属前句,实则应该逗断在“从”后,虽然“身”作“从”的宾语,“从身”亦通,但此处显然是意在强调,因而“身”作后句主语更为恰当,句式也更整齐。试将第二首过录如下:
金庭金阙,金柱金门。金鞍金马,里有金人。东厨金釜,百燃金薪。金盘九阙,金盏金樽。饮者金酒,食者金珍。仓置金粟,出乘金轮。金枝簇从,身是金吾将军。荣华富贵如此,纳庆且寿新春。
二
关于这两篇作品的定名,黄征先生拟名为《银歌》、《金歌》,张先生定名为《儿郎伟》,本文基本同意张先生的看法,并补充几条理由如下:
首先,就整篇文书的书写而言,虽不能说作品的抄录者就是创作者,但其中的“金”、“从”、“且”诸字和抄录在同一写卷上的《儿郎伟》作品中的“除”、“从”、“苴”等字的用笔规律一样,应该可断定为同一人书写,不排除该书手所抄录者全为《儿郎伟》作品。
其次,就已知的《儿郎伟》的句式来说,并没有规律,大致上有整齐的六言,如P.2058背面《儿郎伟·今者时当岁暮》;也有杂用四言、六言的,如P.3552四首《儿郎伟》;也有纯用五言的,如P.2569V《儿郎伟·圣人福禄重》;还有杂用四言、六言、七言的,如P.2612V《儿郎伟·青阳上元》。P.2569V(今P.T.113)这两首诗的第二首也是用了四言、六言,第一首则是整齐的七言诗,大致符合《儿郎伟》的句式结构。
再次,从现存的敦煌儿郎伟写卷的标示情况来看,也不一样。有些每首前面都标有“儿郎伟”,如P.2058V;有的则只写第一首,后面全部不标,如P.3552;有的第一首不标,而标明后面的几首,如P.3270;还有完全不标的,如S.2055背面“正月阳春佳节”一首。本篇涉及的两首诗处在该写卷的右端,前面并没有标明“儿郎伟”。由于敦煌文书的留存较为复杂,除了一些佛道经卷保存较好且内容连续,世俗文书大多残缺,因而无法考知页面的存续,仅凭留存的残页不能排除这两首作品属于儿郎伟。
再从诗歌的内容来看,第一首明确说“今消(宵)故此来驱傩”。第二首最后说:“纳庆且寿新春”,且提及金吾将军,可以说都与驱傩有关的。
从现有资料看,金吾将军驱傩屡见于记载。唐代金吾将军本由前代的“执金吾”而来,《汉书·百官公卿表第七上》“金吾”条:“应劭曰:吾者,御也,掌执金革以御非常。师古曰:金吾,鸟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职主先导,以御非常,故执此鸟之象,因以名官。”[16]驱傩也是要驱除不祥,这二者应该不是巧合。唐代金吾卫职责之一,就有“天子出行,职主先导”,《唐六典》卷25《诸卫府》“左右金吾卫”条载:“……凡车驾出入,则率其属以清游队建白泽旗、朱雀旗以先驱……”[17]同样能看出率先开路以驱除不祥的。此外,据宋人王溥《唐会要》卷71《十二卫·左右金吾卫》载:
元和十三年十二月,左右金吾引驾仗奏:以旧例,驱傩侲子等金吾将军以下,并具襕笏,引入合门。谨案:大傩者,所以驱除群厉,合资威武,其光仪襕笏之制,常参朝服,旧制未称。今后请各衣锦绣、具巾袜、带仪刀、部引出入、则与事合宜。从之。[18]
除了以上记载,还可以从文人的描述中得知,如唐王建《宫词》:“金吾除夜进傩名,画裤朱衣四队行。院院烧灯如白昼,沉香火底坐吹笙。”[19]可见,金吾将军在晚唐五代职掌驱傩之事已是定制。综合上述,这两首诗歌确属傩词,厘定为“儿郎伟”大致不误。
三
最后,谈谈与这两首作品相关的几个问题。
1. 关于其作者
敦煌写卷多不见撰者,且抄者与作者多非一人,故文书的考释十分不易。本写卷亦没有标明撰者,只能结合作品内容权作蠡测。从用词上看,这两首作品中多处出现了包含“金”、“银”的词语如“金庭”、“金阙”、“金柱”、“金门”、“银树”、“银花”、“银叶”、“银柯”等。“金”、“银”本属于佛家“七宝”(其余为砗磲、琉璃、水晶、珍珠、玛瑙),尤为多见于佛经中。典型的如《大楼炭经·忉利天品》:“佛语比丘:‘须弥山王顶上,有忉利天,广长各三百二十万里。上有释提桓因城郭,名须陀延,广长各二百四十万里,七重壁、七重栏楯、七重交露、七重行树,周匝围绕姝好,皆以七宝作之,金、银、琉璃、水精、赤真珠、车、马瑙。金壁者银门,银壁者金门……金栏楯者金柱栿银桄,银栏楯者银柱栿金桄……金交露者银垂珞,银交露者金垂珞……金树者金根茎银枝叶华实,银树者银根茎金枝叶华实……”[20]类似的描写还可见于其他佛经,兹不赘述。诗中又提到“金粟”、“金轮”,这些词汇也是佛典中屡见的,如《佛本行集经》、《法句譬喻经》、《太子须大拏经》、《起世因本经·阎浮洲品》、《大楼炭经·转轮王品》、《般泥洹经卷下》、《佛说菩萨本行经》、《佛说轮王七宝经》,等等,可谓不胜枚举。又《俄藏敦煌文献》第4册Ф223《十吉祥颂》第4有《仓变金粟颂》,前云:“仓变金粟者,满仓金粟,变作黄金。家僮踊踊而焚香,长幼忻忻而发愿”。后附诗云:
忽然金粟自盈仓,满月晨昏见宝光。万囤安排多贮积,一家新贺有余粮。诸人见者咸言差,闻说难思实异常。直像菩萨来斯界,感应名为妙吉祥。[21]
再结合诗中“南岳界”、“澡浴”、“银娑(颇)罗”诸多与宗教有关的词语来看,虽然不能断定诗作者就是一位僧人,但这位作者谙熟佛学是肯定的。敦煌本为佛国圣地,亦有“金地”之称。如S.2575背面第3篇《道场祈愿文》:“于是星罗金地,洒丽清华。”[9]102P.3262《河西节度使尚书建窟祈愿文》:“林树芳荣,宫人散诞于灵窟,舍珍财于金地。”[22]诗中的“金鞍金马”则可能是附会敦煌的金鞍山。金鞍山(即今阿尔金山)亦称金山,约位于敦煌西南,是晚唐五代时期敦煌人民心目中的神山、圣山。“当时敦煌地区的官府、民众把金鞍山作为敦煌的神山多次设坛祭祀,官府还把祭祀金鞍山神作为常例按时派人祭祀。张承奉建立西汉金山国,其名称就得自于金鞍山。”[23]记载较明确的是S.5548《敦煌录》:“金鞍山,在沙山西南,经夏常有雪。山中有神祠,甚灵,人不敢近。每岁土主望祀献骏马,驱入山中,稍近,立致雷电风雹之患。”在现存敦煌文献中也屡屡为文人所歌咏,如S.6249《祈愿文》:“先奉为金鞍东界,天龙布欢喜之云;玉塞西疆,梵释降祯祥之气。”P.2864《白雀歌》:“嵯峨万丈耸金山,白雪凝霜古圣坛。金鞍常挂湫南树,神通日夜助王欢。山出西南独秀高,白霞为盖绕周遭。山腹有泉深万丈,白龙时复震波涛。”P.3633《龙泉神剑歌》:“金鞍山下是长津,天符下降到龙沙。”
2. 关于这两篇作品的创作时间
杨秀清先生曾述及本写卷七首《儿郎伟》中有两首提及“长史、司马”,“透露了张承奉上台之初即派人联络中央的史实”[24],那么至少这些作品抄录于张承奉继任归义军节度使之后是没有问题的。
本写卷第2首诗中提及驱傩由金吾将军来主其事,如前所述,唐末五代的金吾将军是主管天子宫廷卫御及相关礼仪的官员,而结合敦煌实际,在张氏、曹氏前后多任归义军节度使治下近180年的敦煌,虽然都是地方小王国的格局,但名义上还是接受中原王朝管辖的,未见明目张胆地设置此官。查考敦煌的历史,只有在张承奉时期曾建立西汉金山国(后改称敦煌国),而这一时期的文书中屡见“金山天子”、“圣文神武天子”的称谓,如P.2838《斋琬文》、P.3405《金山国诸杂斋文范》及P.3633《龙泉神剑歌》等文书。另据杨秀清先生研究,西汉金山国曾经建立起一套和中原王朝类似又略有调整的政治制度[25],并且从《龙泉神剑歌》也可看出,张承奉确曾有立太子(“太子福延千万岁,王妃长降五香车”)、册后妃(“六宫并是名家子,白罗绰约玉颜新”)、封百官(“百官在国总酋豪,白刃交驰为告劳”)之举。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明确提到“当锋直入阴仁贵,不使戈鋋早用枪。堪赏给、早商量,宠拜金吾起上将”(以上所引诗句并见于颜廷亮先生《〈龙泉神剑歌〉新校并序》[26]),只是尚难确定阴仁贵是否即是诗中所写“金吾将军”。张承奉建国以白雀为瑞应,文臣张永特意写了《白雀歌》进献,“偕以霜、洁、白为词”(P.2594V)表达其美好祝愿,再联系此作也是以“金”、以“银”为内容,同样为祈福呈祥而作,推测二者之间可能不无关系。此外,敦煌写卷P.3405是张承奉时期用于佛事活动的斋文杂集,学界通常称为《金山国诸杂斋文范》,或称《金山国佛事文范》,李正宇先生定为张文彻所撰。其中有一篇原题《水旱霜蝗之事》,有“我皇稽颡”之句,李先生认为其中的“我皇”即是张承奉,应当不误[27]。据文中“既霜风早降,致伤西作之苗;螟蝗夏飞,必殒东成之实”可知,张承奉建立西汉金山国之后,敦煌地区曾有过头一年遭受霜冻灾害之后、第二年夏天又遭受严重的蝗灾事,以至于身为天子的张承奉都亲自“手执金炉”、捧香祈祷,可见灾害给当地农业生产带来的损失必定不小。天灾频遭加上外族侵扰,无疑会给民众生活带来巨大威胁,这种情况下,驱傩就更具有现实意义。再从诗作中“金吾将军”、“荣华富贵”、“大富大贵”等语词推测,这两首作品很可能也和《白雀歌》一样,正是张承奉时期某位文人对于金山国建立之后某年为禳灾避疫而于岁末举行的宫廷驱傩活动的记述。正因为如此,所以抄写者才将其抄录于篇首。如其为实,从中似乎透露出敦煌西汉金山国宫廷活动的某些消息,则这件文书就更具其历史和文献的价值了。
参考文献:
[1]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5.
[2]黄征.敦煌文学《儿郎伟》辑录校注(P3552、P2569)[J].新疆文物,1990(3):114.
[3]张锡厚.全敦煌诗:第12卷[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5690-5692.
[4]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371.
[5]杨亿,等.西昆酬唱集[M]//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22.
[6]刘禹锡.刘禹锡集[M].《刘禹锡集》整理组,点校.卞孝萱.校订.北京:中华书局,1990:53.
[7]刘禹锡.柳河东集:第6-7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93-110.
[8]高楠顺次郎,等.大正藏:第1册:阿含部上[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No.0023:297a.
[9]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英国国家图书馆,等.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5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183.
[10]魏征,等.隋书:卷83[M].北京:中华书局,1973:1855.
[11]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1998:11.
[12]余欣.屈支灌与游仙枕:汉唐龟兹异物及其文化想象[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36-38.
[13]张锡厚.全敦煌诗:第6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2425.
[14]廖立.岑嘉州诗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428.
[15]邵博.邵氏闻见后录[M].刘德权,李剑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62.
[16]班固.汉书[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733.
[17]李林甫,等.唐六典[M].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638.
[18]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1284.
[19]王宗堂.王建诗集校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638.
[20]高楠顺次郎,等.大正藏:第38册:经疏部六[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No.1767:294a.
[21]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俄藏敦煌文献:第4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284.
[22]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5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24.
[23]郑炳林.唐五代敦煌金鞍山异名考[J].敦煌研究,1995(2):127.
[24]杨秀清.再论张承奉时期归义军同中央政权的关系[J].台北:南华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敦煌学:第27辑,2008(2):203.
[25]杨秀清.试论金山国的有关政治制度[J].敦煌学辑刊,1998(2):36-42.
[26]颜廷亮.《龙泉神剑歌》新校并序[J].甘肃社会科学,1994(4):108-112.
[27]李正宇.敦煌历史地理导论[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