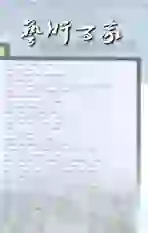洪武九年自刻本《书史会要九卷补遗一卷》题跋与过录文字考释
2016-11-02郭建平
郭建平
摘要:明洪武刻本《书史会要》是书画史上知名著录,被日库馆臣列于子部艺术类书画属,此著录洪武刻本上有盛昱的一段题跋,记录了此版本著录与明人顾仁效的渊源,盛昱跋旁还有其过录王文恪《阳山草堂记》的一段话,盛昱过录的有关顾仁效的生平的这段文字,也涉及了中国古代文人山水画的创作问题。同时也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背景下的文人“诗意地栖居”的一种反映。
关键词:中国美术史;书法艺术;古籍刻本;《书史会要》;题跋;顾仁效
中图分类号:J2
文献标识码:A
《书史会要》9卷成于明洪武九年(1376)。选100余种书籍,补遗卷,共收录400余位书法家;余绍宋在《书画书录解题》中言《书史会要》“披采至为繁富,文笔简当,间加评论,褒贬颇得其平”。从文笔及评论水平的角度看余绍宋对此书评价较高,但是此书结构有些混乱,引文和作者的评论混在一起,史料出于其他书籍者,却未被标注,又存在真伪杂糅的问题。
《书史会要》此书列于子部艺术类书画属,四库馆臣也对此书(浙江鲍士恭家藏本)进行了一定的总结:“《书史会要》九卷,《补遗》一卷,明陶宗仪撰。《续编》一卷,朱谋垔撰。宗仪有《国风尊经》,已著录。谋垔字隐之,号厌原山人,宁藩支裔也。是编载古来能书人上起三皇,下至元代,凡八卷。末为《书法》一卷,又《补遗》一卷。据孙作《沧螺集》所载宗仪小传,称《书史会要》凡九卷。此本目录,亦以《书法补遗》共为一卷。而刊本乃以《补遗》别为卷,又以朱谋垔所作《续编》一卷,题为卷十,移其次于《补遗》前。殆谋垔之子统鉷重刊是书,分析移易,遂使宗仪原书中断为二。今仍退谋垔所补自为一卷,题日《续编》,以别宗仪之书。而其《书法补遗》如仍合为一卷,则篇页稍繁,姑仍统鉷所编,别为一卷,以便省览。宗仪旧本,以元继宋,而列辽、金於后,与所作《辍耕录》中载杨维桢《正统论》以元继宋者所见相同。维桢论已仰禀睿裁,特存其说。宗仪是编,亦谨仍其旧文焉。”“而刊本乃以《补遗》别为卷,又以朱谋垔所作《续编》一卷,题为卷十,移其次于《补遗》前。”及“殆谋垔之子统鉷重刊是书,分析移易,遂使宗仪原书中断为二。今仍退谋至所补自为一卷,题日《续编》,以别宗仪之书。”这两段话交代了《书史会要》内容的有关增补、源流、出处情况;与四库浙江鲍士恭家藏本相比,国图藏洪武九年自刻本《书史会要九卷补遗一卷》,显然不包括朱谋垔撰《续编》一卷的内容,中国古代藏书史上,同一著录有不同版本流传,而各个版本的内容增补情况不一致的情况也广泛存在,本文就不再赘言。“宗仪旧本,以元继宋,而列辽、金于后,与所作《辍耕录》中载杨维桢《正统论》以元继宋者所见相同。”
四库官臣还特意提到此书在时间分段上,列辽金于元后,这个观点与同为陶宗仪所著的《辍耕录》中所载杨维桢的观点相同;《书史会要》传世不同版本很多,有元刊巾箱本,明钞本,八千卷楼钞本,明洪武刊无续本、明崇祯八年刊无续本,三续《百川学海》本、四库文澜阁本、民国十八年武进陶氏影印洪武本和上海书店影印洪武本等。傅增湘在《藏园群书题记》对《书史会要》洪武刻本的情况进行了介绍:“《书史会要》九卷,补遗一卷,元南村处士陶宗仪九成著。洪武刻本,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字,黑口,左右双阑,版心上鱼尾上记字数。前有洪武九年金华宋濂序,次永嘉曹睿新民序,次洪武丙辰宗仪自序,次江阴孙作撰《南村先生传》,次引用书目,次总目,次姓名考。卷末有洪武丙辰四明郑真俊序。没卷后均列有捐资人姓名,今详列于后方,俾世人知刊书分卷醵金者不独梵经为然也。”
傅增湘阅过此版本的《书史会要》后,对此版本的情况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揭示。首先介绍了此刻本的装帧情况,然后介绍了此刻本的序言(或叫序跋)的情况,清代曾国藩在《经史百家钞》中曾言:“序跋类,他人之著作述其意者。”西汉孔安国《尚书序》认为序宗旨在于“序作者之意。”“中国古代书画著录上存有大量古代、近代知名学者所作序跋,包括刊本序跋及藏书序跋;前者,简单来讲是指与文本内容一起出版的序跋或叫序,常常说明著述的出版宗旨或作者背景;后者,简单而言是指后世或同世的藏书家或借书者在书上靠前页或靠后页所题的跋,一般为手书形式,藏书序跋涉及的内容与刊本序跋相同;”看来,此版本的《书史会要》有四人写过类似序的文章,并随内容一起刊刻。而“没卷后均列有捐资人姓名,今详列于后方,俾世人知刊书分卷醵金者不独梵经为然也。”从中国出版发展史看,一般情况下,佛经出版时受资助刊刻的情况比较多,而此书非佛经,但是也有人捐资出版。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书史会要九卷补遗一卷》(11327,明陶宗仪撰,洪武九年自刻本,盛昱跋二册十一行二十字黑口左右双边。)上有盛昱的一段题跋:“余前得宋椠《方言》,有顾仁效印记,丙申夏更得此《书史会要》,又顾君藏书。偶阅《震泽集》,录此于福叶。伯羲记。”与盛昱跋写在一起的还有其手录王文恪《阳山草堂记》的一段话,由于这个版本著录上面盛伯羲手跋与其手录文字这二段话离得很近,又出自于一个人笔迹,所以手录的这段话也很容易被认为是盛昱的跋。
首先谈谈作跋者盛昱,爱新觉罗氏,字伯熙,一作伯羲、伯兮、伯熙,号韵莳,一号意园。满人,肃武亲王豪格七世孙。盛虽出身贵宵,但一生中并未担任高官显职,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其精力更多地花在了诗文考据上,他一生在传统文化领域几乎无所不窥。善诗文词,“简贵清谧,崇高风雅,所交皆一时魁杰。以文章道义相友善,文誉满海内。”有首诗约写于1897年,为赠友人的《赠云门》,“瑟缩深居气不扬,因君脚发少年狂,游山随俗携茶具,久病从人集药方。丰世声名皆疚清,八年风雨话沧桑,侧面投足知无所,省识桃源是醉乡。”“瑟缩深居气不扬”,暗示其八年隐居,心情不畅的压抑生活;而少时旧友的到来,令其回首往事,有所感概;“省识桃源是醉乡”则揭示了其一生中有个阶段是出于隐居或半隐居状态的;盛昱好藏书,藏书印有“圣清宗室盛昱伯熙之印”、“伯羲父”、“宗室文悫公家世藏”、“郁华阁藏书记”等。后世袁克文购藏其藏书最多。而伯羲手跋所提之顾仁效,为明代书画家、藏书家,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结庐阳山,隐居于“阳山堂”,善画、善吟咏、善诸种乐器,喜藏书。藏书印有“静学文房”、“南京兵马指挥司副指挥关防”、“夹山人书画”、“水东馆考藏图籍私印”等。
顾仁效在美术史上也是有记载的,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下)曾言:“明代画家之著名者,不可指数,上所列者,择其较有关系画史之演进,非独以艺术称也。其次名家,以其所长者归纳之,有兼长山水花鸟者,约二十余家,兼长山水人物者,五十八家,(……解珙、林宾齐、张世禄、夏鼎、林广、彭舜卿、杜琼、孙蹊、顾仁效……等)。”可惜其作品流传下来的甚少,美术史上曾经有很多类似顾仁效这样的小名头的画家,也许在当时、当地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但是由其作品流传下来的很少或者没有,那么这样的人也许最终湮灭在历史尘埃中,后人再也无法复原其真实艺术水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而“余前得宋椠《方言》,有顾仁效印记”盛昱此跋揭示了其见到了顾仁效收藏过的两本书,说明了顾仁效藏书还是有一定数量的,而这本宋椠《方言》应该为《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是汉代扬雄(前53一18)所著的训诂学领域的一部重要的工具书,顾仁效、盛昱二人都曾收藏过这个版本的《方言》。
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洪武刊本字体秀丽圆湛,犹有元代风范,顾传本至稀,余生平所见只罗氏、朱氏二帙,江南国学图书馆亦藏一帙,为杭州丁氏善本书室旧物。顷以探海南游,于上海忠记书庄得睹此帙,诧为珍秘,《方言》宋本余已于二十年前得之,并影印刊以传世矣,喜此书旧为一家眷属,因书阳山草堂记于副业。今籍三百年后仍归于一姓,形影相依。免离群索居之感,亦书林中一重佳话也。”傅增湘所提之《方言》,应为盛昱跋中所提之《方言》,而“洪武刊本字体秀丽圆湛,犹有元代风范”这段话揭示了洪武刻本还是具有书法研究价值,字体应该是学元人。江庆柏《图书与明清江南社会》载《铁琴铜剑楼藏(二妙集)》,上有无名氏跋尾,云:“吾友顾仁效过访次山秦思宋,执是为蛰。嘉靖丙申寓绣石堂识。”这是说长洲顾仁效以此(二妙集)为见面礼,去拜访无锡秦沐。两人都是藏书家,所以以书为礼。图书在这里起到了沟通情感的作用。从这些信息来看,顾仁效生平与书有很深的缘。
盛昱过录的文字也显示了其对前人顾仁效的尊重与感念,此过录的文字内容是:“王文恪震泽先生集阳山草堂记阳山在吴城之干位,益众山所从,始顾君仁效结庐其下,仁效年少耳,则弃去举子业。独好吟咏,性偏解音律兼工绘事。每风晨月夕,闭阁垂帘,宾客不到,坐对阳山,拄颊搜句日不厌;或起作山水人物。或鼓琴一二行,或横笛三五弄,悠然自得,人无知者,知之者其阳山乎。因扁其居日阳山草堂,余间造而问焉,曰子于是焉,日对阳山其亦有得乎无也,虽然有一焉,吾观兹山峰峦得出没高下险夷之象,观其石得吞吐之象,观其云烟得开阖晦明卷舒之象,观其草木得葳蕤震靡荣悴之象,观其鸟兽她虫得蠼虬螺飞跳跃之象;以是发诸诗形诸丹青,播诸丝竹,自视若有异焉,而不知其果异乎,无异乎?有得乎?无得乎日然子之学,其将日进而,未巳也,虽然盍亦求其本乎,遂书其室以为记。”此段过录的段落揭示了顾仁效的生平,其在苏州的阳山筑草堂隐居,生性淡泊,而盛昱一生中有段时间也是处于隐或半隐的状态,所以。盛昱看到顾仁效的藏书会有所感慨,亲录一段王文恪有关顾仁效生平的小品文字。过录通常是指把一个版本上的手跋或者其他内容的文字抄到另外一个版本的书籍上,过录文字在中国古籍上大量存在。过录的内容也有研究价值,往往揭示了过录者的学术认同及感受,所以也值得关注。这段文字与明清文人传世的精品小说文的文风相契合,明清时期的性灵小品文常有感悟人生、独抒自我、寄情山水的率真情感流露,而这种“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小品文往往也在题跋、序跋中大量存在。
而此过录文字所叙述的“吾观兹山,峰峦,得出没高下险夷之象;观其石,得吞吐之象;观其云烟,得开阉晦明卷舒之象;观其草木,得葳蕤霉靡荣悴之象;观其鸟兽她虫,得蠼虬螺飞跳跃之象”,“以是发诸诗,形诸丹青,播诸丝竹”正与中国画写生的真正过程相契合,中国画写生往往是“写生命”、“写生活”,观察天地万物的生机、生气,然后画家内化此生机,自然笔墨自然有生气。中国美术史也有“师自然”、“写生”一脉,当然古代中国所言之“师自然”、“写生”与我们当代的所说的写生是有异同之处的,在此就不赘言。值得注意的是洪武刻本《书史会要》的这段过录文字透露出了中国古代文人典型的隐居状态,在中国历史上,隐士文人艺术家尽量疏远权力与财富,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景仰,他们的人生不断被后世同质群体所效仿,其艺术及学养甚至被当时及后世新的正统派和学院派所汲收;因为中国古代,韬光养晦的退隐之路往往是一种保全自己的最好选择;《易》中谈隐及隐士,日:“天地闭,贤人隐。”《南史·隐逸》云:“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这样看来,各个朝代被尊为隐士的人不会是凡夫俗子,应为名士、贤良,有才艺、有学问;隐士经营诗文书画的一个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就像中国学问里讲究“体用”一样,——在“天人合一”语境下的审美创作中去努力构建人与己、人与人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嵌入了内心修为、实践道德。海德格尔关于“人诗意地栖居”的理念实际上与中国古代隐土文人的生活轨迹是契合的;例如,盛显过录的有关顾仁效的生平的这段文字,恰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背景下的文人“诗意地栖居”的一种反映。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绘画史上“山居”母题(therne)系列是一个相当大数量的存在,诗文中的山居意象反复而长久地作用于后世人的意识与情绪,并成为为后世人的共同的心理机制、民族记忆、集体潜意识,也即有了“原型”的力量。通过阅读此段过录文字,不难想象顾仁效绘画的题材也有可能多为“山居”系列。中国艺术史上著名的山居主题的绘画作品,例如《山居图》《富春山居图》等,其创作者钱选、黄公望都有从世俗世界隐退、隐居山林的生活经历;就传统著录来看,与山居有关的诗文跋札举不胜举,例如,魏晋南北朝谢灵运的《山居赋》、唐王维的《山居秋暝》等,包括此段过录文字,这样看来,使人“心放俗外”的山居意象在文字作品中不断重复出现,这似乎也标识着其在中国艺文史上的份量。其实,盛过录的顾仁效经历的文字可以作为中国古人把山居文字转换为山居图的一个文化史上典型的例证,“每风晨月夕,闭阁垂帘,宾客不到,坐对阳山,拄颊搜句日不厌;或起作山水人物,或鼓琴一二行,……”又,“吾观兹山,峰峦,得出没高下险夷之象;观其石,得吞吐之象;观其云烟,得开闲晦明卷舒之象;观其草木,得葳蕤霍靡荣悴之象;观其鸟兽她虫,飞跳跃之象。”
图像艺术有着天然的“在场性”的优势可以将其文学原型以视觉地方式直接作用于观者。为其提供可以更直观地步入“山居”的途径。宋代郭熙《林泉高致》曾言:“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然则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在焉,耳目断绝,今得妙手郁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实获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贵夫画山之本意也。不此之主而轻心临之,岂不芜杂神观,溷浊清风也哉!画山水有体:铺舒为宏图而无馀,消缩为小景而不少。”叉,“盖身即山川而取之”,“夺其造化……饱游饫看,历历罗列于胸中而目不见绢素,手不知笔墨,磊磊落落,杳杳漠漠,奠非吾画。”所谓“身即山川”、“饱游饫看”,恰与洪武本《书史会要》上的过录跋相呼应:“吾观兹山峰峦得出没高下险夷之象,观其石得吞吐之象,观其云烟得开阖晦明卷舒之象,观其草木得葳蕤露靡荣悴之象,观其鸟兽她虫得蟮虬蠼飞跳跃之象;以是发诸诗形诸丹青,播诸丝竹,自视若有异焉,而不知其果异乎。无异乎?有得乎?无得乎日然子之学,其将日进而,未巳也,虽然盍亦求其本乎,遂书其室以为记。”这段文字揭示了顾仁效“身即山川”、陷入山川,后下笔绢素;所绘图像必然以山居为主。我们知道图像作为言说符号的在场效果会使接受者陷入其中,会有“看此画令人生此意”的感受,而这之前应该首先是画者对山水世界的陷入,只有这样,图像符号和存在世界才可以达到无缝对接。“观其石,得吞吐之象;观其云烟,得开阖晦明眷舒之象;观其草木,得葳蕤震靡荣悴之象;”正是“夺其造化”的过程,也正是画者对山水世界的陷入。
王文恪《阳山草堂记》涉及顾仁效的内容被盛昱过录在洪武刻本《书史会要》上即反映了盛昱对于隐者顾仁效的感念认同,也揭示了此版本著录的一段递传史;通过此段手跋我们对此著录此版本的收藏情况有一定的了解,而且通过此段精妙生动的过录文字,我们似乎更加认同在历代专制王权下,与其在庙堂中做一个低微的况且又来之不易的并且与保持人性的尊严不兼容的官位,不如退隐山林,啸傲林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