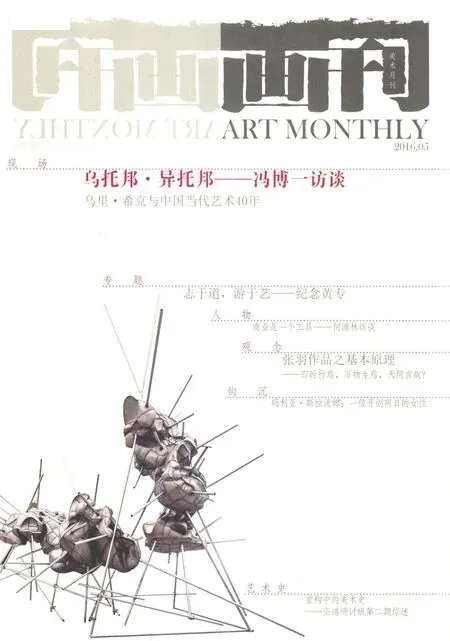玛利亚·斯拉沃娜:一位开创明日的女性
2016-11-01安通尼亚福伊特AntoniaVoit翻译李双志
[德] 安通尼亚·福伊特(Antonia Voit)翻译:李双志
玛利亚·斯拉沃娜:一位开创明日的女性
[德] 安通尼亚·福伊特(Antonia Voit)翻译:李双志
在柏林和慕尼黑度过了并不艰难的学生时光之后,玛利亚·斯拉沃娜(Maria Slavona)从1890年开始在巴黎实现了自我发展——不仅仅作为女艺术家功成名就,而且也取得了单身母亲的成功,独立养活了她和她的孩子。
“在女学生们中,有一些人天赋极高”[1],柯勒惠支(Kaethe Kollwitz)回顾她在慕尼黑女子艺术学院度过的求学时光时写道。她指出其中一位便是“以其艺名为人所知并且出类拔萃的斯拉沃娜”[2]。玛利亚·斯拉沃娜与珂勒惠支结成了保持多年的艺术家友谊,在她们共同的学业结束之后,她们还多次在柏林和巴黎见面。
玛利亚·斯拉沃娜,原名玛利亚·肖勒(Maria Schorer),出生于一个开明家庭。她1865年3月14日在吕贝克降生,是药剂师兼化学家提奥多尔·肖勒(Theodor Schorer)与妻子奥提丽亚(Ottilie)的女儿。“4岁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画画了,”斯拉沃娜回忆道,“之后空下来的每一分钟,我都用来尝试画画。在我母亲的家族里,从事艺术活动并不是罕见的事儿。她的哥哥弗里茨·施特格(Fritz Steger)是雕塑家,不过年纪很轻就染上瘟疫,在维也纳去世了。她支持我对画画的爱好,她有敏锐的艺术理解力。在我父母家里堪称佳作的铜版画、蚀刻版画和雕塑,很早就塑造了我的品位。没有她的支持,没有我们家族环境的保护,我作为女性可能没法在一座轻蔑艺术的城市里得到发展。”[3]玛利亚·斯拉沃娜的父母为自己的六个子女,其中四个是女孩儿,提供了符合各自禀赋与愿望的教育。
在17岁的时候,玛利亚·斯拉沃娜奔赴柏林,以便获得绘画和素描方面的培训。她首先上的是埃希勒(Eichler)的私人学校,然后又转入柏林工艺美术学校。1887年,她报名参加了女性艺术家与艺术之友协会开设的素描与绘画学校。就像柯勒惠支在1886、1887学年所做的那样[4],她在卡尔·斯陶芬·伯尔尼(Karl Stauffer-Bern)的肖像画研究班学习。回顾那段岁月,她说:“在四处试读了一番之后,我发现斯陶芬·伯尔尼就是我最需要倚仗的老师,他强化了我对古典大师们的仰慕之情,并特地指点我学习丢勒和霍尔拜因,还有那些杰出的荷兰画家,像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和泰尔博赫(Gerard Terborch)。”[5]
“4岁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画画了,斯拉沃娜回忆道,“之后空下来的每一分钟,我都用来尝试画画。”
古典大师对于玛利亚·斯拉沃娜的示范意义也反映在了她1887年的自画像上,这幅画被称为“德国艺术史上最美的女性肖像画”之一[6]。斯拉沃娜在这里显然是参照了伦勃朗作于1633年[7]和1634年[8]的两幅自画像:“就像伦勃朗一样,她挑选了一个真人大小的半身像;在上半身的一半侧面中,她自然地转过头来,目光直接迎向观赏者,嘴角附近有一抹似有似无的微笑。这张脸笼罩在微微卷翘而凌乱的头发下,就连披覆在肩背上的衣领也让人想起伦勃朗画中带有荣誉项链的铁质衣领。”[9]这幅画在构图和表现上与伦勃朗的作品有相同之处,在绘画技巧和用光上,玛利亚·斯拉沃娜则表现出自己的风格特征:“她的彩色粉笔画所具有的均衡的明亮度、柔和的阴影和淡薄的用色与伦勃朗毫无关联,体现出的是她自己对色彩的敏感。”[10]

《卖花老妇》 玛利亚·斯拉沃娜 布面油画 66cm×121cm 1893年
1888年,玛利亚·斯拉沃娜到了慕尼黑,一开始并没有真正“习惯慕尼黑当时的艺术与生活氛围”[11]。她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这里的一切都透出一种清新的格调,这里的人看待生活时毫无任何矫情伤感。这就对了,女孩们应该和大学生们一样享受自己的生活,这样再接着工作的时候才会焕然一新。”[12]斯拉沃娜一开始就读于阿洛瓦·艾尔德尔特(Alois Erdelt)的私人绘画学校。她的女同学评论道:“在这位年轻女画家的习作中表现出了纯粹的、完整无缺的艺术本质。尽管她的技能还有点不稳定,但她挥洒起画笔来却有着独特的盎然生气和音乐感。”[13]之后不久,斯拉沃娜就换到了慕尼黑女艺术家协会开办的女子学院,进入了路德维希·赫尔特里希的班上学习,当时珂勒惠支也在这个班上。珂勒惠支证实,斯拉沃娜“在用色上要比我有天赋得多”[14]。赫尔特里希对斯拉沃娜来说是第二重要的老师:“除了在赫尔特里希这里,在任何地方都学不会绘画。我真的要赞美我到慕尼黑来上这个学校的那一时刻。我在之前几个月里获得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对每一个去不了巴黎的人,我都只会建议他,到慕尼黑这里来吧,柏林什么都没有!”[15]斯拉沃娜在慕尼黑的学习时代只有少数几件作品保留了下来,其中有1889年画成的油画习作《金发女孩头像》,从中可以看到她作品中对固定轮廓的惊人稀释。[16]
在回了一趟吕贝克,并与几位斯堪的纳维亚的艺术家如乔治·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赫尔曼·邦(Herman Bang)、尼尔斯·皮德森·摩尔斯(Niels Pedersen Mols)和威廉·皮特森(Vilhelm Petersen)相会之后,斯拉沃娜决定去巴黎:“他们的讲述让我心动,尤其让我向往巴黎;我在慕尼黑的年度展上认识了伍德(Uhde)、利伯曼(Liebermann)和特吕波纳(Trübner)的作品,并了解到他们认为自己很受益于法国影响,于是我就鼓起勇气,向我当时颇受震惊的家人坦白说我要去巴黎。就连我好心的母亲这一次也不完全赞同,觉得必须劝阻我。”[17]斯拉沃娜的决定得到了威廉·皮特森的支持,后者自己就计划去巴黎,而且一再坚持说:“您太好了、太严肃了、太天赋出众了,根本不能留在这个庸俗市侩气十足、特别衰老、病入膏肓的德国。”[18]斯拉沃娜与皮特森一起在巴黎尝试着实现以尼采为精神榜样的生活方式。她从慕尼黑的旧日同学罗莎·普菲弗英尔(Rosa Pfäffinger)那里获得了经济上的支援,罗莎稍后不久也闯入了这个圈子:“我们的生活共同体形成了一个实验室,在这里未来在用新的生活形式、新的道德做实验。要尝试打破现存的、僵化的,但又强调情感的、主观主义的家族、家庭、婚姻体系。个人在未来应该比现在更能成为独立个体,但同时比现在更系统地服务社会。”[19]除了为葛列托成本昂贵的生活转变和合居共同体提供资助的普菲弗英尔,伊瓦娜·科比尔卡(Ivana Kobilca)和丹麦雕塑家汉斯·比尔施·答勒鲁普(Hans Brich Dahlerup)也属于这个紧密的小圈子。此外,葛列托还与后来的出版商阿尔伯特·朗恩(Albert Langen)、作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和弗兰克·魏德金德(Frank Wedekind)保持着联系。1891年9月底,玛利亚·斯拉沃娜与威力·葛列托的女儿莉莉出生。10个月之后,葛列托与罗莎·普菲弗英尔的儿子乔治来到世间。葛列托没有为这两位女性支付任何钱,但给她们留下了凡·高的画作,他凭可靠的直觉预言凡·高将有伟大的未来。斯拉沃娜和普菲弗英尔在1893年便已达成一项“决议”:“我们是现代女性,是开创明日的女性,要保持自己和孩子们的独立。”[20]在这之后,当葛列托眼见普菲弗英尔财产耗尽而日益退缩时,两位女性与葛列托的关系也逐渐瓦解。不过,作为要单独抚养孩子的单身母亲兼艺术家,她们要保证生存基础却十分艰难。珂勒惠支在1904年也来到巴黎,她为罗莎·普菲弗英尔当时身处的贫困处境大感惊诧,便提出收养罗莎的儿子乔治,乔治随后便与珂勒惠支的两个儿子一同在柏林长大。
玛利亚·斯拉沃娜在1895年便在柏林再次见到了珂勒惠支。在同一年,她的油画《卖花妇人》在柏林大型艺术展览上展出。这幅画是斯拉沃娜两年前画的,在1893年便已在巴黎的战神广场沙龙里展出过[21]。在一个没有清晰面目的背景前伫立着一个老妇人的正面整体形象,她双手提着盛满花的篮子放在身前。衰老的面容、劳累过度的双手和以彩色粉笔色调画出的娇嫩花朵之间的反差在妇人简朴的深色衣裙映衬下得到了强化,最终却被斯拉沃娜以调和的方式化解了:“整个布局让肖像平添了尊严、宁静、一股欢快的气息。与利伯曼毫不动情地画出的那些日常劳作中的老妇人不同,玛利亚·斯拉沃娜升华并理想化了现实,避免了任何让人沮丧的印象,为老妇人赋予了一圈友好的光环。”[22]
斯拉沃娜在巴黎的最初时光还留下了另一幅画作——创作于1891年的《戴皮帽子的男人》。画中是一个坐在扶手椅中的男人,头部是用较细腻的笔触较为细致地描绘出来的,而身体和手则是用糨糊状笔法画出来的,没有清晰的轮廓。在这两幅作品中还可以明显看到斯拉沃娜的慕尼黑时代对她的影响以及她对荷兰古典大师的偏好[23]。
19世纪90年代晚期,玛利亚·斯拉沃娜在巴黎结识了瑞士艺术商与收藏家奥托·阿克曼(Otto Ackermann),1900年嫁给了他。阿克曼收养了她的女儿莉莉。这一对夫妻住在一栋对外开放的住宅里,艺术家像卡米耶·毕沙罗(Camille Pissarro)、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卡尔·爱德华·迪利克斯(Karl Edvard确D i r i k s)、珂勒惠支、瓦尔特·莱斯提柯夫(Walter Leistikow)、马克斯·利伯曼(Max Liebermann)、莱纳·玛利亚·里尔克和和平主义者贝尔塔·封·苏特纳(Bertha von Suttner)都出入其中。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斯拉沃娜创作出了她最杰出的作品。她自己如是说:“我的个人发展和我与色彩的关系,我都只得益于法国,得益于法国乡土的空气和巴黎的气氛。马奈、莫奈、雷诺阿和与我有着一种对我来说裨益良多的美好的同志关系的老毕沙罗,都成了我的引路人和充满愉悦的学习经历。”[24]她的肖像画和风景画——后者是她致力越来越多的专题——体现出越来越强的印象主义倾向[25]。斯拉沃娜于1903年和1904年参加了秋季沙龙展,1903年至1908年在独立协会展出作品。1907年,法国出资购买了她的一幅风景画。与此同时,从1901年开始,斯拉沃娜也有作品在柏林“分离学派”展上展出。从1902年起,她成为该学派的通讯成员,从1913年起成为正式成员。1914年她换入由马克斯·利伯曼领导的“自由分离派”[26]。后来斯拉沃娜与丈夫、女儿离开巴黎,迁居吕贝克。由于她在吕贝克找不到适合女艺术家的创作条件,她又与家人一起在1909年搬至柏林。这位女艺术家在当时的艺术业界已享有的特殊地位体现在她的个展数量上[27],比如说,1908年在维也纳米特科(Miethke)画廊、1912年在柏林卡西尔沙龙和1926年在温特图尔博物馆(Museum Winterthur)举办的个展。1931年她去世后,柏林国家美术馆在王储宫为她举办了一个大型的纪念展,该展览直到1934年在德国多个城市巡回举办[28]。

《戴皮帽子的男人》 玛利亚·斯拉沃娜 布面油画 47cm×55cm 1891年
注释:
[1] 珂勒惠支:《日记》,Jutta Bohnke-Kollwitz主编,Siedler出版社,Berlin 1989年,页737。
[2] 同上。
[3] 引自Gustav Lindtke:《玛利亚·斯拉沃娜》,见《车:吕贝克年鉴》,Paul Brockhaus主编,H.G.Rahtgens 出版社与Franz Westphal出版社,Lübeck 1957年,页88。
[4] Alexandra von dem Knesebeck:《珂勒惠支:成长岁月》,Michael Imhof出版社,Petersberg 1998年,页38。
[5] 引自Lindtke:《玛利亚·斯拉沃娜》,页89。
[6] 引自 Bröhan:《玛利亚·斯拉沃娜》,页26。
[7] 头戴插羽毛的天鹅绒贝雷帽的自画像。
[8] 穿皮毛领大衣的自画像。
[9] Bröhan:《玛利亚·斯拉沃娜》,页26/27。
[10] 同上,页27。
[11] 引自Lindtke:《玛利亚·斯拉沃娜》,页89。
[12] 引自Carl Meißner:《玛利亚·斯拉沃娜》,见《钟楼看守》,第34年度,第1期,页404。
[13] 《巴黎的波西米亚人:女画家罗莎·普菲弗英尔的自传记录》,Ulrike Wolff-Thomsen主编,Ludwig出版社,Kiel 2007年,页24。
[14] Kollwitz:《日记》,页739。
[15] 引自Meißner:《玛利亚·斯拉沃娜》,页404。
[16] Bröhan:《玛利亚·斯拉沃娜》,页27。
[17] 1890年1月12日,Willy Petersen写给 Marie Schorer的信,引自《巴黎的波西米亚人》,页162。
[18] Ulrike Wolff-Thomsen:《威力·葛列托(1868-1923):他在1900年左右国际艺术行业与艺术贸易中的地位》,Ludwig出版社,Kiel 2006年,页38。
[19] 《巴黎的波西米亚人》,页100。
[20] 同上,页133。
[21] 据她自己所说,她是在参加这次展览时给自己起的艺名。参见Lindtke:《玛利亚·斯拉沃娜》,页90。
[22] Bröhan:《玛利亚·斯拉沃娜》,页27。
[23] Alexandra von dem Knesebeck:《“我在慕尼黑真正学会了去看”:与印象派女画家玛利亚·斯拉沃娜的一段艺术家友情》,见Hannelore Fischer与Alexandra von dem Knesebeck主编:《“巴黎让我着魔”:凯特·珂勒惠支与法国现代派》,Hirmer出版社,Köln/München 2010年,页42。
[24] 引自Lindke:《玛利亚·斯拉沃娜》,页90。
[25] 同上,页46。
[26] Ulrike Wolff-Thomsen: 《玛利亚·斯拉沃娜》,见Ulrike Wolff-Thomsen、Jörg Paczkowski主编:《凯特·珂勒惠支与她在柏林分离派中的女同行》,Boyens,Wertheim 2012年,页137。
[27] 同上,页138。
[28] Bröhan:《玛利亚·斯拉沃娜》,页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