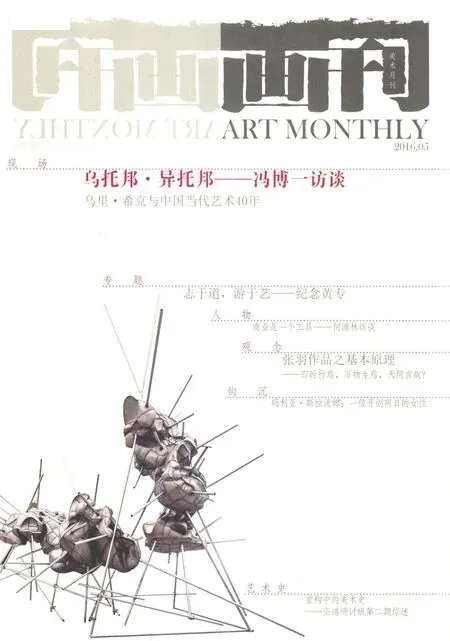论赞助人与艺术家的关系:关于为科学家拟议的一个范式的一些评论(1964)[1]
2016-11-01迈耶夏皮罗MeyerSchapiro翻译王玉冬
[美] 迈耶·夏皮罗(Meyer Schapiro) 翻译:王玉冬
理论研究
论赞助人与艺术家的关系:关于为科学家拟议的一个范式的一些评论(1964)[1]
[美] 迈耶·夏皮罗(Meyer Schapiro) 翻译:王玉冬

迈耶·夏皮罗(1904-1996年)
在一篇讨论研究机构中雇主与雇员问题的文章中,威廉·埃文(William M.Evan)教授建议将赞助人与艺术家的关系作为行业科学家的一个范式[2]。他认为:假若这一范式能被接受的话,科学家由于目前对各类研究机构的依赖而产生的压力,可能就会减少。我希望从一个艺术史家的视角来讨论埃文的这一范式构想。我的目的不是去评判这一模式对于现代科学家的适用程度,而是去思考埃文对构建在过往历史之上的这个模式的描绘是否正确。我的评论或许有助于解决他提出的问题。
埃文以一个“赞助人和艺术家之间理想型关系”观念开篇。
……在这样一种关系之中,赞助人给予艺术家自由,让他以自己的方式去追寻他的艺术灵感。诸如“一个自治的、非实用的、本身值得欣赏的艺术”或者“为艺术而艺术”的构想,虽然已经为希腊人所熟知,但在中世纪时被人遗忘,文艺复兴时期又得以被重新发现。
过往各时代赞助人同艺术家之间的关系,与埃文的记述有很大差异。在希腊罗马世界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大多数有创意的绘画和雕塑都是服务于一个明确目的的定制品。为了装饰建设中的一幢建筑物、一所寺庙、一处丧葬建筑,或是一个凯旋门、凯旋柱,艺术家才会去制作雕塑。定制这件作品的个人或群体会规定题材,而且会对材料、尺寸、地点及其他事项给出详细说明。文艺复兴留给我们大量艺术家们签署的合同,它们指定了成品绘画或雕塑的题材以及其他事项。所有这些都与“本身值得欣赏的艺术”这一观念不相矛盾;我们经常会发现论述一件作品之美的材料,但它们对这件作品的功用却只字不提。不过,和我们时代的艺术家不同,传统艺术家很少会在没有定制的情况下去自发地创作。
这种繁复的定制作品,通常需要几年的努力和昂贵的材料。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为市场而作的“工业化”艺术。宝石匠和制陶人事先预知集市上或大街上会有买者,所以在作坊里制作他们的艺术品。和他们一样,艺术家会自担风险,为民众制作小型雕塑和绘画。丢勒的坦纳格拉陶塑人像、木版画和蚀刻画等,就是为了那些潜在但未知的买者而作。毫无疑问,对于拥有它们的人来说,这些也是能带来审美愉悦的物品;16世纪购买那些现成版画的人,通常是些鉴定家,他们为个人收藏寻找备选样品。
与一般的理解相反,在中世纪,除了定制品之外,还有一种独立于市场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实践。从7世纪到15世纪,寺院僧侣们会去装饰教堂的祈祷书和其他法典,这些书籍制作于寺院的缮写室之中,带有丰富的、因为美丽而得到人们珍视的装饰和图像。和一些人假想的不同,这些珍贵写本中的绘画几乎不可能是为了指导文盲而设计。同抄手一样,僧侣艺术家并没有酬劳,一般来讲他们的作品也不会去出售。它们是对漂亮形式和色彩的喜好的一种自然产物,是艺术灵感的结果。这种存在于宗教环境之中的艺术灵感,以基督教崇拜所设定的各类任务作为契机[3]。它们呈现了无数自由想象的个案,通过这类想象,艺术家得以“宣泄”各种欲望与恐惧,而完全不受作为这些情感表达载体的物品的宗教性质所桎梏。当主教、修道院院长或教士向僧侣或受雇的世俗匠人定购一件作品时,他们通常不会对装饰的特色作任何规定。在某些情况下,主教或院长本人就是艺术家。罗马式与哥特式建筑上的很多石作雕塑,尽管是由教堂定制,但却并不具有明显的神学意义。大量同时期的文献提及过艺术品新作的魅力与想象力。通过这些创作,一所教堂会显得更加漂亮、更加令人难忘,而它的声名也因此变得更加显赫[4]。
“在希腊罗马世界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大多数有创意的绘画和雕塑都是服务于一个明确目的的定制品。”
艺术品上大量的签名和题记说明,这一时期的艺术家对他们自己的创作能力有清醒的认识,而且认可他们成就中的个人功绩。我想引用一个个案来证明,即使在主顾的严格掌控之中,中世纪艺术家仍然会保有他的自尊。在米兰圣盎博罗削教堂(S a n Ambrogio church)的金色大祭坛上,那位9世纪的雕塑家不仅签上了自己的名字“Wolvinius magister phaber”(制作大师沃尔维纽斯),而且还在与定制了这处祭坛的安吉尔柏图斯(Angilbertus)大主教的圆形浮雕像相对称的图像中,将自己表现为正在被教堂的圣徒守护神加冕。在画面中,安吉尔柏图斯正将祭坛奉献给圣安布罗斯,而后者则在为此施主加冕[5]。
埃文认为:文艺复兴之后赞助人至少从两个方面逐渐地背离了这种赞助人与艺术家的理想型关系。他们或者是扮演了艺术家“雇主”的角色,或是扮演了类似于“客户”的角色。无论是哪种情况,对理想型各种形式的背离,都破坏了艺术家的自主性。作为一个“雇主”,赞助人会觉得,根据正式或非正式的合同关系,他有权对艺术家最终成品作出明确规定。他认为他不仅有权决定受雇人应该做什么,而且还有权决定他如何去做。在前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确处在类似受雇人的一个位置;实际上,他们通常被称为“匠人”而不是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受到教会和行会规定的严格约束[6]。
中世纪与后文艺复兴之间,艺术家受制于赞助人,这一叙述与某些历史学家的观点相吻合,埃文可以引用近期的一些著作作为其叙述的权威支撑。文艺复兴被埃文描绘成自主艺术家自发性的一段插曲。不过,正如我已经阐明的,在文艺复兴时期,许多存留至今的合同证明,画家们会接受那些最为详细的规定,这些规定的约束力同那些左右了众多中世纪艺术品的规定相比,并不逊色。当然,艺术家会独立地制作一些作品,但是大多数重要的文艺复兴绘画和雕塑都是定制品,是为了一些富有、权重的个人或团体而作。拉斐尔或米开朗基罗的非定制作品,就极为稀见[7]。
然而,在这一时期或者此前及此后的各时期,对于定购的依赖并不意味着“对艺术家最终成品作出明确规定”。没有一个外行人能够做到这一点,甚至艺术家本人也无法事先“明确地”说出最终成品是什么样子。如果说合同规定了题材、尺寸、边框特点、如何使用金色和上等色彩、人物的数量,以及同相邻作品的关系,那么在如何让成品具有符合时代审美品位的事项上,合同却只字未提或者极少提及(那种整个作品或部分作品由大师而不是他的助手来制作的规定除外)。即便赞助人罕见地要求某种特定风格的时候,这种诉求也不过类似于要求一曲音乐应该采取某种调式,要求一首诗应该是田园诗还是挽歌,要求一幢建筑应该是托斯卡纳式还是多立克式——艺术家将它们作为内在于他们技艺之中的传统任务,愿意满足这些要求,并且具有满足这些要求的必要技巧。原则上,聘请一位艺术家来创作一件预期的作品,已经是对这个人创作方法的认可,已经是对他用自己那种令人尊敬的方式去实现定制计划的能力充满信心的表现。1647年,当普桑的赞助人尚特卢向画家抱怨,说普桑为他创作的这幅画没有艺术家为另一位赞助人所作的画那么赏心悦目时,普桑答道:这正是你所要求的。他解释说:实际上,题材和尚特卢的性情是产生这一差异的原因。他为尚特卢创作的这个题材,需要用另外一种表达“调式”(他将此比作音乐中的各类调式)进行表现,这样才可以彰显它的特色[8]。
17世纪的一段非凡轶事,可以更加清楚地让我们了解画家同赞助人之间的种种关系。它讲述的是那幅现已广为人知的、注视着荷马半身像的亚里士多德,它是伦勃朗为西西里贵族安东尼奥·鲁福(Antonio Ruffo)所作的画。这个赞助人想为此画制作一幅对称图像,因此雇请一个意大利大师圭尔奇诺(Guercino)来提供第二件作品,以与伦勃朗的画相配。他要求这个意大利人使用他过去的风格来创作,这个风格与伦勃朗的风格十分接近。圭尔奇诺这时的创作采用了一个更为古典的样式,但在开始阶段,他却是一个以强烈的光影为特点的画家。圭尔奇诺对此表示同意,并制作了一幅与伦勃朗作品配对的画作。我们只是从存留下来的一幅草图才得知,此画描绘的是正在触摸一个星球体的天文学家。圭尔奇诺应该不会觉得伯爵的这一委任是对他自主性的一个伤害。相反,从他的信中我们了解到,他非常高兴能被邀请来创作一幅能与他敬慕的艺术大师伦勃朗的画作比肩而立的作品[9]。
真正引起艺术家与赞助人或客户之间摩擦的,是艺术家众所周知的拖延交货。有很多文献说到了艺术家过久的延迟和赞助人的焦急。有些作品因为艺术家接受的新定制而被中断,以至于拖延数年。赞助人通常会以分期付款的方式预先支付给艺术家,希望他能以一个债务人的身份持续工作。但在另一方面,赞助人也经常会拖延支付已完成的作品。在艺术家写给他们的赞助人的许多信件中,艺术家会提醒赞助人尚未交付的债务[10]。
所谓“在前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确处在类似受雇人的一个位置”,因为“他们的作品受到教会和行会规定的严格约束”的说法,完全没有抓住事情的要领。作为“工匠”,他们有自己的工具,他们是“师傅”,有时会拥有一个大的作坊,雇用许多助手和学徒;各种行会是他们的组织,他们在其中任职。在解决同主顾的争端的时候,调停人通常就是艺术家。雕塑家和画家几乎不会觉得委任他们的条款中教会的详细要求,或者是其中的技巧准则及行会设定的质量标准,是对他们艺术自由的侵犯,这就和今天的工程师不会认为那些对其所做工作的种种规定是对他的职业自由的限制是一个道理。但在另一方面,也有伟大的布鲁内莱斯基所经历的事件:因为他没有交会费,行会对他所签署的建构佛罗伦萨大教堂拱顶的合同提出了异议。佛罗伦萨官员强迫行会放弃这一异议。在此,问题的关键不是艺术家是否可以使用他自己原创性的手法去自由设计一件作品,而是他是否有权从事这一工作[11]。
作为“客户”的赞助人,“可以说完全听凭艺术家的摆布,希望艺术家作为一个有能力的‘职业人’,可以提供给他最好的服务”[12]。而文艺复兴意义上的赞助人则不要求艺术家任何具体的事情,只是为后者提供“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追寻艺术灵感的自由”。对我来说,埃文在“赞助人”同“客户”之间所作的这一区分,完全是出于想象,毫无历史根据。如果今天从一个画家或雕塑家那里定制了作品的人,无法确定最终结果如何,这并不是因为他没有追随文艺复兴时期的赞助人,给艺术家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从而破坏了在旧时代确保艺术项目成功的那一自主性。我们知道,文艺复兴赞助人的确会给艺术家提出一些具体要求,而且他们有时会对结果感到遗憾。和现在一样,对于建筑师的“客户”而言,总有建筑师会利用低级材料来进行创作的危险。
文艺复兴时期的赞助人一般不会去支持艺术家根据“为艺术而艺术”的理念,自由地“追寻艺术灵感”。他是艺术家的一个有权势的客户,他用钱雇请艺术家为他制作一些具有一定特色和范围的特定作品;除非材料和人工花费(这其中包括作坊里助手们的人工费)以合同的方式得以事先保证,否则艺术家无法从事这项工作。这些作品是赞助人的财产,在一个将艺术物品视作财富、权力及文化的标志的社会中,赞助人凭借它们(无论他收藏这些作品,还是将它们交给教会)来获取声望。
当然,也有一些对艺术家个人感兴趣,以至于与他产生了真正友情的赞助人。例如,瓦萨里就记述过,佛罗伦萨人马尔泰利(Martelli)曾邀请年轻的多纳泰罗到他家中客居。但这只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特例,并不影响那一时期艺术家与赞助人之间典型的经济与法律关系,就好像19世纪众多年轻门徒的例子,并不能改变绘画是为一个公开竞争的市场而作这种一般特征。在过去数百年,也有这样一些现象:某人会在对艺术的纯爱的鼓舞下,用全无目的的慷慨去支持一个画家(更多情况下,去支持一个诗人或作曲家),这完全出于他对他们之间关系的一个理想化的理解,他也完全不会考虑通过与艺术的联系或者是通过占有宝贵的艺术品来提升自己。更为常见的是:偶尔会有赞助人通过购买年轻或不知名艺术家的成品的方式,以此来表达他对这个艺术家的信心。我们通常会在所谓当下艺术赞助的关系中,遇见到各式各样建立在固有价值观基础之上的志趣,也就是那些充满热情的文化“门外汉”们的所作所为。著名的喀斯乐伯爵(Count Kessler)就曾经为他的个人收藏定制作品,发表带有艺术家插画的书籍,他也由此加入到了艺术运动之中。“在前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确处在类似受雇人的一个位置;实际上,他们通常被称为“匠人”而不是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受到教会和行会规定的严格约束。”
但即便是这类赞助关系也是极为罕见的。我可以大胆猜想,如果在这个国家有2万人可以被称作职业画家和雕塑家,他们之中只有不多于100人,或者说只有50%的人可以受到一个毫无所求的赞助人的持续支持。在这里我没有包括那些在确立了自己原创艺术家的地位之前的早期生涯中受到家庭支持的学生和年轻艺术家。
在另一方面,在今天的艺术界的确存在一种赞助体制,它提供给艺术家长期支持但却并不规定或者定制任何特定的作品。这就是艺术品商人和艺术家之间的关系:前者同意每个月支付给艺术家一定的金额;作为交换,艺术家将交给艺术品商他所有的作品或一定数量的作品。艺术品商和艺术家共同决定这些作品的市场价值,这一价值与预付的金额相当。这类协议有赖于艺术品商的信心和期望——他认为这是个好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很快就会为人所知。假如结果让他失望,他就不再会续约。通常,这类合约中会包含一条,约定合同期间艺术品商有独家展览和销售艺术家作品的权力。画家不是艺术品商的雇员,他也不是服务于艺术品商的一个职业人。这是两个事业人之间的关系,其中一个是商人,另一个是生产者。在某种意义上,后者类似于将商品批量卖给零售商的工匠或生产商,但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今天的艺术家自由而且富有创意地生产,无需考虑如何让他们的产品去适应一个特殊的需要;由于他们不断试验有关形式和色彩的新理念,他们总有失败的危险。
还有另外一种体制,在其中艺术家同意只通过一个特定的艺术品商来展览和销售他的作品,他偶尔接受一些预先支付,来完成进行中的作品。即使没有这些预支,艺术家也一样会在这类同艺术品商的关系中,找到一种安全感,因为这个商人不仅会举办他的个展,而且会向客户长年持续地展示他的作品。艺术品商通常在取得艺术家的同意后,来决定作品的价格。他自己会提取销售价格的三分之一或更多。艺术品商支付展览图录、广告、保险和储藏的花费。当然,他还负责租用画廊及其工作人员的开销。对于那些不那么知名的画家,艺术品商可能会要求更大份额的回报。
这种契约关系有相当多的局限和困难。艺术品商可能会对艺术家感到失望,这或许是因为后者制作的作品过少,或许是因为他的作品质量没有达到预期标准。艺术家可能会否定画廊的样子或所处位置,他可能不赞同宣传的方法、客户的来源、艺术品商的个性和他的精打细算。他可能会觉得,艺术品商更偏爱同一画廊中那些成功地吸引了买家的其他艺术家;他会因为其他人的作品遮蔽了他的作品,而感到沮丧;这或者是因为那些作品画得更好或更糟,或者是因为它们使用了一种他并不喜欢的风格。所以说,在这种艺术家与艺术品商自主选择的关系中,存在有相当多的紧张状况。一般而言,一个艺术家渴望遇到一位真心敬佩他的作品、即便作品销路不佳但仍旧一如既往地展示它们的艺术品商。当艺术家改变了风格,正在探寻或试验而毫无真正意义上的产品面世时,这样的艺术品商完全不会有异议。他那种高贵、新颖且极具个人特点的公众形象恰好迎合了艺术家的想象力与品位;这样的艺术品商一定尊重艺术家的个性。有一些艺术品商人,对他们而言,艺术品商业是一种真实的个人表达,是他们加入到那个引人入胜、令人激动的原创艺术家世界的一个手段,他们会与这些艺术家保持长久的友谊。这类艺术品商并不常见(我可以举出与我相识的几位——D.H.坎魏勒、柯特·瓦伦丁、J.B.诺依曼和贝蒂·帕森斯);由于画廊为他们提供的帮助不同,大多数艺术家对艺术品商的态度,可能是宽容的,但也可能是怨恨的[13]。
在所有这些关系中,有一个特点是恒常不变的:艺术家是一个拥有属于自己的劳动工具的制造者,他自己为全部产品负责,这里没有劳动分工的问题。(对于雕塑家和平面艺术家来说,有时会有复制技工的合作,比方说铸工、铸造工或者是印刷工,但最终的产品却被视作出于艺术家之手。)就这点而论,作为中世纪手艺人的一个奇异幸存者,他代表了现代社会中的一个特例[14]。虽然他为一个并不确定的市场而制作,但是却有下面这个想法来做支撑:如果他能成功,那么他就会在金钱和社会地位上获取极高的回报,这一回报将远远高于古今任何一个手艺人所能取得的。由于他的作品的价值估摸不定,也由于他必须经常在作品毫无销售希望的情况下长时间工作,他的职业就成了一个不稳定的职业。这种情况决定了艺术家一些特有的外貌及行事特点,或者说这种情况至少可以解释和支持他们的这些特点:他的孤独感,他对边缘人物的同情,他举止的随意,以及他在道德和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中所拥有的更大自由。
根据这样一个关于艺术家、赞助人、艺术品商和市场之间复杂关系的叙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科学家同其雇主或机构的关系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除了数学家(或许还有理论物理学家)之外,科学家需要昂贵的研究设备、实验室、图书馆以及技术人员,这就使得他的工作变成了一项集体任务的一部分。通常,这一任务有严密的劳动分工。不同于作为独一无二的艺术品的图画和雕塑,他的产品不是物质产品,而是一些对共有知识库的贡献。其他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决定了这些贡献或者被共有知识库吸收,或者被它拒之门外。他的成果一旦发表,除了工资的增长之外,将不会带来任何经济利益,除非成果中包含一些可以用作商品或经商方法的专利内容。更接近艺术家的,是那些老派的发明家,他们独立工作,希望具有市场价值的单项成果能够带来高额回报。与此相反,过去几代的科学家是教师、大学教授,或者研究实验室、研究所的雇员。这种职业选择,确保了他拥有一个稳定安全的生活来源。他自己是支持他工作的那些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倘使没有他,这些机构将无法生存。在研究组织或研究行业中工作的科学家,或许更像是那些掌握了一种罕见的技巧,并将此技巧用于销售的商业艺术家。他们与那些在市场上售卖成品,而不是售卖技巧或劳动力的“审美”或“纯”艺术家,没有可比性[15]。
如果我们这个社会的政府、产业和基金会扮演科学赞助人的角色,不去设定明确的任务,允许科学家自己去选择课题,那么他们就是在做一件在艺术领域里从未大规模尝试过的事情。在艺术界,这类赞助人在过去只是些孤立、少有的个体而已。在一些小国家,如果一个艺术家被视作伟大的天才,并且为国家带来了荣誉,那么他有时就会被赠予一间画室和一份补贴。但这并不是一个可以用于所有艺术家的范式。将科学当作一个需要支持而且值得支持的商品的想法,是文化的产物,而不是经济谋划的产物,尽管经济谋划使得这一想法更为普及(而且这一想法通常掩盖了背后的经济谋划)。
在某种程度上,被埃文描绘成理想型的赞助人/艺术家以及赞助人/科学家关系,在苏联存在;在那里,国家支持基础研究及艺术,但并不设定明确的任务。人们假设,因为艺术家认同政府的艺术构想,所以他并不会被这一构想所限制。据称,他的“艺术灵感”与国家需要相吻合,就如同文艺复兴的画家们的艺术灵感同他们那些热爱艺术的赞助人的观点相吻合一般。然而,尽管俄国有基础科学和高科技的产出,但是我们已经见证到,在过去的30余年,这种有组织的赞助体系是如何限制了艺术家的自由,它又是如何将俄国绘画变成为国家工具——作为艺术毫无生气,但在传播官方信仰方面,或许有用。不过,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的最初几年,俄国绘画和雕塑沿着之前10年的前卫艺术道路,曾一度站在欧洲创意艺术的最前沿。由于国家的支持,许多前卫艺术家对革命感到欢欣鼓舞,而且在作品风格上也没有受到统一意识形态的限制[16]。
注释:
[1]本文选自迈耶·夏皮罗(M e y e r Schapiro)所著《艺术的理论与哲学:风格、艺术家和社会》一书(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凤凰文库》艺术理论研究系列)。
[2]William M.Evan,Role Strain and the Norm of Reciprocity in Research Organization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LXVIII (1962),第346-354页,特别是第351页及其之后数页。
[3]关于寺院中制作这些昂贵的插画写本的问题,参见E.Lesne旁征博引的著作Histoire de la propri ét é ecclésiastique en France, IV:Les Livres(Lille: 1938),特别是第80页及以下,第319页及以下。关于运用金银的作品,另参见 Vol.III,glises et trésors des églises (1936), 第180页及以下。
[4]关于中世纪的这一特征,参见我的文章“The Aesthetic Attitude in Romanesque Art”,Art and Thought,Essays in Honour of A.K.Coomaraswamy(London: 1947),第130-150页;同时参见Art Bulletin XLV(1963),第351页及以下。
[5]参见Arthur Haseloff,Pre Romanesque Sculpture in Italy(Florence and New York,无出版年月,约1930年),第64页及图版72。
[6]参见[2]引文,第351页。
[7]关于文艺复兴的艺术家和他们的赞助人,参见Martin Wackernagel,Die Lebensraum des Künstlers in der florentinischen Renaissance,Aufgaben und Auftraggeber Werkstatt und Kunstmarkt(Leipzig: 1938);关于从古希腊到1800年期间的这类关系,见R u d o l f a n d Margot Wittkower,Born under Saturn:The Character and Conduct of Artists: A Documentary History from Antiquity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New York: 1963)。我曾在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I(November 28,1963,第7页)上评论过后面这本书。
[8]Lettres de Poussin, ed.Pierre du Colombier (Paris: 1929), 第239、240页。[9]关于此轶事及圭尔奇诺的信,见Jakob Rosenberg,Rembrandt(Cambridge,Mass,1948),I,第165页及以下。
[10]见Wackernagel上引书,第344、350、355、357、370页及以下;Wittkower上引书,第35页及以下,第40页及以下(关于“艺术家的迟缓”),第59页及以下(关于“具有创意的懒散”)。弗洛伊德将列奥纳多创作时的迟缓解释为一种神经症。在此点上,这些记载值得我们牢记。这是一个比弗洛伊德所预想的要远为常见的行为特点。如果人们认为列奥纳多比其他艺术家在交货时更为迟缓,那么下面这一点也是事实:比起文艺复兴时期任何一位艺术家,或许比起任何时代的任何一位艺术家,他留给我们更多的文字作品、更多的科学观察以及更多的技术创新。
[11]1434年,石匠与木匠行会因为布鲁内莱斯基所欠的债务,拘捕囚禁了他;当时他是大教堂的建筑师。这项工程中的当权者很快将其释放,并且囚禁了行会官员作为惩罚。(见Wackernagel上引文,第308页)
[12]Evan(埃文)上引文,第351页。
[13]对艺术品商与艺术家之间关系感兴趣的读者,会发现下列著作非常有启发性:Venturi,Les Archives de l’Impressionisme, 2 vols (Paris and New York: 1939),此书包含有印象派艺术家与他们的艺术品商杜兰德·吕埃尔(Durand Ruel)之间的通信;凡·高《书信集》,主要是写给他的弟弟艺术品商提奥的信;Ambroise Vollard,Souvenirs d’un marchand de tableaux(Paris: 1937);下面这本书,对于当代艺术尤为重要,Daniel Henry Kahnweiler,Mes galléries et mes peintres.Entretiens avec Francis Crémieux(Paris: 1961)。此书富含关于立体派画家的叙述,坎魏勒是第一个真正理解立体派画家的支持者与代言人。
[14]我在《艺术新闻》(Art News,Summer:1957)中讨论过艺术家的这个职业特点。
[15]大企业从著名艺术家那里定制作品的做法是些例外。为了宣传它们的产品,美国装箱公司曾雇请画家和雕塑家来创作艺术品,用以阐释西方某一位重要思想家的一个哲学表述。一些艺术家对这类项目表示欢迎,但这些个别事件对艺术实践或艺术市场的运作并无影响。
[16]参见Camilla Gray,The Great Experiment: Russian Art 1863—1922(New York: 1961),第215页及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