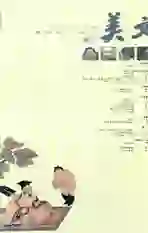从岩石区开始
2016-10-31吴树乔
称呼
2011年11月底,我去欧洲旅行。离境的前夜住在上海,那天刚好是我的生日,所以记得比较清楚。线路是罗马进巴黎出,中间在瑞士还有几天的游程,因为先在意大利转了好几天,到瑞士小城卢塞恩(也称琉森)大约是12月初了。卢塞恩是个非常漂亮的小城,位于瑞士中部,市区人口只有7万人,号称是瑞士最美丽、最理想的旅游城市。我和妻子本想先游览景区,怕迟了光线不好影响拍照。但是导游说要统一先去买手表,剩余的自由活动时间再去游览。
就先去买手表。一路上看整个卢塞恩好像全是中国游客,听到的都是中国话,跟在国内似的。进了手表店,一位长着褐色头发的年轻人快步朝我走来,“领导请跟我来!”他的中国话说得还不错,但他管我叫领导让我很不舒服。一个洋人不叫我先生却叫我领导,这让我想起了许多别的事情。我不知道他是跟人学的还是他自己觉得就该这么叫才讨人喜欢,我宁愿相信他压根儿就不知道“领导”是什么意思,只是听人家这么叫他也跟着瞎喊。这件事情一直影响我的整个行程,时不时地就想起中国人的称呼。
我想起我姐夫跟我说过的一件事情,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把话题扯远,而是一路上老在想这件事儿,竟然没有心思看风景了。我姐夫是某地级市的中级人民法院的刑庭法官,但是庭审中嫌犯们竟然异口同声地称呼他“江政府”。我姐夫姓江他们不叫“江法官”却叫他“江政府”,我想,在看守所里,嫌犯们肯定是有交流的。怎样称呼,法官比较受用,他们心里有数。法官高兴不高兴也许与他们将来的刑期长短有着微妙的关系。有些人觉得自己就是政府,心里也许比较满足,当然称呼也不能叫过了头。
我以前经营着一家小工厂,被一些部门刁难那是常有的事,我当然也学会了各种恰到好处的称呼。来查暂住证的明明是个协警,我一定是要称呼他为警官的。有一次厂里被盗,我去报案,接警的是位协警,那时孤陋寡闻的吴树乔竟不知何为协警,一看他穿的不是警服,便称他为保安。那年轻人马上就发火了,谁是保安?我是协警!这时屋里的一位真警察出来了,问我什么事。我说厂里被盗了,损失约八万元。他说,可见你工厂里的安保措施一塌糊涂,造成这样的局面我们是要追究你的责任的。我虽然觉得荒唐,但我一点也不怀疑惹火了他将会把我铐在这里。于是,我一边点头一边后退,然后转过身夹着尾巴逃跑了。
税务所的来查账,尤其是临近年底的时候,他们会来要钱,有时候说是今年税收任务没完成,要我再拿几万;有时候会说政府今年花费比较大,要我们自觉再出一点。我做企业后才知道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依法纳税,多半都是依需纳税,政府需要多少我们就缴纳多少。我试探着称呼他们为李税务官、张税务官。观察他们的表情,似乎对于这样的称谓还是比较接受。也有一些部门的让我犯难,不知怎么称呼他们,比如工商所的常来工厂检查,有时候突然就来,也没什么规律。如果称他们陈工商、王工商,似乎不怎么恭敬,并且还有调侃的嫌疑。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我姐夫的故事,就装傻叫他们所长。陈所长王所长地叫,没想到他们还挺高兴的。
我的工厂是生产眼镜配件的,曾经有位客户就是工商所的。我至今也没弄明白一个工商所的公务员,怎么又当起恒盛眼镜公司的老板?肯定是有能耐的人。我当然是要称呼他陈所长,可后来一打听这陈所长陈纪国还真是某工商所的副所长。大约是2000年的时候,他开始到我的工厂拿货,当然是赊账。我每次拿着出库单去他公司结账都会被他婉转地回绝,总是叫我再等几天,一直等到2005年的春节前夕,才把出库单换成了一张欠条,这欠条直到现在还在我手上,永远也不可能变成货款了。陈所长因为有一点小权而拿货不给钱,我不知道他公司的产品是否都不用成本?
我想,如果我们这个社会总有一些人惧怕另一些人,一些人百般讨好另一些人,那就让人没有了幸福感,这让生活平添额外的痛苦,与和谐社会不相容。更为令人沮丧的是国人的弱点被洋人识破,为了利益,他们知道怎样恭维中国人,而许多中国人面对洋人的恭维一定是非常享受的。
从岩石区开始
岩石区是悉尼最热闹的区域之一,它位于悉尼大桥南岸,和悉尼歌剧院很近,只隔了一个很小的海湾。在悉尼,这样的小港湾到处都是。岩石区最早的建筑物,都用当地的砂岩建造,岩石区也因此而得名。岩石区是澳大利亚最早开发的区域,第一个自人殖民区,这一殖民区最初是英国政府流放囚犯的地方。英国历来都是把罪犯流放到很远的地方,远离英国本土,也许他们认为这样有利于国家的安全。库克船长发现澳洲之前,英国政府一直将犯人押往北美殖民地,1776年7月4日在北美十三个原英属殖民地代表会议上,一致通过了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宣告了北美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随着美国的独立,也就永远地结束了北美流放地。1788年,菲利普船长一行押着第一批英国罪犯在这里登陆,从此开始了新的殖民。这支舰队在海上漂泊了半年多才来到悉尼的岩石区,船上共载1478人,其中750名囚犯,其余的是军人、狱卒,此后不断有罪犯被送到这里。我们不能想象二百多年前,还没有柴油机,仅靠风帆竟然能从英国来到南半球的澳洲。要知道现如今从悉尼到英国坐飞机得24小时呢,而那时他们要漂泊250天,那海上的日子肯定不好过。我想,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不管是军人还是囚犯,他们同样面对着磨难,体质差的、扛不住的一定死了不少,能最后抵达岩石区的都是强壮的、有活力的生命。现在我们看到的澳洲白人也许遗传了先辈的基因,体格强壮而长寿。
游历澳洲之初,曾经有那么一刹那,我的脑子里闪过了他们是罪犯的后代这一想法。但马上我就为自己的阴暗心理感到自责,如此类推,美国人亦然乎?可见出身论的余毒在我的体内尚未完全清除。现在他们悠闲而尊严地生活在这片他们自己开辟建设的土地上,国富民丰少有生存压力。在菲利普船长一行登上悉尼岩石区整整二百年后,在布里斯班市举办了第三十四届世界博览会。1988年世博会的举办地“南岸公园”里,延绵数百米的花廊贯穿其中,那花便是当年世博会留下来的厦门市花三角梅。我去的那天晴空万里,风和日丽,阳光特别明媚。在这花廊的两旁,排列着许多的烧烤炉,这是政府免费提供的,用电,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不锈钢的台面同时也是铁板烧的平底锅,大约两米乘两米见方。当地人一家子,或是一群年轻人围坐在四周,一边烧烤一边喝着酒,极惬意。要知道,当地的海鲜和红酒都是非常便宜的,超市里有卖的那种红色大虾,也不知叫什么虾,反正很好吃,已煮熟的卖8块澳元一公斤,而红酒只要5、6块澳元一瓶,口感非常好。据说他们的平均工资为三、四千澳元。我看他们烧烤的是这种大虾和其它海鲜,喝的也是红酒。当他们吃完了以后,会自觉把垃圾清理干净,并且把这不锈钢的台面擦拭得光可鉴人,以方便别人使用。
我特意去按了按那不锈钢的台面,估计有0.5毫米的厚度。我是做机械和钣金出身的,我想如果有人用餐刀或是叉子敲击台面,是一定会留下无数小坑的,但那些台面都平整如新。我就想不通,怎么就没人悄悄把它拆了去卖废铁,拆不了台面把电线剪下来卖总不用费多少力吧,可就是没人做这种事。那个导游小姑娘刘畅告诉我,在澳洲的公共休闲区这样的烧烤炉随处可见。我在心里感叹:这些罪人的后代啊!
在澳洲旅行了十来天,好像从来也没遇见过一个警察,所以也不知澳洲警察的装束是什么样,我在悉尼塔附近的街道上瞎逛时,但见整个街区交通繁忙,车辆如织。满大街竟然找不到一个警察,但却秩序井然。控制红绿灯的按钮在路口的灯柱上,行人要过马路得自己按一下。我突然想起有好几天未闻警笛声了,颇觉不适。细想澳洲怎么没有警车呢?
后来在玫瑰湾游览的时候,终于在道口发现一个警察局。全世界的警察局都会醒目地标着police,很好认的。导游说这个警察局只是一个摆设,很是不解导游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彼时大家都被玫瑰湾的景色迷住了,正在扎堆拍照,港湾里泊满了豪华游艇,海水比天空更蓝,并且清澈得能看见鱼在游弋,海风中闻不到一丝腥昧。岸边树木葱茏,豪宅掩映其中,这是悉尼的富人区。这会儿导游正闲着没事,我又提起刚才的话题:这警察局怎么就成了摆设?他笑笑说:这个警察局原先配备了好几名警察,后来因为没人报警而无案可办,整个警察局被削减得只剩下一名警员,无事可做又没人说话,无聊得很。最近有市民投诉:不能拿纳税人的钱养一个闲人,于是有议员提议撤销这个警察局。按照程序,一旦议会通过了这一议案,市长只能照办,因为官员只是纳税人花钱雇来管理这座城市的,他本人没有一点特权,不能代替市民做任何决策。看来这唯一的警察也快失业了。
面对此等奇闻,我愕然无语!
加里波利的墓地
飞抵伊斯坦布尔的当天就来到了达达尼尔海峡,这里是土耳其的西北部。加里波利是土耳其爱琴海畔欧洲部分的半岛,对面是亚洲部分,中间只隔着不是很宽的达达尼尔海峡。车子往渡口去的路上,那个能说一口字正腔圆汉语名叫琳达的土耳其导游,指着远处山顶上的一座建筑说:那是恰纳卡莱之战纪念碑,那里埋葬着1915年4月那场战争阵亡的土耳其士兵以及入侵者澳新军团战死者的遗骨。这处战争遗址并不在我们的游程之内,所以我没有亲眼看见这个著名的纪念碑上土耳其之父凯末尔所写的铭文。
从土耳其回来后,我没有去写我看过的其他一些著名的景点或是遗址,比如特洛伊、以佛所、圣索菲亚大教堂、蓝色清真寺,这些都是极富历史沉淀的所在,而是一直牵挂着加里波利墓地。我想,这可能是那里共同埋葬着交战双方阵亡将士的遗骨,这让我觉得有些匪夷所思:月黑风高之时,这些亡灵不会争吵打斗吗?他们难道不是互为敌人吗?我感觉这一事件打乱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对事物的习惯性思维。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回国后马上查阅了有关这场战争的资料,又额外获取了一些信息。加里波利之战是英文的说法,土耳其语称之为“恰纳卡莱之战”。1915年4月25日,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协约国的英法联盟策划了这次海军行动。他们闯入达达尼尔海峡,企图打通博斯普鲁斯海峡,然后占领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这场海战的始作俑者就是后来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令他没想到的是,登陆时遇到了奥斯曼陆军上校凯末尔率领部队的拼死抵抗。战役持续了9个月,总共造成50万人的伤亡,凯末尔的部队几近全部战死,但最终守住了阵地。
还有一个故事值得我们去回味:交火中一位名叫默罕默德的土耳其士兵,将一位名叫约翰的协约国伤兵抱回到敌军阵营,以便敌军的救护队能够及时地抢救他的生命。这则拯救敌军士兵的故事,后来被制成雕塑,矗立在昔目的战场上,成为永久的纪念。我这样说不是要宣扬这场战争,我只是赞誉战争中的人道主义情怀。
是的,这让我联想起了美国的南北战争。这篇短文的篇幅有限,就只说战争的结束吧。战争后期,南军败局已定,南方联军司令罗伯特·李将军已经在考虑投降的事。但此时军队和民间出现了一种呼声:把军队化整为零融人民间,用持久的游击战来继续和北军对抗。李将军断然拒绝了这种将战争导入民间、把南方变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的做法,他认为那是对人民生命不负责任的举动。
李将军给北军司令格兰特将军送去一封信,要求会面商谈投降的条件。几个小时后,当格兰特将军见到令他尊敬的敌军司令李将军时,生怕伤害到这位老军人的自尊心,一直在叙旧,始终不愿提起投降的事。最后还是李将军开口,格兰特将军,我想,我们这次会晤的目的是非常清楚的,我要求你提出接受我们投降的条件。格兰特只说了,军官和士兵放下武器。当他看到李将军身上的佩剑时,他认为没有必要解除老将军的佩剑,于是又说,这不包括军官的马匹和私人物品。当李将军读完那份《投降协议》后沉默了一会儿,有一件事,我们的骑兵所使用的马匹都是他们自己的,能否让他们保留,以便回到家乡继续用于耕作。格兰特非常大度地说,我将告诉我的军官们,允许所有声称拥有自己马匹和骡的人把他们的牲畜带回家,为他们的小农场效力。李将军告诉格兰特:我那边大约有1000名北方军战俘,已经好几天没东西吃了,因为我的士兵也同样没有食物。格兰特找来他的军需官,命令他向南军提供足够所需的食物。
李将军和格兰特将军共同签署了投降协议,然后握手言和。格兰特目送李将军走出这间屋子,这位不再是南军司令的老军人,穿着整齐的灰色军服,腰上系着鲜红的腰带,步履有些蹒跚。北方军鸣响大炮庆祝胜利,但立刻被格兰特将军制止:“他们曾经是叛军,但现在又是我们的同胞了,我们不羞辱他们的失败,就是对我们胜利的最好表达。”
但是,众所周知,南方联军所代表的是奴隶主的利益,难道他们不是反动派、反革命集团吗?令我不解的是,反动集团何以能够与林肯总统为代表的北方革命派一笑泯恩仇?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没有一名俘虏,也没有一个人因战败而被关押。相反,今天的美国,在葛底斯堡国家烈士公墓以及其他城市,都可以看到李将军的雕像,美国人视他为最伟大的将军。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恰纳卡莱那块著名的、最具人道主义意义的纪念碑吧,上面镌刻的是土耳其之父凯末尔1934年发表的一段著名的讲话:
“献给那些流血牺牲的英雄们,你们现在躺在友邦的国土上,在和平中得以安息。在我们的国家,在我们的脚下,肩并肩沉睡着的无论是约翰们还是默罕默德们,都无任何区别。
你们,母亲们,送子远离故土参战的母亲们,擦干你们的泪水吧!你们的孩子们如今沉睡在我们的家庭里,非常平静。在这片土地上牺牲了生命以后,他们就成为我们的孩子。”
凯末尔把死去的敌人都看成是自己的孩子,这需要多大的气度。我想,只有如此胸怀,方能化干戈为玉帛。
美国著名的歌手,今年七十一岁的音乐创作人,同时也是诗人的鲍勃·迪伦说过一句极其经典的话,我不能完全记住他的原话,但大意是:一个政权的好坏,不在于它如何对待那些有功之人,而在于它如何对待那些有罪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