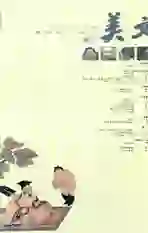美国记事(二)
2016-10-31王陌尘
王陌尘 原名王向晖,江苏泰州人。北京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在《中华读书报》《北京日报》《中国文化报》《中国文化研究》《随笔》等刊物上发表文章。著有评论集《倔强的拇指》《商业时代的英雄情节》等。曾任教美国,现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
沙漠罂粟——拉斯维加斯
从大峡谷往西,车像开进了新疆的沙漠、戈壁,满眼望去一片枯黄。黄色的沙石裸露地表,贴地趴着一些干枯的毛毛草;偶尔冒出些仙人掌、灌木,也都孤军奋战,与头顶毒辣的日头争夺最后的绿意。大巴载着一车被沙漠单调风光折磨得精神疲倦的旅客,在望不到尽头的沙海中飞奔。路上车很少,走一两个小时到休息站才看到人烟。大家很庆幸不是自驾游,不然车出了故障真就被抛弃在荒野了。导游提醒大家不要小看了这条不起眼的公路,这是号称美国“公路之母”的六六公路,是当年人们往西拓展的重要通道。
我想起美国作家约翰·史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长篇小说《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中有关六六公路以及公路上寻求新生活的人们的描述,特意找出来插进本文中,重展作家当年描写的史诗般的画卷:
“六六公路是主要的移民路线,是逃荒者的路。为了逃避风沙和日渐缩小的耕地,逃避轰鸣的拖拉机和日渐缩小的土地所有权,逃避沙漠北侵的威胁,逃避风灾和水灾,人们从各条支线,从大车走的上路和崎岖的乡间小道来到六六公路。”“六六公路是干道,是逃荒的路。逃荒的人在六六公路上川流不息,有时候是单独的一辆车,有时候是小小的车队。在那些超载的旧车上,司机一路提心吊胆地倾听着车子的种种音响。如果响声或者节奏起了变化,说不定会在路上停个把星期。但愿这老爷车别在到达加利福尼亚以前完蛋。”
当年人们从美国各地奔向加州,因为那里发现了黄金。他们都和《愤怒的葡萄》中约德一家一样,像一群信念执着的乌龟,渴望从六六公路爬向富裕的天堂。事实上靠淘金暴富的美国人毕竟是少数,美国人了不起的是即使在沙漠中他们也能找到创造财富的机会。在美国人的价值观中,发财是硬道理,他们从来只要结果,不管方式。所以六六公路在往西延伸的途中,又开成了两条淘金之路,一条从胡佛水坝通向拉斯维加斯,另一条则延伸到旧金山。有人把拉斯维加斯当作一个聚宝盆,认为这个沙漠之城的兴起体现了美国精神,我却以为起码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来说,这里是一个用钢筋、水泥铸造的潘多拉的盒子,从打开的那天起,各种可怕的灾难、罪恶、痛苦就由此产生。
有人把胡佛水坝当作进入拉斯维加斯的大门,认为不了解胡佛水坝的历史就不能了拉斯维加斯,这是有道理的。先别说拉斯维加斯的电力全靠胡佛水坝提供,没有胡佛水坝拉斯维加斯就成了瞎子;看看水坝附近公路上残留的当年建坝工人住的破烂的帐篷,帐篷上还写着“old Las Vegas”,就知道赌城的故事该从这里说起。
胡佛水坝建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当时的美国总统胡佛建议由政府出资在这片荒无人烟的地方建造大型工程,拉动内需,增加水泥、钢铁等建筑材料的消费,为大批工人提供就业机会,还可有效利用科罗拉多河水发电、灌溉。1931年,胡佛总统主持水坝开工后,工地从当地山区招募5000名劳工,每日三班昼夜施工。赌博成了工人们工作之余兴起的一种群众性娱乐项目。男人们聚在一起无聊了耍点小钱,这本来是人类普遍的恶习。咱中国农民农闲时也会偷偷地扎堆赌博。更何况在沙漠中工人们的工作环境极其艰苦,报酬却很低,对管理者来说,工人们在帐篷里赌博解解闷都比流窜着商量罢工强。如果在中国,警察会每天拿着手电筒查赌,因为在新中国赌博是非法的,政府总在告诫人民赌博会毁掉许多人健康的人生,和吸鸦片一样吸食人的灵魂。内华达州政府却发现赌博是一条生财之道,政府成了最大的庄家,可以通过收税获得大量财政收入。正如内华达州政府所料,1931年将赌博合法化以后,世界各地的资本滚滚涌入这片不毛之地,许多人疯魔般提着一生的心血来到这里,有盖赌场的、盖宾馆的,有赌徒,不管这些人处于食物链什么位置,内华达州政府都轻易掏到了他们的钱。
从此,胡佛水坝以西不远处出现了一座奇特的城市。这座城市具有点石成金的神奇魔力,把全世界的财富都吸附到它永远干渴的躯体中。旧赌城、新赌城像沙漠中两朵巨大而鲜艳的罂粟,硬是在干涸的沙地上生长起来,美丽妖冶、神秘鬼魅,吸引了无数赌徒为它倾家荡产犹不收手。有人把拉斯维加斯叫作成年人的迪士尼,我觉得这种叫法是对人类童年梦想的亵渎。与其说拉斯维加斯的兴盛是人类实现了超凡想象力的结果,不如说它正体现了资本的罪恶、贪婪、血腥。资本家为了滚到尽可能多的钱,无视人类本该遵守的道义和法则,把无尽的贪欲裹上合法的外衣,诱惑人们走进心灵的迷途。《愤怒的葡萄》中关于资本的描述写得非常深刻:“银行和公司不呼吸空气,不吃饭,它们呼吸的是利润,吃的是资本的息金。要是得不到,它们就会死,跟你呼吸不到空气,吃不到饭会死一个样。”从拉斯维加斯机场到旧赌城到豪华的宾馆,到处都摆着老虎机,它们张着大嘴把放进去的钱连本带利一起吃掉。
在夜幕降临之后,在人类灵魂本该安睡的时候,拉斯维加斯却睁开了雪亮的眼睛。胡佛水电站的电力把拉斯维加斯照成一座光怪陆离的不夜城。在强烈电光的照耀下,游走在这个城市的人们轻薄得失去了重量。这里确实是有许多人在欣赏世界上最壮观的音乐喷泉,也有人驻足于世界最宏伟的天幕表演,还有人走在模拟的威尼斯天空下……但大家都心知肚明:到这里一定要赌一把。一把是多少钱呢?朋友给我讲过一个数学教授的故事。他退了休到美国看女儿,怀揣着积攒了一辈子的辛苦钱。第一次到拉斯维加斯和我一样,只是慕名而来。第一次坐在老虎机旁,他和我的手气一样,赢了10倍。当然我的赌金小,1个刀。他放进了100刀。他听到了金币长时间泉水般流淌的声音,打出账单,兜里一下子有了1000刀。那一天他满面红光地回去了,一个团的人都知道这个老头发财了。他倒不向别人炫耀自己的运气,而是告诉大家他的算术能力超过低能的机器。
以后他就跟这些低能的机器较上了劲。当他女儿发现他已经一文不名的时候,他还认为是自己哪里没算准,哪天算准了他就可以上财富排行榜了。他女儿坚决把他送回了中国。不幸的是他把家里的房子卖了又去了美国,又赶到了拉斯维加斯。好在他女儿在拉斯维加斯大街上找到他时,他身上还有一身体面的衣服。
我们最后用1个刀赢了2.5刀。弋舟后悔放钱少了,我给他讲了那个数学教授的故事。
赌徒故事讲得最好的还是茨威格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茨威格变着法写赌徒心态,其实就是一句话,对赌徒来说,除了赌桌,“整个世界,整个人类都熔化了。”赌徒已经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和大烟鬼一样,一条道走到黑,早已忘了信仰,忘了家人、朋友,更别提什么事业、爱情。烟鬼需要鸦片、大麻麻醉神经,赌鬼的眼中只有那些滚动的球。真正的赌徒已经不是为钱而赌,而是为赌而赌。只要手中有钱,就要在赌桌上变出更多的钱;即使没有钱,去骗、去偷也要变到钱回到赌桌,这就是拉斯维加斯财源滚滚的原因。
天下财富原本很多,我看过故宫、凡尔赛宫、枫丹白露……当时真把那些黄金、珠宝当作艺术品,一走而过,心中波澜不惊。可在拉斯维加斯,贴近的是摞成小山一样的百万美金,摸的是不经加工的巨块黄金,你真感觉财富离自己如此之近。那些罩着美金的玻璃就是台透明的老虎机,它告诉每一个经过的人,只要运气好,这些钱就是你的。随意走进一家宾馆,一层大厅一律打造得富丽堂皇,有些还把世界最优美的风景微缩到这里,衣着体面的服务员随时会出现在你的身边。在这个一切都显得那么舒适、得体、雅致的环境中,心中的欲望被吊得满满的:有了钱,把耳边哗哗流淌的老虎机中的钱挣入自己的口袋中,就可以永远享受这样的生活了。站在金色大厅中央,站在老虎机丛林中,人的精神像笼罩在鸦片的迷雾中,心中很容易幻化出老年浮士德的迷梦,以为看到了一生中最渴望实现的梦想,心中生出虔诚的祈祷:“时间,请在此停留。”命运的大门已经敞开了巨大的缝隙,金色的光线刺痛了人们饥渴的眼睛,多少人被眼前虚幻的光芒吸引住了,人生从此陷落在这里。
政府福利房里的孩子们
我住在工作的Anlbedy小学校附近的政府福利房里,这里的孩子们都属于这个学区。安顿下来以后美方秘书才告诉我这个房子的性质,并且说这里的孩子不太好,对弋舟的教育不利。不久我就发现小区里大多是黑人家庭,还有少数黑、白结合的家庭。到了篮球场附近,和弋舟差不多高的小子有和大孩子扎在一起抽烟的,里面还混着个别女孩。
弋舟到美国上七年级,相当于美国的初中二年级,在国内他该上小学六年级,还是个单纯的小学生呢。小区有一个他的同学,他们在班车上认识的。一天我们在小区里散步,正好碰到这个同学。弋舟给我们互相介绍,这个大男孩旁边还跟着个矮点的孩子,他们跟我点了个头就要走,弋舟非得陪着我,说以后再单独过来找他。第二天放学后弋舟又谈起他的这个同学,说他是个好人,可脑袋不太机灵,吃饭的时候总被同学折腾。一次吃饭的时候女生打架,把挤了一盘西红柿酱的色拉都扣在了他身上。“别人打架,怎么会弄到他呢?”我很奇怪。“要不然说他傻呢!我们都闪一边看热闹,就他坐在那儿不动,那些女生是故意的。”弋舟虽然进美国中学不久,但他很快习惯了学校的生活。他虽然看着一脸稚气,但块头大,个子在美国孩子中也算高的,所以不用担心他受人欺负。
一天弋舟回来说他的那个朋友说羡慕自己有一个好妈妈。那个孩子看到我们总在一起打球,而他自己的妈妈从来不搭理他。我问他家有几个孩子,弋舟说只知道那天遇到的是他的弟弟,他妈妈每天让他放学后带弟弟玩,所以他不能跟别人玩。“跟弟弟玩也可以跟别人玩呀。”我很自然地说。“他弟弟告状,他妈妈会处罚他。”显然弋舟也替他的朋友抱不平,他大人似的叹了口气。我想起那个孩子长相老实的面孔、有点木讷的表情,心里也为他难过。
我们住下来后不久,一天下午突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一群小黑孩。我让他们都进来。问他们有什么事。几个孩子抢着说话,我大概听懂了他们是Ambedy小学的学生,搞活动需要钱,出来募捐来了。一个小姑娘把捐款单塞给我,另一个姑娘一直瞪着大眼睛紧张地不停地说话,声音又高又尖。我看了一下捐款单,应该是校方提供给学生的,上面让写上捐款人姓名、联系方式。纸上已经签了好多人的名字,大部分人捐一个美元,个别的给两个美元。我拿出一张五美元给了那个不停说话的孩子。她拿到钱后一挥手说:“走啦!”转身匆忙往外撤。拿捐款单的孩子赶上她,从她手里抢过钱登记。别的孩子跟在后面呼啦撤退,我给最后的两个孩子一人一块糖,她们笑着道谢。
孩子们走了以后我猜想她们多大了?在哪个年级?一天上班我在学校门口遇到一个到我家募捐的孩子,她也还记得我,可能因为那天我对他们的“贡献”比较大。她有点腼腆地对我笑了,全没有在我家时严肃、紧张,甚至让人感到有点厉害的表情。我和一个美国同事谈到孩子们的募捐活动,同事说每学期孩子们都要自己搞一些活动,他们活动的经费是自己筹集的。富裕家庭的孩子有父母支持,我住的那个社区的孩子只能靠自己。“孩子们这样挨家挨户筹钱心理会有障碍吗?”“不会的,他们有人还到马路上去做点小事找钱呢。这是让他们接触社会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可是我总无法忘记那个不停地说话的孩子盯着我的紧张的大眼睛。
暑假我和弋舟在大花园的边上踢毽子。弋舟自己踢也就踢四五个,我们俩对着踢就能踢十来个。踢了一会儿我发现远远地有一个小黑孩盯着我们看,我觉得他像我的学生马多鸣,可是不敢认。在我眼里,许多老美长得太像了,随便瞎喊有时会很尴尬。那个孩子慢慢走近了,他隔着马路怯怯地喊:“王老师!”我高兴地跟他招呼,让他过来跟我们一起玩,他一下子活泼起来,高兴地穿过马路跑了过来。
在学校,马多鸣是个聪明可不太好学的孩子。他坐在第一排,只有做游戏的时候积极举手,学习时老趴在桌子上。美国孩子上课和中国孩子不同,弋舟上小学一年级时我去小学课堂感受过,孩子们要求手背后、笔直地坐着听讲,身体有点歪斜一定会被老师批评。弋舟因为纪律问题在小学阶段没少写检查。美国老师不能骂孩子。不能伤孩子的自尊心。像马多鸣这样趴在桌上的孩子算是听话的。还有像艾则恩那样老师一转身就跑到座位外边跳舞的、朱塞思那样自己站着抢着要当老师的,没有一个个有趣的游戏拉着他们学,像中国课堂那样正经上课不出五分钟就会乱成一锅粥。
每天又唱又跳地当了一学期小学老师,我也“返老还童”了。孩子们把我当成了大孩子,每天等着带他们做游戏。在家里,弋舟成了我的指导老师,他教给我一些自己在学校学到的游戏,还帮我甄别网上哪些游戏好做且有趣。弋舟在学校很怕老师,有时在路上遇到老师,一路走半天脸色才能恢复正常。我问过弋舟为什么那么怕老师,他说老师骂人太厉害了,骂完了还要写检查,有时检查还要拿到别的班去读。马多鸣可不怕我。他更不怕弋舟。他可能已经站在远处看我们半天了。他拿起毽子就踢,掉到地上捡起来再踢。踢了几个都踢不上脚,急了,像踢足球一样踹起来。我和弋舟都笑了,弋舟示范给他看,我帮他训练了几个假动作。他模仿能力很强,踢一个的动作很标准,可毽子还是往外飞。弋舟看得不耐烦,自己跑一边找松果玩去了。
我看马多鸣踢一个捡一回,踢得太辛苦,就教给他一个新的玩法,不只用脚踢,还可以用手把毽子托起来,这样他就可以用手调整毽子方向,手脚并用就容易多了。这一招果然很灵,毽子飞出去是总能被他用手救起来,他突然开始用汉语数出了声:“十一、十二、十三……”我很惊讶,平时课堂上以为他什么都没学会,看来他人趴着心还是在听讲。
马多鸣踢得正开心,一个小不点姑娘歪歪扭扭走了过来。以前我就看到过她一个人在马路上玩,我还跟弋舟说这么小的孩子在马路上玩,多危险呀!孩子矮,司机开车马虎看不见,孩子就到车轱辘底下去了。我还试着跟她说话,她说什么我也不懂。小姑娘虽然脸上很脏,衣服也脏,可真是个漂亮的浅棕色孩子。马多鸣说:“这是我妹妹。”他转向妹妹说了一串话,突然用汉语说:“你好!”他的小妹妹跟着说:“你好!”弋舟从松树林里跑出来说:“你好!”小姑娘又说了一遍,笑着坐在地上。这时马路对面的树林里又钻出一个有五六岁的姑娘,马多鸣用汉语说:“这是我的大妹妹。”他对走过来的姑娘又说了一串,姑娘用汉语和我们打招呼:“你好!”马多鸣骄傲地说:“都是我教她们的!”他把新学的技术展示给妹妹们看,两个妹妹都用崇拜的眼光看着自己的这个大哥哥。
我们玩得正高兴,孩子们已经不是“踢”毽子,而是用手“托”毽子,大孩子、小孩子有时撞到一块儿,乐得又笑又喊。街对面门口一个白女人冲着我们这伙快乐的人叫喊,马多鸣立刻成了个规矩的孩子,向女人介绍说:“这是我的老师。”我们互相点了下头算是打过招呼,马多鸣的妈妈转身进了屋。我问马多鸣平时说什么语言,他说他家人都说西班牙语,他爸爸是墨西哥人,妈妈是美国人。我关照马多鸣照看好小妹妹,不要让她在大马路上玩。他懂事地点点头,带着妹妹们回家了。
暑假我和弋舟在小区里玩,经常可以听到有孩子冲我们喊“你好!”他们或许是做游戏的时候跟小伙伴学的吧。一天我和弋舟走到大花园和森林之间的沼泽地附近,遇到一伙小“罗宾汉”,可能有四五个男孩,他们正在舞着大棍子“打仗”,看我们过来,小子们放下了武器。其中一个小黑脸喊“你好!”说自己是Amberly一年级的学生。他大概知道自己的脸太脏,怕我认不出他,扯过衣服摸了把脸,这下更成了张大花脸,别的孩子哄地一下都笑了。
夏天的晚上,我的屋子一到晚上就弥漫着一股烟味,楼前空地上聚着一伙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他们很晚了还在聊大天、吸烟。他们嗓门很大,笑声很大,和平时在公共场所看到的教养有素的美国人很不一样。他们总把自己的一辆烂车停在独自坐在门口说话的老头家门口。有时老头坐在椅子上,冲着另一把椅子哇里哇啦地说话,这伙人也堆在一起说话。我们在楼上看着很滑稽,两路人各说各的,毫不相干,距离却那么近。这时我想到那些可爱的小“罗宾汉”们,他们都是大自然的孩子、社会的孩子,却很少是父母疼爱的孩子,他们会在谁的引导下长大?长大了又是什么样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