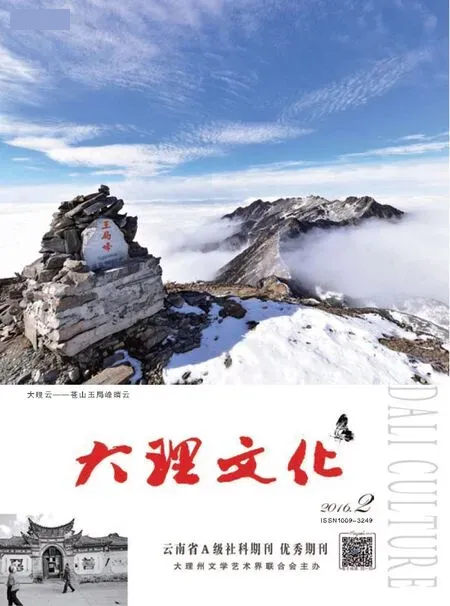光阴记
2016-10-27忆苏
●忆 苏
光阴记
●忆苏
一
入秋以来,一直在忙碌一件有意义的小事——为儿子十八岁生日准备礼物。
我把他出生以来有代表性的照片,一直保存在盒子里的乳牙,穿过的小鞋子,奶奶织的小毛衣,线条稚气的第一幅涂鸦,染满墨汁的第一幅书法作品,还有入小学后的第一本作业,第一张试卷……那些都是原先一直收藏在箱子里的成长痕迹,全部拍下来,做成一册小书,当作成人礼送给他。
翻出柜子里几大本记录了儿子成长时光的影集,一个个日子,随着一张张照片呼啦啦从光影之间回到眼前。
第一张照片,是还没满月时候拍的。一个肉呼呼的小婴儿,穿着粉色的小衣服躺在襁褓里熟睡。第二张,睁开了眼睛,很奇怪地看着为他拍照的爸爸,那时,他是不是在想,爸爸手里那个黑乎乎的东西,是不是可以尝一尝?然后是我坐在卧室的地毯上抱着小小的他。那时的我,身材变形,体重从九十多斤攀升到将近一百四十斤,圆圆的脸上笑容甜蜜。还有一张,是奶奶抱着他,刚退休就当上奶奶的母亲,满脸幸福。
孩子出生的那个秋天——1997年11月,我们这个居于小城南边绿树成荫的院子,所有人的心中,都开满了鲜花。一个小生命的到来,如一束光,照亮了我们的人生。
影集一页页翻过,这张里,他已经会爬,那张里,他学会了走路。第一次上公园,是在三个月大的时候,镜头里,妹妹抱着他在百鸟朝凤浮雕前开心地笑着。还有那张,小小的他包着花头巾,被我们放在刚买回的红陶大花盆里,手里举着一束鲜花,张着嘴巴开心地叫着。那脆生生的声音,如此地清晰明亮,仿佛昨天,仿佛刚才,就在园子里,就在葡萄架下,笑声如小羊咩咩,一步一晃的孩童,呼一下,就已经是十八岁的英姿少年。
一周岁,两周岁,三周岁……他小时候,我和他爸爸曾经约定,每年过生日,都到照相馆郑重地拍一张全家福。这件事一直坚持到他上小学,后来,琐事缠身没有继续。想来感到可惜。那些不可复制的时光,去了,就不再。
整理完照片,曾经的日子,伴着孩子成长的一天天,在心底过了一遍。那感觉,温暖,甜蜜,幸福,还有一丝淡淡的怅然。
那份惆怅,源于何方?
源于一种欣喜,一种不舍,一种无奈。从出生时五斤四两的小婴儿,到如今一百二十多斤的大男孩。从身长三十多厘米的小东西,到今天将近一米七的高个子。从第一个印下的八厘米的小脚丫到如今四十二码的运动鞋。十八年的光阴,在彼此的身上留下清晰的变化。小书的封底内页里那张我和他最近的合影,说明了一切。
八月的玫瑰园。远山,竹林、蓝天、白云、花海里相依的母子。当年被妈妈抱着的那个小男孩,满脸英气,搂着依旧长裙长发的妈妈,像一个英伟的男子汉。
岁月不是走来,是离开。
相册一页页翻过,照片里的小孩一天天长大,照片的场景也在一天天变化,越来越丰富。从小床上到推车里,从卧室到院子,从院子到了田野,从巍山到大理,到丽江,到迪庆,到昆明,到北京,场景一天天变化,孩子出行的脚步也一天天渐远。
步入青春年华的他,将会离开父母,去广阔的天地找寻精彩和梦想。而我们,会在他出生的园子里,种下绿草鲜花,让每一天,都如当年他到来的那个日子。
秋菊盛放,丹桂飘香。
二
一幅彩色旧照片,一直珍藏在我抽屉里。
鲜艳的色彩,灿烂的笑容,两个小女孩,红扑扑的脸蛋,嘴角上扬,眼睛笑成一弯新月,一派掩饰不住的无忧和天真。
那是我和表妹。地点,大仓照相馆。应该是1980年前后吧,我大概七八岁,表妹六岁左右。那时的小城刚刚有彩色照片。那照片的颜色,是要在冲洗时候上上去的。时隔三十多年,色彩依旧鲜艳,可见当时照相师傅的技术地道而纯熟。
那张照片,在当年曾经被放大当作广告,挂在大仓照相馆的橱窗里,像两个小明星。
每次拉开抽屉看到它,童年的时光,刹那之间就活了起来。
记忆里,八十年代的大仓是一个朴素却热闹的小镇,也是我们几姐妹的乐园。爸爸的妹妹,被我们称作孃孃。她那时应该是三十岁左右,带着两个女儿,也就是我的两个表妹在大仓工作。叔叔远在部队,回来的次数极少。孃孃非常疼爱我们姐妹两个,一到假期,就将我们接到大仓家里。那时的家,不过就是单位的集体宿舍。当时住过大仓照相馆的家属院,也住过供销社的大院。
我还记得当时大仓照相馆幽深的院子,低矮的房屋,还有一起住在大院子里的人家,那些人家的哥哥姐姐。记得孃孃年轻时的容颜。她长得像奶奶,瘦高个子,身材修长,一头乌黑的长发,编成发辫绾在脑后。穿着整洁,性情开朗。房间里,永远都是清清秀秀的干净,厨房里,一到吃饭时间就菜香扑鼻。
在我记忆里,孃孃是一个很会生活的女子。到今天,我还记得她房间门上的珠帘,记得她每天都在房间里点燃的一炷茉莉香。在那之前,我只在寺庙里看到过供给佛祖和家中供给祖先的香火。在那样的年代,清秀整洁的房间里一炷青烟袅袅的素香,还有飘渺的烟里淡淡的茉莉花香。如一幅永不褪色的经典黑白画面,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版图里。如今,我也焚香。每天清早,洗漱净手,点燃铜香炉里的沉香,然后心情愉快地出门上班。
如今的孃孃,已经六十多了。神采依旧,发辫依旧乌黑,每天下午都来家里约母亲一起散步。家中有好吃的,仍然挂着我们。照片里那两个脸蛋红彤彤的小明星,如今都已为人母。表妹从百货公司下岗后,自己开了一家服装店当起了老板,她性格开朗,主顾很多,在小城的古街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我每天上班工作,休息的时间几乎全部交给园子里的花草树木,交给一摞摞书册和一个个方块字。但是,每隔一段时间姐妹几个都要聚一聚。孩子之间也是感情深厚,在下关读书的儿子周末回家,一定要约上两个小表妹,出去溜达玩耍。
除了那张彩色照片之外,儿时的照片,几乎都是黑白的。小幅,可以放在小小的相框里。妹妹留着一幅我和她的合影,也是在大仓照相馆里拍的。我们身上穿着灯芯绒的外衣,领子上有绣花,头上都扎着小辫,辫子上有蝴蝶结。那蝴蝶结,一定是孃孃为我们扎上的。
母亲的老相册里,我小时候的照片最多。
母亲说,当年父亲隔三岔五就会带我到小城唯一一家照相馆里拍照。坐在椅子上的,骑在“大象”上的,穿着花裙子,小皮鞋,怀里还抱着一个布娃娃。那时的我,幸福得无与伦比。在七十年代的小城,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有这样的机会,能够留下那么多的照片记住童年。而我,幸运地拥有了。
父母对我的爱,用含在嘴里怕化了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记忆里,从小就有糖吃,有漂亮的花裙子穿,从来不用像周围的孩子放学还要去帮大人劳动。我就是一个在蜜罐泡大的孩子。所以,我对物质没有过强的欲求和虚荣,能从容淡定地面对生活里的人和事。这点,要感谢父母从小给我的生活。
一个人的童年记忆,会影响他的性格和今后的生活。
这话不假,童年的幸福,让我内心强大,豁达温暖地走在自己的人生路上。特别是中年以后,愈发能怀一颗慈悲之心,面对岁月里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甚至,每一朵小花。
三
一张黑白的旧照片,就是一段渐渐老去的时光,经典,永恒。不会褪色,在岁月的深处,一直都在。
照片里那个笑颜绽放的小女孩,如今也已步入中年。而带她拍下照片的父母,已经是古稀老人。
光阴带来的怅然,无时不在。
旧相册里的父亲,是那样的英俊。有几张特写,像电影明星一样。那时的他,多么年轻,神采奕奕,英姿勃发,眼神里满是希望和憧憬。母亲有一张照片最好,穿着花衬衫,半蹲着,长长的发辫,眼神清亮,笑意盈盈。那时,多好啊!年轻的岁月,年轻的父亲和母亲,年轻的生命,被一帧一帧的小照,定格在时光里。
那时,还没有我。我的姗姗来迟曾经为父母带来过无尽的烦恼。也是我的出生,让他们的生命,显得丰盈饱满而有意义。
妹妹和我相隔四岁。一起长大的姐妹俩,读书,上学,工作,结婚,为人妻,为人母。慢慢脱离了父母怀抱的我们,和父母的照片也越来越少。有一幅,一直珍藏在相册里。
那是新居落成后的院子里,一家四口站在花丛中。那时园子里的花可真多啊,全部是月季,红的,黄的,粉的,白的。和我现在后园里廊前一样。四十多岁的父亲母亲,略显苍老。在那样的年代,刚刚建起一大院新居的他们,付出的艰辛和劳苦,是我们现在很难体会的。照片里的我,正在读初中,妹妹还在读小学。满脸稚气的我们和人到中年的父母,还有那时的蓝天白云,绿树鲜花,被一双按动快门的手,定格在画面里。
那时的母亲,发辫依旧很长。那时的父亲,身材依旧挺拔。那时的天很蓝,花正开,云很淡,风很轻。花丛中的一家人,心底,有一种情愫像花儿一样绽放——那种情愫,叫幸福。
照片从不会骗人。岁月的记忆,在这样的一个个小框里,从不说谎。
这几年为父母拍下的照片里,暮年的苍老和曾经的年华对比鲜明。前几年,商量着让他们外出,去了一趟北京。看着照片里的老两口,让人想到那句很糙的话:岁月是把杀猪刀。
当年的父亲,英俊潇洒、风姿飒然的父亲,身材不再挺拔,背微微弯曲,脸上满是皱纹,曾经明亮深邃的眼神里,有了苍老之气。母亲的大辫子早就剪去了。微卷的短发夹杂着银丝。站在人群里,显得那样弱小。
——时间,最是无情。它将曾经那样英气的两个人,我的父亲母亲,变成一对暮年里的老人。
还好,还好。有那些照片,留下他们曾经的年华,留下我们永远珍藏的记忆。像珍珠,在岁月的贝壳里,磨砺出熠熠的光芒。
四
年华似水。
一幅照片,一寸光阴,一份记忆。翻开,曾经的旧时光,萦绕心间。
喜欢拍照的丈夫,这几年也添置了很多照相器材。从傻瓜胶卷相机,到现在的数码相机。索尼,尼康,徕卡,长枪短炮。经常随身带着,出门就放在车上。精彩的瞬间,美好的风景,在光影里定格,曾经的日子,在光阴里,活着。
去年春节,父亲兄弟姐妹一大家子四十多号人终于聚齐。几兄妹都已老去,我们九个表兄妹也已人到中年。三代人,相约一起在老家旧院旁的正觉寺里过年。一起拍下全家福。三代人,最老的,是父亲,七十四岁。堂弟的孩子最小,不到六岁,在昆明读幼儿园。堂姐的儿子最大,二十三岁,在杭州读大学。我们这一辈最大的是堂哥,比我大四岁,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最小的是堂弟,三十出头,靠自己的打拼,在昆明和大理都买了很多处房产。
镜头里,庄严的正觉寺大殿前,葱翠的柏树绿荫里,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坐在中间,膝下,蹲着一排天真可爱的孙男孙女,中年的我们兄弟姐妹站在最后。大家脸上,都写满了笑意和幸福,一派家和万事兴的融融景象。
那张照片里,父亲兄妹六人,缺了一个老大——姑妈。当时她卧病在床不能回来。在我记忆里,没有见过他们兄弟姐妹一起照的相片,如今也难以聚全。父亲和他的三个弟弟一个妹妹,安详地坐成一排,在儿女的镜头里,留下也许是他们的第一张合影,却已经是人到暮年。
然后是每一家都拍一组照片,担任摄影师的丈夫按动快门,为每一家都留下一份值得珍藏的纪念。
今年春天,我的园子里,花开得好极了。前庭的杜鹃绚丽得一塌糊涂,后园水池边那株桃花灿然盛放。我们一家八口的全家福,和满园花儿一起定格在镜头里。
那天,春日的阳光恰到好处地晴暖,廊前的花儿恰到好处地盛开,天正蓝,风正清,云正淡,花正开——一切,都恰恰好。
父母坐在中间,两旁是儿子和侄女,我们姐妹两家四人站在后排。身后,是青石贴就有落地玻璃窗的房子。旁边,是盛开的鲜花。那一刻,时光深处熟悉的场景,一下子活了起来。
今夕何夕?
还是那年的园子吗?还是那年的一家人吗?
光阴里,一切都在改变。
——却又好像,什么都不曾变过。
五
母亲的旧相册里,有一张古老的旧照片。
照片上,一个仪态端庄的小脚女子,身穿民国时期的衣裳,宽袍大袖,坐在椅子上,手里还有一支长长的烟管。身旁,一个头戴瓜皮帽的男孩子安静地站着。一盆幽兰,在高高的几上盛开。母亲说,照片上的女子是爷爷的母亲,也就是我的老祖母。老祖母一生只生育了爷爷一个独子,很年轻就守寡的她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那张泛黄的老照片,应该是家中最老的一笔关于家族的记忆了。
还有一张全家福,很多年前姑妈一家回来时照的。那时的我们还是孩子,爷爷还在,穿着对襟盘口的蓝布衣衫,坐在正中间(奶奶去世得早,在我才七岁那年就离开人世)。以爷爷为中心一字排列开的,是他的六个儿女,以及儿女们的孩子。照片上,父母一辈正是壮年,我们姐妹兄弟,还是青春葱茏的少年时光。和去年拍下的照片不同的,是旧相片上的人,有四个已经不在了。
先是爷爷,养育了六个儿女的老人,一辈子在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爷爷,在大年初三的夜里无疾而终,走时,九十三岁。
然后是让人猝不及防的,壮年的表哥,姑妈的小儿子。记忆里永远幽默感十足,活泼好动,最得我们喜欢的表哥,在一场应酬豪饮回家后,悄无声息地躺在沙发上走了。
然后是四婶,不到六十,生病医治无效,也走了。
到我今天写下这些文字之时,姑妈刚离开三个多月。一辈子勤俭持家的姑妈,晚年被糖尿病折磨,也与今年初夏离去。来不及等八月份抱上重孙。

爷爷和奶奶生前的照片,被放在相框里,挂在二楼一间专门设计好的祖宗房里。父亲兄妹几家,家家如此。不管房屋如何设计建造,装修如何洋气时尚,都要留下楼上的一间供奉祖先的牌位,和爷爷奶奶的照片。
每到初一和十五,母亲就会到房间里,点燃盘香,放上大悲咒,给瓶子换上鲜花柏枝。每逢爷爷奶奶的忌日或是节日,还要烧纸钱,给爷爷奶奶供上他们生前最爱吃的饭菜。
我经常出入那间屋子。清扫,整理,换上鲜花。还在门口养了一罐碧翠的绿萝。
每次进出,抬头看照片里,奶奶笑容满面,满眼慈悲。爷爷的皱纹像一朵不会败的花儿,永远地开着。
一切,好像都还在。
爱。亲情。血脉。温暖。回忆。
还有,光阴。
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