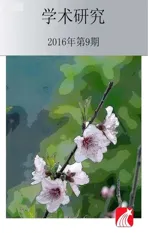福利国家社会政策发展:资本、劳工与国家集中化互动逻辑*
2016-10-17彭华民
彭华民 黄 君
政 法 社会学
福利国家社会政策发展:资本、劳工与国家集中化互动逻辑*
彭华民 黄 君
社会政策发展逻辑是政治学、社会政策学、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领域的重要议题,同时也是分析福利国家社会政策发展的重要路径。在多种社会政策发展逻辑的理论观点中,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独树一帜。资本积累和劳工抗争始终是福利国家中不可消除的矛盾冲突以及共生两面体。特定阶段与福利国家环境下的资本积累、劳工阶级斗争以及国家结构集中化是社会政策发展的重要动因,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促进了现代福利国家制度的发展完善。福利国家社会政策发展逻辑研究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社会政策资本积累劳工斗争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福利国家
一、新马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理论研究背景与意义
中国进入了注重民生发展福利的制度建设新时期。2004年中国共产党把和谐社会作为政党建设和社会发展目标,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 2006年,胡锦涛在中央党校专题研讨班上进一步阐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政治要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社会要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人民幸福与社会和谐需要国家提供更高水平的社会福利。2014年,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不断完善和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把改革的红利转化为发展新动能和民生新福祉。[1]
新时期的中国经济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等发展水平的新时期。中国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2009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2007年中国GDP最终数据比上年增长13%,GDP为257306亿元。[2]2007年的人均GDP已经达到2800美元。[3]国际通行的标准是把人均GDP3000美元作为中等发展水平的标志,而其的社会福利含义是人均社会福利接受水平的提高。因此,经济发展为社会福利制度创新提供了物质基础。西方福利国家在与中国现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同的时期,就在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方面进行了多项创新: 英国早在1948年,在人均GDP还不到1000美元时,就宣布建成了政府承担社会福利提供责任,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民生的福利国家。美国也在人均GDP大大低于我国现有水平的1935年制定了《社会保障法》,不断发展了多个社会福利项目。日本1965年的人均GDP为1071美元,但在1947年就通过了《儿童福利法》,1951年颁布《社会福利事业法》,1957年就设置老人年金和母子年金制度。福利国家的经验说明,社会福利体系发展创新是中国作为一个中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后的首要任务。近十多年来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前后,福利国家都在寻找社会福利适应性发展道路;东亚国家地区建设嵌入本土的福利社会;在社会福利理论研究领域,有多个具有创新性的理论出现。社会福利已不是消除社会问题、减少贫困的手段,而是作为社会投资、积极社会建设、伙伴关系、社会融入、社会质量、人类幸福的制度手段。批判性地借鉴福利国家理论和发展经验,是发展创新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势在必行的工作。
20世纪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实践之一就是建立了福利国家,宏大的社会福利制度解决或化解了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社会政策是社会福利制度安排的核心,并因此成为一门重要的学科。20世纪70年代前关于福利国家社会政策发展逻辑的主流观点有:贝弗里奇的社会问题逻辑、蒂特马斯(R. Titmuss)等的工业社会发展逻辑、马歇尔(T. H. Marshall)的公民权(citizenship)逻辑、高夫(I. Gough)等的新马克思主义逻辑、源于帕森斯(T. Parsons)的社会制度功能论逻辑等。人们用这些逻辑来诠释社会政策产生的动因,众说纷纭。一般的观点认为社会福利制度发展是福利国家最重要的标志。福利国家是为其成员福祉承担法定的、正式的和明确的责任制度的表征,它的发展是解决市场经济自主运作导致的社会问题重要标志。福利国家被认为是民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理论高点和政策标杆;是大多数国家追求社会公平与公正,消除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排斥,提升社会民众生活质量的理想。社会一般采用的社会政策发展的工业逻辑,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个体在市场之手的控制下逐渐成为人性异化的营利工具,一切不符合竞争需要的个体社会成员被市场抛弃,由此造成底层社会弱势群体和严重社会问题,甚至引发大型社会动荡。福利国家采取一系列社会政策应对工业化社会造成的个人收入损失或生活无着问题,促进了福利国家的发展。但这样的分析未能深入到社会政策嵌入的国家结构和社会结构中,未能发现社会政策发展的逻辑,从内容和形式都比较表面化。
在福利国家理论中,以继承马克思的批判主义方法为代表性标志的新马克思主义异军突起,其观点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理论。新马克思主义在福利国家和社会政策领域中发展很快,以高夫(I. Gough)、欧费 ( C. Offe) 、欧康纳(J. O’Connor)、 金森伯格(N. Ginsburg)、费格深(I. Ferguson)等人为代表的学者在马克思阶级与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矛盾等理论概念基础上展开各自对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的研究,形成了社会福利领域中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另外,新马克思主义者出版了《社会工作与福利国家批判丛书》(Critical Texts in Social Work and Welfare State,Macmillan Press)对福利制度、健康政治、社会工作、女性主义、政治经济、阶级、工会运动、意识形态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这是新马克思主义将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社会福利服务、社会工作、社会政策实践结合的一套丛书。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多部论著成为这个领域的经典。其中《失能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Disablement)于1990年出版,1991、1992、1993年多次再版。《福利国家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elfare State)1979年出版,于1980 年(两次)、 1981年、 1982年、1983年、1984年、1985年、1988年、1989年、1992年等再版,被翻译为六种文字。《人类需要》(A Theory of Human Need, with L.Doyal) 1991年出版后被翻译为三种文字。新马克思主义不单单是在理论上进行论证发展,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层面上也进行了讨论。其中批判性社会工作(Critical Social Work)形成过程中受到的影响不仅仅来自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还有以德国为中心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性理论。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自己立足于马克思传统的理论假设,又未局限于经典理论,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更加开放的研究领域。他们继承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4]新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领域的兴起的重要原因,一是福利国家存在各种不可解决的矛盾;二是支持福利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需要更新,三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主义精神有助于他们的理论发展。
社会政策的发展不仅与福利国家的发展进程紧密相连,而且与人民福祉提升密切相关。因此,重新审视与深度分析新马克思主义对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发展动因以及其相互作用逻辑研究,不仅有利于认识中国社会政策发展的动力机制,更有助于促进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鉴于相关理论众多,放在一起研究未免失去本真,本文主要基于福利国家的政治经济视角,在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讨论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发展逻辑。
二、社会政策发展初始动因:资本积累与劳动力再生产
社会福利制度发展是福利国家最重要的标志。福利国家是为其成员福祉承担法定的、正式的和明确的责任制度的表征,它的发展是解决政治和经济自主运作导致的社会问题重要要素。[5]福利国家被认为是自由民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高点;是大多数国家追求社会公平与公正,消除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排斥,提升社会民众生活质量的理想。一般对社会政策发展逻辑的理解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个体在冷酷的市场中逐渐成为营利的工具,一切不符合竞争需要的个体社会成员被无情地抛弃,由此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不同的国家采取一系列社会政策措施应对工业化社会造成的收入损失或生活无着的社会问题,促进了福利国家的发展。[6]这样的分析未能深入到国家结构和社会结构中,未能发现社会政策发展的内在动因,过于简单。
新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政策发展动因的论述基于古典马克思主义资本积累的观点。古典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积累即把剩余价值当作资本使用,或者说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资本积累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体现。剩余价值是资本积累的源泉,是资本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7]资本主义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资本来维持再生产,以期获得更多的利润。在马克思看来,提供资本积累的剩余价值并不是如资本家所言是通过资本获得的,而是工人的劳动创造并被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因此,不断扩大的资本积累意味着资本家占有更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家为了能够持续进行资本积累,一方面需要不断占有更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同样需要保证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力的供给,需要在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等方面投入更多资本。资本主义尽其所能地榨取剩余价值、积累资本,严酷剥削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冲突,工人的反抗此起彼伏。因此,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代表资本家阶级的国家不断出台社会政策来保证工人的权益,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是化解反抗冲突的重要方式。这促成了英国等国家不断完善针对民众的社会福利制度。1948年,英国工党政府根据贝弗里奇报告进行社会保障立法,宣布英国在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建立福利国家,开创了国家保障资本积累的政策化机制。
新马克思主义者高夫将福利国家界定为:运用国家力量去修正劳动力再生产与维持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非工作人口的正常生活的制度体系。现代国家的福利活动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人类社会得以维续的劳动力再生产。资本主义制度下有两个基本机制确保在生产过程的执行。第一,(全部种类的)工人的劳动为他们赚取到一份工资或薪资,藉此他们能购买消费品与服务;第二,家庭更进一步地生产着一系列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这主要由家庭主妇来生产,而且主要以服务形态出现。[8]这两种基本机制能够持续补充保证劳动力的再工作能力。现代福利国家透过多种方式介入劳动力再工作能力补充的过程:建立保障个体社会安全的体系,促进人们的消费数量和消费能力,保障劳动力再生产的物质供给;国家通过管制人们购买具有使用价值的商品,保障使用价值物品的供给与满足;国家资助或提供某些特别的物品与部分服务,保障非工作人口的基本生活;国家通过直接服务的提供,确保有使用价值的服务落实与发挥效用。
福利国家通过建立一系列家庭津贴与社会保险给付制度来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使其具有足够的人力资本投入到生产实践中。需要注意的是,仅仅注重劳动力再生产的量还是不够的,要保证资本主义利润的积累,还要注重再生产劳动力的质的问题。在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稳健的人格结构和特征、良好的工作能力和工作动机、行业自律规范等等是再生产劳动力的质的体现。福利国家大力发展保证劳动力再生产质量的社会政策,推动各种类型的教育、开展社会工作服务、进行人力资本开发和发展等方面的福利服务。除了保证劳动力再生产外,还需要注重非工作人口的生活福利保障。所有的社会都有许多无法通过自己的工作来维持生活的群体,诸如儿童、老人、病人及残障人士等。这些非工作人口中,最主要的是儿童和老人。儿童是国家的未来,也是潜在的劳动力,几乎所有的社会政策都强调加强家庭养育儿童的能力,不同的社会都发展出相应的机制,将部分社会发展成果转移给这些群体,这些措施和机制都在不同程度上地促进了社会政策的发展。
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扩大,资本不断在社会政策领域形成新的需要,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出现的四个发展和转变趋势,推动社会政策的重大发展。这四个发展和转变包括:第一,快速、无序的工业化发展导致劳动力工作环境恶化,许多国家相应规定了工人的工作时间及工作条件,对于在工作中受到伤害的补偿方案逐渐形成,促成了社会政策的最初形式。第二,资本的发展客观上促使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受雇于资本,劳动力个体需要面对年老、生病和失业等多种紧急情况,催生社会保险政策。第三,社会分化不断加剧,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致。社会分工的发展导致劳动力市场对新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促进了高等教育及大众教育政策的发展。第四,城市的发展催生了对公共住房及公共健康的需要,政府采取多种形式不断满足公众的住房和健康需要,并将其以社会政策的形式固定下来。[9]
由此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新生产方式的变革,迫使资本主义国家采取更加具有针对性的社会政策措施回应资本积累过程中出现新需要,而不断膨胀的福利需要必然会导致国家财政开支增大,进而造成福利国家财政危机。新马克思主义者欧康纳(J. O’Connor)在其所著的《国家的财政危机》中指出,国家必须尝试去维护或创造使有利可图的资本累积成为可能的各种条件,但也同样需要去创造维系社会安全和谐所需的各种条件。[10]这是两种相互矛盾,但又必须同时给予满足的需要。一方面,资本的积累(accumulation)有助于促进福利国家的发展;另一方面,社会的安全体系建构及社会和谐的稳定维护又是保证福利国家资本积累合法化(legitimisation)的重要途径。福利国家通过制定一系列相应的政策来调和积累和合法化之间的矛盾,双重影响并促进了社会政策的发展。
三、社会政策再发展动因:劳工抗争性斗争和国家集中化
福利国家并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社会福利专家和资本利益集团制造的产物,而应该理解为一种抗争性政治展开过程。劳工阶级的反抗和斗争是促进福利国家社会政策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工人阶级与资本家两个相互对立的阶级,资本家掌握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而工人阶级只有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获得生活来源,这种相互对立的阶级利益是资本主义矛盾的根源。劳工阶级是资本创造的核心力量,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他们并不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甚至连作为劳动力的自身也处在资本家阶级控制的范畴。资本家与劳工阶级处于既斗争又依赖的关系中,资本家的扩大生产与资本积累的增加需要劳工阶级的努力工作,劳工阶级的生活需要依靠给资本家出卖劳动力来维持。这正是资本主义阶级矛盾和冲突的根源所在。在这一冲突阶级关系过程中,福利国家既需要代表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考虑资本的积累和发展,同时又必须面对劳工阶级与资本家之间的抗争与冲突。为维护资本家的资本积累,同时又要保障劳工阶级再生产的能力,形成国家借助社会政策的形式调和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的格局。
福利国家为了削减市场施加给资本身上隐藏的压力,同样会考虑会从外部即社会政策对这一矛盾进行干预。因此,劳工阶级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为自身争取了劳工条件改善及自身发展的福利措施,但是这些福利政策却间接促进了资本主义建立更加稳健的、更加隐秘的剥削。资本的积累进一步加强,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强化。这个事实的本质在于,劳工阶级既是资本生产的一个要素,同时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类,需要争取提升他们生活水平以满足需要。尽管有福利国家社会政策发展,但劳工阶级的抗争仍然层出不穷,特别是在一些大型的工厂企业,这种类型的工人斗争更加频繁。这是因为大型工厂的工作场所使得劳工阶级成员能够集中在一起,他们的工作逐渐走向集体化,因而发展出他们得以组织和行动在一起的能力。虽然工人的集体组织通常只是着重在工作场合或某种工业、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和社会控制议题,但它偶尔也会通过全国性的大罢工导致整个国家政治的波动。如2006年3月由于英法两国社保制度的改革同时引起工人大规模游行示威与大罢工事件,迫使政府部门进行妥协让步。[11]
另一个关键的内容是福利国家中抗争性斗争——劳工阶级斗争日益被整合进政治竞争和竞选过程中。社会政策已经成为一种政治选举的工具,将有投票权的劳工阶级逐渐整合到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争取组织化劳工运动做出某些让步。如英国工党是劳工阶级在议会的代言人,他们通过依靠工会的力量,促进了工党的壮大。随着众多劳工阶级政党的成长和发展,福利国家中的资本家明显感到巨大的压力,这迫使原有的代表资本家与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联合发展起来。虽然劳工阶级的斗争为争取福利给付权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因为所有的社会福利都同时含有条件的给付(provision)和社会控制(control)要素,正是因为这些社会政策的实施,劳工阶级进一步被资本家所控制,资本家获得更大的资本积累和利润。因此,福利国家中抗争性斗争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结局:不断增加的社会福利同时发挥着赐予利益及施加制裁的双重功能。
社会政策的发展不仅仅是受到资本积累和劳工斗争的拉动,具体细分其还受到阶级冲突的程度尤其是劳工阶级斗争的强度和形式的影响;以及福利国家政府制定与执行政策以确保资本主义社会关系长期再生产的能力的影响。但这两个因素对不同类型的社会政策影响不尽相同。阶级冲突的程度更多影响到涉及劳工阶级自身权益方面的社会政策,而在保证资本主义长期再生产能力的因素直接影响以家庭为单位的各种社会政策的出台和实施。然而,同样也存在资本家与劳动者同时要求国家在社会福利领域的更广泛地进行干预,即资本家与劳工阶级具有一致的利益促使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的发展,如医疗卫生健康保险的出台和实施。劳工阶级与资产阶级对待某些政策的发展态度是一致的,合二为一的动因能够有效促进这种类型社会政策的发展。对于劳工阶级而言,任何能够减轻其生活困境或是修正市场力量的盲目运作的政策,都会受到欢迎;而对于资产阶级而言,由于某些社会政策能降低劳工阶级的不满,政策提供额外的工具来整合与控制劳工阶级,因而也获得经济或意识形态上的好处。[12]
抗争性斗争和阶级冲突并不足以解释影响社会政策发展的全部,社会政策的发展同时还与日益集中化的福利国家结构互相影响。在社会政策发展中国家结构出现更多集中化。集中化程度不同的国家结构对社会政策发展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国家通过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来保存资本主义的利益关系,以对抗劳工阶级的利益。即有些政策是源于资本积累的结果,被用来满足资本的需要;有些政策是资产阶级中具有远见的代表人物推动的,他们察觉到国家必须实现“再生产”功能的需要,因为与劳动力市场相互作用的社会政策一旦制度化,它必然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深刻的影响。在资本主义国家结构范畴之内,国家凌驾于个别资本“派系”的短期、个别的利益之上,以便照顾整个资本的长期利益,形成福利国家结构的集中化。这集中体现在一些反对资本主义、维护劳工利益的社会政策得以发展。集中化的福利国家结构不仅影响着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反过来,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又进一步强化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权力,同时也影响福利国家合法性建构。不同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结构的集中化程度不同,相应的社会政策对象、覆盖面、福利提供内容也不一样,这种差异性的结构影响着不同福利国家的政策实践,[13]形成不同类型的福利国家。
二次世界大战后,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增加对经济发展的干预,社会政策的发展受到国家角色普遍扩张的影响。在工业领域,伴随着国家、资方与劳工的三边协商制度的确立和发展,社会政策制定的委员会作为控制工业冲突和确保企业与工会之间重要的协议的工具,促成英国国家在战后积极地扮演福利国家的角色。由于二次世界大战特殊形势对劳工抗争行动势力的强化,以及劳工抗争运动进一步刺激国家的集中化,在福利国家中出现新的社会立法以保证劳工和工会的权益。[14]随着战后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繁荣,以及国家干预的角色日益增强,尤其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福利国家特别是英国等典型福利国家经济开始出现衰退,失业等社会问题突出,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适度干预角色重要性日益凸显。这些问题因素与传统的动因混合,形成社会政策发展的综合动因。适度干预的社会政策出现新趋势,如与贝弗里奇的社会安全传统的决裂、先前的住宅政策的逆转、高等教育的扩张等等。而这些改变的背后,则是资产阶级与劳工阶级两个势力、资本积累与抗争行动不断交互作用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后,福利国家重新认识到社会政策对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并着手进行新改革,通过引入工作福利制度(workfare),在政府和市场之外寻求新的福利资源供给。
四、新马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理论的发现和借鉴意义
艾斯平-安德森(G. Esping-Andersen)认为,因为经济现代化撕裂了原有的社会整合制度,社会政策处于社会整合要求的独特张力之中。西方国家发达的福利制度为社会重新整合提供了可能。[15]新马克思主义学者高夫等则采用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下影响社会政策发展的因素,以更加整合的视角剖析了社会政策发展中受到资本积累、劳动力再生产、劳工抗争、国家结构集中化等多重影响因素(图1)。

图1 影响社会政策发展的因素与政策发展逻辑
首先,社会政策的发展动因来自特定阶段与国家环境下资本累积、劳工阶级斗争以及集中化的国家结构。资本通过特定的方式不断扩大再生产,进行资本积累,资本扩大生产方式使对劳工阶级的剥削日益加重,因而产生了劳工阶级与资本家之间抗争性斗争。代表资本利益的国家为了缓和资产阶级与劳工阶级的利益冲突,出台相关社会政策对财富进行再次分配,在一定程度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随着工会组织的劳工斗争愈演愈烈,资本积累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冲击,国家通过社会福利给付对劳工阶级斗争的干预控制愈加明显。越来越多的工会和劳工阶级政党领袖被整合进国家管理层之中,福利国家结构出现集中化趋势。资本累积、劳工阶级的斗争与集中化的福利国家结构共同促进了社会政策的发展。
其次,劳工阶级的抗争性斗争为争取提高社会福利给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同时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敏锐地察觉到,所有的社会政策与福利提供都同时含有行动控制与福利给付的双重要素。社会政策发展一方面有效改善了工人的工作生活状况,保证了劳动力再生产的环境和条件;另一方面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又给资本积累提供了基础。特别是代表资本利益的国家通过出台相应的社会政策及社会服务开展,不仅有效缓解劳工阶级的斗争,同时也进一步控制了劳工阶级,资本家获得了更大的资本积累和利润。
最后,新马克思主义研究清楚地揭示了福利国家内在矛盾与社会政策动因之间互动的关系逻辑。福利国家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福利国家需要对市场力量的盲目运作施加社会控制,推动社会政策发展,提供福利给劳工;另一方面,福利国家又需要运用压制与控制手段,使人们服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利益要求。[16]劳工阶级的抗争性斗争使得“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与新马克思主义观点相呼应,欧洲知识分子如皮埃尔•布迪厄(P. Bourdieu)、尤尔根•哈贝马斯(J. Habermas)以及雅克•德里达(J. Derrida)都主张通过社会运动(包括劳工阶级斗争)来捍卫“社会的欧洲”。[17]如果没有劳工阶级斗争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运动,社会政策是无法实施的。
社会政策发展动因研究对于中国社会政策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中国社会分层以及贫富分化的矛盾冲突也是中国社会政策发展的动因。我们既要通过各种社会政策制度的实行满足和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同时又要控制和维护资本良性积累过程。帮扶社会下层,调节社会上层,促使形成更加公平、更加合理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其次,正确认识中国农民工以及其他群体的抗争性行动,以及近年来出现一系列由于分配制度不完善而导致的群体性事件。国家在福利供给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有责任为全体公民提供普惠型福利。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资本积累日益增加,社会福利政策在社会建设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再分配角色。国家需要重视关乎民生的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既要强调在福利制度建设过程中国家作为福利提供主体的责任回归,警惕由于国家福利责任的退出导致贫富分化的状况,同时又要看到这一过程中国家所面临的挑战。最后,探索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组合式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从福利国家社会政策实践可以看出,与国民经济增长相适应的福利水平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能够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新时期中国社会福利政策制度建设既要考虑满足社会成员的福利需要,同时又要考虑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18]国家将社会政策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手段,化解社会矛盾,减少抗争性冲突,促进社会建设,提升大众福祉。
[1]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政府工作报告,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guowuyuan/2016-03/05/content_5049372. htm,2016年3月5日。
[2][3]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第37、38页。
[4]王卓祺、邓广良、魏雁滨:《两岸三地社会政策:理论与实务》,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7年,第67-70页。
[5][德]弗兰茨-克萨韦尔•考夫曼:《社会福利国家面临的挑战》,王学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3-14页。
[6]周弘:《福利国家向何处去》,《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36-637页。
[8][12][13][14]高夫:《福利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古允文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5年,第68、97-98、94-96、105页。
[9]彭华民、张晶:《新马克思主义论福利国家内在矛盾与重组》,《国外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10] James O’Connor, The Fiscal Crisis of the State,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1973,p.87.
[11][加]R•米什拉:《社会政策与福利政策——全球化的视角》,郑秉文译,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年,第184-188页。
[15][丹]艾斯平•安德森:《转型中的福利国家——全球经济中的国家调整》,杨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页。
[16]彭华民等:《西方社会福利理论前沿:论国家、社会体制与政策》,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第92页。
[17][英]贾森、安奈兹等:《解析社会福利运动》,王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3页。
[18]彭华民:《中国组合式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构建》,《学术月刊》2011年第10期。
责任编辑:王雨磊
C913
A
1000-7326(2016)09-0054-07
*本文系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0JZD0033)和国家社科重点项目(11ASH009)的阶段性成果。
彭华民,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与政策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黄君,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江苏 南京,210023)。